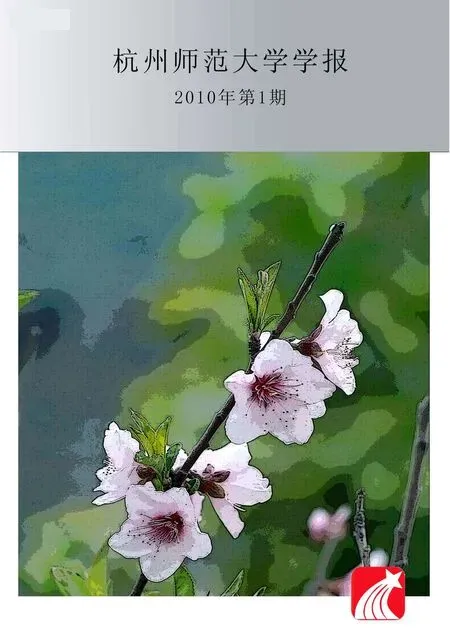“性命”怎么和“天道”相贯通的
——理学家对孟子核心概念的改造
杨儒宾
(新竹清华大学中国语文学系)
“性命”怎么和“天道”相贯通的
——理学家对孟子核心概念的改造
杨儒宾
(新竹清华大学中国语文学系)
主流理学的主要议题集中在天道性命上面,“天道”是形而上学的语汇,“性命”则是心性论的语汇,理学思想中的形上学命题大抵是心性论的延伸,两相比较之下,心性论的问题更为根本。理学家一般都认为其心性论思想来自《孟子》,这样的溯源有文献及哲学理据的双重理由。但笔者认为理学家从《孟子》处借得诠释的正当性时,事实上已作了语义的转换工作。孟子的“性善”与“良知”两个核心概念原本只是纯粹的心性论语汇,理学家将它们扩充到形而上学去,天道性命因此相贯通。理学家的解释有哲学的理由,它可释为原语词蕴义之朗现,但这种朗现也可视为跳跃,其内涵已非原始语义所能拘束。
孟子;理学;良知;性善;性命—天道
一 前言:人性论或性论
《孟子》一书在唐代中晚期前并未受学者太多关注,但从韩愈、李翱以后,经北宋诸子张载、二程与王安石等人共同的努力,其地位已然上升至“经”。*孟子地位的变迁是个很显眼的文化现象,周予同有“升格运动”之说,参见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928-930页。自从朱子将《孟子》一书与《论语》《大学》《中庸》并列,视为道统核心的一环,并编成《四书集注》之后,《孟子》这样的“新经”更取代了原有五经的地位,成为八百多年来国人意识构造核心的因素。孟子地位在这短短不到150年*150年是笼统的估量,我推算的依据如下:孟子的地位在朱子完成《四书章句》时已告确立。朱子终其一生都在改写《四书章句》,其过世时间在1200年,这是时间的下限。理学系统中,张载、程颐首度提出明确的超越的人性概念,这是孟子学的一大突破。张、程两人活动的时间主要在11世纪:1050年,张载30岁,人届而立之年;程伊川18岁,刚以《颜子所好何学论》著称于世。用最宽松的标准,他们提出超越的人性概念不会早于此时。从公元1050年到1200年,差不多一个半世纪。之间所以发生如此戏剧性的变化,是个颇饶思想
史趣味的课题。很明显的,此书的性格在这150年间已急遽突变,其内容被提升到与当时主流的价值相关,而且还是构成此主流价值概念的典籍。笔者认为关键性的因素是此书成了“性命之书”,孟子成了传“性命之学”的学术巨人。
“性命”一词由“性”与“命”合成,依照理学家使用这个词语的习惯,“性”与“命”皆有双重的意义,一指向先天的向度,一指向后天的意义。就前者而言,“性”是“义理之性”之类的意思,“命”则可解读成“义理之命”;就后者而言,“性”是“气质之性”之谓,“命”亦是“气命”之类的表述方式。*陈淳《北溪字义》(台北:艺文印书馆,1996)云:“命一字有二义,有以理言者,有以气言者。”(卷上,第1页)又云:“气质之性是以气禀言之,天地之性是以大本言之,其实天地之性亦不离气质之中。”(卷上,第11页)两种性或两种命的分合是理学传统的大论述,但自然的性命之上另有先天一层的境界,此义大抵为主流理学家所共许。理学的核心要义可以说都和处理“性命”的问题有关,所以这门学问可以称作“性命之学”。性命之学的问题,笔者拟另文讨论,此处姑且提个纲,以为过门。
理学家“性命之学”的思想来源是《孟子》与《中庸》《易传》。《中庸》《易传》比起儒家其他经典,历代传承的谱系比较清楚。但论及核心概念的理解,理学家和汉唐儒者的解释迥异其趣,两者的解释几乎是断层的,这当中关键性的因素乃是本体论观念的介入。由于汉唐和宋明的解释南辕北辙,所以两相对照,异同易显。《孟子》的情况不太一样,由于《孟子》的核心思想从两汉到隋唐,几乎都得不到善解,他们诠释出来的哲学涵义都不强,所以底下行文,笔者不再以汉唐与宋明作对照,而是以《孟子》的原始文本与理学家的观点相互对勘,试图指出后者所作的诠释学观点之转移。
理学家对《孟子》一书最感兴趣的部分是它的人性论,说得更明确些,也就是“性善论”。“性善”是孟子学的核心概念,也是宋明理学家共同接受的理论预设,伴随着性善说而来的概念是“复性”。我们读理学家著作,一再看到“复性”一词,“复性”不只是江右、东林、蕺山诸学派的学说宗旨,事实上,它可视为理学各宗派共同接受的核心概念。“复性”一词顾名思义,是“恢复本性”之意。问题在于什么样的“本”?“本”是虚义字,“本”落在意识层或超越层,其意义大不相同。“本”义难定,如何复其本性?此事遂也有各种解答。
本文将试图说明:孟子所说的性善论乃是人性论的语汇,他没有将此词语扩充到人文以外的领域上去。理学家不然,他们所说的性善论虽以人性论为核心,但范围不仅于此,而可遍布于一切存在界。所以他们的性善论与其说是人性论的语汇,不如说是性论的语汇。而且此性如果是超越的(所谓的先天),那么,主体当有一特殊的直觉能力,才能契近此超越的主体。庄子说“无知之知”,佛教言“般若智”,熊十力言“性智”皆属此义。理学家当然不是每个系统都期望人有此特殊的直觉洞鉴,朱子即不喜道及任何类型的直觉洞鉴作用。但大致说来,有超越的性体预设的理学体系一般倾向于主张:人人皆有洞鉴性体这种直观的能力,理学家称此直观作用为“德性之知”或“良知”。然而,“良知”在明代心学体系中,被视为洞鉴本体的直觉之知的代表性概念,在《孟子》书中,它的地位其实不重要,它的意义也没有和“本体”的概念挂钩。王学将“良知”一词提升到儒学的核心义,那是语义扩充的结果,也是“两种知”长期衍化下的结晶,《孟子》一书中的原义并不如是复杂。
二 天地之性的问题
人性论是中国哲学最古老的议题之一,早在诸子学说兴起之前,“性”字已成了经书中的重要概念。但在儒学的范围内,两种性的区别较晚,放宽标准来说,也许可追溯到孟子。但这样追溯出来的结果还是曲折隐晦,争议的空间颇大。放在近世儒学史的脉络下考量,两种性的区别当始于张载、程颐;唐末的李翱无作此区别,但特别突显“性”的超越性格且形成返本溯源概念,返本溯源即是“复性”说。“复性”说在儒学人性论发展史上占有非常关键性的地位,我们探讨孟子与理学人性论的异同时,可从此点介入。
“复性”说密集地见于李翱所著《复性书》上、中、下三篇,《复性书》谈的就是恢复人的本性问题。这上、中、下三篇的文章旨趣可简摄如下:(一)人性“原本”是寂静无为,光照天下,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圣人,乃因他体现了这样的人性;(二)性会动而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将人性从纯一的状态带到混浊的尘世中来;(三)学者要务,乃是透过“还灭”的历程,以期恢复“原初”的状态:“妄情灭息,本性清明,周流六虚,所以谓之能复其性也”。李翱更进一步说:这种还灭妄情以复其性的方法乃是“无思”。
上述第一点是李翱人性论的核心观念,它预设了某种“原初的”但却又是超越境界的圆满人性状态;第二点用于解释现实的人与理想的人之差距及原因,如果人的感性是人性结构必然的因素,那么,人的“堕落”也就是必然的;第三点则是工夫论的问题,学者透过“无思”的方法,可以将自家性命从堕落的状态提升到原初的理想情境。“原初”的圆满―分裂―再回到原初的圆满这样的构造乃是李翱《复性书》的主要内涵。该文由于佛老虚寂的色彩较浓,受到后世不少儒者的质疑。*李翱对情的抹杀,被批评得尤为厉害,朱子说:“李翱复性则是,云‘灭情以复性’,则非。情如何可灭!”(《朱子语类·孟子九》,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卷59,第10页)真德秀亦有相同的观点,参见《西山读书记》(台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商务印书馆,1983年,卷1,第37页)。陈淳说:“释氏之论大概欲灭情以复性,李翱作《复性论》二篇,皆是此意。”(《北溪字义》卷下,第16页)黄震亦言李翱“灭情以复性者又杂乎佛老”。(《黄氏日抄》,台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商务印书馆,1983年,卷35,第39页)理学家(尤其是朱子学学者)对李翱的形象相当一致,都认为他溺于禅佛。李翱当然不会接受这样的判断,他毋宁认为他只是复兴久已断绝的儒学传统,他所用的概念,比如“无思”,也都出自儒门圣经,绝非阳儒阴释。关于理学家与李翱的论点之是非得失,笔者无意评议,但此文设想的人性论之构造形式基本上可以代表理学家性命之学的一个基本模型。这个模型也许不是唯一,但却是最重要的一个。在圆满―分裂―再度圆满的模式下,可以有些变形的次模式,比如在工夫论方面,有些学者不用无思这类遮拨的方法,他们可能会采取格物或扩充的方式,但他们的目的依然是要复性。
笔者认为北宋理学家不管用不用到“复性”这个语汇,基本上都有“复性”的思想,而且这套思想还是其思想体系中极核心的概念。周敦颐的“主静立人极”,其目的是要回复到“纯粹至善”的“性”。邵雍的先天之学要达到“无尘”之境,这也是复性的模态。二程也有学习的目的在达到“复性之本”*“若夫学而知之,气无清浊,皆可至于善,而复性之本。”《河南程氏遗书》卷22上,《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92页。之说。明代理学继承“复性”线索而来的学派更多,如薛瑄的河东、陈白沙的江门、王学之后的江右、东林等学派皆是,这些学派逆觉体证的性格很明显,“复性”是他们学说的宗旨。比较需要仔细斟酌的是理学的两大派别程朱与陆王,程朱与陆王本人直接言及复性思想的文句虽然不算太多,但这样的思想冠上别样的语辞,它还是深入到他们思想的骨髓里去。
笔者上文所说的“格物”方式,即使连对理学命题不太熟悉的人都知道它是程朱思想的重要概念。朱子一生的学问集中在《四书》,《四书》又以《大学》为支撑的骨架,而《大学》一书最重要的内容,依据朱子的理解,乃在“格物致知”的论点。可惜,此书虽然重要,但从朱子的眼光看来似乎有缺文,而且所缺者正是落在“格物”这样的核心概念上,朱子因此为此书作了《格物补传》。《补传》说:学者的功课乃是即天下之物而穷理之,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随时格,随地格,不要松懈,“及其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这就是“物格致知”的层次。
朱子的格物致知之说很重要,论及此概念及此《补传》之文章多矣,*参见牟宗三《心体与性体》(台北:正中书局,1979)第3册,第384-406页;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台北:学生书局,1986),第278-347页,尤其第312-323页;刘述先《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台北:学生书局,1982),第118-137页;陈来《朱熹哲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0),第241-279页;戴君仁《朱子阳明的格物致知说和他们整个思想的关系》,《孔孟学报》,第9期;友枝龙太郎《朱子格物论の构造》,《日本中国学会报》第12期,1960年。李纪祥《两宋以来大学改本之研究》(台北:学生书局,1988)一书则对以《格物补传》为中心的《大学》改本问题,有较详细的溯源探流工作。一般多将此概念放在知识论的角度下定位,笔者亦不反对此概念具有知识论的内涵;但笔者认为朱子的知识论有其特性,须待澄清。首先,朱子的知识论有存有论的要求,就字义层而言,朱子的“穷理”概念似乎指涉向外求知的活动,但朱子一向坚持得之于外者,实即得之于内,亦即原本潜藏于内的理之重新发现。他的“致知”从来不是“求得知识”之意,而是内外知识之重新认同,再度合流。*金永植反驳胡适等人对朱子格物学的误解说道:“格物”主要相关者并不是理智的程序,事实上,人透过“格物”,了解物理,此事被视为人心之理与事物之理的“共鸣”,因为天理既在心(所以有心之理)也在事物(就是它们的理),所以当学者得到事物之理时,它常被描述为“见到了理”,而不是“认知了理”。换言之,他所得者与其说是理之知识,还不如说是对理的一种洞见。Yung Sik Kim, Chu Hsi on Nature and Science,钟彩钧编《朱子学的开展:学术篇》,台北:汉学研究中心,2002年,第151-152页。笔者赞同此种解释。我们只有将朱子的“心”视为某种与本体有本质上的关联之心,才能了解他何以不能接受“义外”标签的批判。否则,其“致知”“穷理”的意义即无从了解。
其次,朱子的知识论与工夫论是连续性的,甚至不妨说:它们是一体的两面。朱子的知识论从来不是独立的,它是工夫论的一条重要支柱,简单地说,完整的工夫论乃是包涵“主敬”与“格物致知”在内。这套工夫行到极处,会有“豁然贯通”的境界呈现。“豁然贯通”境界,也就是“极夫心之所具之理”之境界。这样的心是圆满的终点之心,但圆满终点时的心也是原初之心。朱子说心是气之灵,这样的界定学者都能知晓其中之义。但目前研究朱子学的通人比较少注意朱子设定一种“原初”的心,他这种最根源的预设与东方主流思潮的体验形上学之预设其实没有两样,朱子也可以接受“本心”的概念,这样的本心具备“明德”,它“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可惜人一生下来即有气禀之杂,所以人必然地要偏离这样的本心。还好,不管气禀如何浊秽,本体之明未尝稍息,学者透过格物穷理的过程,最后还是可以“复其初”。根据《大学章句序》的说法,“复其初”也就是“复其性”,也就是恢复到天理流行、湛然具备之层次。*参见拙作《格物与豁然贯通——朱子“格物补传”的诠释问题》,收拙编《朱子学的开展:东亚篇》,台北:汉学研究中心,2002年,第219-246页。
相对于程朱的“格物穷理”,陆王的“扩充本心”或“致良知”似乎代表的是另外一路。我们单单由“扩充”或“致”这样的语汇,似乎嗅不出“复性”的气味。然而,有两个现象可以提供我们另外思考的角度。首先,陆王的后学皆有强烈的逆觉以复性之主张。陆九渊弟子杨简以不起意为宗,其学以悟本心为准的。陆门主心性为一,因此,杨简之学也可视为陆门版的复性之学。王学的江右言及复性者更多,若罗念庵,若聂双江,其学皆以悟本体为准则。“复性”是他们学说中的核心概念。
即使陆、王本人,他们的学问也当预设着某种超越的体证本体之风光。陆象山是杨简的老师,他对杨简的悟道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心性之学注重自得自悟,但同样注重师门日常的指点。陆象山有“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之说,平日开启学生,亦多言及“宇宙”二字。宇宙是时空之整体,它不是知识对象,现在宇宙居然可以和“心”合一,笔者认为:此种学问只能预设陆象山有“体证本体”之经验,上述这类的语句才可以讲得通。*参见拙作《理学家与悟——从冥契主义的观点探讨》,《中国思潮与外来文化》,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所,2002年,第177-181页。换言之,象山之学重当下推拓,其方向与慈湖之重逆返,似有不同。然而这无损“复性”在其思想中占据重要位置。
阳明的情况亦然,王阳明的龙场驿一悟,所悟何事,他没有明说,高攀龙倒是替他作了解释:王阳明“后归阳明洞习静导引,自谓有前知之异,其心已静而明。及谪龙场,万里孤游,深山夷境,静专澄默,功倍寻常,故胸中益洒洒,而一旦恍然有悟,是其旧学之益精,非于致知之有悟也。”[1]王阳明龙场一悟后,出山讲学,多言静坐明体之事。*王龙溪描述王阳明此时之教法如下:“自此之后尽去枝叶,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为学的,亦复以此立教。于《传习录》中所谓如鸡覆卵,如龙养珠,如女子怀胎,精神意思凝聚融结,不复知有其他。颜子不迁怒,不贰过,有未发之中,始能有发而中节之和,道德言动,大率以收敛为主,发散是不得已。种种论说,皆其统体耳。一时学者闻之,翕然多有所兴起。”《王龙溪语录》,台北:广文书局,1977年,卷2,第5页。等思想更成熟后,他的讲学重点诚然放在“致”上,而不是逆觉静坐。但这无碍于他曾有强烈的复性要求,也无碍于“复性”与“致良知”的密切关联。而且,纵观王学的流变史,很容易看到“现成良知”与“归显于密”一直是交互兴起的工夫论节奏,一张一弛,一弛一张,而不是一了义,一不了义。
宋明理学家言及复性者极多,明儒言之者尤详,上述所说只是勾玄勒要而已。然而,他们所说的性字为何?为何从李翱起,直到当代新儒家学者马一浮创复性书院为止,他们都义无反顾地将“复性”视为为学的最高目的?
“复性”预设经验的人性外还有一圆满的人性,现实的人性要向圆满的人性回归,人格的发展依照某种超越的目的论的方向而行。两种性的对照或分合,这是理学史的大论述,而首先倡导此说者厥为北宋的张载与程颐。*“道夫问‘气质之说,始于何人?’朱子曰:‘此起于张、程,某以为极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朱子语类》卷4,第70页。张载《正蒙·诚明篇》云:
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气质之性”乃是“气性”一词进一步的落实化,这是自然的人性,“生之谓性”传统的一支。张载在此却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作一对照,而且认定“气质之性”不能算是真正的“性”,人性的内涵乃在“天地之性”。“天地之性”一词极怪,因为“性”是个体性原理,而“天地之性”是否意味着“天地”也是种个体,此一极大的个体之本质即称作“天地之性”呢?事实恐非如此,张载的意思很清楚,他不是谈自然哲学,“天地之性”是心性论的语汇,是工夫境界的语汇,它要等待学者“善反”气质之性后,才可以呈显,所以“天地之性”一词不是指“天地”为一极大的个体物之自然性质,而是指人性在“善反之”的超越观点下,它具有绝对的普遍性。此际,个体融进无限,所以说:“性者,万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诚明》)“万物之一源”实即为“万物之同源”,“性”再也不是个人性的,它遍万物而存在,*朱子回答他的学生问“性为万物之一源”时说:“所谓性者,人物之所同得。非惟己有是,而人亦有是;非惟人有是,而物亦有是。”《朱子语类》卷98,第2511页。朱子因此有“枯槁有性”之说,朱子《答徐子融三》《答余方叔》诸信备言此义,参见《朱子文集》,台北:德富文教基金会,2000年,卷58,第2812-2814页;卷59,第2912-2913页。朱子的“枯槁有性”之说传到韩国,曾引发湖洛学派“人性物性异同论”之争。但就朱子的用语而言,枯槁有性,而且此性乃先天意义的“太极”或“理”之谓,这是可以肯定的。我们现在终于知道“天地之性”这样的词语所说何事了。这样的性虽然落实到每个人身上谈,但它的根源却是“天地”的,亦即是宇宙性的,性命的根源深入到天道的范围上去。
以上所说,张载的人性论是种双重的构造,表层的气质之性是气落实到人身上所呈现的特殊的私人性的气性,这样的气性人人皆有,但人人不同;底层的性则是作为宇宙本体的天地之性,这样的性不但是人人共享,而且,我们不妨说人与万物在超越的意义下是同一家族,不,当说是同一的。张载《西铭》这类的伦理学是从这样的人性论引伸而来的结果。
“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这组对照概念到了程颐手里,即变而为“理性”与“气质之性”的对照;经过二程之手,即再变而为更有名的性―气之对照:
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
性—气到了朱子后学陈埴手里即成为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对照。这样的对照组尔后即成了理学家论人性问题时典型的论述,它取代了张载与二程所用的语汇。[2]
二程的“性”与陈埴的“义理之性”不再是私人性质的,程颐说:“性即理”,这个定义被朱子视为千秋万世说性的基础。这样的界定为什么重要呢?因为性一旦被界定为理,依据程朱对“理”的解释,它即提升到超越的理世界上去,亦即属于“太极”层。程朱后来对此一概念有更详尽的说明,其中最重要的补充就是“理一分殊”,此义此处姑且不论。“性即理”之所以值得重视,乃因理是超越而普遍的,它是终极的太极,统体一太极,物物一太极,既然“天下无性外之物”,所以每个人的义理之性必然也是宇宙性的,它必然会参与到天道的范围上去。张载说:“性与天道不见乎小大之别也。”程颐也说:“称性之善谓之道,道与性一也。”二程同意这个论点,朱子、阳明同意这个论点,主流的理学家大概都同意这个论点。程朱陆王对于心性之间的关系当然有不同的理解,但他们都一致同意:超越之“性”不只是心性学或道德哲学的语汇,它也是自然哲学与形上学的概念。它不只见于“人”,也见于“物”。
三 从德性之知到乾知
张载与程颐首先划分两种性,联带地,两人也同样首先划分两种知。张载的划分见于《正蒙·诚明》篇及《大心》篇:
诚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闻见小知而已。天人异用,不足以言诚;天人异知,不足以尽明。
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
“诚明”一词出自《中庸》,它指的是天道,也可指圣人之化境。诚明之知和闻见之知不同,其不同似有两义,一是发用的“主体”不同,一是所见者不同。闻见小知乃经验意义下的“人”所发,闻见是感官的作用,感官所对立之物乃认知之对象。天德良知则为“诚明”所发,也是人的“德性”所发,它所知者不是感官对象,而是良知之感应为物。
程颐的划分见于《遗书》卷二十五:
闻见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则知之,非内也,今之所谓“博物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见闻。
程颐这段话与《大心》篇所说类似,两者应该同出一源,不管始发表者是程颐或是张载,他们两个人应该都同意底下这样的区分:人有两种知,一种出自感官,一种出自德性;一种是“物交”而得的知识;一种是直觉感应之为物。
张载的“物交”与程颐的“物交物”之语词出自《孟子·尽心篇》:
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
“耳目之官”与“心之官”是孟子对“小体”与“大体”的详细诠释。程颐、张载讨论“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的问题时,引用孟子这段话语,这样的选择不会没有意义的,他们应当认为两种知的分别是从“心之官”与“耳目之官”或“大体”与“小体”的对照而来的。
大体与小体的对照意味着人具有双重的构造,他是感性—智性的构造与心体构造的结合。他又具有双重的身分,是现象的身分与体用合一的身分之集合。就人作为感性智性的存在而言,人具有认知心,人可以表象对象物,并获得现象的知识,这样的功能是很清楚的,此义亦不难理解。但就人具有贯通体用的本心,本心有种德性之知,这样的知“不萌于见闻”,这样的意义如何可解,似有歧义。
“德性之知”的提出乃为保证道德判断有一独立于感性之外的根源,它是种天德良知,亦即这种知独立自主,它的作用本身即保证了它本身活动的正当性,就德性之知最明显的意义而言,它是道德学的概念。然而,我们第一节已说过理学家论性,皆将人性提升到天道性命相通的高度,亦即从伦理学的施用范围扩充到存在论的范围,那么,张载与程颐的“德性之知”的根源是否会深到如此的境地呢?
笔者认为张载的德性之知应该与“本心”“大心”“天道”的概念一起解读,而且是同一个层面的概念。《诚明》篇所说的天德良知显然不只是道德的概念,此篇说道:“天人异知,不足以尽明”、“知必周知”,像这样的“知”恐怕都得提升到本体的高度,它才可以“周知”。张载论到“周”这种度量的概念时,有种很自觉的意识,他意识到超越的性、天、理、道这些概念其实是无法用量的范畴界定的,如果要勉强形容的话,只能找“充其量”、“最大量”的状词形容之,此处“天人”与“周知”的“天”“周”皆是此义。张载的重要思想概念可以说都扎根在本体论的基础上,他说的“性”“神”“虚”“道”“大心”无不如此。
《大心》篇说的“德性之知”亦不例外,“德性之知”的意义放在上下文的脉络中可以很清楚地呈现出来。我们前面引文的前头尚有“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物有未体,则心为有外。世人之心,止于闻见之狭。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梏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孟子谓尽心则知性知天,以此。天大无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张载此处的“体”字作动词用,它不只是泛泛之论的“体会”之意,而是“作为本体”之意。所以“体天下之物”一语意味着“成为天下之物的本体”,“成为天下之物的本体”当然也就意味着“体现天下之物”。无疑地,张载所要“大”之“心”,乃是“本心”,本心的活动是种本体论的创造,本心所向,物我皆融入一体的流行中,主体无认知义,客体无对象义。“惟心无对”,“德性之知”自然也是无对,此处的德性之知必然是作为本体的大心、天心或宇宙意识之直觉活动。
张载、程颐的德性之知源自孟子的良知,但它有个本体的向度,唯张、程所说稍嫌隐晦。到了王阳明,他直接就将孟子的“良知”两字接收过去,而且视良知为本体,且看底下所述:
良知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3](《传习录中·答陆原静书》,P.62)
心之本体即是天理,只是一个,更何思虑得,天理原自寂然不动,原自感而遂通。[3](《传习录中》,P.58)
无知无不知,本体原是如此。[3](《传习录下》,P.109)
无声无臭独知时,此是乾坤万有基。[3](《咏良知诗》,P.790)
前面三条皆言及“本体”,其本体义无疑是从“心体”立论,作为儒家道德意识的本体不可能不介入到人伦世界的活动,此王阳明所以有“知善知恶是良知”之说,王阳明言良知大体也都集中在道德判断的领域。对明末严守佛法规范的僧侣而言,王阳明的“良知”说无疑已侵入他们的国境,如何自保,这已是迫在眉睫的大事,明末高僧若云栖祩宏、若永觉元贤皆曾在佛教的“知”与王学的“良知”之间划上一条不可跨越的线。他们认为佛教的“知”才是“真知”,佛教的知觉“灵光独耀,迥脱尘根”,这才是究竟。相形之下,王阳明的良知乃涉及伦理领域之妄境,所以这样的心知根本是不彻底的。
祩宏与元贤的说法是极端护教的论述,他们的语言背后其实仍反映儒学是“人天教”的想法。然而,恰好王阳明的良知说已不能再被归到人天教的范围,它施用的领域绝不只是道德界。上述三条所说的“本体”不是泛泛之论,事实上,阳明及其后学时常言及良知与本体的关系,此事曾引起同代儒者相当程度的反弹。*如阳明前辈的罗钦顺即认为王阳明的“良知”概念颠倒了体用关系,他引孔、孟、曾、子思言及“知”之语言,论道:儒家经典中“凡知字皆虚,下一字皆实,虚实既判,体用自明,以用为体,未之前闻也。”黄宗羲《明儒学案》,台北:河洛图书公司,1974年,卷47,第53页。阳明后学的李材也说:“从古立教,未有以知为体者。”《明儒学案》卷31,第39页。罗钦顺与李材的评语很值得体玩。良知是本体,本体除了知是知非外,它自然也生天生地,良知必然要由意识界走向存在界。以上所引述的这些语言不太容易有太歧出的解释,理学家从周、程以下,凡言及未发之中、寂然不动这类的语汇,其语皆指向超越之境,皆指向意识与存在交会之处的化境。此处既然能所双遣,物我齐泯,则在意识者亦在存在物,在存在物者亦在意识,所以良知为心之本体之说固通,良知为乾坤万有基,此义亦得以成立。
从王阳明之后,良知作为本体之说已成陈谈,而且此本体不但是作为主体的良知之本体,它也是物我同根之本体,此义亦为王学流派诸家之共许。我们且举王畿为例,看他理解的良知之面貌为何:
千古圣学只一知字尽之,知是贯彻天地万物之灵气。[4](卷1,P.6)
良知是造化之精灵……吾之精灵生天生地生万物,而天地万物复归于无,无时不造,无时不化,未尝有一息之停。[4](卷4,P.6)
从古以来生天生地,生人生物,皆此一灵而已。孟子于其中指出良知,直是平铺应感,而非思虑之所及也。[4](卷7,P.4)
王畿这样的“良知”已取代北宋理学家“道体”、“诚体”的概念,都是最高的存有。此际,它虽然还是落在心体上讲,但其心体悬义甚高。王畿的“良知”从先天未判的浑沌中扎下根基,直感直应。王畿后来干脆直呼良知为“乾知”,*《王龙溪语录》卷6,第1b页:“《易》曰:‘乾知大始’。乾知即良知,乃浑沌初开第一窍。为万物之始,不与万物作对,故谓之独。以其自知,故谓之独知。乾知者,刚健中正,纯粹精也。七德不备,不可以语良知,中和位育,皆从此出。统天之学,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者也。”李材认为“乾知”之说极可笑,参见《明儒学案》卷31,第37页。罗钦顺评“良知天理说”亦云:“今以良知为天理,即不知天地万物皆有此良知否乎?天之高也,未易骤窥,山河大地吾未见其有良知也。万物众多,未易遍举,草木金石吾未见其有良知也。求其良知而不得,安得不置之度外邪!”(《答欧阳少司成崇二》,载《困知记》,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23页)由李材与罗钦顺的反驳,更可以从另一种角度看出王学的良知兼具道德主体与自然本体的作用。“乾知”很明显地是从《乾文言》的“乾元”、“乾道”的概念转化而来,“乾元”、“乾道”是本体宇宙论的“道体”的词汇,“乾知”虽然在个体上的道德意识上立论,但它的本质却向上参透到道体的流行。“乾知”的本质如是,所以乾知下判断,原则上是一点灵明圆起圆断。因为它所作的任何的道德判断背后皆有乾天作支柱,所以每一道德行为都是从本体中跃起的事件,事件之相有限,而它所体现的道之涌现的价值则是无限。
四 孟子打通了天道与性命吗
理学家大抵认为他们说的“性”字取自孟子,程伊川说:“孟子所以独出诸儒者,以能明性也。性无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即是理。”[5]性善说是孟子对儒家最大的贡献,从程朱以下,这个断言几乎被所有的理学家所接受,他们大体也认为他们的人性论——比如程朱的“性即理”之说——是继承孟子而来的。
理学家到底是善绍善继,还是过度诠释?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得先回答:孟子的性善论是怎么来的?他要对话或对治的理论为何?
《孟子》一书中有两场大的辩论,一是辩“仁内义外”之说,一是辩性善之说,前者的主要论辩对手是告子,后一项的对手除告子外,另有其他学者的说法。“仁内义外”与“性善”的辩论应该视为同一个问题不同面相的讨论,它们触及的是道德判断的根源问题。《告子上》记载孟子与告子辩过“仁义内在”或“仁内义外”的问题,同样的题目后来也发生在公都子与孟季子身上。辩论的双方对于“仁内”没有什么争议——虽然两者所了解的“仁内”可能意义大不相同,他们的争执主要在“义外”这点上。依据告子与孟季子的理解,我们所以会尊敬长者,乃因“彼长而我长之,非有长于我也;犹彼白而我白之,从其白于外也,故谓之外也。”“长”这个字眼之于长者,就像“白”这个字眼之于对象物(如石头),白是石头的属性,它的存在附属在石头此物上,它本身不能自存。同样的,“长”也是长者的属性,而我们所以会“长之”,乃因我们的态度是由长者的“长”所决定的。
我们都知道孟子的回答。他的答辩诚然有迂回纠缠之处,但主要观点倒扼要得很。孟子问:“长者乎?长之者乎?”这种反问将道德判断的决定权由对象转到自身上来,孟子的立场很清楚:“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仁义礼智只是大分类,严格说来,孟子是主张任何的道德判断都不是外铄我也,都是我固有的。所谓“固有”,并不是拥有,而是由我的本心所自发的。孟子称呼固有的道德认知能力为“良知”,实践此道德认知的力量为“良能”,“良知”蕴含着“良能”。“仁义内在”这样的理论再扩大,即有“性善”之说。
人性善恶之辩是战国时期学界争辩的主战场,学者有言无善无恶者,有言有善有恶者,有言可善可恶者,孟子则力言性善。如果单单罗列这些说法,那么,孟子的性善说只是诸说之一。但如果我们看这些论说的理论依据,马上发现孟子的判断与他们的完全不同。孟子以外的学者论人性,不管是告子、孟季子或其他人,他们立论的依据都是从经验的观点着眼,经验世界的人性自然善善恶恶,三品九品,千殊万差,气成而定,其相关论述皆可在某一种观点下成立。但孟子的论证与之不同,在有名的“见孺子乍入于井”的论证中,孟子提到人的道德判断的准则不是来自世俗功利的考虑(不是纳交于小孩之父母,也不是想得到邻里的赞美),也不是来自于生理机制的制约(非恶其声),而是来自于某种道德心不能自抑的动能。孟子论道德实践的问题时,特别喜欢举一些面临冲突临界点的例子为证:为人子女者如果行走山间,看到父母遗体,“狐狸食之,蝇蚋姑嘬之”,他会起什么反应?听到待宰的动物之哀嚎,闻者的心理状态为何?自己身为天子(舜),公正的法官(皋陶)将犯罪的父亲(瞽叟)定罪,他要如何自处?孟子这些设问都是要将学者逼到意识的死角,要他在各种经验的解释都不足以证成其状况后,直下认取本心的呈现,只有本心所下的判断才是真正的道德判断。
本心自己下道德的判断,“是非对错”的标准由事物、由天界转移到人的主体性上来,陆象山后来以“心即理”三个字总结孟子的道德学。如果将“心即理”一词放在道德领域之下理解,陆象山的解释可谓恰到好处。笔者所以提到“在道德领域下”,乃因孟子的论述施用的范围大体在此,他使用“良知”一词亦是如此。《孟子》书中,“良知”仅见一次,其言如下:
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尽心上》)
孟子所用的“良知”一词,指涉的是本心先天的道德判断能力,这种道德判断的能力绝非后天学习得来,而是人所固有的。这样的“固有”当然不必意味着人即无差异性,它也可以意味现实上的人之良知之呈现可以有极大的落差。但孟子所以使用“良”此一词语,即表示只要是人,只要他还是以人的身分在世间活动,他必然即有道德判断的先天知识。这种先天知识是人的心性本具,人人都有独立于后天知识、习俗权威或生理本能之外的道德判断能力,当代学者用“理性的事实”解释人的良知,这样的解释应当是很合理的。[6]
从“仁义内在”、“性善”到“良知”,这一系列的概念撑起孟子学的具体血肉。这些词语由于后来被理学家全盘接收,成为主流的论述,学者很容易习焉而不察,前后段时期所使用的这些概念之意义被等同起来。但如果回到孟子发言的现场,会发现孟子好辩的形象一大半是因为“性善”“仁义内在”的问题而来的,这两个议题正好也是《孟子》一书中理论趣味最强的两个题目。孟子何以要这般大声疾呼呢?因为他的观点在当时是种新说,他同代的学者都不这样想。孟子一生向往的孔子即不谈性善、仁义内在,但孔子不谈,此事的影响还小,因为孔子是立教者,他只要“示之”,不必要牵涉这方面的争辩。然而,如果和孟子关系颇密切的子思所持的论点是仁内义外,或是站在经验的立场论人性,那么,情况会怎么演变?可以想象孟子的压力会有多大。
笔者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1998年郭店竹简释文出版后,[7]引起学界极大的震撼,此批材料之重要,不在马王堆帛书之下。现在学界大抵同意这批材料的年代在孔孟之间,而且除了《老子》与《太一生水》外,其余材料可能都是儒家的著作,且很有可能是《子思子》一书的材料,至少与子思关系颇深。*参见周凤五《郭店竹简的形式特征及其分类意义》,收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编《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7-59页;王葆玹《郭店楚简的时代及其与子思学派的关系》,参见《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第2册,第137-164页;叶国良《郭店儒家著作的学术谱系问题》,《台大中文学报》第13期,2000年,第5-25页;拙作《子思学派试探》,参见《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606-624页。我们且看下列这几条材料:
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及其见于外,则物取之也……好恶,性也;所好所恶,物也。[7](《性自命出》)
○,义之方也。义,敬之方也。敬,物之节也。笃,仁之方也。仁,性之方也,性或生之。
仁,内也。义,外也。[7](《六德》)
仁生于人,义生于道。或生于内,或生于外。[7](《语丛一》)
仁,人也。义,宜也。仁,人道也。义,天道也。*原竹简残片,据李零之说补之,参见《郭店楚简校读记》,收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17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530页。[7](《语丛三》)
第一条材料以气定性,这是“生之谓性”的老传统。在孟子之前,凡是言性者几乎皆取此义,即使子思,恐怕也是如此。第二条的语义比较模糊,但观其大概,“义”属物,仁属人性所有,这应当是仁义分别隶属于主客的理论。至于第三、四、五条明显的都是“仁内义外”的讲法,仁指道德情感,义指道德判断依循的客观标准,它在物上,这样的义是天生的,所以说“义,天道也”;它不随人的主观意志而改移,所以说“义,无能为也”。义附属在物上,而且用以决定道德判断。
告子可能是位与孟子同期、甚至年长的儒者,*参见陈大齐《告子及其学说》,《浅见集》,台北:中华书局,1968年,第268-305页。而由郭店出土楚简判断,他可能与子思有关。如果这样的观察可以成立,那么,人性的争辩与仁内义外的争辩可以说是儒学内部的争辩。孟子当时所受的挑战可能比我们想象中要来得大,他四面应战,而战场皆设在“人”而非“物”的领域。孟子与同辈学者之辩论,毫无例外地,双方的重点皆落在人性论上。“用气为性”及“仁内义外”说恐怕是其时的主流,孟子则是异军突起的新说。但不管新旧说,敌对的双方所探讨的议题皆属人文领域内的人性论之范围。至于孟子的新说被扩大范围,侵入自然领域,成为新主流学说的经典依据,其年代恐怕要迟至宋代以后。孟子虽然曾对全身发抖的庙牛发出同情的呼唤,但他从来不问牛性善不善的问题,他的性善王国要包容动、植、矿物(仁民而爱物),但动、植、矿物的本质中没有他的性善王国。
五 由道德界到存在界
如果比较理学家和孟子的人性论及良知理论,会发现两者在施用的范围上有明显的不同。孟子论人性,论仁义内在,论良知,他的这些概念都是在道德心的范围,亦即都隶属于一道德主体。而理学家的这些概念所施用的范围都不仅止于道德界,而且也遍布到存在界。枯槁有性,仁为宇宙之生意,良知是乾坤万有基,这些语言都出现了。《孟子》书中到底有没有牵涉到意识与存在共同向度的思想?这样的思想到底能不能视作人性的成分?
很明显的,《孟子》一书确实可以解释成蕴含性命与天道相关联的消息,只是这种关联可以关联到什么程度,我们不太能确定而已。且看下面这几条常被视为孟子重要的“性与天命相通”的文献到底所述何事:
(一)“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公孙丑·上》)
按,这话出自著名的“知言养气”章,孟子在此不是泛论气的自然状态问题,他是放在工夫论的观点着眼。孟子认为心的活动必连着气,“心”可意识到,“气”不可意识到。“心”扩充到哪里,气也相应地跟到哪里。引文说到浩然之气,此气既然盈乎天地之间,反过来想,我们可推知这是心量之极其至。如果用张载著名的话说,此即“大其心”的境界。
(二)“万物皆备于我矣,返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尽心上》)
按,“万物皆备于我”和“返身而诚,乐莫大焉”当有关,亦即前者是境界语,后者是工夫语。学者返身而诚后,可以体验某种特殊的体验,如果人与万物合一,纯然一体,完全消除了物我的区隔,这是种内在的冥契主义类型。如果万物备于我,一体中仍保有万物之形象,只是此万物不以对象面貌呈现,而且彷佛亦具主体,此是外向型的冥契主义之类型。*内向型与外向型冥契主义的区别参见W.T. Stace著、拙译《冥契主义与哲学》,台北:正中书局,1998年,第69-184页。
(三)“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尽心上》)
按,此段话依上下文判断,乃是描述“王者”之神秘感化功能。中国的王者或天子一直没有丧失掉他们特殊的感应能力,他们的“奇理斯玛”与他们感应能力成正比。但“上下与天地同流”一词也不无可能意味着这是某种特殊的冥契经验,由此语具“动态”的语感看来,它偏于外向型的冥契主义。
(四)“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尽心上》)
按,这段话可能是《孟子》一书中最重要的话语,前两句颇有“以心著性”的意味。亦即“性”不是经验世界的概念,它是要体现出来的,而能将它体现出来的作用者,只有“心”,而且只有在此心充分实践它的本质之后,学者才可“知性”。“知性”以后,即可体证存在的终极根源“天”。
上述四段话都触及到主体与存在的关系,但前面三段都没有触及人性的理论问题,它们所描绘的景象,毋宁是某种的“本地风光”之语言。说得更清楚些,我们不妨将它们视为“冥契主义”的语言,这样的语言通常会牵涉到“我”或“人性”的界定问题。因为冥契境界必然意味着无内无外,万物一体,此时此际,何者为物?何者为我?何者为内?何者为外?何者是意识?何者是自然?如果我们将此“上下同流”、“万物齐备”的境界界定为“我”或“性”,那么,孟子的“性”即有可能从道德界走向存在界,人固然有先天的善性,万物也可以超越而非内在的具有此性,因此,蜂蚁有性,木石亦有性——朱子这方面谈得最清楚。然而,这三段话语虽可往这方面发展,孟子却没有从此点界定性。
第四条所涉及的心性问题,最有可能解释成“性”是“天地鬼神之奥”,它不只是人性的概念,也可指涉天地万物。依据后来理学家的理解,儒家性命的问题可以由主体往上谈,也可以由道体落实下来而谈,前者是《孟子》的进路,后者是《中庸》《易传》的进路。《孟子》与《庸》《易》两端进行,性天相通,双头回向,殊途同归。牟宗三先生的观点可作为此说的代表,他说:“天之所以有如此之意义,即创生万物之意义,完全由吾人之道德的创造性之真性而证实。外乎此,我们决不能有别法以证实其为有如此之意义者。是以尽吾人之心即知吾人之性,尽心知性即知天之所以为天。天之所以为天即天命之于穆不已也。天命之于穆不已即天道不已地起作用以妙运万物而使之有存在也。”[8]牟先生这种解释当然是依据陆王心学的解释而来,这样的解释有理路上的一贯性,是种调适上遂的解释,这样的解释在哲学理据上有其说服力。
但即使在哲学论证上可以如此推衍,我们也不得不指出:孟子的“天”是否真有如牟先生所说的“于穆不已”之意,恐仍需推敲。在《尽心》篇的脉络中,孟子说的“天”可以有此涵义;但其他章节的“天”字,如“天油然作云”、“若夫成功,则天也”、“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这样的“天”字大概指自然力量之意的成分较多,而“仰不愧于天”、“天视自我民视”、“天命之”之类的“天”则多少保留了早期人格神的涵义。在《孟子》诸多的“天”之案例中,具有深奥内涵的“于穆不已”之意的“天”字,反而少见。如果孟子将“天”视为其道德意识发展的绝对性原则,他处理“天”的终极性本体义之问题时,未免太轻率了。笔者不认为《尽心》篇的心—性—天之说不重要,但至少在理论上,此章并没有明确指示“心”到底是否如同陆王所说的本心,因此,“其性”是否可以指涉为胡五峰、刘宗周思想中的那种超越之性,最后指向天命于穆不已的道体?此种注解是否为唯一的选择,恐怕不无可疑。因为我们如将此处的“心”、“性”两概念完全放在道德意识的观点下考虑,而不必诉诸另外一种更高的超越的天命之概念,文意上也未尝讲不通。
先秦典籍中,《孟子》一书是少数散佚较少、大体可以完整代表作者本人思想的著作。他谈人性论的问题时,几乎所有的精力都花费在替道德意识之自我判断作辩护。谈“良知”时,其重点也是放在良知独立于一切经验性的因素之外,自己即可提供道德判断的依据。孟子这方面的信念极强,体验极深,如果道德意识独立自主的话,它的根源在哪里呢?“心”是个麻烦的项目,它不像经验世界的存在物。经验世界的存在物定则定矣,它没有纵深的层级问题。但心颇特殊,道德心独立自主,自作判断,但它似乎有无限的纵深。孟子论四端所以喜欢用“泉水”的隐喻,即缘此故。然而,心体与道体联系点的问题固然可以问,孟子生前不见得有恰当的机缘可以向上探询,孟子提到一些类似冥契主义或准冥契主义的文句,看来这些文句所描述的当是四端之心扩充至极的气象。然而,孟子仍没有将“性”字往草木枯槁上安置,亦即他的论述并没有触及到存在的问题,所以枯槁是否有性,万物之性是否可以一时俱得云云,孟子皆未言及。
整体而言,笔者认为孟子的立场大概是这样的:他的“良知”、“性善”诸说都只是用在道德界,也只是用在人的世界,这两个概念没有牵涉到万物存在的问题。但孟子对道德意识有极深的体证,他知道良心之深深不可测,它贯彻形气心(个体),也贯彻万物(存在界),但他没有从“体物”的经验中发展出良知、本心与万物存在的关系之理论。从“体之”到“说之”虽然可说是相去一间,但这“一间”要变成有意义的理论问题,却须艰苦的一跃。
六 结论:刺激说的检讨
理学家无疑认为他们提的另一种类的人性论与良知论是从孟子那边得来的,我们不必怀疑他们的动机,可以承认他们的推论有其正当性。我们应该也可以接受他们的理论是调适上遂的发展,因为由“四端善性”到“天地之性”,由“良知”到“乾知”,这样的发展可视为内在的因果性之体现。内在因的诠释路线推论到极点,概念容易实体化,历史的作用被视为本质上不相干的外部因素。当代一些同情儒家的学者倒不见得会持硬性的内在因之立场,他们可以接受佛老与理学的兴起有关,但他们比较相信这种相关是种“刺激”,而不是一种本质性的影响。我认为这种“刺激”说其实仍是“内因说”的一种型态,它或可视为弱的内因说,因为此说承认“内因”仍须外在因缘的刺激。笔者可接受刺激说的论点,但在内外因素的比重上,觉得还可讨论。
“刺激说”可以解释儒释道三教在交互影响下,相互吸收,但各有胜场的现象。然而,换另一种角度设想也不无趣味。我们不妨设想:理学的兴起与理学家对佛老(尤其佛教)的流行极感不安有关,理学家反对佛老(尤其佛教),已经不能再诉之于夷夏之辨,也不能只在日用伦常的层次内与之较量是非。理学因抗衡佛老而生,它的价值取向与佛老大不相同,但它思考问题的角度却受到佛老思考方式的制约,理学思考方式的“成见”或“前结构”来自于佛老的文化氛围,这种“成见”或“前结构”不见得为理学家意识所及,但它们却构成了儒佛论辩中共同分享的隐暗向度。结果是佛老达到了什么样的思想高度,理学也当相应地达到性质相类似的思想高度,否则,理学家何以说服学生、说服国君、更重要的是说服自己逃佛归儒。
相应于儒家的“性善论”,我们马上联想到佛教的佛性论。大乘佛教的佛性说异说很多,但无一不与佛教基本义理的空性结合在一起,它施用的范围遍一切法界,《大乘起信论》所谓的“一法界大总相法门体”者是也。依据法严判教,《大乘起信论》属大乘终教,它的理论虽不圆,却是其他各教的共同基础。至于在一般的知之外另立可以洞穿本性的“知”,这种论述在佛教也是极常见的,僧肇首立“般若无知”之论,天台宗有“一切智”“一切种智”之说,神会亦提“心体即知”之论。这种来自真常惟心系佛学的理论乃是唐宋士子每日浸润的文化氛围,理学家在这种文化氛围下成长,受制于这种文化氛围的无形约束,很难避免佛教的思考模式。
从魏晋到隋唐,贯穿法界的佛教真心思想是此时文化中的显性因素,同为一时显学的道教也发展出类似佛性的道性因素,在重玄道教系统中,道性变成极重要的概念,潘师正说:“一切有形,皆含道性。”这样的“性”显然超过“人”的范围,而进入道家人士爱用的“天”之层次。但潘师正的解释其实仍不够精致,无法穷尽“道性”与“道”的紧密关系。《道教义枢·道性体义》说:“道性以清虚自然为体,一切含识乃至畜生果木石者,皆有道性也……自然真空,即是道性。”[9]这样的话语才是称理之谈,道性不只见于“一切有形”,它事实上是见于一切存在,《道性体义》的话语隐隐然有“道在尿溺”的意味了。笔者上述的联想并不突兀,笔者认为庄子的“道在尿溺”其实可视为“道性”论的前身,“道性”这样的概念则是道教在与佛教的长期竞合中,发展出的更精致的说法。
北宋儒者活在道佛这么深厚的“虚空即性”之文化氛围,他很容易受到启发,自然而然地提出同样可以施用于一切法界的心性论,包含对人性与良知的重新界定。
性善论与良知论由道德界走向存在界,最关键的因素是本体论概念的介入。本体与体用这类的用语是理学家彼此对话或过招的招呼语,它的流传过程如何,仍有待仔细参究。但作为一种有影响力的思想概念而言,它不可能被推到先秦的《易经》,*顾炎武的观点,参见《与李中孚手札》,《亭林佚文辑补》,台北:世界书局,1963年,第249-250页。推到魏晋的王弼也不是很恰当,*陈荣捷著,杨儒宾、朱荣贵等译《中国哲学文献选编:下册》,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93年,第446页。滋养这种概念的土壤恐怕还是佛教与道教。*晁说之即说:“经言体而不及用,其言用则不及体,体用所自,本乎释氏。”(黄宗羲编《宋元学案》,台北:河洛图书公司,1975年,卷22,第70页)李颙更进一步落实说:“惠能实始标此二字,惠能禅林之所谓六祖也,其解《金刚经》以为‘金者,性之体;刚者,性之用。’又见于所说法宝坛经,敷衍阐扬,谆恳详备。既而临济、曹洞、法眼、云门、沩仰诸宗,咸祖其说,流播既广,士君子亦往往引作谈柄。久之,遂成定本。学者喜谈乐道,不复察其渊源所自以矣。”(《二曲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73年,卷16,第7页)晁说之与李颙时代,道教的研究尚不兴盛,当代的道教研究显示:“体用”这组语汇,重玄道教也是很重视的。参见林永胜《南朝隋唐重玄学派的工夫论》,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论文,2008年6月。理学家在根源的价值取向上不能赞同佛教缘起性空的世界观,又觉得道家的文化意识不足,他们有本体论的焦虑,也有本体论的追求,这种强烈的心理动能使他们重新发现了孟子,重新发现同时也就是重新诠释。这种重新诠释过的人性与良知概念带有本体论的风味,我们如从内因说的立场考量,说它们是从孟子潜存的本质发展出来的存在固可。但从潜存到存在,路程这么遥远,如果没有理学家的努力,很难想象它们的潜存会发展成什么样子。我们不妨想想:很多优秀的学者主张过康德很接近孟子,但康德的性命与天道却从来不贯通,为什么?
[1]高攀龙.三时记[M].//高子遗书:卷10.台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商务印书馆,1983.618.
[2]杨儒宾.儒家身体观[M].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所,1996.364-365.
[3]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4]王畿.王龙溪语录[M].台北:广文书局,1977.
[5]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18[M].//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204.
[6]李明辉.康德伦理学与孟子道德思考之重建[M].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所,1994.45-57.
[7]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Z].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8]牟宗三.圆善论[M].台北:学生书局,1985.133.
[9]孟安排.道教义枢·道性义第二十九[Z].//正统道藏:册41.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77.809.
(责任编辑:朱晓江)
How“Xing-Ming”isConnectedto“Tian-Tao” ——OnNeo-Confucians’sTransformationofMencius’CrucialConcepts
YANG Ru-bi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Tsing Hua University, Hsinchu 30013)
The main theme of Neo-Confucianism is about Tian-Dao (天道) and Xing-Ming (性命). Tian-Dao is a term of metaphysics, while Xing-Ming is a term of the mind-nature theory (心性论) and is more radical than the former. The Neo-Confucians thought their source of the mind-nature theory wasMencius, and they had both documental and philosophical reasons for this assertion. But I think the Neo-Confucians had transformed the meaning ofMenciuswhen they thought they had acquired the validity from this book. In this article, I will center onMencius’ two crucial concepts——“goodness of nature” (性善) and Liang-Zhi (良知), and show that these words which the Neo-Confucians expanded metaphysically so as to make connection between Tian-Dao and Xing-Ming were simply terms of the mind-nature theory initially. This transformation could be seen as a manifestation of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words, and a leap that went far beyond their original meanings.
Mencius; Neo-Confucianism; Liang-Zhi; goodness of nature; Xing-Ming—Tian-Dao
2009-12-10
杨儒宾(1956-),男,台湾台中人,新竹清华大学中国语文学系教授,台湾大学中国文学博士。
B222.5;B248.2
A
1674-2338(2010)01-00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