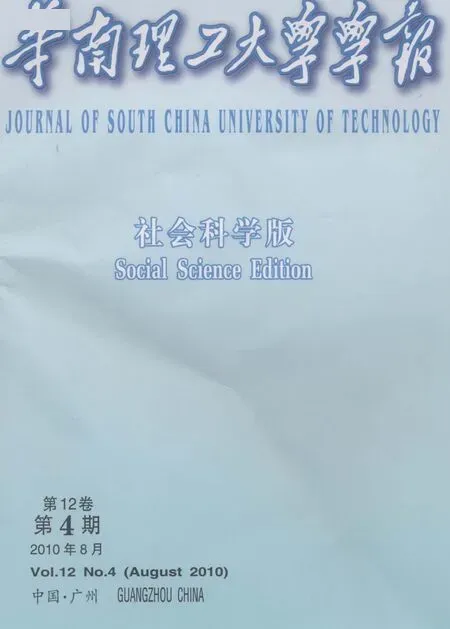胡登跳与丝弦五重奏
沈云芳
(华南理工大学 艺术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40)
丝弦五重奏是由上海音乐学院教授、 作曲家、 民族音乐家、 教育家胡登跳先生①胡登跳先生是上海音乐学院的教授、 作曲家、 民族音乐家、 教育家。一生创作了近200首音乐作品, 主要以中国民族器乐为主; 写作、 发表的论文近20余篇。1982年出版的专著《民族管弦乐法》是我国第一部有关民乐配器方面的著作, 至今仍是民族器乐配器、 写作的权威参照之一。他先后培养了一批民族音乐理论和作曲人才, 如唐朴林、 何昌林、 阎惠昌、 陆在易、 周仲康、 徐坚强等。胡登跳数十年来共获各种奖励19项。1991年受到国务院“为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做出突出贡献”表彰, 享受国务院批准的政府特殊津贴。确立的一种新型民族器乐重奏形式, 同时也是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系师生长期艺术实践的成果。这种由二胡、 扬琴、 柳琴、 琵琶、 筝五件各具特色的丝弦乐器互相配合, 融合了中国传统小型合奏乐与西方重奏写作技巧, 充分发挥了民族乐器特有音色、 性能的民族器乐重奏形式, 既有中国传统的风格, 又具现代生活的气息, 既能表达高雅的意境, 又富有生动新颖的情趣。被誉为“像中国丝绸一样美妙的音乐”, “中国乐器能产生这样绝妙的效果令人难以置信”。②《丝弦女》(CD-0036 ISRC CN-E04-94-337-00/A·J6)唱片介绍, 1994年上海音像公司出版。
虽然丝弦五重奏以其独具特色的魅力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但是, 专门对此进行研究论述的文章并不多见。作为上个世纪七、 八十年代上海音乐学院和全国民族器乐(尤其是民族室内乐)领域中一件比较重要的事件和新型艺术品种, 人们对其关注与研究是不够的。站在历史的高度, 回顾丝弦五重奏发展路程, 觅寻胡登跳先生之民族室内乐创作踪迹, 发掘其存在价值, 不仅仅是一种历史的回味, 对于其后的民族器乐创作也是一种必要的理论积累, 将有着一定的启迪意义。丝弦五重奏产生在特有的历史时段, 有着特定的历史缘由, 其源头始于胡登跳于20世纪60年代创作并获成功的《田头练武》。
一、 丝弦五重奏的历史钩沉
(一)初期萌芽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 上海音乐学院为响应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 开展了一系列为工农兵服务的活动。1964年2月24日, 全院师生组成两个大队到金山、 奉贤两县参加为期70天的“四清”运动。胡登跳也随其中一队来到奉贤县庄行公社。由于大家分散在各个村庄, 来往不便, 为农民演出很难组成常规编制的乐队, 胡登跳借鉴了1960年“六边”活动中的民乐小合奏形式③1960年6月的“六边”活动中, 云贵分队中仅有的三名民族音乐系同学, 分别是二胡专业的吴之珉、 琵琶专业的叶绪然、 笛子专业的谭渭裕, 再加上管弦系一位会演奏扬琴的同学谭密子(长笛专业), 四个人组成了一个民乐小合奏组, 演出了广东音乐《连环扣》和张敦智根据少数民歌音调改编的作品《阿西里西》。同年7月中旬返校之后, 民乐小合奏组又到了广州、 深圳演出, 参加了上海之春、 纪念毛主席讲话等重大演出, 深受欢迎。, 选用了当时能够参加演出的二胡、 扬琴、 琵琶、 月琴和三弦等五种乐器, 创作了一首有感于当时农村生活的重奏曲《田头练武》(曾灌制成78转的唱片, 但文革期间被毁), 由周德明(扬琴)、 叶绪然(琵琶)、 张念冰(大三弦)、 梅雷森(月琴)、 吴之珉(二胡)五人演奏[注]由于1964、 65年全国人民都学习毛主席语录, 演出的曲目除了《田头练武》之外, 又增加了王久芳创作的《毛主席著作越读心越亮》。。作品出乎意料地受到农民和演奏者的热烈欢迎。一种新的民乐体裁——丝弦五重奏就这样萌生了, 但那时还只是称为民乐五重奏。
“四清”活动结束后, 重奏组返回上海演出, 作品和演出形式在城市中也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这深深地触动了胡登跳, 他感受到了具有深厚文化传统的民族丝弦乐器组成重奏有着极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可惜的是, 尚未待他仔细深入地去思考和研究, 历史进入了文革时期, 他被借调到上海京剧团进行样板戏的创作, 民乐五重奏暂时无暇顾及了。
(二)中期定型
1972年政治上略有松动, 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系的五位青年教师(吴之岷、 郭敏清、 张念冰、 孙文妍、 叶绪然)又聚在了一起, 自发地成立了民乐五重奏小组, 使得丝弦五重奏在一种不自觉的状态中重新开始萌芽。
任何一类音乐品种、 音乐体裁都必须要以一定的作品为依托。中国小型器乐合奏创作历来带有某种随意性, 要想形成一个新的不同于传统、 有着强大生命力的音乐类种, 必须要有作曲家的介入, 从其音色音响的诞生、 确立、 成型到发展, 作曲家的作用不可估量。民乐五重奏组首先面临的是演出的曲目问题。演奏家们根据自身演奏经验也曾即兴编配, 但都不尽如人意。于是, 演奏家们恳请已被调去样板戏《龙江颂》剧组工作的胡登跳为五重奏小组创作。在当时以样板戏为主导教材, 并以此作为检验教学方向重要依据的社会环境下, 胡登跳根据样板戏《龙江颂》中女主角的重点唱段“一轮红日照胸间”进行改编, 作品《一轮红日照胸间》(后更名为《晨曦抒怀》)用胡琴模仿唱腔, 乐曲简短动听, 政治上又无可挑剔。就这样, 这个被称为民乐五重奏的组合形式就在胡登跳先生和五位青年教师的共同努力下, 以一个长期固定的组合, 自然地在上海音乐学院扎下了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丝弦五重奏这一音乐类种的生命从此和胡登跳的名字连在了一起, 同息共存。
1976年, 民乐五重奏被文化部选入北京在中山音乐堂参加全国文艺调演, 演出在北京引起了轰动, 当时的文化部长于会泳还亲自接见了重奏组成员。这种新型艺术品种在音乐界备受推崇。这时, 胡登跳经过慎重考虑, 把“民乐五重奏”正式定名为“丝弦五重奏”。[注]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退休教师吴之岷口述回忆, 2006年11月21日吴老师接受采访, 详细讲述了丝弦五重奏的来龙去脉, 并提供丝弦五重奏演出剧照、 早期的乐谱等珍贵资料。这是个中西合璧的称谓, 后缀“五重奏”源自西方室内乐概念, “丝弦”既概括了五件演奏乐器的属性, 又在本民族的传承史上续延了中国音乐史上古已有之的丝弦乐演奏形式。作品在创作手法上, 亦是中西互融, 既深植于传统沃土, 又使得西方室内乐的写作技巧成为其横向的参照借鉴。
(三)兴盛阶段
文革结束后, 胡登跳重新回到上海音乐学院。他潜心学习、 研究民族民间音乐, 创作了大量风格多样的丝弦五重奏作品。逐渐, 丝弦五重奏进入了其鼎盛的黄金时期。
1979至1981年, 胡登跳陆续创作完成了丝弦五重奏系列作品——《回忆》、 《欢乐的夜晚》、 《思念》、 《畅想》。尤其《欢乐的夜晚》演出次数最多、 演出效果极佳, 经常作为返场曲目演奏。1984年文化部在“第三届全国音乐作品评奖”之际, 授予《欢乐的夜晚》特别荣誉奖。1980年胡登跳根据古琴曲改编而成的《阳关三叠》, 于1984年由专家会议审议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联合编制音乐教材。
1982年他根据叶栋破译的敦煌曲谱改编创作《长沙女引》和《又慢曲子西江月》。1986年创作《跃龙》获全国第六届音乐作品(比赛)三等奖, 1992年评选二十世纪华人音乐经典时, 《跃龙》作为唯一的一首民族器乐重奏曲入选。
丝弦五重奏影响愈来愈大, 从上海、 北京延伸到全国, 甚至蜚声海外。胡登跳亲自培养的重奏组多次赴日本、 南斯拉夫、 美国、 荷兰、 比利时等国家访问演出。受到了不同肤色民族的欢迎。五重奏获得了音乐界的高度认同, 同时又受到社会大众的欢迎, 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极富效果的民族器乐节目之一。北京、 南京、 杭州、 合肥、 济南、 昆明、 重庆等国内一些城市以及海外新加坡、 香港的一些艺术院校、 民乐团体亦先后排练这些作品, 进行公演或出国访问。民族乐坛出现了各方竞奏“丝弦五重奏”的情景。
二、 胡登跳对丝弦五重奏的历史贡献
如果说丝弦五重奏的最初诞生是一次历史机缘, 胡登跳先生因时因地因材、 在无法选择的境况下创作了第一首丝弦五重奏作品《田头练武》, 那么, 丝弦五重奏后来的定型、 发展、 乃至流传海内外, 却因了这个历史的偶然。胡登跳厚实的民族音乐素养与西方音乐学养的碰撞, 以及对于发展民族音乐的志向和理想, 赋予了丝弦五重奏以灵动的气韵, 使得丝弦五重奏的成功成为偶然境况下的必然结果。
胡登跳首先在乐器的性能及其组合问题上进行认真细致的研究。1976年丝弦五重奏定型之前, 胡登跳曾考虑和调试过其它的乐器组合, 作过各种变化。如70年代他在为上海电台少儿广播乐队排练指导时, 曾以大提琴替代过古筝, 作品《喂鸡》以及《映山红》初稿所用编制即是二胡、 扬琴、 琵琶、 柳琴、 大提琴。[注]2007年3月笔者采访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卢建业老师(当年卢建业老师曾在上海电台少儿广播乐队任指挥), 由卢建业老师口述回忆。又如《霓裳曲》(1981年《中国音乐》第四期发表了此曲谱)中, 尝试用过箫、 琵琶、 扬琴、 二胡、 大胡的组合方式等。最后, 确定采用二胡(可变通用高胡、 京胡等)、 扬琴、 中阮(柳琴)、 琵琶、 古筝等五件乐器的固定组合。这五件乐器所构成的音域宽广, 从古筝最低音D到柳琴最高音g4, 跨五个八度以上, 提供了广阔的写作空间。通过古筝低音区的运用, 弥补合奏中低音之不足, 获取音响效果之平衡。再从音响色彩方面考虑, 五件乐器中, 二胡是唯一的拉弦乐器, 它具有柔美、 圆润的“线状”音色; 其余四件均为弹拨乐器, 琵琶明澈、 中阮淳朴、 柳琴亮丽、 古筝浑厚、 扬琴清亮, 它们都具有灵巧的、 坚实的“点状”音色。不同音色相互辉映, 点、 线交相互补, 可幻化出绚丽多彩的音响效果。在五者之中, 扬琴相对个性稍弱, 但刚柔并济, 擅长演奏和音, 长时间的余音, 令其可制造出片状的色彩, 因此它的协调能力强, 在乐器之间起着融合剂的作用。而且, 胡登跳选择的是当时研制改良的十二平均律扬琴,[注]由原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系教师洪圣茂在20世纪80年代研制改良。半音演奏技法可得以灵活运用。这样, 五件乐器在声部的纵横交织中, 既可尽情发挥各自的独特个性, 又可勾勒出立体的多层次色彩。
丝弦五重奏是传统小型合奏乐的新型延伸, 如何利用传统的乐器组合阐发出不同于传统且高于传统的更为丰富的表现力, 织体语言的表现手法显得尤为重要。胡登跳充分考虑到了中国传统小型合奏乐的各种形式、 手法, 精心研究了民间的丝竹乐和弦索乐。除了在乐器组合表层上与弦索乐有着某种共性, 丝弦五重奏又从弦索乐、 江南丝竹、 广东音乐等合奏乐的乐器性能表现、 组合织体中汲取更深层的养分, 借鉴传统并加以发展和延伸。在以中国传统弦索乐和丝竹乐作为传统承载源的同时, 胡登跳又大胆融入西方作曲的和声、 复调技法, 使得丝弦五重奏的声部线条变得复杂、 生动。
由于产生于特殊时代, 丝弦五重奏早期作品受当时社会大环境的影响, 所表现的主题内容和素材与时代紧紧相扣, 作品较活跃地反映了当时的时代情绪和群众心理。在样板戏替代一切音乐的年代, 胡登跳根据《龙江颂》唱段改编了《一轮红日照胸间》、 《让青春焕发革命光芒》、 《让革命的红旗插遍四方》等,[1]巧妙地将样板戏的音乐素材用于丝弦五重奏中, 把那个年代特有的“激情”融于活泼朝气的民族器乐重奏形式中。他根据20世纪70年代的“流行歌曲”——电影《闪闪的红星》插曲改编《望北斗》和《映山红》。10来年间, 他还改编了《喂鸡》、 《加快步伐朝前走》、 《白毛女》等作品。这些改编类作品为丝弦五重奏的创作积累下了颇为丰厚的经验。
在特定的时代里, 胡登跳不得不选择一些和那个年代相关的歌曲进行改编, 但是他从未停止过对艺术创新的探索, 因为他认为“任何艺术品种, 没有新的创作, 就谈不上发展”。[2]1979至1981年, 胡登跳创作完成了《回忆》、 《欢乐的夜晚》、 《思念》、 《畅想》四首作品。这组乐曲的诞生使丝弦五重奏进入了一个创作的新阶段, 改变了之前以改编为主的格局, 四首作品分别蕴含了作曲家回忆往昔、 欢欣今日、 思念故者和寄想明天等四种思绪, 人一生的悲苦欢欣在曲中尽阅无遗, 因此, 曾经有人说这四首乐曲构成的是一部组曲。[注]在常受宗的“民族器乐演奏的新形式——介绍胡登跳的几首丝弦五重奏曲”(《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1981年第3期)和周瑞康的“民族乐苑的重奏之花——胡登跳和他的‘丝弦五重奏’”(《音乐爱好者》1987年第2期)文章中, 都认为这四首作品是一部组曲。虽然它们在内容上的确寄托了相互连贯的四种情绪, 但是从音乐结构、 甚至演奏上却并不太具有组曲的特征, 人们在谱面和舞台上常常看到的仍然是独立演奏的四首乐曲。
1986年胡登跳为纪念青年时代的母校——浙江宁海中学校庆六十周年而创作的《跃龙》是丝弦五重奏创作的又一个突破和制高点。宁海城南有一座跃龙山, 山下有个神龙潭, 传说中的神龙往来其间, 留下多少美丽的传说……作品即以此展开无限的遐思, 采用其家乡面临消亡的稀有剧种“宁海平调”的音乐为素材, 描写了跃龙山秀丽的景色, 抒发对故乡先辈的感念之情。曲中大胆地使用了神秘、 激烈的堂鼓鼓点和飘忽、 奇幻的女声哼唱。二度的横向进行和纵向的和音迭置贯穿始终, 结合自由散奏、 调性迭合以及乐器的各种奏法等, 既呈现出古老戏曲的遗风余韵, 又散发出时代的气息。
在创作的素材和题材方面, 胡登跳汲取古、 今、 中、 外各方面之精华编创、 发展“丝弦五重奏”。他根据根据古琴曲、 叶栋解译的敦煌乐曲分别改编成《阳关三叠》、 《长沙女引》、 《又慢曲子西江月》, 意境悠远又不失古风。他把加拿大歌曲《清晨的雨》、 匈牙利作曲家巴托克的小曲三首——《卡农》、 《笛曲》、 《狂想曲》等外国音乐, 移植成丝弦五重奏, 赋予异国曲调以全新的生命力、 表现力和盎然的生机情趣; 他还曾帮助电子琴演奏家浦琪璋一起把琵琶曲《天山之春》、 南斯拉夫歌曲《啊, 朋友》作配器修整。20世纪90年代, 胡登跳身体每况愈下。中风以后, 他还倚靠在病床上, 用左手一字一音地把传统乐曲《步步高》、 《二泉映月》、 《夜深沉》、 《春江花月夜》、 《阳春白雪》、 《光明行》、 《平湖秋月》、 《渔舟唱晚》、 《霓裳曲》、 《三六》等改编为丝弦五重奏。这些作品都不是简单、 浮浅的曲调挪用, 而是紧紧把握原曲的“神”和“意”, 给予新的创意。
丝弦五重奏创作确立了胡登跳的艺术语言, 无论旋律、 音色、 织体、 结构布局等方面都形成了一种只属于他的特有的创作语言,[注]关于胡登跳具体的作品分析, 将另有文章专门进行阐述, 为免重复, 这里不加展开。其作品深深地烙上了他对于中国民族器乐音乐的独特的创作观念和审美情趣。
三、 丝弦五重奏创作的现代启迪
胡登跳丝弦五重奏的初期创作, 如《田头练武》、 《一轮红日照胸间》(即《晨曦抒怀》)等作品虽然有着深刻的时代烙印, 但却不失中国传统音乐的行腔韵味, 他用一种新的创作思维对传统乐器进行新的编配组合, 给予人全新的音乐感受, 辟寻和踏足于真正具有重奏意义的民族室内乐创作之途。在其后来的创作中, 政治性因素被逐渐抛开, 他更加追求传统音乐之神韵, 恰到好处地发挥每一件乐器的个性、 音色, 又不断尝试、 追求新的音响、 新的创意, 且不留任何技术痕迹, 通过缜密的艺术思维、 强烈的创新意识, 更大幅度地拓展五重奏的表现力, 如《欢乐的夜晚》、 《跃龙》等作品细腻、 精致, 音响奇特又具有时代气息, 显示出了其自身的艺术品位。
胡登跳的丝弦五重奏创作中, 始终浸透、 渲染着简单、 简洁而又发人深省的三个字——“土、 新、 情”, 这是他创作的元特征, 也是至今仍可适用于中国作曲家所借鉴的创作理念。
自小受家乡乡土音乐熏染的胡登跳, 中国本土民间音乐早已深深地溶入其音乐之中。大学校园里, 他在接受过西方音乐及其理论严格训练的同时, 更激发了他要振兴中国民族音乐, 要让中国的民族音乐有朝一日能屹立于世界艺术之林的志向。[3]基于这样一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意识, “土”的创作理念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 他的作品中扑面即来的自是传统音乐文化的意蕴气息。
“土”, “中乐作品要有土味”,[4]要富于中国民族风格。“土”常被人理解为土气, 某种程度上带有几分藐视的意味, 但是只有“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 但是乡下, ‘土’是他们的命根”。[5]正因为有了土的滋养, 才有了“脸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业, 才有了中国人生生不息的传统文化根源。
在音乐艺术表现中, 乐器是一种音乐文化特质、 风格的承载工具, 胡登跳认为, 要“一头扎进祖国大地, 滚上一身泥巴”, 民间乐器中有代表性的传统演奏特技必须要去了解、 学习而后传承下去。“乐器的演奏与作品的风格关系更大。同一旋律, 可能通过不同的演奏, 表现不同的风格。如果要中乐作品表现出土味, 就必须重视民间的演奏技艺”。[4]他深谙中国乐器的演奏法, 充分发挥五件乐器的各种演奏技巧; 他洞悉每件乐器的性能, 细微到每件乐器在不同的部位、 不同音域能发出怎样不同的音响效果; 他不断地研究、 探索中国本土的民族配器法, 非常讲究把五件乐器极好地融合成一个有机整体, 与此同时又充分展示、 升华、 张扬出每件乐器各具魅力的独特个性, 承继、 发展着中国音乐一贯追求丰富幻变、 细致入微的音色变化。
中国音乐在旋律音调、 主题发展、 节奏律动、 谋篇布局、 审美情趣等方面都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叙事方式和创作、 表现意识。胡登跳熟悉且钟情于这些传统的音乐表达方式, 在他的丝弦五重奏创作中到处可觅寻到这些踪迹, 它们有时是明显的, 有时又是隐匿的。从其细部来看, 作品旋律大都曲调清新, 极具传统的五声风貌, 作曲家常常通过民间“隔凡”的手法不露痕迹地变换旋律的宫调, 民间音乐常见的合头换尾、 合尾换头、 鱼咬尾、 加花变奏、 紧缩简化、 衍展等旋法在主题发展过程中运用自如, 民间打击乐丰富多变的节奏和戏曲的元素等在胡登跳用来就如同从记忆的布袋里探囊取物。从宏观布局来看, 丝弦五重奏的作品结构非常精到, 中国民间吹打音乐、 文人音乐等常用的结构安排被悄然引入, 隐藏于貌似西方音乐作品的曲式结构框内。作家老舍在创作《龙须沟》时曾说: “一个作家, 他箱子里存的做成的或还没有做成的衣服越多, 他的本事就越大。……他的箱子越阔, 他就游刃有余, 箱子里贫乏, 他就捉襟见肘”。[3]胡登跳就是这样一位拥有着一个“大箱子”的作曲家, 他的“大箱子”里装着他对传统的理解和关爱, 所以他灵活自如地游走在本民族的风土当中。胡登跳从音乐本体的主观表达方式和音乐的客观彰显手段上阐述了他的“土”, 自身亦亲力亲为地印证了他的“土”。
“土”所对应的传统并不仅仅意味着守旧、 陈腐, 传统是“流”而不只是“源”, “中国民族的历史, 就是一部不断创新的历史。”[4]艺术之道贵在创新, 没有创新的艺术是不具备灵动的生命活力的。“新”, 就是要追求变, 追求时代气息、 现代感, 作品须带给人以新颖的美感。
胡登跳的丝弦五重奏改变早前中国合奏音乐单线条为主的织体状况, 代之以多线条、 多层次的立体构筑, 在和声、 结构甚至是主题动机的展开等方面运用西方的手法, 将中国音乐的元素巧妙地融合, 既没有特别浓重的西方音乐痕迹, 亦没有中西两者硬性的拼贴。他在充分调动、 发挥五件乐器传统的常规演奏技巧, 还根据音乐情绪的需要拓展出一些新型的、 非常规的演奏法, 如扬琴击面板、 扦尾拨弦、 摘音(一手捏弦、 一手持竹拨弦), 琵琶拍面板, 柳琴拨奏琴码下方第三弦、 二胡弓杆击琴筒等, 与传统奏法产生的乐音效果, 形成对比。“拍、 击”等非乐音的出现, 体现了作曲家在民族器乐重奏创作上大胆的创新意识。特殊演奏技法的添入, 使得乐器不但能奏出旋律音, 又能奏出节奏音, 极大地拓宽了演奏技法。他充分拓展了原有乐器的极限音区、 音域和非乐音, 如扬琴用双竹来回敲击码外琴弦, 这些码外音由高往低, 没有准确的音高, 只有大致的音域范围; 又如用柳琴拨奏琴码下方第三弦, 奏出极限音高。作曲家寻求极限的音高、 音域, 织造新颖、 独特的音色变化, 极大地发掘了乐器潜在的丰富色彩。有时, 乐器在演奏时只给出一个高音点和一个低音点的大致范围, 任由它们各自由低至高, 又由高至低地来回游走, 充满了随机自由意味的不确定音高进行。有时他又用某种新的方式将传统演奏技法整合, 或在五重奏中别出心裁地吸收戏曲中的帮腔, 加入人声、 大鼓等“编外乐器”, 不断拓展出新的音源、 新的音效。
同时, 他把握着一条最为平常亦是最易为人所忽视的原则, 即创新要有度, “尊重听众的欣赏习惯和接受程度”, “掌握出新的比重”。“音乐创作这种精神生产, 有时比化学反应还要神奇。土的洋的、 新的旧的, 会在一定条件下互为转化。在中国风格的前提下, 创新不否定传统, 有时反而能强化传统。传统在创新中不断丰富。传统与创新是现代中国风格不可缺的一对支柱”。[4]胡登跳通过他的创作将传统的元素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同时又为民族器乐重奏的发展提供了思路。
对于“情”, 胡登跳主张秉承中国音乐创作的传统——“寄情于乐”, 这“是中国音乐创作的传统, 中国风格的中乐作品应该继承这个传统”。[4]中国古代画论说: “情乃诗之胚” , 《文心雕龙》作者刘勰说: “繁采寡情, 味之必淡”。只有将技术与情感相融合, 才会创造出独特的佳作。“音乐创作是作者创作时理性思维与感性思维、 艺术思维与感情抒发反复交替结合的产物。……”。[4]这就意味着“情”的表达要真诚无伪, 《乐记·乐象》说: “是故情深而文明, 气盛而化神, 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 唯乐不可以为伪。”丝弦五重奏每一首作品, 如《田头练武》的英姿勃发, 《回忆》、 《思念》的深情、 沉痛, 《欢乐的夜晚》的欢腾雀跃, 《跃龙》的遐思、 对先祖的感念等, 无一不是胡登跳心灵的真情流露, 因为, 只有深切真挚的情感才能产生感人至深的作品, 在作品的表达内容上要“出情”, 才能更富有中国的艺术神韵。
胡登跳一生留下的文字不多, “土·新·情——我对中乐作品中关于中国风格的认识”这篇文章是他一生艺术创作中十分重要的文献资料, 简洁、 朴实的三个字却蕴含极深, 最能体现他的艺术创作理念, 是其对自己创造思维的一个集中剖析。作曲家真实的原话最能印证其创作。胡登跳始终遵循恪守着土、 新、 情三者相结合, 外形与内涵相统一的原则, 力求完美地表现具有现代气息的中国音乐风格。他的作品雅俗共赏, 从来不是蜗居在金字塔里, 追求一种时髦或者纯粹的技巧, 从来不远离大众、 远离传统, 他创作的“丝弦五重奏”的音乐语汇策应了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审美听觉情趣, 既保存了传统音乐旋律语汇的精髓, 又不拘一格。在传统中追求变化、 追求突破!
如今, 人们欣喜地看到民族器乐正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的各种可能, 与此同时, 回味胡登跳创作的元特征, 忆想当年丝弦五重奏带来的振奋, 其中之含蕴仍然是值得人们不断深思的, 人们在接纳当代音乐的同时, 如何继承传统、 拓新传统、 在出新中尽抒己风, 或许也就是胡登跳留给后人的重要启迪和深刻之课题。
参考文献:
[1] 周瑞康. 民族乐苑的重奏之花——胡登跳和他的“丝弦五重奏” [J]. 音乐爱好者, 1987(2): 10—11.
[2] 胡登跳. 青出于蓝 后来居上——观第二届海内外江南丝竹创作与演奏比赛 [J]. 人民音乐, 1993(3): 10—11.
[3] 熊军. 民族音乐家胡登跳 [J].上海滩, 1987(10): 17—19.
[4] 胡登跳. 土·新·情——我对中乐作品中关于中国风格的认识 [J]. 人民音乐, 1989(3): 2— 4.
[5] 费孝通.乡土中国: 乡土本色 [EB/OL].(2005-04-26)[2008-03-20] http://book.sina.com.cn/excerpt/2005-04-26/114118384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