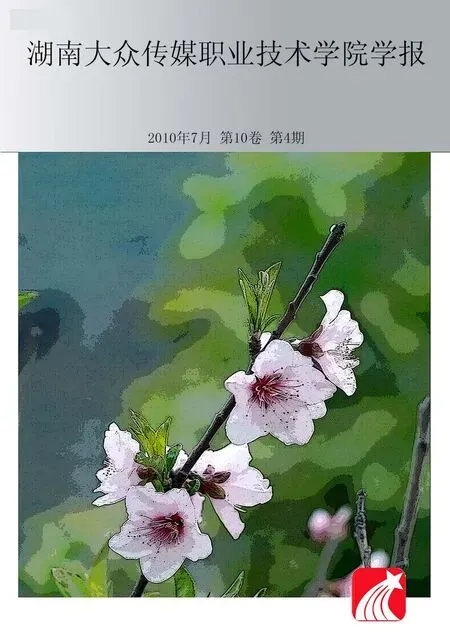“被网络红人”现象浅析
禹雄华 马 杰
(1,2. 湖南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一、“网络红人”与“被网络红人”
说到“网络红人”,另一个角色是不能不提的——“网络推手”,也称网络营销策划师、网络推客,有些人也称之为网络公关。他们对网络技术运用娴熟,深谙网络受众的心理,有的甚至是网络把关人,其中也不乏运用自己的独特角色和在网络中的权限来炒作某些人或者事物,以达到某种利益之人。“网络红人”的出现与“网络推手”有紧密的联系。如果从“网络红人”与“网络推手”的联系来看,“网络红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自己推自己的“网络红人”,实质是“网络红人”与“网络推手”两个角色的合一,如痞子蔡、安妮宝贝、慕容雪村等等。他们都是网络写手,借助网络推广自己另类的写作风格和突出的写作才华。另一类是“网络推手”为寻求利益而操作网络舆论,从正面或负面将炒作对象设置为网络舆论里的主导议程使之“红”,再借助传统媒体的“翻炒”使议程扩大化,从而打造出的“网络红人”。
但随着“网络狂欢”现象的盛行,对于推手推出的所谓或美或丑的“网络红人”,大众的免疫心理越来越强。除了“看太多”的理由,还因为大众摆正了自己的位置,以前总以为自己是在“看”,后来才发现原来自己也是“被看”的对象,转而回归到初始的寻求魅惑的心理。像“犀利哥”、贾君鹏等现象的出现就是此种心理的明显体现。猫扑网的一个帖子,使得原不知姓名的乞丐成了网民们津津乐道的“犀利哥”,他的混搭照片甚至与国际品牌的服饰相联系,国外媒体都予以报道;魔兽论坛的一声“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去吃饭”引出了无数的“贾君鹏家人”和无数类似“某某,你某某喊你做某某事”的话语。正是网民心理回归,使得“犀利哥”这样的乞丐和贾君鹏这样不知名的人物被网络“红”了一把。但“被网络红人”并非与“网络红人”相对应的被动式,他们不是“网络推手”的杰作,而是网民猎奇心理与网络造星运动集体无意识的产物。社会人本身就有寻求魅惑的心理,而在现代社会,电子图像的大规模生产和网络的出现,以及网络匿名性、去中心化等特征,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更私隐的寻求魅惑的方式。
二、“被网络红人”出现的必然性
正如樊葵在《媒介崇拜论》中所说:“现代偶像不再有主宰人类命运的无边威力,他们只是人们世俗生活的一种心灵寄托。”[1]与其他大众媒介相比,网络中的每一个网民是这张巨网的一个独立的结点,现代生活的快节奏、大压力、重秩序使得他们越来越依赖这个属于自己的自在空间、虚拟世界。“网络红人”是现代造星运动产物中的一种。从各种“网络红人”、“被网络红人”来看,无论是芙蓉姐姐带来的审丑风潮,还是天仙妹妹的美丽情结,亦或是“犀利哥”的另类特质,对未曾谋面的贾君鹏的呼喊所带来的童年回忆,此种造星与网络嫁接的结果,就是樊葵所说的典型的世俗生活的心灵寄托。
“魅惑”这个词不仅包含着感官上的刺激,也包含着心灵的沉迷,强调瞬间的销魂,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在一般人的理解中,它总与堕落、越轨等相联系,常包含着令人不齿的意义。如果按照通常的贬义理解,将它与文化活动相联系,势必引起人们的高度戒备,或者被定势思维一棍子打死。而今天,我们应该理性地思考“魅惑”的意义,思考其与“被网络红人”的深层联系,所以,被魅惑并不一定意味着堕落。
在《网络研究 数字化时代媒介研究的重新定向》一书中,作者戴维·网特利特将当代的网络浏览的网民心理研究与19世纪初美国的“畸形人表演”相联系,认为二者并非毫不相关。他总结出此二种现象的产生都依托于人们对于差异或者“和自己不同的人”的好奇心理,即实质上的被魅惑心理。网民们在网络虚拟世界中遨游,是通过在一个媒介即电脑屏幕上独自浏览网页完成的,因而此时他们可以摆脱社会群体对个体行为、道德的约束,也不必对观看的对象负责,可以挣脱世俗规制,自在地寻求被魅惑,毫无顾忌地“看”。从另一层意义上来说,技术拓展了人们寻求魅惑的空间,感受魅惑在网络中变成了一件个人化的事情,魅惑的世界变得电脑化了。
“被网络红人”正是这种被魅惑心理的产物。网络为网民提供了一个寻找的平台。一种情况是,网民从“被网络红人”身上寻找其与自己的差异,即猎奇心理,“犀利哥”现象就是此种心态的例证。一个平凡的乞丐混搭着各类服装和配饰行走在大街上,在生活的世俗规制中,人们对他顶多是“多看两眼”,而网络世界中没有那么多世俗规制,不用负责的心理使得魅惑无限扩大化,因而“犀利哥”成为网络上的英雄式人物。在现代生活中,相互魅惑成为文化生活的主要模式,此模式造就了寻求魅惑的第二种情况,即当一个人着迷于与他不同的事物的时候,实际上他是在对方身上寻找自我。“某某某,你妈妈喊你回去吃饭了”这句幼时在我们耳边经常响起的一句话,让网民们找回了丢失很久的“小时候的感觉”。“魅惑的瞬间,人们所感叹的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而是人类共性以及与他人暂时的接近感。”[2]在现代快节奏的生活中,一种遥远而熟悉的感觉突然袭来,使网络狂欢有了新的由头,于是乎感情在虚拟世界中泛滥,一时间该呼喊的衔生话语铺天盖地而来。
三、“被网络红人”现象的伦理反思及对策
“被网络红人”现象与“网络红人”现象一样滋生于网络媒体,并对传统媒体和现实社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尤其给人们带来了关于此现象的伦理反思。
(一)网络责任意识进一步淡化
“被网络红人”虽然少了“网络红人”那种为了“红”而不择手段的功利性和不惜自我贬低的个体本位价值观,但是推动其产生的网民随心所欲地“看”和“想看”的心理助长了网络中本来就缺乏的责任意识。网络的独立性和匿名性,使网民和生产者分离,观众不用对被看的对象负责任,由此而来的后果是没有自律心理的网络脱离了现实社会伦理道德的约束,网民可以肆无忌惮地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寻找到要窥伺的东西。这种易得性和不用负责的心理让寻求魅惑的初衷无限蔓延。虽然笔者在前文中强调寻求魅惑并不意味着堕落,但是寻求被魅惑心理和偷窥癖在网络中的“彼此不分”,使得网民的责任意识更加淡薄,成为网络正常秩序的隐患。
(二)对主流价值观的挑战
目前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再加上全球化的影响,各社会成员和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格局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利益多元化很可能带来认知错位,以及不同程度的认同危机和信仰迷茫。由于青年期是各种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定性阶段,因而这种现象在青年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在网络的无中心、无边缘特质的影响下,青年群体的“过渡人”、“边缘人”心理比传统社会持续的时间更长。
求新求异和寻求欲望满足是网民心理的两大特点。形形色色的“网络红人”正是“网络推手”利用网民的各种价值判断标准推出来的,而“被网络红人”则是网民各种价值判断在网络中的体现。“犀利哥”、“雪碧哥”、“深邃哥”等人的美丑优劣在个人的价值判断中各有不同,但是在“被网络”后他们都“红”了,这其中就包含着青年网民价值判断迷茫的因素。这些不被主流价值所推崇的事物,在现实社会中本不为人重视,进入网络世界后,这种非主流价值观扩大化,对现实的主流价值观构成挑战。“犀利哥”出现之后,“雪碧哥”、“深邃哥”等一系列乞丐曝光于网络,这从表象上看是“无聊”的,但是随意曝光各类非主流价值观所推崇的人物,有可能导致按这种惯性的A哥B哥不断出现。这样,社会法制与社会道德的神经,也就很快会被所谓的“好玩”、“新奇”给麻痹掉。
(三)“被网络红人”与隐私、人肉搜索
“被网络红人”一开始的“被”字辈现象就意味着这其中诉说的对象并非是自愿的。“被网络红人”有的本身就是人肉搜索的产物,有的在成为网民关注的热点后也逃离不了被人肉搜索的命运。应该注意的是,人肉搜索这种现象本身就在隐私权和伦理上有不合理的地方,“被网络红人”与其的密切关系必然存在着伦理方面的问题。“犀利哥”在被人肉搜索后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关心,找到了亲人,也回了家。但有人私自拍摄“犀利哥”与家人的视频并传到网上,还在网上发布很多不实消息,让“犀利哥”与其家人受到了很大伤害。另一个悲剧式的“被网络红人”是贾君鹏,被人肉搜索后的贾君鹏一家受到诸多骚扰,给他们造成很大的精神压力。贾君鹏本人更是严重失眠,最后因疲劳驾驶失去生命。
媒介作为社会瞭望者、舆论引导者,在倡导社会核心价值观上起着巨大的作用。尤其在我国,媒介一直以来就是“党的喉舌、人民的喉舌”。而网络的低门槛和把关不严,是造成网民价值判断多元化、隐私权被侵犯的直接原因,网众自我把关能力低则是责任意识淡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受到挑战的深层原因。目前,我国加强网络言论管理确有一定难度,但在国家和相关部门的努力下,网站注册进一步规范,网络实名制也呼之欲出,网络环境监测有了改善,进一步要做的是提升网众的媒介素养。“被网络红人”是网民自身力量的体现,而“被网络红人”的质量参差不齐就是网民的判断力出了问题。网络已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学会怎样在虚拟世界里判断好坏和甄别真假是全体网民的必修课,尤其是甄别力尚不完备的青少年的必修课。
四、“被现象”中的有幸与无奈
从“被自杀”、“被离婚”到“被小康”、“被就业”等,如今“被现象”泛滥,这些加了“被”字前缀的公共舆论词汇主要产生于网络,并且总是能够引起一定的社会共鸣。原因就在于他们“被”的无奈中或强或弱地反映出某种较为普遍的社会情绪,何况网络本来就是网民的舆论宣泄处。这些“被现象”的共同点就是,当事人在不情愿、不知情的情况下,而被人强加造成了某种事实,所以往往会对当事人产生不公、不利甚至伤害。“被网络红人”就是当事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网络”了,而且“红”了。
梅洛维茨的媒介情境论认为电子媒介能促成原来不同情境的合并,尤其是在有了网络之后,视频、音频、图片等技术让很多的私人情境变成公共情境。一旦现实情境被搬上网络情境,就会被无限扩大。“被网络红人”作为一种“被现象”,当其现实情境中的许多负面信息被搬上网络之后,反响相当大。从“犀利哥”和贾君鹏“红”了之后的经济收益来看,“被网络红人”在“被现象”中算是很有幸的,毕竟仍有很多人竞相成为“网络红人”。
[参考文献]
[1] 樊葵. 媒介崇拜伦:现代人与大众媒介的异态关系[M].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 188.
[2] David Gaultett. 网络研究 数字化时代媒介研究的重新定向[M]. 彭兰,译. 北京:新华社出版社,2004: 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