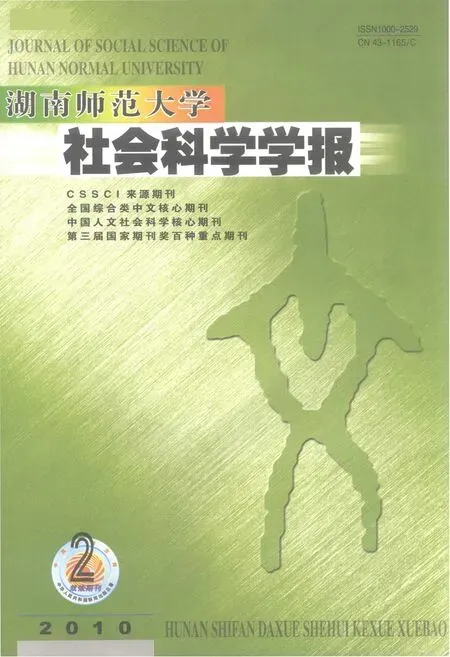探求死亡伦理
张怀承,姚站军
(湖南师范大学 道德文化研究中心,湖南 长沙 410081)
探求死亡伦理
张怀承,姚站军
(湖南师范大学 道德文化研究中心,湖南 长沙 410081)
死亡伦理研究刚刚兴起,相对而言环境伦理已较成熟,我们可以受后者的研究思路启发来探求前者,立足存在的人类在自然之思的深层价值面上便产生了环境伦理,立足在世的人类在死亡之思的深层价值面上对应有了死亡伦理。在从出生到临终的人生旅途中,我们无时不能缺少对生命的伦理关怀,甚至生命的终止(死亡)之时或死亡之后,这种伦理的关怀仍在我们关注的视域之中。
死亡伦理;生命拓展;生命超越;生命境界
一、从“环境伦理”到“死亡伦理”——生命拓展的哲学情怀
对于生存的人类自我而言从空间意义上说是与存在的自然环境相对,我们通常从主体与客体的两分来理解;立足存在的人类在自然之思的深层价值面上便产生了环境哲学和环境伦理。而对于生存的人类自我从时间维而言是与人类的消亡即死亡的人类应对,我们一般从今生与来世的两分来剖解,立足在世的人类在死亡之思的深层价值面上对应地有了死亡哲学和死亡伦理。人类在发展史上经历着由自我的生的关注到非我的生的关注;由自我的生的关注到自我的死的关注。在环境伦理中的主旨是人类应对非人类之物讲道义、讲道德,“非人类”本身具有某种重要价值值得敬尊,特别是环境伦理学中时下的主流学派“自然中心论”者认为自然不仅对人类具有手段价值或工具价值,而且具有自身的“内在价值”或“固有价值”,与人类具有同等地位的“目的价值”或“终极价值”。在死亡伦理中我们也不妨借助类似的思路去探索人类的生存是否应对人类的死亡讲道德、讲道义,生人是否应对死人或者“临死人”、“准死人”、“垂死人”讲道德、讲道义?(当然死亡的标准以心脏停止跳动还是以脑死亡为底线尚在争议之中,也是死亡伦理研究的一个前期问题)。生者是否对死者有必要的道德义务和责任?死亡本身是否具有“内在价值”?死亡对于生存是否具有价值及这种价值仅仅是手段意义上的吗?人类的死亡是否对人类的生存还具有不局限于“工具价值”的意义?人的死亡是否与人的生存一样具有它的“目的价值”、“固有价值”或者说“死亡”本身就是某种“终极意义”的存在?
如果正如“自然中心论”者所承认的人类对自然有道义责任,非人类(自然)与人类一样具有值得关怀的道德地位、伦理内涵,那么这种义务和责任又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这种道德价值的认可又有何学理缘源和现实需要性、意义性呢?这种伦理价值在现实中又能否得以实现和普及推行,又会有多大的影响和效益?这样的相关的问题对于死亡伦理同样适用。死亡伦理首先考察的问题是人类的生存是否对死亡有伦理义务。
我们在这里主要关注的死亡伦理是狭义的理解,即关注人类的生存对人类自我的死亡这种关系;但是广义的死亡伦理还要关注人类的生存对人类以外的生命的死亡的关系,所以从这层面来看死亡伦理学,人类的生是研究的起点或出发点,而“非人类”的“死”和“人类”的“死”(总称“生命的死亡”)是研究的终点(对死亡中心论者来说)或者中点(对生存中心论来说)。从死亡的广义外延来看生命可分为生物的生命和非生物的生命,前者又可分为人的生命和非人的生命,对应人的生命的死亡与非人生物的生命死亡都是死亡伦理考察的对象,其他生命的死亡与人的生命的死亡在伦理意义上的值得敬畏的地位有别吗?如一个人为救一只心爱的狗而死与一只狗为救一位它忠诚的善良的人而死的伦理意义有何不同?而后者之说有我们常常所提到的诸如“产品生命周期”、“组织生命周期”。在这里提到的生命即非生物的生命;在这种生命界定的理解上,万事万物的新陈代谢及“旧的不去,新的哪来”中“新”的来临即是“生”,“旧”的离去即为“死”,当然与死相对的“生”不仅包括生存的状态而且包括产生的过程和动作。死亡对于生而言从发展的内涵即旧事物的没亡和新事物的产生兴起看是必要的、也是合乎进步道义的,必要的死对于高质量的生具有神圣的义务和责任。当然生存对于无辜的死而言也是具有不可推御的道德责任。所以,死与生的伦理关系中具有复杂的二重性。我们随意可联想到对人类而言如果没有死亡的话,则地球上的人口只添不减则资源有限的地球将无法承载巨大的人口压力。另一个例子是如果一个谋财害命的杀人狂在一个社会中不受到谴责和惩罚,试想那样的社会还有伦理道德可言吗?
在生对于死应讲道德的论证中,认为生对于死仅具有工具手段价值的死亡伦理学派是“死亡中心论”者,而认为生对于死具有绝对目标、终极价值的死亡伦理学派是“生存中心论”者。关注生存与死亡的价值定位,重新审视生与死的道德关系是现代死亡伦理学的要务,但是死亡伦理的思想从古就有,中西皆有探索。传统的“生存中心论”者只是一味地追求生存的纵欲和宝贵的享受,而从来就忽视对死亡的尊重,对人生寿命的限制的尊重,最终过分地掠夺生存的生命资源,甚至超过了生命本身的自然承载力,到头影响了生存的状况,悄悄加速了死神的来临。因此生的时刻也不可完全忘掉死亡威胁的时刻存在,如平时饮食起居等都不可不注重养生之道,类似我们人类不能一味掠夺自然资源一样不能无端掠夺生命资源,死亡伦理要求不仅尊重生命的生活质量还要尊重生命的健康长寿。否则会如人类受到大自然灾难惩罚一样会受到轻则病重则死神的警告和制裁。
有鉴于上述不足,现代(弱式)“生存中心论”是在经历了“死亡中心论”对传统(强式)生存中心论的诘难反思之后的一种生存中心论。而“死亡中心论”者那里灵魂的尊贵度大大高于生命的肉体的尊贵度。死得伟大则意味着死亡是道德的。我们不能盲目地排斥死亡,否认死亡的价值,否认选择死亡的意义。有时对于死亡的选择不仅是其具有对于生存的更好意义,而且是为了人类更好地对死亡本身的尊重。如对于垂死病人或一些脑死亡而心脏仍跳动的“植物人”,“死亡中心论”就普遍认为安乐死方式的主动选择是合乎伦理道义的。这不仅不是对生命的残害,而且是对生命质量的尊重,对死亡价值张扬。其实当我们认为死对于生而言没有所谓的好与坏之别,仅是一种同等地位的选择时,则我们对于死与生的态度就不会有如此大的反差,进而会显得更为平淡地看待生与死。“生亦死,死亦生,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在这个意义上颇与“人类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大自然也是人类的有机部分”相似。弱式死亡中心论者往往认为生存与死亡无所谓手段亦所无谓目的,目的即手段,手段即目的,死亡在人的观念应具有与生存一样的尊贵价值。这样对死亡的态度就不会再有大悲大惧,而会从自然之道看待生死。强式死亡中心论者更是明确地认为死亡具有内在的伦理价值,不仅是为生的价值而存在,而且有时超越生的价值,有它本身固有价值,就如同一种高出现实生存价值的极乐世界的价值,或者成仙成佛的价值。
现代(弱式)生存中心论者认为人类关注、关怀死亡最终是为了提高人的生存质量和进一步提高人对待死亡的智慧。死亡仅是考察生存者之间伦理关系的一个中介过渡。死亡伦理关注死亡、尊重死亡及思考如何处理生与死的关系,实质上还是在处理、调整生存者之间的道德关系,即生与生的关系,一部分生者与另一部分生者的关系。例如“今世人”的死是为了“后代人”的生,甚至比“今世人”的生更美好;而一小部分的死是为了更广泛的人更美好的生。
现代(弱式)“生存中心论”者一定程度上是传统“生存中心论”与“死亡中心论”者的一种妥协产物。对于死的理解上,死亡哲学也往往从静动观来察思,即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动中乃生,静及极至则达死。弱式“生存中心论”者和弱式“死亡中心论者”似乎都认为死中有活,活中有死,死与生水乳交融,死与生达到一种中庸是死亡伦理倡导的一种境界。强式生存论者认为死亡是黑暗的海洋,是痛苦的地狱。而强式死亡论者认为死亡是灵魂与肉体的分离,是从肉体的有形之动升华到精神的无形动即至空至静,即无我与超我的天堂圣境。
现代“生存中心论”者以死亡为中介关怀从而更好地关注生存质量,对死亡的研究关注仅仅是为了更好地有利于我们人类的生存,有利于我们生存着的生命更加安顿,在浮躁的世俗社会中能常常清醒和镇静,也有利于临死、垂死的人能安息,能更坦然、更轻松地走进死神。他们认为死亡伦理表面上是为死亡作道德辩护,如取义成仁的倡导以生为工具来实现死的伟大,以生命肉体的失去来争取精神和灵魂的永存(正如有的人肉体死了,但他们的精神还活着),但事实上为“义”而死的这种“义”本身有时就值得怀疑,如果最大的道德是对生命生存的尊重,那么这种肉体死后灵魂的升华本身难道还有价值吗?灵魂有伟大的伦理内涵吗?对灵魂价值论的怀疑是他们死亡伦理中的问题要害。
贵生说在现代生存论者与传统生存论者中间存在的一个巨大区别在于前者不仅认为“贵己生”而且要“贵他生”,不仅要贵他生而且要贵芸芸众生,不仅要贵当代人生而且要贵后代人生;而后者常常仅限定贵生为贵已眼前之生,甚至可以以其他所有生为代价来成就自己眼前当务之生。当然生存论者的贵生说与死亡论者的贵死说相对而言的特点在于前者认为死亡伦理研究死亡归根到底是为生存之需要,死亡没有目标价值,最终的伦理价值还是为了服务于生。而后者认为死亡本身就是一种道德价值的实现,本身成仁即如此。
环境伦理的“贵物论”(自然中心主义)与“贵人论”(人类中心主义)对死亡伦理的“贵死说”(人死后化归于自然)与“贵生说”(人作为主体独立于自然客体)有很大的相似启发性。如果说按“贵物论”,哪怕“弱式自然中心主义”,万物与人的关系至少也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人之生命则是没有绝对意义上的终结,生死是一体的存在,正所谓“万物一府,死生同状”。既然如此,死又何惧?也就会有一般人“贵生轻死观”转向“生死齐一观”,这也可以界定为前文分析中得到的“弱式死亡中心论”。如果说按“贵人论”的“人优越于自然万物”,则人的死去将失去这种优越,而对死亡的伦理态度必然也是消极的,因而较易得出“贵生说”。
二、死亡伦理的求索——生命超越的道德智慧
当然当我们跳出“贵生说”与“贵死说”之争看死亡伦理的宗旨就离不开对死亡本身的看法是否合乎道德性及这种道德性标准又是如何的思考。这就涉及到死亡的道德评价及对死者权利的尊重及减少死亡过程生理、心理上经历的痛苦及体现对生命价值善始善终尊重的临终关怀等一系列问题,另外在于死者殡葬的选择问题上也存在一定的道德性评价及道德性标准问题之争,及对死亡方式的选择和决定上也有巨大的道德性标准的分歧和道德性评价问题等。
1.人生时序中的死亡伦理:临终关怀
一个人临终时,回顾往事不应为“碌碌无为而空叹”,不应为“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不应自惜“冯唐易老,李广难封”;临终对于临终者本人而言最大的伦理关怀是为自己壮丽的一生而自豪,自我对临终时的幸福感的享受有巨大的人生责任,他看似从生到死无任何带来也无任何带走,但在他的墓前高尚的人们将默默地洒下充满深情与崇敬的热泪。
一个人一生总有无数没法了却的心愿,所以到了临终之前,给临终者最大的伦理关怀,对于临终安抚者及送终者而言,最重要的是承诺或现场尽力了却临终者一些极想但已无力了却的心愿。这样当临终者合眼时,尽可能减少一些遗憾,这会大大减少临终者心理的“死亡痛苦”。人死亡前之所以不能安然瞑目,是因为往往牵挂得太多,其人太在乎生前已拥有的自以为美好的一切,其不想放弃这些拥有,也不甘心一些其认为的美好却不再拥有,同时,此时他才会发现生前拥有的一切比任何其他时候看来都更难得、更珍贵。如果“上帝再给我一次生命,我会百倍于前一次生命的珍惜之”。所以大多数临终者都放不下心理的包袱,送终者也很容易陷入伦理的自责中。
2.生命终结的死亡伦理:殡葬选择
殡葬是对死者尸体的一种处理形式,传统有土葬,现在有火葬。殡葬的讲究涉及遵从老人生前的遗愿选择合适的形式,这也当是死亡伦理中的一部分,而这里又有一个火葬的道德性对传统土葬道德性的挑战问题。何谓移风易俗?这种移风易俗又能否在特定地区、特定人群中被接受不至于让他们认定是反他们认可的传统道德的不道德之风?一个老人要求死亡之后儿女务必将之土葬,然而儿女为了遵遁国家法令政策,不得不对老人火葬,此时,面临的道德义务冲突又如何选择?“忠孝不能两全”时,这里面的思考更值得我们具体地分析论证。殡葬仪式的选择对于有宗教背景的民族而言,一般都与宗教教义相联,在这种教义中所要求的形式一般在该社会中被认为是道德的,否则是大逆不道。如回族对猪非常崇敬,羌族人对鱼非常崇敬,若回族人用猪祭祠是大逆不道,羌族人用鱼则同样如此。当然,现代人更能接受生前尽孝道比死后尽孝道是道德得多,而生不孝死后孝是假孝,甚至同样认为是大逆不道的,不伦理的,所以笔者认为死亡伦理学对殡葬的探讨应当强调临终者的意愿,当然更应尽量在各种义务冲突中求良好的平衡。
3.超越生命的意义——死亡目的性价值与手段性道德关注
关于死亡的德性问题的思考主要指死亡的目的的伦理性与死亡手段的伦理性的理解。死亡是否值得?“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认为杀身成仁值得。“鱼亦我所欲,熊掌亦我所欲也;生亦我所欲,义亦我所欲”,“舍鱼而取熊掌,舍生而取义也”,死亡对于充满“浩然正气”之人好像并不是最可怕的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自横刀向天笑,唯有肝胆两昆仑”,“一腔热血勤珍重,死去犹能化碧涛”。在仁人志士眼中“砍头不要紧,只在主义真”,死亡对于他们心中的神圣的信念理想、终极价值和认可的伟大的事业、道义而言算不了什么,只是一种相对次要的东西,人的物质生命在这些仁人志士的伦理价值观中是比其拥有的精神生命次要的,物质肉体生命是精神灵魂生命的手段工具。他们认为真正的“安乐之死”即“大义之死”、“无憾而终”。
死亡哲学中有肉体之死与灵魂之生,灵魂精神之死与肉体之生的学说,正如“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臧克家诗)中前者是肉体之死;“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中后者是灵魂之死。肉体之死并不能阻碍伟大的道义、事业和思想的不朽和永生,正如马克思主义并没有随马克思之死而死,毛泽东思想也没随毛泽东逝世而与世绝亡。对死亡伦理目的性价值的研究能使我们看懂为什么有的人临死是如此安祥,而有的人临死是如此慌恐不安;有的人的死是如此伟大庄严,重于泰山,永垂不朽,而有的人的死是如此可卑可笑,轻于鸿毛,遗臭万年。
关于死的方式方法的选择也是死亡伦理关注的一个有机方面,如对于死刑问题的处死方式历来是一个伦理问题的争议焦点。用血腥残暴的手段结束一个生命,如千刀万剐、绞刑、砍头等,还是用比较温和的方式如注射、服药、甚至“安乐死”,这两种类型的人道性是否应在死的目的的价值性问题上进一步探讨?笔者认为死亡手段的道德关注不可不察思。就死刑而言,它的存在与否本身就是一个伦理问题,死刑对于犯罪而言可能有点不人道,可是对于受害者而言,难道“废除死刑”是“人道”?
三、死亡态度的伦理寻根及争鸣——生命境界的神圣提升
为什么要死?怎样死?愿不愿死?这些问题的寻根就是对死之态度的伦理层面的挖掘过程,也是生命境界的不断升华过程。
与人同归于尽的狂徒总喜欢以自己什么都不拥有的现状来跟相对于他拥有多得多的人比较,认为自己的贱命换仇敌的贵命划得来、合算。“生不如死”是自杀最简单的理由,还有什么“长痛不如短痛”之类的补充理由。但他充其量更多地看到对自我的死亡道德关怀,却忽视了“自我死亡”对他人如亲人的伦理责任。当然每个人由于生前的价值观不同,从而对精神、物质上的痛苦的看法也就不可能一样。虽然每一个成熟的人都知死后将意味着生前所有的精神、物质上的痛苦将消失,但他又不敢轻易地死,首先他就害怕死亡的肉体生理上的痛苦。可是如果现代医学的高度发展能为你提供合情合法的“安乐死”呢?即死对于人而言不需经历肉体上的多大痛苦时,我们一般还是不敢轻易选择死亡,因为我们无能预测死亡以后自己的处境,这是生人世界无法得知的,到底有没有鬼神的世界呢?我们生人无法目睹,只能想象之或凭我们生人的世界进行联想。另外毕竟我们人性中的惯性对生的世界有一种“迫不得已”的留恋。至少我们只要生存中还有希望拯救自己极不愿接受的精神、物质上的痛苦时,我们一般不会放弃这种努力的。但是对于“方生方死,方醒方醉”的辩证法大师庄子而言,妻子死后他却无动于衷,相反击鼓作乐,邻人不解,他却言,人死与生皆是自然之道,痛苦不可定论,因为在他的意念中是超越生死的“逍遥游”。临终关怀中不管是临终者还是送终者对于死亡的智慧方面似乎都可以从古人这方面吸取、借鉴。这种智慧即是对死亡伦理的关注,追求生命超越的境界,这也是人生素质教育中的重要的一课。
死亡有自然之死、主动之死、被动之死三种类型。自然之死在道教教义中是“至善”之死,功德圆满,自然化归,如水浒传中的鲁智深坐禅立地成佛成仙,这一点在佛教中轮回报应学中得到精当阐释,认为生时济善行德,死后升入天堂极乐世界成仙成佛;而生前作恶多端,道德败坏,死后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佛家以死的来世学说来警戒引导、规制生的今世行为。道教中的自然之死是生命的灵魂,精气神的统一超越物质生命载体,独立分离出来游离于宇宙太空之中即阴阳两隔,从阳间的人走到阴间的鬼神,类似于基督教中的此岸、彼岸之学说,所以道教中的自然之死即成仙过程,是精神不断升华、提升肉体生命到一定阶段终于发生了质的变迁。而佛教的自然之死便是去了西天极乐界成佛。在儒家的理论中,自然之死属于寿终正寝。
主动之死是对死的一种自我选择,有自杀和牺牲两种截然相反的表现,自杀是因为畏惧于生的痛苦,对生命和前途的绝望,在自杀者的观念之中,活着已经是一种难以忍受的痛苦,生命对他而言只具有负的价值,减少或者消除痛苦的途径就是结束。而牺牲则属于舍生取义,是为了追求某种更高的价值而舍弃生命。例如,在儒家学说中,生命的价值在于内蕴于生命之中的道德价值,生命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承载并能够实现某种道义的价值,因此,当生命与道义发生矛盾的时候,就应该杀身成仁,因而是“至善”之举。
被动之死属于非正常死亡,它也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因天灾人祸而死,二是自己不敢死,不愿死,但在某种特定的情形下不得不死,例如,因为触犯刑律而被处以极刑的人。不管是什么类型,其结局都是一样,即生命的终结,但是,对死的意义的理解和不同类型的死对生命的意义,则是有很大差别的。
中国道教追求长生,是力求避免生命的死亡结局,但我们不能将其理解为贪生怕死,而是在追求对生命有限性的一种超越,希冀在现实的生命存在之中实现永恒。因此,他们将自己的生命本身尤其是精神的独立视为最高的价值,并鼓励为了保持这种价值的纯真性而回避现实社会的纷争,通过某种修持的手段来求得精神的超越与生命的安宁。
与道教的以避世之态达入世之治不同,儒家以入世之道达出世之境,由正心、诚意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再到社会人类之外的宇宙自然天地之间。笔者认为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与新儒家的“内圣外王”同心圆扩散理论相似,马斯洛所谓的“自我实现”层次是“入世”的最高境界,而他晚年又加上由本我到超我、无我、真善美终极价值的实现乃出世之境。佛家的佛法无边即无法,道教的道可道即无道,儒教的格物致知、修身成性成圣,其实都是圣王之道,王即圣,圣即王,哲王治国乃理想国。哲学素养治理对于人生而言亦如此,相对于宗教教条仪式而言它关注的是实质内涵,在哲学素养求索中佛、道、儒三家归一为心灵净化之学、优美心灵管理之学,如生拥有大多时,到临终时患失的大多便自然心理痛苦、精神遗憾。临终关怀的宗教仪式不如哲学素养的心理治疗,不管是对于临终者还是送终而言都是如此。哥德的“没有拥有科学,也没有拥有艺术,就让他拥有宗教吧”,这里的宗教改成哲学或伦理学更有意思。
这三家的思想共同之处都是对生命的严肃思考,都在探讨死亡的价值,探讨对死亡的超越,只是各自选择了不同的超越路径。它们给我们的启示是:入世与出世在死亡伦理中是融通的,死亡伦理与其说是知识,不如说是体验,对死亡态度的坦然需要由本我(小我 大我)到超我、无我至天地万物与我一体便自然归化于极乐世界成仙成佛。死亡有智慧,死亡有境界,对死亡的态度是一种素质。超越生命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伦理。生命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只有一次,不可能失而复得,如果能够死而复生,我又何尝不想去感受一次死亡的滋味,对于死亡时刻肉体上的痛苦,我们生者只能从其他临终人的表情上来体会,自我却不能亲自去体验,没有勇气去为一次异样的体会去永远结束生命,因为在这里,挑战生命肉体的极限就是挑战死亡。
Exploration of the Death Ethics
ZHANG Huai-cheng,YAO Zhan-jun
(Research Institute of Ethics,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Hunan 410081,China)
The environmental ethics has been relatively more mature than the death ethics.We can explore the death ethics ideas by the environmental ethics.Human beings for the existence has given rise to environmental etihics underlying the value of nature after deep consideration.We could not never care about ethical life for a moment.The ethical care is still our concern even after death.
death ethics;life development;life excess;life realm
B80-02
A
1000-2529(2010)02-0018-04
2010-01-05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9年度重大项目“灾害伦理学研究”;2008-2009年度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自然灾害伦理学问题研究”(0802005B)
张怀承(1957-),男,湖南常德人,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姚站军(1978-),男,湖南新邵人,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校:文 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