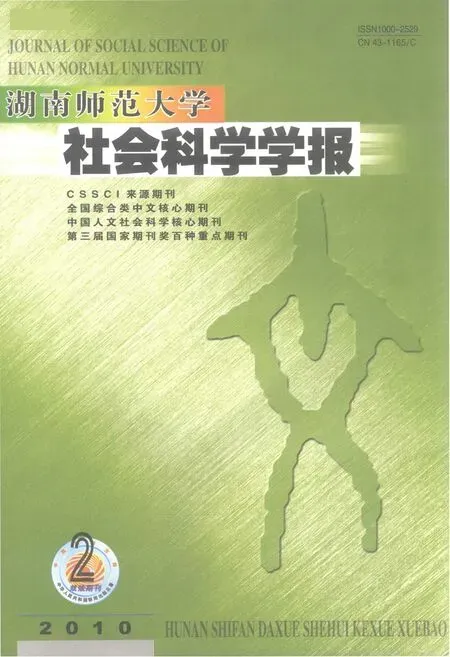转型时期的耻感文化:蜕变与重建
邹兴平
(长沙理工大学,湖南 长沙 410076)
转型时期的耻感文化:蜕变与重建
邹兴平
(长沙理工大学,湖南 长沙 410076)
尽管很多人对社会转型以来道德滑坡的原因提出了不少与事实相符的看法,但耻感文化由羞恶到羞输再到羞失的蜕变无论如何是非常重要的一条。此种情况的出现不仅与历史的迁延,而且与今人行为的失当有着紧密的关联,因此,为使这一问题得到较好的解决,最终有俾于和谐社会的建设,人们无疑应采取各种具针对性的措施。
耻感文化;蜕变;重建
很早以来,耻感就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道德心理范畴,而在中国,以这种意识为基础和核心的耻感文化更是传统文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由于很早就“广泛融入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人士的道德践履中,成为决定人们行为选择和价值取向的重要因素”[1],因此,这一文化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但令人遗憾的是,社会转型以来,由于种种原由,这一文化发生了严重的蜕变,并因此对人们的工作和生活产生了多种负面影响。有鉴于此,尤其是在当代中国,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随着时代的推进不断凸显,人们便有必要对这一现象予以正视和剖析,以能使已蜕变的耻感文化得到以内涵的界定为主要内容的重建,最终有俾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一、“羞恶”—“羞输”—“羞失”
在当代中国,相对经济的高速增长,道德建设的严重滞后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此,人们只要看看诸多令人难以忍受的现象,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道德的缺失在时下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而非个别人的行状呢?尽管不少有识之士对此进行了专门的探索并提出了不少与事实相符的看法,但有一点却是需要包括他们在内的所有民众都予以正视的,那就是耻感文化的蜕变。实际上,正是因为很早以来,人们在以何为耻的问题上出现了极其严重的认识失误,因此,便最终使得他们在措置各种事务时出现了不少违背甚至践踏社会道德的行为。
如众所知,耻感文化是一种观念文化,其基础和核心是人们的耻感意识。对这两者的关系,人们完全可以说,有什么样的耻感意识,就有什么样的耻感文化;一旦耻感意识有变,耻感文化也会随之发生变化。那么,具体到中国,人们的耻感意识又是怎么回事呢?很明显,那就是长期以来,无论上下尊卑,皆以作恶为耻,以行善为荣,从而使得耻感文化实际上成为了一种以惩恶扬善为取向的道德文化。这一点,人们甚至无须综观诸多贤哲有关耻感意识的论述,只要看看“亚圣”孟子对“耻”的阐释,就可知一斑。因为在谈到人的心性的时候,孟子曾非常明确地指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也就是说,在孟子看来,所谓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乃是最基本的善行;它们不仅是仁、义、礼、智四种德行的萌芽,而且共同构成了人类道德行为的全部意识基础。任何人,如果无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则善在他们那里就是一句空话,而他们亦只会是不仁不义、非礼非智之人。比如羞恶之心就从来是“义之端也”。不能羞恶,人们就没有耻感;而没有耻感,则什么坏事、丑事都能做出来。即由于羞恶同恻隐、辞让、是非一样,同为人性根源和德性本体,孟子便强调知耻的重要性,指出“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孟子·公孙丑上》)的同时,还对什么是耻进行了阐释,指出它就是“恶”。从而表明,在他那里,知耻即羞恶,不以作恶为羞,是无有德性,不配做人的。
由对孟子言论的回顾可以知道,在过往的中国,知耻就是羞恶。任何人,只要良知未曾完全泯灭,于自己的恶行都会产生一种羞愧的情感体验,或曰一种发于心底的道德谴责。也正是因此,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顾炎武在谈到以何为耻的时候,便再一次重申:“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亭林文集·与友人论学书》),将不能行善——自然,更遑论作恶——作为了耻感的内涵。但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几千年来,人们皆认为知耻就是羞恶,并以此规范自己的行为,却由于种种原因,还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于耻感意识上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对此,有那细心的学者观察到,至迟自唐宋起,人们言耻,已不再是——至少不再主要是——着眼于善恶,而是更多地着眼于输赢,也就是说,他们更多地是以输为耻(当然,也就是以赢为荣)。这样一来,便实际上使得耻感文化不再是一种善恶文化,而是成了一种“输赢文化”(或曰“胜败文化”)。比如唐宋间那些寒窗苦读的学子,以及他们的父母和师长,就无不以科考成功为荣,一旦落第,则觉得颜面尽失,耻于见人。实际上,也正是因为自那时起越来越多的人在对自己和他人的行为进行道德评价时不再是羞恶,而是羞输,因此,上述学者便指出,他们的此种行为使得“‘耻’的含义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化,就像岔路口的一块警示牌被人转了一个向。”[2]
然而,对今人来说,由羞恶而羞输,尽管是耻感的一大变化,却仍非问题的全部。实际情况是,社会转型以来,耻感的内涵又发生了一次大的异变,这就是时下不少人不仅以羞输代替了羞恶,而是更进一步,将羞失(或曰羞亏)亦当成了耻感的内涵。也就是说,对这些人来讲,使其感到羞耻的不仅是他们在与他人的竞争中落了下风,于面皮上不好看,而且还有更重要的一条:不能经由各种途径和手段获得令自己满意、为他人艳羡的物质利益,不能因物欲的极大满足而能骄矜于他人。在他们看来,不讲因行善,就是因竞争胜利所具获的自我心理满足,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对人来说,真正有价值的只有一条,那就是物质利益的获得,因为惟有这一条才能使他们既过得舒服,又得到社会的良好评价。正是因此,在现实生活中,他们便不仅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包括不正当的竞争甚至行凶作恶——去获取物质利益,而且有意无意造作、宣扬以羞失为内涵的耻感文化,以达到为其不良甚至不法行径辩护的目的。也正是在他们此种言行的作用和影响下,传统的耻感文化便极大地被改写,失去了应有的引导人们向善祛恶的功能,从而最终导致了各种不良甚至违法犯罪的社会现象的出现。
总之,在中国,很早以来,耻感文化就发生了其内涵由羞恶到羞输再到羞失的“三段式”异变,致使人们在其影响之下,不仅恻隐之心大减、辞让态度罕见,连对是非的判断都出现了问题。面对近年来一些人贪不为耻、淫不为耻、奢不为耻、赌不为耻、窃不为耻、坑不为耻的表现,不少严肃人士在深为之忧虑的同时又感到极度困惑,常常生发“今夕何夕”的感叹,殊不知这都是传统的道德标准遭到颠覆的结果。如果不是耻感文化出现了严重的蜕变,使人们在处理各种事务的时候不再究问这是行善还是作恶,而是只汲汲于物欲是否得到满足,时下各种丑陋的现象,诸如买官卖官、包养“二奶”、考试舞弊,等等,是决然不会出现在社会主义中国的。
二、历史与现实、体制与意识
由羞恶到羞输再到羞失,这无疑是耻感文化之内涵的一场巨变。正是这一巨变,不仅使得社会道德的基石在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遭致了毁坏,而且使得社会成员的心理出现了不应有的集体迷失,最终导致了人们的行为失范和社会的运行失序。鉴于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尤其是昔日仅为少数人看好的歧路极有可能变成为多数人认可的正道,不少有识之士便对此开展起了深入的探讨。比如有的文化学者在解释时下高考的成功以何会给一名学生及其家庭乃至其家族带来巨大荣耀感的时候,就指出,这很大程度源自历史,尤其是源自唐宋兴起的科举制度。因为正是这种“鲤鱼跳龙门”式的社会流动方式,使贫寒学子的社会地位骤然提升,获得为一般人难以获得的名利,从而使得后者艳羡不已,以至忘记了人世间还有祛恶行善这一更应令人珍视的行为。正是因此,他们认为,科举制度尽管对人才的选拔不无贡献,但它对文人集体人格的损害亦不能小看,因为它极大地促成了以“输”(考不上)为耻的意识的产生。正是这一变化,不仅在古代造就了不少范进式的知识分子,而且还因他们上千年的文化体验,最终积淀为一种强烈的文化心理,演绎成一种影响巨大的耻感文化,自兹以后一直作用于人们。如果说今天会有那么多的人不再——至少是不仅——以恶为耻,而是更多地以输、失为辱,则寻根溯源,最终应追究到此种制度。
无待说,在耻感文化的内涵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变异的问题上,学者们将探索的眼光投向过往是很有道理的;而且人们只要坚持这样做,还会得出不少有效的解释。比如当人们回顾一下思想史时,就会发现,早在战国时期,杨朱就提出了“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的命题。尽管这种“极端重视个人生命和个人利益”[3](P193)的话语很不中听,但由于它强调的是“贵己”、“为我”,而恰恰在一切生命体那里,“为我”都是它们存在和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即便是强调仁爱、向往“大同”的儒家,亦没有也不可能否定这一点),因此,便对社会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以至时之贤哲在谈到这一点时,亦深为感叹,道是“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只是,在对这些给予了应有的正视之后,人们又应意识到,对于耻感文化为何发生异变这一问题的解答来说,向历史寻找答案固然有其合理性和实效性,却并非是唯一的途径。由于羞输、羞失在今天已是具有很大普遍性的社会现象,甚至可以“人心不古”来形容之,因此,人们就还有必要在当今社会寻找一下原因。
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对当代中国意味着什么,这在今人似乎已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事情。由于这一体制具有多种功能,诸如:合理配置社会资源、推进生产社会化不断向深度和广度发展、自动调节供求、价值评估、奖优罚劣以促进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不断提高,等等,因此,在当代中国生产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上便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也因此得到了人们的高度肯定。然而,诚如不少有识之士指出的那样,在现实生活中,这一体制并非是尽善尽美、全无缺陷的。由于它作为一个平等竞争的平台,所能满足的只是人们对物质财富而非精神文明的需求,因此,只要社会对这一事实失却应有的关注和正确的措置,便不可避免地会使人们将价值仅仅理解为物质利益而非人本身,从而使得它的确立会在思想道德领域引起双重效应,即一方面它固然促进了正当的个人利益观念及效益观念、竞争观念等的产生,以此使经济的发展获得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杠杆[4](P179),但另一方面它又使得人们于不经意之间以羞输、羞失取代了羞恶,致使唯利是图、尔虞我诈、损人利己、敲诈勒索等不良、不法行为因耻感意识的异变而常常能逃避舆论的谴责,至少不是像以往那样被牢牢地钉在社会的耻辱柱上。正是因此,当人们在探究耻感文化为何会在今天发生那么大的变化时,便不能忘记,市场经济的消极方面确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如果不是它所带来的消极效应,这一文化即便在科举制度盛行的时候就已开始异变,亦只会是以羞输取代羞恶,而断不会像时下很多人那样极度羞失,公然认为“笑贫不笑娼”之类的社会现象是有其道理的。
又如,不能很好地守望传统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在何为耻感、它于人有何作用以及如何发挥它的作用等问题上,中华民族向有优秀的传统。比如对于何以为耻,古人就非常明确地指出:“宁可穷而有志,不可富而失节”,即认为富并不一定使人感到光荣,如果品格低下,倒不如那些志趣高洁的穷人。又比如对于耻感于人的作用,他们的理解是“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牧民》)。这种从国家生死存亡的角度看待耻感的作用的观念,对人们的警示无疑是极其巨大的。再比如对于如何发挥耻感的作用,古人亦有深刻的见解,指出人们应“沽身励行,思学正人之所为,……凡污贱淫恶,不肖下流之事,决不肯为(《传家宝·人事通》)。”但令人遗憾的是,对于这样一份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人们并没能给予很好地守望。基于各种政治目的和社会需要,再加上缺少辩证思维,他们在不少关键所在都没能予传统道德以合理评价和正确对待,致使耻感文化的蜕变在某种意义上竟成为了一件难以避免的事情。对此,人们只要看看以下事实——戊戌变法时期,国人是那样看好进化论,以至认为以它为指导就可以解决中国陆沉的问题,至于五千年传统文化,则其社会建设功能庶几可忽略不计;“五四”时期,最先进的知识分子都认为传统礼教的功用就是“吃人”,既要大兴科学和民主,就得打到“孔家店”,彻底荡涤包括耻感文化在内的“旧道德”;“文化大革命”时期,在“破四旧、立四新”的口号中,传统文化几乎全被摒弃,无数恶行因“革命”而能丝毫不被谴责地畅行于世,等等——就可知道,在耻感内涵由羞恶到羞输再到羞失的变化上,优秀的文化传统不能得到有效的发扬和光大起了多大的作用。如果人们对于知耻即羞恶有稍多一点的理解和守望,则耻感文化是绝不会出现严重的蜕变,最终影响到人们的德行和操守的。
还可以举出若干,如道德教育的不力、公共治理的缺失,等等。总之,对于当代中国来说,耻感文化蜕变的原因既有历史的,亦有现实的;而在现实这一方面,社会的转型尤其是新的经济体制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和传统道德的不能有效继承更是最重要的原因。人们如果对此视而不见,不能采取具针对性的措施,则这种情况还会继续下去,最终严重影响到人们素质的提高和和谐社会的建成。
三、正理·重教·建制
由对历史和现实、体制和意识等方面的情况的分析,可以知道,耻感文化的蜕变不是无缘无故的,相反是有着相当的必然性的。不过,在对这一切给予正视的同时,人们又还要认识到,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耻感文化的这种变异面前便束手无策、无能为力,因为耻感文化毕竟是一种社会现象。既然这个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从来就是变动不居的,那么,它就不会永远只表现为一种状貌,停留在一种状态上。也因此,只要人们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即在弄清始终原委的前提下,采取各种针对性的举措,就一定能使已然发生蜕变的耻感文化再一次发生有利于社会的变化。
那么,具体说来,在耻感文化的重建上,人们究竟应采取那些措施呢?
首先,人们应当正理,即对耻的内涵予以正确而又具体的界定。
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究竟以何为耻,这是重建耻感文化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如果在这一问题上出现了错讹,不能做到“耻所当耻”,那么,即便发生蜕变的耻感文化因人们的举措有所更新,亦不能于人们以积极作用。从前已述及的情况看,耻感文化的蜕变主要是耻的内涵由羞恶变成了羞输、羞失,既然如此,那么,人们便应对此采取有效的措施,至少为恢复优良传统计,人们都应以作恶为耻,为自己的日常行为提供一个基本的准则。
不过,对于耻感文化的重建来说,仅仅在思想观念上以作恶为耻,仍然是不够的,因为恶是一个极其抽象的概念,而恰恰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以抽象之恶,很难尽释各种不良甚至违法犯罪现象。因此,人们在耻感上的正理,便除了以恶为耻,将羞恶作为知耻外,还要联系实际,尽可能地具体化。也正是因此,社会转型以来,便有了胡锦涛总书记郑重提出的“八荣八耻”之说。以往,人们在评论胡总书记的这一说法时,只是注意到它是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重要构成,而且提出得非常及时,殊不知它亦是对当代中国社会条件下之耻的内涵的一个准确而又具体的界定。如果不能阐明新时期内人们究竟以何为荣,以何为辱,则即便知道世界上有善恶之分,甚至知道知耻就是羞恶,仍是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的。弄得不好又会在徒知抽象的善恶的情况下使耻感文化发生新的异变。
其次,人们应当重教,即通过道德教化使民众对何以为耻有一正确的认识。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耻感因其存在方式、作用范围等的不同可作多种区分,比如它可以是一种心理现象,即个体道德意识的一种表现形式,也可以是一种文化,即借助外部强制力规范人们的行为的社会意识。而这样一来,便使得它为人们所认可、奉行需要各种不同的条件。比如作为一种个体道德意识,耻感的形成很大程度依靠的是行为主体自身的自觉建构(此即是人们常说的“自省”),至于作为一种文化,则其形成无疑离不开对全体成员有目的的教化。俗语“人上一百,形形色色”,由于人们在知识、能力等各方面尤其是对生活的态度上存在着千差万别,因此,如欲使每一个人在何以为耻的问题上不经教化便都具有正确的认识,从而形成一种同一性极大的耻感文化,显然是不可能的。正是因此,通过强有力的宣传教育使人们对何以为耻有一正确的认识,便成为了转型期耻感文化重建的一项重要工作。
此外,还需指出的是,对于耻感文化的重建来讲,强调重教并不仅是出于逻辑的推论,而是在于大量事实表明,之所以社会转型以来耻感文化发生蜕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有关方面在推进社会发展时只注意到经济增长的重要,忽视了对民众的思想教育,即没有做到邓小平所说的两手都要硬,而是出现了“一手硬,一手软”[5](P217)的情况,致使一些领域道德失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滋长,封建迷信活动和黄赌毒等丑恶现象沉渣泛起,假冒伪劣、欺诈活动成为公害,文化事业受到消极因素的冲击,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蔓延,等等,以此似乎使羞输、羞失的合理性得到了实证。也正是因此,即便有关方面通过正理这一工作使耻感的内涵得到了正确而又具体的界定,仍需要通过重教使正确的耻感为广大民众所理解、承认和接受。只有如此,方能既使作为一种道德意识的耻感在每一社会成员的心中生根,又使作为一种道德文化的正确耻感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再次,人们应当建制,即通过外在约束机制的建立和强化,使正确的耻感在外力作用下为民众所认可和接受
一种正确的耻感要为民众所认可和接受,进而蔚为一种文化,固然很大程度在于每一社会成员的自觉、自律,但人们同时又应看到,恢复已经丢失的正确的耻感,回守被冲决得漏洞百出的道德底线,单靠自觉、自律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无论是理论还是事实都已证明,在很多时候,除自我认识、自我约束外,人们还需要来自外界的帮助和督导。而这一点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就是知耻环境的建设、外在约束机制的强化,等等[6]。人们如果得不到应有的导向和监督,则即便经由正理、教化等途径和方式使自己的耻感意识回归了正确的方位,亦不能因更多的人们的认可和接受成为一种社会风尚。
从时下的情况来看,在如何重建正确的耻感文化的问题上,有关方面于必要的制度和体制的建立上面无疑存在着一定的不足。正是因此,便使得“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礼记·大学》)”的局面一直没能形成,致使各种越线行为一直没有得到社会大环境的严厉反对甚至惩罚,最终影响到了正确耻感的重建。推究这种局面的出现,当然与大多数人持具的一种道德意识的形成主要依靠社会成员自身的努力的观念有关,而且认真说来这种观念也无有什么不妥,只是他们同时又应知道,即便道德意识的形成主要依靠自己,但这并不等于他律便没有一点作用。尽管不少事实证明,来自外界的责罚只是治标之计,治本的关键仍在于如何让公众拥有平衡的社会心理与符合道德基准的社会回报,但亦有不少事实证明,真要使人们在无有任何责罚的情况下都能羞恶,却是不太有可能的;更何况让公众拥有平衡的社会心理与符合道德基准的社会回报从来就是制度作用下的产物,离开了相关制度的建设,没有这些制度的作用,任何社会成员要获得符合道德基准的社会回报从而做到社会心理平衡,都是不可想象的。
关于如何重建耻感文化,人们还可列出其他一些措施,如营造氛围,即在取向界线明确以后,大力宣传,不断弘扬,以能对民众起到一种促进作用,等等。总之,只要全社会高度重视、积极探索,是一定能想出好办法,提出好对策,使当代中国人的耻感意识和耻感文化不仅增添新的时代内容,而且既祛除有害成分,由是焕然一新,在精神文明的建设进而物质文明的建设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1] 胡 凡.传统耻感文化的形成及其对中国历史的影响[EB/OL].光明网,2009-9-24.
[2] 方立正.评重塑“耻感文化”[EB/OL].中国新闻网,2009-06-19.
[3] 叶 朗,费振刚,王天有.中国文化导读[M].北京:三联书店,2007.
[4] 易培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6]杨峻岭,任凤彩.道德耻感的基本样态分析[J].伦理学研究,2009,(5):56-59.
Shame Culture in Transitional Period:Transform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ZOU Xing-ping
(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Changsha,Hunan 410076,China)
Though many ideas about the causes of the moral deterioration since the transional period have been proposed,which are conforming to facts.The idea that shame culture develops from shame guilt to the shame loss and then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shame loss is the most important one anyway.Because this state is closely related not only to the historical procrastination but also to the improper behaviour of modern people,in order to find a better solution to this problem and make it more beneficial for constructing the harmonious society.Certainly various pointed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shame culture;transformation;reconstructions
B82-052
A
1000-2529(2010)02-0028-04
(责任编校:文 建)
2010-01-05
邹兴平(1968-),男,湖北荆州人,长沙理工大学副教授,硕士。
——评章越松著《社会转型下的耻感伦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