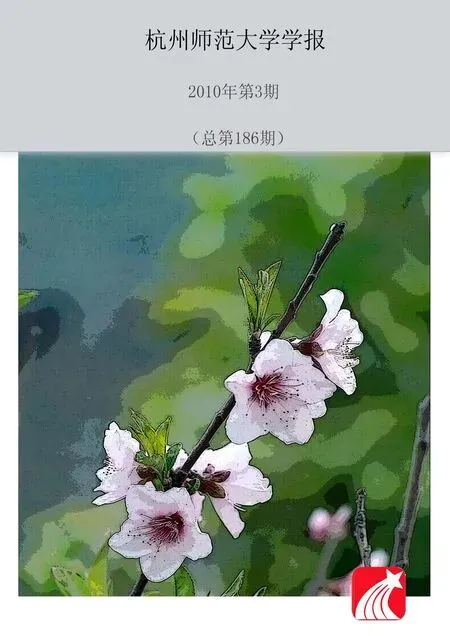蒯因对分析哲学的实用主义变革
姚介厚
(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蒯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1908一2000)是当代美国变革分析哲学的首要开创者。他在20世纪50年代初展开对逻辑经验主义基本理论原则的锐利批判,吸收实用主义思想改造分析哲学,提出一种逻辑实用主义,建立新颖的语言哲学和逻辑哲学。他的学生、著名美籍华裔哲学家王浩教授称他是分析经验主义中的“逻辑否定主义”(lgical negativism)的创立人。[1](P.8)他的挑战在英美分析哲学界引起持续十多年的论战,开启了当代美国分析哲学、科学哲学兼容实用主义一体发展的新历程。
蒯因学术生涯凡60年,哲学和逻辑研究成果迭出,著作共约20部。他对逻辑经验主义早持批判态度。在20世纪30年代他就写过两篇从本体论角度研究逻辑哲学的论文,反对拒斥形而上学。1948年发表著名论文《论何物存在》(OnWhatThereIS),着手建立逻辑分析的本体论。1940年他在哈佛偕同塔尔斯基,就分析性问题和卡尔纳普展开争论。1951年他发表《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TwoDogmasofEmpiricism),推翻从实证经验论到逻辑经验主义的根本理论支柱,被公认为当代分析哲学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献。1957年他出版《从逻辑的观点看》(FromALogicalPointofView),此书结集的论文表达了他的基本哲学观点。此后他发表一系列论著,详细阐发逻辑实用主义思想,主要代表作有:《语词和对象》(WordandObject,1960),《本体论的相对性及其它》(OntologicalRelativityandOtherEssays,1969),《指称之根》(TheRootsofReference,1974),《理论和事物》(TheoriesandThings,1981)。蒯因又是一位杰出的逻辑学家,对现代数理逻辑、集合论和模态逻辑等素有研究,发表了《数理逻辑的新基础》(NewFoundationsforMathematicalLogic,1937)以及《数理逻辑》(MathematicalLogic,1940)、《逻辑方法》(MethodsofLogic,1950)、《逻辑论文选集》(SelectedLogicalPapers.1966)等多种著述。
我们可从以下三方面概论蒯因的基本哲学思想是对分析哲学的实用主义变革。
一 以实用主义整体经验论批判实证经验论传统的两个教条
从休谟到逻辑经验主义的实证经验论传统,都仰仗两个密切相关的信条:一是严格区分只以意义为根据、不依赖于经验事实的分析真理和以经验事实为根据的综合真理:二是意义证实的还原论,即还原为感觉、知觉等感知经验的要素。蒯因抨击这两个教条没有根据,应予抛弃,其结果就是转向实用主义,并且不再承认形而上学同自然科学对立。
蒯因和弗莱格(G.Frege)一样主张意义和指称不可混同,例如,专名中“暮星”与“晨星”、通名中“有心脏的动物”和“有肾脏的动物”,指称相同,而意义却不同。意义是分析哲学的核心范畴。逻辑经验主义严格区分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就因为前者的意义只靠逻辑分析证明,后者的意义要靠感知经验要素的事实证实。
蒯因批判经验论的第一个教条,首先集中在意义理论中的分析性问题。分析陈述有两类:第一类是逻辑上必然真的陈述,如“没有一个未婚的男子是已婚的”,根据“A不是非A”的重言式逻辑关系就可确定它是真的;第二类是更大量常见的主、谓词同义性的分析陈述,如“没有一个单身汉是已婚的”,通常认为“未婚男子”和“单身汉”有语言形式的同义性,通过同义词替换,就可使这类分析陈述也具有第一类的逻辑真理。蒯因指出,分析性的实质在于同义性。问题正出在“同义性”概念不清,它不能成为分析性的根据,反倒要依靠无数反复的总体性经验观察,因此也就不能根据它为分析陈述和综合陈述划出严格界限。
蒯因论评通常有两种确立同义性的论证方式,认为都不能从中得出分析性。第一种:定义确定了被定义词和定义词的同义性。蒯因指出:所有词典式的定义,例如将“单身汉”释义为“未婚男子”,并不是词典编纂者的先天领悟,而是总体经验事实的记录,是他们根据语言行为,对观察到的无数同义性事件的报导。哲学家、科学家们的解释型定义,只是以提炼和补充被定义词的意义的方式,改进其语境的用法,这也是以记录总体性经验观察的同义性为根据的。因此,定义并不是同义性之本,也不能使同义性具有分析性:定义反倒是概括地记录总体经验事实才形成的。第二种:保全真值的互相替换性,即两个语词的同义性出于它们在一切语境中可以互相替换而真值不变。这种说法也有困难,如“bachelor(单身汉)有少于10个的英文字母”这个句子中,用同义词“unmarried man”(未婚男子)替换“bachelor",这个句子就失去真值。两个外延一致的词要在一切场合互换而真值不变,这种保全真值本身正是以两个词有同义性为前提,用它论证同义性和分析性的根据,就陷入循环论证的错误。
还有一种论证为区别两类陈述的分析性提供根据:现代逻辑符号表达精确的人工语言,不仅可澄清日常语言的含混歧义,而且能区别分析陈述和综合陈述,因为根据人工语言中所确定的语义规则,可以构造全部分析陈述。蒯因驳斥:这种语义规则实质上是日常语言和人工语言之间的翻译规则,它本身具有约定性:人工语言陈述的分析性倒要通过日常语言的译文去辨认,后者则涉及心理、行为和文化的诸多经验因素的整体。因此,主张人工语言的语义规则蕴涵分析性,这也是预设结论的无效论证。蒯因认为:真理依赖于语言和语言之外的事实。主张有事实成分等于零的陈述即有先天合理性的分析陈述,从而严格划出分析陈述和综合陈述的界线,这既不切合事实,逻辑上也不成立。硬要划出这条界线,“这是经验论者的一个非经验的教条,一种形而上学的信条”。[2](P.35)
蒯因批判第二个教条即意义证实说和还原说,这是对第一个教条批判的继续和深化。意义证实说主张一个陈述的意义在于它的证实方法,经验验证和逻辑分析的不同证实方法,就区别了综合陈述与分析陈述的不同意义。蒯因批判第一个教条已着重否定了分析性的根据。这里,他主要直指意义证实的还原论,那就是,实证经验论皆相信每个有意义的陈述,都等值于某种以指称直接经验的名词为基础的逻辑构造。还原的单位有所变动,但都诉诸孤立的陈述和感觉经验。洛克和休谟以每个观念为单位,还原为原子式的感觉和印象:弗莱格、罗素等人将有意义的单位从观念扩展为整个的陈述,还原为感觉资料的经验事实;卡尔纳普等逻辑经验主义者虽然运用大量逻辑记号从事世界的逻辑构造,对可证实性原则也屡有修改,但没有超脱所谓彻底还原论,仍主张每个科学陈述孤立地还原为观察经验来加以证实。蒯因指出:“即使以陈述为单位,我们也已经把我们的格子画得太细了”,“我们关于外在世界的陈述不是个别地,而是仅仅作为一个整体来面对感觉经验的法庭的”。[2](PP.38-40)他承认科学双重地依赖于语言和经验,但指斥还原论将科学整体肢解为个别陈述,孤立地还原为单个的语言成分和事实成分来验证,这“乃是胡说,而且是许多胡说的根源”,[2](P.39)因为具有经验意义的单位应当是整个科学。
他吸收实用主义的整体经验论思想,来阐发他自己的“没有教条的经验论”。
蒯因认为人类知识和信念的整体,是一个包括从地理、历史的最偶然的事件,到原子物理以至纯数学和逻辑的“人工织造物”,他将这个整体比喻为一个力场,它的边缘同经验紧密接触,各门科学的陈述按照它们同边界经验相距远近和普遍性程度高低,结成一个逻辑上互相联系的连续统一体。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力场并不静止、僵滞,在边界会和动态、连续的经验发生冲突,引起科学整体内部的调整;而对某些陈述重新分配真值,又会引起对其他陈述的再评价。边界经验对科学场并无严格限制,科学场内部也只有松懈的联系,因此人们根据某种相反经验更动一些陈述,有很大的选择自由:只要科学场的其他陈述部分也作出必要调整,使其内部意义融贯一致,就能使场内的所有陈述都有真值。这就是说,科学中没有任何陈述可永久免受修改,即使是处于核心地带的逻辑真理,例如逻辑学中的排中律,也可以修改,用来作为简化量子力学的方法。前文提到的第一类分析陈述即最可靠的逻辑真理,蒯因在论述同义性时未及论评,这里也指出它是可以动摇、改变的。总之,他认为:科学是有一定内在联系的动态整体,它在同外部经验接触、冲突中自身内部有理智选择和调整的自由;逻辑经验主义将科学看作静态逻辑框架和零碎经验的拼合,将科学肢解成碎片孤立证实,从而截然划分分析陈述和综合陈述,这样只会使研究科学知识误入歧途。
蒯因以整体论推翻实证经验论传统的两个教条,实质上是引进实用主义来改造分析哲学。他指出卡尔纳普等人在选择语言形式和科学结构上的约定论时已倾向实用主义,只是在分析和综合的界线上停止了,他则赞成“一种更彻底的实用主义”。[2](P.43)他主张:科学的概念系统是根据过去经验预测未来经验的工具,物理对象的概念只是方便的中介物,在认识论上同荷马史诗中的诸神一样,是一些不可简约的文化设定物,它们是作为易处理的结构嵌入经验之流的手段,只是在程度上比神话更有效而已。科学系统的边缘要谐和经验,系统内部为着实用目的有很大的人为调整和选择的自由。选择中为维护科学整体只需要两个标准:一是保守主义,修改理论要尽可能小地修改已习惯了的概念系统,以免损害其解释功能,引起麻烦;二是简单性,以尽可能少的陈述阐明知识内容,这实为思维经济原则。
既然任何理论都是解释经验的工具,分析哲学拒斥形而上学就没有道理。蒯因指出“本体论问题是和自然科学问题同等的”,例如,是否赞成普遍的“类”是一种实体,只是为科学选择一种方便的语言形式、概念体系或结构,这同争论有无半人半马怪物或争论某条街上有无砖房等事实问题,只有程度差别而已,它们都取决于“调整科学织造物的这一股绳而非另一股绳以适应某些特定的顽强的经验这个模糊的实用倾向”。[2](P.43)
二 本体论的承诺:一种实用主义的多元真理观
历来本体论都研究存在问题。蒯因在分析哲学界为本体论与形而上学恢复名誉,认为本体论有无处不在、不可抹煞的普遍意义。然而,他并不因袭传统的本体论去探究存在的本原或“第一哲学”,而是用兼容语言与逻辑分析和实用主义的方法,提出“本体论的承诺”说。
他认为,任何哲学、科学的陈述都蕴涵着承认某种存在的本体论断言。例如,说“这是一条白狗”,就承诺了白狗的存在;说“有大于100万的素数”,就承诺了这种素数存在。因此,“一个人的本体论对于他据以解释一切经验乃至最平常的经验来说,是基本的”。接受一个本体论,原则上就是接受一个科学理论,科学总是把无秩序、零星片断的原始经验,组合安排成为简约的概念结构;而哲学本体论就是“择定要容纳最广义的科学的全面的概念结构”。[2](P.10,16)本体论承诺同科学理论构建一样,要通过语言分析来建立和澄清。
蒯因批判两种常见的错误的本体论承诺。第一种认为命名就是承诺了名字所指称的对象存在。例如,它主张命名了“飞马”,飞马虽然是非存在,也必定存在,至少作为人心的一个观念存在。蒯因讥刺这就像柏拉图论证非存在必定在某种意义上存在,是“柏拉图的胡说”,并且揭露它的错误是混淆了指称和意义,根据罗素的摹状词学说,有意义的陈述不一定都预设了指称对象的存在,命名并不保证有本体论的承诺。第二种是共相的本体论承诺。它认为使用一个谓词如“红”,就是承认在具体的红色事物之外存在由这个谓词表示的共相“红性”独立存在。蒯因持唯名论倾向,反对这种柏拉图主义的实在论,认为它错误地在个体事物之外虚构了抽象的共相实体。
蒯因认为规约本体论承诺的正确途径,是使用外延语言的现代一阶谓词逻辑中的约束变项(或称量化变项)。早在1939年他在《对本体论问题的一种逻辑探究》(ALogicalApproachtotheOntologicalProblem)一文中,已提出本体论承诺的公式:存在是约束变项的值。约束变项是有量词约束的变项。有存在量词的变项(ヨx)表示“至少有一个东西”或“有一些东西”,有全称量词的变项(Vx)或(x),表示一类中“每个东西’’或“一切东西”。变项x作为不确定代词代表一类事物的变域中取任一分子为值,变项的值就是代入命题、置换变项的事物,表示此事物的名词则可称为“代代词”。蒯因只承认个体量化,否定谓词量化。他认为约束变项是指称的基本手段,陈述一个存在物,可看作一个变项的值。本体论承诺可以是具体、多样的,但都是在(ヨx)或(Vx)这些量化变项所辖的范围,确认个体化事物的存在。例如,说“有些狗是白的”,就是承诺某些狗的个体存在,它们是白的,绝不是承诺狗性或白性是实体:说某些动物的种是杂交的,那些动物的“种”也是作为可个体化的存在物被承诺。大而言之,一个科学理论的语言结构,决定了其约束变项的取值范围,也就是承诺了这个值域中的存在对象。
蒯因指出:存在为约束变项的值,表述语言使用中的本体论承诺,完全是同语言相关的问题。这种本体论承诺的标准是中性的,而实际上要采取什么本体论的问题仍未解决。对种种不同或对立的本体论,难以作出绝对裁决,而应采取“宽容和实验精神”。当然,蒯因并不是主张任何理论的任何本体论承诺都是真的,但是他的本体论承诺的标准确实有很大的相对性。
蒯因的本体论承诺说,实质上是用现代逻辑分析手段采纳了实用主义的多元真理观。他说:“要问一个概念系统作为实在的镜子的绝对正确性,是毫无意义的。我们评价概念系统的基本变化的标准必须是一个实用的标准,而不是与实在相符合的实在论标准。”承诺一种本体论,就是“为科学选择一种方便的语言形式,一个方便的概念体系或结构”。[2](P.73,43)
三 贯穿行为主义的自然主义语言哲学
蒯因的后期著述,本着逻辑实用主义精神建树自己的语言哲学,深化他的本体论相对性思想。
他认为近代以来的经验论经历了五个转折:从观念转向语词;语义的焦点从词项转向语句;语义的焦点从语句转向语句系统;摒弃分析一综合的二元论;最后达到他的摒弃传统第一哲学的自然主义,那就是,发展实用主义的经验论,将语言的意义看作可观察的行为经验的后果。皮尔士、詹姆斯和杜威都是自然主义哲学家。蒯因赞赏皮尔士提出实用准则,用行动的效果说明信念和概念的实际意义;他不接受詹姆斯的唯心主义感觉本体论。蒯因声称他的自然主义哲学是一种“素朴的和非再生的实在论的本体论路线”,主张“物理对象,一直到最具假说性的粒子,都是真实的”,科学系统则是相对可变、可修正的,不恪守绝对真理,而采取一种“可错主义”。[3]
蒯因的自然主义语言哲学贯穿一种行为主义。他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性的艺术”,完全依赖于主体间可交流的意向,应当根据人在社会生活中对可观察的刺激的反应加以说明。逻辑和语言不是先天完善的工具,应当开阔地考察语言发生的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他具体研究儿童学习使用语言时,语言指称对象的形成过程:婴儿最早会说母亲、红和水三个词时,不能清楚辨识它们指称的三个不同对象,往往用三个词一起对某种刺激情况作出反应;后来才学会辨认出个体对象存在和使用个体词,这就有了“个体化的内在模式”,涉用“本体论的词”;继后逐渐懂得一类对象的同一性,学会用普遍词来指称。对各种特定的语言和非语言的刺激作出行为反应,这构成一个人所掌握的特定语言的基础。[4](p.ix)
蒯因指出:既然语言是对环境列举的经验行为反应,它不能给人提供探悉物自体的通道;语言的意义随着人的行为倾向而多样可变,有相对性、不确定性。历来有些哲学家主张意义是某种独立、固定的精神实体,语言是这类实体的标签。蒯因批判这种语义学是“博物馆神话”,在这个“博物馆”中,语言成了僵死的精神实体陈列品的标签。[5](P.27)
根据语言的不确定性、相对性,蒯因进而提出语言的译不准原则和本体论的相对性。不同种类的语言作为对环境刺激的行为反应,受制于复杂多样的社会和心理因素,必然有多元性、差异性。不同的人将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会有不同的“翻译手册”,它们虽然都和语言倾向的总体相容,彼此之间却并不相容,没有绝对划一的译准模式。为理解这种语言的译不准,要追溯到“根本的翻译”,就是对尚未接触过的人群的语言进行翻译。例如:土著部落人见到一只兔子跑过,便说土语“Gavagai”,语言学家用英语记下“兔子”一词,后又屡次在有或无兔子跑过的观察语境中考察土著人的行为倾向,获得土著人说“Gavagai”的刺激意义。这只是推断出翻译此词的总体倾向,并不能断定英语“兔子”已绝对译准土语“Gavagai”,因为“Gavagai”在其他条件下会有不同的刺激意义,就得改换翻译表达式。这里,蒯因并不是忽然热衷于研究语言的翻译理论,而是为了通过对语言的哲学理解,论述科学知识体系中的本体论的相对性。上述实例,只是翻译一个观察语句,理解和翻译理论语句的真值,则不仅取决于非语言的环境刺激,还得求助于一些包括哲学在内的背景理论假设,更难做到绝对准确,有时甚至连名字的指称都不可测知。大而言之,各种科学理论体系都是适应环境和经验的有用工具,各有互不相同、相容的本体论承诺和概念结构,因而在有不同约定性的科学理论体系之间,没有公共测度和翻译的标准。人们有为任何理论体系选择本体论承诺的自由。不同科学体系的语言各有自己的本体论,概念系统的变换总伴随着本体论背景和语言意义的变换,彼此之间不可公度。蒯因关于语言译不准和本体论相对性的观点,对20世纪60年代初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ual Kuhn)形成科学范式之间不可通约的学说,有直接影响。
蒯因虽以兼容实用主义方式改造分析哲学,但也仍秉承、发展弗莱格和罗素的逻辑思想,逻辑研究成果丰富,特别在两个方面引人瞩目:第一,他在《数理逻辑的新基础》中提出新的数理逻辑系统(简称NF),改进罗素和怀特海在《数学原理》中建立的系统(简称PM),他只用属于、析否和全称量化三个概念,更为简约地构造数理逻辑的概念系列。1972年他在《逻辑哲学》中否定集合论属于逻辑,实际上挖掉了逻辑主义的基石。第二,他在《指称和模态》等文章中,批评了刘易斯(C.I.Lewis)、克里普克(S.A.Kripke)和玛库丝(R.B.Marcus)等人的模态概念和量化模态逻辑,认为这会导致指称含混,而且由于其模态语义学诉诸亚里士多德的本质属性概念,会陷入传统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这就引起美国哲学界围绕模态逻辑的量化和语义解释问题的热烈争论。
蒯因哲学问世,在英美分析哲学界激发很大反响。1970年其弟子戴维森(D. H. Davidson)和欣梯卡(J.Hintika)编的《语词和异议》(WordsandObjections)、W.沙汗等编的《蒯因哲学评论集》(1979年),汇集了围绕蒯因哲学争论的主要文章和蒯因的答辩。支持蒯因变革分析哲学的取向的人为数不少。和他年资相仿、同在哈佛大学任教的古德曼(N.Goodman)同他观点相近,建立了一种现代唯名论和现象主义哲学体系。
蒯因哲学对当代美国哲学演进有深刻影响。它打破逻辑经验主义的基本理论框架,使后来的分析哲学家能开创多元化的种种新学说;它拓开实用主义思想进入分析哲学的途径,这成为当代美国后分析哲学和实用主义兼容而为一体这种显著特色,也发展为当代美国新实用主义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与趋向,它是更具建设性的。蒯因开启了20世纪后半叶美国后分析哲学的进程,它虽分立为多元学说,但有三个主要诸派基本相似的新趋向:第一,它吸纳、融和了原先和逻辑经验主义相对峙的实用主义,使分析哲学及相关的语言哲学、科学哲学立足于一种动态的整体经验论。当今美国实用主义的主导趋向也已更新为兼容分析哲学型的新实用主义,表现在对分析哲学的渗透、改造之中。第二,它不再拒斥形而上学,但也不是简单地回归传统的形而上学,而是以实用主义的动态的整体经验论,重建分析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这种动态的整体经验不同于传统分析哲学依据的静态、孤立、无形而上意义的原子式的经验,而有形而上学背景意义并富有历史文化含义。从蒯因的多元真理的本体论承诺、戴维森(D.H.Davidson)的语言本体论和“变异一元论”到塞尔(J.R.Searle)的言语行为理论以意向性为联结语言、心智与实在的中介、论述意向与实在的因果性与整体性,皆可见此特征与趋向。后分析哲学也扩及哲学史研究,包括希腊哲学(特别是奠立分析理性的亚里士多德哲学)研究,但这种为分析哲学“寻根”,是为印证分析哲学的历史合理性和用之研究哲学史的有效性,并不表明当今美国后分析哲学放弃其实用主义整体经验论的形而上学基础,而已回归传统哲学。第三,心智哲学(philosophy of mind)已是后分析哲学探究的前沿领域。这既是后分析哲学用于科学发展的需要,也是重建分析哲学之形而上学根据的需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综合科学认识论、现代逻辑、语言与心理、人工智能为一体的认知科学理论等相关新学科在产生、发展,各种分析哲学学说乃至乔姆斯基(A.N.Chomsky)的语言哲学,也大多深入到心智哲学这一前沿层面,探究身、心关系和语言、认知的终极本性,
都在此领域做了大量探讨,各有立说。蒯因的动态的、内涵历史文化要素的科学知识整体论和本体论相对性的思想,直接促使当代美国科学哲学中托马斯·库恩(T.S.Kuhn)等人的历史主义学派形成,对后继的新历史主义学派、科学实在论的科学哲学也一直有不同程度与方式的影响。
[1]Wang Hao. Beyond Analitic Phiilosophy[M]. Boston: The MIT Press,1986.
[2]蒯因.从逻辑的观点看[M].江天骥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3]蒯因.实用主义者在经验论中的地位[J].哲学译丛,1990,(6).
[4]W.V.O. Quine. Word and Object[M]. Boston: The MIT Press,1983.
[5]W.V.O. Quine. Ontological Relativity and Other Essay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9.
——充满艺术的实用主义者Eva Sol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