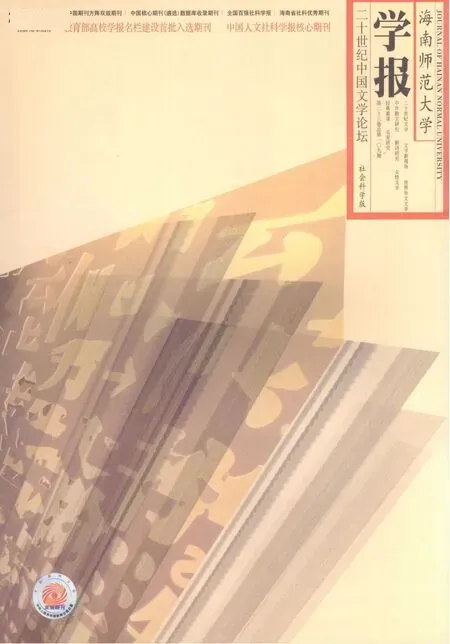文学史写作的求“真”精神
张 瑜,张 琳
(1.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250014;2.河北政法职业学院管理系,河北石家庄 050061)
文学史写作的求“真”精神
张 瑜1,张 琳2
(1.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250014;2.河北政法职业学院管理系,河北石家庄 050061)
在多元化重写文学史的倡导下,文学史写作与研究仍需遵循一定的规范。文学史写作应遵循求“真”精神。所谓“真”的精神,即对文学历史抱以真诚而非凌虐、同情而非苛责的态度。“真”是文学史写作者保持文学史独立性的根本前提和最高原则。
文学史写作;“真”;历史的同情;史料
文学史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虽都以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但三者的评价标准不同,文学史注重通观,文学理论追求彻底性,而文学批评则强调品位。既如此,文学史写作就应在客观、全面的前提下对于历史上发生过的文学事件进行整体性的观照,而不是偏执地按照书写者个人的好恶来进行肆意的臧否、筛选。这就要求史家在从事文学史写作时必须追求“真”的精神。可以说,“真”既是文学创作的最高境界也是文学史写作的基本原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学史写作的“真”即意味着对历史抱以真诚而非凌虐、同情而非苛责的态度。
一 文学史写作求“真”的必要性
“真”是文学史写作者保持文学史独立性的根本前提。福柯认为“在人文学科里,所有门类的知识的发展都与权力的实施密不可分……总的来说,当社会变成科学研究的对象,人类行为变成供人分析和解决的问题,我认为,这一切都与权力的机制有关……”[1]历史的实践也证明,易代之际,历史的真相最容易失去。文学史作为历史写作的一种,也常常随政治、经济等社会领域的波动而发生变异,甚至失去自身的独立判断。历史变动最为剧烈的时期,尤其是在朝代更迭之际,历史的真相往往因政治上的因素,使得史家不能或不敢秉笔直书,至多是曲笔隐晦地表达一己之见。文学史的真相也就往往在历史真相的缺失中被遮蔽。而“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不能遮蔽历史,更不能改写与歪曲历史。”[2]说起来,这本是不言而喻的常识问题。文学史写作、研究,当然要从历史实际出发,从作品和史料的实际出发。然而,恰恰是在这个最简单的常识性问题上,我们接二连三地重蹈了“非真”的覆辙。
新中国成立后,新政权同时具有了在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的双重权威,即不仅拥有政治领域的领导权,还拥有思想文化领域的绝对支配权,文学日益沦为按照政治需要运作的“齿轮”和“螺丝钉”。长此以往,在文学领域形成了以政治文化为价值中心的最高秩序,文学的独立性、自足性被漠视,并越来越成为政治文化及社会思潮的附庸。在“政治运动”的干预之下,文学史的本来面目遭到了“篡改”,以至面目全非。
建国初问世的几部较有影响力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就是很好的例子。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观点统领全书,明确地表示文学史要为无产阶级服务,强调政治标准第一且唯一,要求通过“廓清一切蒙蔽文学历史真实的谬论邪说”,阐明新文学“在中国革命运动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如此鲜明的功利目的性和明确的政治指向性,使得史家所持有的“真实”已经偏离,走上了非真的邪路。如,在战斗的政治思维的统挈下,漠视文学的本体规律,将现代作家作品置于简单的新旧、敌我、主从的话语系统,且就此将周作人、张资平等归入敌方,并把鲁迅的创作道路归纳为由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友人直至一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成长道路的投影;在阶级意识的支配下,认为胡适的新诗创作远逊于李大钊,因为胡适的《人力车夫》等诗阶级意识模糊、充满毒素,而李大钊的《欢迎陈独秀出狱》等诗则满沁着阶级友爱与战斗精神;此外,在实证式的思维模式的影响下,作者对于文本的评价往往超出了审美的范畴,如认为郭沫若的《女神》“过分神往于人和自然统一的物我无间的境界,而没有把自然看成是人类斗争的对象;在赞美近代物质文明的诗歌中,他歌颂了20世纪的名花——近代文明的严母,而没有看出在资本主义文明外衣掩盖下的阶级矛盾和斗争。”这种非分的要求已经与要求哑巴唱歌无异了。显然,刘绶松的文学史写作是严格按照政治指令进行的,这种与政治权威的无限趋同性使文学史丧失了自身的独立风貌,也就此失去了文学作为历史的真实性。
相形之下,王瑶的《新文学史稿》虽也是政治化的产物,但由于相对保持了对于“真”的诉求,因此能在政治与文学的夹缝中间寻找到巧妙的中间物。王瑶从《新民主主义论》等学说中寻找理论支撑,突出与强化其“人民本位主义”、“革命的现实主义”的文学史观,“表现为可以操作的写作模式,则是以‘反帝、反封建的方向’和‘文学与普通人民的关系’为考察中心,以文学的现实性或与社会的关系为评价的切入口。”[3]如《新文学史稿》的第一编注意到了“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各种思潮、观念的差异,而一致的要求则是反对旧文学“封建性的内容”和“文言的形式”,是“要求建设一种用现代人的话来表现现代人思想的文学”,是民主主义文学取得正宗地位。“这种史述实际上就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政治性评价,而比较切近史实,也有较大的包容性。”[3]另外,他并没有把无产阶级分析法照搬到《史稿》中来,而是以“反封建”、“现实性”等词语作为从政治到文学的中间物,并在此维度的关照下,给予郁达夫“性的描写”、巴金笔下燃烧着的青年的信仰与感情、曹禺文本中爱与死的纠葛以较为公允的文学史评价,也没有对当时已有定论的“汉奸”周作人略过不谈或大加挞伐,而是仍然实事求是地进行了具体作品具体分析,并客观地指出“周作人、林语堂他们都指出文章中透视‘有一个叛徒和一个’,和我们的说法不同”。[4]正因为王瑶坚持了文学史家对于“真”的学术诉求,才使其文学史虽有若干不尽如人意之处,却始终能够成为现代文学史写作的坐标式文本;也才有后人作出如此评价,“他四十年来对于中国文学史研究的观念、方法的现代化与科学化问题的孜孜不倦的探索,为铸造一种我们这个世纪学人应该拥有的最值得宝贵的学术品格,为现代文学史学科沿着科学化的轨道进一步发展,给现代人和后来者,提供了一份值得珍视的精神遗产。”[5]
可见,只有坚持“真”的文学史写作这一价值评判标准,史家才能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的真面目,文学史也才能避免被外力过度撕扯以至失去本我。换言之,只要文学史家真正从自己的阅读体验出发,摒除外界的干扰,依照自己的独特的视角去评判文学现象、鉴赏文学作品,他的著作就能够获得长久的生命力。这在价值多元的“重写”时代,仍是重要的警示。尤其是在文学大众化、消费化的今天,张爱玲、徐志摩、沈从文等大有把鲁郭茅巴老曹赶下神坛的趋势,文学史家更应提防从政治话语控制的极端走向另一个或大众或消费或玩世的极端。
这是史家在求真的基础上保持文学史的独立性的一个方面,即保持文学抽身于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
另一方面是指中国本土文学史写作本身的独立样态。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学都处在如何走向世界的焦虑之中,区别只在于栉欧风沐美雨与对苏联老大哥的效仿。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对于过去32年的文学活动需要进行梳理和检视,以便更好地指导新文学为新政权服务。然而,文学史写作在当时几无范例可循,于是苏联模式便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的便捷样本。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建国后几部有重大影响的文学史都浓重地保留着苏联模式的生硬照搬和摹仿的痕迹。当然,新政权初创,对于文学史的编写还缺乏经验,但简单机械地模仿却也在事实上伤害了中国文学史的独立性和自足性。温儒敏认为这是学术研究体制化、组织化、生产化的产物,是“为革命修史”、妄言“理论显示度”的冒进恶果。他选择了张毕来的《中国新文学史纲》、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和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作为言说对象。认为“这些论著在推进现代文学这一学科的建立,并将现代文学研究与教学结合方面,都做出了一些贡献。但是又都程度不同地受到苏联当时‘正统’的文学史观念的影响,即特别注重运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标准来衡量作家作品,用阶级分析方法考察文学历史现象,表现出浓厚的政治化色彩。……他们由于都是初步学习和运用新方法、新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仍缺乏深入的了解,加上又受当时苏联比较僵化的研究模式的影响,在急用新学的情况下,就很容易产生教条主义的生硬的毛病。所以这几部文学史都有生搬硬套马列词句、用政治分析代替艺术评价和以论代史、以现实原则强行剪裁历史等弊病,并都程度不同地表现出粗暴的‘政治沙文主义’。这些文学史大同小异,都在共同建构一种新的知识体系并且已经顺利地纳入当时的教学与学术的生产体制,在‘消费’过程中发生实际影响,影响着人们对文学经典、历史与传统的理解,甚至影响着人们的阅读方式。”[6]可见,这种简单的照搬模式扼杀了研究者的学术个性,而且日益成为学术研究的顽症,使文学史写作、研究受到干扰而偏离了健康的发展轨道。
应该说,在当下多元化的今天,回顾这一段时期的文学史写作有助于我们增强自省意识,促进文学史写作的健康发展。通常我们所谓创新,无非新方法、新观点、新材料三途,在1980年代西方文艺思潮的冲击之下,文学史的重写也更多地呈现为一种写作方法的创新。然而,前车之鉴警示我们:“对于文学史家来说,所有的理论设计都是达到对象的桥梁。”[7]42因此,对于来自异域的文学史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我们应理智地进行鉴别,合则取之,不合则弃之,不能因单纯追求理论方法的创新与视角的前沿而丧失文学本身的真实,以至削足适履、方凿圆枘。无论是建国初的马克思主义,还是新时期以来巴赫金、福柯等的理论冲击,都只是可以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转化变形,但切忌照搬、套用。因为“作为研究思路,文学史家不同于文学批评家之处,就在于其是为了更好地阐释对象而选择某一理论,而不是为了展示或论证某一理论而选择史实”。[7]24因此,在方法论媚惑文学研究的当下,研究者应保持必要的理智与从容,以对“真”的追求诉诸文学史写作,警惕并避免理论对于文学史写作的阉割。没有对于“真”的坚守,即使舶来形形色色的新观念、新方法,文学史的书写也会是支离破碎,不可能在内在精神上形成真正意义的文学的历史。
二 历史的同情:文学史家的“真”精神
20世纪上半叶史学家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一文中提到:“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吾人)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庸廓之论。”
谢泳在文章中说:“钱穆在《国史大纲》的扉页上曾写过几句话,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公民对于本国以往的历史需保持‘温情和敬意’,他虽然说的是中国的古代历史,但是对于中国的现代史,也应当以这样的态度对待。”[8]
无论是陈寅恪所言“具了解之同情”,还是钱穆所秉之“温情和敬意”,于今人研究古人著述仍具有启示意义,同时也是史学研究所能达到的较高境界。陈寅恪以“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作比,可知对待文学创造活动尤需此等“了解之同情”。具体到文学史写作来说,历史的同情并不是没有是非判断,而是在简单的判断之前,了解历史处境、增加历史沧桑感,“借助细节,重建现场;借助文本,钩沉思想;借助个案,呈现进程。”[9]因此,“所有不属于我们这时代并且不属于我们的文化的艺术作品,都一定需要我们置身到创造那些作品的时代和文化里去。”[10]
那么,在“历史的同情”的观照之下,文学史就不再仅仅是属于胜利者的战利品、附属品,而应是对文学现场的尽可能逼近。需要我们带着历史的同情回到现场。这在一方面,许多研究者贡献了可资借鉴的成功范例。如钱理群用“单位观念(意象)”研究法,极力用作家自己的“个人话语”去解释作家自己的作品,而不是将其纳入现成的某一“时代话语”中去,成为某一既成理论框架的“实证”。同时,他又不断寻找自己(研究者主体)与作家、作品(研究对象)之间心灵的沟通与契合,并在对作家、作品做心灵的探寻过程中追求自我生命的净化与升华。[11]114-115具体来说,钱理群的文学史写作所采取的方式是“文学史中的每一个历史细节都必须是有充分的史料根据的,绝不允许杜撰;所要追求的是报告文学那样丰富而具体、生动的典型现象(人物与事件)与典型细节的描述,以及由此造成的现场感”。[12]在此观念指导下,钱理群首先“回到鲁迅那里去”,寻找能够揭示鲁迅独特的思想风貌的单位观念(意象),如“一切”与“无所有”、“先觉者”与“群众”、“爱”与“憎”、“人”与“兽”等,再把鲁迅全部著作及重要的、具有可靠性的回忆材料中凡是有关上述单位观念(意象)的词句全部分别抄录,取得“量”的依据,然后再逐一进行“质”的分析与开掘,尽可能做到准确、辩证。这样立足文本,寻找细节,既能揭示鲁迅的主要精神,又充分注意到其表现形态的复杂性、丰富性。而“所有这一切看似拙笨的努力,都贯串着一个自觉的追求——尽可能地接近鲁迅‘本体’,揭示其心灵的本来面目”。[11]109
另外一位从事当代文学史写作的研究者在此方面也为我们提供了优秀的摹本。洪子诚认为文学史的编写重点不是对文学现象的评判,即不是将文学问题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抽取出来,按照史家的价值尺度任意臧否,而是应努力将问题放回到历史情境中去审查,即“能整理、保留更多一点的材料,供读者了解当时的情况,能稍稍接近‘历史’,也许是更为重要的”。[13]因此,他更关注文学的产生、演化及文学活动背后的传播、体制等问题,以增加我们靠近历史现场的可能性、真实性。“这种方式将致力于还原历史情境,通过‘文本的语境化’与‘语境的文本化’使文学史的研究转变成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的平等对话,这不是荒诞地力图否定相对确定的真理、意义、文学性、同一性、意向和历史的连续性,而是力图把这些因素视为一个更为深广的历史——语言、潜意识、社会制度和习俗的历史的结果——而不是原因。”[14]
可见,所谓回到“历史现场”,不仅要回到特定的空间位置,回到事情发生的那个时代,而且要设身处地回到事情正在发生的过程之中,与历史人物一起经历其事,不是作为旁观者,也不仅仅是参与者之一,而是和所有亲历者一起经历他们各自所经历的全部过程。研究者回到现场是他展开文学写作的前提,预设情境也并非完全拒绝文学的衡量尺度和价值标准,而是以历史的同情眼光,对于文学活动、文学事件进行客观的筛选、剪辑、整理、描述,让读者通过对历史细节的触摸,回到历史现场,对文学活动作出合乎历史原则的判断和定位,这正“犹如上演一出戏剧,研究者如场记,知道每一位角色做什么和为什么会这样做。他只是客观地展示实情,不必导言剧情”。[15]
中国历来有“国可灭,史不可灭”的传统史学观念,可以说文学史最大的特征和价值,就在于“真”。文学史而失“真”便不能称其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史。因此,史家责无旁贷地要以为文学史存真作为终极追求。当然,特定政党治下的政权完全不欺凌文学史的神圣与尊严,是不可奢望的想象,但是作为严谨的文学史家,有史德的文学史书写者、研究者,则必须以近于真为自己学术事业矢志不渝的信念。毕竟,胜败,只是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变化,所谓“兵家之常事”也就意味着,失败者或少数的一方绝不是历史的垃圾堆;史家更不能以胜者王败者寇的观念对于文学现象进行生硬的撕扯。因为真正代表文学发展规律的往往在于少数人的见解,而非多数人的潮流。例如,对于胡适、张爱玲、梁实秋、沈从文等其人其文的文学史评价,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不公正的。只是到上世纪80年代之后,这一系列作家,尤其是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徐訏、无名氏等才像出土文物一样浮出历史地表。而实际上,对于这些作家的发现并不困难,并不是夏志清拥有的材料比我们丰富,而是“非真”的文学史态度遮蔽了史家们的眼睛,令史家不能充满“温情和敬意”地对历史抱以同情,从而使这些作家作品被有意地放逐了。可见,相对公正的评价、相对客观的观照离不开求“真”的态度,离不开求真态度引导下对于历史所抱以的同情和尊敬。虽然胡适说“历史……可以任人打扮”,但其前提还必须是要保证历史这个“小姑娘”不被打扮得面目全非。
三 史料运用过程中体现的求“真”精神
由以上论述,我们知道文学史写作过程中,“真”是第一位的。这也就是要求我们在进行文学史写作时,必须要凸显一种真实感。然而,史家对于求“真”精神的秉持也好,写作过程中所抱有的“历史同情”也罢,都只是属于史家精神活动的层面,读者难以把捉。那么,“真”究竟如何物化在文学史文本当中呢?即史家如何才能以具体的文学史写作给人以真实感呢?这就涉及到对于史料的取舍问题。本文以为,史料运用过程中也应体现出文学史家求“真”的精神。
首先,如何搜集文学史料?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认为,对于史料应做竭泽而渔式的挖掘。即,在挖掘、整理史料的过程中,不是关注文学史料本身的真理性,而是关心如何在不考虑文学史料本身的对与错或优与劣的前提下,尽可能全面地将搜集到的史料进行整理和分析,并在此相对全面的史料研究基础上,探寻文学发展的规律以及在这一规律性形成过程中所经历的变化。这样,我们就能相对地突破新旧、敌我、优劣、左右等二元对立的价值标准,更全面更真实地返回文学现场。在这样一种认识机制中,我们所需要处理的就是作家、作品在某时某地的出现意味着什么,处身于彼时彼地的中国人为什么要对生活做如此想象等一系列问题。如,以知识考古学的挖掘方式,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时间虽然短暂,却样态丰富,流派纷呈。如果不以是否合时宜或政治方向是否正确为选择标准,我们就能挖掘出像周作人、胡适、梁实秋、施蛰存等这样创作个性非常突出的作家。相反,若是单纯以政治规约为文学史料的选取标准,那么,一部炫目的文学史就会变得干瘪、枯燥。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虽有很多弊病,却仍为国内的现代文学研究界提供了更为开阔的视野。另外,改写和修订是现代文学史作品的一个突出特点。例如,老舍的《骆驼祥子》和郭沫若的《女神》,作家都在不同时期进行过改写,有的版本甚至与初版本大相径庭。这也需要史家进行搜集。因此,只有对史料进行考古式的挖掘,我们才能通过“文本的语境化”与“语境的文本化”使文学史的写作、研究呈现为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的对话,才能在对话中彰显出一个时代之于另一个时代的发展或者是演变。因为,究其根本,文学史写作本身也是一种对话:与凝聚为文本的作家心灵对话,也与落实为论著的各式文学史诠释者对话。
其次,何种史料可以进入文学史的言说范畴?
价值无涉理论是马克斯·韦伯倡导的一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准则,要求研究人员在进行研究时,不能带有任何预设的价值取向,因为学术研究只解决“是什么”的问题,而不是解决“应当是什么”的问题。当然,所谓价值无涉并不是没有价值标准,而是说,在进行史料遴选时首先要抛出先在的价值定势,给各种文学形态以平等的对话、竞争的空间。这有点类似于在史料搜集过程中的竭泽而渔式态度。其必要性不再赘言,但就其价值预设的恶果而言,建国初的文学史也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教训。
客观地来看,王瑶的《新文学史稿》中所涉及的文学史料还是比较丰富、多元的。然而到了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就开始明确地对胡适、胡风采取否定的态度,且对路翎、鲁藜、绿原等当时已经被列入批判对象的“七月派”成员则完全不提。至1958年以后出版的现代文学史,由于受政治气候的影响,丁玲、艾青、冯雪峰、姚雪垠、秦兆阳、黄谷柳等几十名作家都突然失踪(偶有保留者,也都冠以“丁玲批判”、“艾青批判”字样)。到了“文化大革命”前的1964年,连夏衍、阳瀚笙、邵荃麟、瞿白音等作家也都受到公开批判,于是现代文学史中入选的作家作品就寥寥无几了。直至“林彪、‘四人帮’这些野心家、阴谋家篡权期间,事情更是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50多年文学史只能讲鲁迅、浩然两人,成了所谓‘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于是,“在吃够了林彪、‘四人帮’苦头之后,人们痛定思痛,不得不去回顾,不得不去思考,也就发现:问题不仅出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里,一些随意修改历史、隐瞒事实真相的不科学、反科学的做法,早在‘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里就存在了(当然,程度、性质都和10年浩劫期间不一样)。”[16]1980年代初,严家炎的这种观点代表了一种普遍的看法,即认为在“政治运动”的干预之下,文学史的本来面目遭到了“篡改”,因此,要“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对于文学史料进行重新搜集和整理便是亟待进行的工作。
毋庸置疑,包罗万象的文学史是不可想象的。所谓价值无涉只是理论设想。史家不可能把搜集到的所有文学史料都平等地置于文学史的叙述之中,总要有所取舍、侧重。毕竟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文学史写作都是一种主体性的参与和想象,现代文学史的长河也只能流动在不同时期书写者、研究者们的感受、发现和阐述之中,因此,文学史在其时间维度上是一个不断流逝的过程,而在其空间维度上则是一个不断阐释的过程。这种阐释性表明,文学史不是与阐释者完全隔绝的物自体,而是一个站在阐释主体面前的阐释对象。那么,对于史料的选取,史家是否可以根据自己对于文学史的想象和设计任意取舍文学史料?本文以为,主体性的彰显并不意味着任意而为,而是在一定规范之下做出的自由选择,正如艾青所言,最大的自由是使自己成为约束。因此,对于史料的选择应该是在价值无涉的理论前提下,以史家的史识和价值观念为标准做出的合理取舍。
文学史家的主体性也恰恰就体现在这一方面。应该说,一部文学史著作对作品的筛选取舍,其实就是史家价值观念的体现,也是文学史之反复重写的理论前提。韦勒克指出:“在文学史中,简直就没有完全属于中性‘事实’的材料。材料的取舍,更显示对价值的判断;初步简单地从一般著作中选项出文学作品,分配不同的篇幅去讨论这个或那个作家,都是一种取舍与判断。甚至在确定一个年代或一个书名时都表现了某种已经形成的判断,这就是在千百本书或事件之中何以要选取这一本书或这一事件来论述的判断。”[17]仍以现代文学史的写作实践为例,无论是1930年代以新旧为价值标准的进化论范式,还是建国初期以唯物史观或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为基础的阶级论范式,亦或1980年代中期“重写文学史”以来,以现代性为评估体系的所谓现代性范式,文学史家的文学史观无不是通过对文学史料的选择、取舍体现出来的。唯一不同的只是,随着文学史写作的成熟和现代文学史学科的正规化,文学史观更趋向于审美性和文学性的维度。
最后,关于文学史料真实性的考订。
史料的真实是文学史家做出正确、真实判断的必要保证。因此,史家应该具备对于史料的甄别能力,即对史料进行去伪存真的能力。史料考证不是文学史家的目的,而只是其达到真实的手段。这方面,文学史家要具备历史学家的科学精神,更需要耐心、冷静、审慎的冷板凳精神。当然,这也是以史家广博的学识做保障的。
唐弢在不同地方多次谈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撰原则,1982年10月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现代文学教师进修班”上他就总结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原则:“第一,必须用原始材料。第二,要吸收已有的成果。第三,要适应教学的需要。”[18]原始材料是第一手资料,最能反映出作家作品的真实风貌,所以才是最有力的证据。所谓信史就是要言之有据,而不是言之有理或动之以情。在1983年的《求实集序》中,他又再次重申了这些原则:“一、采用第一手材料,反对人云亦云。作品要查最初发表的期刊,至少也应依据初版或者早期的印本。……四、复述作品内容,力求简明扼要,既不违背原意,又忌冗长拖沓,这在文学史工作者是一种艺术的再创造。五、文学史采取‘春秋笔法’,褒贬从叙述中流露出来……等等。”[19]应该说,史料的真实是文学史写作的最基本的学术前提和具备恒久生命力的质量保证。在这方面,陈平原等一批学者的文学研究堪称典范,其对文学史细节的挖掘和考证保证了学术研究的质量和水准,更为得出有效的研究结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除了真实性之外,史料的选择需要史家的“诚”。这个“诚”字具有非常强的主体选择性。写作者准备向谁负责、为谁说话,就决定他将以什么态度去选择材料、使用材料。可以说这个“诚”字所承载的主体价值取向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部文学史的价值取向。因此,可以说,真实和真诚是文学史料选择的最高标准。
小结
“真”是文学史写作的价值标准体系中最基础也是要求最高的一环,除此之外,史家还需具有“善”与“美”的品格。简单来说,“善”涉及到文学史写作的人文价值追求和文学对人类文明的推动作用,“美”则宽泛地指向叙述方式、叙述语言等文学史本身的表达形式层面的内涵。本文对此两点不拟赘言。总之,尤其是在价值标准多元化的今天,重写文学史要力避“重复”,又要在创新基础上坚持学术规范,否则,“重写文学史”就会脱离其所指含义,成为一种观念意义上的事物或曰“公共的象征”。
[1]〔法〕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31.
[2]董健.找回历史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3]温儒敏.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与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J].文学评论,2003(1).
[4]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卷)[M]∥王瑶全集:第三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194.
[5]孙玉石.作为文学史家的王瑶[C]∥陈平原.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455.
[6]温儒敏.“苏联模式”与1950年代的现代文学史写作[J].北京大学学报,2003(1).
[7]陈平原.小说史:理论与实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8]谢泳.杂书过眼录[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
[9]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5.
[10]〔俄〕车尔尼雪夫斯基.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M]∥生活与美学.周扬,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59.
[11]钱理群.返观与重构——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12]钱理群.略谈“典型现象”的理论与运用[J].文艺理论研究,1998(5).
[13]洪子诚.简短的前言[M]∥1956:百花时代.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14]李杨.当代文学史写作:原则、方法与可能性[J].文学评论,2000(3).
[15]桑兵.从眼光向下回到历史现场[J].中国社会科学,2005(1).
[16]严家炎.从历史实际出发,还事物本来面目[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4).
[17]〔美〕韦勒克,奥·沃伦.文学理论[M].刘象愚,邢培明,陈圣生,李哲明,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32.
[18]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问题[M]∥唐弢文集:第9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371-398.
[19]唐弢.求实集序[M]∥严家炎.求实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3-4.
The Spirit of“Seeking Truth”in the Writing of Literary History
ZHANG Yu1,ZHANG Lin2
(1.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Jinan250014,China;
2.Department of Management,Hebei Vocational Colleg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Shijiazhuang050061,China)
In the course of rewriting literary history,literary history writers and researchers should follow certain norms,that is,the spirit of“seeking truth”must be strictly observed.The so-called the spirit of“truth”is the sincere and sympathetic attitude to literary history,while“truth”is the essential premise and highest principle for literary history writers to retain the independence of literary history.
literary history writing;“truth”;sympathy of history;historical materials
I 206.09
A
1674-5310(2010)-05-0067-06
2010-06-01
张瑜(1981-),女,河北石家庄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2009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河北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张琳(1981-),女,河北石家庄人,河北政法职业学院管理系教师。
(责任编辑毕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