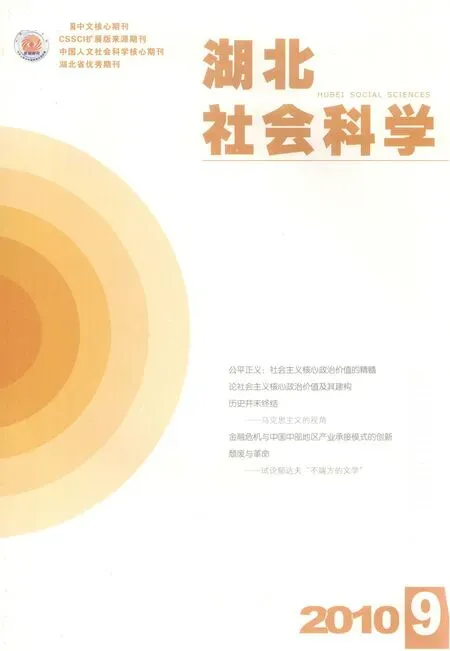老庄道论的三重视域及其与现象学直观的可能对话
李义民
(九江学院政法学院,江西九江332005)
老庄道论的三重视域及其与现象学直观的可能对话
李义民
(九江学院政法学院,江西九江332005)
中文“道”字隐含有一个本源性含义——观看,在《老子》文本中“道”有“徼道”、“妙道”和“玄道”三种不同层次但又内在统一的含义。老庄的玄道就是一个构造世界万物的现象学视域意识。同时,借助于胡塞尔的本质直观,我们可以在“道”的世界中不停地发现、创造新的世界,一个超越了自然世界的真、善、美的新世界。
老子;庄子;道;胡塞尔现象学;本质直观
在《庄子·应帝王》中有一个著名的寓言,南海之帝和北海之帝出于善意为浑沌凿七窍,“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一般认为老庄道学的核心概念“道”就是一个神秘的浑沌,两千多年来,人们对“道”所作的汗牛充栋的注解似乎被庄子不幸而言中,其中虽不乏一些精辟见解,但都没有从理论上超越老庄,也没有全面地切中“道”的真意,往往是抓住一点而不及其余。根据庄子的上述寓言,可以认为传统的对道解释的失败,原因在于哲学方法论上的圆凿方枘,都是使用“凿”的办法。任何哲学的成立首先必须是方法论上的成立,“凿”意味着企图洞穿“道”体以解“浑沌”之密,结果却是使道成为一种僵死的东西。
在老庄那里,“道”是一个活生生的、无限的世界整体,是一个使我与世界“一气”相通的现象学视域(Horizont)。对于老庄和胡塞尔而言,世界首先总是与我们的“观看”相关,其次,明察世界本身就成了哲学的最高要求。因而哲学的前提在于观看,直观是人与世界沟通的唯一通道,只有透过直观返回到一个前哲学的原初本真的世界,人类理性与生活才可能获得一个确定的根基。因此,胡塞尔一生都致力于探讨一种“面向事实本身(Sache selbst)”的方法,而老子重“归根”,庄子重“真人”,老庄都把开启一道直观世界的“众妙之门”作为哲学的最高使命。哲学应当洞察事实本身可以说是老庄道学与胡塞尔现象学的共同立场和出发点。本文通过对“道”与现象学直观的比较,试图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分析“道是什么”这个中国哲学中悬而难决的古老问题。
1.道与观看(Erschauen)。
一般认为,道的本义是道路。道字最早出现在金文中,从行从首。[1](p1138)早期的道字被训为“道路”和由其引申出来的其他相关意义。比如《易经·履》的爻辞说“履道坦坦”,《尚书·洪范》中说“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等等。不过,在造字之初,当人们倾向于把道字作为“道路”或“导引”等含义来使用时,道的一个更本源的意蕴——“观看”——就被完全遮蔽了。在金文的道字中,那个醒目的、处于中心位置的“目”,对造字者而言并不是个随意创造的、可有可无的成分。与字母文字不同,每一个汉字都浓缩着一段文化史,它的每一笔画与构成都包含有特定的对世界的理解和对生活的感悟。笔者认为金文道字中的“目”与“首”不仅仅是在指示着“人”的存在,而且是在表明一种行进中的观看。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测,如果没有“目”的审视,人们会陷入盲目性,会误入歧途,“道”也就不成其为“道路”了。因为只有通过“目”的观看,“道”才能成为某种确定性的东西,比如“道路”、“导引”、“规则”、“言说”等等。
在老庄道学中,“观看”的意义始终以一种时隐时现的方式在“道”中呈现。《老子·二十一章》说:“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以此。”①这里我们可以发现,隐的方式在于道是观看的对象,道总是与观看有关。“道之为物,惟恍惟惚”,它显然不是胡塞尔所说的自然观点中的经验事物,故而是“视之不见”的;另一方面,道又是“其中有象”、“其中有物”、“其中有精”、“其中有信”的“无状之状”、“无物之象”,如果完全不能被观看,那么何以知“道”?所以道始终与观看相关。显的方式在于以道的方式观看,“阅”即通过观看了解,与“众甫之状”相呼应。《庄子·秋水》中也明确地说:“以道观之,物无贵贱”。②这种以道的方式的观看表明道就是观看,一种使“无状之状”、“无物之象”可视的独特观看。
由此可见,在老庄那里,道事实上是观看方式与被观看之物的统一,与胡塞尔现象学的意向活动与意向对象(Noesis -Noema)结构相类似,前者统一于“道”,后者统一于意向性。
2.道的三重视域。
一直以来,人们讨论“道”是什么,却都忽视了在老子那里道具有不同层次的含义,即由于观看方式的不同,在观看中“道”呈现出不同的层次。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两者同出,异名同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老子·一章》)这一章是老子道学认识论的纲领,明确区分了徼道、妙道、玄道三种不同的视域。不过这三者又是统一的,“两者同出,异名同谓”表明徼道与妙道都出自玄道这个普全视域(Universalhorizont)。徼道与妙道虽然“异名”并具有本质差别,但是又“同出”、“同谓”于“玄道”——一个囊括了无限可能经验的世界,简之即“众妙之门”。这三种“道”构成了我们理解世界的三重视域。
徼道是“有欲”之观,这种直观总是从人有所欲、有所为、有所用等目的出发,把事物作为我所欲求的外在对象而不做任何反思。当心灵蒙上了欲望的面纱,知识会被欲望(包括认知的欲望)所遮蔽,能够获得的只能是人类学的知识,而不是关于世界本身的知识。“徼”即边际、界限,徼道只见事实与经验,所以这种知识是有限的、残缺的,其结果是“智慧出,有大伪”。庄子区分了“大知”和“小知”,认为“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小知不及大知”,因为小知只是经验知识,例如“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正是表明经验的有限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老庄对认识可能性的问题确实有一定的反思。总之,徼道作为感性经验的视域,意味着知识的有限性与不可靠性。胡塞尔同样认为在自然的思维态度下,“认识只是人的认识,并束缚在人的智力形式上,无法切中物的自身的本质,无法切中自在之物”,因而“始终面临着倒向怀疑主义的危险”。[2](p38)
妙道是“无欲”之观,是欲望被悬置后对事物与世界的直接把握。无欲就是去对象化,是拒斥自然主义的思维方式,不再把世界作为我所欲求的外部对象。老庄认为在涤除欲望、打扫干净心灵之后,就可以直接把握世界本身的深微奥妙。这是一个通过现象学还原达到“先验意识”的过程。在老子看来就是“致虚极,守静笃”,以观看事物“朴”、“根”等“原本被给予的东西”而“知常”;在庄子则要求“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以彻底排除自然世界和一切成见而“同于大通”。老庄都清醒地认识到,如果要真切地认识外部世界,就必须首先能够在心灵内部把世界“看”个清楚明白。显然,如果内心一片迷茫,何以认清外界?这与胡塞尔的明见性(Evidenz)要求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老子说:“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这段话引起了人们很多误解,后世注家或解为“神遇”,或解为以“道”知物,也有人认为是“神秘主义”、“唯心主义”。笔者认为老子的本意就是强调一种认识的内在明见性,也就是庄子所说的“闻以有知知者矣,未闻以无知知者也”。
妙道与徼道虽然本质区别但又内在关联,两者的一个共同点是“有名”。胡塞尔也认为事实和本质有不可分离性,“每一偶然事物按其意义已具有一种可被纯粹把握的本质”。[3](p3)通过目光转向,我们可以把红纸感性的“红”直接把握为本质的“红”及其观念。这就是本质直观,一种从事物本身把握事物之所是的方法,老子也曾谈到过类似的方法。《老子·五十四章》说:“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这里“以此”的“此”是此章前半部分所隐喻的道,这个道显然不是徼道而是妙道。不过,无论是妙道还是徼道,它们所把握的都是事物的“名”,“事虽殷大,能以一名举”。不过在这里,老庄与胡塞尔有一种十分微妙的不同,尽管老子已经谈到了“美之为美”、“善之为善”的问题,但老庄都不看重对作为事实的“名”(事物的名称)与作为本质的“名”(普遍的观念)进行明确区分,因为他们更在意的是“有名”与“无名”的区别。
3.玄道与晕(Hof)。
“玄道”就是老子所说的“玄之又玄”的“众妙之门”,“徼”与“妙”“两者同出”且“异名同谓”于玄道。也就是说,经验事物及其本质(名)归根结底都在玄道(无名)之中发生并由玄道规定,因此玄道就是现象学里的视域意识。
胡塞尔认为,“所有真实显现之物之所以是事物的显现之物(Dingerscheinendes),只是因为有一种意向的空乏视域(Leerhorizont)围绕着它们并和它们混杂在一起,只是因为它们周围有一圈与现象有关的晕(Hof)。这种空乏不是虚无,而是一种可以充实的空乏,它是一种可确定的不确定性。因为意向视域不是随意可充实的;它是一种意识视域,它本身具有作为关于某物的意识基本特征。尽管这个意识晕是空乏的,它仍在一种先示(Vorzeichnung)的形式中规定了向新的现时化的现象过渡的规则。”[4](p49)这就表明每个事物(有)都有一个潜能性的、无限的但又并不是随意性的视域(无),只有在这里新的事物才能够被经验和规定。同时,每个新的事物本身又具有其自身开放的视域,视域始终是活生生的、流动的视域,“有”与“无”总是处在无限的、非随意性的“相生”过程中。在这里老庄完全可以实现他们“无为而无不为”、无用而有大用、无知而无不知的理想。在胡塞尔看来,每个事物都不是一个孤立的对象,而是一个视域,一个权能性(Vermglichkeit)的“游戏空间”(Spielraum),它在内时间意识中构造着世界。一切事物都处在普遍世界视域之中,相应地,世界视域就是任何事物的存在基地。因此在我们真切地把握任何一个事物之前,我们就已经预设并信仰了一个无限而又统一的世界(即玄道)的存在,否则我们不能认识任何事物。同理,老子也强调要“知其白,守其黑”。
与胡塞尔通过详尽的现象学心理学的分析、描述来揭示世界视域不同,老子则是通过诗意的描述和“正言若反”的方法来指示着玄道的存在。老子有很多对玄道的诗化描述,比如“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第四章》)“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第五章》)以及“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物,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第十四章》)等。
诗意化的描述虽然形象地表达了玄道虚而不无、生而不动、象而无形等特点,但是它缺乏确定性,会引起人们的误解,所以老子同时又大量使用了“正言若反”的方法。这里仅举几例:“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方无隅”,“大成若缺”等等。庄子也使用了这两种方法来表达玄道,这里就不再举例了。
4.自然与生活世界(Lebenswelt)。
玄道与世界视域都为我们指向了一个前科学的世界,老庄认为它是“自然”世界,胡塞尔认为它是生活世界,两者在不同意义上回到了世界本身。老庄认为事物的本质没有确定性的意义,而构造这些事物的玄道才具有终极价值,玄道“虚而不屈,动而愈出”,无尽地进行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灵动过程,但是这个发生过程是一个无目的论的过程,在这里先验意识已经悬置了意志和情感,所以玄道失去了人的意义,它的全部意义就是无知无欲的天真。而胡塞尔认为,事实本身是每一个当下拥有的事物的本质(埃多斯),它由世界视域所构造,每一个构造都是先验自我(乃至人类精神)包含目的论的“原创造”(Urstiftung),这是一个通过“赋予灵魂”(Beseelen)和“意义给予”(Sinngebung)而实现超越的过程,并且只有这种“立义”(Auffassung)才能使对象为我把握而成为我的意向对象。
通过比较可以认为,老庄的玄道不过就是指引我们回归天道、“正言若反”的生活辩证法,他们在悬置了外在世界与一切成见之后也悬置了一切有意义的价值创造,世界失去了与我的价值纽带,成了一个非人的但人又必须归顺的“自然”,因此在玄道中必须通过意义给予和文化创造来拯救自然。晚年的胡塞尔在批判实证主义时说,“是理性给予一切被认为‘存有者’的东西,即一切事物、价值和目的以及最终意义。这也就是说,理性刻画了自有哲学以来的‘真理’……这个词和其相关的词‘存有者’……之间的规范关系。”[5](p989)这个批判对老庄的自然主义同样有效。
其次,老庄的天道哲学坚持了一种彻底的整体论观点,认为每个个别事物只有在整体性的世界之中才具有其是之所是的意义,每个孤立的个体的“有为”、“有用”、“有名”乃至是非、祸福、贵贱、美丑、善恶、大小等等没有任何绝对价值,个体一旦融入世界整体就可以“无为而无不为”、无用而有大用、无知而无不知,所以老庄坚决反对用“名”、“言”这种“特未定”的东西来割裂世界。《庄子·天下》中进一步认为,诸子百家“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导致“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和“道术将为天下裂”的结果。因而只有“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才能感受、认识“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并做到“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庄子·知北游》)这里出现的“天地大美”似乎拯救了道家那个毫无意义可言的自然世界,但是这个“天地大美”的人文精神使庄子浑然不觉地陷入了与其自然立场的深刻矛盾之中。
胡塞尔则认为普全的世界视域虽然是事物成立的基础并包容了一切事物及其一切可能性,但它本身就被每个事物所当下拥有,因此把握每个事物的确定本质非但不能割裂世界,反而正是赢得了一个无限的世界,所以现象学始终是为严格的哲学与科学奠基的本质科学。哲学只有把形而上学的“大钞票”兑换成现象学的“小零钱”,才能获得无往而不是的科学性。在这里老庄的天道精神与西方普遍知识的理性主义传统是彻底决裂的。
通过与现象学认识论的对话,我们可以发现“道”更丰富的内涵。老庄的道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非常接近了胡塞尔的科学精神,这是今天两者对话对我们的意义之所在。同时我们也应当继续发掘老庄人道的天道精神,它意味着一个在世的、进行中的、适时的观看,意味着一种人与世界的某种交融关系,人总是“在—世界—之中—(观看地)存在”着。老庄要求我们不能总是面对事实生活,要求我们过天真自然的生活,“自然”是我们的家,这是一个伟大的“原创造”。但回归自然绝对不是简单地“复归于婴儿”,正如参天大树不能复归于幼苗。一方面,我们需要按照自然规则完成我们的自然使命;另一方面,道也意味着我们在不断地观看世界中也在不停地发现着新世界、创造着新世界,一个超越了自然的真、善、美的新世界,这或许就是胡塞尔的本质直观对我们的重要启示。
注释:
①本文所引用的《老子》全部为通行本《老子》,出自李先耕著《老子今析》,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
②引文使用的《庄子》全部出自: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全三册),中华书局2004年第二版。
[1]高明,涂白奎.古文字类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2]胡塞尔.胡塞尔选集(上)[M].上海:三联书店,1997.
[3]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M].李幼蒸,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4]胡塞尔.生活世界现象学[M].倪梁康,张廷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5]胡塞尔.胡塞尔选集(下)[M].上海:三联书店,1997.
责任编辑 高思新
B223
A
1003-8477(2010)09-0112-03
李义民(1970—),男,硕士,九江学院政法学院讲师。
——专栏导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