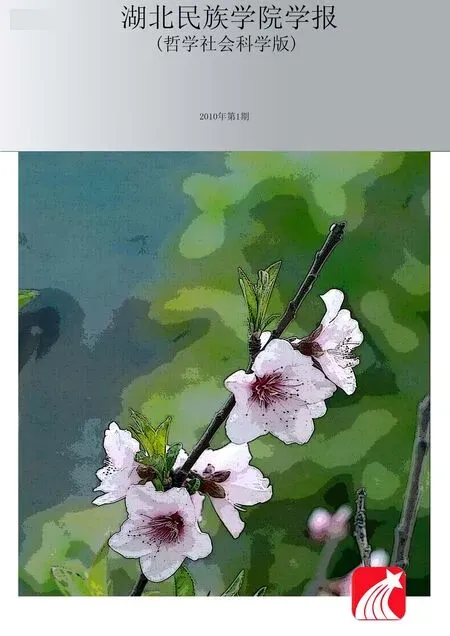家国旧情迷纸上,兴亡遗恨照灯前
——陈三立“崝庐诗”主题思想研究
孙 虎
(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江苏苏州215009)
家国旧情迷纸上,兴亡遗恨照灯前
——陈三立“崝庐诗”主题思想研究
孙 虎
(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江苏苏州215009)
陈三立“崝庐诗”是由历年省墓述哀诗组成,但它已超越了单纯的悼亡的含义,而具有特殊的“感兴”。组诗主题由父子之情述及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进而拓展到家父君国、兴亡遗恨的体认,透视出历史与现实的人生大关怀。在“家国旧情、兴亡遗恨”的主题下,崝庐诗的悲感更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彰显了义宁家族精神传统中“国身通一”的思想。
陈三立;崝庐诗;家国旧情;兴亡遗恨
戊戍政变后,义宁父子(陈宝箴、陈三立)因参与变法被议革职,罢归江西。三立侍父筑室南昌西山,在其母墓旁建屋数楹,“取青山字相并属之义,名崝庐”[1]858,崝庐内“往往深夜孤灯,父子相对欷歔”[2]。不久,陈宝箴即“以微疾卒”①“(戊戍)二十六年四月,不孝方移家江宁,府君且留崝庐,诫曰:‘秋必往’,是年六月廿十六日,忽以微疾卒”,见陈三立.先府君行状[M]//散原精舍诗文集.李开军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三立葬父崝庐,感痛异常,崝庐“遂永为不肖子烦冤茹憾、呼天泣血之所”[1]859。其后三立寓居南京、上海、杭州等地,仍岁时不忘去西山祭扫,或小住一段时间。此间写下了大量与“崝庐”特定地点相关的诗作,故名之为“崝庐诗”。
崝庐诗与传统的悼亡诗不同,具有特殊的感兴寄托。皆由一己之悲情,念及“九州四万万之人民皆危蹙莫必其命,益恸”[1]859。台湾著名学者龚鹏程先生说:“故崝庐者,于散原诗中,亦犹海藏集中之重九,皆有特殊感兴。”[3]因此,有必要研究“崝庐”诗的主题思想,发覆其中隐秘的“特殊感兴”。并且,诗作以“啮墨咽泪常苦辛”(梁启超《广诗中八贤歌》)为一共同语调,真挚悲壮;在艺术上情景理治融为一炉,别具一格,自成体系。
一、父子之情
“崝庐”是陈三立父母墓冢所在,是其寄托父子之情、述哀托思之所,但“崝庐”组诗中的悲情体验,又远远超出通常悼亡诗的范畴,具有特殊的“感兴”。
陈宝箴之死,给三立带来锻魂锉骨的沉哀。生离死别,本是人生不可避免的,但陈三立的这种“沉哀”是超越常情的,具有隐秘的冤楚。陈三立在《先府君行状》中说:陈宝箴在“卒前数日,尚为鹤冢诗二章”,“前五日,尚寄谕不肖,恳恳以兵乱未已,深宫起居为极念。”[1]然不曾想短暂的别离,却成了一生的憾痛,致使“通天之罪,锻魂锉骨,莫之能赎”[1]856,在《崝庐述哀诗五首》中,陈三立全面地倾诉哀痛,追述父子之情,诗云:
昏昏取旧途,惘惘穿荒径。扶服崝庐中,气结泪已凝。岁时辟踊地,空棺了不剩。犹疑梦恍惚,父卧辞视听。儿来撼父床,万呼不一应。起视读书帏,蛛网灯相映。庭除迹荒芜,颠倒盘与甑。呜呼父何之,儿罪等枭獍。终天作孤儿,鬼神下为证。
架屋为层楼,可以望西山。咫尺吾母墓,山势与迴环。龙鸾自天翔,象豹列班班,灵气散光采,机牙森九关。其上萧仙峰,形态高且娴。雨如戴笠翁,妍晴立妖鬟。云霞缭绕之,光翠迴面颜。父顾而乐此,日夕哦其间。渺然遗万物,浩荡遂不还。今来倚阑干,惟有泪点斑。
墙竹十数竿,杂桃李杏梅。牡丹红踯躅,胥父所手载。池莲夏可花,棠梨烂漫开。父在琉璃窗,颏唾自徘徊。有时群松影,倒翠连古槐。二鹤毰毸舞,鸣雉漫惊猜。其一羽化去,瘗之黄土堆。父为书冢碣,为诗吊蒿莱。天乎兆不祥,微鸟生祸胎。怆悢昨日事,万恨谁能裁。
哀哉祭扫时,上吾父母冢。儿拜携酒浆,但有血泪涌。去岁逢寒食,诸孙到邱垄。父尚健视履,扶携迭抱拥。山花为插头,野径逐汹汹。墓门骑石狮,幼者尤捷勇。吾父睨之笑,谓若小鸡竦。惊飙吹几何,宿草同蓊茸。有儿亦赘耳,来去不旋踵。
忆从葬母辰,父为落一齿。包裹置圹左,预示同穴指。埋石镌短章,洞豁生死理。孰意饱看山,隔岁长已矣。平生报国心,只以来訾毁。称量遂一施,堂堂待惇史。维彼夸夺徒,浸淫坏天纪。唐突蛟蛇宫,陆沉不移晷。朝夕履霜占,九幽益痛此。儿今迫祸变,苟活蒙愧耻。颠倒明发情,踯躅山川美。百哀咽松声,魂气迷咫尺。
整首诗分五章,将真挚悲壮之哀情层层推出:首章写梦境幻觉,表示作者对父亲的寻觅。“万呼不一应”、“呜呼父何之”,这是诗人内心对父亲的呼唤,既是梦境,又是诗人精神上的寻父。寻父不遇,才有“儿罪等枭獍”的悲情感受。负疚之情,锉骨之哀,却又莫能救赎,世之人皆莫吾知也,只有求证于鬼神,以明心迹,这又何其似屈子《涉江》中所表现的哀情感受。第二章宕开笔墨,勉强从悲哀中挣扎而出,描写了西山之灵秀深隐,然面对此景,诗人无法不回忆“父顾而乐此,日夕哦其间”之乐。风景依旧,物是人非,诗人再次为深郁的悲情所捆缚,而无法自拔。在艺术表现上,本章也运用反衬手法,以父亲昔日之乐,反衬孤儿今日之悲,哀情动人。第三章细数与父亲相关之旧物,一花一木,无不受父亲魂气笼罩。诗人对“二鹤”命运之细述,近乎归有光哀祭文写法,将“微物”与“大悲情”相寄托,摄“微物”之精魂,抒一己之幽情,沉痛入骨,真挚感人。第四章采用对比写法,由今日扫墓之悲对比“去岁”寒食之乐,以乐景写悲情,悲情增倍。第五章细述右铭公之志事遭遇,出处大节,而又以“百哀咽松色,魂气迷咫尺”结束全篇,点明“述哀诗”主旨。吴宓读后记曰:“《崝庐述哀诗五首》,真挚悲壮,为集中上上之作。‘平生报国心,……苟活蒙愧耻’一段将右铭公(讳宝箴)之志事遭遇,出处大节,简明叙出。类谢灵运《述祖德诗》。按:右铭公薨于庚子年(丁酉冬十二月),散原先生丧母,并葬南昌西效外四十里西山之崝庐。自后每岁一次先生必来崝庐小住,拜扫哭祭,而皆有诗。其诗皆真挚感人,为集中之骨干。类黄公度《拜先大母李夫之墓》诗,而又睠怀君国,忧心世变,寓公于私,尤可得知先生之抱负与此时代之历史精神也。”[4]
“哀”是这首诗的主基调,也是整个崝庐诗的主基调。诗人对招致父亲之死的“祸变”,表现出强烈的冤恨。在古典诗歌意象中,表现哀怨情感最为激烈的莫过于“杜鹃啼血”了。近代诗人也常以“杜鹃啼血”表现胸中冤抑之情,以致陈衍有“鹃声满耳”之讥评,而真正有如陈三立一般冤抑之情、真挚感受的,用此则尤为恰切了。在崝庐组诗中,诗人常以“杜鹃啼血”之古典,表现自己对父亲的思念与内心冤抑之今情。古典今事,融为一炉。“有鸟飞上昼夜啼,似怜先公亲手植”(《咏阶前两桂树》);“孤儿犹认啼鹃路,早晚西山万念存”(《返西山崝庐将过匡山赋别》);“翠华终自返,碧血更谁怜。”(《长至抵崝庐上冢》);“千山压人去,处处杜鹃声”(《别墓》);“万翠压荒亭,啼魂认屡经”(《望城岗》),“微雨独来摩泪眼,千山染血待啼鹃”(《微雨中抵墓所》)……。唐宋诗人常用“杜鹃啼血,望啼愁魂”的典故表现家国之悲,诗人以此表现对父亲的思念与理解,寄托政治批判的深意。唐杜甫诗曰:“杜鹃暮春至,哀哀叫其间。我见常再拜,重是古帝魂”;唐代李商隐亦有诗曰:“莫学啼成血,从教梦寄魂”,含蕴家国之悲感。诗人借助化魂的杜鹃,与父亲在精神上相往来。而杜鹃所啼之血在这里却是“碧血”,暗用“苌弘化碧”之典,表明父亲忠直坚贞而蒙受冤屈,溅血而死。诗人年年拜墓,对西山鹃声尤为敏锐,“岁积苌弘碧,春深杜宇哀”,这种哀痛成为父亲去世之后他全部的生命感受,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陈三立此段时期生命的意义,只是为了向世人展示父亲的冤屈,鸣心中不平之音。“人生留命殉歌哭,龙虎啖食鉴者谁”(《三月二十六日渡江入西山作》);“自写悲怀向天壤,从来顾影属吾曹”(《携曹范青新诗至山中读之题其后》)。对于陈三立而言,父亲突然故去,是其悲哀无法救赎的根由,往事不堪回首,而又心有不甘,他唯有将这浓烈的哀怨深藏在“奥衍生涩”的诗句之中。
部分学者曾对陈三立在崝庐诗中所表现的父子之情不能理解,甚至以为是老莱子似的矫情,这是缺乏同情的了解。陈三立崝庐诗中所表现的哀恸之感,并非只停留于一般的父子之情,而是已经超越了血缘关系,在亲情之上更有理想与事业的寄托。故其对父亲的怀念,更有一种对个人政治理想凭吊意味,且由一己之情感放大开来,具有悲天悯人之情怀。
陈三立曾有过随侍父亲左右的经历,而湘中治迹,更是父子共同作用的结果。“一省政事,隐然握诸三立之手,其父固信之坚也。”[5]王闿运曾戏言陈宝箴在湘中倡导的维新归于“江西人好听儿子说话”这一惯例。语虽不经,却也道出陈三立在其湖南新政中的襄助之功。事实上,自1895年9月12日(阴历七月二十四日),陈宝箴升任湖南巡抚以来,陈三立则一直随侍左右。曾参与新政变法的梁启超在《谭嗣同传》中曰:“时陈宝箴为湖南巡抚,其子三立抚之,慨然以湖南开化为己任。”[6]其时,正值甲午战败以后,朝野不少人士已达成共识,只有讲新学,重洋务,才是救亡之道。而天下事从来就是发空言易而办实事难,真正能致力于“营一隅为天下倡,立富强根基”的实事改革,惟义宁陈氏一家而已。故湖南成为新政与理想之摇篮,对维新人士尤其具有吸引力。维新人士认为:“湘省居天下之中,士气最盛,陈右帅适在其地,或者天犹未绝中国乎?”[7]义宁陈氏父子也乘此“广延四方俊杰之士,襄助新政。”而“凡此为政求贤,皆先生所赞襄而罗致之者也”[2]。一时间,名士荟萃,嘉宾云集,一起“相与剖析世界形势,抨击腐败吏治,贡献新猷,切磋时文。乐则啸歌,愤则痛哭,声闻里巷,时人称之为‘义宁陈氏开名士行’”[8]。时在长沙,长于宾坐的曾广钧①曾广钧,字重伯,号觙庵,别号旧民,湖南湘乡人。曾国藩之孙。光绪十一年乙丑进士,官广西知府,著有《环天室诗集》等。曾以《天运篇》追忆当年“时会趋新,群流竞奋”的盛况:
……。一别湘州事势新,其间岁月颇嶙峋。前辈将才余几个,义宁孤立古君臣。我时谒告游巡署,日接黄(遵宪)梁(启超)一辈人。健者谭(嗣同)唐(才常)常抵掌,论斤麻菌煮银鳞。廖(树蘅)梁(焕奎)诗伯兼攻矿,一洗骚人万古贫。沅水黄(忠浩)熊(希龄)来应梦,双珠(朱萼生、鞠生兄弟)盐铁佐经纶。中丞东阁贪宾客,公子西园赏好春。楚士英英多入彀,十梅礼绝平原宾。[9]
曾氏所载的四方俊杰之士,多为巡抚公子陈三立交游引进,于是陈三立顺理成章地介入到新政各项事业中去。戊戍政变后,清政府谕旨诏示:“……,伊子吏部主事陈三立,招引奸邪,著一并革职。”就清庭的立场而言,此论也决非虚语。
因此,陈三立在崝庐诗中,每每追忆新政事迹,具有父子之情与政治理想双重凭吊的意味。“况当圣政初,万情费量揣。拨乱加绸缪,孤蹈摆誉毁。造次省民艰,若疾痛在体。引绳喻仁术,鳞爪一毛耳”(《崝庐书所见》);“白发苍颜今相见,避谈旧事益凄然。……,昨逢里正谈蒙学,苦问朝廷变法无。”(《崝庐雨坐戏为四绝句》);“烦念九原孤愤在,忍看宿草碧磷新”(《纪哀答剑丞见寄时将还西山展墓》);“我自楼头悲往事,十年听尽鸟呼风”(《崝庐楼望》)。“旧事,往事”时时浮现于崝庐诗中,诗人已将个人理想事来与父子之情相绾合,故这种情感较一般父子之情尤为深挚、曲折。
其外,诗人对父亲的情感,除政治寓托之外,尚有内心的疚愧之情,而这对于“忠孝传家世所尊”的陈三立而言,更令其坐卧不安。陈宝箴于戊戍政变时尚获全身而退,却于庚子年死于非命,这是诗人一生之悲痛,而其中之不幸多少是与诗人有牵连的,因此崝庐诗中常常见出陈三立哀毁、疚愧欲死的形象。“呜呼父何之,儿罪待枭獍”、“儿今迫祸变,苟活蒙愧耻”(《崝庐述哀诗》);“忘世反靡躯,疚恚讼我顽”(《到塞上还宿崝庐》)。这种负疚感一直萦绕到晚年的陈三立,“自信眼穿偿一死,扶舆初烬未成灰”(《初度日写愤寄朋》),晚年上冢诗仍有“断肠非痛定”(《崝庐楼居五首》)的悲愤感受。戊戍政变后,诗人对世人“不自陨灭,祸延显考”的谣诼[10],不屑一辩。然而,“此中委屈,殆非世俗所能喻,而其支离突兀,掉臂游行,迥异常人,犹可敬也。”[11]诗人的心是孤独的,他只能在崝庐诗中与亡父交流内心无语的深悲。
在陈宝箴死后,诗人的精神几近崩溃,父子之情化为“孤独”的生命感受。“孤独”是诗人生命状态与精神气象上的全部反映。“壬子间杨昀谷赠诗曰:‘四海无家对影孤,余生犹幸有江湖。’是为诗人的确切写照”。[11]97诗人在崝庐诗中,屡屡抒写作为“孤儿”的悲伤体验:“终天作孤儿,鬼神下为证”(《崝庐述哀诗五首》);“孤儿犹认啼鹃路,早晚西山万念存”、“杂花时节春风满,重到孤儿是路人”(《清明日墓上》),“明灭檐牙挂网丝,眼花头白一孤儿”(《庐夜漫兴》)、“群山遮我更无言,莽莽孤儿一片魂”(《雨中去西山二十里至望城岗》),年近半百的诗人,尚有如此的“孤儿”感受,且真挚沉痛,字字如迸血泪,其中自有“无可告人之天人悲原”尚待发覆。俞大纲先生认为:“盖先生当时诗境,未尝不同于屈子之忧愁忧思。太史公论《离骚》谓劳苦倦极,未尝不呼父母。先生《崝庐述哀诗》及年时谒墓之作,至性至情,真是胸有万言艰一字,发而呼天呼父母之声矣。”[12]诗中自有“无可告诉之天人悲原行乎其间”[3]182。有似“群山遮我更无言,莽莽孤儿一片魂”(《雨中去西山二十里望城冈》)的无语深痛。“灵气望城岗,飞花覆酒所。西山诚暱余,云中与谁语”、“群山遮我更无言,莽莽孤儿一片魂”(《雨中去西山二十里望城岗》),晚清政局的昏暗,导致诗人的无言,这是“世人莫吾知”绝大孤独,也是家国一体、存亡与共、覆卵之下无完巢的绝大孤忠,更是洞知历史深意的苦心孤诣。
二、家国之感
如果说陈三立的崝庐诗仅停留在哀叹个人遭际的不幸,抒发父子之间的亲情,排遣心中的郁闷,那么他的诗很难产生震憾人心的感召力,其社会价值与文学价值也只能是有限的。陈三立诗歌之所以能在近代诗坛占有重要的一席,还在于“生世相怜骚雅近,赋才独得杜韩遗”(陈宝琛《题伯严诗》)的家国一体精神。
就崝庐诗思想主题而言,陈三立上承《诗经》、《离骚》、杜甫、韩愈“变风变雅”的诗学传统,能将个人的际遇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吟诵出诗史般的佳作。从而,使诗的生命真正博大起来,“有不可一世之概”[1]1217。其泣诉家难,更充溢着忧国忧民之情。从而使诗歌摆脱“小我”的局限,而走向对时代的、国家的、民族的关注。其序《梁鼎芬诗集》曰:“吾不敢谓梁子已能平其心一比于纯德,要梁子志极于天壤,宜关于国故,拘肝沥血,抗言永叹,不屑苟私其躬,用一己之得失进退为忻愠,此则梁子昭昭之孤心,即以极诸天下后世而犹许者也。”[1]825-826移之评陈三立诗歌,同样为中的之论。王赓《今传是楼诗话》曰:“散原集中,凡涉崝庐诸作,皆真挚沉痛,字字如迸血泪,苍茫家国之感,悉寓于诗,洵宇宙之诗文也。”[1]1228吴宓也认为其诗:“睠怀君国,忧心世变,寓公于私,尤可得先生之抱负与此时代之历史精神也。”[4]551“苍茫家国之感”、“睠怀君国”,“忧心世变”,皆揭示了崝庐诗并不局限于父子之情,而寓含家国兴亡的关怀。
家国兴亡之感,是陈三立崝庐诗中反复倾诉的主题。诗人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下,通过由国事的关切,对百姓的同情,表达对父亲理想的追随,试图化解心中的悲郁之情。“国忧家难正迷茫,气绝声嘶谁救疗”(《由崝庐寄陈芰谭》)、“誓墓羲之聊复尔,买山巢父与谁同。痴儿谬托桑榆地,种树书成酒梡空”(《崝庐庐夜》)、“岁时仅及江南返,祸乱终防地下知”(《墓上》)、“归携亡国恨,就卧看云床”(《雨霁崝庐楼寓兴》)。除了这些在扫墓时直抒家国之痛的诗外,诗人更多的是通过反思个人身世,追怀同道契友,曲折含蓄地表露自己恋主、忧国、伤民的内心世界。其《壬寅长至抵崝庐谒墓》诗曰:
天乎有此庐,我拂苍松入。壁色满斜阳,照照孤儿泣。登楼望高坟,微醉草木气。一片好山川,冥然接寤寐。几日酹春风,儿归又长至。荒茫五洲间,余此呼籲地。国家许大事,长跽难具陈。端伤幽独怀,千山与嶙峋。贫是吾家物,宁敢失坠之。江南可怜月,遂为儿所私。大孙羁东溟,诸孙解诗史。三龄稚曾孙,伊嘎学兄语。小立风满山,默祷泪如泻。万古落心头,仍卧心头夜。
这首诗作于1902年,诗人50岁。而对“壁色满斜阳”的崝庐,伤心的“孤儿”泪如泉涌。浊浊尘世之外,惟有崝庐这片幽独的天地,留与诗人与其父精神天地相往来。“荒茫五洲间,余此呼籲地”,这是诗人值得庆幸的地方,也是诗人将多日来的悲哀加以宣泄的地方。诗人面对落照下的湖山,多日的积怨喷涌而出。陈三立的姻亲挚友范当世曾赠诗曰:“不醉几番真负汝,日归何事益凄然。惟应岁晚风涛外,落照湖山有泪涟。”(《酿雪不成送伯严江西省墓》)[14]崝庐墓侧,诗人首先想到的不是一己之处境,而是家国大事。“国家许大事,长跽难具陈”,是承陆游“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爱国传统。可是,诗人很快以“难具陈”将尚未开始的陈述匆匆结束,实在是这两年来中国处于最为黑暗的时期。国事日非,民不聊生,诗人实在无怡心快事告慰亡父,只能叹“祸乱终防地下知”了。这种以无声代有声,以虚代实的写法,更能体现出家国患难之深重。“端伤幽独怀,千山与嶙峋”,这是一种冷静时的反思,更是痛不欲言的无奈。国事的沉痛,一直笼罩在对家事的陈述表达上,使之对家事的陈述显得缭草而空洞,以至近乎一种搪塞了。否则,则让人无法理解诗中为什么对不甚悲惨的家事的陈述,却让诗人“默祷泪如泻”的伤痛。①陈锐曾赠三立诗曰:“崎岖赤县中兴日,安稳青山薄葬魂”(《送伯严归省西山展墓》),见陈锐《抱碧斋诗集》。但这只是老朋友的良好祝愿,而实际却与此相反,清末中兴的局面在庚子后没有重现,诗人也只能无言以“安稳”西山魂魄了。
其《长至后七日抵西山谒墓》诗云:
拂袂江汉滨,视疾俄叹逝。(兹行先赴武昌视黄小鲁疾,乃于三日问及此事遽逝),折途犯重湖,染我西山翠。沙淤作陂陀,岸树倒旗帜。烟岚引一痕,车音飞破碎。日斜穿松楸,陌陇念宿置。遣儿荐节物,墓门留烛泪。(大男衡恪长至抵墓所)咫尺呼如应,岩峦拥魂气。老愈疲腰脚,莽莽接寒吹。草蟄已绝吟,零雁不成字。所匿片云下,寻常阅年岁。万情竞颠倒,遑云世可避。只待补松株,六合毕此事。径旁野花丛,樵章尽剪刈。会当芽春风,再逐仙蝶至。
这首诗作于1910年,诗人58岁,诗笔更显沧桑老练。诗人写到江滨疾逝的黄嗣东,有“裵褱皆路人,感旧余国故”之意[15]。再写到泪留墓所的大儿陈衡恪,以及“老愈疲腰脚”的诗人自身,娓娓道来,于“草蛰已绝吟,零雁不成字”的凄凉晚景下,型塑出忧愁悲苦的诗人形象。若仅如此,则诗境稍狭窄,“万情竞颠倒,遑云世可避。只待补松株,六合毕此事。”诗人以“隐逸”代写实,巧妙地隐含进深广的社会现实内容,使诗境顿开。若非国事日非,士不可为,何以诗人有此急急求隐的思想,诗人哪里是真的羡慕崝庐的野花、春风、仙蝶,实不得以而强作欢喜。家国深痛,似在不经间表露于字里行间。此外,如“国覆复为人,惨淡亲魂魄。”(《清明日上冢》);“隔世诉肺肝,待寻巾柴车”(《崝庐三首》);“神灵缥缈迎披发,江海飘零诉剖肝。”(《月夜墓上》);“人亡国亦粹,对语交涕流”(《张岘堂来宿崝庐晨兴相怀眺墓后诸山》);“隔岁如隔世,活国计安出。黍离悲已沈,诸夏亡无日。预恐吞鲸鲵,匪特持蚌骛。宿昔绸缪意,事往谁复恤”(《清明日祭墓》);“国度荡无纪,层累窥神奸”(《浴佛日雨中发南昌抵崝庐上冢三首》),等等。无一不是家与国密切相关,于家痛中显忧国之思,在“寻巾柴车”、“剖肺肝”、“悲黍离”之中,跃动的是诗人爱国忧民的心。
陈三立崝庐诗不仅仅是从个人和亲友的视角去观照整个社会的内忧外患,而且还以“西山崝庐”这一独特的空间去折射华夏大地的风云际会,往往在父子隐秘的对话之中,释放出对山外世界的无限感伤。在崝庐诗中,诗人多处写到登高远眺,这种由视觉的转换,从眼前写到久远,由崝庐进而窥视天下。他在崝庐远眺,面临的竟是如此催人生愁的场景。“山光蓊郁树青红,村落都移日影中。我自楼头悲往事,十年听尽鸟呼风”(《崝庐楼望》);“苍茫云雾梦魂处,了了山川生死哀。风光万花乱人眼,独听鹃声松柏堆。”、“朝看万马自天下,暮觉双凤骞云浮。……,至今风雨阑干上,使我凭之泪又流”(《登楼望西山二首》)。“十年”、“云雾”、“山川”、“风雨”,这种由时空转换,阴晴风雨的变化,为崝庐辅上了厚重的时代风云景象。“傲挺之姿,苍郁之气,犹盘纡于文字之间”[12]150。崝庐一景一物,常能触发诗人无限的家愁国恨,使诗人欲静之心不止。其《楼坐戏述》诗云:
城市共舆儓,山中喧虫鸟。併百千万音,沸向楼头绕。陂田尽蛄黽。游蜂亦来绕。鸟鹊雊雉外,布谷黄莺好,牛犬声蠢蠢,豕唤鹅鸭恼。鸣鸡在邻墙,风雨尤自扰。豺狼有时啼,悲风振林杪。苍鹰尔何知,逐鸠下嘴爪。我欲洗心坐,冥合万物表。樵歌又四起,牧童和未了。何况溪涧流,断续满怀抱。一笑谢巢由,勿为外人道。
自然界的一切声响,都激起诗人内心的波澜,使“使我洗心坐,冥合万物表”的求静之心,不能实现。在动与静,入世与出世之间,诗人无法做到真正的“袖手人”的境界。他的心仍睠怀君国安危,故时代的风雨,狼啼鹰啸之声,诗人无法漠然视之。其诗强称“戏述”,却是诗人内心无法平静,无法超脱时代、政治之外的真实的反映。乱世的纷挠,不仅处处侵袭诗人欲静不止的心,而且时时折磨诗人疲惫不堪的灵魂。纵然在历来文人得以获取宁静的一豆灯火之下,诗人静夜长思,也不是个人之得失,而是家国的安危存亡。“昏灯揽崝庐,惨淡立四壁”、“万远互回翰,只劳中怵惕”(《腊月二日到崝庐作》),数尺见方的卧塌之地,也成了观风察雨,体验世态炎凉的天地。“咫尺存吾庐,塞松迷户牍。趺坐生尘榻,哀思扫无帚。”(《发南昌晚抵崝庐》)无论是白昼黑夜,阴晴风雨,还是春来秋往,远眺静思,陈三立笔下总是回荡着“百年歌哭”之声。崝庐特定的地点,使诗人触景生情,“百忧千哀在家国”、“抚膺家国逼灯前”,皆为诗人家国情怀的真实流露,而这种家国之感,早已超越了单一的政治内涵,而更有“兴亡遗恨”的文化意味。
三、兴亡遗恨
陈三立年年崝庐扫墓诗,都打上了时间的印记。现存的诗集虽始自光绪二十七年(1901),但其前后的重大的历史事件,都在崝庐诗中能发现它的投影,使崝庐诗更具有史笔诗心的诗史特点。
在对“史实”的叙述之中,他更关切其中的“家国兴亡史”。“变乱散唐宫,历历兴亡史”、“兴亡一蛭影,影中验得失”(《爰命题为万寿山怀古余忝与会归而补作》),从传统中总结时代之得失,对近代以来的时代危机、文化危机更具有深刻的警示意义。
但作为一位时代政治的参与者与反思者,他更关注当下政治的兴亡成败。其中与崝庐、先君相关,令其刻骨铭心的戊戍变法史事,成为他一生的伤感主题。在《崝庐述哀诗五首》中,他借祭父诗文,泣诉戊戍履霜的前因后果,感慨戊戍变法之失败是由于“维彼夸夺徒,浸淫坏天地。唐突蛟蛇宫,陆沉不移晷”。他对戊戍变法兴亡成败原因的反思是全面的。“前年朝政按党锢。父子幸得还耕钓”(《由崝庐寄陈芰潭》);“云旗弓剑重重恨,猿鹤沙虫稍稍传”(《微雨中抵墓所》);“昨逢里老谈蒙学,苦问朝廷变法无”(《崝庐雨坐戏为四绝句》),等等。这些诗句或隐或显地痛陈血泪往事,表明诗人难以抹去戊戍政变在心头留下的阴影。他认为政变的挫败,既有夸夺徒的激进“坏天纪”,也有“蛟蛇宫”的从中阻梗,更有新旧“党锢”之争,致使新政事业失败,变法不得善终。这种悼念往事、痛感现实的心情,一直延续至晚年仍耿耿在心地曰:“宿昔绸缪意,事往谁复恤”(《清明日祭墓》)。
崝庐诗相当一部分诗作“以诗存史”,抒发兴亡遗恨。光绪二十九年(1903),日俄构兵,在中国境内鹜蚌相争,清政府保持所谓“局外中立”,极显国际政治外交、军事斗争上的无能。诗人当即在扫墓诗中曰:“惊耗排天入,奇哀进酒浇”(《长至墓下作》)。次年,日俄战争爆发,诗人上冢述哀,更为矛盾痛苦:“岁时仅及江南返,祸乱终防地下知。”戊申(1905)国变,诗人的“两宫隔夕弃臣民,地变天荒纪戊申”、“烦念九原孤愤在,君看宿草碧磷新”(《纪哀答剑丞见寄时将还西山展墓》,一个时代兴衰已成为历史,然而,遗恨却永远留在历史参与者心头,这种遗恨是无法随时代的灭亡而消除的。
辛亥鼎革,诗人更多悯乱伤时之作,但对历史兴亡之感则更为强烈。王赓《今传是楼诗话》称:“辛亥以后,君诗境一变,闵乱伤时,多变雅之作。”对于辛亥年的巨变,诗人虽有诗曰:“春灯不管兴亡事,又照新亭过客诗”(《为王梧生题朝鲜全秉熏所写金陵游诗卷子》),但这首《墓上》诗中,仍有“忧天成泪尽,来护夕阳山”的感伤。辛亥三年后,诗人仍不忘在上墓诗中追述辛亥革命造成社会巨变和民生灾难。“荐物阻兵戈,三岁霜露隔。松楸亦改世,抚我先朝碣。国覆复为人,惨淡亲魂魄。九幽目不瞑,易器乖肘腋。非想托华胥,诬天熄王迹。”(《清明日上冢》)民国五年(1916),年逾花甲的诗人仍未忘情于世事兴亡,仍有“观兵烽尘蔽,玄黄一战区”(《渡江入西山晚抵墓所》)战事的叙述。前后不同时期的崝庐诗,恰好勾勒出晚清民国交替迁延的历史线索,诗人于兴亡感慨之中,也将崝庐寄寓兴亡之意展示无疑。“兴亡遗恨”,在某种程度上是诗人寄命、干世的依据和表现。诗人在史实叙述之中,有着对历史的兴亡的清醒的自觉。其晚年诗曰:“侵夜山风喧,兴亡迹俱扫,呼唤换人世,寄命千劫表”(《己巳十月别沪就江舟入招牯岭新居》)。已77岁高龄的诗人,表示从此与纠缠一生的历史兴亡遗恨作一别离,重新“换人世”,这种决裂之中,反见出诗人兴亡感之沉重深邃。其《拔可寄示晚翠轩遗墨民诵默然缀一绝归之》诗赠杨锐曰:“此才颇系兴亡史,魂气留痕泣送春。”移之评定散原之兴亡遗恨,述史纪哀,甚为恰切。
在“兴亡遗恨”这一主题下,诗人对崝庐的民生情况也深为关注。这使他的崝庐诗的悲感更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也折射出杜甫“穷年忧黎元”的博大的人道主义精神。其有诗句缅怀亡父爱国理想,“生世糜躯殉黔赤,娱老未及持觞看”(《崝庐墙下所植花尽开甚盛感叹成咏》)。这种爱国忧民的思想,也有义宁家族精神的一脉相承性。在他的诗作中,对生活在最下层的农民投入了极大的关注。“初有舍人妇,暴卒变窀穸。嫁婢又死去,孤雏寄之食。平生歌哭地,于汝见颜色(《腊月二日到崝庐作》)。将自己的歌哭与人民的苦难相联系。“可怜妇孺啼号极,匿案戴盘冀自免。天灾人祸不虚应,好事闻之也烦懑”(《庐旁被雹灾聊记之》)。对灾难中的民生状况的刻画,更具悯乱伤时的感情。而这种关注民生、体察民情的思想与中国古典诗歌的爱国忧民的传统是有先后相承性的。故这种情思,也决非崝庐一地所能限制,具有普遍意义。
崝庐诗虽为历年省墓述哀诗组成,但它已超越了单纯的悼亡的含义,而是由父子之情述及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进而拓展到家父君国的一体关怀,透视出历史与现实的人生大关怀。溯其所本,乃我国传统思想中的“国身通一”之旨①陈寅恪:《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曰:“尝读元明旧史,见刘藏春姚逃虚皆以世外闲身面而与人家国事,况先生少为儒家之学,本董生国身通一之旨,慕伊尹天民先觉之任。其不能与当时腐恶之政治绝缘,势不得不然。“这段话自是为梁启超辩,但其中“以世外之闲身与人家国事”和“国身通一之旨”两句话,殊堪注意,疑心寅恪先生在作此语时,心目中一定有散原老人在。参见陈寅恪,寒柳堂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166.,视家国为一体,家国并提,“羁孤念家国,悲恼互奔凑”(《鸡笼山舟上答谢熊六文叔惠丰桔》);“旋出涕泪说家国,倔强世间欲何待”(《与莼常相见这明日,遂偕寻莫愁湖,至则楼馆荡没,巨浸中仅存椽而已,怅然而作》):“向人但能结舌喑,百忧千哀痛家国”。这种乱离之悲、家国兴亡之感,也深入到义宁陈氏家族血脉之中,成为其子陈寅恪先生诗歌中反复咏叹的主题。“家国旧情迷纸上,兴亡遗恨照灯前”,寅恪先生的这两句诗,可为散原此类崝庐诗作总结之语,也可见出义宁精神的历史传承。
[1] 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M].李开军,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2] 吴宗慈.陈三立传略[J].国史馆馆刊,创刊号.
[3] 龚鹏程.论晚清诗[M]//近代思想史散论.东大图书公司,1991:181.
[4] 吴宓.读散原精舍诗笔记[M]//袁行霈,国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545-551.
[5] 陈灨一.睇向斋臆谈·陈三立[M]//睇向斋谈往.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145.
[6] 谭嗣同.谭嗣同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544.
[7] 梁启超.致汪康年函[M]//汪康年.汪康年师友书札: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831.
[8] 陈小丛.庭闻忆述:注文[M]//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64.
[9] 曾广钧.天运偏[M]//钱仲联.近代诗钞:三.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1436.
[10] 王闿运.湘绮楼日记[M].长沙:岳麓书院,1997:2476.
[11] 徐一士.谈陈三立[M]//一士类稿.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98.
[12] 俞大纲.寥音阁诗话[M]//俞大纲全集[M].台北:台北学生书局,1987:147.
[13] 范当世.范伯子诗文集[M].马亚中,陈安国,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14] 程颂万.鲁髯养疴崇府山麓九日以庖珍饷予和伯严韵与小鲁为登高之会不果三篇为答[M]//石巢诗集:卷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王飞霞
On Themes of CHEN San-li′s“Zhenglu Poem s”
SUN Hu
(School of the Humanities,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uzhou 215009,China)
CHEN San-li′s“Zhenglu Poems”,cornposed of the graueyard elegies,have surpassed the pure mournig connotations and taken on special attachment.The themes of this collection of poems have extended from true feelings between CHEN San-li′s fater and himself(the son),and confilicts between their ideal and reality to the ident if ication of his fater and hismother land and the eternal regret for their country,thus showed their greatest concern for history and reality,and the sadness ofQinglu poems displays a commoner social significance aswell.
CHEN San-li;Qinglu poems;old sentiment for a family and a nation;eternal regret for rise and fail of a nation
I206.5
A
1004-941(2010)01-0087-07
2009-12-30
孙虎(1974-),男,安徽庐江人,副教授,文学博士,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代诗学与思想文化,清代江南家族文化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