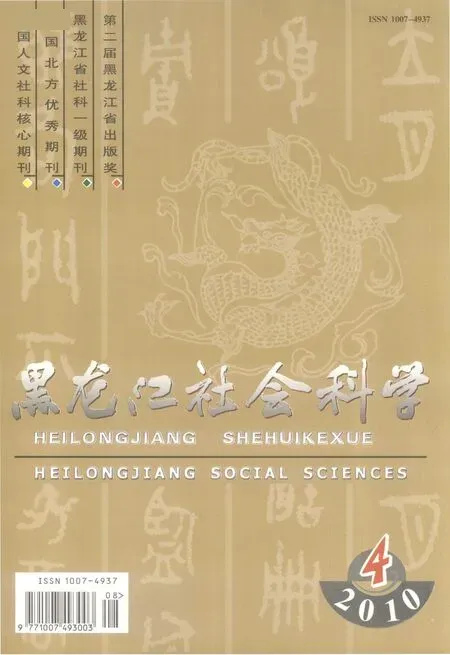福克纳南方家庭小说中的父辈形象的二元对立
匡 骁
(1.黑龙江大学西语学院,哈尔滨 150080;2.华东师范大学文学院,上海 200241)
福克纳南方家庭小说中的父辈形象的二元对立
匡 骁1,2
(1.黑龙江大学西语学院,哈尔滨 150080;2.华东师范大学文学院,上海 200241)
南方家庭小说(fam ily rom ance)是美国南方文学传统的核心。福克纳作为南方文艺复兴的代表作家,继承了南方文学中家庭小说的传统,创作了约克那帕塌法世系小说。福克纳在其小说中对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刻画中充满了矛盾,在将这些种族主义者塑造成旧南方体系中的英雄的同时,还通过这些形象揭露了旧南方的腐朽本质和对人性的践踏。正是在这种批判意识中,福克纳的家庭小说既完成了对南方文学的继承和发扬,又实现了对它的超越。
福克纳;南方家庭小说;种族主义;二元对立
20世纪上半叶,美国南方突然呈现出文化和文学上的空前繁荣,产生了一大批杰出的作家、诗人、戏剧家、学者、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史称“南方文艺复兴”。这些南方作家和知识分子不但在创作中继承和发扬了美国南方优秀的文学遗产,而且在艺术手法上进行了大胆试验和创新,所以可以说“南方文艺复兴”是南方文学传统同现代主义潮流有机结合的产物。这一特点在南方文艺复兴的代表作家——福克纳的作品中体现得最为显著。虽然南方文艺复兴不是一个有组织和统一纲领的运动,但福克纳的思想和作品无疑最具代表性,其创作必然同南方文艺复兴有着深厚的渊源。
著名南方史学家理查德·金(R ichard King)对南方文艺复兴的见解最具权威。他认为,南方文艺复兴即 20世纪上半叶的一些南方知识分子和作家,力图寻找某种正确认识并理解旧南方的传统价值的途径,同时探求过去对现在有何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他们的这种“纪念碑式的历史意识”又使这些南方作家在探索过去和现在关系的过程中充满矛盾[1]。这一矛盾集中体现在南方文学创作的核心——“南方家庭小说”(fam ily rom ance)中。
一、南方家庭小说的起源和特点
“家庭小说”的雏形——庄园小说随着 1830年后的社会变革应运而生。南方家庭小说的兴起同南方庄园经济的繁荣直接相关。19世纪 30年代,南方经济由于轧花机的发明而获得长足发展,这也正是庄园浪漫小说产生的时期。约翰·肯尼迪写于 1832年的《麻雀仓房》一般被认为是庄园文学的源头。这种书信体小说已粗具庄园文学的一些基本特征:庄园生活宛若一首田园诗,庄园主慷慨好客,对奴隶关怀备至,庄园象征着秩序、和谐。内战后,一些南方作家处于对金钱至上、社会和文化“荒原”的不满,开始描写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庄园生活,形成了一直延续到 20世纪的庄园流派,通俗小说《飘》就是其代表。
庄园小说的存在从某种程度上是为奴隶制进行辩护,或者至少掩盖了它的罪恶,是对奴隶制以及建立在奴隶制和种族主义基础上的南方社会的竭力美化。南方被吹嘘成“令人销魂的乐土”,而奴隶制更是“上帝的恩赐”。奴隶主是仁慈的主人,黑人是忠顺的奴仆。黑人孤立无援、愚昧无知,他们的“动物性”(anim ality)经常被强调,所以他们必须依靠奴隶主的“照料”,而他们也因为得到主人的关心和照看而感恩戴德。不难看出,南方白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拒绝接受他们残忍和不公正的形象。在他们眼中,蓄奴制体现着他们对一个“无助的”、“未开化”种族的高度关怀。所以,庄园小说具有强烈的政治意义,主要是用来维护奴隶主的利益;另外,庄园文学在一定程度上也能掩饰或减轻白人种族主义者良心深处的不安。
严格地说,家庭小说仍是以战前种族秩序为模式,把黑人看做是整个南方大家庭中无辜的、无害的孩子,需要强大的白人的管理和教育。位于家庭小说中心位置的是白人父亲。尽管在现实生活中,南方妇女经常是家庭的强有力的主心骨,但在传统小说里,相对于强大的英雄式的父亲,母亲始终处于附属地位。父亲的形象通常是慷慨正直、有绅士风度的大庄园主,内战时曾英勇地与“北方佬”进行过顽强的抵抗。而和这些英雄的祖父辈相比,南方下一代的父辈在他们儿子眼中似乎略显平庸乏味,黯然失色。所以在家庭小说中,父子关系往往不如祖孙二人融洽亲密。此外,尽管在重建时期南方人乐观地相信社会进步,然而这种乐观也时时被一层阴云所笼罩,那就是对“英雄时代”是否已经一去不复返的疑虑。因此,家庭的兴衰也是家庭浪漫小说不断重复的主题。
下面,让我们以福克纳作品中的几个典型人物为例,来了解一下南方家庭小说中的父亲形象。
二、昔日英雄/种族暴君:福克纳笔下种族主义者形象的二元对立
福克纳的约克那帕塌法世系小说(Yoknapatawpha saga)中的父亲们虽然各有特点,但他们身上也有很多共通之处,最突出的恐怕就是他们大多是暴君式的家长专制的父权主义者,他们冷酷、残忍,是非人道的南方社会本质的反映,是其奴隶制、种族主义和加尔文主义的集中体现。他们或是狂热的清教徒,用宗教给自己的专横和无情披上神圣的外衣;或是像福克纳的祖父“老上校”那样的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们是家族缔造者,作为一种影响存在于故事中,其在子孙后代心中的高大形象也多少是被虚构和改造的产物。
在福克纳的反种族主义著作《八月之光》中,我们为一系列凶狠、暴戾的父亲形象感到震惊,他们身上被深深地刻上了清教加尔文主义的烙印。主人公乔·克里斯玛斯还未出生就成了他外祖父的受害者,他的悲剧很大程度上源于他缺少家庭温暖和亲情的悲惨童年,而扼杀了乔美好童年的最直接“凶手”就是他的外祖父道克·汉斯。汉斯不仅是个残忍的极端种族主义者,还是个狂热的宗教徒。仅仅因为女儿的情人肤色微黑,继而怀疑他身上有黑人血统,就不由分说将其枪杀。由于女儿的“堕落”,在女儿临产时,他持枪守在房门外,禁止任何人,包括他的妻子去找医生,并说这是在“执行上帝的旨意”,以至于亲生女儿死于难产,乔一出生即沦为孤儿。不仅如此,他还把尚在襁褓中的乔在圣诞节前天晚上遗弃在孤儿院门前,因为他把乔看成是“魔鬼的产物”,把毁灭其一生作为自己生活的唯一目的,因此汉斯并没有结束对乔的摧残:他随后又来到孤儿院,成了看门人,以达到随时监视乔的险恶目的,使这个“魔鬼的产物”永远逃不出惩罚。汉斯还居心叵测地告诉孤儿院的其他小孩,乔是个“黑鬼”,使乔被孤立在孩子们的圈子之外,致使乔一生都被“我是谁”这个没有答案的问题所折磨,而在孤儿院的几年对乔的一生更是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乔的外祖父汉斯是乔悲剧的第一个执行者,而他却给自己的暴行披上神圣的外衣:“主叫老道克·汉斯做什么,他就做什么。”[2]361正如他妻子所说的,他仅仅是用“上帝的名字来为他自己身上的魔鬼辩护和寻找借口”[2]352。
乔的第二个迫害者是乔的继父麦克伊琼。和汉斯一样,他也是个虔诚得近乎极端的清教徒,以上帝的名义对幼小的乔进行身体和精神上的虐待,不断惩罚鞭打乔。当他逼迫乔背诵《圣经》中的教义时,他一本正经,冷若冰霜,就像《旧约》中的上帝那样。福克纳对麦克伊琼的声音的描写最能表现他的特点:“他的声音并非不和蔼,它根本就不是人的声音。它仅仅是冷漠的、无情的,就像写出的或印出的话语。”[2]139当乔背不出教义时,他对孩子的抽打就像一种仪式,不掺杂任何情感:“麦克伊琼开始有条不紊地抽打,慢慢地,使足力气,仍然不带任何情绪和愤怒。”[2]140小说以各种方式表明他并非天生残忍,只是他所信奉的清教主义使他认为这样的严厉控制才能把乔教育成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在他看来,喝酒、跳舞、找女人这些享乐都是不可饶恕的罪恶。他在领养乔时,对一个五岁孩童说的话竟是:“尽你所能干活,那会防止你捣蛋。我很快就会让你知道人的两个恶习就是懒惰和胡思乱想,两个美德就是工作和敬畏上帝。” 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乔感受不到任何温情和父爱,所以外祖父和继父对乔后来扭曲畸形的性格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另一个典型的暴君式人物就是《押沙龙,押沙龙!》里的托马斯·斯特潘。他一生唯一的梦想或追求就是创造一个纯白人血统的贵族式家庭:“我有一个蓝图。为了实现它,我需要钱,房子,庄园,还有奴隶和家庭——当然碰巧也需要一个妻子。”[3]所以无论任何人,对他来说不过是实现这个“蓝图”的工具。为达目的他不择手段,冷酷无情地抛弃有黑人血统的妻子,毁了自己的四个孩子,继而却也毁了自己亲手缔造的显赫一时的大家族。实际上他的“蓝图”是南方庄园主梦想的体现,他家族的败落是整个旧南方崩溃的缩影。
然而,细读福克纳的南方家庭小说文本时不难发现,福克纳对这些旧南方的白人父辈的刻画,在尖锐批判揭露的同时,却也不乏一种同情的含混笔触,因而形成了白人种族主义者形象的种族暴君/昔日英雄的二元对立,这种矛盾性实际也反映了作为土生土长的南方作家的福克纳,对南方始终怀有一种爱恨交织的、复杂的情感。
应该看到,以上描述的福克纳家庭小说中的作为暴君式家长的父亲,并非天生邪恶残忍,他们也不时表现出人性的一面。在这些旧南方的守护者身上,我们也能看到勇敢、顽强、坚定,在艰苦环境下为理想而不屈不挠的优秀品质。所以我们也不能否认这些父亲身上那种早期拓荒者的美德。其实,这些白人种族主义者本身也是南方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受害者。福克纳的重要艺术成就之一就在于表现那些受传统压制和摧残的人物流露出的人性光辉。这种塑造不但使人物形象更真实可信,而且还在刻画旧南方英雄的同时,更深刻地揭露了旧南方腐朽的本质和对人性非人道的践踏。比如在《下去吧,摩西》中的卡洛萨斯·麦卡士林,他生前灭绝人性的乱伦行为给后代蒙上了挥之不去的阴影:他不仅强奸了家中的女黑奴,而且竟然又和由此生下的亲生女儿乱伦,导致女仆跳河自尽。尽管卡洛萨斯从未承认自己带有黑人血统的孩子,但仍在遗嘱中留给他一千美元。虽然主人公艾克对这种姿态充满蔑视和不屑:“那比对一个黑鬼说我的儿更为廉价。”[4]但是至少说明卡洛萨斯内心深处不无愧疚羞愧之情。在南方,奴隶主根本不敢承认自己有带黑人血统的孩子。卡洛萨斯表面上的冷酷无情,实则掩饰了他受传统压抑的心灵和内心的脆弱。这笔遗嘱就是一种补偿,一种减轻负罪感的方式,而这种负罪感则源于他那尚未丧失殆尽的良心和人性。
福克纳研究专家肖明翰先生在其著作中对这个问题的总结非常精辟:“……福克纳笔下的父亲们并非天生的恶棍或生性恶毒的虐待狂。相反,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都是美国南方社会各种非人道力量,如奴隶制、种族主义、加尔文主义的受害者。社会现实和传统观念把一整套符合一个父亲、家长或奴隶主身份的思维方式、世俗观念和行为规范强加给他们。这些因素压抑了他们的人性,把他们变得冷酷无情……他们可能获得尊重和顺从,却得不到理解和真诚的爱。在他们威严的外表下,在他们内心深处不得不忍受感情上的痛苦和良心上的折磨。结果是,他们不仅使自己同其他人疏远和对立起来,而且同自己作为人的本性疏远和对立起来,把自己异化了。”[5]
通过这些形象塑造中的含混和矛盾,福克纳探求南方大家族衰败的根源是和他对各种违反人性、非人道力量和腐朽势力的批判紧密融合在一起的。虽然福克纳对南方怀有深沉的爱,对那片“邮票般大小的故土”怀着深厚的感情,然而他最终还是能超越自己的感情,超越传统家庭小说的局限性,充分暴露和鞭挞旧南方的罪恶,表明了自己鲜明的人道主义立场。
[1] King,H.R ichard.“A Southern Renaissanc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35.
[2] Fau lkner,W illiam.L ight in August.V intage Books,1975.
[3] Fau lkner,W illiam.Absalom,Absalom!L ight in August.V intage Books,1972:263.
[4] Fau lkner,W illiam.Go Dow n,M oses.L ight in August.V intage Books,1972:269.
[5] 肖明翰.福克纳研究[M].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1997:189.
〔责任编辑:王晓春〕
J4
A
1007-4937(2010)04-0086-03
2010-04-28
匡骁(1978-),女,黑龙江哈尔滨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从事文艺理论、美国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