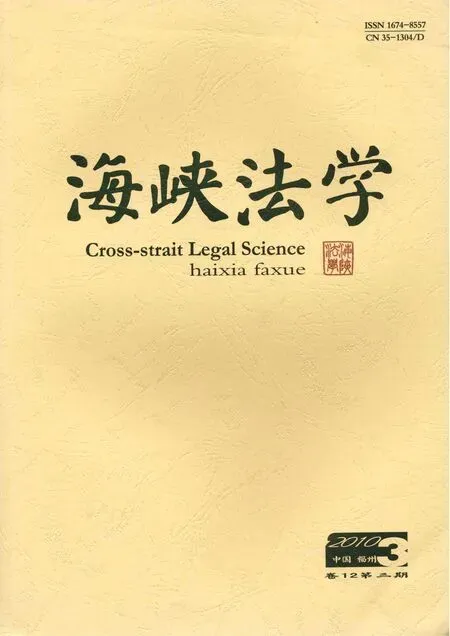论合同冲突法中强制规则的适用
李凤琴
(嘉兴学院文法学院,浙江海宁 314001)
论合同冲突法中强制规则的适用
李凤琴13
(嘉兴学院文法学院,浙江海宁 314001)
在合同冲突法领域,强制规则会对合同准据法的确定产生影响。一方面,一国法院应当适度有限地解释和适用本国强制规则;另一方面,为了案件的公正解决,从尊重他国重要政策出发,法院也应对外国强制规则予以适当关注。我国合同冲突法中的强制规则尚未形成清晰的机制,这不利于保护我国的重要政策和弱者利益。时值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正在起草之际,欧盟较为成熟的合同冲突法强制规则理论与实践可以为我国提供借鉴。
合同冲突法;国际强制规则;法院地强制规则;外国强制规则
在合同冲突法领域,意思自治原则已成为各国所普遍承认和奉行的基本原则,它意味着合同当事人有权协议选择支配其合同的准据法。但是,意思自治原则并不表明合同冲突法对其毫无限制,强制规则正是体现了国家对意思自治原则的干预。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为保护重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利益,在各领域制定了大量的强制规则,如反垄断法、外汇管制法、价格法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这些强制规则不容许当事人通过协议加以减损,甚至有些强制规则可以撇开冲突规范而直接适用于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中。[1]因此,在合同冲突法领域,强制规则必然对合同准据法的确定产生影响。
在我国强制规则尚未形成清晰的机制,仅仅通过法律规避和公共秩序保留制度来保护我国的重要政策和弱者利益。在跨国交易相当繁荣的今天,缺少强制性规则这一保障措施不利于我国国家利益和国民利益的保护。[2]欧盟于1980年制定了《关于合同义务法律适用的罗马公约》(以下称《罗马公约》),该公约于 2008年转换为欧盟立法,即《关于合同义务法律适用的罗马条例》(以下称《罗马条例I》),《罗马条例I》在合同冲突法强制性规则上建立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同时欧盟各国法院在“强制规则的适用”上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因此,研究欧盟合同冲突法强制规则体制和各成员国的司法实践,不仅对于我国正在草拟中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具有借鉴作用,同时可以指导我国法院在实践中如何正确处理强制规则与合同准据法确定之间的关系。
一、强制规则的界定
强制规则作为独立的定义导入合同冲突法领域,源于1980年的《罗马公约》。现在由于欧盟各国对《罗马公约》的国内实施以及《罗马条例 I》对欧盟各国的直接适用效力,不论该成员国的合同冲突法体系中是否有强制规则的概念,目前均已成为欧盟成员国内合同冲突法领域的一项重要规则。[3]然而,对于何为强制规则,各国并没有形成统一观点,产生了许多定义和分类体系。[4]通常说来,可以将强制规则划分为国内强制规则和国际强制规则。
(一)国内强制规则
在大陆法系国家中,从国内法角度讲,强制规则是与“任意规则”相对的概念。这是按照法律规则指示的当事人的自主程度所作的分类。[5]任意规则往往允许当事人可以在合同中另行约定以改变法律的既有规定;而强制规则根据《罗马条例I》第3条第3款的规定,是指那些不能被当事人通过协议减损的法律规则。
然而,世界上任何国家并不存在一个被称作“强制规则”的部门法,强制规则可以源自于公法规则,也可以源自于私法规则。因此,众多的强制规则实际上散见于各个法律部门及单个法律文件之中,这便产生了国内强制规则的界定问题。
1.通过法条本身的规定加以界定。有些强制规则本身直接规定了其适用范围,如根据我国《合同法》第126条第2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履行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开发自然资源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此类合同就不允许当事人通过协议规避中国法律的适用,具有强制性规则的特性。有些强制规则在法律条文中含有“不得”、“必须”等词语,表明其规定的不可违反性。如我国《担保法》第 214条规定:“出质人和质权人在合同中不得约定在债务履行期届满质权人未受清偿时,质物的所有权为质权人所有。”再如,我国《票据法》第 8条规定:“票据金额以中文大写和数码同时记载,二者必须一致,二者不一致的,票据无效。”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强制性规则与任意性规则的区分远非这样明了,法律条文中并没有上述区别性文字,那么如何界定其是否为强制规则将变得较为困难。[6]
2.从法条规定的内容和实现的目的加以界定。如果法条并没有规定其适用范围或者并不含有“不得”、“必须”等区别性文字的,那么应当结合法条的内容和制定该法条所要实现的目的、该法律条文所在法律文件的上下文及违反法律规则的后果等因素进行考察,如果法律规则的目的是保护一国重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利益,违反该法律规则会导致当事人的协议无效,则该法律规则对当事人而言就是强制规则。[7]
(二)国际强制规则
国际强制规则,又称为冲突法上的强制规则或优先性强制规则,它意味着国内强制规则的跨国适用。根据《罗马条例I》第9条第1款的规定,国际强制规则是指被一国认为对维护该国的公共利益,尤其是对维护其政治、社会和经济组织的利益至关重要而必须遵守的强制性条款,以至于对属于其适用范围的所有情况,不论根据本条例适用于合同的是何种法律,它们都必须予以适用。 其实对于什么是“国际性强制规则”在欧盟内部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罗马条例 I》至少明确了“国际性强制规则”存在的领域,强调其存在于一国保护公共利益的领域中。
从上述概念可以看出,国际强制规则的确定必须满足两个条件。首先,从国内法角度,该法律规则不能被当事人通过协议加以减损;其次,从冲突法角度,不论根据冲突规范所确定的准据法为何,该法律规则必须得到适用。换句话说,国内强制规则中只有一小部分可以被认定为国际强制规则。这种限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冲突法的基础就在于依据冲突规范所确定的准据法必须被适用,即使有时以牺牲国内强制规则为代价。[8]
国际强制规则可以分为法院地强制规则和外国强制规则。在合同冲突法领域,国际强制规则在一国法院诉讼中的适用与在国际商事仲裁中的适用不同,法院对于强制规则的适用并不中立。一国法院较为偏好适用法院地国的强制规则,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也会考虑外国强制规则的适用。
二、强制规则在合同冲突法中的适用
(一)法院地强制规则的适用
法院适用法院地国的强制规则无可非议,一些国家和地区还在立法中作了明确规定。如《罗马条例I》第9条第2款规定:“本条例中的任何规定都不限制法院地法中强制性条款的适用。”1987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第 18条规定:“不论本法所指定的准据法为何,都不得损害因其特殊目的应予适用的瑞士法律的强制性规定。”1995年意大利国际私法第 17条和魁北克民法典第3076条也有类似规定。
在实践中,可以依据冲突规范指引所确定的合同准据法的不同,将法院地强制规则的适用分为两种情形:
1.合同准据法为外国法时法院地强制规则的适用
无论如何,以牺牲应当适用的外国法为代价而适用法院地强制规则并不存在太大的问题,因为只要法院发现有足够的利益去适用本国强制规则。任何法律体系中都存在这种情况。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法院地法并不能完全取代外国准据法的适用,而只是以法院地法中的强制规则来取代外国准据法中与之相冲突的部分规则,也就是说,此时外国准据法与法院地强制规则是并存适用的。[9]
然而,法院地的强制规则中只有一小部分才能代替外国规则,因为其具有国际强制规则的性质。接下来的问题是,法院如何在根据冲突规范指引应当适用外国法的情形下,决定优先适用的法院地强制规则的“国际性”。《罗马条例I》对此并没有给出答案,而是留给各国内法自行决定。但是很多法院地国内法中缺乏明确的立法指导,此时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就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在实践中,法院很少会解释国内强制规则成为国际强制规则的具体理由。法院一般要识别国内强制规则所要实现的重要政策和目的,才可背离冲突规范加以适用,但这并不足够,法院还必须确定国内强制规则在国际案件中适用的必要性,评价是否还有其他更有效地方法促进该重要政策的实现,这就意味着,当适用外国准据法能够获得相同效果时,那么法院也就无需适用国内强制规则。
2.合同准据法为法院地法时法院地强制规则的适用
此类情况较少有人关注。因为如果法院地法作为合同准据法,一般认为法院地法中的强制规则和非强制规则都应当适用,然而,情况并非如此简单,法院有时需要考虑是否存在可保护的本国利益,从而决定本国强制规则的适用与否。
第一,当交易与法院地无实质联系,国际合同当事人只是将法院地法作为“中立法”加以选择适用,法院又基于“协议管辖条款”享有对该合同纠纷的管辖权时,如果被选择的法院地法中包含有强制性条款,但是该强制性条款完全只适用于国内案件,与国际交易无关,那么法院也就无需适用该强制规则。比如,法院地法规定,国内保险经纪人开展经营活动必须以向当局注册登记为前提,否则其对外所签订的合同无效。那么当一个国际合同与法院地国无实质联系,而法院地法又被选择为合同准据法时,就无需因为该保险经纪人未在法院地国登记注册而宣告合同无效,因为法院地法规定的强制注册条件只适用于国内保险经纪人,其目的也只在于保护国内利益。[10]
第二,有时因为交易的国际性特点,在诉讼中适用法院地强制规则反而会损害法院地国的利益。1950年由法国最高法院裁决的Messageries Maritimes一案较为典型。在该案中,法国公司为贷款方,荷兰公司为借款方,以加拿大元为货币在加拿大签订了借贷合同。合同中包括了一个“黄金保值条款”,并允许贷款方自由选择法国或荷兰作为合同履行地。但是随后法国法和加拿大法都规定“黄金保值条款”无效。债务人荷兰公司以此为由拒绝履行该条款。法国最高法院认定该“黄金保值条款”有效,主张国际借贷合同由于其资金流动跨越国界,因而其需要以特殊规范加以调整,国际借贷合同当事方达成的“黄金保值条款”虽然与调整其合同的法国法中的强制规则相矛盾,但是这种条款的有效性得到法院的承认,因为其与法国法中的国际公共政策一致。[11]通过此案我们可以看出,在国际交易中,法国法院通过拒绝适用本国强制规则从而有效地保护了本国当事人的利益。
从以上对法院地强制规则的适用情况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法院适用本国强制规则虽然无可非议,但是法院地强制规则仍不能当然地被适用,法院只能适度有限地解释和适用本国强制规则。
(二)外国强制规则的适用
传统观点认为,外国强制规则对一国法院是没有强制适用效力的。然而随着现代国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上的依存度加深,各国需要相互支持国家间重要的法律规则和政策,开始逐渐认可法院享有适用外国强制规则的权力。这种趋势已经在一些国家或地区的立法中有所体现。《瑞士联邦国际私法》第19条规定:“依照瑞士法律观念,当所要求的利益是合法的并且明显占优势,可考虑本法案中提及的法律之外的另一法律中的某一项强制性规定,倘若所处理的情形与该等其他法律存在密切的联系。”《罗马公约》第7条第1款规定:“在依据本公约适用某一国家的法律时,如果另一国家与案件存在密切联系,则对该另一个国家法律中的强制规则的效力应给予考虑。”然而该条款在欧盟内部引起广泛争议,英国、卢森堡和德国对该款予以了保留。为此,2008年以欧盟立法形式出现的《罗马条例I》在第9条第3款设置了一个高度创新的条款,将适用外国强制规则的情况作了进一步限定,并且不允许成员国作出保留,该款规定:“当合同义务将要或已经在一国履行,只要该国的强制规则认为其履行为非法,那么,该国的强制规则的效力则可以予以考虑。在决定是否承认此种强制性规则的效力时,法院应当考虑该强制规则的性质、目的以及适用或不适用将导致的后果。”该款表达了成员国对其它国家立法政策的尊重。其结果是,外国强制规则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被适用。
然而,即使《罗马条例 I》和一些国家的立法对外国强制规则的适用作了规定,但是在实践中法院如何适用外国强制规则仍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当合同准据法为外国法时,该外国法中的强制规则和非强制规则一般都应当予以适用,除非法院认为该外国法的适用会损害法院地国的公共秩序而拒绝适用之;而当合同准据法为法院地法时,法院考虑适用外国强制规则的情形就变得较为复杂。
1.法院可以考虑适用哪些外国的强制规则
根据一些国家或地区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法院可以考虑适用三类国家的强制规则:
第一,合同履行地国家的强制规则。在英国,法院不会去支持履行地国法律认为履行为非法的合同,即使合同准据法为英国法。如,在Foster v.Driscoll一案中,英国法院宣称一个关于将威士忌出口到依法禁酒的美国的销售合同由于违反了合同履行地美国的法律规定,从而违背英国的国际友好义务和公共道德而不能履行。[12]
第二,消费者惯常居住地、雇员工作地或雇主营业所在地国家的强制规则。这是一种保护性强制规则。法院适用保护性强制规则,其目的在于纠正特殊领域当事人之间利益的失衡状态。根据《罗马条例I》第6条第2款的规定,消费合同当事人的法律选择不得剥夺消费者惯常居所地国强制规则给予消费者的保护;第8条第1款规定,个人雇佣合同当事人法律选择不得剥夺雇员惯常工作地或雇主营业所所在地国强制规则给予雇员的保护。这就是说,不管根据冲突规范确定的准据法是否为法院地法,如果消费者惯常居所地、雇员惯常工作地或雇主营业所所在地国强制规则给予消费者或雇员更有利的保护,那么法院就应当考虑这些国家强制规则的适用。
第三,最密切联系地国的强制规则。法院应当考虑适用与案件存在最密切联系地国的强制规则,目的在于防止当事人利用意思自治选择合同准据法以规避本应适用的强制规则。在Alnati 一案中,荷兰最高法院认为,“当合同与他国存在密切联系,对于他国来说甚至在它的领土之外遵守它的某些条款是非常重要的,以至于法院必须考虑优先适用它们,而不是适用合同方所选择的另一国法律。”[13]在英国的一个判例中,买方从印度购得货物,运往其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的营业地,并且只支付了部分的货款。他援引西班牙的价格管制法规为由,拒绝支付所余货款。尽管合同本应受英国法支配,但英国法院最终适用了西班牙的管制法规,免除了买方的义务。法院的理由就是买方必须遵守其营业地国的价格管制法规,这与合同是有密切联系的。[14]
2.法院如何确认外国法律规则的强制性特征
一国法院对他国法律体系并不熟悉,因此妥善确定和解释另一国家法律规则的内容显得较为困难,而确定哪些法律规则具有强制性特征则更加困难。传统的解决办法是,不论合同准据法为何,这些规则都希望被适用。也就是说,从法律制定国角度来看,基于法律规则中所体现的重要利益,这些规则必须适用于相关的交易中。在某些情况下,法律直接规定某些条款必须被适用,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法院无法直接从法律条款的内容上判断其是否必须被适用。[15]此时,法院必须考察该法律规则所体现的国家政策及其所要实现的重要利益,评价如果未被适用在相关案件中,是否会严重损害该国的利益并被认为是对该国的不友好行为。以此同时,法院还应将它同法院地国政策的实现与维护、国际秩序的维护和促进、当事人的正当利益、个案公正和实质正义等若干因素相互比较,并作出权衡。[14]
3.法院是否应当适用具有公法性质的外国强制规则
上文已述及,强制规则可以源自于公法规则,也可以源自于私法规则,那么当外国强制规则属于公法规则之时,法院是否可以考虑适用?如果根据古老的“公法禁止原则”(Public Law Taboo),一国法院就会拒绝考虑适用具有公法性质的外国强制规则。然而随着国际交往的深入,国家对经济干预的加强和公私法划分的弱化,一些国家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逐渐愿意考虑适用具有公法性质的外国强制规则。
国际法学会 1975年威斯巴登会议上的决定明确规定,冲突规范所指引的其他国家法律规范的公法性质不影响该规范的适用,但根据公共秩序所作的根本性保留除外。1987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第13条规定,不得仅仅以他国法律规定具有公法性质而排除其适用。
对法院考虑适用公法性质的外国强制规则在实践中也可以找到相应的案例。在德国Kulturguterfall一案中,联邦法院面临的是一桩尼日利亚文化遗产非法出口问题。争议的焦点是,一家德国保险公司是否需要为一批货物从尼日利亚向德国运输过程中发生的损害进行理赔。保险合同适用德国法。法院认为,依据德国法,违反尼日利亚的法律被认为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因此法院判定合同无效,不存在可保利益。在这则案例中尼日利亚法既非合同准据法,又非法院地法,但是德国法院仍将具有公法性质的尼日利亚强制规则考虑在内,使尼日利亚法律得到实际适用。[16]法国法院采取了相似理由考虑适用了公法性质的强制规则。如法国塞纳法庭曾经判定一个贷款合同无效,虽然合同准据法是法国法,但是考虑到委内瑞拉法律禁止签订其目的在于支持国内叛乱的贷款合同,根据法国法,违反委内瑞拉法律被认为是不道德行为,从而合同无效。[12]
4.法院是否有义务必须适用外国强制规则
即使适用外国强制规则的路径已经建立,一国法院仍没有必须适用的压力。因为在上述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中,均采用了“可以”(may)适用一词。因而,就适用外国强制规则而言,这只是一项任意性规定,不具有强制效力,法院拥有自由裁量权。最近法国法院裁决的一个案件正说明了此种情况。在该案中,一法国公司向加纳买方出售冷冻牛肉,货物是通过海运运至加纳。但因为加纳通过了一项禁止进口法国牛肉的法律,导致该批货物无法交付。随后卖方起诉。本案合同准据法为法国法,但是被告承运人认为,根据法国民法典第113条,有着非法约因的合同是无效的。即承运人主张,该合同依据法国法是无效的,而这种无效正是由于外国禁运法律的存在而产生的结果。在2010年3月16日作出的判决中,法国最高法院认为,本案应当探究根据《罗马公约》第7.1条,法院是否本应当赋予外国法以效力。但本案可能并不需要真正适用外国法,而仅仅是为适用法国法律而考虑外国法的存在及其对合同的影响。法院最终没有考虑加纳禁运法而驳回了承运人关于合同无效的主张。[17]因此,从本案来看,虽有可适用的外国强制规则的存在,但法院基于保护本国当事人利益的需要,仍然可以拒绝考虑外国强制规则对合同效力带来的影响。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对强制规则的适用已经从法院地国扩展至其他国家,法院不再一味坚持只适用本国强制规则,而对外国强制规则的适用予以了适当考虑。然而我们也应当看到,尽管国际社会较多关注外国强制规则的适用问题,欧盟及一些国家的立法还将规则制度化,但是在实践中法院考虑外国强制规则往往是基于保护本国利益的需要,因此,要想真正实现平等适用外国强制规则这一目的,还需要各国的司法合作。
三、强制规则的适用理论与实践对我国的启示
(一)我国关于强制规则适用的现状
我国目前没有统一的国际私法法典,合同冲突规范主要规定在《民法通则》、《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中,其主要以公共秩序和法律规避制度来保护我国的重要政策和弱者利益。
《民法通则》第 150条规定:“依照本章规定适用外国法律或者国际惯例的,不得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公共利益。”而作为《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起草基础的《民法(草案)第9编》依然沿袭了相同的规定。由于立法对“社会公共利益”缺乏准确定义,弹性过大,使得公共秩序保留成为争议最大而适用最少的一项制度。[18]而且它作为法院拒绝本应适用的准据法的最后渠道,只起到消极的防御功能,无法积极主动地保护国家重要政策和弱者利益,需要由强制规则制度加以补充。
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意见(试行)》第 194条中规定:“当事人规避我国强制性或禁止性法律规范的行为,不发生适用外国法律的效力。”同样,在《关于审理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纠纷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中也有类似规定。可以看出,司法解释试图通过法律规避制度限制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从而达到保护我国重要政策和弱者利益的目的。然而,这一目的在实践中难以实现。一方面,在合同冲突法领域,法律规避所要求的“欺诈”或“故意”要件在大多数情况下难以得到证实;另一方面,随着跨国交易的持续增长,国家对当事人意思自治限度的逐步放松,对法律规避的行为并非一律禁止。因此,只对实体法中的一些重要条款通过冲突法意义上的强制规则以确保他们不被合同双方借意思自治逃避其适用即可。[19]
在司法实践方面,根据学者对近三年来我国涉外民商事案件的抽样统计来看,在调查的案例中法律选择方法为法律规避或者强制性规定的比例为:2006年6%,[20]2007年为4%,[21]2008年为0。[22]这组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法院在涉外案件中适用强制性规则的现状,绝大多数案件还是根据我国的冲突规范来确定准据法,只在少数案件中采用法律规避或强制规则直接排除本应适用的外国法。这类案件主要存在于对外担保合同纠纷和涉外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中的无单放货纠纷。然而由于我国并没有系统建立强制性规则制度,亦未对强制规则作出任何划分,未能区分国内强制规则和国际强制规则,导致实践中法院在审理涉外合同纠纷中过宽解释本国强制规则的国际性特征。比如在无单放货纠纷中,有些法院以当事人约定的外国法与我国海商法第四章规定的“承运人凭单交货”的强制性规则相冲突而判定当事人的法律选择条款无效从而适用中国法。①但是“承运人凭单交货”是否具备国际性强制规则的特征从而足以排除根据冲突规范确定的应当适用的准据法?这就需要判断“承运人凭单交货”的规定是否为了国家重要的政治、经济或社会目的。从我国《海商法》的立法条文来看,这一规定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能够安全交货,或者是为了将合同项下的货物交给有权接受该批货物的人,以便利害关系人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它并不隐含特别重要的特定的政治、经济或社会目的,因而应当属于一种国内强制性规则,在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关系中不具有直接适用性。[23]
(二)对中国在合同冲突法领域建立强制规则制度的相关建议
时值《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起草之际,我国应当建立系统化的强制规则制度积极保护我国的重要利益,同时应当将公共秩序保留作为保障我国重要利益的最后渠道,这样的“双重防护网”显然更能充分地保护我国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的重要政策。
1.建立冲突法意义上的强制规则,在以后的立法中规定,“不论本法所指定的准据法为何,都不得损害因其特殊目的应予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2.建立保护性强制规则。在以后的立法中体现对消费者、雇工等弱势方当事人利益的保护。明确当事人选择法律不得剥夺本应适用的法律中强制规则对弱势方利益的保护。
3.一定条件下考虑外国强制规则的适用。是否采用“外国强制规则”,这是个存在争议的问题。我国对此应谨慎处理,毕竟“强制规则”很多属于公法规则,目的在于保护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24]笔者认为,为案件的公平解决,从尊重其他国家的立法政策角度出发,促进我国强制规则域外效力的实现,可以赋予法院在一定条件下考虑适用外国强制规则的权力。其条件是:(1)当合同义务将要或已经在一国履行,一旦该国的强制规则认为其履行为非法;(2)考虑该强制规则的性质、目的;(3)考虑其适用或不适用将对案件结果公正所产生的影响。但是,目前笔者并不建议考虑最密切联系地国家的强制规则,因为,法院对于最密切联系地的确定较为灵活,加上法院可以自由裁量是否考虑适用外国强制规则,这将会导致合同当事人无法预见和确定合同准据法的适用。
注释:
① 参见(2004)沪高民四(海)终字第87号。
[1] 田晓云.“直接适用的法”与合同准据法的确定[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4,(2):41.
[2] 杨永红.论欧盟区域内的强制性规则[J].当代法学,2006(4):42.
[3] 徐冬根,王国华,萧凯.国际私法[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224.
[4] Hannah L.Buxbaum,Mandatory Rules in Civil Litigation: Status of the Doctrine Post-Globalization[J], The American Rev iew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2007,Vol.18, p.21.
[5] 金彭年.法律规避中的强制性和禁止性规范研究[J].福建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4):10.
[6] 胡小红.论私法的强行性规范[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4):69.
[7] 张圣翠.国际商事仲裁强行规则研究[D].上海:华东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8] Bernard Audit, How Do Mandatory Rules of Law Function in International Civil Litigation [J].The America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2007,V ol.18, p.38.
[9] Andrea Bonomi,Mandatory Rules i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J].Yearbook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1999,p.223.
[10] Bernard Audit, How Do Mandatory Rules of Law Function in International Civil Litigation[J].The America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2007, Vol.18, p.39.
[11] See Horacio A.Grigera Naón,Choice-of-law Problems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M].J.C.B.Mohr (Paul Siebeck).Tübingen.1992, p.160.
[12] Article 7(1) of the European Contracts Convention: Codifying the Practice of Applying Foreign Mandatory Rules [J].Harvard Law Review.Vol.114.2001, p.2461.
[13] Katharina Boele-Woelki,Dutch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Pluralism of Methods[EB/OL].http://www.library.uu.nl/publarchief/jb/congres/01809180/15/b11.pdf, (last visited March,26,2010.)
[14] 胡永庆.论公法规范在国际私法中的地位——“直接适用法”问题的展开[J].法律科学,1999(4):98.
[15] Hannah L.Buxbaum, Mandatory Rules in Civil Litigation: Status of the Doctrine Post-Globalization[J].The America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2007,Vol.18, p.23.
[16] 卜璐.外国公法适用的理论变迁[C]//武大国际法律评论(第八卷).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145.
[17] Gilles Cuniberti, French Case on Foreign Mandatory Rules[EB/OL], http://conflictoflaws.net/2010/french-case-on-foreign-mandatory-rules/comment-page-1/#comment-274173.(last visited March,28,2010.)
[18] 史笑晓.论法律规避中的强制性和禁止性规范[J].浙江社会科学.2002,(3):75.
[19] 杨永红.论契约冲突法的保护性强制规则——以欧盟为例[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8,(3):75.
[20] 黄进,李庆明.2006年中国国际司法私法实践述评[C]//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刊(第十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386-396.
[21] 黄进,胡炜,王青松.2007年中国国际司法私法实践述评[C]//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刊(第十一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442-453.
[22] 黄进,胡炜,杜焕芳.2008年中国国际司法私法实践述评[C]//中国国际私法学会2009年会论文集:中国国际私法六十年回顾与展望.2009:6-14.
[23] 王娟.从国际私法视角对两宗“无单放货”案的对比分析[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12.
[24] 许庆坤.论国际合同中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限度[J].清华法学,2008(6):88.
(责任编辑:苏 婷)
D913
A
1674-8557(2010)02-0093-08
*本文为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研究成果,项目编号为0901010。
2010-01-11
李凤琴(1972—),女,浙江海宁人,法学博士,嘉兴学院文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