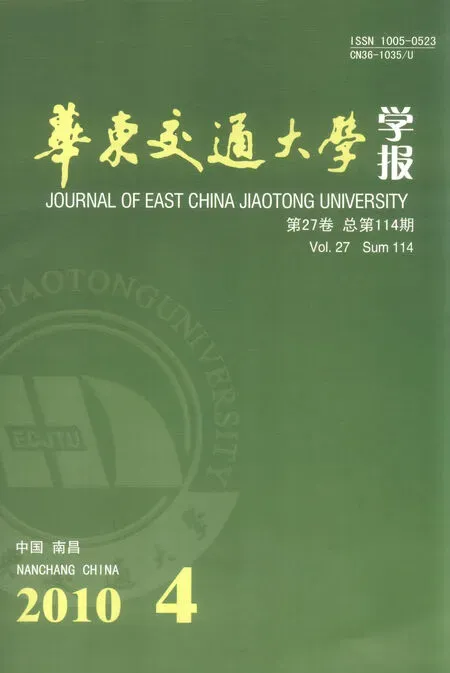意识流小说《达洛卫夫人》的批评话语分析
管淑红
(华东交通大学外语学院,江西南昌330013)
意识流小说《达洛卫夫人》的批评话语分析
管淑红
(华东交通大学外语学院,江西南昌330013)
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简称CDA)是通过分析语篇的语言特点和它们生成的社会历史背景来考察语篇所蕴涵的价值体系或意识形态,并进而揭示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文章以CDA理论为指导,结合福柯有关“规训权力”和“精神医疗权力”的论述,采用韩礼德的功能语言学分析方法来阐释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著名意识流小说《达洛卫夫人》的文学意义及作者对社会制度的批评。
批评话语分析;权力;意识形态;意识流小说;社会批评
批评话语分析自20世纪80年代初诞生以来,已经走过了30年的发展历程。国内外涌现了大批专家、学者致力于该学科的研究。国外主要的代表人物有福勒[1-2]、费尔克劳[3-6]、汤普森[7]和范戴克[8]等。他们主要用批评语言学理论分析了非文学的大众语篇。在国内,陈中竺[9-10]和辛斌[11]最早向国内介绍了CDA。近几年,不少学者也相继加入了CDA的研究行列。一些学者着重CDA的理论介绍与综述性研究,如项蕴华[12]和丁建新[13]等;另外一些学者借助CDA理论模式对大众传媒、新闻话语、法律、教育、政治语篇等进行批评分析,如辛斌[14]、吕万英[15]、田海龙[16]和徐涛[17]等;如今越来越多的学者转向了英、汉语篇的批评性对比分析,如曹广涛[18]和徐王君[19]。综上所述,对文学语篇进行批评分析的文章却鲜见。本文意欲用CDA理论分析文学语篇中的特殊语类意识流小说。
1 批评话语分析理论概述
CDA是通过分析语篇的语言特点和它们生成的社会历史背景来考察语篇所蕴涵的价值体系或意识形态意义,并进而揭示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福柯关于权力和话语的理论是CDA的倡导者们的理论渊源,而CDA的主要的理论依据和方法论来源是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2]。福柯运用知识考古学、权力谱系学的研究方法,提出了有别于马克思主义者的权力观。他认为权力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关系,一种复杂的网络。权力的实施是通过规范、纪律等手段来完成,并与知识共生共荣[20]。与福柯对权力的理解有所不同,CDA的代表人物范戴克认为权力意味着“控制”,即“一个群体成员对另外一些群体成员的控制。这种控制涉及行为和认知:一个权力群体不仅会限制其他群体的行为自由,也会影响他们的思想”[8]。意识形态(Ideology)是指一种观念的集合。马克思主义定义下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具有理解性的想像、是一种观看事物的方法,存在于共识与一些哲学趋势中,或者是指由社会中的统治阶级对所有社会成员提出的一组观念。汤普森却从意识形态和权力的关系定义了它的概念:“意义在特定情况下为权力服务、帮助确立和维护不对称权力关系的方式……从广义上说,意识形态就是服务于权力的意义”[7]。费尔克劳也认为权力和意识形态关系密切。他认为“在现代社会里,权力的行使越来越通过意识形态,具体地说,经过语言的意识形态运作……语言或许已经变成了社会控制和权力的基本媒介……”[3]。辛普森再次陈述道:“主导的意识形态作为维护社会不对称权力关系的机制进行运作。由于语言可被权力群体使用来加强这一主导意识形态,那么语言需要作为具体的斗争场所”[21]。从以上论述,我们知道意识形态总是参与维持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并往往通过语言获得表达。意识形态有很多不同的种类,如社会的、政治的、伦理的等等。在社会研究中,政治意识形态是一组用来解释社会应当如何运作的观念与原则,并且提供了某些社会秩序的蓝图。本文以CDA理论为指导,结合福柯的有关“规训权力”和“精神医疗权力”的论述,主要采用韩礼德[22]语言学的及物性系统分析方法来阐释著名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意识流小说《达洛卫夫人》中意识形态观念在医生和精神病人不均衡权力关系斗争中的运作,进而揭示伍尔夫对英国社会制度的批判。
2 《达洛卫夫人》的批评话语分析
发表于1925年的意识流小说《达洛卫夫人》是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代表作。小说摈弃了传统的情节描写(仅描写了1919年的夏天,达洛卫夫人在伦敦一天的活动:从清晨离家为举办宴会买花到子夜晚宴席散为止),关注了人物心理活动及意识流动的摹写,以逼真地再现生活。作品采用了第三人称有限叙述视角,自由间接思想是描写人物思想的主要表达方式。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评论界对伍尔夫作品的评价是:没有政治性、不关心社会问题。直到1986年,亚历克斯·兹沃德林(Alex Zwerdling)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和现实世界》(Virginia Woolf and the Real World)的出版,才质疑了这些观点。兹沃德林认为伍尔夫一生对社会权力结构和运作极感兴趣,是一位力图改革社会权力关系的“社会批评家和改革者”。伍尔夫本人也曾在1923年6月19日的日记中这样说到:“在此书中,我所要表达的想法实在太多了。我要表现生与死、理智与疯狂;我要批判社会制度,使之原形毕露”。在小说《达洛卫夫人》中,伍尔夫对社会制度的批评重点放在了描写医生的章节里。这章叙事视角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改意识流小说的第三人称有限叙述视角为传统的第三人称全知叙述视角。全知叙述者通常是最可靠的叙述者,他知晓人物的一切事情,可以发表自己的评论,提供对人物行为的判断和评价意见。作者用讥讽的口吻和辛辣的笔触描绘了医生,揭露和批判了二十世纪初,一次世界大战后,以威廉爵士为统治阶级代表的英国社会所倡导的“平稳”(proportion)和“感化”(conversion)意识形态观念以及社会不平等权力关系的运作机制。在这章的叙述中,作者大胆地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福柯[23]关于规范化裁决(normalizing judgment)和偏离(deviancy)的阐述在伍尔夫的小说《达洛卫夫人》中得到了完整的再现。借助小说的“平稳”和“感化”观念,伍尔夫不仅展现了20世纪初英国社会规训权力的普遍存在,而且也揭露了不符合准则,偏离准则所遭受的规训处罚。在与医生的权力较量中,赛普蒂默斯成为了规范化裁决的众多牺牲品之一。威廉爵士,作为医学界的ISA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他有权建立规范,确立变态,并且行使惩罚权。那么精神病医生威廉爵士是如何来判定病人的“不正常”,又如何来使他们“正常化”的呢?叙述者首先评价了威廉爵士的诊疗技术以及对赛普蒂默斯的诊断:
他不仅具有闪电般的绝技和几乎万无一失的诊断,而且富有同情心,手腕高明,洞察人心。当他们俩(沃伦·史密斯夫妇)一走进房间,他便一目了然;一看到赛普蒂默斯,他就肯定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病例。他在几分钟内就断定,这是精神崩溃的病例——体力和神经全面衰竭,每个症状都表明病情严重。(引文中的黑体为作者所加,下同)[24]97
叙述者用夸张的手法描绘了医生诊疗技术的高超,快捷为“闪电般的”,诊断的精确为“万无一失的”。两个表示“是”的关系过程明确了赛普蒂默斯犯了严重的疾病。而高量值的心理过程“肯定”和“断定”表明了威廉爵士对赛普蒂默斯是否犯病的绝对判断。尽管他避免提及“疯癫”两字,他的潜台词却是“赛普蒂默斯是个精神病患者,是个“疯子”。这应和了福柯有关精神医疗的论述。他认为精神医疗知识的运用和一般的医学诊断不同,它所作的不是“分类性的差异诊断”,而是在于决定疾病的存在与否(疯或不疯,绝对性诊断)[25]。福柯还坚持精神医疗是权力,而不是知识。尽管表面看来,它是属于医学的。作为一名受人尊敬的精神病医生,医学的权威(知识的代言人),威廉爵士几乎从未受到过质疑。
在威廉爵士的诊疗所,他对病人赛普蒂默斯的问诊,相当程度上保持着对会话过程的引导与控制。威廉爵士的话轮是21次,而赛普蒂默斯只有7次。医生总是启动话轮,处于主动地位,而病人仅回应医生的问话,处于被动地位。医生经常中断病人的话语去抓住他的话轮,而病人被剥夺了话语权。医生使用完整的句子,而赛普蒂默斯用简短,不完整的省略句子,甚至是口吃“我……我曾经犯了罪……”,“我……我……”[24]96-98。赛普蒂默斯在战争中不仅失去了他的感觉能力,而且几乎丧失了他的言语能力,甚至是话语权。许多次,他的妻子替代他去回答医生的问诊,最后医生干脆询问他的妻子有关他的情况。通过上面的医生和病人之间的问诊分析,我们知道了威廉爵士和赛普蒂默斯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均衡权力关系。
当威廉爵士问赛普蒂默斯在战争中是否表现出色时,病人迟疑地再说了一遍“战争”一词。副词“迟疑地”和疑问词“战争?”暗示了赛普蒂默斯对战争意义的不确定。作为英国“迷惘一代”的代表人物,他不再知道这场战争究竟是为了什么。战前,他酷爱莎士比亚戏剧,是个对未来充满理想的能干青年。一战爆发,他怀着捍卫祖国的崇高理想,响应“民主”、“光荣”、“牺牲”口号的鼓动和召唤,第一批自愿入伍去了欧洲战场。在战场上,他却目睹了人类空前的大屠杀。好友埃文斯战死沙场,使他彻底陷入精神崩溃和麻木状态。他经常被战争的破坏性带来的背叛和空虚感所困扰。从赛普蒂默斯对战争所表现出来的怀疑口气,威廉爵士很快,再次诊断他犯有严重的疾病。普蒂默斯的怀疑表现了他对英国社会制度的不信任。他把欧洲战争喻作是小学生用火药搞的小骚动,传达了他对这场战争的负面评价: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战争。基于他对这场“崇高的战争”的怀疑和对社会的不信任,医生认定赛普蒂默斯偏离了社会的常态,因而视他为“不正常的人”。
后来医生把他的妻子雷西娅叫到一边问她丈夫是否威胁说要自杀(对社会和人生大感失望,而表现的绝望情绪),得到印证后,威廉爵士再一次肯定赛普蒂默斯病得很重。医生诊断他“缺乏平稳感”。尽管医生从来不提“疯癫”两字,事实上他早已把赛普蒂默斯视为“疯人”之列。为了矫正这个“不正常的人”,医生便启用了精神医疗权力。于是他建议雷西娅把她的丈夫送到疗养院去。威廉爵士开出的药方是:在他乡下的疗养院长期卧床休息以便获得平稳感;赛普蒂默斯还必须离开他的妻子。威廉爵士还告诉他们别无选择,说这是法律问题[24]98。1838年的法令,把疯人由家庭的权力中剥夺出来,交给了行政——司法机构:总督即有权下令送疗养院禁闭,不需透过家庭。而这时禁闭已成为法律中最主要的条文……[25]。在这条律法的背后闪现的是疯人作为“社会敌人,威胁社会的危险”的思维方式[25]。疗养院权力和家庭的断裂是把家庭视为和治疗完全陌生,甚至敌对的原则。19世纪初的疗养手段,其中一个原则便在于将患者与家人分离,让病人进入到一个新的世界,在其中,他和家人、朋友、相识者完全分离[26]。
让我们再来看看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小对话:
“我们认为你应该到疗养院去,”威廉爵士告诉他。
“霍尔姆斯办的疗养院吗?”赛普蒂默斯嗤之以鼻。
“是我办的疗养院,沃伦·史密斯”他说,“在那里,我们将教会你休息。”[24]99
明确主观的小句情态“我们认为”和情态操作词“应该”表明威廉爵士用了极高的压力要求赛普蒂默斯去他的疗养院。去疗养院是医生施加在病人身上的强烈的主观意愿,不是他自己的选择。物质过程“我们将教会你休息”暗示成年的赛普蒂默斯却如孩童般,需要别人来教会一些最基本的起居事宜。他完全处于被动和无能的状态,属于弱势群体,而医生却属于权力群体。他们可以把自己的意志任意强加给病人。然而,当赛普蒂默斯问威廉爵士疗养院是否是霍尔姆斯的。行为过程“嗤之以鼻”表现了他对医生的鄙夷,暗示拒绝服从他的意愿。
为了进一步明确赛普蒂默斯“缺乏平稳感”,威廉爵士问雷西娅“他有时会冲动吗?”赛普蒂默斯回答“那是他自己的事。”威廉爵士道:“没有人只为自己活着”[24]99。按医生的意思,假如病人“不合群的冲动”失控,他一定要立刻把他送到疗养院并且规训他们以免危害社会。福柯的精神医疗权力,就使用了“冲动”和“退化”这两个概念重新整合疯人和异常儿童。由于冲动随时,自然地发生,一旦未受到控制、压抑,便会成为“异常”的来源。于是它就变成了异常儿童和疯人之间的联结[25]。
赛普蒂默斯再次尝试承认自己的罪行看看医生是否放他一马,但是他记不起自己究竟犯了什么罪。赛普蒂默斯结结巴巴地,重复说着“我……我……”[24]100。威廉爵士告诉他不要只考虑自己。威廉爵士认为“个人化”是一种精神病的症状。他希望病人转化,服从,忘记自己,不再怀疑这场欧洲战争和大英帝国。
威廉爵士不关心对赛普蒂默治疗,只关注他的荣誉,勇气,高的评价,辉煌的前途,甚至他的钱。我们从他对赛普蒂默的询问中可得知这一切:
“他在战争中表现出色吗?”
“在你的办事处,人们对你的评价也很高吗?”
“那么,你没有什么需要担忧,没有经济问题,什么问题也没有,是吗?”
“你还有远大的前途哩,前途无量嘛。”[24]100
威廉爵士急于想结束问诊,因为他对治疗病人不感兴趣,他只对积累权力和金钱感兴趣。他从不探讨“精神病患者”的真正原因,只想操控病人直到接受他的“平稳”观念并且对他俯首听命。例如:
你们还有什么事要问我吗?……
“一切都托付给我吧。”他说,接着打发他俩走了。[24]100
威廉爵士想要权力,他要求病人绝对地服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雷西娅带赛普蒂默来看医生,目的是想治愈他的“异化感”(与现实世界脱离的感觉)。但是当问诊结束的时候,她甚至和他的丈夫更加疏远,因为医生要求赛普蒂默去疗养院,离开她的妻子。夫妻在一起是赛普蒂默斯还能抓住的唯一救命稻草。去疗养院不是治疗和挽救他,而是逼他去死。事实上福柯认为“疗养院的权力以精神医学为名义,但其最大的特点却是与知识无关,虽然19世纪初的精神医疗一直要把自己建构为精神医学,给予自己科学论述的面貌”。福柯主张疗养院的“治疗效果”和精神医学无关[25]。通过医生和病人之间的问诊,我们知道,医生没有给病人开出任何药物治疗的处方,只是要求强行把病人送到疗养院,“命令病人卧床休息,独自静养,安静和休息;休息期间不会见朋友,不看书,不通信息……”[23]。统治阶级是如何迫使人们接受他们的意识形态观念的?首先,威廉爵士作为权力社会阶层的代表,规训权力的代言人。有权建立他的规范“神圣的平稳”。其次,一旦规范被建立,假如有人偏离规范,他们将很快被划归异常、不符合标准、反常、不道德和不正常。最后权力群体将实施他们的规训惩罚权。英国社会的法律就是要“隔离疯子,禁止生育,惩罚绝望,使不稳健的人不能传播他们的观点,直到他们也接受他的平稳感”[24]101。威廉爵士就是以仁慈“治疗”的名义来实施对疯子的惩罚。三个物质过程动词“隔离”,“禁止”和“惩罚”均携有负面的含义。这些物质过程都充满了权力的行使。由于明确无误的暴力行为,威廉爵士迫使别人分享他的“平稳”感。由于崇拜平稳,威廉爵士不仅自己功成名就,也使英国日益昌盛。这里,叙述者用讥讽的语气谴责了威廉爵士和他所代表的英国统治阶级。
你一旦失足,人性就会揪住你不放,赛普蒂默斯反复告诫自己。霍尔姆斯和布雷德肖不会放过你。哪怕你逃入沙漠,他们也会去搜索,哪怕你逃入荒野,他们也会尖叫着冲过来,还用拉肢刑具和拇指夹来折磨你。[24]99
尽管这段话是赛普蒂默斯的自由间接思想,但是自由间接思想特有的双声效果,让我们也听出了叙述者批评的声音。物质过程动词,“揪住、搜索、尖叫着冲过来、折磨”以及名词“拉肢刑具”和“拇指夹”都含有强者对弱者的权力的行使和惩罚。一旦你偏离了社会的规范和常态,权力阶级就要实施他们对弱者的残酷的压迫和镇压以建立他们所谓的“正常化社会”。
后来,叙述者继续谈论了威廉爵士的另一个思想观念“感化”。他这样评论道:
感化是她的名字。她尽情地蹂躏弱者的意志,热衷于引人注目,发号施令,强加于人,把自己的容貌刻在民众脸上而得意洋洋…她提供帮助,但渴望权力;她粗暴地惩罚异己分子或心怀不满的人,……。[24]101-102
这一段有许多的物质过程。在这些过程中,权力的一方是“感化”(施事者)无权的一方,如弱者的意志,民众的脸,异己分子,心怀不满的人和人们的意志是目标。物质过程动词,“蹂躏、热衷于引人注目、发号施令、强加于人、把……刻在”和“惩罚”都含有否定的意义。这些过程动词也都充满了权力的实施。通过这些表达,叙述者也批评了威廉爵士的感化观。感化伪装成兄弟般的爱,迫使人们遵守社会规范。在印度和非洲殖民地,感化事实上是对权力的追求。而威廉爵士是在殖民人们的思想。威廉爵士在“爱,责任和自我牺牲的名义下”把他的意志强加在那些比他弱小的人身上,如他的妻子,“十五年前她屈服了,拜倒在感化女神的脚下,这是完全无法解释的:没有当众争吵,没有厉声申斥,只是潜移默化,她的意志渐渐消沉,被水淹没,转变为他的意志。她带着甜蜜的笑容,很快地顺从了”[24]102。范戴克[8]认为权力包括对人们行为的控制和对人们认知的影响。在当今社会,后者对权力的实施来得更为有效。权力的行使可以通过伪装、劝服或操纵来使他人的思想向有利于自己利益的方向转变。威廉爵士对妻子的感化过程表明他是非常有效的压迫者和独裁者。20世纪初,科学成为了一种新的宗教,威廉爵士成为了“科学的牧师”。就像宗教信徒经常尝试感化非宗教信徒,威廉爵士试图感化精神病犯者获得“平稳感”,并行使对弱者的权力。按照福柯的分析,权力与知识的关系主要有三个方面:权力产生知识;知识促进权力;知识本身成为一种权力。按照福柯的意思,知识就是权力,掌握知识的人其实也就是掌握权力的人。因而,作为精神病医生的威廉爵士,医学的权威,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医生—法官”的角色。他掌握着对病人的判决和惩罚权。
在医生和病人权力的激烈斗争中,一些软弱的病人被驯服了,而另一些人则挑战他的权威,反抗他的压迫。例如在威廉爵士的诊所里:
有些软弱的病人精神崩溃,放声啼哭,低头屈服;另一些人,天知道他们受了什么过于疯狂的刺激,竟然当面辱骂威廉爵士是个可恶的骗子,甚至更为狂妄地怀疑生命本身。[24]103
没有目标的物质过程“崩溃”、“屈服”以及行为过程“啼哭”表明一些弱者的行为是无效的,他们处于被动地位。而言语过程“辱骂”和“质疑”表明另外一些人敢于对抗和挑战权威,他们处于主动地位。及物性的研究表明叙述者负面判断了软弱者,而积极地评价了那些反抗者。
从医生的问诊中,我们知道威廉爵士拥护平稳观念,光辉的事业,荣誉,勇敢以及家庭的温暖。但是一旦这些失败(平稳观念未被接受),他们将召集警察和社会力量来支持他们,惩罚并压制那些不利于社会的鲁莽举动。福柯[25]认为精神医疗的权力,其基础便在于把疯狂和犯罪钉绑在一起。这不再是一个关于真相的问题,而是一个有关于社会危险及其防卫的论述。
到那时,那位女神便会从她潜伏之处悄悄地走出,登上宝座;她的欲望是镇压反抗,把自己的形象永不磨灭地树立在他人的圣殿内。于是那些赤身裸体、筋疲力尽、举目无亲、无力自卫的人们受到威廉爵士的意志的冲击。她猛扑,她吞噬,她把人们禁闭[24]104。
“女神”意象代表了“平稳观念”,暗示她的权力是如此的至高无上,以致没有人敢违抗她的意志。在英国这样一个规训社会里,统治阶级就是要把他们所倡导的意识形态观念“平稳感”强加在劳动人们身上。这里叙述者把医生看作“平稳感”的化身。一旦遭遇反抗,他们就“镇压、猛扑、吞噬”和“禁闭”。这些携有否定含义的物质过程传达了来自英国社会统治阶级的压迫对弱者的巨大威胁。这些词充满了对权力的实施。形容词“赤身裸体的、筋疲力尽的、举目无亲的”和“无力自卫的”表明了受压迫者无能反抗权势群体,只好接受以威廉爵士为代表的统治阶级的权力意志。威廉爵士有着强烈的控制欲,想把他的意志强加给弱者。他想征服一切挑战他世界观的人。他想转化世界服从他的信仰体系,以获取权力并支配他人,因此,叙述者负面评价了他。
3 结束语
通过对意识流小说《达洛卫夫人》批评话语分析表明,作者选择了大量表达负面含义的充满权力行使的物质过程动词来表达权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规训和暴力惩罚。“医生”、“女神”和“疗养院”意象的使用传达了统治阶级对民众的压迫和操控。医生和病人之间对话轮次及异常语言现象分析展示了他们之间不均衡的权力关系。表明确主观的小句情态,高量值意态的使用也表明了权势者对弱势者的巨大压力。作者的语言选择充分表达了小说的主题意义:英国统治阶级对民众的压迫和操控。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争夺霸权,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英国传统的社会结构迅速解体,传统的伦理道德与价值观被战争的硝烟摧毁,人性受到严重压抑和扭曲。在这样一个社会文化背景下,英国社会制度受到了质疑和挑战。因而英国社会的统治者们急于在民众中传播,并迫使他们接受意识形态观念“平稳感”,目的是为建立他们所谓的“正常化社会”,维持他们对人民的统治权力,从而巩固英国社会制度。小说作者大胆、辛辣地批判和谴责了英国统治阶级和社会制度。因此,可以说伍尔夫的一生不仅致力于小说写作技巧的改革,同时也致力于英国社会制度的批评与改革。
[1]FOWLER R,et al.Language and Control[M].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79.
[2]FOWLER R.On critical linguistic[C]//In C R Caldas-Coulthard&R Coulthard(eds).Texts and Practices:Readings i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London:Routledge.1996.
[3]FAIRCLOUGH N.Language and Power[M].London:Routledge,1989.
[4]FAIRCLOUGH N.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M].Cambridge/Oxford:Polity Press,1992.
[5]FAIRCLOUGH N.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The critical study of language[M].London/NewYork:Longman,1995.
[6]FAIRCLOUGH N.Analysing discourse:Text analysis for social research[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3.
[7]THOMPSON J.B.Ideology and mordern culture[M].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
[8]VAN D T.Principle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C]//In M.Wethell,S.Taylor&S.J.Taylor(eds.).Discourse Theory and Practice.London:Sage Publications,2001.
[9]陈中竺.批评语言学述评[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5,27(1):21-27.
[10]陈中竺.语篇与意识形态:批评性语篇分析——对两条罢工新闻的分析[J].外国语,1995,97(3):42-45.
[11]辛斌.语言、权力与意识形态:批评语言学[J].现代外语,1996,71(1):22-26.
[12]项蕴华.简述Fairclough的语篇分析观[J].山东外语教学,2004,102(5):19-22
[13]丁建新,廖益清.批评话语分析述评[J].当代语言学,2001,3(4):305-310.
[14]辛斌.批评语言学——理论与应用[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15]吕万英.法官话语的权力支配[J].外语研究,2006,96(2):10-13.
[16]田海龙,张迈曾.话语权力的不平等关系:语用学与社会学研究[J].外语学刊,2006,129(2):7-13.
[17]徐涛,张迈曾.高等教育话语的新变迁——机构身份再构建的跨学科研究[J].河北大学学报,2004,29(3):108-110.
[18]曹广涛.汉英对比研究中的权力话语[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3,19(5):130-56.
[19]徐王群.《儒林外史》英汉语对比研究——语言与文化[J].外语教学,2003,24(2):48-51.
[20]FOUCAULT M.Power/Knowledge[M].Brighton:Harvester,1980.
[21]SIMPSON P.language,ideology and point of view[M].London:Routledge,1993.
[22]HALLIDAY M A K.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M].London:Edward Arnold/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1994/2000.
[23]FOUCAULT M.Discipline and punish:The birth of the prison[M].New York:Vintage Books,1995.
[24]弗吉尼亚·伍尔夫.达洛卫夫人[M].孙梁,苏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25]米歇尔·福柯.不正常的人[M]钱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26]黄瑞祺.再见福柯:福柯晚期思想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 王全金 李萍)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n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Novel Mrs.Dalloway
GUAN Shuh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Nanchang 330013,China)
The purpose of CDA is to examine the value system or the ideology hidden in discourse by analyzing their language features and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generated,and thus to reveal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language,power and ideology.This paper is based on CDA theory,combined with Foucault’s discusses on the disciplinary power and the mental medical power,and adopts the analytic approaches of Halliday’s functional linguistics to illustrate literary significance and the author’s criticism of social system of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novel Mrs.Dalloway written by Virginia Woolf.
CDA;power;ideology;stream of consciousness novel;social criticism
H059
A
1005-0523(2010)04-0075-07
2010-05-05
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YY0706)
管淑红(1966-),女,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批评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语篇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