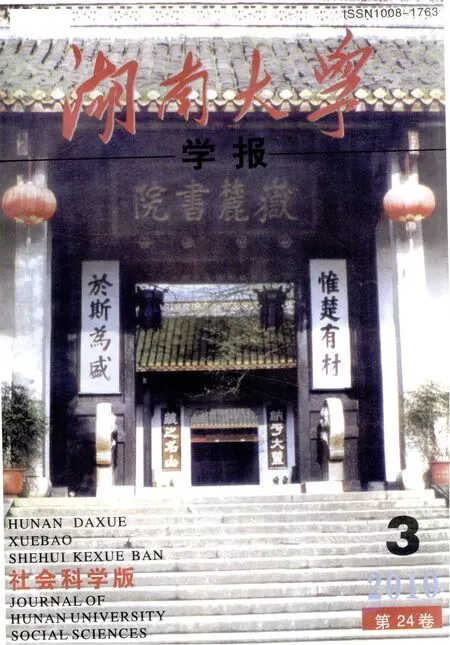文化悲剧与现代性货币——齐美尔距离的生成语境解读*
杨向荣,傅海勤
(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湘潭 411105)
文化悲剧与现代性货币
——齐美尔距离的生成语境解读*
杨向荣,傅海勤
(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湘潭 411105)
在现代性视域下,齐美尔提出距离理论,认为个体面对物化文化的巨大压力,只有通过与其保持距离才能获得救赎。对齐美尔距离的生成语境可以从两个方面展开分析:文化的悲剧性诊断和货币的现代性表征。
距离;语境;文化悲剧;现代性货币
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对资本主义文明带来的工具理性对个体生存的全面压制,齐美尔提出“距离”①距离在齐美尔思想中具有多种内涵。从社会学维度来看,距离是个体在现代社会中得以保存自身的策略.个体只有远离被物化文明所控制的现代生活,才能抵御物化文明对人性内在本真的不断侵蚀。从美学维度来看,距离是现代生活的一种审美维度,距离可以实现对现代生活的审美超越.从现代性体验维度来看,距离是对现代性生活的一种体验,时尚和冒险是这种距离体验的极佳范例,时尚意味着通过距离实现对平庸日常生活的颠覆,而冒险则意味着通过距离实现对现代生存的越境.理论与资本主义物化文明进行对抗。目前学术界对齐美尔的距离理论研究不是很多,而对距离产生的语境更是语焉不详。本文立足于现代性这一维度,力图从文化的悲剧性诊断和货币的现代性品格两个层面对齐美尔距离的生成语境进行解读。
一 文化的悲剧性诊断
在齐美尔眼中,文化是由生命与形式构成的整体存在,是内在精神与外在形式的融合。齐美尔认为,在前现代社会,文化的内在精神与外在形式处于水乳交融的和谐状态,但随着现代社会的出现,这种和谐状态逐渐被打破,外在的物质文化得以高扬,并对主体内在的精神文化构成极大威胁。“近百年来,在生产设备和生产技术服务方面,在各种知识和艺术方面,在不断改善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情趣方面,社会分工日趋繁多复杂。作为个性开化原材料的个人能力很难适应这一发展速度,已远远地落在后面。”[1](P95-96)客观文化的空前膨胀及其对主观文化的全面压制,导致主观文化跟不上客观文化的发展,远远落在客观文化的后面,这就是齐美尔关于现代文化的悲剧性诊断。
齐美尔关于文化悲剧的论述是与其对文化生命与形式关系的论述联系在一起的。在齐美尔看来,当生命由超越纯粹的生物层面进入精神层面和文化层面之后,矛盾便产生了,而整个文化的进化史就是处理这种矛盾的历史。“生命过程的这些产物的一个独特品质是它一诞生就具有属于它们自己的固定形式。……形式在产生之时或许完全适合生命,但随着生命的不断演化,形式会变得僵化,会从生命中脱离出来,并与生命相敌对。”[2](P11)在齐美尔的语境中,文化悲剧的实质是文化生命与形式的二元对抗。生命总是希望获得它不能达到的某种境界,它企图超越一切形式,然而生命只能用形式来体现,生命与形式由此构成一种冲突。这种冲突不仅无法避免,而且也永不会停止,“生命与形式从一开始就处于一种潜在的对抗之中,并在活动的许多领域表现出来。从长期来看,这种对抗关系最终会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危机。”[2](P12)生命总是希望实现它不能达到的某种境界,它企图超越一切形式。然而生命又只能用形式来体现,这些形式作为生命的容器,希望把生命的继续流动都接受下来,而生命是成型的统一体,它企图实现对现有单一形式的彻底超越,打破现存形式的束缚。生命与形式的永恒冲突构成了齐美尔文化哲学的主体部分,成为贯穿其整个文化和美学思想的一条主线。
生命与形式永不停歇的冲突,揭示了齐美尔深以为忧的现代性文化困境。齐美尔认为,文化悲剧在现代社会中将会愈演愈烈,必定会导致人类对文化的普遍不满,以及作为整体的文化的最终衰竭,“文化的不同分支各自为政,互不理睬;作为整体的文化实际上已经难逃巴比伦塔的厄运,因为其最深刻的价值正存在于各部分的集合之中,而这种价值现在似乎岌岌可危:所有这些都是文化演进不可或缺的悖论。它们逻辑上的最终后果将会是文化一直持续发展到灭亡的地步。”[3](P183-184)客观文化的发展以主观文化的牺牲为代价,个体所创造出来的文化反而成为了个体的“他者”,现代文化的深刻悲剧由此而生。
社会学家阿迪蒂认为,在齐美尔的语境中,现代文化的日益客观化,在其最广泛的意义上,势必会导致社会结构中距离现象的增长。[4]我以为,对齐美尔而言,距离既是现代文化日益理性化的必然结果,也是个体在现代社会中得以保存自身的策略,即通过创造一种距离来保存自我的独特性。对此,弗里斯比分析说:“对个人内在生活的强调,与齐美尔保护个体性的意图以及后来——随着与对主观文化和客观文化之间必然扩张的裂痕的日趋容忍——重新构建个体性的意图非常吻合。”[5](P82)弗里斯比还认为,齐美尔语境中的距离,其实就是现代个体在都市中表现出的一种对周围环境完全冷漠的态度。“在极端形式下,随着新鲜或不断变化的印象而来的诸多感觉的持续轰击,产生了神经衰弱人格,它最终不再能够处理这些纷至沓来的印象和冲击。这导致了在我们自身和我们的社会及物质环境之间创造距离的努力。”[5](P96-97)对此,刘小枫也认为,“在齐美尔看来,距离心态最能表征现代人生活的感觉状态:害怕被触及,害怕被卷入。但现代人对于孤独,既难以承受,又不可离弃;即便异性之间的交往,也只愿建立感性的同伴关系,不愿成为一体,不愿进入责任关系。……事实上,距离感的基础是个体身体的不可重复和独一无二性,时装模特与观者在时装表演的时间中交流的是个体身体的感觉,美感的个体主义的实质正在于此。”[6](P334-335)在刘小枫看来,距离导致都市个体间的冷漠和相互设防。然而,正是这种心理距离的存在,可以使我们在过于理性化的生存环境中,获得一块主观性的安全岛,一块秘密的、封闭的隐私领域。
仔细琢磨齐美尔的话,文化的悲剧也许还可以从乐观的角度加以理解。文化悲剧之所以是主观文化与客观文化之间无法调和的冲突,原因就在于不论外在的客观文化多么强大,个体的内在精神生命总是要设法抗拒客观世界对它的压制和封杀。在齐美尔看来,引导个体去抗拒外在世界,实现自我的力量就存在于那富有创造性的、纯粹的个体生命本身。有学者在分析资产阶级文化时提出,当下的文化“所呈现出来的,已经是一种虽然虚假却无比强大的总体性力量。文化工业作为一种虚假的总体性,已经将现代社会中的个体带入到一个无从逃避的文化陷阱之中”[7]。因此,当外在物化趋势愈演愈烈,个体的外在世界变得越来越客观化时,个体的救赎就存在于对内在纯粹生命本身的诉求与挖掘中。据此,齐美尔认为,个体面对物质文化的巨大压力,只有通过远离物质世界才能获得生机。距离是现代个体在现代性语境下对物化文明的一种抵御,是现代人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扩张所造成个体本真体验被剥夺后所提出的救赎之途。
此外,齐美尔所言的文化悲剧也可以看作是启蒙运动以来两种现代性(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冲突在文化中的表征。18世纪的启蒙运动所引发的理性对宗教的取代(韦伯意义上的“祛魅”)意味着世俗社会对宗教社会的胜利。然而理性的高扬所带来的并不仅仅是社会的进步,同时也带来了社会的物化和理性的工具化。韦伯认为,现代性一方面是现代社会高度的理性化和科层化,但另一方面却把现代人带入到一个无法挣脱的“铁笼”,而“铁笼”的异化生存将导致“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8](P142-143)。现代社会成为了一个巨大的铁笼,生活于其中的每一个现代个体都要受到铁栏杆的束缚,成为没有灵魂和自我的另类存在。然而,理性的空前膨胀也滋生了理性的叛逆者。因此,启蒙运动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种种矛盾与冲突,这些冲突最终可以归结为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的矛盾与冲突。启蒙现代性体现在社会层面上,其主要表现是合理化社会的形成和工具理性的蔓延,而审美现代性体现在文化层面上,其主要表现是对工具理性和资本主义文明进行拒绝,以及对资本主义的“合理化后果”进行批判。这种批判在现代艺术中体现为艺术必须站在生活的对立面,与生活意识形态保持一定的距离。正如阿多诺所言:艺术是社会的,主要是因为艺术站在社会的对立面,艺术的这种社会偏离恰恰就是对特定社会的毫不留情的批判。[9](P321)。可见,作为对物化文明的批判,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一样同为现代性的孪生子,这对孪生子从一出生就处于不断的冲突中,而这种冲突却是现代性发展之必然。
二 货币的现代性品格
现代文化悲剧揭示了距离产生的文化根源,而货币的现代性品格及其伴生的都市生活风格则是距离产生的社会根源。
多德认为,货币代表了现代社会和文化的最独特的特点。[10](P31)这一思想可谓与齐美尔不谋而合。在《货币哲学》中,货币对现代文化及个体社会生活的影响,是齐美尔货币文化分析的核心所在。弗里斯比认为,《货币哲学》一书“不仅仅从社会学角度关注货币经济对社会及文化生活产生的作用,而且显示出建立一套文化哲学,乃至生命形而上学的努力”[11](P200)。货币不仅仅是经济现象,它更是现代社会中的文化事件,“作者讨论的是货币,但通过货币,他让我们看到的是人和生活。”[12](P130)对齐美尔而言,货币经济引起了现代社会关系的转化,同时也是现代都市生活风格的主要根源。马尔图切利认为,在齐美尔的视域中,货币是人与世界的相对性关系的最好象征,“是连接和拆散社会生活和主观生活的原因的有效支撑和象征性反映。通过货币,齐美尔试图在生活中最分散和最表面的因素和社会中最深刻和最主要的倾向之间建立一种关系。”[13](P304)货币经济及其所带来的影响,构成了齐美尔现代性分析的核心,而齐美尔从货币的文化后果来分析现代社会这一不可或缺的经济符号,并成功地将原本是经济符号的货币转变为一种文化审美符号。
在齐美尔看来,货币导致了现代生活的量化和平均化,生命的意义在货币面前日益式微。在现代社会中,从货币的汪洋大海中流出来的东西不再带有任何的自身独特之处。货币夷平了所有事物的独特性,使毫不相同的事物具有了质的同一性,“事物都以相同的比重在滚滚向前的货币洪流中漂流,全都处于同一个水平,仅仅是一个个的大小不同。”[1](P266)事物背后的独特内涵在货币面前变得黯然失色,生活的终极追求和意义在货币面前惨遭失落,生命的终极目的也最终被这种纯粹的物质手段所掩盖。货币作为一切价值的公分母,它平均化了所有性质迥异的事物,从而赋予事物前所未有的客观性——一种无风格、无特色、无色彩的单一存在。更可怕的是,一旦现代社会个体只关注作为一种纯粹手段的货币,这种根本上无特色的东西会变得毫无用处,反而使现代人对现代生活彻底失望,产生空虚与无聊,因为“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上的”[11](P10)。对此,有学者指出,现代性的发展已使得货币经济与物质文化日益膨胀,其后果必然是“各种手段甚至那些不惜损害他者利益以满足一己之私的手段都会被不加选择和不计道义地变成牟取暴利的工具,以金钱为核心目的的物质利益诉求成为这种人性形象的欲望法则与生活价值座架”[14]。可见,货币经济的扩展使得现代性自身呈现出某种内在悖论:一方面是经济高速发展与个体生活的丰富,而另一方面则是个体在货币经济强势下的异化。由于货币可以随时地被期望和追求,个体可以在任何时候以任何一种方式去追求它,货币因而成了现代社会个体生命中不受任何限制的目标,它毫无特色,然而又极具诱惑力,它给现代人的生活提供了持续不断的刺激,“给现代生活装上一个无法停转的轮子,它使生活这架机器成为一部‘永动机’,由此就产生了现代生活常见的骚动不安与狂热不休。”[11](P12)当货币以中性、无差别的性格剥夺了所有事物的独特价值和个性后,在永不停息的货币之流中,现代个体就再也感觉不到对象的意义和价值的差别,一切都变得平庸和千篇一律,而没有任何鲜活感。
通过把具有自我独特性的事物以同一的方式置于相同的平面,货币成为了世间所有事物最可怕的平等化中介,不同的事物之间仅仅只具有量上的差异,这使现代生活充满单调而灰色的情调,没有什么事能提起现代人特别的兴趣。当个体的神经拒绝对任何刺激作出反应时,也就导致了现代人的自我意识和个人主义的空前膨胀,并使个体之间的关系变得冷漠无情。齐美尔认为,冷漠和缺乏人情味的现代生活风格虽然是货币经济空前高涨的产物,它带来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猜忌与彼此中伤以及个体在现代社会中的自我退隐,但这种风格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又是对个体的一种自我保护。由于现代文化的发展以客体精神对主体精神的优势为特征,在文化的发展中,个体的主观文化远远跟不上客观文化的发展速度,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就不得不将内在心灵从外在物质文化中撤退回来,以求个性本真的自保。虽然“一定个性的自我保存建立在降低整个客观世界的价值的基础上,而这种降低最终会不可避免地将自我的个性拖向同样毫无价值的感觉”,[15](P179)但这种个体的自我退隐和自我保存在齐美尔看来却是现代人适应都市生活的最后可能性,它通过使个体远离异化的社会而成功保护了个体内在精神的本真与完整。
在齐美尔看来,受货币的同一化影响,现代个体往往过着千篇一律的生活方式,个体在现代都市的频繁刺激下,已丧失了感知体验的丰富性和敏锐性,变得对所有事物都无动于衷,感觉不出事物的独特细微性。齐美尔感叹道:“生活的核心和意义从我们的手指间一次又一次地滑走,确定性的满足感变得越来越罕有,以致所有的努力与活动都失去了实际的价值。”[15](P249)一旦货币对现代生活风格的夷平和对生存本真的遮蔽使现代个体的生存成为了一种毫无激情的体验,那么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个体的内在心灵及自我个性被忽视。而在货币文化的冲击下,个体的内在心灵世界要力争保持自身的自由与自在,就不得不远离不断全面发展的货币文化而以求自保。[16]
个体对货币经济膨胀的恐慌,并千方百计地试图从中逃逸出去,这是个体对货币经济所主导的现代文化形态和社会生活客观逻辑的反弹,是对工具理性化的社会所带给个体的“磨蚀”的一种逃逸和抗拒,它体现了个体力图保持独立个性的努力及要求。面对现代社会的生存困境,个体试图远离货币文化来实现自我的救赎,这就构成了齐美尔著名的距离救赎策略:在物化文明导致个体个性沦丧愈演愈烈的趋势下,个体只有远离物化现实,通过与物化现实保持距离,才能抵御物化现实对人性本真的不断侵蚀,才能实现个体的最终救赎。有学者在分析审美现代性的浪漫情怀时曾指出,寻求生命内在的力量,赋予生命以永恒的意义,这是审美现代性的应有涵义,在其中,“浪漫的审美现代性不满于社会文明发展对人性的异化与逼仄,尤其是技术、机器、计算的效益与功利至上所带来的商品物欲横流、人欲膨胀的丑恶,以情感和审美勾勒社会理想,寻求诗意失落后的补救。”[17]这种浪漫的诗意现代性,其实也就是对现代生活的审美挖掘,而在齐美尔的视域中,这种审美挖掘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创造距离而得以实现的。而通过这样一种审美维度来审视生活,从而可以使个体超越现实生活的陈旧,发现生活的诗意和实现个体的自我救赎。
[1] 齐美尔.桥与门[M].涯鸿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
[2] K.Peter Etzkorn(ed.),The Conflict in Modern Culture and Other Essays[M].New York:Teachers College Press,1968.
[3] 齐美尔.时尚的哲学[M].费勇等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1.
[4] Arditi.Simmel’s Theory of Alien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the Nonrational[J].Sociological Theory,1996,(2):92-108.
[5] 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M].卢晖临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
[6]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7] 李健.文化工业批判再思考[J].湘潭大学学报,2009,(1):118 -121.
[8]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2.
[9] Adorno.Aesthetic Theory[M].London:Routledge,1984.
[10]多德.社会理论与理代性[M].陶传进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11]齐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M].顾仁明译.北京:学林出版社,2000.
[12]Frisby(ed.),Georg Simmel:Critical Assessments,Vol.Ⅰ[M].London:Routledge,1994.130.
[13]马尔图切利.现代性社会学:二十世纪的历程[M].姜志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
[14]李胜清.消费文化的“形象异化”问题批判[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08,(6):60-64.
[15]Frisby&Featherstone(ed.),Simmel on Culture[M].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97.
[16]张文初.文学的精神性:现有理论建构的危机[J].理论与创作,2009,(5):4-7.
[17]赵立坤.浪漫主义与审美现代性[J].湘潭大学学报,2008,(5): 126-131.
Culture Tragedy and Modernity Money——The Reading of Birth Context of Simmel’s Distance
YANG Xiang-rong,FU Hai-qin
(Literary and New s Department,Xiangtan University,Xiangtan 411105,China)
Simmel puts forward distance theory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ity.In his eyes,individuals face the huge pressure of materialized culture,only through keep distance with materialized culture can realize redeem.For the Birth Context of Simmel’s distance,we can analysis from two aspects:the tragedy diagnose of culture and the modernity representation of money.
distance;context;culture tragedy;modernity money
I01
A
1008—1763(2010)03—0130—04
2009-04-01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现代性和审美救赎:齐美尔与法兰克福学派文艺美学的关联研究”(09YBA 142)
杨向荣(1978—),男,湖南长沙人,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西方美学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