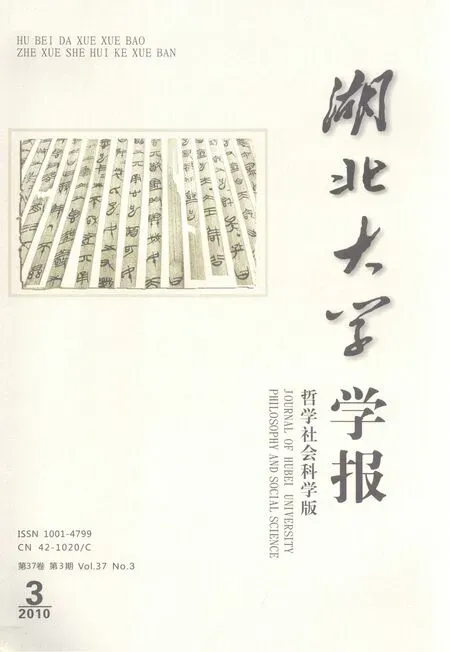平正温雅:曾巩散文风格论
喻进芳
(江汉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湖北武汉430056)
平正温雅:曾巩散文风格论
喻进芳
(江汉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湖北武汉430056)
不同于苏轼的超迈放逸,不同于王安石的简劲果敢,也不同于欧阳修的温婉多情,平正温雅是曾巩文风最鲜明的表现。从某种意义上说,曾巩散文的特色,与其说是语言艺术的成功,毋宁说是人生态度上的特点。可以看到,曾巩平正温雅的文章风格并不是孤立形成的,文章是其生命的有机构成,其创作风格必然与人生的整体态度相关联。因此只有将其文学创作的理念置于全部人生思考的背景中去考察,才能真正把握其文章风格。曾巩用自己的思考方式对儒学作出了合于自己人生态势的解读,也就是说,他的人生思考和行动轨迹基本对应着他对儒学的思考,他的文章则是他的思考轨迹在语言上的对象化,也是他生命形式的忠实展现。
曾巩;散文风格;平正温雅;情感态度;道德涵养
一
茅坤在《复陈五岳方伯书》中云:“仆尝谬论文章之旨,如韩柳欧苏曾王辈,固有正统,……而八君子者之中,曾子固殊属木讷,叫之无声,嘘之无焰,而仆犹取之,以其所序《战国策》诸书,及记筠州、宜黄学诸文,盖亦翩然能得古六籍之遗而言之者已。要之,非世所谓翡翠珊瑚、刻镂剿赝之饰而为之文者。”[1]576袁枚对茅坤标举曾巩为“八大家”之一表示异议,他说:“曾文平钝,如大轩骈骨,连缀不得断,实开南宋理学一门,又安得与半山、六一较伯仲也?”[2]4128这种争议正好引起我们的思考。的确,我们今天初读曾文也同样难得怦然心动,因为曾文既没有气冲斗牛、昂扬感奋的豪气,也没有天马行空、横放斜出的逸气,更没有红紫烂漫、撩人心肠的柔情。曾巩一生相对平淡,对于人生的穷达成败、升沉起落都没有显出大喜大悲,他以对道德的持守从容于俗世,整个人生现出一种淡静泊如的状态。其散文的风格正是他应世观物的情感态度和生命体验方式的外化,体现了相同的特征:平静、节制、中和。这种情感体验以及表现这种体验的特点,即后人评论的平正温雅。
曾巩散文的平正温雅首先表现在应世观物的情感态度上。曾巩青少年时代就开始品尝人生的酸甜苦辣,18岁时父亲落职回家,家庭重担肩于一身,29岁父亲客死外地,独自一人千里扶丧归乡。《学舍记》作于至和元年,其时曾巩36岁,已困于科场十八年,他对自己36岁以前的遭遇一一道来,并无半点牢骚不平,他说:“今天子至和之初,予之侵扰多事故益甚,予之力无以为,乃休于家,而即其旁之草舍以学。或疾其卑,议其隘者,予顾而笑曰:‘是予之宜也。予之劳心困形,以役于事者,有以为之矣。予之卑巷穷庐,冗衣砻饭,芑苋之羹,隐约而安者,固予之所以遂其志而有待也。……’”虽然曾巩在文中也明确表现出自己的遗憾之处,但他采取一种平和的态度,将此时的劳心困形当作一种人生的历练和通向理想之路的磨砺。曾肇评价其兄说:“公性谨严,而待物坦然,不为疑阻。于朋友喜尽言,虽取怨怒不悔也。于人有所长,奖励成就之如弗及。与人接,必尽礼。有怀不善之意来者,俟之益恭,至使其人心悦而去。遇僚属有所按摘,有所过误抵法者。力为辩理,无事而已。”[3]795这种待人接物的态度使他于朋友、于僚属甚至于敌人都能保持一种平稳谦恭的态度。
曾巩对于人生际遇总是采取“不争”的态度。对于一个有着远大志向的士人而言,人生的贫富穷达总是难于释怀的。宋代市民经济的发达所带来的物质诱惑,科举考试屡试不第的困厄,宋人为官所带来的种种矛盾与冲突,包括为官的高下尊卑之分、奔竞与安守的心灵斗争等等,这些都需要有一个精神寄托以保持贞定的形象,从而体现出士人的尊严。曾巩为人行事取法中庸,不走极端,在感情上趋向淡泊平和的情感特征,遇事往往将情感淡化,潜沉内转。尽管科场仕途不遇近四十年,但他从未走向虚无或玩世不恭。庆历二年,曾巩再次落榜,连一向温和的欧阳修都为之抱不平:“况曾生之业,其大者固已魁垒,其小者亦可以中尺度,而有司弃之,可怪也。”[4]2625曾巩虽然也有不平,却认为是自己的才学还不够好:“重念巩无似,见弃于有司,环视其中所有,颇识涯分,故报罢之初释然不自动,岂好大哉?诚其材资召取之如此故也。”①本文所引有关曾巩文章均出自于《曾巩集》,只注篇名。(《上欧阳学士第二书》)曾巩不第南归,有人甚至写诗讽刺:“三年一度举场开,落杀曾家两秀才。有似檐间双燕子,一双飞去一双来。”[5]7屡屡不第,又受里人的冷嘲热讽,可以想见曾巩当时的窘迫处境。然而,曾巩并没有因为科场的败北而呼天抢地,骚动难耐。与《学舍记》写于同时的《南轩记》是一篇座右铭式的题壁文,曾巩在文中说:“士固有所勤,有所肆,识其皆受之于天而顺之,则吾亦无处而非其乐也。”其时曾巩正退休在家,自耕力学,为了勉励自己,曾巩将此文“书之南轩之壁间,蚤夜览观焉,以自进也”(《南轩记》)。在这篇文章中,曾巩大谈其“乐”,以对道德的持守超越具体的现实境遇,获得精神的自得之乐。这种“乐”的心态使他的感情很少走向偏执,而是适时地把握住自己的情感力度,表现出在任何人生情节中的淡定、平静。曾巩的仕途也非一帆风顺,先蹈厉于儒馆近十年,后又辗转各地任地方官约十年,一生与廊庙要职无缘,正如林希在《曾巩墓志》中所说:“公慨然有志于天下事,仕既晚,其大者未及试。”[3]799在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面前,曾巩虽然有些尴尬无奈,但并没有因此而失去精神的平衡。《宋史》本传说:“巩久外徙,世颇谓偃蹇不偶,一时后生辈蜂起,巩视之泊如也。”曾巩对人事的情感反应是那般的平和,不论什么样的人生遭遇,都以淡泊的情感态度化解之,显出温顺平和的个性特点。
曾巩散文的平正温雅在形式上最突出的体现,就是它那散缓的节奏和娓娓不断、不迫不躁的理性分析。曾巩的文章没有奇巧的构思,其平正体现在节奏的散缓和思理的绵密上。日本学者佐藤一郎认为,古文有古文独特的节奏,优秀的古文家都有自己的文章节奏[6]14~27。曾巩极少选用刺耳的字词和火爆激越的音节,这当然不是曾巩在刻意追求某种音乐效果,而是他节制平和的心境自然远离高亢激昂的节奏。不妨用耳朵感受一下《清心亭记》中的一段文句:
夫人之所以神明其德,与天地同其变化者,夫岂远哉?生于心而已矣。若夫极天下之知,以穷天下之理,于夫性之在我者,能尽之,命之在彼者,能安之,则万物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此君子之所以虚其心也,万物不能累我矣。而应乎万物,与民同其吉凶者,亦未尝废也。于是有法戒之设,邪僻之防,此君子之所以斋其心也。虚其心者,极乎精微,所以入神也。斋其心者,由乎中庸,所以致用也。然则君子之欲修其身,治其国家天下者,可知矣。
曾文不在一字一句上争奇斗巧,而是注重句间关系的整体表达:“哉”、“矣”、“者”、“也”这些句末虚词的次第迭用,造成文势轻微的起伏;又借“若夫”、“于是”、“所以”、“然则”这些句中连词使文意开阖有度,语气连贯。末尾三句,将“也”字运用于两个对句的句尾,使本来严整的偶句变得纡缓、从容、镇静,“矣”字放于句末,带有咏叹的韵味,又兼收停顿舒展之功,避免一泻无余之弊,显得散缓而镇定。其语句没有浓丽的色彩,没有愤慨怨激之词,没有严苛训斥之意,没有排山倒海之力,整体感觉像是一位温和的长者,侃侃论理,循循善诱。
曾巩散文善于藏锋敛锷,层层推衍,曲折达意。《寄欧阳舍人书》是曾巩为感谢欧阳修为自己祖父撰写墓志铭而写的一封信。文章起笔即言得欧公为祖父作墓碑铭,“感与惭并”。然而下文却没有紧跟着赞美欧公“蓄道德而能文章”,而是宕开笔墨,把史传与铭志相较异同,又马上将史传撇开,强调铭志当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其严”。紧接着借“铭始不实”跌落到作铭者身上,从而逼出作铭者必“蓄道德而能文章”才能做到“公与是”的观点,并从道德文章两方面加以论述。行文至此,似乎该收回笔墨,赞美欧公了,然而笔锋一转,又说道德文章兼备者“虽或并世而有,亦或数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总之是说得千难万难,终于归结到欧公身上:“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谓数百年而有者也。”沈德潜评此文云:“逐层牵引,如春蚕吐丝,春山出云,不使人览而易尽。”[7]3762这种直觉印象式的品评正好形象地说明了曾文给人的总体感受,不是那种疾风暴雨式的强劲节奏,也不是那种悬崖断壁式的凌厉斩截,而是像“春蚕吐丝”般绵密细致,像“春山出云”般温和畅达。
二
不同于苏轼的超迈放逸,不同于王安石的简劲果敢,也不同于欧阳修的温婉多情,平正温雅是曾巩文风最鲜明的表现。南宋理学家朱熹在唐宋散文八大家中对曾巩推崇备至,他说:“曾南丰文字又更峻洁,虽议论有浅近处,然却平正好。”[8]3309后人对曾巩散文的评价深受朱熹的影响。那么,曾巩的文风是怎样形成的呢?
首先有时代和社会风气的影响。宋代在总结前朝兴衰的教训时,也对前代的文章风格进行了批判,对于唐人的张扬发越进行了扬弃,体现出以理节情的理性态度。宋代虽然从宋太祖开国就实行“右文”政策,文士们有了较前代更多的进身机会,但是宋代保守的政治态度与冗官制度又使宋代士人“兼济天下”之志往往难以实现,“遇”与“不遇”仍然是失意文人不可避免的咏叹调。宋代士人又不同于前代文人,他们在儒学复古思潮的影响下,更注重对历史人生、政治社会作理性的思考,提出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口号,以道德自信来超越不幸,稀释不平。理性的精神表现为人生价值和自我命运的理智把握,对人生缺憾的冷静排解,反应到文学中就是强烈的抒情动机的消解。冷静的人生态度在文学中表现为客观冷静的文风。这可以看作是形成曾巩文风的一种社会学的解释。然而,与曾巩亦师亦友的欧阳修,与曾巩同学的王安石,其文风各不相同,特别是王安石的文章“简劲拗折”,并不像曾巩那么“平正”。可见时代和社会风气的影响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社会学的角度还不足以解释曾文风格的成因。
曾巩曾对自己的文风间接地提供了一种个性方面的解释。他多次自道其性,如:“人之性不同,于是知伏闲隐坳,吾性所最宜。驱之就烦,非其器所长。况使之争于势利、爱恶、毁誉之间邪?”(《南轩记》)又云:“人生省已分,静默固其端”(《杂诗五首》之四),“我亦本萧散,至此更怡然”(《招隐寺》),“颇识麋鹿性”(《初发襄阳携家夜登岘山置酒》)等。曾巩的情感特征一方面可能与天性有关,这些表现了他厌恶喧嚣、喜欢安静的本分。对于自己的亲朋好友,曾巩也着力赞美他们蔼然温厚、渊静沉着的一面:如赞扬自己的二妹“恭严诚顺”(《江都县主簿王君夫人曾氏墓志铭》),九妹“柔悘静颛”、“平居温温”(《仙源县君曾氏墓志铭》),说自己的弟弟“质直孝悌”、“抑畏小心”(《亡弟湘潭县主簿子翊墓志铭》),说侄儿“为人恭谨,循循寡言”(《亡侄韶州军事判官墓志铭》)。清刘熙载认为曾文的形成与曾巩的个人性情、人生态度有直接关系:“曾文穷尽事理,其气味尔雅深厚,令人想见硕人之宽。王介甫云:‘夫安驱徐行,韊中庸之廷而造乎其室,舍二贤人者而谁哉?’二贤,谓正之、子固也。然则子固之文,即肖子固之为人矣。”[9]31但是,曾巩也并不总是呈现出从容温雅的一面。他在《读贾谊传》中对贾谊的遭遇大发悲叹之情;在《与孙司封书》中为孔宗旦辩冤,言辞急切,慷慨淋漓。他的散文,特别是早期的散文也有纵横变化、波澜跌宕的一面。与曾巩同时代的王震指出了曾巩散文特点的变化过程:“异时齿发壮,志气锐,其文章之剽鸷奔放,雄浑环伟,若三军之朝气,猛兽之扶怒,江湖之波涛,烟云之姿状,一何奇也”,最终是“衍裕雅重,自成一家”[3]810。由此可见,曾巩既有平正温和的一面,也有气壮不平的一面。的确,即使再“静默”、“萧散”的人也不可能在近四十年的平淡不遇中没有半句牢骚和埋怨,更何况“世界上本没有一个人能够有持久的宁静”[10]536,因此,曾巩的平正实际上是情感节制的结果。
在个体与现实社会关系、人格价值与外在功名之间,曾巩一开始并没有获得很好的平衡。当他以满腔热情投入社会时,得到的却是令人失望的磋跌困窘。这一点非常突出地表现在他对贾谊的同情共感上:
故予之穷饿,足以知人之穷者,亦必若此。又尝学文章,而知穷人之辞,自古皆然,是以于贾生少进焉。呜呼!使贾生卒其所施,为其功业,宜有可述者,又岂空言以道之哉?余之所以自悲者,亦若此。(《读贾谊传》)
曾巩对贾谊作出这样的体贴理解与宋代大多数士人对人生不遇的乐观情怀大相径庭。可以说,曾巩此处表现的嗟怨之情丝毫不减韩愈处卑位时的寒陋之态,而这种对贾谊的同情共感正是曾巩从崇高理想的云端跌落到现实的强烈反应。在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面前,曾巩显得不安、羞愧甚至愤激,此时他处在一种心理的煎熬中。但曾巩及时调整了寄托理想的方向,把价值期待转向自我,强调自我“得之于内”的崇高性,张扬个体修身守道“见于世”的价值,以此来排遣功名不显带来的不平和压力,使自己不论在何种境况中都能从容面对,始终处于精神不败的状态:“虽有刚柔缓急之异,皆可以进之中,而无过不及。使其识之明,气之充于其心,则用于进退语默之际,而无不得其宜;临之以福祸死生之故,无足动其意者。”(《宜黄县县学记》)其实,早在青少年时期曾巩就对儒家的进退出处之学深有体会,他向往功名,向往在当世获得实际的治世效用,但他同时也有“静默”的一面,他在《南轩记》中说:“得其时则行,守深山长谷而不出者,非也;不得其时则止,仆仆然求行其道者,亦非也。吾之不足于义,或爱而誉之者,过也;吾之足于义,或恶而毁之者,亦过也。彼何与于我哉?”曾巩认识到,过分地徇于外物必然使自己被外物牵着鼻子转,不能超越功名富贵得失成败等外在的形迹,就难于达到心境的淡定平和。
三
从某种意义上说,曾巩散文的特色,与其说是语言艺术的成功,毋宁说是人生态度上的特点。可以看到,曾巩平正温雅的文章风格并不是孤立形成的,文章是其生命的有机构成,其创作风格必然与人生的整体态度相关联。因此只有将其文学创作的理念置于全部人生思考的背景中去考察,才能真正把握其文章风格。曾巩用自己的思考方式对儒学作出了合于自己人生态势的解读,也就是说,他的人生思考和行动轨迹基本对应着他对儒学的思考,他的文章则是他的思考轨迹在语言上的对象化,也是他生命形式的忠实展现。
与日久年深之道德涵养而来的平正冲和是形成曾巩散文风格的重要因素。在曾文中可以看到他排解人生不平的思考轨迹。对于孔孟的解读表现了曾巩对于人格理想和价值目标的思考方式:“得其时,推此道以行于天下者,唐、虞、禹、汤、文、武之君,皋、夔、益、稷、伊尹、太公、周公之臣是也。不得其时,守此道以俟后世者,孔孟是也。”(《为治论》)同是圣贤,因为时势的不同决定他们不同的行为方式。孔孟不得其时的做法是“守道以俟”,对此,曾巩一方面强调孔孟守道是以另一种方式来体现道的价值,同样具有圣贤的品格,同时还隐含了另一种价值期待即孔孟守道虽不显达于当世,但终会流传后世并获得不朽的价值。这一点,曾巩在文章接下来的部分说得更明确:“孔子于周之末世,守二帝三王之道而不苟,孟子亦于其后守孔子之道而不苟。二子者,非不欲有为也,知不本先王之法度则不可以行,不得可为之势则不可以行,不得可为之势则不可以强通。……守之以终身,传之以待后之学者,此二子之见所以异于众也。”这正是孔子人生价值所在,这种价值的获取有别于习见的功业形式,而是在使道久远流传以见于后世的过程中获得的。对孔孟的解读使曾巩获得了在不遇人生中的应对策略,既然不遇是时势使然,那么抱道自守也是实现人生价值的一种有意义的方式。曾巩对儒学个体人格价值的诠释正契合于他抱道自守的人生方式,或者也可以说,他为自己抱道自守的人生方式找到了一个强大的理论支撑。他说:“明先王之道,内足以不惑,外足以行事,情性有不平欤?”(《说非异》)有了道的支撑,人世间的一切穷愁不平之气就在道的磨砻渐养中淡化稀释成和平之音。
从平和的心态出发,曾巩在内心获取高度自信时,把道德的履践和完善贯注于日常生活中,并不显示出傲世独立的状态。对儒道的认同也不是将之上升到一个不可企及的理论高度,而是强调儒道的与时俱进性,即“道不变而法可变”(《战国策目录序》);还有儒道的平常性:“内有以得诸己,外有以与人同其好,此所以为先王之道,而异乎百家之说”(《送丁琰序》)。这种处世心态决定了曾巩在文章的写作中不可能搜奇猎怪,气势逼人,而是娓娓而谈,如同圣人教诲,侃侃论理,循循善诱,显示出平正冲和的特点。对于曾巩而言,通往平和的路并非一路平坦,平和见于涵养,是诗书的渐磨,是人事的陶冶,是绵历世事后的结晶。曾国藩云:“造句约有两端:一曰雄奇,一曰惬适。雄奇者,瑰玮俊迈,以杨、马为最;……惬适者,汉之匡、刘,宋之欧、曾,均能细意熨帖,朴厉微至。雄奇者得之于天事,非人力所可强企;惬适者诗书酝酿,岁月磨练,皆可日起而有功。”[11]538这段话从语言风格的形成上将欧阳修、曾巩归入“惬适”一类,正是看到了道德涵养对其文风的影响。
从平和的心态出发,曾巩将眼光投注到现实生活的凡常诸事,他将自己的笔触伸向水利建设、荒政措施、建筑用工等方面,他常常肯定和提倡一些具体的好办法,供后人借鉴。其《越州赵公救灾记》将救灾之法写得井井有条,足以为“荒政可师者”;其《襄州宜城县长渠记》写得本末如掌,其原因是“山川与民之利害者,皆为州者之任”。他的传记都是生活中的小人物,注意写小人物的“人人所易到”的事迹,不求“摭奇动俗”的效果(《洪渥传》)。由于在题材的选取上能立足于现实,致意于凡俗,其文风自然走向平正冲和。
从心性理论重内在修养出发,曾巩强调内在的充实、外在的简易。宋代美学有“内外”、“中边”之辩,苏轼云:“佛云:‘如人食蜜,中边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别其中边者,百无一二也。”[12]367要体味个中真味,必须由表及里,也就是超越外部深入体会其与表象不一甚或迥异的内涵。这种鉴赏理论同时适用于创作态度。曾巩对“内”与“外”的思考有这样两段话:
文象百变,其为鼎象则一也;文象虽假,其为金则真也。一变而百,百归乎一,假不异真,真不异假。……夫六合内外,万物洪纤,有形无形,有识无识,生死去来,喜怒哀乐,皆一真之所融也,亦犹神鼎之上,一山一川,一草一木,一鸟一兽,莫非一金之所为也。(《全真庵》)
乐之实不在于器,而至于鼓之以尽神,则乐由中也明矣。故闻其乐可以知其德,而德之有见于乐者,岂系于器哉?惟其未离于器也,故习之有曲,以至于有数推之则将以得其志,又中于得其人,则器之所不及矣。(《听琴序》)
这两段文字分别从象与金、器与乐的关系立论,然而阐明的理论却有高度的一致性:其一,抽象的东西虽然微妙无形,却总需要通过一定的媒介显示出来;其二,正是由于内涵的微妙,所以不能停留于表象的品味,而应超越外部,深入体会与表象不一甚或迥异的内涵。这两点又可以从不同视角来解读:首先是对人生态度的影响,既然把握内涵不能停留在表象的层面,对一个人的评价必须超越外在的行表去把握内在的人格美,反过来人生的态度也就可以不受外在的功名、富贵、得失、成败、穷达、生死的牵累而保持精神自得;其次是对文章的影响,对文学的解读虽然必须由外至内,却不可停留在外在语言的工拙上,而要超越字句的表象,把握内在的丰美。反过来,对于创作者而言,语言的工拙只是一种外在形式,文章所表达的内涵才是最重要的。因此,在内外之间,内质无疑是最重要的,任何过分地追求外在形式都可能对内质有所损害,也反映了心理上的不能超越,这样,在内外之间形成一种看似矛盾的表现形式——“巧丽者发之于平淡,奇伟者行之于简易”[13]373,在人生态度上外示凡俗而中存高尚,形成一种淡泊韬晦的人生态度;在文章中则外示平淡而中有至味。
如此的思考,自然可以将外在的功名富贵、穷达寿夭不驻于心,而凭借以心得道的精神优势从容于俗世,取得平和从容的人生姿态。曾巩在《清心亭记》中说:“夫人之所以神明其德,与天地同其变化者,夫岂远哉?生于心而已矣。若夫极天下之知,以穷天下之理,于夫性之在我者,能尽之,命之在彼者,能安之,则万物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其实,正是曾巩在人格上圆成淡泊渊如的境界,才有散文的平正温雅。再大的矛盾、再激烈的心灵冲突,曾巩都能以对“道”的持守加以化解、调适而臻于精神的平衡,所以,曾文常常给人“春蚕吐丝”、“春山出云”般温润和畅的审美感受。要之,曾巩文章的平正温雅正是他平衡理想与现实矛盾之后的平和心态的表现。
[1]茅坤.茅鹿门先生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2]袁枚.小仓山房集[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3]曾巩.曾巩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4.
[4]欧阳修.欧阳修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1.
[5]夏汉宁.曾巩[M].北京:中华书局,1993.
[6]佐藤一郎.中国文章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7]高海夫.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
[8]朱熹.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9]刘熙载.艺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0]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上海:商务印书馆,1982.
[11]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12]苏轼.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3]郭绍虞.宋诗话辑佚[M].北京:中华书局,1980.
I206.2
A
1001-4799(2010)03-0029-05
2009-01-03
喻进芳(1970-),女,湖北武汉人,江汉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研究。
熊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