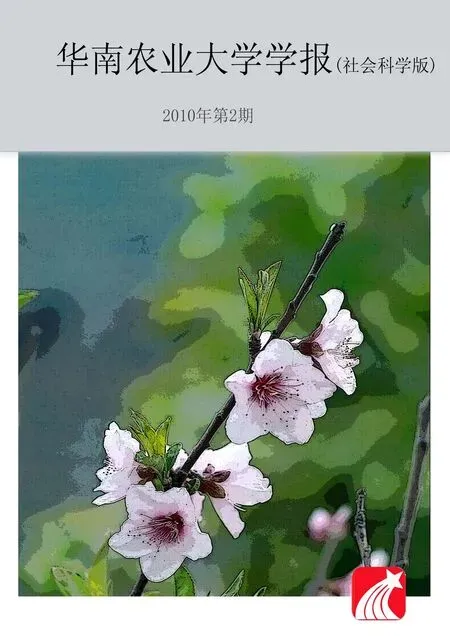论女性主义翻译的后现代性
周小玲
(广东商学院 外国语学院,广东 广州,510320)
一、引言
20世纪60年代随着结构主义的衰退,阐释学、接受美学、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后现代思潮的兴起,女性主义理论也应运而生。由于女性主义理论与翻译研究的基本范畴相互契合,女性主义理论被逐步应用到翻译领域。20世纪90年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在加拿大迅速崛起,形成了以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Spivak)、路易斯·冯·费拉德(Luise von Flotow也有人将其译为弗洛图)和谢莉·西蒙(Sherry Simon)等人为代表的女性主义翻译流派。国内的女性主义翻译研究肇始于2000年,以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一书的出版为标志,该书率先向中国读者介绍了女性主义翻译观。2004年中国翻译第4期刊出了4篇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专题文章,引发了国内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热潮。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经历了十几年的发展,在翻译界引发了一场思想革命,颠覆了传统译论中的语言意义观、对“忠实”、“等值”等概念、以及原文本和原作者的权威地位进行了质疑和消解,全面提升了译者的主体性,强调译者对文本的操作与改写权,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起到了推动作用。人们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态度从刚开始的好奇、追捧转变到近几年的质疑、批评与反思,女性主义翻译似乎在短短10年内行将走向终结。其实在这一片“倒戈”之声中,有关女性主义翻译还有很多课题值得我们研究。
从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女性主义翻译研究虽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也存在很多问题。从国际范围看,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性别与女性主义、女性写作及女性政治被混为一谈;二、女性主义翻译研究主要基于文学文本,而极少将翻译与非文学话语中的性别联系在一起[1]19;三、错误地构建第三世界女性作品在英、美、法等国的主流翻译实践,隐蔽了源于不同文化的女性之间的差异,以及写作上的个人风格,试图实现对于少数族裔的“民主治理”[2]。在国内,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多与理论的介绍相关,较少涉及实践问题,主要表现出以下问题:一、知识的重复消费比较严重,如论题及其展开方式高度相似,被援引频率最高的文献如费拉德提出的三种女性主义翻译实践方式、西蒙[3]提到的哈伍德在《她人的信》译本《前言》中的那段宣言,以及女性主义者惯用的某些表述。二、研究面窄,学术性与系统性不够。以往国内的研究基本围绕着斯皮瓦克、费拉德与西蒙三位教授展开,而鲜有针对德利尔、哥塔德、哈伍德、梅泽、尼科尔·沃德·乔夫与提莫志克等进行专门研究,更不必说玛格丽特·泰勒、阿芙拉·本、斯达尔夫人、玛格丽特·富勒、埃琳娜·马克思、康斯坦丝·加内特、让·斯塔尔·翁特梅尔、海伦·劳伊·波特等早期的重要女性(或女性主义)译者。根据国外有关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最新文献来看,有关后者的研究大有可为。三、部分文章论述上互有出入,甚至误读误解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例如,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究竟旨在凸显差异,还是消除差异?自由女性主义有没有意识到两性不平等的根源是社会差异?这些问题都有待我们进一步思考。
二、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相关性
女性主义翻译研究从诞生之日开始就凸显出其后现代主义的本质,以往国内外的研究也有过这方面的论述,如国内的葛梭琴[4],蒋骁华[5],陈琳[6]等等。作为叙事体系,后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都有其非连贯性。例如,德勒兹与加塔利对于后结构主义的“能指之暴政”曾不以为然[7],福柯的“述行矛盾”,以及他对于启蒙理性、主体的自身认同与欲望等话题的表述也前后矛盾[8]。同理,克里斯廷·德尔菲也曾质疑“法国女性主义”,认为它是英美两国炮制的命题[9]。就女性主义文学而言,后现代主义的某些理论也有解释力不够的地方,如鲍德里亚的“内爆”概念。可是,作为同时期最重要的政治文化派别,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在方法论、理论形态与价值追求等方面又高度相似,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对话语、知识与权力的综合分析、“解构”方法论的运用、反本质主义与普遍意义、反二分法,主张多元与差异,以及反对父权(后现代主义认为,现代性具有父权制特征,因此应遭批判)等。有鉴于此,从后现主义角度研究女性主义便有了空间。而从后现主义角度研究女性主义翻译不仅可以研究性别差异与忠实概念,又可以研究女性主义翻译的干涉策略、权力政治意识、语境意识、语言策略、翻译修辞的修正,以及身体写作与翻译等问题,有助于我们从另一个侧面全面地理解女性主义翻译观。
(一)反抗的权力政治意识
人文科学中,知识与权力之间有着复杂的联系,这一点已经在福柯关于监狱学与神经病学的研究中得到证明。正如研究女性主义文学应该结合考察伊格尔顿所说的文学文本分析模式的意识形态组成部分,以及特定生产与消费方式那样,研究女性主义翻译也应该研究其权力政治意识与批评功能,考察其与社会的历史关联,也即其“效果结构”[10]。例如,阿拉芙·本的翻译是为了实现向男性抗争的身份认同,沃尔斯通克拉夫特的翻译则成了她本人的“政治学徒期”(political apprenticeship)。对于本和沃尔斯通克拉夫特而言,翻译无疑是一项政治事业,而对于斯达尔夫人而言,翻译更是如此,因为它不仅仅机械地传达原文干瘪的文学形象,更能以干涉式的权力机制升华原著的美,有助于重振和丰富民族精神,发展政治解放和民族自治事业[11]。女性主义翻译者将后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文学观,及其批判功能运用于翻译研究,其翻译观表现出鲜明的干预主义与政治性等特征。
在两性关系问题上,女性主义翻译无疑采用了利奥塔关于“崇高感”的后现代主义视角。所谓“崇高感”主张女性的多元性与差异性,反对父权关于女性的“元叙述”。通过在翻译中使用“语言游戏”、“事件”(events)、“片语政体”(regimes of phrases)等试图“合法地解体”(delegitimatize)父权及其话语体系,阐发女性被边缘化之后的欲求,倾覆父权关于女性的规范化主体认同,实现女性族群由“被构成性自我”向“构作性自我”的身份转换。所谓“构造性欲望”是德勒兹与加塔利笔下典型的“游牧式思维”(nomadic thought)方式,它对抗了各种试图谴责、弱化或瘫痪女性欲望的父权力量。具体到女性主义翻译运动,这种“游牧式思维”便是采用“绝无停息”的“解辖化”(deterritorialization)斗争,在性别多样性之余建立“超国家网络”,在女性群体之间打造某种“沟通性权力”(communicative power),反抗顺从与屈服,摆脱父权针对女性建构的“克分子区割”(molar pole segregation)。否则,女性译者如果只懂得在父权话语轨迹中打转,便只会强化父权既有的“统治效应”[12]。“超国家网络”中的女性主义译者对于父权的集体防预与抵制触及到了女性权力意念的“支持系统”。她们认为,这种“支持系统”就是全体女性在社会规范价值方面的共享意识,即通过翻译实现对于父权统治的整体抗拒。这种抗拒不仅提升了译者(尤其是女性译者)的身份与地位,而且瓦解了翻译中的种种等级喻说。
(二)多维的语境意识
勿庸置疑,翻译是一种受制于语境的机会主义行为,它对原文本进行有计划的重写。勒弗维尔的研究表明,现行的翻译研究越来越重视布迪厄的两大社会学概念:习性和场域(habitus&champ/field)。这不仅可以研究译本,也可以研究译者,即研究那些影响文本生产、出版、传播、接受与复兴的各种语境因素,以及译者的主体性与个人政治。毫无疑问,翻译的语境研究受益于后结构主义及其相对主义思想,其强调意义的游移不定(slippery)、主观性(subjective)、机会主义(opportunist)与倾向性(partisan)等主张乃是典型的后现代主义思维模式。
费拉德曾研究女性主义翻译的“表述行为”特征,认为它集中体现了翻译的语境意识[13]。在巴特勒(Butler)[14]与梅尔与肯尼(Maier & Massardier Kenney)[15]看来,性别释义不具有普遍性,而是相对局部的,不断变化的观念结构,它依附于历史与文化因素。非传统的性别展示如异性装扮,或表示同性恋的话语,揭示出了性别自身的模仿结构及其偶发性(contingency),并通过戏讽、夸张与幽默等瓦解了传统性别的稳固性与“自然特征”(natural aspects)。对翻译的“表述行为”特征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同性恋作品的研究与翻译中。哈维曾专门探讨了90年代将身份看成“纯粹的表述行为效果”(pure effect of performality)的种种言论,并关注了标记性语言的跨文化翻译[16],因为异质文化强境中,不同的语言标记,或社会政治背景将影响同性恋者的表述行为性。通过分析戈尔·维戴尔(Gore Vidal)《城市和盐柱》(The City and the Pillar)的法语译文,以及托尼·杜威尔(Tony Duvert)的《幻想之景》(Paysage de fantaisie)的英译本,哈维说明了同性恋文化的特定规范,以及其所处文化语境怎样影响翻译文本的表述行为特征。哈维指出,维戴尔文本的法语译者采取了“低调处理”(tone down)的手段,这可能与法国的同性恋者不愿意依据“性行为特征变体”(variable of sexuality)进行自我身份认同有关,也反映了他们对于建构一个挑战和戏仿异性恋霸权的文化社区的怀疑态度。而与此相反,杜威尔的英译本则反映了同性恋文化在英美范围的实际存在。显然,只有充分理解了不同语境中的性别政治,才能很好地理解翻译文本的生成。
(三)干涉的语言策略
为了获得身份认同,女性主义译者在翻译时采用干涉的语言策略。张伯伦在讨论权利话语与性别模式时认为,女性不仅在身体上,而且也在语言文化上遭受歧视。费拉德认为,这与“翻译的贬值”(devaluation of translation)有关[17]。如张伯伦所说,以加夫隆斯基(Serge Gavronsky)为代表的20世纪翻译理论运用男性语言与神话,将翻译描述成“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忽视了女性的参与和贡献[18]。为了反抗传统文学与翻译针对女性的压迫,女性主义翻译借用女性主义文学观念,反对语言使用上的规范句法与既成文学体式,因为后者折射并固化了父权式权力结构。
只有通过文字游戏等语言手段,才能驳斥现代理性关于知识四大特征的表述[19],才能以后现代艺术般的随心所欲与玩世不恭,实现同父权的规戒性制度、实践与话语的分庭抗礼。如同女性主义文学秉承桑塔格的“新感受”艺术观一样,女性主义翻译也往往表现出模仿拼凑(pastiche)的特征,既引经据典,又诙谐戏谑,打乱了语言符号视听成份(signifiers)与概念成份(signified)之间的联系,印证了后现代主义的差异性与多元化特征。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可以规避语言的男性化倾向,揭示女性的历史与现实,更好地表达符合女性经验的世界观,卸下女性背负的“负面定势”。例如,霍华德·斯哥特曾经讨论波茜安妮克的翻译,认为将“Le ou la coupable doit etre punie”译作 “The guilty one must be punished,whether she is a man or a woman”,尽管“punie”一词在英文中未被呈现,但是波茜安妮克通过这一词所展示的语用意义还是在译文中得以维持,因为正是上述语言手段一定程度上搅乱了性别观念及其象征系统,颠覆了我们关于父权文本中女性形象的被动消费。
(四)“身体翻译”:女性主义翻译的色情性
西塞分析了写作的世界,指出女人的命运尚属未定之列,并认为“女性写作”可以帮助女人谋求出路。女性身体的节奏与情感可以为推翻“父亲之名”的主宰提供可能。父权制对于阳具的强调使人们忘却了“人”对于母体——人的主要生育者——的最初依赖[20]。因此,只有发明语言,女性才能光复自己的不可或缺性,打破父权制规戒的功能性存在。父权制的符号体系如不能破除,女性自身的话语体系与写作模式若不能确立,则女性只能继续被幽禁在失语中。
为了恢复被物化、被遮掩、被诋毁、以及被驯化的女性身体,女性主义者倡导“身体写作”,旨在表现被父权审查与诋毁的女性生理部位。对于翻译而言,“身体文学”的困难既在于译语词汇、句法的难以确定,也在于“身体写作”这一概念在文化与文化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构成的整个语义场中认识的难以统一[21]。波伏娃在其作品中常常直接或间接提及“性欲”(sexuality)一词,英语世界对于她的研究不断诉诸于其文本中的性描写及女性色情,并指出其在性的问题上有父权看法。在费拉德看来,这样的批评虽然不是全部来自于译文,但译文本身的确影响了波伏娃在英语中的接受。由于存在译者的“自我审查”(self-censorship)以及原语与目标语文化观念的差异,“身体写作”在文化间传递时会出现被遮蔽或被放大的现象。以《被遗弃的妇人》(La Femme Rompue)为例,主人公穆里埃尔(Murielle)在新年前夜的那段独白体例上颇似意识流,其间夹带了不少对于性的影射,整段文字既粗俗,又尖锐。穆里埃尔不断重复其想象中别人的性经历,以强化她对于性的厌恶。帕特里克·欧布赖恩(Patrick O’Brian)在翻译此段时不仅没有清理穆里埃尔的语言,反而通过扭曲它加强了原文的粗俗气。如将“leurs conneries”译为“all their balls”的做法一样,欧布赖恩通过语言的阳性化处理指涉了男性生殖器。在女性主义文学与翻译中,“身体”的书写与翻译非常重要,因为它可以反抗社会政治经济关系及父权叙述范畴对于女性的盘剥,甚至如尼采所说可以给予西方形而上学以毁灭性打击,因此也是后现代问题。
(五)文字游戏:女性主义翻译的语言痛楚
女性主义认为,规范的句法与既成文学体式折射并固化了父权式权力结构,而反句法特征的戏谑式文学手法则可以展现女性的“构造性欲望”。例如,朋·坎蒲(Penn Kemp)的《同声翻译》(Simultaneous Trans lation)一诗,虽然共计只有35行,但其中并置了大量同音位,且英语、法语夹杂,以描写女性的无能感,及其对此的抵触。该诗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方式,道出了父权制语言中的女性缄默与无法自表。坎蒲认为,父权制语言逾越了个体语言差异,将沉默追加于女性,并迫使她们为了表达自己而不得不“翻译”男性语言[1]14。为了解构传统语言句法与意义,重构音韵,坎蒲在吟咏上表现出强烈的口语化特质。
翻译这样的文字游戏要想既保持原文的词素音位与语用关系,又保持原文词汇形式是极其困难的。比较明智的选择乃是如同哈伍德翻译布隆萨德那样,有所取舍地保全译文。女性主义写作针对翻译提出的挑战既是技术上的,又是理论上的。译者在遭遇充斥着文字游戏的文本时,只能尽力所能及,提供具有最佳关联效果的创造性解决方式,以弥补语言之间的差异,以及译文效果与作者预期之间的距离。作为达丽的德语译者,威斯林克曾经痛心疾首,感叹译文的难以确定。例如,德语中用来指代“therapist”的乃是“Therapeut”,而“rapist”则对应于“vergewaltiger”。二者在“词素音位关系”上没有相似特征。同理,威斯林克将达丽用以指代飞船的“wound-tomb”译为“Mutterschop-Grabstatte”也只译出了表面意义,而没有传达音韵关系。达丽的文字游戏表现的“诺斯替主义”(Gnostic)特征对于历史、哲学与文学等均提出了挑战。就翻译而言,这样的文本其翻译难度可想而知。如威斯林克所说,达丽文本的生命力在于其文字游戏,但要翻译出它们困难重重,甚或不可能。费拉德在阅读了德译本与英语原本之后指出,德文读者从威斯林克译本中所获得的效果与原文相比已经南辕北辙。当然,威斯林克的译本中确有精彩译例。例如,在某处讲述太空探索的用词之上,达丽调侃了人类在技术面前的奴役状况,指出所谓太空旅行不过是受控于计算机的爬行而已[22]52。然而,当媒体报道这样的情况时,它却被掩盖在有关性爱的种种喻说之中。达丽将所谓“太空中的第一次国际对接”(first international docking in space)戏谑为“国际间的性爱行为”(an act of international intercourse),是一次“淫荡的连接”。在这其中,“美国飞船扮演着男性,或能动的角色……”它将自己(阳具般)的头部戳进了俄罗斯飞船[22]51。威斯林克在翻译这段话时采用了表示“dock”与“hook up”的“koppeln”,以及表示“match-making”的“kuppeln”二词。于是,“international docking”变成了“erste internationale Raumschiffkoppelung”,而“international intercourse” 则变成了“internationale[r] Kuppelei”。费拉德认为,尽管威斯林克并没有译出“intercourse”一词,但 “Kuppelei”一词效果更好,因为它正确传达了达丽文字游戏中的贬损语气。
女性主义文字游戏的处理有多种手段,如雅克琳·亨利提出的“三种方法”,即 traduction isomorphe、traduction homomorphe和traduction heteromorphe;有弗兰克·海伯特的另外“三种方法”,即基于“Inhalt”、“Technik”与“Stil”的不同取舍[23];还有德克·德拉巴斯蒂塔的“八分法”[24]。然而,无论译者采用何种翻译策略,译文要想保全原文的全部形式、语义和语用元素根本不可能。如德拉巴斯蒂塔所说,文字游戏的可译性最终还是只能取决于“文本方式”(textual means)与“文本功能”(textual functions)的区分。有时译者只能舍义取音,采用声音模仿技巧”(imitation phonetique)的翻译策略保留原文的“形态音位”与“句法”关系,而不是“词汇含义”。
(六)去“本质主义”:女性主义翻译的多样性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立足于后现代视角,销蚀了传统翻译理论的二元法则。如哥塔德所说,旧的二元观念消除了文化痕迹与反射自身的元素,剥夺了翻译的事件基础。为此,女性主义注重研究翻译中语言的性别角色与转换,如女性译者的历史与现代作用、翻译中阴阳两性语言的处理,以及作为涉及性别角色的女性主义翻译准则的确立等[6],并将翻译置于后现代主义各派系的整体框架之下,因而带有明显的反本质主义特征。过去30年间,性别研究转向了“女性拷问”(woman-interrogated),以及男同性恋与“同性恋方法”(queer approaches)的研究,这表明了性别概念的多变,以及翻译研究对此的灵活反应。20世纪6、70年代,妇女运动主要关注女性行为的刻板模式,规避女性差异,强调女性的共同经验。到了80年代,则开始研究并揭示女性在历史与跨文化中的差异。与此相适应,早期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主要致力于构建女性整体共有的、恒定的女性性别身份,即基于确定的性别差异。这一范式主要关注探寻翻译中女性作家遭到的曲解、女性译者的隐身,以及翻译理论与话语的父权特征如考德鲁、亚力山大与费拉德等对于英译波伏娃的分析批评,克里斯蒂娜·德·皮桑文本的早期英译本研究,16世纪女性译者的《圣经》第51首赞美诗的译本比较研究,以及匿名的英法圣教徒传记作家兼译者的作品研究等[25]54。
女性主义翻译观将女性看成在社会、文化、经济与政治等方面共享相似受迫情形的群体,这既拓展了性别差异范围,同时也拓展了翻译对于差异性的关注。这便是艾丽丝·帕克所说的翻译的多元性(polysexual)与多性别(multi-gendered)方法。费拉德认为,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多样化受益于女性主义研究思想上的新近变化,是一种策略上的转变。这种基于女性的身份政治、处境状态与历史维度的重新思考对于翻译学术的进度无疑作用巨大。
三、结语
综上所述,女性主义翻译观无疑具有鲜明的“后现代”特征,因为它与伊格尔顿对修辞学与历史的考察、托多罗夫对于批评的批评、伽达默尔对于真理与方法的“阐释”、福柯对于知识考古学的谱系分析,以及德里达对于书写的“文字学”研究及“撒播”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女性主义翻译的后现代特征既有其语言学、文学理论与文化思潮基础,也有其遥远的神学与哲学基础,如“神性放弃”、“雌雄同体”与“撒播”等。女性主义翻译观摆脱了传统的关于二元的“控制单位—反应单位”权力关系模式,包括男/女性、作者与原作/译者与译作等,使后者从父权构建的差异化与等级化概念,以及传统翻译研究所构建的“二元”确定性中解脱出来。女性主义翻译者在对象征父权的文学文本的解析中,采用的正是后现代主义的话语理论。他们希望通过“重写”、“干预”等策略来探寻父权文本中蕴含的权力关系与性别斗争,从而恢复总体化叙事压制之下的自主话语与知识,揭示其声音。虽然学界对女性主义翻译观存有不少批评与质疑,认为这一后现代话语理论过于偏激,批评女性主义翻译观“偏离甚至歪曲了翻译活动的本质”[26],“矫枉过正”[4],“太情绪化、太主观、太宗派化和理想化,因而不能成为真正的学术研究”[27],但是女性主义把我们从传统思维的藩篱中解放出来,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巨大的思考空间,这是值得肯定。
参考文献:
[1] FLOTOW,LUISE VON.Feminism in Translation: the Canadian Factor[J].Quaderns.Revista de traducció,2006,(13):19.
[2] SPIVAK G C.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M]∥in Michèle Barrett and Anne Phillips(ed.).Destabilizing Theory.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280-282.
[3] SIMON S.Translation and Gender: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Transmission[M].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96:15.
[4] 葛校琴.女性主义翻译之本质[J].外语研究,2003,(6):35-38.
[5] 蒋骁华.女性主义对翻译理论的影响[J].中国翻译,2004,(4): 10-15.
[6] 陈 琳.近十年加拿大翻译理论研究评介[J].中国翻译,2004,(2):68.
[7] GUATTARI F.The Postmodern Dead End[J].Flash Art,1986,May/June: 40-41.
[8] 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M].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99.
[9] DELPHY C.The Invention of French Feminism: An Essential Move[J].Yale French Studies,1995:190-221.
[10] 耿幼壮.书写的神话[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27.
[11] 费小平.翻译的政治-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D].四川大学,2004:91-101.
[12] FOUCAULT M.The History of Sexuality[M].New York: Vintage Books,1980:102.
[13] FLOTOW,LUISW VON.Genders and the Translated Text: Developments in “Transformance”[J].TextusⅫ,1999:275-288.
[14] BUTER J.Gender Trouble,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M].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1990:136-137.
[15] MAIER C,F Massardier-Kenney.Gender in/and Literary Translation[M]∥in M.Gaddis Rose(ed.).Translation Horizons Beyond the Boundaries of Translation Spectrum.New York: Centre for Research in Translation,Binghamton,1996:225-242.
[16] HARVEY K.Translating Camp Talk: Gay Identity and the Translated Text[J].Traduction,Terminologie,Redaction(TTR),2000:305.
[17] FLOTOW,LUISE VON.Mutual Pun-ishment? Feminist Wordplay in Translation: Mary Daly in German[M]∥in Dirk Delabastita (ed.).Traductio: Essays on Punning and Translation.Manchester:St.Jerome Publishing,1997:45-66.
[18] 刘军平.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研究的中西话语[J].中国翻译,2004,(4):7.
[19] 谢立中.现代性、后现代性社会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402.
[20] 李 德.法国后现代主流女性主义研究评述[J].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97-101.
[21] FLOTOW,LUISE VON.Translation and Gender: Translating in the ’Era of Feminism’[M].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18.
[22] DALY M.Gyn/Ecology.The Metaethics of Radical Feminism[M].Boston: Beacon Press,1978 (trans.by Erika Wisselinck as) Gyn/Okologie.Eine Meta-Ethik des radikalen Feminismus[M].Munchen:Frauenoffensive,1980.
[23] SCHUTTE K.Translating Puns in Feminist Writing[D].Utrecht University,2007:19-25.
[24] DELABASTITA.Introduction,Wordplay and Translation[J].Special Issue: The Translation,1996(2.2):127-139.
[25] WOGEN-BROWNE J.Wreaths of Time: the Female Translator in Anglo-Norman Hagiography[M].in R.Ellis and R.Evans(eds.).The Medieval Translator 4.Exeter: University of Exeter Press,1994:54.
[26] 张景华.女性主义对传统译论的颠覆及其局限性[J].中国翻译,2004,(4):20-25.
[27] 杨 柳.中国语境下的女性主义翻译研究[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7,(6):6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