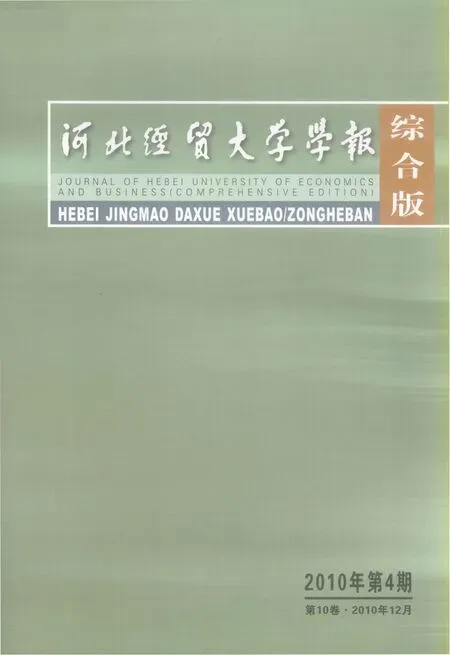试论传统情理法文化中的诗性思维
崔明石
(吉林大学 理论法学研究中心,长春 吉林 130012)
●法学研究
试论传统情理法文化中的诗性思维
崔明石
(吉林大学 理论法学研究中心,长春 吉林 130012)
诗性思维是理性启蒙前古代各国一种普遍的思维方式。诗性思维与传统情理法文化有着密切联系,这可以从案情的认识、法律的适用、案件的司法结果三个方面得到体现。
诗性思维;情理法;法律文化
马克斯·韦伯曾把不同的法律制度做了概念意义上的区分,形成了以形式主义和理性①与工具主义和非理性二元对立的划分。在韦伯看来,如果说西方法律是理性主义的话,那么中国法律就是非理性的,即所谓的“卡地”法。无疑,韦伯观点之诟病在于其无视一种文明在成长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复杂的情形以及归纳之特征略显类型化。与韦伯思考的进路不同,意大利哲学家维柯认为存在一种以感觉力和想象力的智慧表现形式的“诗性逻辑(logic of imagination)”。逻辑一词被冠之以“诗性”,乃是缘于这种逻辑是一种汇入了并充盈着鲜明而强烈的感性色彩和浪漫主义的想象性意蕴的逻辑。这种以想象力为基础,以诗为表现形式的智慧,维柯视为“诗性智慧(wisdom of imagination)”。
就诗性思维(智慧)的涵义而言,“维柯只是从多角度阐释了它的功能,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这或许意味着,它本身就是那种只能‘显现’而无法‘定义’的东西。”[1](P38)诗性思维源于对世界的感知,其内核即在于以己度物,“由于人类心灵的不确定性,每逢堕在无知的场合,人就把自己当作权衡一切事物的标准。”[2](P99)同时,这样的心灵还带来另外的特点,即“根据已熟悉的近在手边的事物去进行判断。”[2](P100)总而言之,诗性思维是一种对客观事物的认知意向,它存在于各种文化之中,同时也显现在政治、法律等各个层面。本文以维柯的诗性思维为理论进路来认识和思考以情理法为表征的传统法律文化,以此来拓展其研究的视野。
一、情感因素与价值衡量:诗性思维下的案件认识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合理模式可概括地表述为:发乎情,合于礼,成于乐。这是一种情理交融,以自然的情绪作为基础的思维方式。在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为内核的传统社会中,合情合理成为一个固定群体的共同意识(或常识)——“是一整个阶级、一整个人民集体、一整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所共有的不假思索的判断。”[2](P99)以文化的角度视之,这便是一个表征社会传统和思维内质的文化性状。继而对于司法判决可接受性以及立法的合理性而言,很自然地就表述为“揆之天理,合于人情”。
对于案件的认知和纠纷解决的结果,明人海瑞所见颇有代表性:“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乡宦计夺小民田产债轴,假契侵界威逼,无所不为。为富不仁,比比有之。故曰救弊。)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乡宦小民有贵贱之别,故曰存体。若乡宦擅作威福,打缚小民,又不可以存体论。)”②这即是说,假如事实之是非曲直无法查清而又不得不结案,便可以伦理之尊卑来决断;若兄弟相讼、叔侄相讼、官绅与小民相讼,则应依兄尊弟卑、叔(伯)尊侄卑、官绅尊小民卑的伦理原则来判决。作为一个包青天式的清官,对于案件的处理和认知都沁着“救弊”和“存体”的道德情怀与责任情怀,奉其为世范的其他执法者也要萧规曹随了!
《名公书判清明集》中曾记“女嫁已久而欲离亲”③一案。聂懿德之女阿聂嫁与胥吏王伯庆之子王显宗已十九年,王显宗破荡不检,屡遭刑罚。聂懿德以其玷辱家门,欲命其离婚,然而阿聂自称夫妇和睦并不愿离。但胡石壁并没有依据两造之词来断案,而是从一个名公的视角出发“推原事情”,认为案件存在以下几处疑点:一是阿聂不离王显宗,是否是追求“烈女”之名;二是根据“王伯庆逐子留妇”之供词,又恐阿聂不离婚是与王伯庆有瓜李之嫌。判决阿聂回父家,不许擅自改嫁,待王显宗改过后复为夫妇。对于案件的认识,仅凭两造之词就妄下结论似乎是不妥的;主观地对案件进行臆测(如:“烈女”和“瓜李之嫌”判断)也是古代法官所不能规避的。
概而言之,前述例证便是诗性思维在案件认识上的彰显。古代法官用糅合了理和义成分的人情来判断是与非、对与错,其标准和原则是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相结合的,因而也是可以因人、因事而异的。继而,以情理为核心的衡平观(法律正义)被打上了一种不具有实定性的个人“感觉”的烙印,因此用它作为衡量标准便具有某种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而减少模糊性的有效途径就是查明案件事实的“真相”,追溯纠纷发生的根源,体察一般人的感受与评价,使之与法官的价值判断相衔接。所以,在诉讼中,这样的“真相”不仅是法官作出裁判的根据,更是裁判获得当事人以及社会认同的基础。
二、诗性逻辑与移情就律:诗性思维下的法律适用
“玄学或形而上学与逻辑之分在于玄学观照各种事物的一切存在的形式,逻辑考虑到一切事物可能指的那一切形式。因此,我们……也把同样的诗当作诗性的逻辑来看,诗凭这种诗性逻辑来指明神的实体的意义。”[2](P197)在维柯看来诗性智慧和哲学是处于一个对极的二元,因而在逻辑的形成上也就引出不同的指向。形式逻辑是客观事物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下的某些最简单、最普遍的联系,是思维活动保持确定性、稳定性的根本保证;而诗性逻辑追求的是一种个人的感悟,是用感性意向感知的。
诗性的思维在情理法的语境下,彰显出传统的执法者在法律适用的过程中不注重形式逻辑的推理。有学人通过对清《刑案汇览》中随机抽样的案件进行分析梳理认为,清代官员在案件的论证中形式推理、论理解释、比附和实质推理所占的比例分别为36.7%,8.3%,41.7%,13.3%。④学者一般认为即使是在形式推理中都存在大量的主观价值判断,更遑论比附和实质推理了。从哲学的意义上看,林语堂认为逻辑适用与否的问题是和中国人对真理的认识密切相关的。[3](P75)由于缺乏西方的理性启蒙实践历史,因而古人认为逻辑推理上的真实客观上并不能保证结果的有效性。由此“中国古代法官睿智地发现,三段论操作之前,对大小前提的确定就不得不包含了价值判断。”⑤这里价值判断所依凭的虽然是以儒家理论整体为核心的伦理道德,但是不免落入个体性和主观性的窠臼,因而是诗性逻辑的一个显证。诚如贺卫方先生所指出的,“古代中国法官在判案过程中继承了儒家的天理人情高于逻辑差异的传统,从不‘专决于明而失人情’,明白地主张‘官司不当以法废恩’。”[4]
《刑案汇览》中有一个案件:李许氏因耕作忙,所备菜少,被姑叱骂;许氏之翁抱怨妻贪嘴,致其气忿自尽。刑部判“将李许氏比照‘子贫不能养赡致父母自缢’例满流”。⑥以今天的观点来看,在这一事件的因果关系中,致许氏之姑死亡的直接原因是死者丈夫的抱怨;许氏的过失充其量只是其诱因。但在刑部官员看来“百善孝为先”,由于儿媳的饮食不备有赡养不周之处,故在许氏的行为与其姑自尽二者之间建立了其认为足以自圆其说的逻辑关系。
诗性思维在法律的适用上一方面体现为法律逻辑的匮乏;另一方面则体现为移情就律。后者即是法官依据案件的情况、自身的价值判断等因素裁剪案件对可归责者进行酌情处罚。《刑案汇览》还有一案,杨氏与人通奸,其姑贺氏得知后令其母家管教,杨氏之兄反称贺氏诬蔑、意欲告官。贺氏遂气愤自尽。裁判者知“是王贺氏并非为伊媳犯奸轻生”,但仍欲对其处以严刑。按照清律,妇女与人通奸致使并未纵容之父母羞忿自尽,妇女拟绞立决;裁判者比照援引后予以移情就律,量减一等,判杖一百、流三千里,但仍依例实发驻防给兵丁为奴。⑦从此案来看,作为间接原因的通奸行为无论是对社会秩序的违反还是从法官个人情感上都具有可归责性,因而受到严厉惩罚。直接原因的制造者、杨氏之兄经案件的裁剪后反而未受到追究。
在传统情理法文化的语境下,法官“依法”断案并非如西方社会是以理性主义为核心的、以制度安排为保障、谋求整体公平的系统化的价值和制度为核心的审判模式,而是一种更多体现为法官个人的道义诉求,是以情理衡平为核心的审判模式。法律适用层面上的诗性逻辑以及移情就律,究其原因,学者梁治平认为道德化的法律不需要严密的逻辑结构,因为道德判断本身就不是根据逻辑得出的。[5](P335)法律和律学这种逻辑性和系统性的缺乏,给通过司法实现建构统一、整齐、协调的规范体系的目标带来了很大困难,但同时也扩大了司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从而为以诗性思维为特质的情理法文化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三、个案衡平与罚当其罪:诗性思维下的司法结果
诗性思维作为一种思维的方式专注于个别的事物。维柯认为:“诗性语句是凭情欲和恩爱的感触来造成的,至于哲学的语句却不同,是凭思索和推理来造成的,哲学语句愈升向共相,就愈接近真理;而诗性语句却愈掌握殊相(个别具体事物),就愈确凿可凭。”[2](P122)诗性思维在情理司法的语境下,作为执法者一方面是“公心如称”——执法者的内心确认成为衡平的前提;另一方面是缺乏对法律共相的抽象思维,本着罚当其罪的目的追求个案正义。
真德秀在《论州县官僚》一文中曰:“公事在官,是非有理,轻重有度,不可以己私而拂公理,亦不可骫公法以徇人情。诸葛公有言:吾心有秤,不能为人作轻重。此有位之士所当视以为法也。然人之情每以私胜公者,盖徇货贿则不能公,任喜怒则不能公,党亲戚,畏豪强,顾祸福,计利害,则皆不能公。殊不思是非之不可易者,天理也,轻重之不可逾者,国法也。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则逆乎天理矣!以轻为重,以重为轻,则违乎国法矣!居官临民,而逆天理,违国法,于心安乎?雷霆鬼神之诛,金科玉律之禁,其可忽乎?故愿同僚以公心持公道,而不汩于私情,不挠于私请,而无冤抑不平之叹。”⑧真德秀认为作为执法的官员在处理案件的时候应当在“天理”、“人情”、“国法”寻找一个衡平点,做到情法得宜。而其立论的出发点即为诸葛公所言之“吾心有秤”,这在实际的操作中体现在“诛心”与“酌情”。
《清明集》中有“诸定婚无故三年不成婚者听离”一案。此案女方时隔五年之后悔婚,无论是县断还是丞厅看定都欲劝以“择日完婚”。无奈两词争讼不已。此案陈监禀称时过三年未来成亲是因其为避寇而远走安吉州,似可排除法定解除婚约之“订婚无故三年不成婚者听离”之条。经查,女家听说其婿陈凯家道破落且“不学无文”,母之爱女心切遂背前盟,虽逾时三年的法定期限,但是其没有经法定的程序经官返还聘礼。同时,一个既成事实是欲聘之女魏荣姐已被女方嫁与他人;兼及陈监之词前后矛盾。故法官赵惟斋断曰:
以世契而缔姻好,本为夫妇百年之计,今乃争讼纷纭,彼此交恶,世契既已扫地,姻好何由得成?以法意论之,则已出三年之限,以人事言之,成毕之后,难保其往。今既各怀忿憾,已败前盟,初意何在?男女婚姻与其他不同,二家论诉,非一朝夕,倘强之合卺,祸端方始。今幸亲迎未成,去就甚轻,若不断之以法意,参之以人情,则日后必致仇怨愈深,紊烦不已。……所有聘礼当还男家,庶得两尽人情,可无词说。⑨
法官赵惟斋能够没有简单地适用“订婚无故三年不成婚者听离之条”的法定条件解除婚约,也没有如初审官员般强制婚姻成立,而是在综合了女已嫁人、陈家多年未娶等情况酌情判为:承认已成的事实婚姻前提下,并返还聘礼,使案件得到解决。
乾隆二十七年,曾有“裴秉若肆意殴逼妻妾仆婢,先后致死七命”一案。案中苏抚将裴秉若比照杀死缌功卑幼一家非死罪二人例,拟绞立决,具题。刑部认为:此等残暴之徒,淫凶不法实出情理之外,仅拟缳首,殊觉法轻情重,若驳令该拟又未免稽迟时日,转使凶徒藉以苟延。应将裴秉若改照光棍例,拟斩立决,迅即正法,以快人心,以昭炯戒。本案的拟断,非常典型地反映了清代法官的能动性以及道德情感在裁判中的法源性地位;同时考虑到犯罪动机恶性,强调了“诛心”原则。在中国人看来,犯罪是对秩序的破坏,因此当犯罪行为发生后,若要恢复自然的和谐状态,只能对该犯罪施以适当的惩罚——即所谓“罚当其罪”。但是,若对犯罪施以不适当的处罚,那么,其后果比不处罚还要糟。[6](P312)当应“诛心”之徒的行为,超乎了法官的感情承受能力,现有的法律规定出现应对的空白,或者严格地按照规则主义的法律审理无法实现个案的正义时,法官的法律解释本着“吾心如称”的原则,依据“情罪相当”或“原心定罪”的朴素正义感进行裁判,以达到情感与案件结果之间的衡平。在诸如此类的司法裁判中,执法者内心中的“情感意志”因素,如直觉预感、非理性的偏爱对于案件的结果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美国学者孙隆基认为:“人对客观世界的概念化是人的‘认知意向’与客观世界之间达成的一项协定。从不同观点出发的认知意向,就会与客观世界达成不同的协定。”[7](P1)以诗性思维为思维特质的执法者在案件的审理上力求做到“合情合理”。因而,由此获得的案件审判结果既不是基于法律规定的权利的恢复,也不是为了类似案件得到类似处理,更不是出于对社会制度的信赖;而是法官“吾心如称”之后的“原情定罪”,即体现的是裁判者个人对诉讼人的同情和对个案的特别处理。换言之,这样的审判意味着力图在处理每一个案件时都总是一次性地分别实现对于具体的当事人和个别的案情来说最为妥当的解决。[8](P124)
四、结语
诗性思维与传统情理法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这表现在法官的个人价值判断显露于案件的认识;形式逻辑的不足继而法官通过案情的裁剪而“移情就律”;司法的结果专注于罚当其罪,追求个案正义。无可否认,诗性思维这种思维特质是与主体的情感与良心价值衡量关涉的。但是,在人文或文化的语境中,“情感并不仅仅只是属于感性个体的东西,在情感中蛰伏着神性的东西。神性不过是对立物的尚未对立的统一,而情感作为直接的自我意识能够把一切对立物以之为基础的统一内在化。”[9](P72)从诗性思维的理论进路,我们可以发现传统的情理法文化为事实和规则之间矛盾冲突的解决提供了一个实践场域。诗性思维使得裁判者得以在法律刚性之外,寻求一种超越法律的正义。
注释:
①韦伯所称之的理性和非理性是在西方中心论的语境下的。在韦伯看来理性和非理性都是从法律条文到司法判决的推理过程。参见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78页注释7。
②《海瑞集》第117页,转引自【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57页。
③《名公书判清明集》,后文简称《清明集》,卷十,人伦门·夫妇,“女嫁已久而欲离亲”,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79-380页。
④⑤参见郑志华:《试论清代刑案裁判的正当性论证》,北大法律信息网,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_Detail. asp?ArticleID=24651,2010-08-22。
⑥《刑案汇览》(卷三十四),“姑嫌菜寡被翁抱怨致姑自尽”,第1251页。
⑦《续增刑案汇览》(卷九),“子妇犯奸氏兄护短逼姑自尽”,第227页。
⑧《清明集》(卷一),官吏门·申儆,“谕州县官僚”,第6页。
⑨《清明集》(卷九),户婚门·离婚,“诸定婚无故三年不成婚者听离”,第349-351页。
[1]刘士林.中国诗性文化[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
[2]【意】维柯.新科学[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3]林语堂.吾国与吾民[M].黄嘉德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4]贺卫方.中国古代司法判决的风格与精神——以宋代判决为基本依据兼与英国比较[J].中国社会科会,1990,(6).
[5]梁治平.寻找自然秩序中的和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6]【意】布迪,莫里斯.中华帝国的法律[M].朱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7]【意】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M].南宁:广西大学出版社,2007.
[8]【日】滋贺秀三,等.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和民事契约[M].王亚新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9]刘小枫.诗化哲学[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7:72.
On the Poetic Thought of Traditional Legal Culture
Cui Mingshi
Poetic thought was an universal method of thinking in the ancient countries before the Englightenment.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poetic thought in the traditional legal culture of the sentiment,reason and law from three aspects,that is the identification of case,the appliance of the law and the judicial sentence.
poetic thought;the sentiment,reason and law;legal culture;equality
D909.2
A
1673-1573(2010)04-0030-04
2010-08-29
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08Bfx13);吉林省教育厅“十一五”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吉教科文合字(2008)第39号]
崔明石(1977-),男,辽宁辽阳人,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2007级在读博士研究生,吉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法学理论和法律文化。
王岩云
责任校对:关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