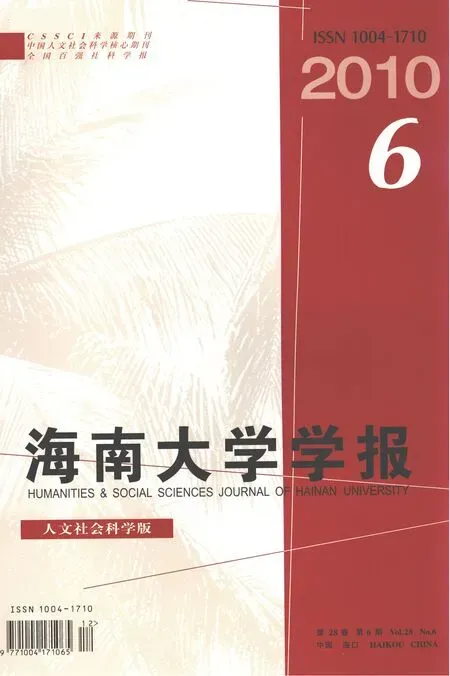关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说的界定问题
王馨
(深圳大学社会科学教研部,广东深圳 518060)
关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说的界定问题
王馨
(深圳大学社会科学教研部,广东深圳 518060)
柏拉图的政治思维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他所建构的是先验的理想国,而非经验的政治国家,所以他的政治学说可以被界定为理想化了的政治哲学;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是实践型的,他关注的是经验的政治国家,因而他的政治学说可以被框范为经验的政治(科)学。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说;先验的;经验的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西方哲学史在介绍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时,将它们分别简单地界定为德治、人治和法治,“以便”遵循黑格尔式的正、反与合的逻辑理路,并似乎由此就完成了“哲学史”的理论蕴涵。但是,思想本身的演进与人们希望的演进绝不是一回事,换言之,虽然可以将思想的演进按照一个比较合理的线索进行研究,但是有一个前提,思想本身首先必须是自在的,否则由众多思想片段所构成的只能是一个自我闭锁式的思想体系,也就是说,哲学史的研究不能以丧失哲学思想本身的活力为前提。在研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说时,这个问题就比较突出:能不能简单地用泛逻辑化的观点界定二人的政治学说?如果不能,怎样的界定才是比较合理的?
一、一种可能的界定:“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
(一)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雅典进入“三十僭主”专政时期,而柏拉图并未凭借母系亲戚关系中的大人物涉足政坛,他有自己的观察和判断。这个短命的政权只存在了8个月的时间。而之后代替僭主政权的便是民主政体,而恰恰是这个民主政体,将柏拉图的恩师苏格拉底判处死刑。所以,到柏拉图开始形成成熟的政治思维的时刻,他对民主政治的印象,几乎都是负面的。所以,在柏拉图75岁前后写的那封最著名的《第七封信》当中,他回忆道:“原先满怀热切渴望想要参与公众事务的我,在省思这一切并且看到周遭事物一一瓦解时,终于觉得头晕目眩了。……除非是让一批真正而纯粹的哲学家拥有政治上的权力,不然就是让拥有政治权力的人,借助神明的恩赐而成为真正的哲学家。这是我初次抵达意大利与西西里岛时,心中所持的信念。”[1]这是柏拉图18岁到40岁期间的真实的心灵写照。可能柏拉图自己都未料到,正是从“怎样才能建立一种合乎正义的城邦”这个问题出发,慢慢助他发现了成全他一生英名的理念论哲学。而这种理念论的哲学,又促使他进一步形成了完整的理想国的诸多构想。当然,这是后话。
目睹了种种不合理的政治体制之后,柏拉图将整个政治学说的出发点定义为要对现实秩序进行重新创建,而这种激进的变革方式决定了其对现实的扫荡一定是残酷的、不留情的。因为清理废墟是缓慢的,而且有可能死灰复燃,总不如完全建构一种新模式来得彻底。而对柏拉图而言,这一新的模式,即是将其最好的哲学与政治思想相统一,用以根除现实中的诸多不合理和不正义。但是,一旦准备将现实的政治置于先验的哲学之下,并且企图将二者做出“器”与“道”那样的截然二分式的定位,可能吗?
任何以意识形态为根本起点的学说都只是一种假设,这种从假设出发所建立的政治体系一旦在现世中运作失败,那么要否定的将不仅仅是政治本身,而且会牵连到与之相关的他物。柏拉图的理想国,就是沿着这一条必然途径而慢慢消逝的——原本试图从一个非现实界的、彼岸的理念出发(即从向善出发),途经“洞穴”(即人们迷惘于其中的表象世界),再经过“四线段”说(即依次通过印象、感觉、理智和辩证法),到达“太阳”下面(即见到真实的理念世界),看到远古的神(即建立完满的理想国)……但现实却向他展示了另外的图景:人们砸碎了原来的“洞穴”(即否定了原来的现实世界),却进入了一个更大的“洞穴”(即个人由于突然摆脱了束缚而又寻不到确定性时的茫然无所依的心态),而且连原来墙壁上的影子也看不到了,更无从说通向洞口的小路和“等候”在外面的“太阳”……人们没有办法按照柏拉图所言的途径去建设国家——为了控制人口,而去接受城邦的主动干预;或是为了废除私心和占有欲,而去“共子、共妻、共夫”,人为地废除家庭。换言之,正是由于柏拉图没有考虑到(或更确切地说是他不愿意考虑)现实,才令自己的政治学说带有明显的乌托邦性质,从而丧失了其在现实中得以存在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更为可惜的是,政治实践的失败也直接导致了后期柏拉图对自己哲学体系的深刻怀疑,于是才有对自己先期理念论的批判,其实对哲学体系的重建已势在必行,只是他已力不从心。柏拉图开始明显地妥协,于是才有后来《法律篇》中将法治国家作为“第二好的国家”的说法,这只是他为自己找出的一个体面的理由。“《法律篇》比柏拉图的任何其他作品,更直接涉及写成它的时代的政治生活,而且是预定满足一种紧迫感的需要的。”[2]
因此,柏拉图的政治学说是抽空了现实性的理想状态,只能被看作是理想化或理念化了的“先验的政治哲学”。
(二)较之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缺乏一种现实的紧迫性,再加之他对于历史的态度是前瞻式的,因此他可以更客观并且乐观地关注政治,从而也就具有更多地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可能性。
在总结何谓政治学时,亚里士多德说:“政治学术应考虑适合于不同公民团体的各种不同政体。最良好的政体不是一般现存城邦所可实现的,优良的立法家和真实的政治家不应一心想望绝对至善的政体,他还须注意到本邦现实条件而寻求同它相适应的最良好政体。……政治学术还应考虑,在某些假设的情况中,应以哪种政体为相宜;并研究这种政体怎样才能创制,在构成以后又怎样可使它垂于久远。……政治学术还应懂得最相宜于一般城邦政体的通用形式。政治学方面大多数的作家虽然在理论上各具某些卓见,但等到涉及有关应用(实践)的事项,却往往错误很多。我们不仅应该研究理想的最优良(模范)政体,也须研究可能实现的政体,而且由此更设想到最适合于一般城邦而又易于实行的政体。……有关政体的建议必须以当代的固有体系为张本而加上一些大家所乐于接受并易于实施的改变。”[3]176-177
在《雅典政制》和《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温和而细致地描述了雅典的历史和政治,它们被后人的诸多著作证实之后被应用于希腊研究的各个方面,作为解释那个时代的历史背景的确凿资料。这两部书涉及了希腊158个城邦的政体结构和政治得失,其中涵盖了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共和政体、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和民主政体,等等。虽然每种政体都有缺陷,但是综合考察后的结论不是推翻所有的统治形式,像柏拉图一样意图回归克洛诺斯神话时代,而是综合各个政体的优势,建构了一种“温和的民主制”,即寡头政治和民主政治的综合体,来作为他的政治设想,而且这个设想,是依据“乐于接受并易于实施”的尺度进行的。亚里士多德对理想的政治与现实的政治区分得很清楚,将政治学术与政治实践也区分得很清楚,他心目中的理想政制是梭伦式的,他称“世上如果出现这样一位人物,他既然善德优于别人,而且兢兢为善,没有人能够胜过他,只有遭逢这样的人,大家才可以永远追随并一致服从他,仍然不失为正义和优美的治道”[3]350。但由于雅典的现实情况所限,这只能作为一种理想存在,而“切实可行的理想”应该是共和政体(寡头政治与民主政治的混合物),在共和政体下,统治资格不是具有高度文明的美德,而是中产阶级坚定的军事美德。之所以得出“共和政体”最可取的结论,其考量是多方面的:人们由于财产多寡引起的纷争是致使雅典不稳定的主要因素,因此最富的人与最穷的人都不应该执政,中产阶级是最适合的掌权人;政府的动机是区分正确政体与错误体制的主要依据,只有以公共利益为目标的政府才是真正的政府,而城邦的公共利益就是要同时考虑财富与最大多数人的同意,因此,将财产与人数结合起来的政体——共和政体才是最好的政体,等等。他尤其不赞成柏拉图的共妻儿的说法,并且对于这种非所有的所有权进行了驳斥,他甚至得出一个结论:在每一个儿子可能将有千百个父亲的情况下,做一个真正的表兄弟比做一个柏拉图式的儿子要好很多!
总之,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是实践型的,是在可被操作的情况下做出的最优选择,他关注的是经验的政治国家,他的政治思维可以被界定为“经验的政治科学”。
二、可被预期的分道扬镳:人是手段,还是目的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最初对于最好的政体的设定,都来自于一个共同的前提:即实现“善”。但是,正是在实现“善”的过程当中,两人几乎触碰到了康德的命题:人,到底是目的,还是手段?
(一)正如上文所言,柏拉图对于抽空了现实性的理想状态的偏爱,使得他对政治做了应然的设定,这就导致了他同时模糊了以伦理道德等为对象的价值世界和以客观事实为依托的经验世界,并不可避免地将经验与先验相混淆。
首先,柏拉图设定了一个美好政体的先验的逻辑基础,即“善”的理念。
在柏拉图苦心经营的理想国中,“善”的理念是指导一切的,因为它位于彼岸,完满而永恒,不会像现实中的事物一样瞬息变幻。同时在理念世界中,等级又是分明的,所以以它为范型所建立的理想国中的等级秩序就有了学理上的依据。更重要的是,理念是神所创造的惟一的存在,遵循它,也就等于遵从了神的意志。
基于上述考虑,柏拉图创建了他的理念王国。在柏拉图看来,最好的“理念”当然是“善”,以享有“善”的多少为依据又产生了理念王国中的各个等级。但是不管处于哪一个等级,他们的目标又始终指向上一个等级,并最终指向“善”。从这个意义上说,别的理念与“善”的理念的关系,与其说是部分与整体之关系,毋宁说是手段与目的之关系。
其次,将“理念”在“国家”的大目标下重新进行解读,换言之,在理念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寻求一座桥梁,使得此岸与彼岸的沟通成为可能。
按照上面的说法,人们依照理念王国的样子就可以建构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国家,问题是,理念王国虽好,但是能洞察彼岸理念的人是稀少的,因为彼岸的遥远决定了通向它的路途上必定坎坷无穷,这种坎坷,就是“欲望”,是凡人不能超越的所在。换言之,只有超越了这种欲望的纠缠,才有洞察彼岸理念世界之可能。于是,“教育”在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地位至关重要,但是即使通过严格的教育,由于人之先天素质及领悟力的不同,也不可能在获取智慧方面收到同等的效果。哲学王是经过层层筛选才产生出来的,他是权力与理念的完美结合,他位于一切人之上,他的智慧与权力“不是神的,也似是神的”[4],他是现世的神。而理想的国家,必然需要一位“神”一样的人物进行统治,因为只有他的先觉才可能预先设定好理想的国家模式,才能带领大家一同启程,并将大家带到那个距离彼岸的无限美好的理念王国最近的所在。确切地说,“哲学王”就是那座使得此岸与彼岸的沟通成为可能的桥梁。于是在这里,柏拉图又偷渡了政治学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即将目的解释为手段——将先验的理念王国偷换成了经验的政治世界,并同时将政治世界简单地等同为“谁来统治”,“WHAT”简单地替换成了“WHO”。这个替换,开启了西方后来的“人治”或“神治”传统的先河,千余年的基督教哲学统治下的中世纪是最好的说明。后世的学者就是以柏拉图的学说为起始点,对“人治”或“神治”提供了各式各样的学理上的论证。在他们看来,对政治的终极意义的思考所得出的结论就是:人们需要一种外在的、施加于他们的同一的力量,以使得目的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
再次,在此岸建成彼岸的世界,完成权力的完全让渡。柏拉图引导大家走的是一条不归路。
从上述论证可以看出,柏拉图从“善”的理念出发,经过政治需要的淘洗,建构了一座桥,通过这座桥,将彼岸世界拉回到了此岸。但是要清楚,柏拉图这样做的目的,并没有远离他的主旨,而只是缩短了“距离”,使先验的世界与经验的世界在现世中得到了统一,换言之,使伦理道德与政治行为在人身上得到了统一,使人在政治操作过程中实践伦理。然而由于人们不可能把握住伦理与政治的关系,于是不可避免地要在庞大的共同体前迷失自己,为防止这种断裂,公民要有如臣民,完全服从哲学王,因为哲学王是现世的神,拥有至高的权力与完满的道德,而且也只有通过他,人才能找到通向彼岸世界的路。而这种“服从”,是全方位的,是将权力的完全让渡。于是,与产生“哲学王”的方式一样,柏拉图又简化了程序,将原来的“谁来统治”过渡到了“如何统治”,这是又一次巧妙的偷渡,将“WHO”替换为“WHO AND HOW”。这个程序,又开启了西方集权主义的先河,对德、法的政治思维模式产生了很大影响,即在人治或神治的基础上,实现权力的完全转移。
但是在这些问题之前,有一个大前提是务必要注意到的,那就是,人的出发点与哲学王或神的出发点是一致的,都是“向善”。也正因如此,人才会对王或神有认同的可能,人才会心甘情愿地让渡自己的权利。在这里,人几乎不考虑相互之间的倾轧的可能,也不考虑人神之间可能出现的矛盾,即不具有后来社会契约论者的那种防范思维——防范社会与国家之间的混淆——于是权力才具有不可分性,而只有让渡的可能。柏拉图相信经过教育的人是好的,是善的,他相信道德万能,所以有人称柏拉图具有“道德理性”。一个相信“道德理性”万能的人的出发点也许是好的,是出于拯救的目的,但是一旦这个前提成立,那么剥夺他人权利就有了合理的理由,个人对共同体或共同体的化身就有完全服从的义务,人之反抗就是犯罪。人又一次沦为工具,消逝在庞大的共同体或共同体的化身之下。
(二)与最初的柏拉图相似,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伦理、政治思维很多时候也是混杂在一起的,他的哲学对于伦理学、政治学也具有铺垫和指导作用。可以说,亚里士多德之所以没有如柏拉图一样建立自己的先验理想国,没有肯认柏拉图的理想国的思想模式,也是因为他对于后者的理论基础——“理念”哲学没有加以完全地肯认。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理念”虽然是优越于实体的,但不是脱离于实体的纯粹的存在,他指出理念论的根本错误在于既将理念当作普遍的东西,同时又把它们看作是可以分离的、单独的个体,因此在建立自己的“形式质料说”时,将形式与质料视为是不可分的,形式只是在逻辑上优先于质料,质料是在现实中逐渐被实现的所在,是渐次接近于完满的形式的。在这个哲学的基础上,亚里士多德将潜能与现实的关系等同于质料与形式的关系,认为潜能是尚未实现的现实,现实是实现了的潜能,运动也就意味着事物由潜能的存在向现实的存在的转化。这是受到苏格拉底思想影响的自然目的论,也是亚里士多德实践其政治抱负的思想轨迹。换言之,亚里士多德也将政治看作是形式获得质料的过程和从潜能到现实的过程,他关注的是自己的政治愿望在现实中获得实现的可能性,因此他是基于实践的目的来操作其政治愿望的。
所以,单单就潜能获得实现这个角度而言,诚如黑格尔所说:如果理想主义是一种力量,它首先是追求现实中的理想因素,其次才是粉碎现实以期望在其他地方发现理想,那么,比起亚里士多德来,柏拉图还“不够理想”[6]。
同时,亚里士多德很自然地将伦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都置于“实用学”的目标之下,因为这三个学科类别全部都指向一个初始命题:“善”,即指向美好的生活、人类的幸福以及可能性的最好的秩序,等等。正因为如此,亚里士多德在论述政治的时候一直围绕着每个主体应该具有的政治责任而展开,没有哲学王,没有断裂,也没有拯救,所以,也就刚好避开了集权主义的诱惑。
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身后的世界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身后的两千多年中,世界政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西方世界也在古希腊自由民主的基调下辗转反复,演绎着其继承、批判、再反思的历史。
信奉柏拉图的人坚信政治生活和国家目的是追求终极的善。他们通常相信人的理性是万能的,他们对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抱有绝对的信心,相信通过人的不断的努力,可以使世界趋于至善。凡是恶的东西,无论这种恶来自于社会还是来自于个人,都应该将其铲除干净。大凡是具有这种政治观的思想家都赞成一种“圣贤统治”,人民缺乏政治参与的可能性,一切由国家以“至善”的目的去组合和排列。这种对“至善”的政治理想的追求很容易导致用目的的正当性证明手段的正当,甚至导致以目的的善为手段的恶做开脱。赞成这种政治观的思想家或者极力推崇现实的宗教,或者“一方面积极废弃传统的宗教,一方面试图把现代世俗社会再神圣化”[6]。后世的奥古斯丁和卢梭,就分别发展了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和道德理性万能的思想,他们都是柏拉图的拥趸。
同时,柏拉图也是这个世界的清醒剂。他用“理念”这个词,时刻提醒人们:超验的东西不可或缺。如果心中没有它,人们就不可能在向下投入现实世界时,依然保持着热忱与纯洁。
而亚里士多德这种谨慎地对待现实中的不合理因素,注重从社会已有的状况中发现解决问题的办法的做法,使人们不再相信人类的心智可以达到无所不能的地步,人们开始注意到跟人性相关的现实中的恶,时刻为一种“幽暗意识”所笼罩。他们尊崇宗教的至高地位,相信人在上帝面前都是渺小的(正是这一点说明了人与人的平等),人没有觊觎上帝地位的必要和可能,人只在上帝的关爱下做好人间的事情,他们不期望在人间建造天堂。人性的恶(表现为自私与贪婪)在政治领域中的表现即是对权力的无限制的追求,而人的本性又决定了权力必将导致腐败,因此制度上的防范才是必要的。这种政治观尊重法律,尊重人的自由选择的权利,不要求个人为共同体的目的而放弃自己的理想,共同体大都具有“工具”性质,所以在这样的社会中至少不会出现个人理想与国家理想双重失落的悲剧。尊奉这种政治观的社会大都选取“民主共和制度”作为它们的政制,一方面允许公民自由施展自己的抱负,另一方面又用法律和制度来保障每个人享有不受别人侵犯的权利,这两方面的结合使民主社会同时收获了公平与效率。继亚里士多德之后,西塞罗、托马斯·阿奎那、马基雅维里、洛克、孟德斯鸠、麦迪逊、J·边沁、詹姆斯·密尔等人都可以归为这类,而且可以看到,这类的思想家在近现代密度很大,他们对于近现代国家的政治建构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1]傅佩荣.柏拉图[M].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9:4.
[2]A·E·泰勒.柏拉图——生平及其著作[M].谢随知,苗力田,徐鹏,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658.
[3]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彭寿,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4]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310.
[5]W·D·罗斯.亚里士多德[M].王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70.
[6]刘军宁.善恶两种政治观与国家能力[J].读书,1994(5):56-63.
On the Definition of Plato’s and Aristotle’s Political Theories
WANG Xin
(Social Science Teaching and Research Section,Shenzhen University,Shenzhen 518060,China)
Plato’s political thoughts constituted a completely logical system.What he established was a transcendental ideal country,not an empirical and political state,so his political theory can be defined as“ideal political philosophy”.While,Aristotle’s political idea was practical.What he paid close attention to was an empirical political state,thus his political theory can be defined as“empirical political science”.
Plato;Aristotle;politics;transcendental;empirical
B 502.232;D 091.2
A
1004-1710(2010)06-0037-05
2010-08-12
深圳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09QNCG40)
王馨(1975-),女,黑龙江齐齐哈尔人,深圳大学社会科学教研部讲师,主要从事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研究。
[责任编辑:张文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