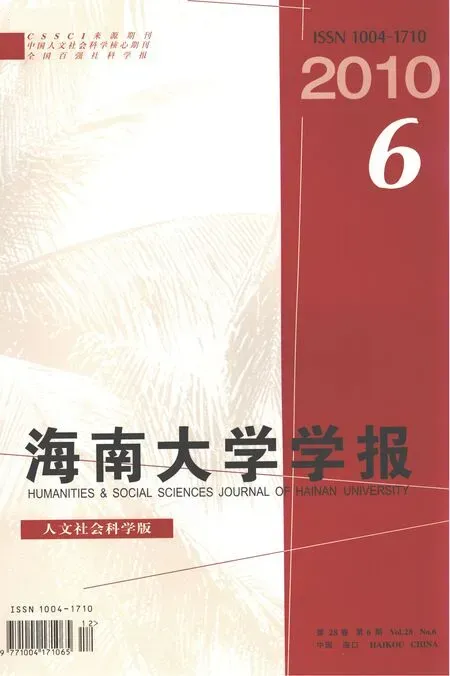第俄提玛的最高爱欲教诲——柏拉图《会饮》210a-212c释义
唐敏
(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海南海口 570228)
第俄提玛的最高爱欲教诲
——柏拉图《会饮》210a-212c释义
唐敏
(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海南海口 570228)
重点读解柏拉图《会饮》中第俄提玛的最高爱欲秘传,试图追索施特劳斯反省西方现代性危机的思想历程。近代政治哲人马基雅维利抛弃了哲人的最高的爱欲教诲,认为人之中的最高乃是现世功业,是对不朽荣耀的爱。这在一定程度上标示着古今断裂,呈现了事关哲人品质的古今之争。
爱欲;哲学;诗;马基雅维利
1959年秋季,施特劳斯在大学课堂逐字逐句地讲解柏拉图的《会饮》。其时,施特劳斯刚刚完成自己的重要论著《思索马基雅维利》,重新准确细致地勘定了古代与现代的裂口。在《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一书的美洲再版前言中,施特劳斯交待了自己找寻古代与现代断裂之处的思想转变历程,寻觅、诊断到了古代与现代的脱节点。施特劳斯一边追溯马基雅维利丢失的东西(苏格拉底式的古典理性),一边研习中古哲学,从启示与理性之间的张力来理解哲学。他因此获得了一条线索,这条线索从阿威罗伊、迈蒙尼德、阿尔法拉比直通柏拉图,这样回溯古典理性就具备了一种更加坚实的力量。
并非偶然,也是1958年,施特劳斯在芝加哥大学公开讲授“政治学问的起源和苏格拉底问题”。在第六讲中,施特劳斯告诉人们:“将古典政治哲学与现代政治哲学所呈现的哲学选择对峙起来”固然重要,但人们还是要像古人理解自己那样理解古人,也就是把研究“限制在关于古典政治哲学的性质和主张的问题上,限制在它试图解决的问题上,限制在它试图克服的阻碍上”。至于问题和阻碍,施特劳斯说,就体现在阿里斯托芬描写的那个苏格拉底身上。哲学最大的对手是诗,哲学必须面对诗的批判,夯实自己的基石。阿里斯托芬的苏格拉底是非爱欲和非缪斯的。而《会饮》中的哲人苏格拉底一方面在诗人面前大谈爱欲;一方面向在场的喜剧诗人和悲剧诗人宣称,同一个人可以既擅长喜剧又擅长悲剧。据伯纳德特说,施特劳斯讲授《会饮》前(以及讲授期间)一直在与友人阅读讨论《会饮》。施特劳斯在审理马基雅维利之时(或之后),用力于柏拉图的《会饮》也许不是偶然。在《思索马基雅维利》的引言开头,现代社会科学家们为了给马基雅维利的坏名声做辩护,认为他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针对这种说法,施特劳斯巧妙地援引了《会饮》中阿里斯托芬的“对自身的爱”。爱国主义是一种对自身的爱,这种对自身的爱,“在品第等级上低于既对自我又对道德上的善所怀有的爱”[1]1-4。在讲解苏格拉底讲辞中的爱欲最高秘传前,施特劳斯提到了马基雅维利,并指明了马基雅维利到底在何处背离了古典理性传统,以及背离了怎样的古典理性传统。由此看来,阅读《会饮》关系到古今断裂的厘定和古典哲学自身面貌的呈现。
一、爱欲秘传
爱欲的最高教诲处于苏格拉底的讲辞忆述的末尾。苏格拉底“讲辞”先谈及爱欲的自然,再讲述爱欲的作为或者说对人的好处(201e,204c)。爱欲乃是欲求自己永远拥有好的东西(206a),方法就是通过在美中生育,达至不朽。这表现在父母生育子女,工匠制作什物,立法者奠定城邦和建立法度,诗人创作曼妙的诗篇,永世流传(208c-209e)。第俄提玛讲述完诗人达到不朽的方式,接下来就表述哲人的方式①苏格拉底公开爱欲秘传影射亵渎厄洛西斯宗教秘仪事件和雅典西西里远征。据说,西西里远征时,爱欲扑向整个雅典。柏拉图似乎暗示西西里远征是雅典爱欲欲求建立帝国(政制)达到不朽,但此时雅典却并不知晓爱欲的最高秘密,哲人却已知道,还在会饮场合公开。,这便是爱欲的最高奥秘。至此人们才明白过来,第俄提玛一步一步走着上升的路。而要抵达顶点,就得净化此前讲述的爱欲类型,才能揭示最高的爱欲——导向至善②意味着仅仅谈爱欲善好不够,蝇头小利也是善好。从某方面说,现代性的表征恰恰是至善逐步降解为技术欲望和私利。。在之前第俄提玛大谈诗人留下诗篇或生育美德以达到名声不朽,而在哲学这里最主要的是沉思而不是生育。第俄提玛一派智慧满满的样子,打算对苏格拉底倾囊相授“最终的、最高妙的奥秘”。她提醒苏格拉底尽力跟随她指引的道路,能领悟多少,全凭热爱智慧的苏格拉底自身了。在这一阶段,美占据了最高教诲的中心,于是看(凝视)就成了爱欲秘传中显露的主要特征,爱人不断掉转看的对象成了描述的重点。首先,起点是向往美的身体,男童恋只是上升的起点,上升即离弃;接着是撇下单个美的身体,向往所有美的身体。接下来,从身体转向灵魂。不再在意这情人身体是否丑陋,而是关注灵魂的美,并通过言辞来孕育美,进而关注在操持和诺谟斯中的美。承接而来,是看到知识的美,到达这个地步,身体、行为的美就不算什么了,而准备迎接最终的目的地。最后上升的顶点,会突然瞥见美本身,这美呈现为“自体自根、自存自在、永恒地与自身为一”(211b)。此时才明白过来其他美的东西跟它相比衬,只是分有了美本身。第俄提玛对苏格拉底说,生命若到了这一境地,这个终点,人们才明晓生活的意义,才知道何为值得过的生活。人真正的幸福就是瞥见美本身,与之融为一体(212a)。触及真实遂能生育真实的美德,诗人的爱欲生育由于不能瞥见美本身,就只能产生美德的影像。
第俄提玛关于爱欲的最高教育最终消除了爱欲。在最初几步爱欲阶梯里,爱欲还紧紧凝视情人身体的美,也还可以与情人依偎在一起。可一旦离弃情人的身体,转向操持和诺谟斯、知识中的美之后,爱欲就只剩下凝视,没有可供依靠的形体了,爱欲也就不成其为爱欲了。第俄提玛说,哲人瞥见美本身,与之融为一体,不可思议(全能的神?),消除了爱欲的两重性即凝视和在一起之间的差别。因为既瞥见美,就意味着哲人与美本身有距离,而又要与之融为一体,意为距离的消弭,两者不可能同时发生,爱欲土崩瓦解。
第俄提玛的最高秘传或多或少地掺杂了两位诗人对爱欲的一些理解,同时也拒斥着他们的某些理解。一方面从一个美的身体转向两个美的身体,再转到所有美的身体,这也构成了最初一系列的爬升(211c)。爱欲确实表现为不断的欲求,不断调转欲求的对象,就对爱欲的欲求来看,这里涵括了阿里斯托芬对爱欲的理解。只是这种欲求不是寻求自身,而是努力克服自身的卑琐寻求超越于自身的东西——美。
另一方面,美成了第俄提玛的最高爱欲描述中每一环节的扭结点,这和诗人阿伽通的爱欲是对美的热爱一脉相承。但他们的区别也很明显,第俄提玛设立了一种美本身,以美本身取代了阿伽通尽善尽美的爱神,它成了哲人不断努力向其回溯的顶点,而美在阿伽通那里只是表现在诗艺制作的诗篇中,在第俄提玛看来,这只不过是美的东西而已(211b)。在爱欲上升的最后的几个阶段,先看操持和诺谟斯中的美、知识中的美以至最后瞥见美本身(211c),爱欲主要变成了凝视(沉思)。当阿伽通谈到爱神的智慧时,爱若斯的智慧是一种创生,这也是诗人的智慧——制作。诗人留给世人美丽的诗篇,还创造了永活的诸神以及创典立法。通过这些美的创造,诗人之名长久留传,诗人关心自己的不朽。第俄提玛描述哲人懂得什么样的生活最值得过,那就是努力瞥见美本身,与之融为一体,哲人并不生育,生育是为了延续有死的生命,哲人并不是为了自己不死,瞥见整全融为一体意味着个人自己的消寂。
为何最后的教导以“美”为枢纽作为爱欲上升的阶梯呢?在施特劳斯看来,以美为教导的枢纽,这在《会饮》中表征着对哲学诗歌式的描绘[2]236-238。哲人苏格拉底面对着两位诗人,引入美作为生育的中介(206a-207b),结合了阿里斯托芬的“爱我们自己”、阿伽通的“爱美”和哲学的“爱善”,先哲学地展示了诗歌,阿里斯托芬忽视了美和善,而阿伽通则混淆了美和善,揭示了诗人爱欲生育中的美和善的区分(诗歌的美和名声不朽的善),但在哲学发现(区别于诗人的创造)的整全等级秩序中,诗人的美只是个别的,诗人的善归根到底不过是城邦视野里的善好。在爱欲最高阶段,哲人抽离了“爱我们自己”,结合“爱美”和“爱善”,并把瞥见美本身直接等同于善,诗歌式地展示了哲学。
二、古今争执
初看之下,第俄提玛爱欲的最高教诲似乎清楚明白,但倘若切问近思,就觉得其大有名堂。在讲解总结上一部分时,施特劳斯提到了马基雅维利,他是这样引入的:
在柏拉图很久以后,试图理解整全的人(the whole man),亦即整个政治生活(the whole political life),是从这个第二部分的角度来理解人的,也就是假设人之中最高的乃是他对不朽名声的爱(the highest in man is his love of immortal fame)。这就是马基雅维利。为了描述马基雅维利和柏拉图的关系,人们可以简单地说,倘若他们都在这里(就指上一部分)止步,他俩会达成一致。但是随之而来的某些东西(something)被马基雅维利丢掉了。[2]230
在这里止步,这里是指诗人制作作品,通过作品葆有名声,诗人的爱欲是对自己不朽名声的爱。立法者则孕育政制、法律和政治美德。诗人和立法者相继提及,并且两者之间的承接处有一个让步含义的表达,“再不,要是你愿意的话”(209d),暗示诗人比立法者更高[2]229。他们各自的作品也显示了两者的高下,荷马的史诗至今流传,而梭伦的雅典早已湮灭。在这个意义上,诗歌的爱欲成了哲学之前的最高表达。诗歌爱欲也可以为了自己的(荣耀)不朽创立政治基业,孕育政治德性,教育政治家和立法者。施特劳斯说,人之中的最高乃是对不朽名声的爱,这是马基雅维利对整个人和政治事务的理解。马基雅维利就此止步,但柏拉图还要继续往上攀升,这就是第俄提玛爱欲的最高教诲。施特劳斯说,马基雅维利把这个最高教诲丢掉了。在马基雅维利那里,人之中最高的东西是对不朽名声的爱。在柏拉图这里,第俄提玛的爱欲教诲才是最高的,这也就是说,马基雅维利把人之中最高的东西降低了。最高教诲谈的是哲人的方式,那么把对人之中的最高理解降低,也就是将哲人这类人打发掉了,或者说把苏格拉底式的古典哲人败坏了。首先,笔者简略地谈论马基雅维利对哲学和爱欲的看法。
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是呈献给在位君主的邀宠之作,主要谈论“君主政务”[3]1-2。《君主论》大致可以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第一章到第十二章)主要讨论君主国的种类和特性,盛衰原因,夺取和保持的权谋。第二部分(第十二章到第十四章)主要讨论君主的军事事务和责任。第三部分(第十五章到第二十三章)谈论君主及其盟友。最后部分(第二十四章到第二十六章)讨论一个古老的话题——机运[1]67。在第二部分的开头(也即第十二章),马基雅维利将君主国的基础置于军队和法律之上,并认为相比法律,良好的军队更为重要,随之避而不谈法律问题,而只谈“军队问题”[3]57。接下来的第十四章标题是“君主关于军事方面的责任”。马基雅维利直接将君主等同于军事首领,认为这事关国家的兴亡。稍微一比较就知道,马基雅维利篡改了柏拉图《理想国》中哲人—王的隐晦教导。为王者只要精于战争技艺,而无须进行哲学操练,至此他对哲学只字不提。马基雅维利接着谈论了君主进行军事训练的两种方法,其一就是采取行动,其二是靠思考。采取行动就是长期不间断地进行狩猎,增强体魄;观察君主国的地理环境[3]70。在这里,马基雅维利列举一个阿凯亚人的君主菲利波门的例子,隐晦地谈到了哲学,即菲利波门与他的朋友们在乡村的和平时节里,清闲地交谈。但跟柏拉图的苏格拉底与人闲暇交谈的内容却大为不同。菲利波门和朋友谈论的是在特殊地形下军队的进攻防守之道。苏格拉底则与人谈论正义、美和善的问题。在《君主论》中,哲学也就是对军事问题的自由谈论。由此,可以简单地看出哲学品质的转变。关于第二种方法——思考,也完全脱离了古典哲学沉思静观的理解,而仅仅作为一种对古代伟大政治军事人物的模仿。马基雅维利谈到了色诺芬的居鲁士,并提到了西奇比奥的成功与他对居鲁士的效仿有着莫大关系。但马基雅维利却绝口不提色诺芬的另外一个主人公——哲人苏格拉底[1]466。在第十五章,马基雅维利首次比较公开地宣告了与传统的决裂。他说他的写作意在对人们产生效用,因此他谈论事物“在实际上的真实情况”,而不是事物的“想像方面”。
许多人曾经幻想那些从来没有人见过或者知道在实际上存在过的共和国和君主国。可是人们实际上怎样生活同人们应当怎样生活,其距离是如此之大,以致一个人要是为了应该怎样办而把实际上是怎么回事置诸脑后,那么他不但不能保存自己,反而会导致自我毁灭。[3]73
马基雅维利明确地将其论说定位于现世处境、实际情况及人们在这个实际情况下怎样生活。哲人苏格拉底之死就是这种“自我毁灭”的典型。第十五章的标题是“论世人特别是君主受到赞扬或者受到责难的原因”。在现实的世人中,君主处于最高序列。而君主在实际情况下的谋略算计,最后只是为自己赢得不朽的功业和荣耀。这即是马基雅维利的最高爱欲表达。
有关爱欲的最高教诲到底描绘了怎样的哲人?第俄提玛在讲完诗人的爱欲之后,传授的就是哲人的爱欲。这个关于哲人爱欲的教诲核心是什么?爱欲的最高教诲哲人试图达到的最终目标是瞥见美本身和生育真实的美德。第俄提玛说瞥见美,也就意味着知道了何种生活是值得过的(211d),言下之意是瞥见美本身之前,哲人知道应该如何生活,即让美成为爱智(慧)生活的引导,向美欲求[4]。诗人、立法者(政治家)的爱欲理解是欲求个人荣耀的不朽,指向现实该如何生活。据施特劳斯说,这就是马基雅维利开辟的新道路,丢弃询问人应该如何生活,降低转向人们在现实中如何生活[3]73。这个转变的直接后果就是对德性的重新解释。德性不再是“国家为之而存在的东西”,相反,是“为了国家的缘故才存在”[5]。在《理想国》中(368D-E),苏格拉底为了看清灵魂中小写的正义,尝试着建立言辞城邦以便先弄清大写的正义,然后由大见小。第一个言辞城邦被格劳孔称为“猪的城邦”,是因为这个城邦纯粹是为了身体需要构建起来的,人们互帮互助,自给自足,天真纯朴,还没有出现统治。由于格劳孔的激忿不满,遂转到第二个言辞城邦“高烧的城邦”,遂出现了战争与护卫者阶层,相应地对于统治的需要也出现了,德性才产生。这种德性是为了城邦共同体的保存和发展,是城邦范围内的德性。在古典哲学视野里,还有另外的德性,即哲人的德性,它基于哲人灵魂的智慧追求,超越于城邦所划定的界限之上。这正应合着第俄提玛的描述,哲人瞥见美,触及真实而生育真实的美德(212a),而立法者和政治家产生的只不过是德性的影像——政治德性(209a)。马基雅维利把哲人败坏是否可以说就是把真正的哲人德性抹去了[6]。当施特劳斯讲到为何要讲解柏拉图《会饮》时谈到,阅读《会饮》意在努力试图理解人类事务(政治事务)的自然基础。而在柏拉图看来,这个自然基础正是爱欲(eros)[2]10-11。根据第俄提玛描述的爱欲最后图景,爱欲促使着人在自然的等级秩序上不断攀升,朝向整全。这就是古典的自然世界。对马基雅维利来说,这恐怕也早已逝去[5]。
三、结语
马基雅维利是现代政治哲学的肇始人,对马基雅维利的清算关系到人们重新看待理解现今的世界图景和危机。他将政治从哲学或“人类的最高德行”的审查和限制下分立出来,成为一个“依自为的目的”,根据“自身的法则”运作的独立领域[7]。他将最高的爱欲视作对不朽名声的爱正跟他精心的哲学现代性筹划一脉相承。
[1]列奥·施特劳斯.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思考[M].申彤,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2]STRAUSS L.On Plato’s Symposium[M].Chicago﹠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1.
[3]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君主论[M].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4]柏拉图.会饮[M].刘小枫,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93.
[5]列奥·施特劳斯.现代性的三次浪潮[M]∥刘小枫.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施特劳斯演讲与论文集:卷2.丁耘,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32-46.
[6]刘小枫.施特劳斯如何读马基雅维利[M]∥贾冬阳.思想的临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45-287.
[7]曼斯菲尔德.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M]∥刘小枫,陈少明.经典与解释1:经典与解释的张力.何子建,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237-255.
Diotima’s Highest Teach of Eros——Reading Plato’s Symposium 210a-212c
TANG Mi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entre,Hainan University,Haikou 570228,China)
This article interpreted the highest Eros teach of Diotima in Plato’s Symposium and tried to trace the thinking course of Leo Strauss’,who reflects the crisis of modern western world.Modern political philosopher Machiavelli betrayed the highest Eros teach of Plato and suggested that the highest goal in man is his actual achievement and love for immortal fame,which marked a break between the ancient and the modern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thus brought about the controversy on the virtue of philosophers.
Eros;philosophy;poetry;Machiavelli
B 502.232
A
1004-1710(2010)06-0033-04
2010-04-27
唐敏(1985-),男,重庆忠县人,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2007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古希腊哲学。
[责任编辑:张文光]
——读《图像与爱欲:马奈的绘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