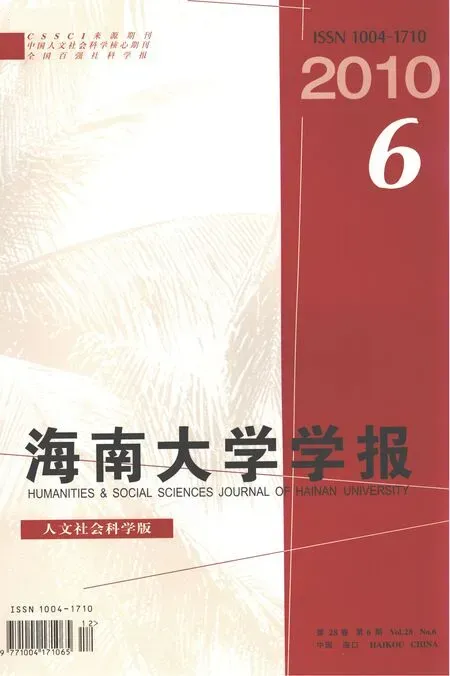“严肃”的“诚实”——罗蒂、施米特与施特劳斯的差异视角
张鑫焱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杭州 310028)
“严肃”的“诚实”
——罗蒂、施米特与施特劳斯的差异视角
张鑫焱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杭州 310028)
在《托洛斯基与野兰花》中,对哲学的“使命”或“任务”这一问题罗蒂无法作出回答。在《民主先于哲学》中,罗蒂提出为自由而牺牲道德是一个合理的代价。论题从对这两个问题的疑问展开,然后从施米特的视角思考,通过施特劳斯对施米特的阅读来理解政治哲学的重要性,突显道德的“严肃性”。最后,重新提出“为什么要哲学”这一问题,对施米特的政治哲学提出质疑,对罗马人施米特保持警惕。
哲学;政治哲学;道德
一、为什么要哲学?
在自传《托洛茨基和野兰花》中,罗蒂不无反讽地自嘲:“当有人询问我(呵,常常有人问我)什么是当代哲学的‘使命’或‘任务’的时候,我总是舌头打结,无以言对。”为什么一个15岁就进入芝加哥大学的神童大哲当被问到自己这么多年学习哲学的使命时竟如此窘迫呢?无论如何,罗蒂并不是想要主张“哲学从社会意义上讲是无用的”,因为毕竟柏拉图、康德、达尔文的工作都说明“理念产生了后果”,思想对于社会还是产生了影响[1]376。问题只是形而上学家试图将一切归结为“一”及以此为世界提供原则基础的努力破产了,如此一来,生活中只有芸芸纷杂的意见呈现,行为也没有共同遵守的“惟一”价值和“公共权威”了,一切都是偶然相对的。任何对于终极意义的提问都变成为虚假的,甚至提出类似的问题都是可笑的,从而使得提问本身变得不再可能。永恒不变的神圣规则沦为笑谈,只余下手段这一暂时起作用的“游戏”规则。于是,当面对“哲学的使命”这样的终极问题时,罗蒂自然难免窘迫。
与此相关,哲学不再是文化的女王,哲学家成为与其他学科专家一样的哲学专家,正如化学家熟悉各种化学物质及各种物质混合后如何反应,哲学家熟悉死去的“某些思想传统”能够进行一些思想的混合实验[1]376。哲学对于社会和行动的指导意义即使有,如柏拉图、康德、达尔文的思想的确对社会有影响,但那只是“偶然意外的”,哲学的社会意义微乎其微,只能够偶然地产生影响,“哲学对于对付纳粹和其他恃强凌弱者没有什么帮助。”[1]372
与其他种类的文化在人类生活的不同领域保有各自“自主性”一样,哲学只是社会多元文化的一个门类而具有自身的标准,保持着自身文化的独立自主性甚至到了完全孤立的程度。罗蒂完全放弃了形而上学的努力,将哲学作为文化的一个类别,哲学无法提供知识作为根基,在社会团结上又不如文学能够讲述一个充满同情的故事,那为什么还要哲学呢?罗蒂保留下来让哲学发挥功用的地方就是仿文学的功能——重新描述,反讽同一性,揭穿形而上学的虚假,回到偶然,回到最初原则的非此即彼,放弃任何调和统一的努力。
哲学只是文化的一个门类,而“技术和民主制度能够联合起来增进平等,减少苦难”,民主有着种族中心主义的最高价值,是不断自我完善的,技术获得了与民主同等的显赫地位。作为个人有推翻独裁统治的义务,要对他人保持同情以保证人类团结的希望,但个人并没有任何道德义务,“自由社会典型的性格类型是盲目的、计较的、渺小的、没有英雄气概的”,一切对个人自由的侵犯都被认为是强制,是邪恶的。而牺牲个人的道德,成为“盲目的、计较的、渺小的、没有英雄气概的”自由人是为了保证个人自由所要付出的“合理代价”[2]。无法对人做出要求是因为没有什么客观道德原则作为基础,“上帝和道德法则都务必被时间化、世俗化和历史化才是可信的”,没有什么永恒原则,只能是黑格尔式的历史主义态度,一切都是当下。
二、《政治的概念》及其《评注》
虽然屡遭挑战,但是对用于界定政治和国家的特殊性的分类问题,今天最为司空见惯的真正自由主义答案却依然如故:类就是“文化”,即“人类思想和活动”的整体,它划分为“各种相对独立的领域”,成为“各种文化区域”。[3]194
“自由主义最终的自我认识就是文化哲学”[3]198,这种文化哲学将“文化”即“人类思想和活动”的整体划分成为各种各样的、相对自主的领域,不仅各个文化领域在彼此关系上是独立自主的,而且作为整体的文化也是自主的。人类思想和活动的各个领域都能和平共处,一个人可以在各个文化领域中作为一个自由的决断者行事,“审美”、“道德”、“经济”都是相对独立自主的领域,甚至“战争”、“专政”、“革命”、“技术”都被说成是非政治的文化领域,是自我发展、不断进步完善的。施米特与这种流行的文化概念分道扬镳,要求凸显政治的特殊性,政治即朋友和敌人的划分,“既不等同于也不类同于……其他(‘在道德领域是善与恶,在审美领域是美与丑,在经济领域是利与害’[4]106)那些划分”,因为,尽管在个人主义的自由社会中,一个人能够有自主性“为任何他情愿以身相殉的东西而死”,任何重要的事情都可以变成只是“私事”,但是在“政治领域中”却不得不为某种外在力量所决定,而且这一力量关乎生死。战争作为“最极端的政治手段”让个人完全无法回避,个人在战争这“最可怕的紧急状态”中必须明确自身的处境——即必须正确地划分敌友,“因为战争不但关系到而且一直关系到‘肉体屠杀的现实可能性’”。对政治的这一结构性定位,“说明了政治是基础性的,而不是一个与其他领域并存的‘相对独立的领域’。”[3]195政治“既不等同于也不类同于”道德、审美和经济等领域,政治是“尺度”。在1933年版《政治的概念》中施米特改写了关于政治的权威性这段话,更加鲜明地反对自由主义试图中立化和非政治化的“文化哲学”,甚至有些决绝地预言政治作为尺度的地位:
一旦出现政治单位,他就是权威性、总体性和至高无上的单位。政治单位是“总体的”,首先因为每一事物潜在的都是政治的,并因此受到政治决断的影响,其次因为,人类就其总体而言在生存上是通过政治参与而得以理解的。政治就是命运。[3]21
政治作为绝对的“现实性”,“根本无法以某种理想来衡量”,所有用于政治上的理想只是“抽象”而已,而用于政治上的所有“规范性标准”只是“虚构罢了”。施米特直言不讳地道出了政治的实质:
政治是借助于人对人“肉体屠杀的现实可能性”来建立的,“决不存在什么理性的目的和规范,更遑论真假,决不存在什么纲领,更遑论可否值得效法,也根本没有什么社会理性,更遑论其是否美好,这里既没有什么合理性也没有什么合法性能够把人对人处于自己的原因而相互杀戮正当化。”[3]199
这样说来似乎要进入现实与应当的区分,施米特对政治的肯定是因为政治是绝对的真实,是必然的,区分敌友是“民族政治生存的本质所在”;而如罗蒂这样的自由主义民主乌托邦则代表着政治的理想,按照历史主义的态度,政治的恶应该朝着这一多元文化的乌托邦方向不断地进步,政治的恶只是手段而已。施米特似乎并没有完全否弃这一非政治化的理想,他说自己并不知道这种理想是否能实现,“至于这种状况是否能出现,何时出现,我一无所知”[4]133。但是,施特劳斯敏锐地洞察了施米特,这根本不是知不知道的问题,而是“他的确憎恶这种理想”[3]204。笔者还是跟随施特劳斯来寻找施米特信念的阿里阿德涅线团吧:
如果……朋友与敌人的划分即使作为可能性也不复存在了,世界上将不会再有政治,也不会有国家,只剩下一种与政治无关的世界观,只剩下文化、文明、经济、道德、法律、艺术、娱乐①在《政治的概念》1933年版中,并非“娱乐”这个词,而是“闲扯”(unterhaltung)。施米特在《政治的概念》1963年版补注中提到正是由于施特劳斯《评注》对于“闲扯”(unterhaltung)这个词的特别强调,使得自己认识到了在1933年时将“该词用在这里完全不够充分”,而且当时的思考也处于“不确定状态”。为了更准确地表达与施特劳斯正确认识到的“娱乐”是与“严肃”(ernst)相对的概念,施米特决定使用“娱乐”一词。等等。[4]133
庐山我家楼下的六间门面,全租给人家做生意。有一家是开照相馆的,招牌叫“真光”,至今很多人家保存的庐山老照片都有“真光”字样。还有一家面包房,整日弥漫着烤面包的香味,十分诱人,我们家人平时买面包只需记个账,最后归总抵房租。我们最喜欢去王家坡游玩,路好走,风光美,有双瀑,瀑下深潭可游泳,当年王家坡是很出名的景点,上庐山的人都会慕名前往。
施特劳斯紧紧咬住“娱乐”不放,如猎犬般注意到在“文化”、“文明”、“经济”、“道德”、“法律”、“艺术”这一系列“严肃”的追求压迫之下,施米特让“娱乐”几乎“销声匿迹”;尤其是紧跟着“娱乐”一词的“等等”更是掩盖了“娱乐”是这个系列中的最后一个词,掩盖了“娱乐”一词的“终结性质”(finis ultimate)。施特劳斯的魔眼发现:原来,施米特在刻意隐藏“娱乐”一词。施米特让什么欲盖弥彰?在《政治的概念》第三节“战争是敌对性的显现形式”中,施米特设想了一个政治不复存在的世界,“可以想象这样一个世界照样包含很多或许相当有趣的对立和对抗,各种竞争的谋略,但是却不复存在那种富有意义的对立面,以要求人们去牺牲生命……”。在第六节“世界并非政治的统一体,而是政治的多样体”的注释中,施米特举了一个例子——与“朋友和敌人的划分”不再相干的但含有“相当有趣的对立和对抗,各种竞争谋略”的活动:象棋博弈游戏。施特劳斯提醒人们注意“或许相当有趣”的“或许”一词所“掩饰同时又流露出”的施米特隐含着的反感:这是“一个娱乐的世界、一个消遣的世界、一个毫无严肃性的世界”,“趣味性和娱乐性”是这一世界的内涵。这是一个你的政治敌人所期望看到的世界,人们追求“娱乐”而忘记了真正重要的严肃的东西。这真正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施米特为何肯定政治性呢?施特劳斯循着施米特的线团,在经过了“娱乐”与“或许”之后,找到了迷宫的出口:
他之所以肯定政治性乃是因为他在受到威胁的政治状态中看到了对人类生活之严肃性的
威胁。所以,对政治的肯定最终无非是对道德的肯定。[3]205
“所以”前面的一句话可以得到理解:罗蒂为了消除冲突、保护个人的自由和财产而“信仰”“技术和民主”愿意牺牲道德义务安于平庸,即使自由社会的典型性格是“盲目的、计较的、渺小的、没有英雄气概的”也是“丢卒保车”、“物超所值”了;施米特针对此“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社会”强调“民族国家”的整体:政治“要摆脱一切任意的私人判断”,有着“超越私人的义务(verbindlichkeit)特征”,为了“人类生活之严肃性”,为了“那种富有意义的对立面”,为了对“道德的肯定”,寻找“要求人们牺牲生命”的意义,要勇于“放弃现有的安全”。在“娱乐”和“严肃性”的意义上来说,对“政治的肯定”就是对“严肃性”的肯定。但是,这里依然保留在之后才能得到充分展开的问题是:施特劳斯“对道德的肯定”这一表述还是有些模糊——“谁的道德”?,难道自由主义“不道德”?
在《中立化与非政治化的时代》一文中,施米特将现代世界描述为一个非政治化的时代,其法则就是否定政治是区分敌我,是生死攸关的生存斗争,逐渐使政治中立化,不惜一切代价达成暂时的“一致与和平”。可这一代价是放弃了目的“转而只关心手段”,导致没有人能够回答“为什么要哲学”、没有人能够“严肃地提出何为正义这个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将会导致“一系列无法解决的难题”,围绕目的本身总是争吵不断:“围绕什么是正义、什么是善,我们总是在互相争吵,不但与别人吵,而且还与自己吵”;而对于手段的关心最终沦入了对技术的信仰:“当今对技术的普遍信仰是不言而喻的……显然没有比技术更中立的东西了”,“技术服务于所有人”,“所有人都利用技术并理所当然地享受技术带来的方便和舒适”,这就“与神学、形而上学、道德甚至经济方面那些可以永远争论下去的问题不同”,技术的问题可以得到清楚的解决,技术“似乎成为一个和平”的中立领域[4]184。自由主义者正是利用通过技术革新导致社会文明不断进步的观念而逐步使得政治斗争非政治化、中立化,最终达到“技术宗教时代”。施米特将这种技术性精神称为“一种空想或魔鬼般的信念”,它使得人们“相信人类的无限力量以及对自然、甚至对人性的控制,相信‘自然之边界的消退’是没有限度的,相信人类社会能够不断改变,永远繁荣下去。”这意味着,此种精神中立性使得人要“随着技术驶进了精神虚无(beim geistigen nichts)的港湾。”[4]186
可是,技术的中立性只是虚假的表面现象:“技术永远只是一种工具和武器;恰恰因为它服务于所有人,它不具备中立性”,此种“工具和武器越有用,利用它们的机会就越大。”[4]184对于技术的信仰使得世界失去了“严肃性”,进入了“娱乐”和“消遣”的“精神虚无港湾”,失去了对于目的本身——道德的关怀,人成为手段,沦为技术工具。必须重新提出“人生意义”的问题,人才能作为目的而非手段;必须重新提出“何为正义”的问题,人才能真正成为人。区分敌我这一生死攸关的政治问题之合法性基础在于必须提出这个“严肃”的哲学问题:“何为正义”[3]206。
面对为什么要哲学这样的问题罗蒂尴尬万分无法回答,任何终极的问题都被消解成为虚假的问题以致丧失了提问的可能性,只余下暂时起作用的游戏规则;施米特斩钉截铁地强调“政治就是命运”,为了对于道德和终极意义的寻求必须放弃“游戏”,放弃“趣味和娱乐”而重新提出“什么是善、什么是正义”这样的哲学问题。自由主义者放弃了追求“严肃”的信念,放弃了寻找“人生意义”的终极目的问题而安于平庸,这是身为罗马人的施米特绝对无法接受的。
三、罗马人施米特
相传,施米特在魏玛时期对尼基希说:“从渊源、传统和法上讲,我是罗马人”,尼基希也深谙施米特的来历:“施米特是在对罗马这个伟大典范的认同和敬畏中成长起来的”。在《罗马天主教与政治形式》一书中,施米特开门见山地指出:“有一种反罗马的情绪”,施米特认为没有什么比这种情绪更糟糕的了。法贝尔在其文章《罗马人施米特》中认定像施米特这样的人“一定有一种强烈的亲罗马情绪”[5]227。
施米特的帝国概念是由罗马帝国演化而来,因此是罗马的,而且是德意志式“罗马的”,而非盎格鲁-萨克森式“罗马的”。在施米特眼里,“德语不是法的语言”,而罗马人是“法的民族”,“罗马的和平秩序同样得归功于拉丁语言,也就是说,拉丁语的词语句同事物本身以及法律秩序相吻合,与之相反,盎格鲁-萨克森语言是海洋般起伏不定的”[5]229。象征着“土地”的罗马精神与象征“海洋”的英美自由精神相对抗。“海洋般起伏不定的语言没有能力统治世界”[5]230,因为海洋没有“性格”(“性格”这个词从希腊语charassein而来,是雕刻、刻入和印入的意思),海洋无法通过劳作得到“雕刻”。虽然海洋有着“鱼、珍珠”等丰富的宝藏,但是没有“需要按照播种和收获这一内在尺度的劳动”:“在海中没有田地可以播种,也不能划出固定的边线”,“驶过海洋的船只不会留下任何痕迹”。也就是说,“海洋不存在空间和法律、秩序和定位统一的含义”,“在波涛之上只有波涛”,没有劳动可以刻下任何痕迹。而土地是“最公正的”(诗人维吉尔justisima tellus),只要播种就有收获,英雄们夺得土地并“划上坚固防线”:在土地上建立“长城”这样的界限守护,把和平的秩序与无序分开,将受保护者安全地包裹在界墙之内,成为这片土地的子孙。在这个意义上说,“法植根于大地,与大地相连”,它是“大地劳作的报酬”,“作为一条固定的界限”,明显地标志着“秩序”。所以施米特提议“谁若把‘最公正的土地’作为母亲,他一定持反海洋态度。”[5]238
“罗马精神”是“土地与血的精神”。在《语汇:1947—1951年笔记》中,施米特明确地写下:“空间(raum)与罗马(rom)是同一个词”[5]236。据施米特从词源学上考证,“空间”一词为日耳曼语言所共有,其词根为rum,意指获得生存的区域。施米特提出的“大空间秩序”就是罗马秩序,是日耳曼人的罗马秩序,而“掠夺土地”就是这“空间上最初的秩序”,它“包含着所有以后具体秩序的起源以及所有以后的法律的起源。……从这种‘绝对的权利’中演化出所有以后的占有关系和财产关系”。施米特把夺取土地和夺取女人等同起来,因为“女人”与“土地”一样,只要男人占有和耕种,就能得到属己的“收获”[5]233。施米特所要求的“大空间秩序”按照罗马人的解释即是“夺取土地和女人”,这是属于日耳曼“有血性男人的一种命运”:对“空间”的神魔般的憧憬。
罗马人施米特断言:“不会再有和平,只有消除国家间的战争并且带来战争的转型,即世界范围的内战”。而“国家=主权=决断权=结束国家范围的内战(仅由此而得以建立国家)”这一等同公式使得施米特对法西斯持肯定态度,因为它“结束了内战”,“法西斯国家希望带着古希腊罗马式的真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5]243。
四、“严肃”的“诚实”
纳粹失败了,但民族国家依然如故。施米特的“种族生存论”、“区分敌友论”、“战争高于和平论”喊得固然明目张胆,可是谁又不是偷偷摸摸紧锣密鼓呢?一个民族国家采取什么样的“主义”与制度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内部的自由民主一点不妨碍国际上的独断专行,同样,内部的专制独裁照样可以在国际上大谈多元平等”。施米特与希特勒相联系是“偶然”的机缘,但是与民族国家相连,却是必然的[6]。
施米特告诉人们:“政治就是命运”,为了种族生存不但自我要牺牲更要牺牲别人,战争就这样被合理化了。在施米特的政治彻底性中,施特劳斯看出了另外一面:“恶能够以腐败、软弱、怯懦、愚蠢的面目出现,但是也能够以‘残忍’、本能冲动、生命力、无理性等面目出现。”[4]138也就是说,恶是“人性之卑劣”抑或“兽性力量”。施米特把人在自然状态的恶等同于后者“兽性力量”——“把人性之恶看成动物性的无辜之恶”。这样一来,战争,即便是侵略战争也只是“无辜的恶”:异族存在本身就是对我族生存的自然威胁,为了我族生存的需要必须建立以我族为中心的空间秩序,战争不可避免。也只有这样,施米特的政治行为——“区分敌我”、“战争高于和平”就顺理成章而不必承担政治行动启动之后随之而来的罪行。施米特以明确的“同情”口吻谈论“没有道德含义的‘恶’”,但是“这种同情无非是对动物强力的推崇而已”。施特劳斯认为这仍然是在自由主义的牢笼之内批判自由主义(生存论的性恶论)。要回到霍布斯之前,“回到把恶作为道德之卑劣的观点”,惟有如此,施米特才能找到出路:“‘政治理念的核心’乃是‘道德要求的决断’”[3]204。
至此,就可以将施特劳斯的这句话:“所以,对政治的肯定最终无非是对道德的肯定”解释清楚了。施米特肯定政治的合法性基础在道德,但这并不是说自由主义者没有道德,肯定政治的希望战斗的人与自由主义者一样的“宽容”,只是意图却正好相反:
自由主义者尊重并宽容一切“诚实”的信念,只是他们仅仅认为法律秩序与和平神圣不可侵犯,而一个肯定政治本身的人则尊重并宽容一切“严肃”的信念,即定位于战争之现实可能性的一切决断。[3]208
这不是肯定一个否定另一个,而是要表明“诚实”之“严肃”。施米特和自由主义并不是“死敌”,施米特“对自由主义的批驳只是伴生性和准备性的”,而真正的“死敌”,“决定性的斗争”双方是:
斗争的一方是“技术精神”和“激发反宗教的世俗激进主义的群众信仰”,另一方则是相反的精神和信仰,它至今似乎依然没有名称。最终,对何为正义这个问题的两种截然相反的回答相互遭遇一起,这些回答均不允许任何妥协和中立。[3]209
这是两种精神之间的斗争。
[1]罗蒂.托洛茨基和野兰花[M]∥罗蒂.罗蒂自选集:后形而上学希望.张国清,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2]罗蒂.民主先于哲学[M]∥罗蒂.罗蒂自选集:后哲学文化.黄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174.
[3]施特劳斯.《政治的概念》评注[M]∥迈尔.隐匿的对话——施米特与施特劳斯.朱雁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4]施米特.政治的概念[M]∥刘小枫.施米特文集:第1卷.刘宗坤,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5]法贝尔.罗马人施米特[M]∥刘小枫.施米特与政治法学.增订本.刘锋,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6]墨哲兰.这样的历史是否过去了?——西蒙问题与现代性危机[J].开放时代,2001(9):43.
The Honesty of Seriousness——Th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f Rorty,Schmitt and Strauss
ZHANG Xin-yan
(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28,China)
In the essay Trotsky and the Wild Orchids,Richard Rorty got tongue-tied when he was asked,“what is the‘mission’or‘task’of contemporary philosophy?”The article begins with two questions.First,why Richard Rorty could not rise to that challenge?Furthermore,why,in his Democracy and Philosophy,he sacrificed“Morality”for“Freedom”——“that even if the typical character types of liberal democracies are bland calculating,petty,and unheroic,the prevalence of such people may be a reasonable price to pay for political freedom”?After that,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Carl Schmitt,we can understand the seriousness of virtue and the importance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by Strauss’s reading of Carl Schmitt.Finally,we examine Carl Schmitt’s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keep watchful to the Roman,Schmitt,by throwing out the question again:“what is the mission of philosophy?”
philosophy;political philosophy;morality
B 505
A
1004-1710(2010)06-0042-05
2010-06-14
张鑫焱(1981-),男,河南洛阳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2007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政治哲学。
[责任编辑:张文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