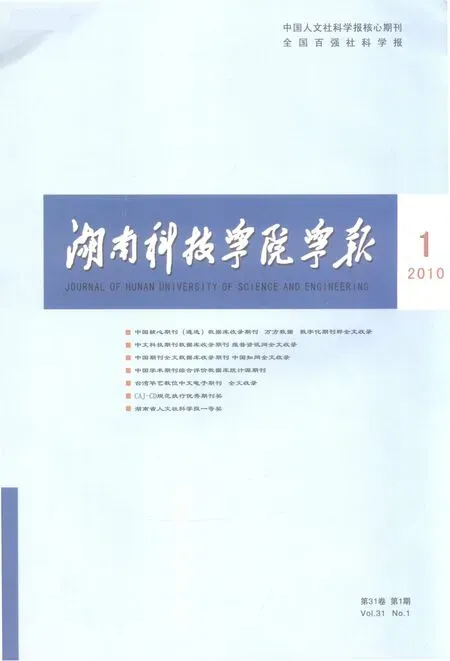女性文学视角下的外部世界
——杜拉斯的中国情缘
潘 昭
(西安外国语大学,陕西 西安 710128)
女性文学视角下的外部世界
——杜拉斯的中国情缘
潘 昭
(西安外国语大学,陕西 西安 710128)
由于玛格丽特·杜拉斯自身经历与中国的不解之缘,以及她的作品中常常出现的对中国这片充满神秘的东方土地的描写,均使其文学中呈现出与中国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同时也表现在作家的生活和回忆之中。随着20世纪80年代初期之后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作品相继被译介到中国,也为她赢得了广大的中国读者。当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作品在中国流传的过程中,从作家的中国情缘为切入点对其进行解读,也是能够更深刻的理解其作品的一个值得尝试的方法。
女性文学;杜拉斯;新小说
阅人无数,历尽沧桑也好;游戏人生,嬉笑怒骂也好;放荡不羁,轻描淡写也好,心灰意冷,坚不可摧也好。只要心中还有爱,就依然宛如十五岁半的小女孩,穿着旧的丝织连衣裙和金边高跟鞋,睁着无辜的眼睛,怀着一颗惴惴不安的水晶般的心。有的女人,慢慢的老去,眼睛却依然如同赤子 ,明亮,清透,这样的意志与心绪,要么是大福大贵家的女儿,现世安稳,没有受到一丝损害;即使是千层丝绒下的一颗小豌豆,也没有机会存在。要么便是坚韧到底的女子,内心强大,最终使自己的心意如同天地般无情并不留下任何阴影。作为一个女人,你可以爱她,也可以恨她;而作为一个作家,她的魅力无可抵挡。这个人,就是——玛格丽特·杜拉斯。
玛格丽特·杜拉斯于1914年4月4日出生在印度支那嘉定市。父母都是小学教师,受殖民主义宣传的影响,从法国本土来到当时是法属殖民地的印度支那。她本人则在印度支那度过了她的青少年时代,直到十八岁时才回到法国,定居巴黎。因此,东方的文明,异国的情调都在杜拉斯的内心烙上了深刻的印记,这种难忘的经历,对其今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一 杜拉斯小说中的中国情缘
印度支那这片土地令杜拉斯沉迷,东方的神秘渐渐开启了杜拉斯创作的灵感,而在东方这片古老大地上的中国,又与其有着一段不解的情缘。然而,杜拉斯对于中国的了解,抑或是整个东方的了解,并不是身临其境的,成年后,她再也没回去过童年时的东方故乡,她固执地守着发黄的照片,还有那段不能回避的往事和切肤的痛,因为现实只会破坏记忆中的印象,就像她对米歇尔·芒索说的:“所有写出来的东西都是真实的。现实生活中没有任何东西是真实的。”印度支那就是他记忆中的印度支那,东方亦就是他感觉中的东方。也就像其自己所说的:“我写作是为了走出自己,进入书本,是为了减轻我的重量。我愈写我就愈不存在了。”
杜拉斯对中国的了解或许就是她的中国情人,那段刻骨铭心的失意的爱情一直是她的心结。从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里的诺先生,到《情人》,再到《中国北方的情人》 都出现了和中国的一段情缘故事,几部不同的作品中,中国情人的形象日渐丰满。从小说中反应出的主人公对中国情人的态度,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通过这其中的种种变化,我们可以看出从中映射出她与中国的这段不解之缘,以及她对中国这片充满神秘的东方土地不断的了解和态度变化的过程。
在1950年出版的《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诺先生丑陋猥亵,除了有钱一无是处。苏珊对其并未有过多的好感,以至于描写一开始就是这样不怀好意的场景:“诺先生是那个足智多谋很有办法的人的蠢得可笑的儿子。此人家财万贯,可是继承人只有一个,这个继承人又非常缺乏想象力。……对这个孩子,人们是不抱希望的。你以为是孵出了一头雄鹰,可办公桌下却飞出来一只金丝雀。……这就是那个坠入情网的男子,有一天晚上,在拉阿姆,爱上了苏珊。他可交了好运,又碰见了一个约瑟夫。还有那个母亲。”在这部小说中,事实上苏珊拒绝与他相爱,且对他没有什么好感的。
“诺先生和她讲了留言机以及留言机种种不同的价值,要求苏珊给他打开浴室房门,让他看一看她全裸的摸样,条件是送给她一架新型胜利牌留声机带唱片,巴黎最新出品……‘开开门’诺先生说,声音很轻。‘我不碰你,你不进门,我只是看看你,开开门吧。’苏珊不动,一直等着想知道该怎么办好。……就像这样,当她要开门的时候,让世界一睹其人,世界竟将她置于卖淫的地位……她软弱无力地说:‘你这个下流坯’”这一幕对于诺先生与苏珊二人可能发生的种种关系来说,是具有象征意义的:这是一下降到以具体报偿为条件的单纯观淫癖的私人之间的关系。1977年的《伊甸影院》(《抵挡太平洋的堤坝》的戏剧版)里的诺先生痴情,不断的用金钱和钻石去诱惑苏珊,但苏珊并未失身于诺先生。
再到《情人》,从湄公河上的渡轮上“我”和他见面的第一眼,相互之间就产生了一种微妙的情感,十五岁半的这段经历,在“我”的心里烙下了深深的印记,以至于她后来在《情人》中写到了这个细节“战后许多年过去了,经历几次结婚,生孩子,离婚,还要写书,这时他带着他的女人来到巴黎。他给她打来电话。是我。她一听那声音,就听出是他。他说:我仅仅想听听你的声音。她说:是我,你好。他是但怯的,仍然和过去地样,胆小害怕。突然间,他的声音打颤了。听到这颤抖的声音,她猛然在那语音中听出那种中国口音。他知道她已经在写作,他曾经在西贡见到她的母亲,从她那里知道她在写作。对于小哥哥,既为他,也为她,他深感悲戚。后来他不知和她再说什么了。后来,他把这意思也对她讲了。他对她说,和过去一样,他依然爱她,他根本不能不爱她,他说他爱她将一直爱到他死。”这是《情人》的结尾,不过我道宁愿相信,这是杜拉斯给自己构筑的一个幻象,当她抛弃了抱怨、愤怒、偏执等种种情绪之后,她更愿意将她笔下的情人塑造得更美好、更般配,使得爱情故事更为浪漫。他依旧是那个胆小的,在面对她时会颤抖的那个中国男人,一如很多年前。在她的心中,这样一个形象是伴随了她一生的,无论如何无法改变。有些事情是难以遗忘的,时间是最笨拙的工具,它只会让人们对年少经历的爱情愈加清晰愈加怀恋愈加感伤。在情人的心底,他把对她的爱保留了一生;在她的笔端,她把对情人的回忆交于了她所有的文字。那是内心深处发出的一声长长的叹息,来自遥远的中国,在西方的天空划过,但它决不是转瞬即逝的流星,它会在空中久久的驻足,久久的凝神,为这个世界,为文学留下绝妙的咏叹调。杜拉斯一生有过许多情人,但这段初恋在她的心目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她曾说:“他使我生命中的其他爱情黯然失色。”
再就是《中国北方的情人》这部作品,女主人公对中国情人的感情就更加的厚重了,她说:“我真希望我们也结婚。让我们成为终成眷属的有情人。”这样的一句话,也许不但写出了小说中女主人公的心声,更写出了杜拉斯本人到了晚年的感情观。水一旦流深,就不会发出声音。人的感情一旦深厚也许就会显得淡薄了吧。正是这样简单的话语,也许更能表达出这种深厚的感情。杜拉斯本人也在《情人》出版后接受电视采访时曾说:“这是我第一次没有写虚构的东西。我以前的书都是虚构。”[1]《中国北方的情人》发表时作者更是强调:“这部作品编造的成分比《情人》里更少,都是真的。”[2]三部作品的创作,所涉及到的中国的内容也越来越多。在《中国北方的情人》中,第一次,“他”给“我”讲了中国:讲中国的历史,讲鸦片战争,讲共和,讲孙逸仙、蒋介石,讲共产党,在这一刻,中国在“我”的眼中是如此的神秘又充满向往。
开始以后,便不能回头。一次偶然的邂逅或是一份迟来的感情,人的矛盾和选择总是不可避免。也许没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也只有坚定的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才能做完一些事情。对自己喜欢的东西沉着冷静,内心笃定,那么此时,结果与否,又有什麽关系。有时候我们只是需要一个人在身边陪伴,也许那个人是谁根本不重要。三部不同的小说,三个不同的结局,三段不一样的情感,三种不一样的心态。这其中的滋味,我们不得而知,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中国这个响亮的名字已经在杜拉斯的心中慢慢的沉淀了下来。
二 杜拉斯与中国的不解之缘
关于杜拉斯的中国情缘,也许还要追溯到其迷一般的身世中去:意大利的安吉罗·莫里诺揭示了这样一个惊人的秘密,杜拉斯笔下的情人不是她的情人,而是她母亲的情人!当她的父亲在法国的普隆比埃尔养病的时候,正是这个情人与她的母亲生下了她和她的弟弟的时间,在她长大后又与她发生了关系。这方面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杜拉斯越到晚年,她的混血儿的面孔就越像亚洲人,或者说像她在书中所写的那个中国人。莫里哀指出,她的母亲是让女儿向他卖身,以换取全家返回欧洲的路费。但据查阅过杜拉斯私人档案的洛尔·阿德莱所著的关于她的传记中透漏,她的母亲是为了让吸毒的大儿子有钱去买毒品。[3]这个事实固然令人触目惊心,但是在杜拉斯的作品的字里行间,在她的影片、照片和生活里都能够找到无数的佐证和痕迹。由此,我们也便不难理解,杜拉斯为何并未到过中国,却时常在小说创作中注入中国情缘的元素。
三 杜拉斯作品在中国的流传与接受
再说杜拉斯与中国的情缘不仅仅反应在其小说的创作和其迷一般的身世中,这种缘分还体现在中国对杜拉斯作品的接受上。在信息和网络如此发达的当今社会,涌入中国的外国作家不在少数,但杜拉斯作品在中国的名气可以说是有目共睹的。其最早被翻译到中国的作品是1980年王道乾译的《琴声如诉》 ,稍后,另两本杜拉斯作品也由王道乾译成中文:《昂代斯玛先生的午后》(1980)和《广场》(1984)。但其真正在中国声名鹊起是由于《情人》在中国市场上取得的成功之后。因为在此之前,杜拉斯的作品一直是被看作是难以阅读,只有知音才可接近的读者,而在1984年《情人》获龚古尔奖显然大大推动了杜拉斯在中国的流行(中国出现了第一次译介杜拉斯的热潮:两年内出版了6个《情人》中译本,1985年3个,1986年3个)。尤其是女作家把情人的身份定格为30年代西贡富有、英俊的中国男子,“柞丝绸和英国香烟的味道”,1991年出版的《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中杜拉斯更加明确地点明了情人的身世渊源,这无疑让中国读者、尤其是中国男性读者的虚荣心大大地膨胀了一下。再到电影《情人》的放映,加上中国籍演员梁家辉的演绎,更是使杜拉斯被中国人所熟知,也让很多从来没有翻开过杜拉斯的书的人知道了她的名字。
很快,杜拉斯成了在中国被最广为译介、阅读和研究的法国当代作家之一。1999和2000可以毫不夸张地被称为“杜拉斯年”,两年内约有30本杜拉斯作品和关于她的传记和研究著作被译成中文,掀起了杜拉斯在中国译介的第二次热潮:1999年漓江出版社出版4卷本《杜拉斯小丛书》,同年作家出版社出版3卷本《杜拉斯选集》,2000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许钧主编的15卷本的《杜拉斯文集》。劳尔·阿德莱尔的《杜拉斯传》和扬·安德烈亚的《这份爱》和《玛·杜》都被译成中文,其中后两本的中文书名被译为很有卖点的《我、奴隶和情人:杜拉斯最后一个情人的自述》和《我的情人杜拉斯》。而《情人》,以8个中译本,制造了中国的一个“文学现象”,不仅成为杜拉斯最为中国读者熟知的作品,也成了最受某些中国当代作家推崇模仿的外国作品。
玛格丽特·杜拉斯以其嵌入自己经历的写作和人生追求创造出了具有当代特征的女性叙事,从一个女性的文学视角出发,通过特殊的表达方式来表现出了其所处的外部世界。有评论者曾说:“杜拉斯的所作所为在法国文坛上可说是最无法归类、最不具典型性的。从法国共产党党员到社会党总统密特朗的密友,社会边缘人物的喉舌;从‘新小说’同路人到‘新浪潮电影的先锋;从充满魔力的文学语言到有悖常理的对社会新闻的干预;从电台报刊上文学的、政治的高谈阔论到街头酒吧里与酒徒、流浪汉的畅饮狂欢,这一切都无法归入任何规范。’”[4]杜拉斯成了一个神话,一个时间还没来得及检验就已经成为“经典”的当代女作家。女权主义者把她视为女性解放事业的一面旗帜,而社会学家则把她视为时尚和习俗改变的一个敏感的风向标。她的成功,对中国女性文学,尤其是对于中国九十年代涌现的女性写作及女性文学批评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之后,对中国影响较大的作品中,值得一提的是1986年王道乾还翻译了《广岛之恋》和《长别离》。如果我们用比较文学和历史反思的眼光去审视,这一翻译选择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偶然。先看《广岛之恋》:如果说书中的爱欲描写和电影中的男女亲热镜头让一直视性爱为禁区的80年代的中国人觉得“震惊突兀”的话,《广岛之恋》的主题和风格却和80年代风行中国的“伤痕文学”有很多的默契。而且该书的中译本序的题目就是“规范之外的伤痕爱情——玛格丽特·杜拉斯:《广岛之恋》”,作者柳鸣九用的正是“伤痕”一词来形容纠缠故事始终的存在之苦痛和悲凉。“作者的感情与立场不是“阵营性”的,而带有人道主义的色彩。她关心的是人,是人的城市、人的物质生活、人的生命在战争盲目的毁灭力量面前会变成什么样,她表示了一种泛人类的忧虑,一种超国度、超阵营、超集团的人道主义的忧虑,对于整个人类命运的忧虑。”[5]
杜拉斯小说的传入,与当时中国所处的现实状况,还有更深一层的情缘在其中。不难理解为什么杜拉斯的《广岛之恋》和《长别离》会引起中国读者的关注:战争的伤痕让人联想到文革的伤痕,这两种类似的伤痕都需要被讲述,被揭露,痛苦的记忆需要再现,需要缅怀,然后才能被埋葬,被超越。但“伤痕文学”在中国很快过时,而让杜拉斯在中国红极一时的也不是因为她作品中体现出来的人道关怀,更不是基于她在法国新小说的探索上的建树。打动中国读者更多的是作家传奇而让人非议的生平和爱情,她女性的、敏感的、弥漫着浓厚的自传色彩的写作风格。历史考据式的解读无法接近杜拉斯的小说,我们不能再用真实与虚构的维度来衡量和判断她的写作。杜拉斯说:“我无时无刻不在写,我每时每刻都在写,即使在睡梦之中。” 对杜拉斯而言,割裂了现实与作品的虚构是不存在的。她相信,无论是作品,还是生活,都是她个人内在心灵世界的不同投影。写作消除了存在与表象世界的差别,甚至可以说,杜拉斯的写作是她摈弃生活真实的一种方式,她将写作替换了生活,用文本产生现实。自柏拉图以来,西方就确立了真实与虚构相对立的诗学传统。在小说创作中,作者是真实的本源,作品是作者的投射体,其真实性必须依赖于作者的赋予;同时,在小说阅读中,作品是真实的本源,是读者获取真实的保证。这意味着,在对真实的把握上,作者拥有高于读者的权力。
四 结 语
随着20 世纪语言意识的凸现,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等级秩序被颠覆了,虚构作为真实的模拟、附属、派生的地位得以改变。杜拉斯所强调的“生活不必要, 必要的是创作” 的观念,不仅混淆了真实与虚构的界限,还混淆了作者和读者之间本末源流的界限。虚实之间到底何谓真何谓假,我们已无从知道其中的种种,也或许真假在此时已经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杜拉斯这位杰出的女性作家笔下的外部世界,使我们以另一种角度审视了身边的一切。真假也好,结局也好,又如何,如果仅仅是为了结局,那么我们可以从出生就直接走到死亡。一切已经过去的事都会无可避免地打上封印,遗忘在时光中随着年岁渐长,慢慢开始相信,人的一生中,最大的财富,是经历。其实爱一个人,是一件简单的事。就好像用杯子装满一杯水,清清凉凉地喝下去,你的身体需要它,感觉自己健康愉悦。从此认定它是一个好习惯。所以愿意日日夜夜重复。爱着一个人,并且被之所爱。长路且行且远,心里有着单纯而有力的意愿。者所有的一切都要承担,并且感恩和宽悯。杜拉斯小说中的中国情缘也好,抑或是杜拉斯本人的中国情缘也罢,确实让中国人接受了她,中国也便成为了她内心深处最浪漫、神秘的归宿。
[1]Jean Cazenave Apostrophes,Prod[M]. Antenne2.émission de Bernard Pivot,réalisation. 1984.
[2]黄晞耘.一个形象的神话[J].北京:外国文学评论,2001,(2).
[3]吴岳添.法国文学散论[M].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
[4]王东亮.盖棺难以定论的杜拉斯[J].世界文学,1996,(5).
[5]柳鸣九.枫丹白露的桐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参考文献:王晚霞)
book=36,ebook=517
I106
A
1673-2219(2010)01-0036-03
2009-10-11
潘昭(1985-),女,河南郑州人,西安外国语大学法语语言文学专业2007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法国“新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