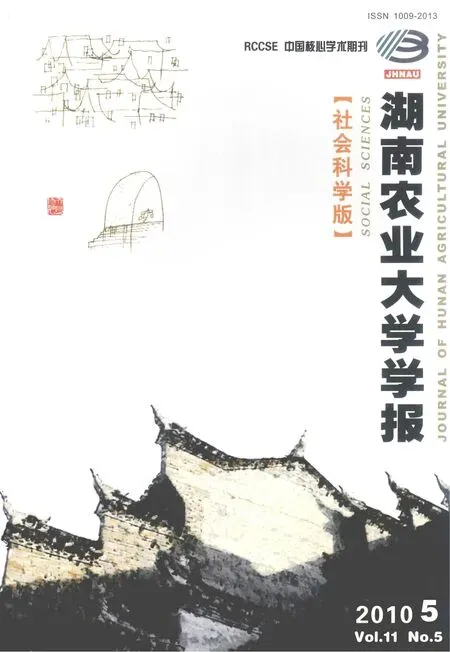中国乡村社会结构与人际关联的历史嬗变
张健
(咸阳师范学院 政治与管理学院,陕西 咸阳 712000)
中国乡村社会结构与人际关联的历史嬗变
张健
(咸阳师范学院 政治与管理学院,陕西 咸阳 712000)
人际关联是社会结构的基础,社会结构决定着人际关联模式。传统乡村社会的封闭性和内聚性决定了血缘和地缘是人们最为主要的社会关联。近代以降,现代商品经济活动打破了村落的封闭性,国家政权建设破坏了乡村共同体的内聚性,村庄内部不断分化,宗族和村政日益丧失强有力的聚合作用。人民公社时期政社合一体制使农民之间以及农民与组织之间关系具有行政化色彩。改革开放后,乡村受行政权约束减弱,农户之间以“庇护关系和原子化”为基础。未来农村职业分化日趋明显,出现不同的利益阶层,乡村人际关联呈现先赋性与契约性的特征。乡村社会结构的制度建设的路径是加强公权力约束机制和民生保障制度建设。
乡村;社会结构;人际关联;民生
一、问题的提出
国内外学界关于社会结构及人际关联的研究,一类是以西方的社会资本理论、社会网络理论、社会交换理论等为代表的研究,一类是中国本土学者从自身的文化和社会传统所展开的本土性研究。相比较而言,本土学者的研究理论具有更强的解释力,与本土的现实也具有更高的契合性。在西方,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较早使用“社会网络”概念阐述社会结构中的人际关联,认为社会结构象是一个网络,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接触看起来就象是网络中结点之间的关系;关系有强、弱、无之分,正如人际交往中交往频繁、关系一般以及从不来往的现象[1]。美国人类学家许烺光采用结构分析法和内容分析法,比较中印两国家庭制度,分析中国人“情境中心”的处世态度,认为“中国人的家庭由一种死亡也无法割断的纽带连接在一起,因此家庭中无论哪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都是由一个成员对另一个成员的责任和义务之类的观念支配着”。所以,中国人家庭具有更大的凝聚力和连续性[2]。杜赞奇提出“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认为权力的文化网络是指乡村社会中的政治权威体现在有组织体系和象征规范构成的框架之中,包括在宗族、市场等方面形成的等级组织或巢状组织类型,还包括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网[3]。随后,各种理论层出不穷,如符号互动论、戏剧论、日常生活方法论、社会交换理论等。在中国,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认为,中国人的社会结构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击的就发生联系”。“熟人社会”理论认为“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4]梁漱溟的“伦理本位”认为,中国人不讲自己、处处尚情,突出了中国人和谐、内聚的人际关系特征[5]。林耀华认为,人际关系处于类似橡皮袋和主干的网络体系中,在均衡与不均衡间摇摆,并总是试图达到平衡,平衡受内在关系和文化环境两方面因素的影响[6]。毫无疑问,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为我们认识乡村人际关系或中国传统人际交往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结论和方法论的启示。但西方理论在解释中国人人际关系时难免出现“橘逾为枳”之嫌,而中国学者又多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去发掘人际关系的潜在意蕴,很少从乡村社会结构与人际关联的关系角度探索社会结构的变化对人际关联的影响,笔者拟对此作进一步思考。
人类对人的认识实际上是将人放在了一定的社会之中,单个的人是无法谈论人类的共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生来就必然要组成一定的社会,必然要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群体之中,社会群体的组合形成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并将这种关系融化于人的生存之中。人的必然社会性决定了社会群体社会化的客观必然性,也决定了人际关联的社会性。马克思指出:“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7]埃利亚斯(Elias.Canetti)说明了个人与社会的相对性,即“群体之于单个个人即我们所谓的‘个体’的关系,个人之于人类群体即我们所谓的‘社会’的关系”,并且“人是在与他人的联系中并通过这种练习改变了自身,他们在彼此的关联中不断地塑造和改造自己——才根本地刻画了人的交织化的特征”。[8]西美尔从人的社会化角度分析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认为个人只不过是各种社会的联系连接的地方,个人人格只不过是实现社会联系的特殊方式,因为人们意识到整个人的行为都在社会之内进行,没有任何行为能够逃脱社会的影响[9]。马克斯·韦伯从个体与社会文化的追求视角分析了两者的生命力和历史地位,认为任何一种社会追求,如果不是社会中每个个体的追求的简单迭加,而是该社会文化产生的精神追求的体现,那么这种追求必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如果这种追求同时由于历史的进程并行不悖,那么它必然会取得应有的历史地位[10]。由此可知,人类是社会化的个体人际关联的聚合,只有在人际网络之中,依赖社会结构,才能生存和发展。也就是说,人际关联寓于社会结构之中,社会结构决定着人际关联模式。
笔者认为,乡村社会结构是指乡村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多方面结构状况的集成状态,反映着农民中不同群体之间相互联系的基本状态,决定着农民应对事件的能力。传统乡村社会结构单元至少包括这样几个结构性因素:乡村共同体、宗族、宗教、通婚圈、水利协作圈、武装自卫圈等。现代乡村社会结构在前者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因素:经济圈、民间组织圈。乡村人际关联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人与人交往关系的总称,而是指具有行动能力的农民群体之间的联系,是一种“社会化”的乡村人际交往。这种“政治社会化”的联系影响着乡村的秩序,激发乡村社会结构重构,以不同方式及实现形式塑造着每个农民在村落共同体中的地位。
二、1919年前传统乡村社会结构与人际关联模式
关于中国乡村社会基本结构的研究,最经典的范式是西方理论界的“两个假设”:平野义太郎的“村落共同体假设”认为中国农村存在着“乡土共同体”,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村落以农村共同体为基础,以家族邻保的连带互助形式实施的水稻农业要求以乡土为生活基础,以生命的协同、整体的亲和作为乡土生活的原理;主张村落在农村生活中的农耕、治安防卫、祭祀信仰、娱乐、婚葬以及农民的意识道德中的共同规范等方面具有共同体意义[11]。施坚雅的“基层市场共同体假设”认为单纯的村落无论从结构上还是功能上都是不完全的,构成中国乡村社会基本结构单元的应该是以基层集镇为中心,包括大约18个村庄在内的具有正六边形结构的基层市场共同体[12]。中国学者则从村落文化出发,以伦理本位为基点,以“家”为人际关联的基本空间单位,提出了乡村人际关联的“差序格局”。[4]各种论述对传统乡村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定位不同,但是,共同点在于传统乡村社会是一个内聚性和相对封闭性的共同体。农民的经济活动、乡村治理和文化习俗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圈子中进行,有着共同的行动方式和生存状态,稳定的乡村共同体是他们日常生活的行动单位。
实际上,在传统乡村,不管人们生活的圈子直径有多长,封闭性和内聚性是一种常态。人们之间的关联只是一种日常交往,寓于日常生活中。而“日常生活是以个体的家庭、天然共同体等直接环境为基本寓所,旨在维持个体生存和再生产的日常消费活动、日常交往活动和日常观念活动的总称。”[13]所以,传统社会,居住在闭塞乡村里的农户“安土乐居”,村民之间、乡村社会与外部世界之间经济与社会交往极为有限,“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反映了乡村社会结构的封闭性和乡土性特征。
封闭性和乡土性的社会结构决定了血缘和地缘是传统乡村人们最为主要的社会关系纽带。血缘的天生性使每个农民从出生之日起就置身于某种血缘关系网络之中,而地缘的不流动性则形成了聚族而居的习惯。费正清认为:“从社会角度来看,村子里的中国人直到最近主要还是按家族制组织起来,其次才组成同一地区的邻里社会”。[14]由此,形成了传统乡村社会的人际关联模式:宗法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
宗法制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父系家长制为内核,以大宗小宗为准则、按尊卑长幼关系制定的封建伦理体制。宗法社会中,家族是具体的核心组织,以血缘为纽带,依据一定的原则组织起来并开展活动。乡村日常生活主要是以家族或宗族为群体边界,家族边界是清晰的、稳固的,表现在:农业和手工业以家庭或家族为单位,以性别为分工完成生产和再生产。一般的生产活动和消费活动总是在“血缘圈子”中展开。
地缘关联是指没有血缘亲属关系的人们之间由于居住的生存空间的比邻而发生的各种各样关系的总和。大多数农民终生居于村落,生活在家族遮蔽之中,对他们来讲,乡村就是一个不流动的惰性社会。“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4]地缘关联有两个范围的界限,第一是村落内部。人们集聚在一定的寓所族群而居形成亲密的邻里关系,“远亲不如近邻”。扩大的邻里则至村落,“几十户、几百户乃至上千户的居民,比屋而居,烟火连接,组成一个村落。这种村落,北方叫‘庄’、‘屯’,南方多叫‘塆’、‘冲’等等”。[15]第二是村落外部。由于人口繁殖,土地面积限制,乡村出现“细胞的分裂”,人们奔走他乡谋生,迫不得已自动切断了乡村自然的人际关联。另外做官、出外经商、逃难等行为也将个体与村落剥离。离开村落进入一个没有血缘关联的环境之中,人与人之间交往成了契约关系,但是并没有切断地缘情感,乡民在外地总会依其地缘关系构造一个亚社会结构,地缘关系仍然是一种极为重要的社会联系网络。
三、1919—1949年近代乡村社会结构与人际关联
近代以降,作为现代化特征的工业化、商业化、民族国家建设以及现代交通运输的发展,是对农业社会传统结构的反动力量,解构了乡村社会基本共同体的封闭、内聚和自足性,改变了乡村社会结构。以下重点分析国家政权建设对乡村社会内聚性的破坏。20世纪20年代,地方政府权限伸张,地方政治现代化发展迅速,村庄组织在内部半无产化与国家权力渗入的双重压力下瓦解崩溃,即使仍然把原来的权力组织——村公会维持下来应付国家政权的入侵以及赋税负担的加重,乡村共同体与国家的关系仍然处于紧张状态。国家政权与村庄共同体关系的剧变,使地方上的土豪和恶霸有了滥用政权蹂躏村庄的机会,导致旧的国家、士绅和村庄的三角关系转变成了一套新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在乡村,新的社会政治结构出现了[16]。如杜赞奇认为,随着国家政权力量的渗入,乡村社会中充满着“赢利型经纪”,“他们大多希望从政治和村公职中捞到物质利益。村公职不再是炫耀领导才华和赢得公众尊敬的场所而为人追求,相反,村公职被视为同衙役胥吏、包税人、赢利型经纪一样,充任公职是为了追求实利,甚至不惜牺牲村庄利益”。而且原本“有声望的乡村精英不是逃离村庄,便是由富变穷,那种名副其实的保护人在逐渐减少”。[3]村庄内部不断分化,宗族和村政权日益缺乏强有力的聚合作用。
现代商品经济活动渗入村落和国家政权建设破坏了基层共同体的内聚特性后,乡村社会不再保持原来静止、封闭和单质的特征,已经被纳入整个国家政治的变迁体系之内。传统乡村人际之间血缘和地缘关联处于迅速的松动状态,渗透着国家政治的质化特征。杜赞奇认为,“随着国家政权的深入,捐税增加,村务扩大,这使宗族之间的争斗更为激烈”。[3]可见,当国家政权为了获得行政费用而建构村庄行政组织后,宗族关系日益恶化,村社内部关系日趋紧张。于建嵘认为,“民国的族权更多的是一种经济的强制”,“宗族缺乏对族人进行人身限制或惩罚的权力”。另外,“绅权开始变质,从民众自愿的服从发展成为以暴力和强权为基础的地方恶势力”。他们“与官府及宗族组织相互勾结,巧取豪夺,横行乡里”,[17-20]不再是发挥稳定村庄公共责任得以实现的财政承担者,也不再维护村民的生存和安全,更不是巩固村社内聚及相应秩序的组织者。因此,村民没有了依附的对象,其人际关联一步步走向分散化。
四、1949—1978年乡村社会结构与人际关联
国家政权建设在明确和强化基层村庄共同体边界的同时,却破坏了村庄共同体的内聚特性,这一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的国家政权建设中体现得更加明显,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把村庄共同体的边界划分得一清二楚,但是同时也把村庄共同体的内聚力剥夺得一干二净,尤其是在人民公社时期。农村人民公社体制实行“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行动战斗化”,公社既是乡村基层政权机关,又是经济生产单位,集政治、经济、文化于一体,管理本辖区的生产建设、财政、贸易、民政、文教、卫生、治安、武装等一切事宜。公社垄断了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以及各种发展资源,社会意识形态高度政治化,整个农村社会生活几乎完全依靠国家机器驱动。而且为了实行特定的政治经济目标,国家政权开展了一系列政治、思想、文化运动对乡村社会进行了全面的社会动员。总之,这一时期乡村治理的方式是国家及其代理人垄断了乡村社会的全部权力,控制了乡村的一切资源的“集权体制”。
在公社体制下,国家权威打破了农村社区的人际边缘的界限,用强制手段加强了社区之间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联系。超血缘关系的劳动组织和统一指挥的生产经营活动弱化了家庭的生产职能。只有国家的权力,而没有社会的权力,或者说,社会的权力由国家权力强制表达出来了。这样的政治生态环境将农民融入革命和建设的潮流中来,整个乡村社会沿着高度集中的、政治化的轨道运行,笼罩着浓厚的政治气氛。一切事物都被置于政治的标准下进行衡量,农民之间以及农民与组织之间的关联镶嵌着浓厚的政治色彩。
五、1978年改革开放后乡村社会结构与人际关联模式
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农村进行了历史意义的巨大变革,乡村社会在经济生活、社会结构、政治文化形态等诸方面都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一过程必然对传统的乡村社会结构产生影响,并决定着乡村人际关联模式的型构。在经济方面,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彻底改变了乡村社会的结构形态,使中国乡村社会走向了利益分化与整合的过程。首先,农民在经济收入上得到大幅度提高。其次,农民收入结构出现多元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收入在全部收人中的比重逐年下降,而来自非农产业如个体经营、本地和外出打工、在乡镇企业就业等的收入日益成为农村居民收人中非常重要的来源。最后,以前那种“平均的贫困”不复存在,乡村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在社会体制上,村民自治制度逐步推行,各种民间组织如农民协会、农民合作基金会及其他宗教、宗族、社会经济组织开始出现或复兴。
乡村受行政权约束减弱后,农民人际关联呈现两种模式:一种是“原子化”模式。农民横向之间不存在基于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中的内在联系,成为分散和孤立的个体,极少为共同利益达成有效的合作,农户们仅仅只是基于“土地”的联系和“行政隶属关系”的联系,才在同一农村社区中生产和生活。这集中体现在农民经常说的一句话:“现在大家都忙着各自挣钱,都不怎么关注集体的事,没人能把大家组织起来”。因此,村民间人际关联逐渐松散、疏远。这是因为,小农分散经营以及外出务工人员增多,导致农民交流渠道减少和交流时间缩短;现在需要农民集体参与的社区政治、文化活动很少,不用合作抵御自然灾害,不需合作进行农业生产,这无形中缩小了农民交流的平台;农村生产、生活的很多环节都已实现现代化,即使没有他人帮助,农民也能正常生产和生活,致使村民缺乏交流的缘由。
另一种是“庇护关系”模式。“庇护关系”主要体现为农村家族主义的复兴。家庭承包责任制后,农民不易从村集体中获得生存与安全的保障,他们转而寻求家族的庇护,试图以重建家族集体主义满足他们生存理性和安全第一的伦理需求。实际上,依附家族寻求庇护是传统乡村社会人际关联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翻版,只不过这种庇护关系不仅仅存在于小农生产中,而是伴随农村政治结构的变化扩张到了政治参与、资源分配和利益表达之中,村民选举中家族主义功能的彰显就是明证。即使这样,家族主义在利益分化的农村中往往还要让位于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使家户的社会联系逐渐弱化。当然,同时也应看到,两种模式之间仍然保持着互相融合的关系,“人们是以个体为单位来追逐自己的利益,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人是在一种与世隔绝的环境中追求自己的利益,他在追逐自己的利益的过程中仍要与其他人发生种种社会联系”。[21]
六、未来乡村社会结构与人际关联演进趋势
通过不同历史时期乡村社会结构与人际关联的梳理可知:乡村社会结构的激变决定着乡村人际关联模式的嬗变,乡村人际关联以乡村社会结构为基础。那么,未来乡村社会结构与人际关联是何种状态?
笔者认为,随着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乡村村民自治制度将日臻完善,各类农村民间组织尤其是经济互助合作类以及社会服务与文化公益类民间组织,如农村专业经济协会、经济合作社、老年协会、扶贫协会、能人协会、维权协会等发展迅速。农民政治满意度与参与意识逐渐增强,对所在社区的政治环境和政府绩效有更高的要求,对政府政策和村民委员会的决定有自己的见解。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当部分农民的原始资本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并获得明确的体制与制度的支撑和充分的劳动力资源保障后,农村职业分化日趋明显,形成带有明显职业特征和不同身份地位的农村雇佣业(指农业和农村非农业临时工)、农村种(养)专营业、城镇打工业、农村个体工商服务业、农村知识分子(包括教师、医生、技师)、农村事务管理和农村私营企业等七种职业化的分工及相应的利益阶层。由此必然加速农村贫富分化趋势,改变农村资源的分配格局。农村高收入职业和富有阶层,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其社会参与意识和政治诉求逐步增强。但是,农村弱势群体的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问题也会日益突出,乡村群体性事件呈现蔓延趋势,乡村社会处在相对不稳定状态。
受社会结构变动的影响,未来乡村人际关联呈现出先赋性与契约性并存的特点:1)人际关联的“差序格局”依然存在;2)利益追求决定着个体之间关系的组合趋向;3)传统道德观消解使社会生活信任缺失。而这样的人际关联又呈现着平等性、开放性、流动性、竞争性和功利化、自我主义化、表面化、干群冲突紧张化的表象。这就决定了乡村社会:一方面是传统文化、传统信仰和传统行为的复兴和重生,渗透着现代工具理性的以家族为核心的血缘和地缘关系的亲密化;另一方面是以利益为追逐对象的功利主义盛行,人们之间在分割资源、赢取财富和货币原始积累的过程中,结成了不同的契约关系,依据不同的利益主体不断调整人际关联的对象。
因此,要使农村社会结构要素之间平稳有序地互动,使具有共同乡土文化联系的村民之间的人际关联达到和谐状态,使其交往活动遵守共同规范和自觉形成集体认同,就要不断建立和完善各种能够合理配置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机制,并相应地形成各种能够良性调节社会关系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同时根据农村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的新表现、新特点和新趋势,不断创造和完善正确处理矛盾、问题和风险的新机制、新实体和新主体,以更好地弥合分歧,化解矛盾,控制冲突,降低风险,增加安全,增进团结,改善民生。简言之,当前最紧要的就是推行乡村社会结构制度建设,其路径包括以下两方面:
一是“公权力”约束机制建设。农民政治满意度与公共权力施行的尺度有着紧密的关系。基层公共管理机构不仅拥有大量处理公共事务的权力,还拥有土地(农用土地在经济学的意义上本来属于私人物品)的控制权。公共权力还渗透到一些私人事务中。过大的公共权力的寻租性导致权力人荣誉感弱化,将村民自治与巨大的利益关系纠缠在一起,增大了政治发展转轨的难度。所以,必须明确定位地方政府和基层政府职能,约束公权力的过度膨胀,打破“权力通吃”的局面。要把维护农村社会事业的公益性、保障农民基本公共服务需求作为其主要职责。建立面向社会建设指向的公共服务绩效评价体系,纠正地方政府和基层政府职能的异位、错位现象,解决片面追求GDP和政绩以及行为“企业化”、“公司化”的突出问题,粉碎“权力+资本”的自利型集团,改变公权与民争利的利益扭曲行为。更为重要的是使规约村干部行为制度化、法制化。处于最基层的村干部群体,“官”不大,却掌管着农村政务及村民生活的大事小情。一些村干部的违法违规行为直接侵害了农民切身利益,阻碍集体经济发展,破坏了农村基层稳定,酿成一些群体性事件,而且他们把权力作为牟利的工具,使党的惠农政策也就成了空中楼阁,严重损害党和政府在农民心目中的形象。尽管村民委员会的“四民主”制度已进入法制化轨道,但是现实中难以落实,农民仍然希望国家能够履行政府对村干部权力的制约职能。
二是“民生”保障制度建设。实现乡村社会稳定,必须解决好民生问题。民生是指农民基本的生存状态以及基本的发展机会、能力,就基本生活状态来讲指的是农民基本生存的底线问题。农民要有尊严地生活是一个基本底线,涉及到社会救济、最低生活保障、基础性公共卫生等等问题;就基本发展机会和发展能力来讲,农民不仅要有尊严地生活,而且还要有机会和有能力生活,涉及到充分就业、必要的职业培训问题等等,还包括更高层的社会福利问题,比如免单教育、住房等保障制度普及到每一个农民,都应该是民生改善的总目标。所以,必须把实现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作为解决农民民生问题的突破口,立足加快建立公共服务体制,建立健全社会救助制度、医疗卫生制度、养老保障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一系列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从根本上消除改善民生的体制性障碍。建立面向农民民生的财政体制,以制度化、法制化保证政府对农村的财政投入,连续和持久地关注和解决农民民生问题。创造平等的就业机会,提高农村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尽可能使所有农民能够从劳动市场获得比较接近的劳动报酬。
[1]郑思明,程利国.从社会网络分析的视角看青少年的人际关系[J].集美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4,5(1):53-57
[2][美]许烺光.宗族·种姓·俱乐部[M].薛刚,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53.
[3][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16﹑114-115、135、76、143.
[4]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9、26﹑70.
[5]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多维视角中的社会行为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344-346.
[6]林耀华.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220-228.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卷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1.
[8][德]埃利亚斯·卡内提.群众与权力[M].冯文光,刘敏,张毅,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29.
[9][德]盖奥尔格·西美尔.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M].林荣远,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2.
[10][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彭强,黄晓京,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
[11][日]平野义太郎.作为北支村落基础要素的宗族和村庙[C]//东亚研究所.支那农村惯行调查报告书:第一辑.1943,油印本.
[12][美]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M].史建云,徐秀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13]衣俊卿.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32-33.
[14][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20.
[15]雷家宏.中国古代的乡里生活[M].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7:2.
[16][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2000:284-317.
[17]于建嵘.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39、140-141.
[18]仇小玲.从“叫人”到“雇人”:关中农村人际关系的变迁[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5):87.
[19]胡双喜.农村人情现象解析[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9(6):55-60.
[20]闫丽娟.社会转型期中国农村人际关系的变迁[J].长白学刊,2007(6):59.
[21]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255.
Evolution of rural social structure and interpersonal association
ZHANG jian
(School of Politics and Management, XianYang Normal College, Xian Yang 71200, China)
The interpersonal association is on the basis of social structure that restricts the interpersonal association mode.The blood and region are most major social relationship in a closed village.The village scattered continuously in rural commodity in modern age, the national political power destroyed the grassroots community so that the clan and village regime was lack of cohesion.The peasants were in administrative relationship in the people commune system.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up, “Shelter and atom” were two main relationships among peasants in a village weakened by administrative constrain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association is ascribed and contract.Strengthening peasant's livelihood system and public power restriction are one important way to rural harmonious society.
countrysida; social structure; interpersonal association; democracy
C912.3
A
1009-2013(2010)05-0031-07
2010-09-13
陕西省教育厅科研项目(09JK276);咸阳师范学院科研项目(08XSYK303)
张 健(1969—),男,陕西长安人,副教授,管理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政治与农村社会发展。
陈向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