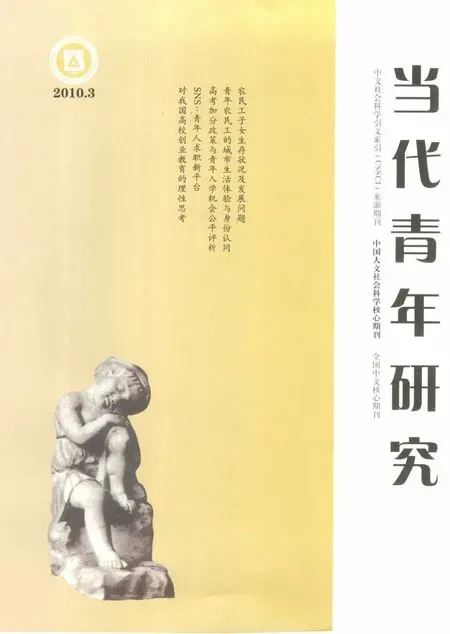青年农民工:主动排斥与被动排斥
◎邱 利
青年农民工:主动排斥与被动排斥
◎邱 利
本文从文化公民身份的视角,采用实证的方法分析了青年农民工在城市中受到排斥的因素:一方面,从小习得的文化习惯和城乡的文化差异,加之城市的生存成本使他们有意识地排斥城市的主流文化;另一方面,户籍制度因素、政策执行中的人为因素、城市交往中的理性化因素也将他们排斥于城市主流文化之外,这种主动排斥与被动排斥的双向互动过程让他们缺少对城市的归属感,遭受 “二等公民”待遇。
青年农民工 排斥 文化公民身份
一、研究背景
据《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5号)》,显示30岁以下青年农民工占52.6%。在这些外出从业劳动力中,初中文化程度占70.1%,高中文化程度占8.7%,分别比上一代农民工高出8.5个百分点和2个百分点,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1.3%。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务工青年涌入城市,“民工潮”这一现象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很多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入的探索,比较有代表性的如推拉理论,社会冲突与社会排斥视角、现代性视角。随着学界对农民工问题的进一步关注,加之媒体对农民工讨薪事件的进一步曝光,国家陆续放宽了对农民工入城制度的限制,并相应出台了一系列旨在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政策。表面看来,外在的制度性环境宽松了,但农民工仍然被称为“流民”,缺少对城市的归属感,依然被排斥在城市文化之外,那么这种排斥究竟是制度的原因,还是文化使然,是单方的被动排斥还是主动排斥与被动排斥的双向互动过程,本文意在通过实证分析对上述问题作出解释。
二、概念界定和文献综述
在以往的研究中,对青年农民工这一群体定义各不相同,王春光(2001年)认为,所谓新生代农村农民工含义有二:一层含义是他们的年龄在25岁以下,于20世纪90年代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村流动人口,与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在社会阅历上有着明显的差别;另一层含义就是他们还不是第二代农村流动人口,而是介于第一代与第二代之间过渡性的农村流动人口。由于按年龄划分具有一定的牵强性,而且标准不一,本文借用目前网上比较流行的一个词汇“80后”来界定青年农民工这一群体,并且将这一年龄段的已婚群体排除在外,所以本文的青年农民工是指80后的未婚农民工群体。
公民身份意味着接纳和排斥。对公民身份的定义,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马歇尔的公民身份理论,马歇尔的公民身份包括三部分:民权,政治权利,社会权利。在《公民身份与社会阶层》一书中,马歇尔将公民身份定义为:国家对作为整体的社会成员的一种接纳。随着公民身份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公民身份在马歇尔理论的基础上扩展为四个维度:合法地位,权利,(政治)参与,归属感。但是传统的公民身份理论也受到了很多人的批评,比如对妇女、土著居民、少数民族、宗教少数派、同性恋群体等许多群体而言,尽管他们也有共同的公民资格,但仍然感到自己被排除在“共同文化”之外。这些群体感到自己被排斥,不仅仅由于他们的经济地位,而且也因为他们的“文化身份”,即他们的差异性。越来越多的理论家认为,公民身份必须考虑到差异性。所以很多学者将研究的视角转向了文化,提出了文化公民身份理论。文化公民身份最初被看作是文化赋权,即有效地、创造性地和成功地参与民族文化共同体中的权力,并且假定这种文化共同体的文化是一种统一的、均质的、整合的民族文化。随着多元文化主义和后现代研究的兴起,尤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跨国、跨地区移民流的加大,阶层、性别、种族等问题不断冲击着传统的公民身份理论,因此,公民身份的概念不能再局限于一个法律框架之内,也不仅仅指公民对国家的文化归属感以及参与到一个民族或一种文化之中,而是一种多重文化归属感,公民身份具有多重性、复杂性和矛盾性。本文试图运用公民身份这种多重性、复杂性和矛盾性来揭示青年农民工在城市遭受排斥,无法获得文化公民身份的原因,认为这种排斥是一种主动排斥与被动排斥的互动过程,这一过程通过法律制度并在日常生活的交往互动中体现出来。
国外对农民工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其合法地位的缺失——户籍障碍——以及由此导致的一系列权力的被剥夺。由于不具有城市户口,他们(农民工)根本没有“资格”享有城市中的正常生计,没有“资格”享有城市居民作为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加以接受的那些社会福利和服务。因此,对于进入城市中的农民流动者(农民工)来说,根本问题不在于直接去争取维持生计的收入、福利、服务等,而是争取获得这些待遇和机会的“资格”,也就是争取“公民身份”。如同国外的研究一样,国内对农民工的研究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户籍制度,对于农民工,要获得合法地位(城市户籍),至少要达到一定的学历并且具备一定的财产。由于全球化、多元文化主义的影响,公民身份是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不断变化的,是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势下不时扩张或收缩的,因此,对农民工获取公民身份的研究不能仅仅从户籍角度作线性研究,它是国家、市民社会(市场)、“农民工”、城市居民等等之间的一个复杂的互动过程。总体来说,国内外从公民身份角度研究农民工问题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许多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很具有启发性,但以往的研究过于强调刚性的制度(如户籍)因素,而忽视了软性的文化因素在公民身份认定上的重要作用,所以本文意在从文化公民身份视角探讨青年农民工问题。
三、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个案访谈法,2008—2009年寒假期间在笔者老家访谈12人,2009年12月在厦门访谈6人,共访谈18人,其中男15人,女3人。
四、调查发现
(一)被动排斥
1.制度性排斥
主流学术界认为,户籍制度因素是造成城乡二元分割的主要障碍,由于户籍制度的刚性规定,导致农民工缺少合法的地位,在法律地位上处于不利境况。由于中国户籍制度的长期存在,农民工只能凭借“暂住证”等作为城市短期临时流动人口,遭受“二等公民”待遇。户籍制的存在使中国形成了等级制的公民身份体制,通过城市中三种公民等级的比较发现,农民工无论在合法地位还是在住房、社会福利、子女受教育等权利上都处于最不利的地位。诚然,户籍的存在不仅仅意味着“城市”、“农村”的概念意义,而是具有了一种刻板的符号意义,农村已经不再是宁静田园生活的代名词,而具有了经济落后、愚昧、教育水平落后等一系列意义,农民已经是一个被“污名化”的概念。在传统的封建社会,在重农抑商的潮流下,农民拥有很高的地位,务农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随着市场经济的引入,城乡差距逐渐拉大,传统上勤劳勇敢、善良、朴实的“农民”这一概念早已经失去了其原本的内涵,农民被划入了弱势群体的行列,而农民工更是成了弱势中的弱势,被排挤于城市文化的边缘。尽管如此,在访谈中笔者却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悖论:虽然学术界和政府认为户籍制度是造成农民工地位缺失的主因,青年农民工自己却并没有过于看重户口因素:
户口倒是没有这些问题吧。因为现在户口不是很大的问题,现在农村的小孩也可以在城市里面上学。而且你有能力在厦门买房子的话你户口完全可以迁过来,所以户口问题还是比较少去考虑的。(CJP龙岩)
如果在城市里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还可以,如果没有稳定工作(户口迁到城市也没有用),庄稼人怎么也得有个养老的东西啊(土地)。(ZJ承德)
无论如何,青年农民工对户口的看法是基于现实条件的一个理性选择的结果。他们心里很清楚,如果想在城市立足,仅仅靠一个城市户口是不行的,虽然他们进城务工是希望在城市寻找更多的机会,但他们并不贪心,处于生计考虑,他们将土地看作是自己最后的退路,虽然表面上他们抱怨务农如何辛苦,农村土地如何大面积地荒芜,但土地在他们心中时时刻刻都存在着,土地是他们最后的一颗救命稻草:
在城市的话必须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没有房子就一个户口在这一切都无依无靠,没有稳定工作的话,也很悬。按他们老人的说法,你再怎么样得有一口饭吃吧。(QJQ三明)
所以尽管学术界一再呼吁打破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政府也在逐步尝试放开户籍制度的限制,但笔者并不认为户籍制度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关键,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城乡不断拉大的差距,一个城市户口对于青年农民工来说可能只是一纸空文。
2.政策执行中的排斥
随着进城务工人员的不断增多,各种拖欠工资事件不断出现,国家也出台了一些旨在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政策,但往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发生了扭曲,拖欠或变相拖欠工资现象仍然屡见不鲜:
人都比较冷漠,对政府不是很放心,比如打工要不到钱的那种,对于这些事情(我)一般看看新闻,听老乡讲一下啊。比如去年我们在××校区,去年的下半年,那边要建学校,当时那里是开发区嘛,当时政府是主导开发的,(我们)给他们(政府)打工,,但是干活之后拿不到钱。当时老板不给钱,找政府,政府又推给他们(老板)。本来就不多嘛,一年最多几千块上万块,拖了好几个月,工友基本上把(自己身上的)钱都花完了,还是拿不到钱。实在没办法就去堵学校,把学校校长堵住了,校长没办法,再找,后来解决了,但是钱还是没有拿到他们该有的那些,还是打折扣了。还有有些政府为了面子工程嘛,你找他们他不理你,你去找记者,找劳动执法部门(都没用),毕竟来说他们还是要听政府的嘛。除非你自己比较有实力,认识的人多,能够帮你。要是你什么都没有,你有问题根本就没人帮你。(QJQ三明)
青年农民工作为城市中的弱势群体,他们一没技术,二没文凭,更无成熟的人际关系网,在城市里无依无靠,小问题可以请工友或老乡帮忙,而遇到拖欠工资等权益受到侵害问题时只能依靠政府的帮助。政府作为最有权力的机构,他们理应站在客观的立场上维护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的利益。但政策制定出来了,究竟执行效果如何?政府部门是否真正能站在农民工的立场上考虑问题,而不是为了部门利益或面子工程去损害农民工利益,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政府的不作为只能让他们对城市对政府逐渐的失望甚至产生敌意,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
那些政策对于我们打工的来说都是虚的。对政府不信任,别说那些报纸都是在帮政府说话,(打工者)说出来了,但是被听到的声音非常非常小。(QJQ三明)
3.交往中的排斥
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是通过语言组织起来的,在这个世界里,我们能在由语言表达的文化同一性意义上实现自我认同。在哈贝马斯看来,真正的合理性应内在于交往行为中,因而社会整合只能建立在交往理性之上,只有通过理性交往才能达到对文化的共同界定,形成社会团结和个性人格。交往和沟通才能够增进彼此的了解,建立双方共有的交往文化。青年农民工之所以被排斥于城市文化之外,这与他们的交际网络有很大的关系,而这一关系又是由主客观因素所决定的。客观上,青年农民工大部分时间被工作所占去,仅剩下的一点时间一般用来休息,有的工作还要白班晚班倒换,这样的工作强度使得他们没有时间去接触城里人,所以身边交往的圈子只是工友或者老乡。客观上经济因素也很重要,青年农民工的经济收入限制了他们交往的圈子:
我觉得我没必要去交往。我的经济状况不允许我去交那么多朋友,朋友出去玩肯定要花很多钱,觉得把时间浪费在玩上有点不值。(CJP龙岩)
有时候,青年农民工渴望与城里人交往,但往往缺少交往的途径,其中一个访谈者的谈话很有意思,他认为城里人的交往具有功利目的:
没有(和其他人)交往的渠道啊,没有认识本地人的渠道啊,现在不可能无缘无故地去跟人家交往啊,你跟人家打招呼人家还以为你是神经病呢。现在感觉你要是和某个人接触,多少有一点利益关系嘛,他从你这边不能获得什么好处的话也没必要跟你联系,有一种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他会想你这人值不值得利用,然后我才跟你交往。两个人都感觉不能从彼此身上获得什么东西,感觉你没什么能帮得上我的,我也没什么能帮得上你的 (就不会交往了)。(QJQ三明)
城市里虽然接触的人多,但往往不像农村那样“有人情味”,那样“交心”,城市的交往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农村则是“血浓于水”。城市交往的功利性是基于理性考虑的结果,在今天这个关系就是生产力的时代,城市竞争的压力让城市人努力扩展自己的人际关系网,但这种关系靠利益来维持着,一旦这种利益关系结束,这一条交往的关系链也就断开了。这是城市中世俗化和理性化的明显体现。而本来处于弱势地位的青年农民工由于无法与城里人建立利益联系,所以交往也就无从谈起。他们虽然渴望与城里人“交心”,渴望彼此被接纳,却也无可奈何:
人跟人之间越来越冷漠嘛,到时候你热脸碰人家冷钉子,感觉很那个。干脆就各顾各吧。像我们都有别人的电话,但联系得不多。一个月两个月不发一条短信的都很多,但是电话号码都有在,基本上没什么事就不打。(QJQ三明)
(二)主动排斥
城乡固有的文化差异会让进城的青年农民工对城市有一种本能的陌生和排斥。这种文化差异既有客观的,比如语言、教育程度、生活方式上的不适应,也有主观的,比如心里的自卑感。“发生在文化上根深蒂固的预先理解之背景中。这一背景毫无疑问是作为整体延续的;知识储备中只有行为参与者在特定时间里使用和陈述的那一部分才被检验。在由参与者自己所作的环境定义内,这个生活世界中的(被检验的)陈述部分是由参与者们以对自我更新的环境定义的协调来处理的。”青年农民工从小习得的是一整套的农村背景文化,这种背景文化已经深深嵌入他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表现在语言、生活习惯等等:
还是农村好,在农村盖几间小房,有个小院子多好。城市太乱,经常上楼,觉得特别别扭。去年开奥运会,我住在北京我姐夫那,在8楼,(去洗手间)怎么用那个便桶也不舒服,没办法只好到楼下去方便,感觉特别不习惯。(ZJ承德)
那时候我从家里刚出来时,普通话不是很好,我们在家都说家乡话,而且都听得懂。我刚出去一两天我都不敢讲话,就怕别人听不懂或者笑话你。去了以后跟别人讲话我也用了15天的时间去适应,才敢跟人家打招呼。(CJP龙岩)
除了客观条件限制外,主观的心理自卑感也让他们排斥于主流城市文化之外:
我觉得农村孩子没有城市里孩子那种优越感,可能自己感觉自己很像乡下人,心理状态一直没办法转变过来。像我们现在出来心理就会慢慢地转变过来,比如去商场,你也可以跟那些销售人员打招呼,要是家里面那些孩子出来的话,可能他刚出来他就不敢,比如别人问他一句话他就脸红了,或者说话结结巴巴的,感觉不自然。(CJP龙岩)
城里的孩子从小被认为是“见过世面的人”,城市里有高楼大厦,农村有的只是低矮的房子;城市里车水马龙,摩肩接踵,农村里有的是泥泞的道路,孩子从小接触的人群是村里的小伙伴;城市里有公园、博物馆、少年宫,农村里有的只是层层的大山或辽阔的原野。这种物质上的巨大差距让农村孩子从小就对城市生活充满好奇和向往,同时潜意识里有一种自卑感,这种自卑感在农村的同辈群体中并没有明显的体现,一旦离开农村,来到城市异文化环境里,在与城市人的接触和比较中,这种自卑感会愈加强烈。萨义德有明确的论述:我们采取的立场试图表明,每一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的存在。这种自卑感往往让他们在城市中失去了自己的定位,他们努力想与城里人交往却又因为自卑感而不愿意与城里人交往,而农村的文化习得又让他们主动排斥城市文化而不愿意改变自己已经有的文化习惯。这种文化习惯的养成一方面有家庭父母因素的影响,但更多的是农村大环境所使然,尤其是同辈群体的作用,这种作用通过日常交往体现出来:
(对孩子的影响)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比如在厦门这边有一个小孩那样做,其他小孩就会模仿,别的孩子就会受他的影响。父母对孩子也会有影响。比如说有些家庭不管小孩子,但父母的影响还是很小的,主要是环境因素。(CJP龙岩)
按年龄段来说吧,我们“80后”都感觉挺盲目的,城里面再怎么差也能读个大学,像农村就只能靠自己了,没有一个能够让我们模仿的对象,比如某个人能走这个路走成功了,城里人有这样的对象模仿,像我们农村就看不到(这样的人),看不到我们前面的那个目标。缺少一个标杆,一切都是靠自己慢慢摸索,很累,花时间也很多。(QJQ三明)
如此看来,同辈群体的影响是明显的,而且是潜移默化的。城市孩子从小接触人际面广,接触信息量大,竞争意识更强一些,他们有很多可以选择和模仿的“标杆”,农村孩子则恰恰相反。内在的文化环境的影响是长期的、隐蔽的,但外在的经济压力却是实实在在的,这些让他们对城市生活望而却步:
我们同事的话都是赚完钱回家盖房子,买房子厦门房子太贵了,根本买不起,像岛外市郊城中村里那种房子还差不多(能买得起)。市区的房子不是我们能买的,是像公务员那种有工作的才买,像我们打工的买房子根本不可能。(QJQ三明)
五、结论
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第二代农民工(青年农民工)出来务工不仅仅为了赚钱,他们更多的是想在城市寻找机会,寻找农村没有而只有城市才可能有的机会,但真正来到了城市,他们却不能被城市所接纳,仍然过着“流民”的生活。一方面,从小习得的文化习惯和城乡的文化差异,加之城市的生存成本使他们有意识地排斥城市的主流文化;另一方面,户籍制度因素、政策执行中的人为因素,城市交往中的理性化因素也将他们排斥于城市主流文化之外,这种主动排斥与被动排斥的双向互动过程让他们缺少对城市的归属感,遭受“二等公民”的待遇。法律上,青年农民工是中国公民,但在与城市的文化互动中,他们却被剥夺了这一公民身份的待遇。笔者认为,要真正给予青年农民工文化公民身份,最根本在于打破一直以来企图将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惯性思维,加大对农村的投入,缩小城乡差距,消除城市中心主义的优越感,让每个公民都能平等地参与,给青年农民工应有的话语权。
1.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322-323.
2.李强.关于城市农民工的情绪倾向及社会冲突问题[J].社会学研究,1995(4).
3.朱力.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J].江海学刊,2002(6).
4.徐晓军.返乡青年农民工的游民化风险[J].当代青年研究,2008(5).
5.李培林.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J].社会学研究,1996(4).
6.周晓红.流动与城市体验对中国农民现代性的影响[J].社会学研究,1998.
7.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J].社会学研,2001(3).
8.E.Isin&B.Tuner,2007,"Investing Citizenship:An Agenda For Citizenship Studies",citizenship studies,London:Rouledge.
9.Bloemraad et al,2008,"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Multicultralism,Assimilation,and Challenges to the Nation-State",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0.B.Tuner,2001,"Outline of a general Theory of Cultural Citizenship",in Nick Stevenson(ed),Culture and Citizenship,London:Sage Publications.
11.O.Aihwa,1996,"Cultural Citizenship as Subject-Making",Current Anthropology,Volume 37,Number 5.
12.Wu Jieh-min,2006,"Chinees Migrant Workers under Differential Citizenship:A Comparative-Institutional Analysis",one country,two societies?rural-urban inequality in contempory china,New York: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3.J.Solinger,1999,"Citizenship Issues in China's Internal Migration:Comparisons with Germany and Japan",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New York:The 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
14.陈映芳.“农民工”: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J].社会学研究,2005(3):721.
15.王小章.从“生存”到“承认”:公民权视野下的农民工问题[J].社会学研究,2009(1):133-136.
16.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17.Lu Wang,2009,"The urban Chinese educational system and the marginality of migrant children",Chinese citizenship,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18.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120-121;交往行动理论:128、135、141.
19.萨义德.王宇根译.东方学·后记[M].上海:三联书店,1999:427.
责任编辑 颜 波
D422
A
厦门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