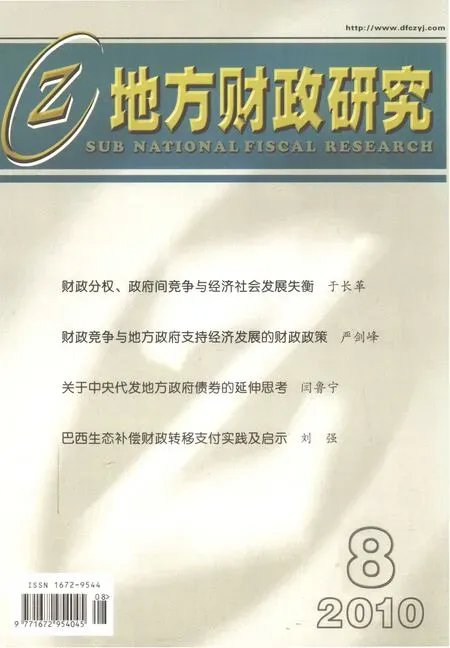积极探寻财政集权与分权的均衡点
本刊编辑部
集权和分权是矛盾的两个方面,过分强调集权则势必牺牲分权,过分强调分权则势必牺牲集权。建国以来,我国财政体制变迁大体上经历了集权模式-行政性分权模式-经济性分权模式的轨迹,具体对应着1949年-1979年、1980年-1993年、1994年以来等不同历史阶段。相当长时期内,就是这样一种简单循环:“一收就死,一放就乱”,不断陷入“条块”矛盾之中。
财政“两个比重”通常是衡量集权和分权程度的重要指标。“第一个比重”(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反映出政府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汲取能力,“第二个比重”(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体现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两个比重”呈现出“高-低-高”的“V”字型演化过程。分别以1995年和1993年为分界线,之前是由“高”到“低”的变化,体现出国家对企业、中央对地方的“双”让利倾向,之后是由“低”到“高”的变化,体现出国家与中央的“再”收权。
一个时期以来,有关财政“两个比重”的争论一直不休。一种观点,目前我国的宏观税负和中央财政集中度不高,认为还有提升的空间和必要;另一种观点,则得出了相反的判断和建议。一个国家,是集权还是分权,与该国的政权组织形式、政府职权范围、经济发展水平、地域面积大小、国内外政治和社会环境等因素密切相关,而且适度集权与分权的数量比例关系的确难以确定。20世纪90年代,国家以“20%”和“60%”作为“两个比重”的调控线,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到2009年达到了20.4%和52.4%(不含债务收入)。表面上,的确不高,尚有提升的空间。实质上,存在着计算口径的差异,即“第一个比重”中的财政收入是预算内的范畴,现实情况是大量的预算外、制度外收入客观存在,考虑这些因素这一比重大约在30%左右,超过了发展中国家所能承受上限25%近6-7个百分点;同样,如果考虑债务因素,“第二个比重”水平则为60%左右,其余多达4级或4.5级(视村为半级)地方政府分享收入40%左右,随着省市再集中,到县乡层面财政初次收入分配少的可怜。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我国财政的集中度、集权度与国情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适宜性。
从适度水平来考察,“两个比重”是一把“双刃剑”,“过高”则会产生“挤出”效应,加重社会经济负担,降低地方政府的努力程度,进而制约经济社会发展;“过低”则难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同时背离了市场经济条件下追求社会公共福利最大化原则。所以,适度降低“两个比重”,积极探寻集权与分权的平衡点,是构建和谐财政关系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