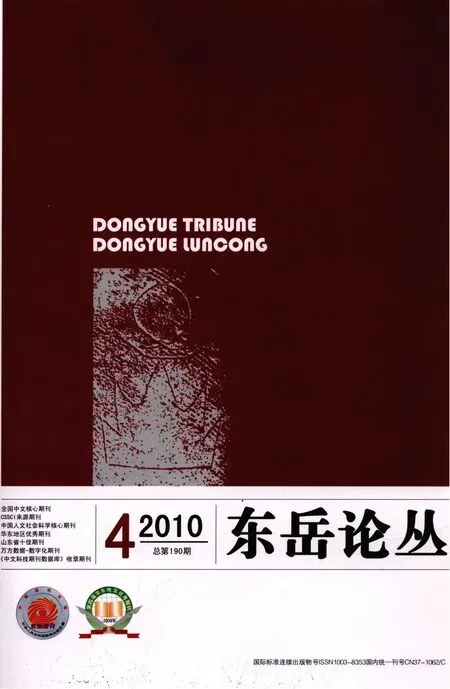六七十年代诗歌语言的口语化特点探析——兼及现代诗歌的口语入诗问题
胡 峰,张玉芹
(1.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 250014;2.齐鲁师范学院中文系,山东济南 250013)
六七十年代诗歌语言的口语化特点探析
——兼及现代诗歌的口语入诗问题
胡 峰1,张玉芹2
(1.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 250014;2.齐鲁师范学院中文系,山东济南 250013)
六七十年代诗歌中,俗字俗语的使用,语法句法的循规蹈矩,口语语体以及在辞格的运用上的不均衡现象共同构成语言的口语化特点。这种口语化特点适应了传递信息的基本功用,但与诗歌自身所需求的“诗家语”之间还存在一定的距离。如何使日常口语更好地转化为“诗家语”仍然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诗歌语言;口语入诗;六七十年代诗歌
在中国悠久的诗歌史上,口语化的语言风格古已有之,这在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表现得非常普遍;后来随着文人诗的逐渐兴起,口语在诗歌中的地位受到排挤。尽管仍有人坚守这一创作风格,但声势浩大地鼓吹口语入诗的现象直到晚清才出现。如黄遵宪率先提出“我手写我口”的倡议,与此同时,“言文一致”的文字改革运动遍及全国。20世纪初,胡适受此影响与启迪,不遗余力地推崇口语入诗,从而使得口语化成为现代诗歌的语言特征之一。盘点 20世纪诗歌发展的轨迹可以发现,诗歌创作中密集彰显口语化特征的现象发生在建国之后的六七十年代。这一历史时期的诗歌语言的口语化风格既与当时特定的诗学理念与历史氛围密切相关,更是与口语传递信息的现实功利性有着内在的勾联。但是,这种过度的口语化倾向与诗歌内在的审美本质之间也存在着相互颉颃之处。
一
胡适提倡的白话文学运动,既受晚清以来文化先驱追寻“言文一致”的语言运动的熏陶,又受英美意象派诗潮的鼓动。在他对白话文学进行理论建构和白话新诗“尝试”的实践中,口语成为整个体系的主要支柱。这从他对“白话”的界定中即可看出:“一是戏台上说白的‘白’,就是说得出,听得懂的话;二是清白的‘白’,就是不加粉饰的话;三是明白的‘白’,就是明白晓畅的话。”①胡适:《白话文学史》,《胡适文集》(4),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 17页。这三层界定中的前两个方面,都与“口说”直接相关。而这种依靠“口说”与“耳听”的方式产生并存在的语言形式就是“口语”。胡适一再强调:“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甚至还把这种见解整合进新诗的建设中去:“我们做白话诗的大宗旨,在于提倡‘诗体的解放’。有什么材料,做什么诗;有什么话,说什么话;把从前一切束缚诗神的自由的枷锁镣铐,拢统推翻:这便是‘诗体的解放’。”②胡适:《答朱经农》,《胡适文集》(3),第 78页。由此可以见出“口语”对胡适白话新诗的重要性。胡适之后,口语入诗的主张与实践在艰难中前行。如二十年代的陆志苇、左翼诗人以及抗战爆发后中国诗歌会的成员都进行过口语化诗歌的创作实践。这一努力在建国以后得到集中爆发,尤其在“民歌加古典”的诗歌创作原则确立以后的六、七十年代,几乎形成了口语化诗歌一统诗坛的格局。其时诗歌口语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俗字俗语”的集中涌现
口语入诗的表现之一,就是日常生活中的俗字俗语被整合进诗歌之中。早在晚清时期,黄遵宪就提出“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斑斓”(《杂感其二》)的设想,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也把“不避俗字俗语”作为文学改良的八项主张之一:“今日作诗作文,宜采用俗字俗语。”③胡适:《文学改良刍议》,《胡适文集》(3),第 28页。二十年代陆志苇曾有过“老弟呀,向前不到一箭路”(《航海归来》)之类的诗句,但这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并未形成普遍现象。而六七十年代的诗歌创作中,俗字俗语则呈现出“井喷”的态势,几乎是俯首即拾。如:
(1)年年有个七月一,/男女渔民笑嘻嘻,/庆祝党的诞生日,/满淀渔船飘红旗。//打上鱼来挑大的,/大的里头挑活的,/活的里头挑好的,/好的献给毛主席。①本文所引用诗歌大多转引自王家平:《文化大革命时期诗歌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以下不再标注。
(2)只要中国永远红,/老子流血乐无穷;/只要中国不变色,/老子死了也值得。
(3)“造反!”“造反!”/老子如今也要“造反”!/“造反”就是能渔利。只要削尖脑袋往里钻,不管昨天保
爷保娘保自己多卖力,/嘿!今天我也要打起“造反”旗!在例(1)中,“年年”、“有个”、“七月一”、“挑”、“大的”、“活的”、“好的”等词语均为远离文雅与正统的书面语而直接源自日常生活中的俗语俗话;例(2)中的“老子”更超出书面用语的范畴,而是沾染了江湖色彩的俗语粗话;例 (3)中的“爷”、“娘”同样是具有世俗意味的生活词汇。当然,在诗歌创作中如果诗人能够恰当地运用俗字俗语,可以增加诗歌语言的亲切感与感染力,从而有利于缩短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而更有益于传情达意;但是,如果不能很好地把握必要的尺度,也会出现流于粗俗或低俗的弊端。这种极端的现象在六七十年代的诗歌中也有所表现:如“混蛋”、“放屁”、“他妈的”、“狗屎堆”、“蠢猪”、“王八”、“破烂货”、“滚蛋”、“婊子”等。这些大量的带有侮辱、贬损色彩的低俗词语与诗歌这种高雅的文学类型之间显然是极为不协调的。可见,俗字俗语有着通俗、庸俗、低俗与恶俗等不同感情色彩与程度的区别,而诗歌并非对上述类型的所有语料都能兼容。
(二)文法上的循规蹈矩
在中国传统诗歌中就曾经出现过以突破文法常规的创新形式来营构特殊的情感空间与审美效果的诗句,如“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杜甫《秋兴八首》),“枯藤老树昏鸦,古道西风瘦马”(马致远《秋思》)等。前者以颠倒正常的语序来实现表达的新奇,而后者则通过几个意象性名词的排列来实现时空的跨越。这种故意“扭曲”语序与语法句法正常逻辑的诗句以“陌生化”的形式给读者造成了一种新颖独特的阅读感受,成就了其中国诗歌史上不朽的地位。而为了实现口语入诗的诗学理念,达到诗歌语言的通俗易懂与明白晓畅的目的,现代白话新诗的奠基者胡适在语法句法方面则更多地依“法”行事,也就是他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所强调的“须讲究文法之结构”。当然,这种文法结构也包括从英语语言中借鉴学习而来的资源,但基本上没有明显的逻辑、结构上的“扭曲变形”所带来的“陌生化”效果。显然,这与他所追求的口语入诗的目标密切相关。而六七十年代的诗歌口语化特征同样也表现在文法上的中规中矩,而很少出现故意突破语言常规的“独造”式的新句子,在其词语的排列组合上也固守常规,以最常见的方式来实现传递信息的意图。如:
(4)下乡去满满一担,/回店来一担满满;/送去了毛主席的关怀,/挑回来山乡人民的心愿。//你铁肩能负重,/你飞腿跑得远,/穿过多少饲养室,/走访了多少庄户院!
(5)火热的话语炽热的歌,/韶山的光辉暖心窝。//一颗颗红心向阳跳,/从韶山跃到金水桥……//临别喝一捧韶山水,/紧跟毛主席不掉队!
(6)大寨人的脾气就爱斗,/七斗八斗不停休!/……/斗得高山低了头,/斗得河水让了路。/斗得七沟八梁变了样,/斗得农林牧副大丰收。
这些例子中的诗句在文法上均无特殊之处,不仅词语的搭配与组合方式符合语言表述的自身逻辑规范与语法规则,而且主谓宾等词序的排列也切合自然的语序。这与郭沫若在《女神》中所运用的“一切的一,/一的一切”等独创诗句迥然不同。当然,也有一些诗句看起来好像有些“特别”之处,如:
(7)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向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联合,大夺权,/夺权夺权夺权夺权。/夺权!夺权!夺权!
(8)造反造反造反,/刀出鞘,弓上弦,/坚决斗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砸烂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反造反造反,/扬鞭纵马卷巨澜,/将“四旧”打个落花流水,/把牛鬼蛇神杀个片甲不还!/造反造反造反,/万马奔腾战正酣,/谁想阻挡我们前进,/嘿,就叫你铁蹄下化灰烟!
(9)打!打!打!打!打!/狠狠地打! ×××不投降我们就要打!/打!打!打!打!打!/准准地打!/舍得一身剐,把他拉下马!
其实,这些貌似“特别”的诗句尽管也出现了某一词语的重复使用,但这种重复并未造就诗歌语法句法上的新异之处,更没有形成表情达意的“陌生化”审美效果,只不过是某种情绪的过度宣泄而已,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与形式主义文论家主张“陌生化”是“对普通语言的有组织的违反”(雅各布森)这一策略的违背。
(三)口语语体的采纳
六七十年代诗歌的口语化特征还表现在诗意诗情的表达口吻上,它采用了一种口语体式的表达方式,假想了叙述对象或者倾诉对象的存在,以面对面交流的方式进行抒情叙事。这种情境的设定,一方面缩短了读者与抒情主体之间的距离,另一方面则有效压缩了书面语可能出现的空间,从而为口语的出场设定了一个良好的语境,更有利于口语特征的凸显。
(10)毛主席呵毛主席,/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岁月,/我们打开您的宝书,/眼前呵大道一行行!/当我们被走资派加上镣铐,/是您点燃文化革命的烈火,/烧毁黑暗的牢房;/当我们被工作组钉上黑榜,/是您斩断 × ×反动路线,/再次把我们解放!
(11)一颗颗红心在尽情地欢跳,/一双双眼睛仰望着您老人家的画像,/爹亲娘亲哪有您老人家亲!/沙深海深哪有您老人家恩情深。
(12)好哇!好哇!/就是好!/临时革命委员会,/让我们一千遍、/一万遍地为您大声叫好。
(13)战斗的 1.22呵,/你是一根孙大圣的金箍棒,/把一切牛鬼蛇神打得人仰马翻,/把广东搞得满城风雨,/大乱特乱!/乱声中,/各个阶级,/各个人物,/纷纷登台表演。
(14)卖报,卖报,/红色电讯报。/砸烂旧党委,/打到 ×××!/卖报,卖报,/革命造反报。/革命人民爱读它,/老保看了睡不着觉。
在例(10)、(11)中,作者设置叙述对象在场的情境,采用面对面交流的对话语体进行情感的表达与抒发,“您老人家”等称谓语正契合了抒情主体的谦恭、敬仰与感激之情;例 (12)、(13)中虽然赞扬的是一个组织团体、一个事件,但抒情者以拟人化的手法(主要是通过拟人化的称谓“您”、“你”来实现的)把它转化为“人”,即听众,因此也实现了对面交流的情境创设与口语语体的运用。例 (14)中的抒情主体以报童的身份出现,以叫卖声这种特定的口语语体来实现其表情达意的目的和用意。这种口语语体的大量出现,正是这一时期的诗歌在语言风格上具有鲜明突出的口语化风格的内在质素与外部表征。
(四)辞格使用上的不均衡现象
为了保证口语的通俗易懂、明白晓畅的特点,口语语言在辞格的使用上也有自己的特点,即一些辞格被经常使用,如比喻、拟人、夸张、借代、对比、引用、反语、排比、反复等。在常用的几种辞格中,出现的频率也并不均衡,而是有着极大的差别。如引用在这一时期的诗歌中使用的频率就非常高,而且引用的范围也极为固定,主要是领袖语录、诗词或者跟当前形势相关的特定话语,如:
(15)“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冲锋,/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冲锋,/胜利的红旗迎风招展!
(16)“宜将剩勇追穷寇”,/刀山火海无阻挡!/贫下中农意志坚,/海枯石烂心不变,/步步紧跟毛主席,/“敢叫日月换新天”。
这两首诗的引用皆来自领袖诗词;夸张的辞格同样也被经常使用,用来表达冲天的革命豪情与决心。如:
(17)天不怕,地不怕,/贫下中农力气大!/端来大海做平湖,/推倒大山垒大坝,/牵来银河遍地绕,/摘来彩虹把桥架。/挥动铁臂扭乾坤,/大批大干大变化。
(18)天山高啊草原宽,/登上天山望韶山。/拨开层层雾,/驱散重重烟,/南望韶山几万里,/一片金光看得见。另外,排比具有节奏感强,增强语言气势,提高表达效果的作用;而对比则能把相互对立的两个事物表达得更加鲜明,更容易激起读者的爱憎分明的情感,因而这在六七十年代的诗歌中也经常被使用。但是,即使出现频率极高的比喻这种辞格,无论是明喻、暗喻还是借喻,也更多地偏重于本体喻体之间的自然联络与过度,从而产生一种形象性的修辞效果。如:
(19)红日出云光万道,/东风万里传喜报。/全国山河一片红,/红旗如海歌如潮。
(20)一夜桃花开万山,/树树燃起红火焰,/毛主席站在高山顶,/一轮红日当头悬。
(21)离“我”远一寸,/干劲增一分,/离“我”远一丈,/干劲无限长,/“我”字若全忘,/刀山火海都敢上。
不过,这些都是“近取譬”,即本体喻体之间有着显而易见的关联,而 20年代早期象征诗人李金发所使用的“远取譬”则罕见其踪迹。“所谓远近不指比喻的材料而指比喻的方法,他们能在普通人以为不同的事物中间看出同来。他们发现事物间的新关系,并且用最经济的方法将这关系组织成诗。”①朱自清:《新诗的进步》,《新诗杂话》,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第 2页。与之相似的是,通感、双关等这种能够给人以新异独特之感、增强凝练含蓄与跳跃性的辞格也极为鲜见。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其实也和诗歌的创作者侧重于情感的表达与抒发而非美感的传达有着密切的关系。“艺术作品尽管自成一种协调的完整的世界,它作为现实的个别对象,却不是为它自己而是为我们而存在,为观照和欣赏它的听众而存在。”②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9年版,第 335页。正因为有着明确的与读者交流的意识与目的,再加上当时正处于激情澎湃之中的读者也期待以诗歌来提高自己的情绪与斗志,而无暇沉溺于含蓄蕴藉的美学享受中去,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的双重需求自然会导致诗歌作品在修辞手法上有所抉择与侧重。
二
六七十年代诗歌的口语化特征之所以如此突出,自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与创作主体的主观原因;同时还与口语化语言自身的特点密不可分。一方面这是由当时的社会语境决定的:六七十年代是一个全民总动员的历史时期,瞬息万变的社会形势与政治变化不能够为诗歌创作留下足够的时间与空间去把日常生活口语推敲、锤炼为含蓄凝练的“诗家语”;同时,处于激情高涨、真情流露的诗人和读者在创作和接受诗歌时也没有考虑其能否成为传世之作,他们无暇顾及诗歌的蕴藉含蓄与凝练深沉的审美特性,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到火热的生活中去,口语化的诗歌所特具的宣传特效恰好适应了他们这一方面的表达需求。这正如卡罗尔·阿诺德所说:“在口头修辞交流中,美学功能及价值只是次要的;对他人意图相关性的现实判断才是主要的。”①卡罗尔·阿诺德:《口头修辞、修辞及文学》,转引自[美]大卫·宁编:《当代西方修辞学:批评模式与方法》,常昌富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 271页,第 272页。这里虽然说的是口语修辞,但同样可以帮助理解口语的基本功能,即口语主要用以传达说话者的思想和情感,至于说话本身的美学价值和艺术魅力则很少顾及。因此,就口语而言,艺术修辞要绝对让位于表达的工具和表达的内容,传达的手段与效果远胜于传达的方式。另一方面,与书面语的单向性、间接性和静态性不同,口语交流具有双向性、直接性与动态性的特点,因此,后者的修饰手段和表意方式比前者更为丰富多样而且主体性更为突出。“口语修辞有两个主要而又特别的特征使得它与一般‘文学’不同,甚至与书面修辞也不同,即传递信息与信息的混合功能以及身处与某一具体的观众的个人化的联系中这一点所带来的制约及机遇。”②卡罗尔·阿诺德:《口头修辞、修辞及文学》,转引自[美]大卫·宁编:《当代西方修辞学:批评模式与方法》,常昌富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 271页,第 272页。这句话点明了口语修辞与书面语修辞者的差异:即 (1)口语修辞者的“双重身份”:既是传递信息者又同时是活的信息;而书面语修辞者则以书面媒介,凭书面这个载体传递信息,自己则隐在后面。(2)口语修辞行为是“活生生的人与人之间的交锋”③王德富:《口语修辞与书面语修辞的差异》,《修辞学习》2000年第 4期。。六七十年代诗歌中的口语化特征也契合了当时突出的主体意识(尽管在更多情况下是以集体代词“我们”而非个体代词“我”)与情感的表达需求。“诗既以传达为要务,就不能不顾到群众了解的便利。还有一层,即从作者的观点看,现代人有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特殊情思,现代语言是和这种生活方式和情思密切相关的,所以在承认古文仍可用时,我们主张做诗文仍以用流行语言为亲切。”④朱光潜:《诗论》,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版,第 81页。这可以视为对六七十年代诗歌口语化特征出现原因的合理注解与说明。
但是,上述口语的特点主要集中于日常生活的口语,而这类口语与诗歌的结盟还需要更多地磨合。换言之,由口语转化为诗家语还要接受诗歌这一特殊文体类型的筛选与“规训”。毕竟诗歌对语言有着更为严格的要求,而口语的许多特点与诗歌的内在要求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颉颃。比如,诗歌的语言要求凝练简约,即以极其有限的文字表达尽可能丰富的内涵。诚如朱光潜所分析的:“无论在哪一国,‘说的语言’和‘写的语言’都有很大的分别。说话时信口开河,思想和语言都比较粗疏,写诗文时有斟酌的余暇,思想和语言也都比较缜密。散文已应比说话精炼,诗更应比散文精炼。这所谓‘精炼’可在两方面见出,一在意境,一在语言。专就语言说,有两点可以注意:第一是文法,说话通常不必句句谨遵文法的纪律,作诗文时文法的讲究则比较谨严。其次是用字,说话所用的字在任何国都很有限,通常不过数千字,写诗文时则字典中的字大半可采用。”⑤朱光潜:《诗论》,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版,第 81页。再者,诗歌语言还要含蓄蕴藉,即言近旨远、回味无穷。“文似看山不喜平”,诗歌更是如此。所以有人为了达到“深文隐蔚,余味曲包”的艺术效果,甚至对诗语故意扭曲、变形,造成一种“陌生化”的感觉。中国诗歌所特有的“意象”、“意境”,有时更无须也不能通过语言就能解释和传递出来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就是例证。朴实直白的口语对此更是无能为力。因此,周作人指出:“我平常很怀疑心里的‘情’是否可以用了‘言’全表了出来,更不相信随随便便地就表得出来。什么嗟叹啦,永歌啦,手舞足蹈啦的把戏,多少可以发表自己的情意,但是到了成为艺术再给人家去看的时候,恐怕就要发生了好些的变动与间隔,所留存的也就是很微末的了。死生之悲哀,爱恋之喜悦,人生最深切的悲欢甘苦,绝对地不能以言语形容,更无论文字。……禅宗的作法的人不立文字,这办法的精义实在是极对的,差不多可以说是最高理想的艺术。”⑥周作人:《〈草木虫鱼〉小引》,《周作人文类编·人与虫》,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8年版,第 7-8页。
诗歌对语言的凝练含蓄、新异陌生的要求也自然引申出入诗口语的文法结构问题。六七十年代诗歌在文法上的循规蹈矩同样与胡适的观点有着极为相似的地方。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既有“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等对语言规则的松绑与解放,但也指出“须讲究文法之结构”。这一思路看似矛盾而实则统一,因为他所偏重的是应用性极强的“文章”而非作为审美对象的“文学”。不考虑文学的特性而就一般的白话文而言,对文法的要求无可厚非,因为传递信息时能让对方接受的原则和前提就是要遵循共同的语言规则;但文学尤其是诗歌的语言则可以冲破这一限制,在字词的选用、顺序的排列、句子成分的设置等方面更加自由灵活,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胡适的立论显然忽视了“文学”这一必不可少的前置词,倒是康白情对此有着更为准确的认识:“文法也是一个偶像”,如果“作诗又要奉戴一个偶像,更嫌没有自由了”。他进一步指出:“零乱也是一个美底元素。我们只求其美,何必从律?”因此,他高唱“打破文法底偶像!”⑦康白情:《新诗底我见》,杨匡汉、刘福春:《中国现代诗论》(上),广州:花城出版社 1985年版,第 40-41页。与之相似的还有俞平伯:“单调的章法句法,也是很讨厌的。文法这个东西不适宜应用在诗上”,“诗总要层层叠叠话中有话,平直的往前说去做篇散文就完了,况且好的散文也不是这样的。”⑧俞平伯:《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杨匡汉、刘福春:《中国现代诗论》(上),第 28页。很显然,康白情、俞平伯的观点出于对诗歌的深切认知,其论述自然更为合理、深刻。这对于正确评价六七十年代诗歌的历史地位与审美价值同样适用。
三
相对于六七十年代诗歌中口语风格的诸多不足而言,现代诗歌发展过程中也不乏在含蓄悠远深邃的诗句中容纳日常口语的成功例子,一些卓有成就的现代诗人有效地绕开了过于直白、乃至俗化的误区而取了重要的收获——如朱湘的《采莲曲》、戴望舒的《我底记忆》等既通俗晓畅而又不失浓浓的诗意诗味。朱湘认为:“新诗的白话决不是新文的白话,更不是……平常日用的白话。这是因为新诗的多方面的含义决不是用了日用的白话可以愉快的表现出来的。……我们必得采取日常的白话的长处作主体,并且兼着吸收旧文字的优点,融化进去,然后我们才有发达的希望。”①朱湘:《中书集》,上海书店 1986年重印本,第 334页。正是基于这种中肯的认知,他的实践取得了成功;戴望舒借助口语把日常生活的诸种意象以娓娓道来的口吻呈现出来,形成现代白话诗歌中跌宕优美、活泼灵动而又不失自然亲切的散文化倾向。艾青从戴望舒的口语化诗歌创作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在理论上把口语美与散文美有机结合起来。他说:“强调‘散文美’,就是为了把诗从矫揉造作、华而不实的风气中摆脱出来,主张以现代的日常所用的鲜活的口语,表达自己所生活的时代——赋予时代以新的生机。”②艾青:《诗论·前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年版。他承认:“从语言上说,我喜欢采用现代口语写的诗”,因为“生活的语言,是最丰富也是最生动的语言”③艾青:《我对诗的要求》,《诗论》,第 15页。。但实际上,他所采用的口语已经经过了情感、色彩等诗质的浸染而成为了较为通俗的“诗家语”,因此才使得《大堰河——我的保姆》、《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黎明的通知》、《火把》等一首首自然晓畅、生动灵活的诗篇成为中国现代诗歌史上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而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竖起了一座以鲜明的口语美为审美特征的里程碑。
而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兴起的朦胧诗潮,可谓是对六七十年代通俗易懂、明白晓畅的口语化诗歌的调整与反拨,为偏重于运用书面语、追求凝练含蓄的诗歌争得了一席之地。舒婷借助温婉典雅的语言,以独白语式传达忧伤凄美的情思,意象的矛盾对立与朦胧,句式的婉转而多变,构筑起多义蕴藉、优雅深藏的书面语体系,如《致大海》、《四月的黄昏》、《思念》、《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等;顾城同样善于构筑独特的书面语系统,以丰富奇异的意象兼容自己的生命体验,成就了迥异于渲泄与说教式的口语化诗歌的审美品性;杨炼的《礼魂》、《诺日朗》、《敦煌》等文化寻根组诗中以繁富密集的意象排列组合成的语言体系,实践了诗人追求的“幻象空间写作”——深度派生难度,而难度也激发深度:诗歌对中文性的探索;语言的造形能力;建立起自己的时空观,由此把“同心圆”的寓意推向极致④杨炼:《诗,自我怀疑的形式》,张新颖编选:《中国新诗 1916—2000》,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第 431页。。显然,这些审美效果是单靠单纯透明、晓畅俗白的口语所根本无法企及的。
此后,以口语入诗为中心的争论此起彼伏。先是朦胧诗遭到第三代诗人群或后朦胧诗的解构,韩东的《有关大雁塔》以日常口语式的语言消融了杨炼的《大雁塔》以书面语所呈现出来的深厚的文化意蕴与崇高内涵;于坚的《尚义街六号》、伊沙的《结结巴巴》等诗作同样以铺天盖地的日常口语把典雅含蓄的书面语排挤出诗歌领地。以口语化写作来软化或冲击书面语的策略成为他们的诗学主张与创作实践之一。他们对口语的倚重和鼓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胡适早期白话诗运动的再现。其中不乏“用口语,用完全属于自己的嘴唇说出完全属于自己的感受,他们的诗几乎就是他们的性情和生命状态在纸页上的再现”⑤沈浩波:《后口语写作在当下的可能性》,《诗探索》1994年第 4期。的优秀之作,但其不足之处也相当突出,那就是“许多的诗歌写作者把诗歌的口语化运动,理解成了毫无意义的大白话。于是,大量平庸、乏味、口水式的诗作折磨着我们。拒绝是必然的。”⑥谢有顺:《1999年中国新诗年鉴·序》,广州:广州出版社 2000年版,第 9页。而拒绝的最终结果便是读者退出诗歌现场,留下诗人自言自语或在沉默中慢步走向“死亡”。
因此,口语入诗的主张与实践必需解决好日常口语向诗化口语的转化问题:首先,无论是口语化的诗还是诗化的口语,都离不开“诗”的本质,诚如海德格尔在《荷尔德林与诗的本质》中说:“诗从来不是把语言当作一种现成的材料来接受,相反,诗本身才使语言成为可能。”⑦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上),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书店 1996年版,第 319页。因此,只有化日常口语为诗语——借助词句的过滤与锤炼、句式的调整与修饰、语气的择取与加工,文法的破格与“陌生化”处理等手段与程序——口语化的诗才能出现;否则,就会再次陷入“收入了口语,放走了诗魂”(梁实秋语)的泥淖;其次,“口语无论它如何富于生活气息,贴近生活,都应当不断地依靠书写来加深它的潜文本。”⑧郑敏:《结构 -解构视角:语言·文化·评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 124页。因此,以口语为基础,广泛地吸收融化书面语乃至文言、外来语之优长,才是使口语化诗歌保持鲜活灵动、丰富广博的有效路径。六七十年代诗歌语言口语化特征乃至整个现代诗歌史上口语入诗的实践过程的经验及教训即在于此。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六七十年代诗歌的语言学阐释》阶级性成果。
胡峰,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齐鲁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张玉芹,齐鲁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
I207.22
A
1003-8353(2010)04-0114-05
[责任编辑:曹振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