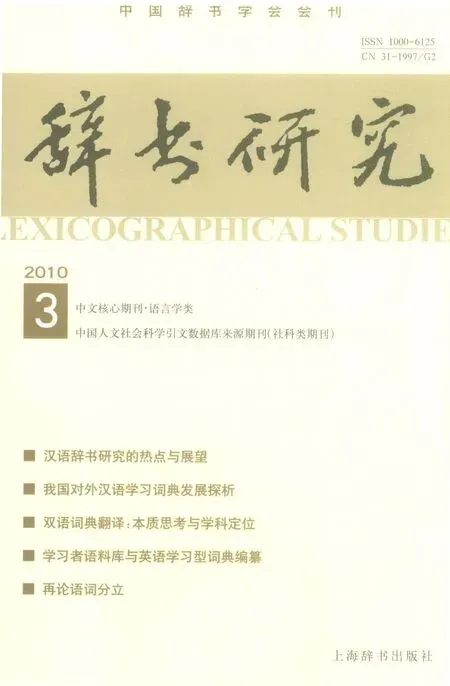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辞书编纂*
徐时仪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 上海 200234)
辞书是社会文化发展的产物,也是一定时期思想、科学、文化和语言发展状况的重要见证。清末民初是中国社会急剧发展变化的时期,中国在短短几十年内经历了封建社会的没落、资产阶级的改良、外来势力的入侵、西学东渐[1]、马列思想传播等一系列重大的撞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外国侵略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另一方面人们对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知识有了进一步的接触和了解。在中西文化的激烈对撞和交融中,“东亚的睡狮”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凌辱中惊醒过来。人们意识到夜郎自大和闭关自守在帝国主义列强的长枪大炮前皆无济于事,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要救国,只有自强;要自强,只有维新;要维新,则只有树起民主和科学这两面大旗;而要树起民主和科学这两面大旗,就必须要获取新知。在这种强烈的救亡图存和振兴中华的政治愿望感召下,一批适应时代要求、旨在普及国民教育和提高全民族文化水平的新型辞书相继问世,开创了我国辞书编纂的新局面。本文拟就这一时期我国辞书编纂的传承和创新略作论述。
一、文白演变与新字典
汉语的书面语有文言和白话两个系统,一为在先秦口语基础上形成以先秦到西汉文献语言为模仿对象的文言系统,一为在秦汉以后口语基础上形成的古白话系统。我国传统辞书的编纂大体上与文言系统相适应,如清代康熙命张玉书、陈廷敬等编的《康熙字典》可谓集我国古代辞书编纂的大成,被誉为“善兼美具,可奉为典常而不易者”。然而西学东渐中大量的新概念、新词语蜂拥而入,每一个新概念、新词语在汉语的表述系统中都有相应的位置,而早在秦汉时期就已凝固定型的文言概念体系无法包容和阐释这些新的文化现象,古白话概念体系由于随历代口语变化而变化的内在活力则顺应了时代要求,这促使了文言向白话的转型。古白话系统在经历了一个口语成分不断增加的量变过程后渐由量变向质变转化,最终在西学东渐的促成下取代了文言,质变为现代汉语书面系统。现代汉语来源于古白话,在语言作为工具的层面上和古白话没有区别,而在思想思维的层面上又与古白话有着根本的区别,即它吸纳了西方的话语方式,融合了外来的概念。如“文化”在古汉语中是“文治和教化”的意思,与“武力”、“武功”相对,“日语用`形借法'借去后,到近代又被日语用来作为英语culture的对译词,后来,又被现代汉语用`形借法'借了回来”。[2]又如“科学”也已不是“科举的学问”[3],“民主”也完全不是孟子所说的“为民作主”,“理性”更与宋代的“理学”有着天壤之别。这些词虽然不是很多,但对中国现代思想以至整个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的影响却非常大,使汉语发生了根本性变革,现代汉语正是在这些思想思维层面上概念的转变中完成文白的转型,由古白话质变为现代白话,形成一种新的语言体系,进而改变了中国的伦理观、价值观、历史观、哲学观、文化观、文学观等,从而从整体上改变了中国的文化状况,导致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从文化发生学角度看,文白的转型体现了当时中国面对伴随西学东渐的现代化和全球化趋势的应对和选择,可以说不仅仅是白话取代文言的语体变革,更是中西和雅俗文化互动的全方位的变革,从而促成了中国文化由传统的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化,也促成了新式辞书的问世。
清末来华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所编《华英字典》中西结合,自成一体,可以说是这类新式辞书的嚆矢。[4]《华英字典》共分三部。第一部中文名《字典》,分为三卷,第一卷1815年出版,第二卷1822年出版,第三卷1823年出版;第二部中文名《五车韵府》,分为二卷,第一卷1819年出版,第二卷1820年出版;第三部为一卷,英文译名《英华字典》,1822年出版。马礼逊参照《康熙字典》的体例和内容框架,以普及知识、满足实用需求为宗旨,从学习者的需要着想,在汲取《康熙字典》代表的中国优秀文化的同时,打破了馆阁体的文风,用民间的白话替换了文言,大量选用宋、元、明的白话例句和当时的口语用法进行诠释,有意识地将当时的西学知识与中国知识相对应地进行诠释,突破了中国传统工具书的编纂模式,开创性地编纂成一部新型的中英双语字典,构建了一座中西方双向通行的知识桥梁,[5]大大方便了读者的使用。如解释的白话词语有“意见、工夫、老实、天然的”等,例句有“大汉手持木棍也不做声照着苏友白劈头打来”、“只怕便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了”、“好生着急慌慌张张鬼赶着似的”等。从马礼逊《华英字典》所举的例句亦可见当时的口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马礼逊对“民主”、“自由”等一些西学知识概念已有解释,如释democracy为“既不可无人统率亦不可多人乱管”,释freedom为“自主之理”。又如“真理”一词一般认为是从日语传来的新词[6],实际上马礼逊编的《五车韵府》中已有“真理truth”[7]。
陆尔逵等编的《新字典》是继《康熙字典》之后第一部收释现代科学新字的字典,191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收字1万多个,以《康熙字典》常用字为主,兼收现代科学新字。序称其编纂宗旨在于对“国民之语言及思想”产生“革新之影响”。
陆费逵、欧阳敷存主编的《中华大字典》则标志了旧字书的终结,成为我国第一部新型大字典。[8]《中华大字典》始编于1909年,成书于1914年,191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这部字典以《康熙字典》为蓝本,纠谬补阙,改进体例,收字4.8万多个,在编纂体制上采用字头分列,首创数字标示义项,确立正俗兼收的原则,收释了不少方言俗字和化学元素名称的译字及借自日语的外来词。《中华大字典》与《康熙字典》相比虽只多收了1000多个字,但这些字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新词,代表了新的事物和新的思想观念,既涉及天文、地理、理化、生理、博物等学科,也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名物制度等各个方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新成就,以现代科技观念采纳新说,满足了读者查检的需要。
二、西学新词与博采新知的准百科全书
明清至民初,随着西学的东渐,大量新词语不断涌现。如明代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撰写和翻译有十几种著作[9][10],介绍西方科学文化,创造了许多新词语,其中如《几何原本》中的“点、线、直线、曲线、界线 、角、平面 、平方 、立方、比例”等,《理法器撮要》中的“面积、体积、弧线、切线”等,《西字奇迹》中的“圣徒、天主、降生、救世、天国”等,《坤舆万国全图》中的“北极、南极、直射、冷带、热带、经线、地平线、天球、月球、地球”等。合信(Benjamin Hob-son)医生编译有《博物新编》,汇集了五门学科的新词语。又如康有为《戊戌奏稿》中的“议院、农学堂、地质局、制度局、国民、光、电”等,谭嗣同《仁学》中的“灵魂、大脑、小脑、养(氧)气、红血(动脉血)、紫血(静脉血)、德律风(电话)”等。这些新词大致可分为如下四类:1.有关物质文明成果的,如蒸汽机、轮船、火车、电报、手表等;2.有关制度设施的,如议院、邮政局、交易所、证券、银行、公司、博物馆、图书馆、公园等;3.有关价值观念的,如科学、自由、民主、人权、进步、进化、民族、社会、文明等;4.有关学科知识和术语的,如伦理、政治、经济、代数 、化学 、概念、判断、推理等 。
我国古代的类书“语其义界,凡荟萃成言,裒取故实,兼收众集,不主一家,而区以部类,条分件系,利寻检,掇资采,以待应时取拾者”[11],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专科或百科性的辞书。这些类书方便读者查阅,然限于经史子集所载,虽在传承传统文化方面有独特作用,却尚乏传播推广新知识的功能。清末废科举制度改用新学,新的学校体系和教材系统逐步建立起来,哲学、政治、经济、法律 、军事 、体育 、外交 、外贸 、医学 、物理 、化学 、生物 、商业 、运输 、宗教、美学、音乐、天文等学科取代了经学等传统学科。考试制度和内容的变革引发了社会的进步和思想的革命,大量的西学新词顺应清末以来洋务派所代表的西化倾向和主张社会革命的平民思想蜂拥而入,据高名凯《汉语外来语词典》,仅从日语传入的就有840多个。接受和掌握这些知识成果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一个人作为“现代人”的必要条件。人们意识到中华民族要自强,面临的一个急迫任务就是必须普及我们民族传统中所短缺的各种新知识。一些怀抱经国济世愿望的有识之士意识到只有唤起民众求新知的欲望,才能走向现代化。人们需要了解新词语,接受新事物和新思想,而类书里的知识系统已既不足以应付新考试,又无法及时更新而与时共进。[12]
为适应人们查阅新词新语和学习新知的需要,这一时期出版了朱大文、凌庚飏编《万国政治艺学全书》(上海鸿文书局,1894),杞庐主人编《时务通考》(上海点石斋,1897),胡兆鸾编《西学通考》(1897),何良栋编《泰西艺学统考》(上海鸿宝书局,1901),马建忠编《艺学统纂》(上海文林,1902),汪荣宝、叶澜编《新尔雅》(上海明权社,1903),曾朴、徐念慈编《博物大辞典》(上海宏文馆,1907),黄摩西编《普通百科新大词典》(上海国学扶轮社,1911)等近50部专科或百科性质的新型辞书,其中有综合型、科技专业型、人名型、地名型、博物型等。[13]这些博采新知、汇编专科或百科知识的辞书改变了传统类书的编纂模式,吸收了西方百科全书的编纂方式,采用图表和新的排检法,可以说是我国过渡型百科全书,已具有准百科全书的性质,开我国百科全书编纂的先声。
三、以字带词与新式辞书
汉语以单音词为主,汉字大约有6万个,这些字所表之义大致即汉语中6万个左右的单音词的词义,基本上是形义结合,一字与一词相对应。汉语语言文字本身的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国古代语言学主要以文字为对象,这也决定了中国古代汉语辞书主要是以单个的字为收录单位来解释词义的字典,而汉语词汇由单音节向双音节发展则是汉语词汇古今演变的大势所趋。
陆尔逵、傅运森等主编的《辞源》适应汉语词汇双音化的趋势,采用以单字为纲,单字下带出复词,兼收古今词语和各种学科的名词术语的编纂方法,贯通典故,博采新知,成为我国辞书史上别开生面的新式辞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奠定了后来汉语辞书编纂的体例格局。继《辞源》之后,1936年中华书局出版了舒新城等主编的《辞海》。《辞海》以百科为主兼收语词,承《辞源》体例又有所改进。1928年成立的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和1936年成立的中山大辞典编纂处也曾着手进行《中国大辞典》和《中山大辞典》的编纂,尽管由于当时时局动荡等因素的影响,这两部大辞典未能最终完成,但毕竟在《辞源》和《辞海》编纂实践的基础上又作了一些筚路蓝缕的探索,为后来编纂大型汉语辞典提供了理论借鉴和实践经验。
一部辞书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不断满足社会需求的辞书编纂史。陆尔逵《辞源说略》说,当时“社会口语骤变,报纸鼓吹文明,法学哲理名辞,稠叠盈幅,然行之内地,则积极消极,内籀外籀,皆不知为何语”,以致“新旧扞格,文化弗进”,认为“一国之文化常与其辞书相比例”,“国无辞书,无文化之可言也”,而“欲求文化普及,亟应创编辞书”。时代是前进的,文化是发展的,现实要求人们编纂新的辞书,以适应新的社会需要。
四、结 语
社会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是辞书发展的动力,19世纪以来有三种因素推动了我国辞书的发展:一是科学上的重要发现、发明以及各种学说、社会思潮对辞书学产生了影响;二是社会的需求促进了辞书编纂的发展演进;三是辞书学自身一系列编纂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三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促成了我国辞书在这一时期的长足发展。据统计,从先秦至清代近两千年中编纂出版了52种辞书[14],而20世纪初11年间出版的中文百科辞书就接近50部,到1949年以前,出版了200部左右的新词语百科辞书。[15]除上文提到的《中华大字典》《辞源》和《辞海》等,还有樊炳清的《哲学辞典》(1926)、柯柏年等的《经济学辞典》(1933)、高希圣的《社会科学辞典》(1929)和《政治法律大辞典》(1934)、唐钺等的《教育大辞书》(1930)、谢观的《中国医学大辞典》(1921)、杜亚泉等的《植物学大辞典》(1918)和《动物学大辞典》(1932)、唐敬杲的《新文化辞书》(1923)、孙俍工的《文艺辞典》(1928)、方宾观的《白话词典》(1924)、陈英才等的《理化词典》(1920)等专科辞书。这些辞书都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编纂者经世济民的愿望,即借编纂新辞书来传播新知,开发民智,匡时救国。随着西学的东渐,从清末至民初,不仅辞书编纂的数量有所增加,而且辞书编纂也由传统模式逐渐转向近代模式,由官编“敕撰”转向由民间学人主持编纂,由传统的字典到新型字典、词典和百科全书,辞书类型趋于多样化,收字范围不断扩大,释义则力求通俗明确,新思想、新文化、新科学在辞书编纂中得到反映。
概而言之,西学的东渐引发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变革,我国辞书编纂在体例、内容、品种、数量及编纂方法上也渐融贯中西,在传承古代辞书编纂传统的基础上,又吸取了外国辞书编纂的经验,从而具有了现代辞书的特征。辞书编纂的理论在辞书编纂实践的探索中也有新的发展,确立了“顺时以应”、“体察用者之需要”的编纂理念,制定了“以字带词”的编纂条例,提出了“字书之学”和“字典学”的概念,[16]辞书学研究的雏形渐露端倪,我国的辞书编纂开始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中国辞书编纂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附 注
[1]东西交通与文化的交流远自有史以前,文献最初记载东方知识的欧洲民族是希腊,后来1至6世纪秦汉六朝时的欧洲人、7至12世纪的阿拉伯人、13世纪蒙古勃兴和14至15世纪元明时的西人与中国皆有交往,本文的西学东渐主要指16至17世纪明末清初西学对中国的影响。
[2]戴昭铭.文化语言学导论.北京:语文出版社,1996:3.
[3]古代汉语中无“科学”一词,与“科学”一词意思比较接近的是“格致”。所谓“格致”,即“格物致知”,亦即穷究物理的意思。《礼记·大学》说:“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不过,“格致”与“科学”在内涵上显然相距甚远,“格致”属于宽泛的科学,近代学习西方的物理、化学、数学、地理等理论以及引进西方的器械和技术则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现代汉语中的“科学”一词是从日语中借用而来,而日语中“科学”则是译自英语的“science”,所以“科学”一词本质上是来自西学东渐时的外来概念词。
[4]据法国费赖之所撰《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这一时期传教士的著述有644种,其中有关字典和文法的有9种。自1552至1687年,传教士也译了数十部中国的经典著作,形成了“东学西渐”和欧洲第一次“中国热”。其时金尼阁专为传教士学汉语撰有《西儒耳目资》,衡匡国撰有《中国文法》,马若瑟撰有《中文概说》。此外,德国米勒撰有《北京官话辞典标本》,法国德经撰有《汉法拉丁对译字典》,俄国帕雷底阿斯编有《中俄大辞典》,瑞典高本汉撰有《中文解析字典》等。
[5]钟少华.从马礼逊的华英字典看词语交流建设;马礼逊的华英字典与康熙字典文化比较研究.∥中国近代新词语谈薮.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6]冯天瑜.新语探源.北京:中华书局,2004:453.
[7]马礼逊.五车韵府.澳门,1819:63.
[8]刘叶秋.第一部新型大字典——中华大字典.中国青年报,1985-07-03.
[9]李开.现代词典学教程.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80.
[10]利玛窦可以说是西方第一位汉学家,来华 28年中先在澳门,后至广东、南昌、南京和北京,孜孜不倦,探索汉语的规律,所撰《中国传教史》绪论的第五章评述汉语有其“独特的表达方式”,书面语“非常高雅美妙”,用极少的音节表达的内涵“用我们西方的长篇大论也解说不清”;所编《中西字典》《西文拼音华语字典》已科学分解了汉语的音素,把官话分为26个声母、43个韵母和 4个次音,提到汉语尚“有平上去入四声”;又与罗明坚合编《葡华字典》;著有《西字奇迹》《交友论》《天主实义》;与徐光启、李之藻合译《乾坤礼义》《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等,介绍泰西学术,乾嘉学者江永、戴震的天文学知识皆肇自这些译著。参:刘羡冰.双语精英与文化交流.澳门基金会,1994:8.
[11] 张涤华.类书流别.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4.
[12]据统计,1908年全国已办新式学堂47995所,有学生130万人以上,高等学堂10余所。参:沈灌群.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的教育.北京: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152.
[13]当时编纂的英汉词典收录和诠释的外来词和新词,在某种程度上也规范了英汉语言间的对应关系,有效地统一了外来词的译名。参:胡开宝.英汉词典历史文本与汉语现代化进程.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14]上海交通大学辞典编辑部.国内工具书指南.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
[15]钟少华.中国近代新词语谈薮.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8.
[16]邹酆.汉语语文辞典编纂理论现代化的百年历程.辞书研究,20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