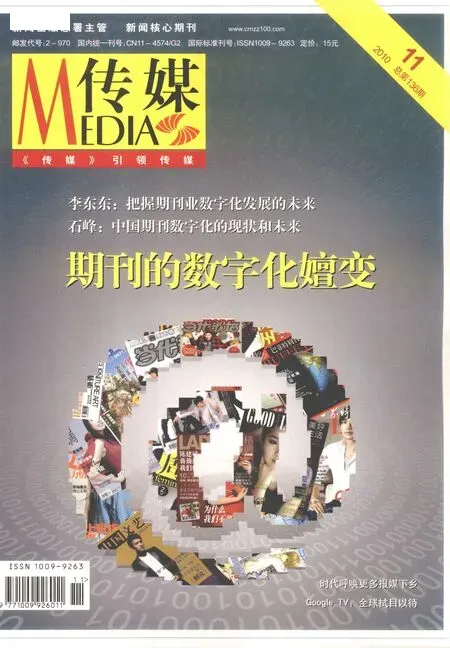传媒社会责任理论再思考
文/朱辉宇
由于传媒自由主义理论自身的缺陷及传媒滥用自由带来的负面社会影响,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问题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引起人们的关注。至1947年,以罗伯特•哈钦斯为主席的新闻自由委员会(The Commission on Freedom of the Press)发表报告《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标志着西方传媒社会责任理论的提出。60多年来,社会责任论在世界范围内大行其道,成为新闻传播领域的主流理论之一。当前,我国新闻出版产业正进入飞跃发展的关键时期,提高传媒责任意识成为当务之急。因此,系统梳理传媒社会责任论的理论建构,分析其理论与现实困境,探讨其实现路径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传媒社会责任论的理论建构
社会责任论缘起于客观现实的发展及理论自觉的进步。西奥多•彼德森将社会责任论的提出背景总结为以下几方面:第一,通讯工业的科技革命带来了社会变迁,改变了国家的面貌及人们的生活方式,使大众传媒具有了巨大的影响力,也造就了少数人控制传媒工具的现实。第二,秉持自由主义理论的西方资本主义传媒因其经济利益最大化及自由选择最大化的追求遭受到各方面的尖锐批评,在理论上直接促成了社会责任论的提出。第三,出现了适于社会责任论生存的新的“知识气候”,这些20世纪的新的世界观对自由主义思想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推动了社会责任论的形成。第四,传媒业界吸收了一些有原则有教养的人,与整个工商业界社会责任感的提升相一致,传媒业的职业精神也获得了发展,为社会责任论的提出奠定了基础。总之,社会现实的发展及整体世界观的改变推动了人们对有关媒体自由的反思,促成了媒体社会责任论的形成。
社会责任论修正了传统自由主义理论。在如何看待传媒社会责任理论与自由主义理论的问题上,部分学者常不自觉地将两者对立起来,将前者视为“道德的”、“好的”,而将后者视为“不道德的”、“坏的”。显然,这是一种误读。事实上,社会责任论是自由主义理论的演化与发展,是适应新情况的新理论。只是,社会责任论对自由主义理论进行了反思,修正了其中部分不合时宜的内容:第一,修正了人性认识中的理性观。在传统自由主义理论下,人被视为有道德的、完全理性的人,能够倾向于追求真理。但历史事实和现代社会学已表明,人类理性并非如此完美。有鉴于此,社会责任论提出,人并非完全的理性动物,人类的目标不是寻求真理而是满足自身直接的需求和欲望,人类理性不可靠且人们懒于运用它,传媒负有引导理性生活、塑造道德精神的责任。第二,扩充了传统的责任观。社会责任论摒弃了绝对自由的观念,强调责任与自由、责任与权利的统一。第三,揭示了责任的社会性。社会责任论不仅强调了责任与权利的统一,还揭示了传媒所负责任的社会性。只要媒体对社会产生影响,其社会责任就是无法回避的问题,越是对他人产生重要影响,其所承担的责任就越重大。因此,那些传媒从业者及传媒集团的控制者对社会整体都负有不可推卸的一份责任。
社会责任论进一步确证了传媒自由理念。第一,社会责任论重新认识了自由与责任的关系,将自由区分为“积极的自由”与“消极的自由”,即“有做……的自由”与“免于……的自由”两大类。同时,社会责任论指出,纯消极的自由是没有实效的,真正的自由必须具备积极、消极两方面。换言之,传媒有自由去获取其道德意识与社会需要所指出的目标,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它必须具备相应的经济、技术条件。第二,社会责任论进一步确证了传媒自由的重要性。传媒社会责任论肇端于人们关于自由主义理论弊病的反思,与传媒自由滥用直接相关,但这并不表明社会责任论否定传媒自由理念,相反,它是对自由理念的扩充和确证。社会责任论之所以强调传媒应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其宗旨在于确保“思想的自由市场”,保障大众自由的信息获取权,维护传媒的健康发展。若要确保传媒社会责任的履行,则必须保障其自由权利的获得。换言之,没有传媒自由,作为社会公器的传媒机构就无义务亦无能力践行社会责任。
传媒社会责任论的诸多困境
传媒社会责任理论自创立以来,获得了广泛响应,在理论呼声中逐步取代了西方自由主义理论而占据了主导地位。但细究下去,则不难发现,与其高涨的道义呼声相比,实际的落实状况并不令人满意。这种现象的出现,既有其理论自身的不足,亦有现实环境的局限。具体而言,一方面,社会责任论面对不少的理论质疑。传媒社会责任论一经提出,就遭受到很多质疑与批评。以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部分学者直接质疑这一理论的科学性与必要性,正如他们反对企业承担任何社会责任一样,他们提出作为经济组织的传媒企业其社会责任只有一种,即不断增加企业利润,使经济效益最大化。同时,有学者认为传媒社会责任论本身具有不可化解的内在矛盾:一是,社会责任论诉求于政府去规范传媒滥用自由的现象有悖于祛除政府干涉的自由主义原则。社会责任论一方面坚持自由传媒的原则,力求祛除政府的干涉,确保传媒的批评监督权,但另一方面又主张在一定条件下引入政府的管束,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二是,社会责任论诉求于人类理性及道德自律来规范传媒行为有悖于它对人类有限理性的批评。社会责任论一方面批评自由主义理论赖以立论的完全理性说,但另一方面又将人的自律理性作为自身理论的基础之一,是自相矛盾的做法。
另一方面,社会责任论面临诸多现实困境。社会现实的不断发展,特别是新型传媒方式的不断涌现使社会责任论的实践面临众多障碍。一是,社会责任的主体认定较为复杂。如儿童接触暴力图片,其责任主体就包括刊载暴力图片的媒体、儿童的父母、暴力图片的提供者等,如何恰当界定责任主体,确定责任大小是颇为复杂的问题。二是,现代传媒巨鳄的出现增加了落实社会责任的难度。在社会责任论提出之初,学者们业已担心传媒垄断对传媒自由、传媒责任的危害,但令人遗憾的是,时至今日,这一现象不仅没有改变反而愈发严重。如甘尼特(Gannett)、克姆卡特(Comcast)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等传媒寡头的出现使得它们对社会的影响更为简易,更无所顾忌,也使社会责任论对其约束更为无力。三是,新媒体的出现改变了社会责任论的理论前提,为其现实落实设置了障碍。各类新型媒体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和盛行,使传媒的主体行为更为隐蔽,使传媒社会责任的认定和追责极为困难,直接造成了社会责任论指导作用的弱化。总之,传媒社会责任论自身的理论不足与现实的客观限制带来了上述诸多矛盾与问题,同时也为我们探讨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预制了新的起点与要求。
传媒社会责任论的实现路径
面临新情况与新境遇的传媒社会责任论,其作用发挥是值得探讨的。特别是,传媒社会责任论在初始状态是以西方白人中产阶级价值观念为核心,带有鲜明西方文化特色的。对于中国而言,其指导价值的发挥就更值得商榷和探究了。因此,我们认为传媒社会责任论的落实可有如下几方面的工作。
应以传媒组织多向度利益的均衡发展为基础。当代社会,传媒组织多是市场经济中的独立主体,既有其作为市场经营主体的经济利益、作为政府“喉舌”的政治利益,又有其作为社会公器的社会利益。诸多利益与传媒组织所承载的社会身份相连,与其扮演的社会角色相关,表现出多向度、多层次的特点。这些利益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传媒组织所负的责任与所担的义务。我们强调传媒的社会责任,不能脱离这个根本的基础,必须客观认识传媒组织所应实现的诸多利益,在促成多向度利益均衡发展的基础上推动社会利益与社会责任的实现。事实上,多向度利益与责任之间是相辅相成的,传媒组织经济效益的增长会提升其实现政治、社会效益的能力,扩展其社会责任的范围与限度;传媒社会责任的落实则会提高传媒组织的社会美誉度,增强其实现经济、政治利益的能力。
应以自由与责任的协同发展为前提。独立自由是传媒组织的生存之基与价值所在,承担责任是传媒组织的内在之道与外在要求。强调传媒的社会责任离不开对传媒独立与自由的确认,离开自由纯粹谈论责任是空洞而有害的。因此,在国家宏观统一部署之下,切实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新闻出版产业改革,就成为当务之急与必然之选。不断深入的改革能够避免传媒组织陷入与异化政治责任、异化经济责任的冲突之中,使传媒组织具有真正的独立地位与自由权利,进而杜绝各种传媒失语、传媒缺位、传媒腐败、传媒庸俗化的现象。换言之,通过宏观制度层面对传媒生命力的释放,传媒自由与传媒责任能够获得协同发展,其社会责任也能够自然而然地获得实现。
应不断提高传媒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与自律精神。如约瑟夫•普利策1904年在《北美评论》上为其成立新闻学院进行的辩护所言:“只有最高的理想、兢兢业业的正当行为、对于所涉及的问题具备正确知识以及真诚的道德责任感,才能使得报刊不屈从于商业利益,不寻求自私的目的,不反对公众的福利”,传媒社会责任论的实现离不开传媒从业人员职业道德的提升。徒法不足以自行,再好的社会规范若没有良好个性美德与职业操守的支撑,都是无法自我实现的,传媒社会责任亦是如此。同时,传媒社会责任论的落实还需要不断提升传媒从业人员的自律精神。在社会责任论提出之初,人们就非常强调传媒的道德自律,倡导传媒的独立与自省。今天,面对各种新媒体的涌现,没有可靠的自律精神,社会责任的承担往往只会流于形式,这既是当前传媒社会责任建设的重点之一,亦是其难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