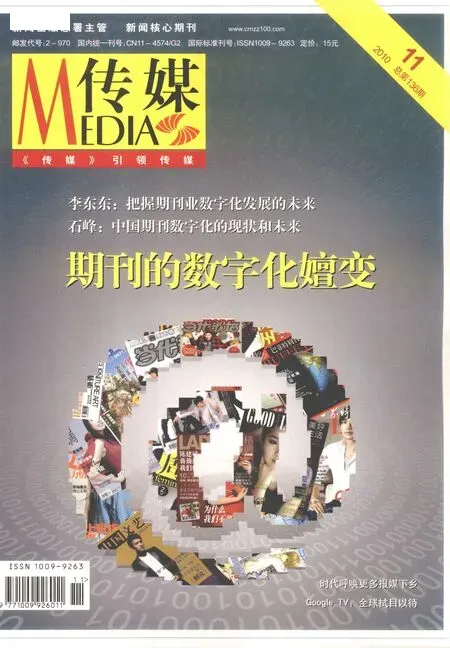纯文学期刊该如何定位?
文/宗仁发
今天,纯文学期刊处境岌岌可危。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它处在国家文化政策的缝隙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认识和重视。事实上,纯文学期刊一直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文化载体,是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传承、呈现的重要平台,是一代又一代作家成长的摇篮,是国家文化安全的屏障。因此,在改革中如何解决好纯文学期刊的定向和定位,绝不是可以等闲视之的小问题。
文学需要市场,但不完全等同于市场
在文学市场中消费者即读者,当然就是上帝,但这个上帝并不会给所有优秀的作家和作品签发畅行无阻的通行证。1956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并被称为“西班牙语抒情诗高度精神和纯粹艺术的最佳典范”的著名诗人希梅内斯在一本书的献辞中就曾写道:献给无限的少数人。同样是获得过诺奖的墨西哥诗人帕斯说得更彻底,他说:“现代诗歌的特点之一就是少数派的坚强意志”,“没有任何一位开创现代性的诗人寻求大多数人的认可,相反,所有人都选择了‘蓄意与公众情趣为敌的写法’。”帕斯说这些话的时候并不是不知道市场的厉害,他说:“我担心我的理由说服不了许多人,对现代思维来说,任何理由都敌不过一个数字。社会学者、教授、记者和掌握出版事务的人都说,他们拥有无可争辩的数字。”是啊,看吧,被称为“诗人之王”的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的代表作《牧神的午后》当时发行195册,11年后,他的自选集更可怜,才发行25册。兰波后来对20世纪诗坛产生巨大影响的作品《在地狱中的一季》,当时只印了500册,而且,除了作者自己拿走了6本之外,其他的都被丢在印刷厂的仓库里。我们再来看看惠特曼,他的《草叶集》第一版是作者自费出版、自己印刷的,发行量是795册。
显然市场的逻辑并非是文学的逻辑。一位出版人曾回忆庞德不止一次对他说过这样的话,庞德说,我的作品能在一本平庸的杂志上发表,能够到达27个读者眼前并使他们心潮激荡,这就够了。1940年,庞德还写信告诫他的年轻朋友:任何为钱写的东西都一文不值;唯一有价值的是对抗市场的创作。没有比钱更有毒的东西了。如果有人收到了一笔巨额汇款单,他马上会想到自己做了某件事情,但很快他的血管里流的就不是血了,而是墨水。许多经典作家作品的遭遇是如此,当下中国的纯文学的命运大家就更十分清楚了。如果我们认为纯文学对市场还会有什么不容置疑的作用的话,那就是纯文学是市场的一种解毒剂。
过去,就发表和出版的时间而言,有以一周为周期的各大报纸副刊,有以月或双月为周期的数以千计的文学期刊,还有每年都要出版一定数量纯文学作品的百余家文艺专业出版社。可是今天它们大多是每况愈下了,报纸副刊的文学功能大大退化。
出版社全面转企之后,市场制约、生存第一的现实让他们至少暂时无暇顾及达不到一定发行量的纯文学作品的出版。纯文学容身的三大板块仅剩下文学期刊这一块领地,但就在这个领地里,也是危机四伏。当年能够大量培育纯文学幼苗的数百家地市级公开发行的文学期刊在上世纪80年代两次刊物整顿之后,至今还发挥作用的已所剩无几。办在出版社或其他系统的文学期刊也都因服从于各自改革的需要纷纷转向了。就是办在文联、作协系统的文学期刊也是有的卖给民营书商,有的租给内部员工,其功能已和纯文学毫无瓜葛。最后还在顽强坚守的能够刊载原创纯文学作品的刊物也就几十家了。在这几十家中目前可以以发行量生存的不足十家,大多数是要依赖政府的公益拨款来维持生存的。如果要给他们断奶,把他们推向市场,让他们转企,那我们的纯文学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可想而知。
纯文学期刊承担着培育经典、滋养新人的重任
政府从公益角度对纯文学期刊予以扶持,可以使纯文学期刊承担起培育经典、滋养新人的重任。回顾一下我们当代文学并不遥远的昨天,有多少优秀的作品都是首发在这些纯文学期刊上啊。就举一个例子,中国文学的最高奖“鲁迅文学奖”五届评奖中的中短篇获奖小说不都是发在这些刊物上吗?我们再查查眼下活跃在文坛上的作家们,绝大多数人的处女作都是发在这些纯文学期刊上的。
如今的中国作协的掌门人铁凝在《教我学游泳的章仲锷》中写到,一次在回答一位来访的日本青年作家提出中国作家和编辑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时,她便想起已经去世的编辑章仲锷。1988年铁凝还在河北保定,她的第一部长篇《玫瑰门》写出几章后自己心里没底,就寄到《文学四季》,心里想最快半个月左右会有回音。五天后时任《文学四季》副主编的章仲锷带着编辑从北京乘火车一路站了几个小时,汗流浃背地来到保定,给铁凝带来了惊喜。章仲锷对《玫瑰门》给予了肯定,坚定了铁凝的信心。同时章仲锷还纠正了作者把“床笫”写成“床第”之类的文字错误。铁凝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处写到:“上世纪80年代一路走来的一大批中国作家,都得到过如章仲锷这样的优秀编辑老师在文学上给予的无私扶持或‘力挺’,他们数十年如一日,坦然隐在名声、荣誉的背后,这样的老师,每当想起他们的名字,我永远心怀敬意。”韩少功在回忆《人民文学》的副主编王朝垠是这样说的:“他把我这个陌生的大学生引入这种精确,引入他狭小的家,用啤酒、凉菜、临时小床,以及他刚刚失去母亲的女儿,接待我在文学上的开始。他的名字在偌大的中国文坛里是如此微不足道,在今后的岁月里想必更是了无痕迹。”“我记得他的家曾经是我上京改稿时的旅舍和餐馆,我也记得他曾经给我写过几封信,最长的一封竟有十页纸上密密麻麻的4000多字。这样的信足以使我对自己后来所有的编辑经历——包括眼下在《天涯》的工作汗颜。”类似的后来成名的作家,这样的文字还有许多。纯文学期刊编辑们这样的敬业精神和个人品格都掺入其中的工作,是不能量化的,也不适合不分青红皂白地纳入文化产业的管理之中。我们知道现在有了互联网,但至少在短期内互联网还无法完全取代这些文学期刊的作用。
纯文学期刊是文化生态中不可或缺的湿地
纯文学期刊是刊发原创作品的最重要的阵地。谁都知道《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这些选刊有较好的发行量。显而易见,选刊选载的作品不都是来自纯文学期刊吗?包括《新华文摘》《读者》中占一定比例的文学作品大多也是来自纯文学期刊。表面上看来,这些选刊拥有较大的发行量,内容也有质量。但稍微往里想想,谁都会明白,它的发行量是建立在对许多原创期刊潜在读者的覆盖基础上的。正因为不少读者都认为花最少的投入就可以从这些选刊上获取集中的文化信息,没必要自己直接再从原创期刊上去一一猎取。
还有影视改编的作品也有许多是从纯文学期刊中找到的。仅以我们的《作家》为例,张艺谋的《有话好好说》改编自《作家》发的述平的中篇小说《晚报新闻》,冯小刚的《天下无贼》改编自《作家》发的赵本夫的短篇小说《天下无贼》,张元的《绿茶》改编自《作家》发的金仁顺的短篇小说《水边的阿狄丽雅》。张艺谋就坦率地承认:“小说家们的作品发表比较快,而且出来得容易些,所以它们可以带动电影往前走。我们谈到第五代电影的取材和走向,实际上应是文学作品给了我们第一步……我们研究中国当代电影,首先要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因为中国电影永远都没有离开文学这根拐杖。”
从生态系统的角度去理解,文化就好比是一个生态系统。一个生态系统是需要多样性的、多元化的,它需要有不同的物种的存在。原创文学刊物,处在整个文化生态系统的源头地带,当然也就是最脆弱、最需要保护的区域。选刊以及影视改编这样的二度使用,往往都是直接无偿使用原创期刊的资源。这也反证了原创文学刊物的公益属性。
纯文学期刊是主流文学的主要平台
中国的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有一个重要的不同,就是前者是非体制化的,而后者是体制化的。我们的文学至少指纯文学或严肃文学,它必然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组成部分。这类文化产品的意识形态属性并未完全淡化,也可以说它的精神形态远远大于市场形态。从党群关系的角度看,文联、作协是党联系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那么严肃的文学期刊就是这个桥梁和纽带的一节一环,要是改变了这一节一环怎能不牵一发而动全身呢?胡锦涛同志《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工作是党和人民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进步文艺,刻写着一个民族的希望,昭示着一个国家的未来,深深影响着一个民族的精神和一个时代的风尚。”站在国家文化安全的立场上说,一个国家其最重要的文化基因密码就保存在这些文化载体中。
当年爱默生等人在商讨创办《大西洋月刊》时,就是要用这本刊物来改变美国的公众精神生活完全依赖阅读英国作品的状况,去定义与创造一种独特的美国声音,注明美国在世界文化中的位置,去提升出某种“美国理念”。按照法国人皮埃尔•布尔迪厄的文学场理论,文学期刊应该本着自主原则,以输为赢,只需要积累象征资本,创造的是信仰的宇宙。就政府该如何认识资助文学艺术的问题,皮埃尔•布尔迪厄认为:“凡是提供‘高级文化’的机构,只能靠国家资助才能生存,这是一个违背市场规律的例外,而只有国家的干预才能使这个例外成为可能,只有国家才有能力维持一种没有市场的文化。我们不能让文化生产依赖于市场的偶然性或者资助者的兴致。”
在文化产业发达的美国,它的纯文学杂志也没有很大的销路,它的生存必须依靠补贴过活。谁来承担这样的职能呢?美国是由大学的出版社或国家艺术基金会来出钱养纯文学刊物。在美国几乎每所大学都有纯文学刊物,例如《芝加哥评论》《密苏里评论》《爱荷华评论》《麻省评论》《耶鲁评论》等。这些刊物名之曰“评论”,实际上都是可以发表文学作品的刊物。像《纽约客》《大西洋月刊》《哈泼斯》这些刊物则都属于政治、经济、文化综合性的刊物,文学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它们是可以靠经营来生存的。而真正的纯文学杂志中就是声誉最高的《巴黎评论》,其销路也不过二三万份。美国人把纯文学杂志称之为“小杂志”,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小杂志共有1200余种。一般发行量为二三千份,有的就是几百份。
其实,西方发达国家在文化传媒的性质划分上,并不是按事业和企业来区别的,而是按赢利和非赢利区分的。这些年,大凡国内优秀的纯文学期刊都曾试图努力通过改版,扩大发行量,寻找解决生存之道。但实践证明这个路径至少短期内是不易走通的,就连大家普遍认为改革最成功的《萌芽》的主编赵长天也认为,文学杂志读者群体萎缩是十分正常的,文学杂志还发挥着类似图书馆、博物馆的功能。目前,我国正在全面推进的文化体制改革涉及国家文化的各个侧面,中国的纯文学刊物机构该怎么办?站在提高国民文化素质,传承民族文化,维持精神生态平衡,保护国家文化安全的立场上,把纯文学杂志明确归属为公益事业是非常需要的。国家在这方面要花的钱其实是很小、很少的,但作用却是无限的、持久的。要意识到这一点,必须放弃文化上急功近利态度,要像认识博物馆的作用一样来认识纯文学期刊才行。
——以纯文学在近代和八十年代的两次现身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