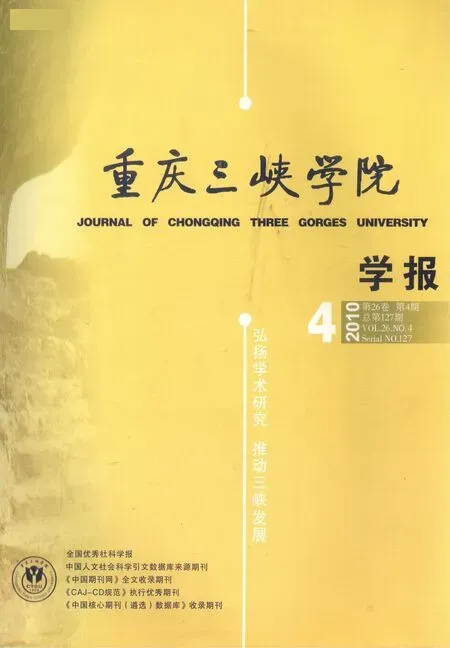文学体制裂缝与“第三代”诗歌呈现
罗文军
(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南充 637002)
文学体制裂缝与“第三代”诗歌呈现
罗文军
(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南充 637002)
“第三代”诗歌在1986年的群体展现之前,与文学体制的裂缝有着复杂的关系。有关朦胧诗的多次讨论,以及《诗刊》等刊物发表的文章,都显示出不同文学话语之间的对立和杂糅。这给“第三代”诗歌的发展既带来束缚又带来时机,还影响到其文学形象的建构。思考裂缝与呈现之间的关系,有助于认识文学历史的繁复面貌。
文学体制;裂缝;“第三代”诗歌
彼得·比格尔认为,文学体制“不过是指显现出以下特征的实践活动:文学体制在一个完整的社会系统中具有一些特殊的目标;它发展形成了一种审美的符号,起到反对其他文学实践的边界功能;它宣称某种无限的有效性。”[1]借此来看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的文学发展,其“实践活动”所包含的“特殊目标”、“有效性”、“审美符号”等,都在发生着重要变化。有关真理标准、人道主义思想、西方现代派文学等问题的讨论,以及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萨特热”等事件的出现,都表明了这些变化的复杂。在这些性质不一的讨论中,多重话语的相互交织,也喻示了该阶段文学体制中出现了众多的裂缝。
也正是在这些裂缝中,1980年代诗歌获得了十分复杂的生发景观。如果把1982年10月,四川高校各路诗人代表在重庆率先提出“第三代人”口号,看作第三代诗歌的发端,把1986年《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组织的“中国诗坛 1986’现代诗流派大展”,作为第三代诗歌群体展现的标志,那么,在这期间,文学体制的裂缝与第三代诗歌兴起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呢?思考这一问题,是否有利于进一步认识诗歌生成的历史面貌呢?事实上,在1980年代上半期,朦胧诗在一次次的论争中,逐步获得了文学机制的准入许可,第三代诗歌也正以“地下性”的方式,在不断寻找从缝隙中探出头来的时机。
一、“崛起”与话语变化
1979年,《诗刊》3月号转载北岛的《回答》等诗,4月号又转舒婷的《致橡树》,8月号发表叶文福的《将军,你不能这样做》,以及《安徽文学》10月号以专辑形式刊出30位青年诗人作品,这在当时都有着寓意性的作用:一种新的诗歌审美取向在文学体制中逐渐显现出来。谢冕在1980年5月7日《光明日报》发表《在新的崛起面前》一文,率先以肯定性的态度来探说这种“新诗潮”。但是,在随后的《诗刊》8月号,章明带有强烈批评性的《令人气闷的朦胧》一文刊载出来,从而引发了所谓的“朦胧诗”大讨论。
其实,在“讨论”之前,有关“朦胧诗”的评说就已经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话语。石平随后就对这种状况做了大致描述:“谢冕在今年5月7日《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指出所谓‘看不懂’或‘古怪’的诗,是新诗发展的‘新的崛起’,是诗人,特别是一批青年诗人对新诗现状不满,由苦闷而进行探索和突破的结果”,而“蓝翎不同意这种意见,他在7月21日《人民日报》以《‘看不懂’的推想》为题发表文章,认为看不懂的诗是存在不下去的。”[2]此外,《福建文艺》1980年2期起开辟了讨论舒婷作品的专栏,其中也出现了两种不同态度:一种认为诗不能只作为阶级政治的臣民,另一种主张要坚持毛主席提出的政治标准,要明确“为谁写诗”。《文艺研究》、《北京日报》等,对相关文章都刊载了。那么,这些不同取向的话语,暗含着什么意味呢?
显然,若从整个文学体制表现出的话语方式来看,一种缝隙已然在诗歌审美取向上产生。随着《诗刊》1981年3月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4月程代熙反驳孙绍振的《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发表,这种缝隙出现了进一步的扩张。此时,还不能称之为是“第三代”的诗人们,虽然大多生活在校园里,一些人只是“看到一些手抄的芒克的诗,北岛的诗”和民刊《今天》,[3]但是,他们已经在开始分享朦胧诗的这种话语遭遇。
1980年9月17日,《人民日报》第五版发表了傅佑、马秀清的《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的读者来信,他们认为我们的文艺领导体制,已到了不改革就不能前进的地步。10月8日《人民日报》又以《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为题,全文发表了著名演员赵丹临终前两天留下的“谏言”。这篇文章引起文艺界强烈共鸣,但却很快受到主流话语的严厉批评。金山《马克思主义宇宙观引导着他的艺术道路》、李准《领导要改善,体制要改革》两文,在《人民日报》10月29日一同见报,他们就表述了如下意思:“文艺只能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因此维护党对文艺事业的正确领导,尤其是在方向、路线和政策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领导,乃是十分必要的。”如此,这种原则性强烈的话语,使“赵丹遗言”对文学体制的冲击在表层上沉寂了下来。[4]可是,就在同一天,《人民日报》也刊载了张家口市一中教师戴白夜的《文艺政策要放宽,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这篇小文章。文中建议:“根据宪法规定,允许民办刊物和不同风格流派的剧团存在”。[5]这些倾向各异的话语,倒的确表明文学体制中多种缝隙的存在,尽管这种存在本身不无模糊之处。
就在这个时期,后来被定义为“第三代”的年轻诗人,已然开始与民刊结下不解之缘。韩东1979年读到了《今天》,随后在大学里开始“云帆”诗社活动,杨黎所办的《鼠疫》1980年10月也已编完。二人对各自的刊物进行了一次公开的张贴,但随后都受到了追查。[6]可以说,他们切身遭遇了朦胧诗“崛起”之时所受到的束缚,也感受到了其他可能性的存在,他们后来对诗歌方式的选择,也很难说没有受此影响。
二、“裂缝”的反复与“第三代”诗歌兴起
随后,在“有效性”、“行为模式”等方面有着举足轻重意义的《诗刊》,其角色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时为《诗刊》编辑的唐晓渡,后来说道:“这种变化并非出于任何个人意志,倒不如说它出于某种集体意志。这种集体意志一方面感受着新诗潮的冲击所带来的兴奋、眩晕和不适,一方面念念不忘主流意识形态、体制和所谓‘新诗传统’的规范”,而关于朦胧诗的讨论,“越是到后来,要求对诗坛年青的造反者进行‘积极引导’的压力就越大。这一特定语境中的‘关键词’透露出,对那些自认为和被认为负有指导诗歌进程责任的人们来说,阅读的焦虑从一开始就与某种身份危机紧紧纠缠在一起,而后者远比前者更令人不安。”[7]事实上,《诗刊》作为诗歌报刊的领头羊,正好直接地显示出文学体制的变化,并承受着其中固有的压力。
在 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文学体制的“有效性”宣称表现出了更为强烈的姿态。“除‘三个崛起’外,在不同程度上被划入‘污染’之列的还包括北岛的《慧星》、《一切》,舒婷的《流水线》,杨炼的《诺日朗》,顾城的《结束》等。……奇怪的是,在相邻的领域,例如小说界,却不存在一场同步的运动。这似乎从另一角度支持了指导者有关诗歌界是一个‘重灾区’的判断。”[7]唐晓渡的这段回忆,在表明朦胧诗受到的文学体制“有效性”宣称的批判之外,却又暗示了整个文学体制中另一种状态的存在:小说界并不如此。文学体制的裂缝,在不同体裁中甚至有不同表现。
“第三代”诗人在这种缝隙中正蠢蠢欲动,他们大多已开始创作,一些流派也已然形成。可以说,正是朦胧诗正面抵挡了来自文学体制的“有效性”界定,“第三代”诗歌才能在这段时间,以民刊的方式来形成自己的文学身份和想象秩序。假如“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直接针对的是“第三代”诗人,那么,在1980年代的诗歌景观中,1986年的“现代诗流派大展”难以那样快就出现。唐晓渡认为:“事实上,只要不是仅仅着眼于官方的诗歌出版物,只要把目光从幻觉中的‘诗坛中心’或‘诗坛中心’的幻觉稍稍移开一点,就会发现广阔得多的诗歌景观。”[7]显然,这里的“诗歌景观”包含着“第三代”诗歌状况,这意味着该阶段“第三代”诗歌作为另一种诗歌秩序的存在,也意味着这种秩序与整个文学体制之间复杂的、甚至不无“同构”色彩的关系。
有关朦胧诗的论争沉寂下来之后,文学体制在1984年下半年表现出了又一次震荡后的宽松。1984年第8期《诗刊》,头条发表了邵燕祥的长诗《中国,怎样面对挑战》。该诗发出了诗歌界大部分人的心声,呼唤“新鲜的岁月快来吧”。随后,“无名诗人作品专号”、“青年诗页”、“朗诵诗特辑”、“外国爱情诗特辑”等栏目在《诗刊》开设,都表明一种新风的再次吹起。1985年7月2—4日《诗刊》召开座谈会,就触及到了若干尖锐的问题,认为诗歌界对一批卓有成就的中、青年诗人,尤其是青年诗人缺乏重视。
与此同时,一种热情培养青年诗人的新景观出现了,并在文学体制的转变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诗刊》社开始招收青年诗人学员,“第一期学员报名的就有2万5千多人”,北京的诗人、报刊编辑、大学老师都来当辅导老师,“学员除了来自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港澳台地区外,还有美国、日本、瑞典、法国、伊拉克等国家。”这种方式吸引了广大诗歌爱好者的注意,使得诗歌界出现了一种新兴局面,而且“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情支持,《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等,以及全国各地的一些报刊、电台、电视台都发了消息和报导。文艺界,特别是诗歌界的老一辈诗人以及中宣部、中国作家协会等领导也十分关心和支持。”[8]如此,“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带来的部分影响受到了消解,文学体制的主流话语更多地接受了新的诗潮。
正是在这样的话语变化中,“第三代”诗歌中的“他们”、“海上诗群”、莽汉主义、圆明园诗群、极端主义、撒娇派等诗群创立而成。可以说,“缝隙”的反复给第三代诗歌兴起带来了可能,并影响了兴起的方式。
三、“大展”前后的话语变化
1985年1月3日,在朦胧诗论争中因《崛起的诗群》一文而备受批评的徐敬亚,[9]南下进入《深圳青年报》副刊部任编辑。7月15日,他发出了几十份“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流派大展’”的邀请,却接收到了“大大超出想象”的反响。他回忆道:“几天后,各类诗歌作品、诗歌宣言,从全国各地纷纷寄向深圳。”,“书信,是当时人们与外界的主要联系手段。而我手中的诗歌地址也仅三、四十位。我不知道我的那封信在各省市县乡经过了多少次复印、转告与传播。”[12]1986年9月12日,徐敬亚编辑了“第三代诗专版”,于坚、马力等诗人的作品出现其中。徐敬亚对文学体制的感受和自身魄力,使他对整个“第三代”诗歌的新态势率先做出了反映,他也由此成为先锋诗歌运动中一个突破口上的象征性人物。
文学体制的缝隙在此已然扩大,整个文学氛围相对宽松,《诗刊》在这个阶段也明确地表现出了“兼收并蓄,团结各种不同年龄,不同地域,不同风格的诗人和各种层次的读者”,“以热情的手,迎接各种流派的诗作,迎接各种流派、风格的探索和创新”的态度。[11]《诗刊》的征订数也大幅度上升,1987年2月号《诗刊》的卷首语就提到:新一年的征订数由上一年的12万增加到14万。[7]也正是这时期,“第三代”诗歌蔚为壮观地展现了出来。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文学体制矛盾的消失呢?唐晓渡在回忆中提到,1986年之后几年总的要求是“要造成和谐、宽容、团结、民主的政治局面”,在文学中政治主导的色彩依然十分强烈。他还认为,“《诗刊》不仅仅是一个我们为诗工作的场所”,“其职权范围包括:一,成为沟通‘指导者’和‘被指导者’的说教渠道,所谓‘上传下达’;二,负责甄选并展示符合‘指导者’的意图和口味,亦即‘合格’的产品,以‘类广告’的方式进行示范、引导和推广;三,及时发现、指明、纠正或整肃‘离经叛道’的异端倾向,以确保产品质量的纯洁。”[7]所以,1986年6期《诗刊》登载的《<诗刊>编辑谈<诗刊>——记<诗刊>编辑部的一次谈心会》中,还强调《诗刊》“对诗歌运动的发展,负有很重要的历史使命,做好当代诗歌刊物的编辑工作,必须加强编辑人员的责任感。”此外,当时较为激进的刊物《中国》,因系列性地刊发“新生代”的先锋诗歌作品,尤其是因为1986年第10期推出的“巴蜀现代诗群”而被勒令改刊,以致《中国》杂志12月印行了带有抗议性质的“终刊号”而结束。
不过,存在于文学机制中的缝隙,此时也足以让“第三代”诗歌浮出地表,获得自己的文学形象。1986年《诗刊》举办第六届“青春诗会”,于坚、韩东、翟永明名列其中,这被认为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诗会,因为它使“第三代”诗人的代表走到了舞台的中央。
四、余论:其他的空间及其意味
如果将目光稍稍越出狭义的文学体制范围,我们就会看到1980年代的流行音乐、先锋绘画、人们的日常生活等都在发生显明的变化。正处于青春时期的“第三代”诗人们无疑更为直接地感受到了社会体制中的这些转变,他们的先锋姿态、秩序想象也明显受到了相关空间变化的影响。
流浪主题、青春感伤、甜美抒情等流行音乐因素,对于“第三代”诗人们来说已不再陌生。杨黎就描写了1982年成都流行“贴面舞”、“看录像”、“听邓丽君”等与传统生活相背的现象,并且将这种现象作为“我们的标志”。[6]
在绘画界,从1979年“星星画展”到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中国的美术先锋们的目的似乎不是对艺术自身经典的破坏和对青春意识形式的追求,他们的目的已大大超越了艺术,他们希望对文化、思想、社会进行对抗与叛逆”。[13](225)一系列的先锋绘画展频频亮相:1983年 9月复旦大学《83年阶段·绘画实验展览》、1983年厦门黄永砅、俞晓刚等“厦门5人展”、1985年12月浙江美院《85’新空间展》、1986年6月南京《新野性画展》、1986年5月广州中山大学《南方艺术家沙龙第一回实验展》……这些空间的变化,无疑为“1986’现代诗流派大展”的出场营造了氛围,对第三代诗歌的呈现起到了声援作用。
显然,文学机制的裂缝并不是一个小圈子或者说狭隘的变化,它包含着20世纪七八十年代纷繁复杂的社会因素的影响,政治思想、文艺观念、对外开放等,都在其中起着深刻的作用。具体到“第三代”诗歌来看,尽管它很长一段时间潜于地表之下,但是它的发展和展现、对先锋形象的自身模拟、对诗歌秩序的主观想象,也正是紧密联系着并且得益于这种文学体制留下的缝隙。这些缝隙也不仅仅来自于对立的话语取向,它还是一个转型时期社会意识变化的产物。第三代诗歌在这些话语缝隙之中,寻求自身的合法性,也形成了较为独特的文学形象,这其实都表明了该时期文学历史的驳杂与繁复。
[1][德]彼得·比格尔.周宪译.文学体制与现代化[J].国外社会科学,1998(4).
[2]石平.一些报刊就新诗创作开展争鸣[J].诗刊,1980(9).
[3]韩东.韩东采访录[M]//杨黎.灿烂.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4.
[4]袁鹰.“赵丹遗言”的前前后后[J].炎黄春秋,2005(12).
[5]戴白夜.文艺政策要放宽,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N].人民日报,1980-10-29.
[6]杨黎.灿烂[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4.
[7]唐晓渡.人与事:我所亲历的八十年代〈诗刊〉[EB/OL].www.shigebao.com/html/articles/22/26.html.
[8]朱先树.我在〈诗刊〉当编辑二三事[J].诗刊,2006(1).
[9]徐敬亚.见证中国新诗[EB/OL].www.shigebao.com/html/articles/22/1208.html.
[10]徐敬亚.一封信引来全国诗歌的漫天大雪[J].诗歌月刊,2006(11).
[11]本刊记者.〈诗刊〉编辑谈〈诗刊〉——记〈诗刊〉编辑部的一次谈心会[J].诗刊,1986(6).
[12]王薇.文化传播中的中国当代流行音乐:1978-1971[J].黄钟,1996(1).
[13]尹国均.先锋实验[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
The Discourse Crack and the Appearance of Third-generation Poetry
LUO Wen-jun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College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nchong Sichuan, 637002)
Before the exhibition in 1986 as groups, the Third-generation poetry had many complex connections with Literary Institution’s contradictions. The discussion about misty poetry and many articles published on journals, such as The Poetry, displayed the opposition and mixture among different discourses. It brought restriction and opportunities to Third-generation poetry, affected the poetics image. The recogni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course crack and the presence will contribute to analyzing the complex appearance of literary history.
literary institution; discourse crack; third-generation poetry
I207.25
A
1009-8135(2010)04-0090-04
2010-04-19
罗文军(1978-),男,四川宣汉人,讲师,中国人民大学2008级博士,主要研究现当代文学思潮与流派。
(责任编辑:张新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