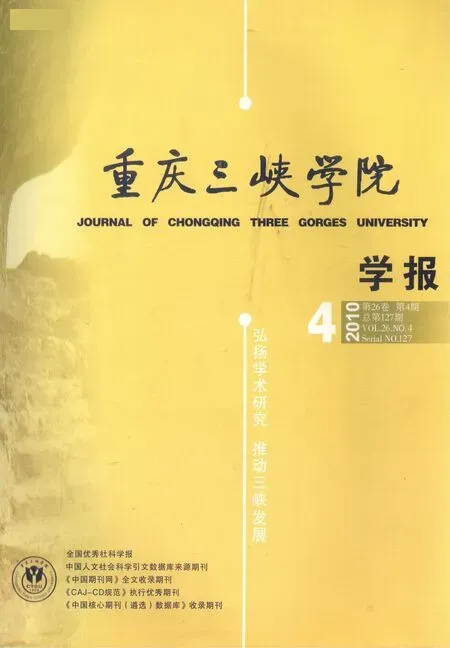历史叙事要素的重构
——论飞花奇幻作品的轮回叙事
蒋 勇
(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 400715)
历史叙事要素的重构
——论飞花奇幻作品的轮回叙事
蒋 勇
(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 400715)
奇幻文学在对各种叙事理论的吸取与创新中,逐渐形成了各自的特点,飞花以轮回性叙事的特点实践了新历史主义叙事的要求,并将历史性叙事与奇幻叙事的长处融合发挥,使奇幻作品得以容纳更广的叙事要素,从而形成了一种时尚与传统、不羁与严肃自然融合奇幻叙事模式。
轮回;轮回形象;轮回叙事;新历史主义
奇幻文学作为当下传播认知度颇高的一种叙事形态,广泛地吸收了各类叙事理念,并加以发挥创造,使奇幻叙事逐渐形成一种类型化特点。奇幻文学创作者也大都自成一家,各自雄踞自家叙事领地,百家争鸣,奇幻创作逐渐展示出其独具风格化面貌。作家飞花以其深邃、唯美的历史轮回叙事使其作品成为众多奇幻作品的佼佼者。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方兴起了“新历史主义”文化理论和批评方法。在这种理论的影响下,文学创作特别是叙事性作品呈现出一种不同以往的全新风貌,它们逐渐抛弃了传统历史主义的“宏大叙事”模式,而在叙事策略上强调现实感和个人体验,使叙事逐渐走向了一个新的空间,既充盈着历史感,又具有很强的个人化色彩。飞花的奇幻叙事具有强烈的新历史主义倾向,她将叙事融入当下极具幻想力的奇幻思维,令奇幻与历史结合,构建了独具魅力的轮回叙事模式。
一、轮回与轮回叙事
轮回又称“六道轮回”,原是印度婆罗门教主要教义之一,佛教沿用发展。认为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在“六道”(天、人、阿修罗、畜生、饿鬼、地狱)中生死相续,无有止息,谓众生由惑业之因(贪、嗔、痴三毒)而招感三界、六道之生死轮回,如同车轮之回转,永无止尽,故称轮回。《佛学常见词汇》释义“轮回”,谓众生从无始以来,即展转生死于三界六道之中,如车轮一样的旋转,无有脱出之期。[1](299)自从佛教传入中国,轮回理论在中土的接受过程中,轮回观念与中国本土思维方式便逐渐融合,形成了中国佛教的独特性轮回观念。例如就轮回的主体性问题上,“一些僧人就直截了当地提出有我论或有轮回主体论。在他们看来,讲轮回没有轮回主体是不可思议的。”[2]中国较早的佛教著述《牟子理惑论》中就曾论及轮回主体问题。牟子认为:“魂神固不灭矣,但身自朽烂耳。身譬如五谷之根叶,魂神如五谷之种实。根叶生必当死,种实岂有终亡?”慧远在《沙门不敬王者论》中说:“夫神者何耶?精极而为灵者也。……神也者,圆应无生,妙尽无名,感物而动,假数而行。感物而非物,故物化而不灭;假数而非数,故数尽而不穷。有情则可以感物,有识则可以数求。数有精粗,故其性各异:智有明暗故其照不同。推此而论,则知化以情感,神以化传,情为化之母,神为情之根,情有会物之道,神有冥移之功。”“火之传于薪,犹神之传于形;火之传异薪,犹神之传异形。前薪非后薪,则知指穷之术妙;前形非后形,则悟情数之感深。惑者见形朽于一生,便以为神情俱丧,犹睹火穷于一木,谓终期都尽耳。”在慧远的认知体系里,生命个体是由“形”与“神”合二为一的,外在形体的覆灭并不会导致“神”的灭亡,相反,“神之传于形”尤其是薪火相传,才是生命的真谛。
中国佛教的轮回观念最大的特点在于它对轮回主体的认可性,没有主体的参与,轮回也就不会继续。但这个轮回的主体并非生理学意义上的个体生命,它是由形神共同组成的,而“神”在轮回的体验中起到关键作用。这种轮回理论的产生与中国古代原始思维有着密切的关系。《礼记·表记》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鬼,据《尔雅》解释,是“归”,即回老家的意思,意谓人死后灵魂的归宿。《左传》昭公二十年记郑子产之言曰:“用物精多,则魂魄强,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说神、神明是精气强盛的人的鬼魂,一般人死后为鬼。或说神为阳,鬼属阴。人死为鬼神的观念及建筑于此种观念的祭祖习俗,长期以来基本上被华夏社会的全体成员所接受,至今在农村尚普遍遗存。这种人死为鬼神的观念,成为佛教轮回说被中土人士广泛接受的基础。[3](194)
轮回主体在飞花的奇幻作品中被赋予全新的意义,它成为链接古今、飞跃地域的关键,在飞花的奇幻世界里,轮回形象是历史的见证者,生命的体验者,更是叙事的执行者,正如《明玉珍·孔雀胆》开篇所强调的:“我们的三世始终同步地存活着,无论过去、现在或是未来。”[4]在这里,“我们”成为体验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空穿梭者,而“我们”的这种能力就得力于轮回。跨越三世的叙事主体因其灵魂的前后承载性,使历史变得不再孤立,这种跨越性的主体叙事和历史性的个体观照,为奇幻叙事增添了一种别样的魅力。飞花的奇幻叙事借助轮回观念,以某个人物的轮回经历,融入广泛的历史元素,形成了独特的轮回叙事模式。在飞花的轮回叙事中,轮回借助轮回主体的生命体验,整合形象在轮回过程中的时空要素,尽可能地发挥这种叙事方式的包容性,用轮回把各种叙事要素联系起来并赋予其逻辑性,用轮回的方式叙述历史,进而拓展了奇幻的叙事对象、丰富了奇幻的想象逻辑。所以说飞花的轮回叙事是建筑在佛教轮回观念上,借助轮回人物形象的奇幻体验而形成的整合无序历史叙事要素的一种叙事逻辑。
二、轮回叙事中的轮回人物
中土佛教轮回观是建构在轮回主体上的一种理论,飞花的轮回叙事也是借助人物的轮回体验而展开的,飞花作品中的轮回人物便是轮回的体验者、历史流变的承载者、轮回叙事的执行者,轮回人物也因此而具备了其复杂性和深刻性。
轮回叙事成为可能,叙事过程将各历史要素相联系,是建立在轮回人物的生命体验及其主体叙述上的。灵魂与元神之辨使这种叙事成为可能。“元神到底和灵魂有什么区别?”这是困扰无双(《摩合罗传·往事记》)许久的问题,也是解答飞花轮回叙事的关键。“灵魂就是一个生命的种子。世界上的有情众生都有一个种子,生命在六道中轮回,无论是在哪一道,这个种子都是不变的。”“元神就是一个人自出生以后产生的记忆,这个记忆是构成他一生的重要环节。人死的时候,元神便散了,所以当他转世后,就不会有上一世的记忆。但是有些人,他不太愿意忘记过去的事情,就算是死了,元神也不愿意散去,反而与灵魂纠缠在一起,被带入了下一世。”[5]轮回人物因灵魂与元神的双重性,一方面人物性格变得复杂,另一方面,元神的特征将历史串联起来,几世的经历合在一起,轮回叙事成为可能。
首先,轮回人物独特的性格因素,与灵魂和元神的二维性密切相关,由于元神带来了前世记忆,轮回形象具备不同于单一生命个体的复杂特征,人性与神性的冲突,几世记忆的羁绊,增添了轮回叙事人物性格的多维度。《倾国》里的妹喜与苏妲己,《摩合罗传·往事记》的无双和璎珞都是这种复杂性格的轮回形象。前世与今生的大相径庭为人物性格的矛盾性提供了可能,轮回人物挣扎于两世情与理的矛盾中,矛盾的叙述则利于复杂人性的凸显,便于情节冲突的展开。另外,融合了几世经历的轮回人物常常被赋予超人般的能力,《神仙学校·灵魂主宰》李锦绣的前世经历为魔幻人物的塑造提供了可能,两世的经历使人物富有奇幻色彩和传奇性,古今时空因此而结合得自然流畅。
超越轮回而独活下来的人性是寂寞而矛盾的,对轮回人物的关注,本来就是“从人间和幻界展示的意识形态狂欢化”,“表现在对于意识形态本体的关注上”,[6]同时更有利于典型人物的塑造和人物性格的关注。超越轮回的个体生命具有不同于常人的超人性格,他们可以拥有无限的生命,生存在人类几百年,所以他们具有几个生命个体的复杂感受,每经历一次轮回,他们所具有的生命体验在灵魂中残留下来,经过了几次转生,几世经历相融合便赋予生命个体历史性的眼光和超然价值取向,用这种眼光来观照每一个历史阶段都将带来不同的审美评判,飞花作品多借助此类人物的视角展开叙事,串联历史进而创作出独特的叙事效果。历史故事奇幻化是对历史事件的重构,将历史人物进行全新创造,原本单调的形象融入奇幻色彩和新的人文内涵,单薄的形象在奇幻舞台上变得立体化,历史在一个个鲜明的奇幻的形象帮助下得到了更好的诠释。
其次,轮回人物有助于从一种独特的视角来完成叙事,产生别样的叙事魅力。“这使他对人类不由地产生了厌恶的感觉,他想这些人虽然长得和他一样,但想法却完全和他不同。虽然猛兽很可怕,但他反而觉得比人类要更加可爱一些,因为它们不会有那么多的机心。”[7]作为社会群体的一份子,人类群体对历史的评判总显得不够客观和纯粹,只有通过对比才可以获得新奇的效果,山鬼用非人的视角观照了人类世界的弊病和荒唐,贪婪成为他控制人类灵魂的工具,而人类自身却从未觉察自己的缺陷,通过非人的视角来观照人类世界,然而非人的虚幻性使这种叙事变得不具可信性,只能够留在欣赏与消遣层面,而飞花轮回叙事里面出现的轮回人物则突破了这种局限,它契合了从古至今人们所信赖的轮回理念,人物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切合了普遍心理状态,通过轮回人物展开的叙事过程则具备了相对强烈的感染力,也更加增添了叙事的可信度。“人类,二千年来,不仅没有改变,还变本加厉地令人觉得厌恶”,也只有在这种叙事环境里才可以出现对人类历史性的反思。
用神的眼光来看待人类,人们习以为常的世界就变得陌生起来,在神的叙述中一些原本普通甚至不易察觉的叙事元素都变得独特而陌生,叙事主体的变化是产生这类叙事体验的重要因素,飞花轮回叙事里叙事主体就是这种不同常人的个体生命,或是超越轮回、转世多次的历史形象,或是误入人世的世外高人,而这一类形象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他们用不同于人类既定的价值取向和审美经验,用陌生化的视角来观照人类世界,反思一些人类自己已经忽略的东西,在叙事上达到了一种独特的审美效果。
三、轮回叙事的形式美
轮回叙事在执行过程中,紧密围绕轮回形象,因形象次第展开,又因形象本身所独具的轮回性特征(经历多次的转生和历史流转)为轮回形象带来丰富的故事性,所以在轮回形象的统筹下,叙事因人而动,将与人物相关的各时代叙事要素整合到一起,从而最大限度地融合故事元素,使叙事丰富而又有逻辑、流畅而不失曲折,在叙事上产生一种蒙太奇的效果,这一链条上的叙事都是建立在轮回形象意识流转和灵魂记忆之上的。人物的轮回,打通了古今、联合了前世与今生,叙事时空自由游走在古今的魔幻空间里,古代叙事与现代叙事相互融合映照,叙事具备了更大的包容性,古今叙事元素的比照、语言的古今对比创造了这种叙事的幽默和趣味,想象力也得到更大程度的发挥。
《大漠飞花》的叙事结构由两条并行线索组成,宁令哥与飞华以及小李飞刀与花非花各自处于自己的情节之中,古代与现代的故事虽毫无关联,但因两故事主人公内在的轮回关系,这两个故事之间便具备了相应的联系,叙事在形式上为人创造了一种新奇的体验,所以,在这类叙事里面,故事自身或许不足以打动读者,但加之叙事形式上的创新,形式美为小说增色不少,有时甚至超越故事情节而一跃成为读者品味的对象。
一方面轮回赋予叙事以形式的美感,同时也为叙事内容注入历史的厚重感,从而使奇幻叙事厚重不失其魅力,夸张而不流于形式,飞花借助这种方式演绎其新历史主义的叙事追求。
某一生命个体的轮回,相对于历史时序,个体生命是具有轮回性的,生到死,死到生,个体生命在某一历史时间段相对固定,然而轮回的生命较之历史则具有了循环性,历史的线性发展与个体生命的相对永恒性相映照,个体就具备了超越真实世界的能力,从而成为穿越时空进而串联各历史时期的关键,这就为奇幻叙事注入历史因素提供了可能,在轮回性个体生命的观照下,各历史时期的叙事要素得以重新组合,并在这个叙事平台上一同上演,奇幻与历史便紧密结合起来。历史叙事因素的加入,一方面为奇幻提供了大量的素材,更重要的是为奇幻注入了历史的内涵,使奇幻更具历史厚重感与文化气息;奇幻涉足历史则为原本枯燥的历史注入了新鲜的活力,通过解构、奇幻等方式为历史增添了戏剧性要素,时尚与传统、不羁与严肃的交融为此类叙事带来了无比的魅力和可延展性。
《烟花不堪剪》里的苏小小作为一个生命体体验了自己的生死,超然于历史时序,用一种灵魂叙事将死后几百年的经历串联起来,并巧遇李贺,解答了历史实际中李贺的《苏小小墓》的创作背景,虽奇幻却又合乎逻辑。
轮回赋予一系列无关联历史事件以严密的时空逻辑,“奇幻文学的叙事时空将线性时间构建成环形时间”,[8]使得本来无关联散落于各时期的历史片段成为一个轮回的整体,这不仅使历史要素被充分利用起来,叙事由原来那种依托一时一事各自独立的锁闭式结构成为一种包容性甚广的太极模式,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任何事件均有其联系的内在可能性,飞花常用的这种叙事突破了新历史主义叙事的时间局限,叙事依托某一特定历史场景,并将众多不同历史时期的场景联系起来,赋予其关联性。轮回叙事为奇幻故事增添了历史厚重感而又不失奇幻天马行空想象的张力,亦雅亦俗,亦真亦幻,奇幻而又不失其厚重,真实而不失其魔幻。
轮回叙事所带来的巨大魔力还与轮回观念所承载的人们的普遍心态密切相关。陈兵在《生与死——佛教轮回说》第一章“灵魂和轮回观念的产生”里,分析了这一人类的普遍心理:本能性的求生欲望和死亡恐惧、恋亲感情和同类相怜特异现象的启示、梦的启发。[9](2-6)由此可见,轮回的广泛认可度与它契合人类本能情感冲动、符合社会伦理道德内在理想等诸多社会因素紧密相连。轮回与人类情感的契合度也是促使轮回叙事产生巨大魅力的深层原因。“命运的玄妙正是在于它的不可超越与逆转,无论是人或神只得遵从于命运设计的路线上”,[10]正是命运成就了奇幻的悲剧性与崇高感,而轮回赋予生活以新的希望,企图借助轮回的力量弥补现实生活的无奈与悲凉,《甄宓》里的宓妃身处命运泥潭而不得自拔,她一生所经历的伦理上的折磨,生命的无奈与理想的丧失而最终自溺,正如作品开篇“宓妃,宿命是无法逃脱的,就算你化而为人,也一样无法逃脱终生寂寞的命运”所写,经历了神与人,这一世命运依旧无法摆脱前世的宿命,如果说现世是无奈的,那么只能寄希望于来世,借助轮回的流转来摆脱一世的悲凉,这也是轮回之所以为叙事带来巨大魅力的根源所在——现实、现世的无奈唤起了读者的共鸣,来世的美好与轮回的力量宣泄了精神的困扰。轮回叙事为读者提供了一条精神解脱的渠道,新奇之余感受精神上的解脱和畅快。
[1]竺摩法师鉴定;陈义孝居士编.佛学常见词汇[M].台湾:佛陀教育基金会印赠,2002.
[2]姚卫群.佛教的“轮回”观念[J].宗教学研究,2002(3):59-67.
[3]陈兵.生与死——佛教轮回说[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
[4]飞花.明玉珍·孔雀胆[DB/OL].晋江文学城,http://www.jjwxc.net/oneauthor.php?authorid=1007 3,2004-4-23.
[5]飞花.摩合罗传·往事记[J].今古传奇奇幻版,2008,(4B):64.
[6]韩云波.大陆新武侠和东方奇幻中的“新神话主义”[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5):65-68.
[7]飞花.神仙学校·灵魂主宰[DB/OL].晋江文学城,http://www.jjwxc.net/oneauthor.php?authorid=1007 3,2004-04-23.
[8]蒋勇.奇幻文学的叙事时空[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0(1):51-54.
[9]陈兵.生与死——佛教轮回说[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
[10]李婷婷.奇幻文学里的悲情因子[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9(6):30-35.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Historical Narrative Elements: Samsara Narrative of Fei Hua’s Fantasy Literature
JIANG Yo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Nowadays fantasy literature has gradually developed its own features based on its absorbing of the different narrative theories and its innovation. Feihua's samsara narrative puts the new historical narrative into practice, integrating the good points of historical narrative and magical narrative, which makes fantasy literature to broaden its narrative elements, thereby forming a fantasy narrative mode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fashion and tradition, freedom and the solemnness.
Samsara; Samsara portrait; Samsara narrative; new historicism
I206.7
A
1009-8135(2010)04-0045-04
2010-04-20
蒋 勇(1986-),男,山东曲阜人,西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文学。
(责任编辑:郑宗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