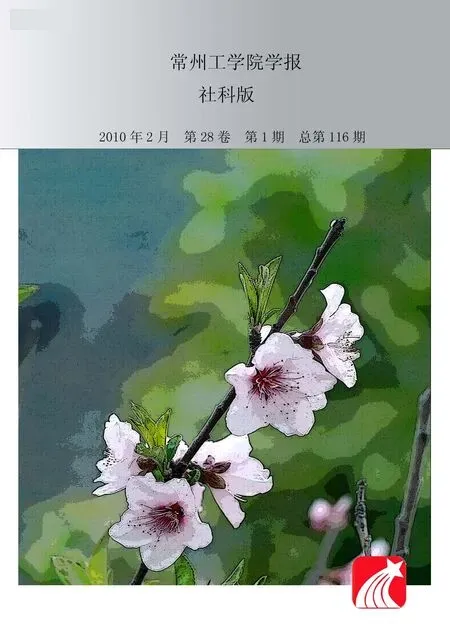从新时期初小说看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
陈智慧
(广东白云学院基础部,广东 广州 510450)
由于历史的惯性,从一个旧的社会秩序过渡到一个新的社会体制,必然要对过去的历史加以概括总结,反思之后才有新的开始。新时期初,经历了长久政治压抑的知识分子和大众,在新的思想文化的指引下,不可避免地要寻找历史和现实的理由,对漫长的悲剧历史进行自己的思考,对未来进行展望。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新的意识形态的建立,人们开始重新确立自己的身份定位、价值取向和人生目标。这尤其体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身上,在经历了十年浩劫之后,在与历史的对话中,他们又有怎样的文化心态?
一、集体话语与个人话语的合谋
回望历史永远是知识分子新时期以来无法逃避的选择,王蒙在《文学自由谈》1990年第2期上发表的《冷暖自知 言为心声》一文中提到:“回想一下我自己的这一生,我的写作,我觉得,我确实还是历史的回音,历史给我厚爱,历史给我启示,同时历史也给我以局限,甚至也有历史的牺牲,甚至我也找不到自己的命运了,因为我的命运完全变成了历史的回音,虽然我主张作家写得可以个人一点,也可以写得花样多一些,但实际上,我做不到,我的作品里除了历史的事件,还是事件的历史,这是一个很大的局限。”其实,这种用“春秋笔法”来书写个人与时代的关系在绝大多数“右派作家”的作品中都存在。在他们的作品里“政治”始终都是一根高度绷紧的弦,不仅牵连着故事的进展,也左右着主人公的行为和精神衍变。其中,“迫害”作为一个核心的意象,在主人公思维意识里不断得到证实和强化,然而迫害并没有动摇他们对祖国的热爱,爱国主义成了集体话语与个人话语的结合点。王蒙通过对钟亦成(忠又诚)二十余年非人的经历并没有摧毁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忠贞之心的人格的锻造达到了与集体话语的合谋。新时期初,意识形态—作家的内心需求—社会大众的阅读期待之间达成一致。它既达到了意识形态引导群众走向新的目标,实现社会转型,重建自身威信的目的,又满足了读者发泄愤怒的要求,另一方面,析解了读者和这段历史的关系,使他们由历史的参与者变成了历史的看客。
除此之外,诉说苦难也成为集体话语与个人话语的联结点。文革以后,思想解禁,大批被划为“右派”和在文革中遭受苦难的知识分子获得了诉苦的合法性。(诉苦是中国革命重塑普通民众国家观念的一种重要机制,诉苦过程往往被看做是一种分类的过程,并进而被理解为一种动员社会的方式,也重构了知识分子与周围世界的关系,包括与国家的关系。)在知识分子的诉苦过程中,不仅建立了消极的国家形象,把苦的来源归结于“四人帮”,同时也建立了积极的国家形象。而这一积极国家形象的建立,就是不断向国家主流意识形态靠拢,在赢得新的政治话语条件下,诉出自己曾经的苦处。王晓明这样形容“三十年代以后的中国历史,就是一部不断逼迫知识分子舍弃理性的自尊和自持的历史,一部不断逼迫她们向求生本能屈服的历史。从消极退让到主动迎合,从自我压抑到自我毁灭,知识分子面对社会的精神姿态越来越低,由后退而下跪,又由下跪而趴下——在‘文革’的最初几年里,知识分子在精神上成片成片地自动趴下”①。在早期的伤痕小说中,文本通过英雄人物罹难历史和光明结局的描写,凸显拨乱反正的政治现实。在这种叙事中,通过把“四人帮”确定为历史的罪魁祸首,使得自身获得批判历史和反思现实的主体地位。“伤痕”、“反思”小说的言说正是其所处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历史情境之下主导性的社会政治话语,其所从事的启蒙工作主要立足于社会政治层面,也就是说,他们的叙事目的主要还是为当时的社会政治实践进行“文学”的论证。
同时,集体话语与个人话语的合谋在知青文学作品中也异常突出。处于文化困境中的知青群体,在作品中表现出强烈的自我认同感。变革而来的焦虑,使一群年轻的知识分子找不到依傍,他们急于找到属于自己的空间,但却又不由自主地落入主流话语的漩涡。知青文学作家要为群体代言,福柯曾说:“知识分子本身是权利的一部分,那种关于知识分子是‘意识’和言论的代言人的观念也是这制度的一部分。”②替群体宣泄普遍情绪,帮助群体解决问题,就必须在创作时更多地调动关于这个群体的集体记忆,有意识地选择那些大多数人可以接受的故事,建构起能够被大多数人认可的知青文学历史图景。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历史图景一旦构建出来,反过来也会成为作家创作的“前文本”,进一步成为他们选择记忆的资源。
1979年前后,全国一千多万知青大批回城,迫切要求安排工作。大返城风潮意味着上山下乡运动的结束,也同时将知青群体变成了一个“虚拟性的社会存在”。就现实的知青个体而言,最迫切的现实需求是在城市找到自己的位置,但对于历史已经定性的“文革运动”的衍生物,城市并不总是含情脉脉。对于知青作家而言,他们被体制的断裂抛挤到一边,处于比较尴尬的文化生存地位,要想迅速融入主流文学界,就不仅需要接通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而且还必须为自己找一个好的出身,这一切都有赖于对自身所属群体的命名。我们如果把伤痕时期知青文学看作是一次向父母(党、祖国)哭诉自己的委屈和受到折磨的文学叙事的话,作为开场白,卢新华的习作《伤痕》引起那么大范围的共鸣与轰动就顺理成章了。我们同样可以在小说《蹉跎岁月》中看到知青作家的这种努力:作者塑造了主人公柯碧舟的高大形象,在不经意间接过了十七年的革命现实主义接力棒,成功占领了新的主流意识一席之地。
为什么知青文学选择了“我们”这种选择记忆的方式来展开想象?许子东说:“前十年证明自己无罪的文化动机制约着知青文学。青年人在文学中,有着过于强烈急迫的同父母家长化的社会对话的愿望,而不是首先同自己对话。”③在经历了新时期初的“我们的知青”写作以后,知青们逐渐找到自己的状态,80年代中期开始,知青作家又开始新的探索路径。以《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北方的河》为代表,知青文学开始以“我”而非“我们”来构建历史,书写青春。
而这一时期的另一个创作群体“五七作家”们,也都几乎无一例外,他们将自己的文学创作与现实政治需求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们的写作姿态,也一直试图与主流政治文化保持紧密一致。例如从维熙这样表达着他的创作初衷:“写过去,我要着眼于未来;写今天,我要联系过去。”张贤亮追求的是怎样使这种伤痕中本来就具有的那种缺陷美的光辉放射出来的理念,并指出痛苦的生活清楚地告诉了我们,个人的命运是和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联的。
二、启蒙主体的身份和精英文化性格
新时期初,“五七”右派和知青群体是这时的两大创作主体。一方面他们是以过来人的身份来回忆自身及民族的历史,同时他们作为文化知识分子,精英意识不自觉地复苏,传统文人那种兼善天下的介入意识和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情怀,使他们不能对现实处境漠然处之。他们以传统文人和现代知识分子的忧患和使命感,抨击时弊,伸张正义。最先在文坛上发出启蒙知识分子的声音,选择启蒙主义立场的是一群从文革过来的文学知青。《公开的情书》、《波动》、《晚霞消失的时候》都显示出他们开始以独立的姿态打量世界,不再相信传统的结论,靳凡在《公开的情书》中说:“我们深深苦恼的是为什么年轻人的思想这么混乱,似乎理论的危机已使很多人从根本上对未来丧失了信心。但我们努力探索着,希望我们的工作成为茫茫大海中的一盏灯,给年轻的朋友们指明方向。我们坚持不懈地努力,不让奋斗精神丧失,不让热情的火花熄灭。我们决心走一条和许多年轻人不同的道路——在理论上进行探索的道路。我们希望我们的思考成果成为扎在海底岩石之中的柱石,不管风暴多么猛,波涛多么大,那些被风吹散的船只能靠到这里拴住它们的缆绳。”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文革当中一代年轻知识分子保持独立思考的历史。也正是他们带来了文革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觉醒,带来了文学中知识分子启蒙话语的复苏。
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几乎每一个作家都充分表达了对人民命运的关注,努力履行着为人民鼓与呼的崇高承担,从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到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从茹志娟《剪辑错了的故事》到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大量作品表现着一个共同的观念:人民高于一切。他们在为人民代言的过程中充当了社会的启蒙者角色。《班主任》改变了知识分子作为“被改造对象”的身份,知识分子变成了启蒙者,而那些使知识分子蒙难蒙羞的“革命小将”重新变成了受教育者。
同时,启蒙意识的苏醒还表现在对国民性的批判中。虽然这种国民性批判并不像“五四”时期那么尖锐和深刻。这一时期国民性特征主要通过从解放战争到文革的转变达到对文革十年浩劫产生和发展的认识。正如高晓声所判断的:“李顺大在十年浩劫中受尽了磨难,但是,当我探究中国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浩劫时,我不仅想起李顺大是否也应该对这一段历史负一点责任。”《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中的许茂,在合作化年代,他爱社如家,关心群众,埋头苦干,公而忘私,然而到了“文革”,则变成了一个苍老、沉默寡言、自私、冷酷无情的人,大女儿病死了,他反对用他的木料做棺材,四女儿遭到不幸,他却不理解她,甚至不予原谅,还狠心地把她赶出家门。许茂老汉的变化,深刻揭露了文革中扭曲的人物形象,也揭示了农民自身存在的自私、狭隘、盲目与封建的思想。他们充当着文革时期的“跟跟派”,间接地导致了这场运动的广泛扩散。
三、知识分子的自省、忏悔意识
“五四”新文学传统中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精英意识的滋长,在新时期初不仅表现在对政治的虚幻热情上,而更多的是知识分子的自省意识和对现实改革的焦虑。一方面借助与主流政治的合流,恢复知识分子应有的社会地位和肯定自身的价值,同时逐渐回归到面向自身,这一时期是知识分子反思和批判自我的主体苏醒阶段。无论知识分子身处怎样的时代环境,面对怎样的道德准则、政治理念,其灵魂深处的思想相互纠缠、冲撞,总是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小说《我是谁》、《记忆》、《洗礼》都体现出人性结构中本能欲望与意识倾向之间的矛盾冲突。
这一时期王蒙的作品最具有代表性。他这一时期的作品基调,是对经历过历史浩劫的个人进入另一个历史阶段可能发生的变异的探究,质疑历史的必然延续性是他坚持的主题。从1978年到1980年,王蒙先后发表《最宝贵的》(《作品》,1978年第7期)、《悠悠寸草心》(《上海文学》,1979年第9期)、《夜的眼》(《光明日报》,1979年10月21日)、《春之声》(《人民文学》,1980年第5期)、《布礼》(1980)、《海的梦》(1980)、《蝴蝶》(《十月》,1980年第4期)。在这些作品里,王蒙并没有以他的书写使历史合理化,他没有竭力去展示苦难或表达人们的忠诚,他关注这些人的内心世界,以此表达文革后依然存在的当权者和人民的界线问题。王蒙延续了他在《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里的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思想显然有着极强的现实针对性,王蒙通过小说的人物剖析了历史人物的价值选择。
在小说《布礼》中,曾经充当“左派”势力的拥护者老魏这么反省:“我们这些人也可怜,说来归其,我们太爱乌纱帽了,如果当初在你们这些人的事情上我们敢于仗义执言,如果我们能更清醒一些,更负责一些,更重视事实而不是只重视上面的意图,如果我们丝毫不怕丢官,不怕挨棍子,挺身而出,也许本来可以早点克服这种‘左’的专横。”这些反省真实地刻画了历史人物的心理矛盾和内心困惑。内心困惑是一种对所认识到的对象感到迷惑不解的精神,是一种把握到多种可能乃至冲突性复杂解释的认知状态。困惑将赋予作家一种强烈的怀疑精神和有力的批判意识。
小说《蝴蝶》中通过儿子冬冬的口吻剖析知识分子:“您们当然站在党的立场,您们牺牲,您们从党那里得到的东西并不比您们贡献给党的少!就是现在您坐了监狱,您委委屈屈,您们每天的收入也比农民一年的收入多。而且,您们当然充满信心,不是今天就是明天,您们又会坐在市委书记的宝座上。”这种对知识分子深刻的剖析,显示出作者对知识分子历史主体地位的认可,并同时隐含了作者对自我的一种批判意识和谴责心理。
巴金从1978年开始写作《随想录》,也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一次个人反省,是老人对自己心灵的无情拷问,是一次伴随着内心巨大冲突而逐渐深入的痛定思痛的自我忏悔。在《十年一梦》中,他痛苦地喊出了这样的自责:“奴隶,过去我总以为自己同这个字眼毫不相干,可是我明明做了十年的奴隶!……我就是‘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隶。这个发现使我十分难过!我的心在挣扎,我感觉到奴隶哲学像铁链似地紧紧捆住我全身,我不是我自己。”④
张贤亮对自己身份的自觉思考则是把自己想象成为人民的对立阶级——“右派”身份开始的。这种对立不仅表现在他在农村接受人民的再教育,更重要的是作者刻意刻画他所反映出来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思想,这与他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如海喜喜、马缨花等劳动人民的正直善良品格形成对比,正是这种自觉思考的结果让他接受了“知识分子要接受人民再教育”的观念。正如郑也夫在《知识分子研究》一书中谈到的:“20世纪初中叶中国知识分子在接受了西方平等思想、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后,认识到自身社会的极大不平等。享受教育,实际上就是一种特权和罪过,因而对劳动人民负有债务,要去偿还,这种世俗原罪感可以使一个知识分子在自我谴责心理的驱动下,把自己的全身心奉献给人民。”⑤
注释:
①王晓明:《激流与漩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91年,第281页。
②(美)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 三联书店,1988年,第105页。
③许子东:《当代小说阅读笔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6页。
④巴金:《随想录》, 三联书店,2004年,第289页、291页。
⑤郑也夫:《知识分子研究》,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第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