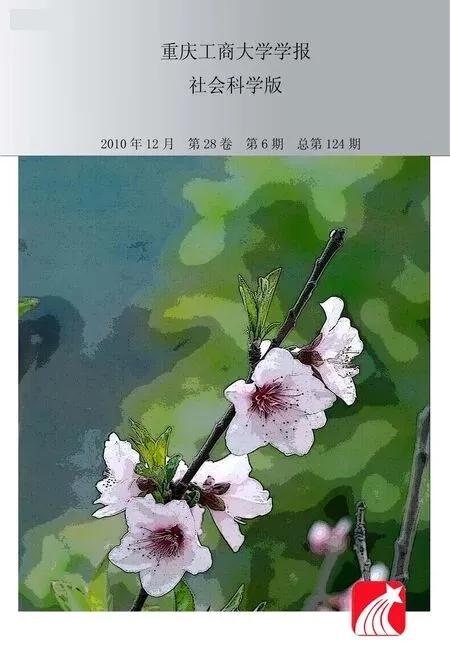稷下学风与孟子之“辩”
李 华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尽管梁萧统《文选》认为诸子散文“不以能文为本”,但《孟子》却因其平易的文风、流畅的语言、独特的论辩风格备受历代文人的推崇,尤其是孟子的“知言善辩”,历来被给予高度评价,孟子同时代的人“皆称夫子好辩”,[1]446孟子也因此被称为“剧之辩者”。[2]65《汉文典》在评价战国时代的诸子文章时,特别指出孟子善辩的特点:“逮至战国,孟子振响,善议论,长于讽陶,文最诀利。”[3]406
但是对于孟子论辩风格的成因,人们却着力甚少,或语焉不详,或将之简单归结为战国时代纵横游说的时代风气。然而《孟子》中的资料却并不支持这一观点,孟子本人就明确界定了自己与纵横家之间的差别:纵横家的论辩宗旨在于“以顺为正”,因而将之称为“妾妇之道”,而把自己所奉行的论辩宗旨称作“大丈夫”之道。通过这一界定可以明显看出,孟子的论辩与纵横家之间存在着本质性的差别。因此,把孟子论辩风格的成因归结于战国时代纵横家游说风气的观点显然也是值得商榷的。既然战国时代的纵横风气对孟子论辩艺术的形成影响甚微,那么影响孟子论辩艺术的外在因素又在哪里?在孟子生活的时代,齐国的稷下学宫——当时东方的学术文化中心——正处于鼎盛时期,而且据钱穆先生考证,孟子不仅在齐国居住长达数十年,[注]据钱穆先生在《先秦诸子系年》中的考证,孟子首次至齐,在齐国至少十八年;再次至齐,又居住了至少八年,这样算来,孟子前后在齐的时间合计共有二三十年之久。而且两次到达齐国,均“正当稷下盛时”,[4]273因此,讨论孟子论辩艺术形成的文化动因,稷下学宫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环节。
一、稷下的学术地位与孟子的“名辩”需要
面对世人对自己“夫子好辩”的指责,孟子曾辩解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1]446这句话传达出两层含义:一是,孟子善“辩”,在当时已成公认的事实;二是,孟子本身并不乐于“辩”,而是因为某些原因使他不得不作出这种选择。
那么迫使孟子不得不选择“辩”术的原因是什么呢?后人曾以《孟子》中的一段记载作为解释:“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陂行,放淫词,以承三圣者。”[1]448这段记载所描述的是盛行于战国后期的名辩思潮,当时杨朱、墨翟的学说影响最大,而儒家学说则面临“尧舜汤文周孔之业将遂淫微,正途壅底,仁义荒怠,佞伪驰骋,红紫乱朱”[1]10的式微态势,在这种背景下,孟子以“据杨墨”为己任,把重新确立儒家学说的地位,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正如《论衡·对作篇》所指出的:“杨墨不乱传义,则孟子之传不造。”然而“名辩”之“辩”与“论辩”之“辩”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前者指的是一种哲学概念的界定形式,后者所指的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一种话语方式。上述记载只是说明了孟子在“名辩思潮”中为儒家学说争取一席之地的必然性,但并没有解释出孟子为何选择“论辩”这一话语方式的真正原因。不过,上述说法的确为我们寻找孟子重视论辩的原因指出了方向:孟子选择“论辩”这一话语形式确实与孟子的“名辩”需要存在关联,而连结两者的关键环节就是当时作为学术文化中心的稷下学宫。
据钱穆先生考证,孟子两次到达齐国,均“正当稷下盛时”,这一现象并非偶然。孟子把重新确立儒家学说的主导地位作为他的主要学术目的,而此时的稷下,恰恰是孟子学说传播和推行的最佳平台。
稷下学宫,因靠近齐国国都临淄城稷门而得名。[注]据刘向《别录》记载“齐有稷门,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也。”《齐地记》也记载说:“齐城西门侧,系水左右有讲室,趾往往存焉。盖因侧系水,故曰稷门,古侧、稷音相近耳。”田氏齐国国君在此设高门大屋,广招天下贤士,“揽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5]1804给予优厚的政治和经济待遇,“为开第康庄之衡,高门大屋尊宠之”,勉其著书立说,讲习议论,这一政策吸引天下士人纷纷来齐,授徒讲学,相互争鸣,一时间这里成了诸子荟萃的学术园地,百家争鸣的讲坛和列国的文化中心。[注]虽然战国后期的学术中心并不止稷下学宫一处,如楚国的兰台、燕国的碣石宫等也均以贤士汇聚而著称,然而影响最大的却非稷下学宫莫属。《史记》载汉初刘邦曾拜当时的著名学者叔孙通为博士,并赐封号“稷嗣君”,徐广解释叔孙通获得这一名号的原因在于:“盖言其德业足继踪齐稷下之风流也。”由此可见,即便到了汉代初年,“稷下”一词仍然是对鸿学高儒的最高褒美。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在百家争鸣的战国时期,稷下学宫所具有的学术重心地位稷下学宫始建于齐威王时,到齐宣王时已达鼎盛,“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皆赐列第,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5]1486正如郭沫若所说,稷下是“学者荟萃的中心,周秦诸子的盛况是在这儿形成了一个最高峰的。”[6]157而孟子所生活的时代,又恰恰是稷下学宫发展最为鼎盛的齐威、宣王时期。当时每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几乎都曾有过游于稷下的经历,据《稷下钩沉》考证,在孟子前后,游历于稷下的学者姓名可考者有“淳于髡、彭蒙、宋钘、尹文、儿说、告子、孟轲、季真、接予、田骈、慎到、环渊、王斗、荀况、田巴、徐劫、鲁仲连、邹衍、邹奭共十九人。其中门派也很多,有道家、儒家、法家、名家、阴阳家。从墨学对稷下的影响来看,墨者也可能到过这里。总之,大抵战国各学派都在稷下留下了自己的印记。”[7]1作为当时的学术中心,稷下学宫中诸子荟萃,且又推行鼓励争鸣的政策,这均为孟子重新确立儒家地位的“名辩”需要提供了一个最合适的平台。可见,孟子要实现其“名辩”目的,稷下学宫是他的不二选择。
二、稷下“议论”风气与孟子对“辩”术的选择
说到论辩,则不得不提及齐国由来已久的好辩风气。在目前可见的汉代典籍中,对齐国民俗的记载往往离不开对齐人善辨的强调,如《史记·货殖列传》载:齐“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5]2464《汉书·邹阳传》载:“齐楚多辩知。”[8]1799《汉书·地理志》则指出齐人论辩中的夸张特点:“夸奢朋党,言与行缪,虚诈不情。”[8]1324《淮南子·要略篇》则认为齐国“民多智巧。”徐干《中论·核辩》在批评论辩风气的时候,特别引齐人为例,称:“俗之所谓辩者,利口者也。彼利口者,苟美其声气,繁其辞令,如激风之至,如暴雨之集,不论是非之性,不识曲直之理,期于不穷,务于必胜。”由此可见,齐人的好辩风俗在当时的诸国中不仅非常突出,而且特色鲜明。
再者,稷下学宫所实行的鼓励议论谈辩的政策,吸引大量善辩之士汇聚于稷下,并进而推进了谈辩风气的盛行。齐宣王给予游历于稷下的学者以极高的政治和经济待遇,勉励他们著书立说,讲习议论,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8]1486《盐铁论·论儒》载:“齐宣王褒儒尊学,孟轲,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宽松的学术环境和优厚的待遇,大大助长了稷下学宫的谈辩风气,而其中最突出的表现便是游历于稷下的知名学者,多为当时因善辩而著称的士人。郭沫若在《名辩思潮的批判》中提到的当时以论辩著名的士人,如列御寇、宋钘、尹文、儿说(亦名:貌辩、昆辩)、告子、公孙龙、墨家辩者、淳于髡、邹衍、荀子等,他们或为稷下之士、或曾到过稷下,总之均与稷下学宫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联系。例如《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记载的邹衍、邹奭、淳于髡三位稷下学者,便是因其不同的论辩风格而得名:“邹衍之术迂大而闳辩;奭也文具难施;淳于髡久与处,时有得善言。故齐人颂曰:‘谈天衍,雕龙奭,炙毂过髡’”。[6]1805而据曹植《与杨德祖书》李善注引《鲁连子》的记载,田巴的雄辩曾达到“一日而服千人”的效果:“齐之辩者田巴,辩于狙丘而议于稷下,毁五帝,罪三王,一日而服千人。”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与善辩之士的大量汇集,必然会使稷下学宫的谈辩风气得到进一步的推进,从而表现出强烈的崇尚谈辩的学术风气。
稷下对谈辩的水平和能力非常重视,甚至谈辩水平的高低会影响到一个士人在稷下学宫的地位高低。关于这点,《新序·杂事篇》中的一则记载颇具代表性:
齐有稷下先生,喜议政事,邹忌既为齐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属七十二人,皆轻忌,以谓设以辞,邹忌不能及。乃相与俱往见邹忌。
淳于髡之徒礼倨,邹忌之礼卑。淳于髡等曰:“狐白之裘,补之以弊羊皮,何如?”邹忌曰:“敬诺,请不敢杂贤以不肖。”淳于髡等曰:“方内而员釭,如何?”邹忌曰:“敬诺,请谨门内,不敢留宾客。”淳于髡等曰:“三人共牧一羊,羊不得食,人亦不得息,何如?”邹忌曰:“敬诺,减吏省员,使无扰民也。”淳于髡等三称,邹忌三知之如应响。淳于髡等辞屈而去。邹忌之礼倨,淳于髡等之礼卑。
淳于髡等人最初轻视邹忌,所以“设以辞”以相辩难,然而辩难的结果却出乎他们的意料:淳于髡不仅没有难倒邹忌,反而因自己的“辞屈”而败下阵来,于是两人的地位立刻产生了逆转,失败的淳于髡由最初的“礼倨”变得“礼卑”,而胜利的一方却由最初的“礼卑”变为“礼倨”。 通过上述记载可见,在稷下学宫,一个士人谈辩水平和技巧的高低,几乎决定了他在稷下学宫地位的高低,可见稷下学宫的学术风气,对“论辩”的能力和水平,有着非同寻常的要求。这也意味着,因“息邪说,距陂行”的“名辩”需要而游历于稷下学宫的孟子,必须采用当时稷下所通行的“议论”方式,来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而且需要在“辩”术上过关,才能在学者云集的稷下学宫占据一席之地,争得儒家学说在稷下的话语权。这是孟子实现其名辩目的的首要前提,同时也是孟子“不得以”而“辩”的真正根源。
三、稷下“谈辩”之风与孟子对论辩技巧的重视
稷下所盛行的谈辩风气,使得任何一个期待在稷下学宫获得关注的学者,都必须首先在辩术上有所成就。稷下学宫重视“议论”的风气,直接促成了孟子对论辩技巧的思考与重视。尽管孟子称自己的论辩是“不得以”的,是被动的,但在《孟子》中,我们却能够发现孟子对“辩”的价值的正面强调,以及在此基础上对论辩技巧的思考与传授。
孟子曾提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孟子·离娄下》)孙奭对此句的注疏深得孟子之旨:“孟子言人之学道,当先广博而学之,又当详悉其微言而辩说之,其相将又当以还反说其至要者也。以得其至要之义而说之者,如非广博寻学,详悉辩说之,则是非可否,未能决断,故未有能反其要也。是必将先有以博学详说,然后斯可以反说其约而已。”孙奭在这一段注疏中三次强调:广博的学识只是学问之道的前提,而详细了解如何“辩说”,即深谙论辩的技巧和方式,才能是达成学问之道的门径所在。按照孙奭的解释,孟子此句是强调博学和雄辩在推行其学说过程中的重要性,并尤其突出了“辩说”的重要功能。而以博学为基础,以雄辩为手段的治学途径恰恰与稷下学宫重视论辩的学术风气若合符契。无独有偶,焦循在《孟子正义》中对这句话的阐释与孙奭如出一辙,同样也是强调了“详说”的重要性:“不博学而徒凭空悟者,非圣贤之学,无论也。博学而不能解说,文士之浮华也。但知其一端,则敬而非要;但知其大略,则浅而非要;故必无所不解,而后能知其要。博、详与约相反,惟博且详,反能解得其约;舍博且详而言约,何以能解?”两位最权威的《孟子》注释者不约而同地强调了孟子此句中的“详说”这一因素,甚至认为“博学”不过是前提,而能够“详说”才是学术活动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关键因素。通过孙奭和焦循的进一步解读,我们能够看到,“辩”在孟子的整个学术思想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孟子对论辩的重视不仅表现在对论辩价值的强调上,而且还体现在其对论辩技巧的思考和经验的传授上。
孟子与齐人弟子公孙丑所讨论的“知言”说,一向被视为反映孟子思想的代表性论述:
“何谓知言?”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 (《孟子·公孙丑上》)
人们向来更为重视孟子“知言养气”说的整体内涵,然而却忽视了孟子的“知言”说中所蕴含的文学价值。孟子在回答弟子关于“知言”的疑问中,把言辞详细地分为“诐辞”、“淫辞”、“邪辞”、“遁辞”几个类别进行讨论,并分别指出每类言辞的薄弱环节。显然,孟子的这一理论是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思考之后,对各种言辞弊病的规律性总结。结合稷下学宫对论辩水平的高度重视,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孟子》中所展现出的“论辩”风格曾经经历过一个有意而为之的思考和训练过程。
与此同时,孟子有意识地把论辩的相关经验和技巧传授给他的弟子。除了指出每种言辞的薄弱点所在以外,孟子还直接或间接地去引导弟子的论辩,如:
孟季子问公都子曰:“何以谓义内也?”曰:“行吾敬,故谓之内也。” “乡人长于伯兄一岁,则谁敬?”曰:“敬兄。”“酌则谁先?”曰:“先酌乡人。”“所敬在此,所长在彼,果在外,非由内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将曰‘敬叔父’。曰:‘弟为尸,则谁敬?’彼将曰‘敬弟。’子曰:‘恶在其敬叔父也?’彼将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须之敬在乡人。’”季子闻之曰:“敬叔父则敬,敬弟则敬,果在外,非由内也。”公都子曰:“冬日则饮汤,夏日则饮水,然则饮食亦在外也?”(《孟子·告子上》)
孟子的弟子公都子在论辩中遇到了困难,面对别人的诘难而“不能答”,公都子便把论辩的相关内容“以告孟子”。而孟子则根据弟子的描述,推测出在论辩过程中有可能出现的观点和应对方式,如此经过孟子的指点之后,公都子再继续与其论敌进行论辩。上述引文正是详细地描述了这样一个孟子对论辩的技巧进行言传身教的过程。
可见,稷下学宫中重视论辩的风气,迫使需要在稷下获得一席之地的孟子不得不选择与之相应的语言方式——“论辩”,并对论辩的技巧给予足够的重视,这正是孟子“不得已而辩”的深层原因。同时可知,孟子论辩艺术的养成并非一日之功,孟子的有意为辩以及对论辩技巧的传授和总结,均得益于稷下学宫重视论辩的学术风气。
四、稷下争鸣与孟子的论辩风格
稷下长期争鸣论辩的浸染熏陶不仅大大提高了孟子的辩术,同时也影响到了孟子的论辩风格。孟子之辩具有“驳”与“博”两大特色,“驳”是指孟子的论辩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不同于以往诸子坐而论道的言说方式;“博”则是指孟子的论辩内容涉及的范围广泛、包含的知识丰富。而这两个特点,均与稷下学宫重视谈辩的风气密不可分。
(一)诸子辩难催生了孟子语言的驳论色彩
《孟子》一书记载了孟子的多次辩论,纵观与孟子论辩的各个学派的人物,我们发现他们多为稷下学士,至少也有过游历于稷下的经历。如其中较为著名的几次论辩有与稷下先生淳于髡的两次辩论,和宋钘的辩论,和告子的辩论等等。当然除了稷下学士之外,孟子还和自己的弟子也有所辩论,这应当也得益于稷下授徒讲学的经历。
查看《孟子》中的论辩,会发现《孟子》七篇具有论战性强,感情充沛,言辞机敏,气势雄健,锋芒毕露的特色,和《论语》等诸子论著的雍容纤徐的风格迥然不同,孟子不再局限于坐而论道的方式,而是更多地采用了针锋相对、声色俱厉、咄咄逼人的辩驳手段,因此与之前的诸子论著相比,《孟子》中出现了大量以反驳为内容的文章。以孟子与淳于髡的一次论战为例: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礼也。”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孟子·离娄上》)
在这里,《孟子》已经打破了以往的诸子文章中设立论点、坐而论道的方式,而是面对真实存在的论敌,采取了有立有驳,有破有立的论辩。这种针锋相对的驳辩方式是孟子论断的主要特色,甚至有文章把称孟子之文为“以反驳艺术见长的辩对散文”,并推崇《孟子》为“我国古代辩对散文的开元者”和“驳论文体的滥觞”。[注]这一论断是否符合先秦散文发展的事实虽然值得商榷,但是对孟子论辩所存在的驳论现象的强调却是慧眼独具的。相关文章参见张惠仁《孟子——我国古代辩对散文的开元者》,四川师院学报(哲社版),1980年第3期,第12页。针对这种以反驳见长的艺术手法,谭家健在《先秦散文纲要》中的分析颇为肯綮:“《论语》中有人讥笑孔子,孔子并没有同他们辩论。墨子曾多次非儒,但儒家观点全系引述,批的是死靶子。庄子肆意嘲儒,儒者形象均为虚构,批的是假靶子。孟子则不同,他和其他学派的争辩十分激烈。墨者夷之、农家许行、言性者告子等人,都坚持自己的观点。孟子批驳他们,针对的是活靶子。因而文章显得格外活跃,双方观点鲜明,针锋相对。”[9]105谭家健先生明确指出,真实存在的论敌,是孟子论辩展现出强烈的驳辩色彩的根源。而这些真实存在的论敌,又往往主要集中于齐国的稷下学宫。
由此可见,稷下不仅为诸子提供了高门大屋,金钱地位,使之能够全心致力于学术,最为重要的是为诸子提供了真实存在、观点鲜活、且善于论辩的论敌。而也正是这点催生了孟子论辩艺术中的驳辩色彩,使之展现出强烈的论战特点。
(二)“相灭相生”的辩驳风气造就了孟子论辩的博学特点
钱基博评价孟文“包罗天地,摇叙万类,以浩然之气,发仁义之言;无心于文,而开圃抑扬,高谈雄辩,曲尽其妙;终而又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己也。’一纵一横,论者莫当。”[10]33王正德《余师录》认为:“孟子极于辩博”。 他们都认为孟子论辩的精彩在于他的“揆叙万类,无所不包”,即孟文具有一种包罗万物的百科全书性质。
这种“无所不包”的特点在论辩思想上的表现是,孟子的思想除了韩愈所说的“醇乎醇”的儒家思想以外,还对当时各派的思想有广泛的吸收。“孟子久居于齐,同稷下先生们常有交往,难免要受到稷下学术的影响而反映到他的学说中来。比如说,孟子‘养心莫善于寡欲’之说,便与稷下先生宋钘的‘情欲寡浅’说有关;孟子心性学说中的‘养浩然之气’、‘存夜气’之说,是吸收改造了《管子》中道家学派的心气理论;孟子的富民思想有不少是对《管子》中有关政治经济思想的直接吸取;孟子思想中最有价值的民本思想也是对稷下民本思想的吸取和发展,‘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名言,就是在稷下学有关思想的影响和启发下提出的。”[11]160再如孟子所提到的 “关市讥而不征”等经济思想,则明显源于齐国稷下管子学派的经济思想。另外,《孟子》中还展现出了丰富的齐国风土人情,政治经济政策,这些内容也往往成为孟子谈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种“无所不包”的特点表现在论辩内容上,便是论辩中展现出的鲜明的博学特色。例如据《韩非子·外储说》记载,儿说曾持“白马非马”的观点,在稷下学者的论辩中获得了胜利,而孟子在齐所作的“人性之辩”,便吸收了儿说的“白马”说作为辩说素材,以“白马之白”与告子讨论人性论的问题。再如孟子的“坚白之辩”,与现存的《公孙龙子》中的说法多有相同之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孟子对公孙龙子一派观点的吸收。而孟子最为著名的“天时、地利、人和”的观点,在《鶡冠子》中也曾有出现:“故善用兵者慎,以天胜,以地维,以人成,三者明白,和设而不可图。”所不同的是,《鶡冠子》的论述重点在于强调用兵的战术,认为必须按照天时、地利和敌我对峙的形势,集中优势兵力,迅速而勇猛的趁“虚”进攻,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而孟子则是吸取了影响战争成败的三大因素“天时,地利、人和”,用以宣扬自己的仁义思想。由此可见,孟子论辩中所表现出的广博特点,并非无本之源,而是往往得益于整个时代中所保存的诸子智慧,而这些智慧本身,又主要源于诸子备至的稷下学宫以及“相灭相生”的稷下议论风气。
鼎盛时期的稷下吸引天下之士纷纷来齐,几乎各个学派在当时都有其代表人物在稷下,这种局面势必会造成各家思想的相互激荡和吸收。刘歆对“九流十家”之间的关系,曾有一段精彩的评论:“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8]1378这一论断如实地指出了战国时代诸子论战的实质,那就是通过论辩的形式,达成与不同派别之间观点的交流与切磋,从而吸收论敌的合理的观点到自己的学说中,以完善自己的学说为根本目的。而稷下诸子也正是在这种“相灭相生”、“相反相成”的对立统一过程中,通过互相批评和驳难、互相吸收和学习而完成各自的发展与交融的。后于孟子的邹衍曾总结稷下的论辩经验说:“胜者不失其所守,不胜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辩可为也。”[5]1821由此可见,论辩的胜利固然重要,但是,通过辩难而相互切磋学习,交换各家的知识与观点,才是诸子论辩的真正意义和目的所在,这一情况对于稷下学宫中参与论辩的士人具有普遍的适用性。稷下学者很重视在论辩中吸收别人的观点,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阴阳家以及其他各家,都表现了一种兼收并蓄、融合各家之长的倾向。“如慎到,是道家黄老学派,又是法家;宋钘既接近墨家,又能街谈巷议,是小说家;淳于髡是儒而法,邹衍是儒而阴阳,荀子则是把儒、墨、道、法诸家融为一炉的新儒家”。[12]51荀子把这种学风总结为“有兼听之明,而无奋矜之容;有兼复之厚,而无伐德之色”,而这种“兼听”和“兼复”,恰恰是各家通过论辩而在切磋中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的过程。这也必然会造成孟子对各家学说的融会贯通,并把这种融会贯通体现到其论辩中。由此可见,孟子论辩的博学特色在很大程度上也受惠于稷下的议论交流风气。
总之,孟子的“好辩”决非偶然,其背后有着整个稷下士人群体和社会环境的强力支撑,说稷下之风是孟子论辩的活力之源,是当之无愧的。
[参考文献]
[1] 焦循. 孟子正义[M]. 北京: 中华书局,1987.
[2] 严可均.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 北京: 中华书局,1958.
[3] 来裕恂. 汉文典·文章典 [M]. 上海: 商务印书馆,1906.
[4] 钱穆. 先秦诸子系年[M].上海:商务印书馆,2002.
[5] 司马迁. 史记[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6] 郭沫若. 十批判书[M]. 上海: 东方出版社,1996.
[7] 张秉楠. 稷下钩沉[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8] 班固撰,颜师古注. 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2005.
[9] 谭家健. 先秦散文纲要[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
[10] 钱基博. 中国文学史[M]. 北京: 中华书局,1994.
[11] 白奚. 稷下学研究:中国古代的思想自由与百家争鸣[M]. 北京: 三联书店,1998.
[12] 李钟麟. 孟子与稷下之风[J]. 船山学刊,20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