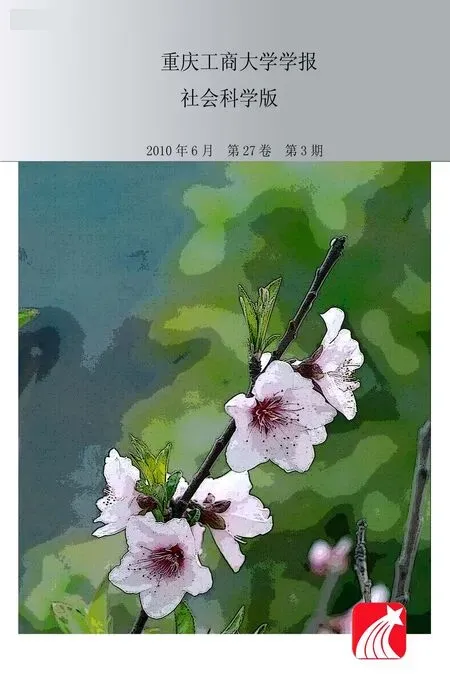多重视角下的乌托邦评述
董四代
(武夷学院 管理系,福建 武夷山 354300)
“乌托邦”一词源于英国作家托马斯·莫尔的同名小说。它的原意是“乌有之乡”,自从严复用“乌托邦”一词将其译成中文以后,就成为学术界普遍认同的概念。人们将它与佛教中的“华严界”、古典散文《桃花源记》中的“世外桃源”相提并论,同时又用它来表达不切实际的幻想,成为空想社会主义的代名词。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乌托邦并没有失去自己的意义,人们在不同的背景下,从多重视角上揭示了乌托邦的含义。
一、乌托邦与意识形态
德国学者卡尔·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阐释。他认为,每一种政治都需要自己的意识形态,在这种统治没有确立之前,批判现实的追求都有乌托邦的色彩,但统治秩序确立以后,其中有些转化为意识形态,而另一些则成为乌托邦。他说:“现存秩序产生了乌托邦,反过来,乌托邦又被破坏了现存秩序的纽带,使它得以沿着下一个现存秩序的方向自由发展。”[1]409因此,他认为乌托邦在历史发展中有重要的作用,并指出:“乌托邦的消失带来事物的静态,在静态中,人本身变得与物没有什么两样。于是我们将会面临可以想象的最大的自相矛盾状态,也就是说,达到了理性支配存在的最高程度的人已没有任何理想,变成了不过是有冲动的生物而已。这样,在经过长期曲折的,但亦是英雄式的发展之后,在意识的最高阶段,当历史不再是盲目的命运,而越来越成为人本身的创造物,同时当乌托邦被摒弃时,人便可能丧失其塑造历史的意志,从而丧失其理解历史的能力。”[1]539
卡尔·曼海姆认为,历史就是在对现存秩序的批判中形成乌托邦,并不断追求新秩序的过程中发展的。他把受压迫者视为乌托邦的追求者,认为:“某些受压迫的群体在理智上如此强烈地对破坏和改革既定的社会状况感兴趣,以致于他们不知不觉地仅仅看到局势中那些倾向于否定它的因素。”[1]83对于追求社会主义的人们来说,“只要他们在与现存世界的关系中还是局外人,那么,乌托邦、观点和行动三者的统一便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1]529
二、蓝图乌托邦与过程乌托邦
乌托邦大都有一种不同于社会现实的理想社会蓝图,这种蓝图就是对理想社会的设计。赫茨勒说:乌托邦思想家“给我们描绘出来某一时代或某一地方的图景;那里会充满公正、友爱、和平、富裕和幸福。”[2]251这样就可以“扫除当前社会和道路的弊端,与他们的时代决裂,摒弃旧的传统和宗教、政治偏见,消除那些阻挠他们前进、使他们不得自由的种种遗产,摆脱‘现行的’陈词滥调,超越他们所处的时代”[2]429。如果把乌托邦视为在对现实不合理的批判中表现出来的一种追求精神,也就是看做一种过程,则能更多的体现出它的批判超越性。这就如莫里斯·迈斯纳所说:“历史的动力(而且的确是一种历史必然的动力),不是乌托邦的实现,而是对它的奋力追求。正像韦伯曾经指出的:‘人们必须一再为不可能的东西而奋斗,否则他就不可能达到可能的东西了。’”[3]92他还说:“维克多·雨果乐观地宣称,乌托邦也许并不是‘明天的真理’,但是人民拥有想象一个美好未来的能力,这对于做出有意义的努力去改变今日之现状却是至关重要的。”[3]2如果说人们在追求美好未来的过程中,形成了并不断保持着对现实的批判超越精神,则可以发现现实的不完美,坚持与时俱进,从而形成历史发展的精神动力。
社会发展是一个过程,蓝图乌托邦强调的是目标的完美性。作为历史进程中的人们,有一盏理想之灯是形成不懈追求精神的必要条件。但是,如果把这种蓝图转化到现实中,则否定了现实中许多合理的东西,必然造成理想之灯的熄灭和社会秩序的破坏。因此可以说,乌托邦的积极意义更多地是体现在精神追求的过程之中,体现在它对现实生活的“诊断”并追求一种社会健康发展的理想境界。
三、传统乌托邦和现代乌托邦
传统乌托邦是在传统社会里出现的社会理想。由于自然经济的社会背景和文化上的封闭性,这种乌托邦是把人类的“黄金时代”视为已经过去的历史,以歌颂古代的方式反对现实,或者是把理想社会置于彼岸的“天国”,以表示对现实不平等的抗议。现代乌托邦是随着现代性的产生而出现和发展起来的。现代性以理性主义为核心,主张市场原则至上,追求效率、自由、平等,它在推进科学技术发展、经济效率提高、政治民主化和人的自主创造性发挥中,又导致了工具理性主义的张扬,造成了贫富分化、民主法制形式化和人的异化,并激化了各种矛盾。艾森斯塔特说:“现代性不仅预示了形形色色宏伟的解放景观,不仅带有不断自我纠正和扩张的伟大许诺,而且还包含着各种毁灭的可能性:暴力、侵略和种族灭绝。”[4]67现代性是被编入资本主义的密码运行的,但“现代乌托邦主义被启蒙运动的一些核心观念——历史进步论、可完善论和乐观主义所滋育”[5]34而发展了起来。现代乌托邦随着现代性的悖论发展了起来。资本主义造就了现代文明,但从来没有实现真正的自由和平等,现代乌托邦先是以空想社会主义的形式出现,后来又成为人们批判资本主义,追求人的解放的学说。曼弗德认为:“即便是‘头脑最为简单的’乌托邦,也‘拥有显著的人类品性’……显而易见,同科学的与军事的‘现实主义’相比,高估了理想力量的乌托邦理想主义者要更为充分地拥有他们的理智,而且也更为紧密地同人类的现实联系在一起。”[6]260现代乌托邦的意义体现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以超越性追求实现人的解放。
现代性不仅使市场原则成为至上的命令,而且“工具理性的极大膨胀,的确带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赢得了人类对自然的胜利,但是与此同时,在追求效率和实施技术控制中,理性由解放的工具退化为统治自然和人的工具。”[7]89现代性的悖论是现代乌托邦产生和发展的根据,现代乌托邦都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但它又在对现代性悖论的批判中保持着自己的生命力。拉塞尔·雅各比说:“在政治让位、疲软的时代,乌托邦精神仍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必要。它唤起的既不是监狱,也不是规划,而是关于人类休戚与共和幸福的理想。”[6]274
四、乌托邦与宿命论
乌托邦在对现实的批判中追求未来,因而总是能集中人类智慧,引导人们突破现实的局限,树立一个更高的目标。赫茨勒说;“乌托邦思想家在他们各自所处的时代,都毫无例外地表现为思想上富于独创性和建设性思想力的人……他们是面对着一片荒野却看到了一座乐园的人。”[2]251-252他还说:“指南星并不因为永远不能达到而失去其指南的作用。理想是目标,也是向导。因此,现实和理想虽有很大差距,但我们知道,除非有一个崇高的理想树立在它的面前,现实是不会有长足进步的。”[2]266-267而宿命论或是使人们满足于现实,按照现行的规则行事,或是视理性为至上命令,这就不能形成解放的追求,从而使人们在追求时尚中失去理想,在理性的支配下成为“单向度的人”。因此,拉塞尔·雅各比说:“与其说单调乏味出自乌托邦主义,不如说更多地源自乌托邦主义的缺席”[6]259他在评价“9·11”后西方社会情景时说:“如果没有乌托邦冲动,政治就会变得苍白无力、机械粗暴,而且往往会沦为西西弗式的神话;尽管它一个接一个地堵塞漏洞,船舱却垮塌了,船也就沉没了。自然,水漏是应该被堵塞。但是,我们也许需要一艘新船,需要一种理想;当水面上升,船员和旅客惊惶失措之际,我们很容易忘记这一理想。”[8]196
宿命论造成了人们追求感官刺激,导致听天由命和无所作为,失去的是对现实的反思和批判,从而听任理性的摆布,成为理性控制下的不自由的人。乌托邦使人们在对现实的批判中燃起追求未来的激情,克服线性思维的局限,寻求社会的和谐和丰富多彩,从而形成一种面向未来的创造精神。或者说,乌托邦可以打破社会发展特定状态造成的局限,不断探索从现在走向未来的道路。也许它对未来的设计有不可行性,但追求未来的精神却使人们有一种批判的超越精神。
五、乌托邦与极权主义
乌托邦与极权主义的关系是一个仍有争议的问题。人们把理性分为客观理性和主观理性,并以此为根据认识社会的发展。艾森斯塔特认为:“总体性把不同的合理性合并在一起,其中最重要的便是理性高于一切的原则(它经常被看成是启蒙时代的中心思想)。这一原则把价值理性或实质理性统摄于以技术统治为特征的工具理性之下,或者把它统摄于一种总体化的道德乌托邦理想之下。在某种情况下,例如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里,技术统治论和道德乌托邦理想可能还会在极权主义笼罩下进一步结合起来。”[4]86-87也就是说,客观理性即工具理性和主观理性即道德理性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制度选择。拉塞尔·雅各比则认为:许多人“对绝对体制的谴责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对乌托邦的谴责,似乎它们有着明显的联系一致。它们是真的有联系吗?事实上,极权主义和乌托邦主义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最起码,如果不将乌托邦主义这一概念扩张到含糊暧昧之中,而要在纳粹主义里面找到乌托邦主义,就是非常困难的事情。”[6]69-70应当说,专制主义的根源并不在乌托邦,但在把乌托邦实践化的努力中也有导向专制的可能。
有学者认为计划经济是一种同样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历史设计,“相信存在着一种全知全能的科学来指导人类完成进步事业,这是最大的乌托邦,一种历史哲学的乌托邦。”[9]93也就是相信发现了终极真理,然后按照它的启示进行实践规划,以主观理性为原则进行社会构建,从而形成与专制主义相联系的乌托邦。在计划经济下,形成了权力控制社会的机制。同时,在社会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建立理想社会,就突出了道德在其中的作用。与以上相联系,道德乌托邦要求有一种英雄崇拜,于是就在这种崇拜中形成了群众运动,这既使人们失去了自我理性判断的可能,又开通了走向极权的道路。因此,乌托邦的意义只存在于从现实走向理想的批判性超越中,而不在于实践化。
六、乌托邦与社会变革
乌托邦体现着对现实的批判和对理想的追求,因而在政治革命中可以成为发动群众的思想武器。在实际斗争中,任何纲领都有不同程度的乌托邦色彩。弗雷德里克·波拉克说:精英人物“ 创造了一些比现实更好的未来社会的积极图景。其中的某些图景恰巧同智力上的洞察力和审美上的要求相结合,产生了同当时社会的和精神的种种需要的共鸣,在民众中唤起了极大的热情。于是,社会便被这些把人民引向另外一个更美好未来的幻想的力量点燃了。这些幻想中所包含的种种诺言通过历史的过去和现在爆发出来了,同时又打开了通向被隐蔽着的现在与未来的大门。”[3]19在不具革命条件的社会改革中,乌托邦既体现着对现实的批判,又提出超越现实的社会理想。这就有利于在认识现行体制的弊端中形成改革方案。所以,拉塞尔·雅各比说:“我们并非只能在理性的建议和非理性的乌托邦两者中间选择。乌托邦思想既不曾破坏也没有贬低真正的改革。事实上,情况正好与此相反;切实可行的改革有赖于乌托邦梦想——或者至少可以说,乌托邦理想推动着与日俱增的进步。”[8]2
任何社会变革都有一种民众的期待心理,这样,“任何的主张都带有理想性,理想总是无法立即、充分且完整地被实践。理想之所以称之为理想,事实上正是由于它不可能被完全实现。因此,理想与现实之间必然有距离,这种距离是理想与现实隔开,但又产生关联的关键所在。”[10]119尽管乌托邦是不能实现的,但正是它包含的批判现实的超越性引导着社会的发展。
乌托邦是社会发展中的一种非理性力量。因此不能以理性主义的逻辑框架证明它的正确与错误。它的内涵的丰富性要求从多视角上对它进行把握。应当承认,在多数情况下乌托邦都与社会主义有联系。因此,我们还不能轻言“告别乌托邦”,而是必须深刻把握它的含义,并在特定背景下认识它在社会发展中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M] .姚仁权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
[2] 乔·奥·赫茨勒.乌托邦思想史[M].张兆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3] 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M].张宁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4] 艾森斯塔特.反思现代性[M].旷新年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
[5] 谢江平.反乌托邦思想的哲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6]拉塞尔·雅各比.乌托邦之死:冷漠时代的政治与文化[M].姚建彬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7] 汪民安.文化研究关键词[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8] 拉塞尔·雅各比.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M].姚建彬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9] 刘怀玉等.走出历史哲学乌托邦——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当代沉思[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10] 叶启政.期待黎明:传统与现代的搓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