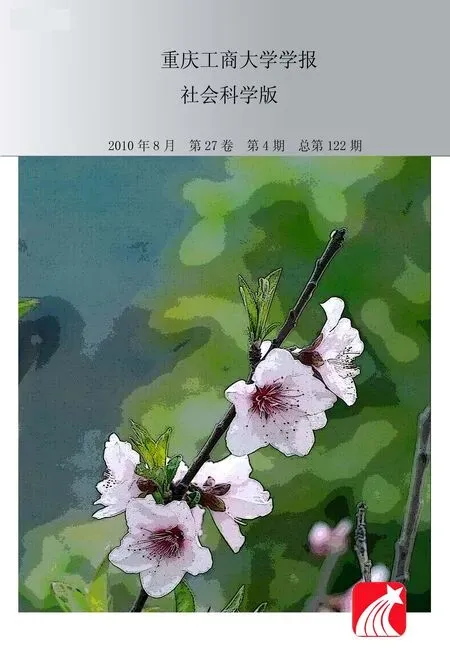美国环境史研究的源起
刘二艳,张国平
(1.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重庆 400715;2.国家气象局,北京 100087)
环境史作为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兴起的学科,归属于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历史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及以自然为中介的各种社会关系,研究的主题集中于重构自然生态系统的历史、社会经济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国家及国际的环境政治与政策和人类的环境思想史。它发祥于美国,是历史学科中前沿的学术研究之一。美国环境史的研究最早可以上溯到西部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他于1893年在美国历史学会上宣读的《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部分地涉及了环境史,[1]遗憾的是他并没有深入研究下去。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的学术从单一走向了多元,传统史学的囹圄被突破;面对着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环境运动如火如荼;历史学家自觉的人文关怀,开拓了研究人与环境的新课题,环境史应运而生。1976年,一群历史学家、环境伦理学家、文学学者成立了以约翰·奥佩为会长的美国环境史学会,同年,发行了会刊《环境评论》。此后,专业团体的人数不断增加,研究范围不断扩大,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人物和著作,环境史的研究蔚然成风。究其源起,可以说是史学理论的创新和环保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一、历史理论的创新
历史理论的创新开启了学者对环境史的研究。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在《历史》中零散地提及了环境的影响;我国战国时期的士人孟子对梁惠王劝告到:“不违农时,谷物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 ;[2]司马迁的《货殖列传》中着重记载地理条件的状况、生产的状况以及经济生活和社会风俗的表现,不同地区在这些方面的相异或相同之处。[3]在他们的论述中提到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人们应该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以及注重地理因素的看法也只是只言片语,即使鸿篇巨制的《资治通鉴》也只是为了总结历史,向帝王阐述治人的经验。中华两千多年的历史,似乎就是人治人的历史。在中国古代,人类对环境的认识水平尚处在初级阶段。可贵的是,在世界历史长河中,不乏高瞻远瞩之人。中世纪阿拉伯伟大的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就提出了许多关于环境方面的具有创新性的理论。近代以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士人的自觉,我们对历史的研究也慢慢地摆脱了以上层人物为核心的政治史、战争史和外交史等“人事的历史”。“旧史学,即使它认识到自然和社会的存在,也只是将它们作为布景和背景,而环境史将它们当作活跃的、塑造性的力量。”[4]当下,历史研究关注更广泛的群体,如自然、穷苦大众、妇女、儿童 、同性恋者,历史学的范围和想象得到了一次根本性的拓展。“史家像这样开始关注曾经无权无势的群体,当然体现了历史的进步。及至环境史,史家关注的对象进一步向下,最终使历史叙述涵括地球本身及其上的生物和其他环境要素,这可视为人类历史不断进步的结果,环境史也因此成为西方史学链条上的一环。”[4]美国著名的环境史家J.唐纳德·休斯(J. Donald Hughes)说道:“世界历史的叙事,如果要做到均衡而又准确,就要考虑自然环境以及它与人类活动相互影响的各种各样的方式。”[5]环境不能再被视为供人类历史上演的舞台布景,“它是演员,它事实上囊括了演员阵营中的大部分角色”。[6]这样的认识已被环境史学者普遍认同,因而成为环境史的一个基本理念。给予自然应有的地位,尊重环境,是环境史研究的前提,这无疑大大突破了以往历史研究聚焦于人类社会的传统,更新了我们对历史的认识。这样,历史研究就更加接近客观事实,更加科学了。思维的拓展,带来的不但是新的研究领域,而且是一种观念的创新,一种亘古不变的学问的精神。
环境史的诞生,进一步推进了人类对大自然的认识。在古代,历史的撰述集中于“人事的历史”,大自然虽是人类活动的舞台,却不为人类所重视,人类史与自然史被长期割裂。在理性时代,西方人对待自然主要存在着两种观点,即“阿卡狄亚式的态度”和“帝国式”[注]阿卡狄亚(Arcadia),古希腊的一个高原区,后人喻为有田园牧歌式的淳朴风尚的地方。“阿卡狄亚式的态度”即是倡导人们过一种简单和谐的生活,目的在于使他们恢复到一种与其他有机体和平共存的状态。“帝国式”就是要通过理性的实践和艰苦的劳动建立人对自然的统治。(〔美〕唐纳德·沃斯特著, 侯文蕙译. 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第2页)的传统。近代,马克思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7]的说法深深地启发了我们。在马克思理论的指导下,我们慢慢地意识到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密切关系。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也在改造自己,自然并非无动于衷,它会反作用于人类。如人类滥砍滥伐,肆意破坏自然,导致的环境问题,反过来危害了人类的利益。环境史的诞生,使我们开始意识到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即使为了人类的利益我们也要和自然和谐相处。动植物适应自然的能力显然比人类差的多,自然条件一旦被破坏,就会直接威胁到它们的生存。事实证明,人类在千变万化的环境中掌握了生存的技能,动植物只能从自然中寻找食物,人类一方面可以制造食物,另一方面利用技术手段,使之适应新的环境。因此,与自然相争的做法是极其不明智的。环境史学家持这样的态度来对待自然,体现了认识论上的进步。
二、对传统史学的拓展
环境史拓展了对上层政治的研究。环境史涉及研究一个社会和国家或是全球的环境政治和政策,如对美国资源保护运动和国际环境政治的研究。环境史必须研究一个社会的政治结构和功能,以理解它和环境的关系。而决策者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和兴趣爱好对环境政策发挥着极大的影响。[8]传统的历史研究中出现了一定范围内的政治层面的真空,“政治是协调人类与环境关系的最好的指挥棒”。[9]美国史学家休斯说道“环境史不能不顾政治、军事力量的现实格局,以及为其堂而皇之的利益所支配的国家集团、经济组织和种族群体”。他认同道格拉斯·维纳的说法,即“每一场‘环境’斗争,在根本上,都是利益集团间关于权利的斗争”。[10]这表明,环境史可以揭示社会利益集团之间围绕自然而展开的较量。对此加以研究,无疑是对传统史学研究的发展,在史学中涌现出新的浪花。探究各国的环境政策和环保法律的制定过程,研究各国历史上涌现出的环保杰出人物以及联合国在保护环境方面所做出的重要贡献,是适时的也是有价值的。环境政策制定的本身就反应了执政高层之间对环境保护的认识和利益群体之间的较量,人们单纯追求经济利益的奢望和对政治权利的贪欲,在对待环境问题上表露无遗。环境政策执行的情况,显露出一些政治层面的端倪。环境史为我们研究历史提供了新的维度,开拓了新的研究内容。
三、跨学科的应用
跨学科研究是环境史研究的指导理论之一。“环境史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它将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整合起来,历史研究的传统方法就远远不够了,传统的资料来源也不能提供研究所需的充分材料。因此,环境史需要生态学、生物学、动植物学、地质学、地理学、气象学、化学及其他许多自然科学的支持”。[8]“跨学科研究就是跨越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及工程科学的界限,互相借鉴和融合,达到从整体上把握世界史的目的。当然,环境史跨学科研究的落脚点一定是历史学,因为历史学在整合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在从整体上认识变化如何发生时最具优势、困难最少。”[11]它为不同学科背景之间学者的合作提供了平台。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结合,无疑会受益于两个学科。历史学家和生态学家原是“老死不相往来”,它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跨越这些鸿沟显得非常重要,哪个学科能把它们联系起来呢?环境史可以说是最好的纽带。人文、社会、自然科学之间建立种种新的联系,无疑会使不同学科之间的学者加强沟通和理解。在沟通和交流过程中,多学科研究方法的使用,如果能够真正结合起来,那么我们对环境史、生态史的认识就更加清晰和深刻了。就环境史而言,与它关系密切的主要有政治学、生态学、经济学、地理学、环境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其中,环境史与政治史的关联,在于与环境相关的政府机构、政策法规以及社会斗争;环境史与经济学的关联,在于自然资源的利用、分布和有限性及其对经济、贸易和世界政治的制约等。[4]自然,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更利于环境史的发展。学科的差异性、研究者的水平决定真正想做到跨学科的研究是有相当难度的,然而,环境史在这方面显得游刃有余。环境史研究的面是包罗万象的,不同学科学者的研究更利于环境史的发展。在环境史方面,历史学家提倡的跨学科研究真正可以得到应用。
四、环境史的全球视野
环境史积极回应并践行着全球视野。环境史在本质和定义上意味着一种非常广阔的视角,包括全球意义上的环境,以及从起源延伸到现在甚至凝视着模糊不清的未来的,也就是说,它的范围不论在时间层面还是空间层面都是很广的。[4]从目前的研究中可以看出,自英国著名的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1955年在《处在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一书中所揭示的主题——“重新定向”,到后来他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明确提出了“全球历史观”被历史学家广泛接受,用全球史观来指导历史各个方面的研究已被学界认同并在不断实践中。自然,我们的视野当然不能囿于个别的国家和地区,全球视野也成为环境史学家的共识。纵观前后,俯仰古今,涉及全球的环境问题在数量和强度上都有增无减。农业革命的扩散、民族大迁徙、传染病的肆虐、大面积的征服战争,无疑证明环境因素不只是在个别地区起作用,牵“环境”这一发,而且在时间上或是空间上都会引起全球的问题。环境史顺着这种趋势,当然不可避免地要采用全球史观。从对地区、国别和地方环境史的研究上升到对整个地球环境的研究,再用全球的视野加以综合分析,环境史这样的研究方法可谓是精益求精。在世界历史的编撰中,加入环境史和自然史的关联,结合各个地区环境的共性和历史特殊性加以研究,更能彰显出环境史的积极意义。
五、环境运动的推动
“环境史研究是环境运动的后裔”,[9]短短的13个字,向我们诉说了环境史兴起的现实基础。环境问题的覆盖面越来越广,环境问题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异常明显。全球环境问题扑面而来,引起了大众的关注。环境保护正式兴起于20世界60年代,它不仅是有目的的个人行为,也是集体性的社会运动。雷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美国的一位海洋生态学家,满腔热情又科学严谨地沉醉其中,并将大半生投入到对海洋生态学的研究与乐趣之中,她在1962年发表的《寂静的春天》是现代环境保护主义[注]环保主义:环境社会学家查尔斯·哈伯的解释为,环保主义既是意识形态又是行为本身。作为意识形态,它是一套宽泛的信仰,相信改变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不仅合乎需要,而且具备可能性。作为一种有目的的行为,它倾向于改变人与环境的关联方式。环保主义不仅是有目的的个人行为,而且也是集体性的社会运动。 (查尔斯·哈伯.环境与社会:环境问题中的人文视野[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 第354-355页)产生的标志。此书揭露了美国农业、商业为追逐利益而滥用农药的事实,对美国不分青红皂白滥用杀虫剂而造成生物及人体受害的情况进行了抨击。通过大量阅读资料和实地观察,卡逊已看到许多杀虫剂在一些物种中引起的巨大破坏,有些证据也足以证明它们残留在人体组织中可以引起无法挽回的生理变化。[12]该书的出版在美国和世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连续31周成为美国最畅销的书籍,销售量达50万册,不久该书在世界其他15个国家出版。此书同时也引起了美国及其西方国家一股关于环境问题的争论和出版高潮,内容范围超越了杀虫剂问题,涉及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整体影响。在此背景下,环境问题迅速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公众的环境意识随之增加。环保主义的发展还表现在环境非政府组织的壮大。从1960年至1972年,加入美国全国性环保组织的成员增长了38%。到20世纪70年代初,山地俱乐部和全国奥杜邦协会的会员人数从稳定的几万人分别猛增到14万人和20万人。[13]与此同时,许多环境非政府的组织相继成立,如1967年成立了环境保护基金、1970年成立了自然资源保护协会和地球之友。随着世界自然基金会、地球之友和绿色和平组织的建立,第一批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开始活跃在国际舞台上。1970年4月22日达到了舆论的顶点。这天是由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盖洛德·纳尔逊(Nelson Gaylord)提议的第一个“地球日”,主要活动组织者则是年仅25岁的反战活动家萨姆·布朗(Brown Sam)。这一天,包括1 500所在校大学师生在内的约2 000万美国民众参加了“地球日”的活动。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Nixon Richard)虽然不是环境保护主义者,但他还是呼吁人民要与大自然母亲和平相处。[14]同时,许多环境保护主义者纷纷著书立说,对工业主义、现代化和发展的价值观进行了重新评估,并对人类活动的环境影响以及环境退化对人类社会的负面影响进行了重新的思考。[15]显然,在20世界60年代末,很难找到一个公共问题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在如此多的国家获得如此多的关注。1972年6月,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第一次全球性环保大会召开,毋庸置疑,这是在环境保护主义运动的推动下召开的。它突破了冷战的面孔,在环境问题上达成了暂时的共识,摒弃了不同的阶级、语言、意识形态和宗教的差别。环境史的研究与环境保护运动密切相关。现代环境危机要求一种新的史学和历史意识。这门新学科的产生固然可被看作是二战后美国学术多元化的产物,但也绝对不能忽略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场意识变革的冲击。
六、结语
历史理论的创新、旧史学的拓展、跨学科理论的应用以及全球视野构成了环境史研究的理论基础,加之环保运动的现实推动,环境史迅速地成长起来。理论是历史研究中突破传统史学的先导,其创新的重大意义不言自明,环境史有了新理论的指导,更利于它的发展。正是有现实的推动,历史研究赋予更多的人文关怀,环境史迅速成为热门的研究课题。这个新学科被介绍到中国,映入了我们研究的眼帘。[16]环境史自身蕴藏的巨大魅力无疑为历史学注入了新的活力,环境史的出现以及在中国的迅速传播,拔擢了我们历史研究的视野,给我们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为古老的历史学注入了新的血液。
[参考文献]
[1] Alfred W. Crosby. The Past and Present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J].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0, 4 (October 1995):1179.
[2] 孟子·梁惠王(上)//诸子集成本[M]. 北京:中华书局,1954:32-33.
[3] 白寿彝. 中国通史(第一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100.
[4] [美]J.唐纳德·休斯.什么是环境史[M].梅雪芹,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3.
[5] J. Donald Hughe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World: Humankind’s Changing Role in Community of Life[M].London: Routledge, 2001.
[6] J. Donald Hughes. The Mediterranean: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M]. Santa Barbara,CA:ABC-Clio,2005,“Introduction” . xvi.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66.
[8] 梅雪芹.环境史学与环境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1,13.
[9] [德]约阿希姆·拉德卡.自然与权力:世界环境史[M].王国豫,付天海.译.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338-339.
[10] Douald R. Weiner. “A Death-Defying Attempt to Articulate a Coherent Definition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Environmental History,10,3 (July 2005):409.
[11] 包茂宏.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 [J].史学理论研究,2000(04):79.
[12] [美]R.卡逊.寂静的春天[M].吕瑞兰,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ⅱ-ⅲ.
[13] John Mc Cormack. The Global Environment Movement [M]. Belhaven Press, 1989.131.
[14] [美]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M].侯文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413-414.
[15] 徐再荣.全球环境问题与国际回应[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7:53.
[16] [美]唐纳德·沃斯特.为什么我们需要环境史[J].侯深,译.世界历史,2004(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