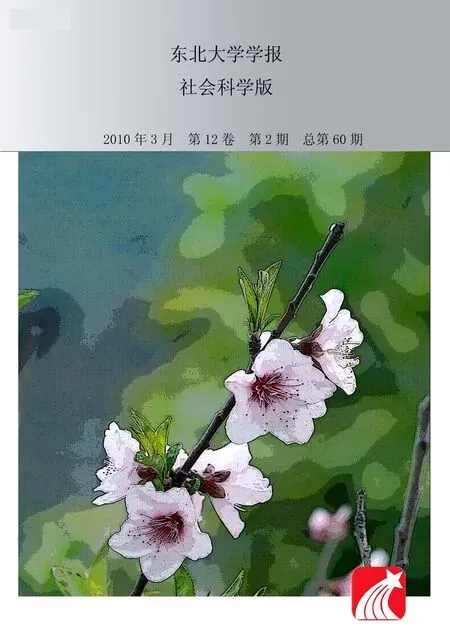科塔宾斯基的实践哲学思想述评
王 楠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人文学院,北京 100049)
科塔宾斯基(Tadeusz Kotarbiński,1886—1981)作为20世纪上半叶波兰最有影响的哲学家和逻辑学家,曾经因为提出科学实在论的早期雏形----实有论(Reism),而受到卡尔纳普等人的高度评价,被视为“波兰分析运动中两位最杰出的哲学家之一”[1]77。然而,科塔宾斯基并没有因此把主要精力放在逻辑学上,而是倾其毕生精力致力于实践哲学----也就是对人类行动的研究。科塔宾斯基之所以这样做,是由于受到当时波兰社会状况的影响。近代波兰频繁遭受战争的磨难,很多波兰人认为革命和暴力这些“非渐进性”因素才是社会发展的出路,但是,科塔宾斯基作为左翼自由主义者、固执的个人主义者,强烈反对这种思想。尽管他没有像罗素那样极端地倡导和平主义,但是,他坚持认为,只有充分实现社会中每个个体应有的权利才会有助于减少波兰反动势力的制约和压迫。因此,“个体生活幸福的条件和实现和谐生活的方法”成为科塔宾斯基十分关注的事情,这也导致他的实践哲学的诞生。科塔宾斯基在他的两卷本选集中的第1卷的引言中写道:“我的‘关于行动的思想’来自于对‘比形式逻辑的学术问题更真实和具体的事情’的渴望。”[1]82科塔宾斯基把实践哲学定义为“指导人的精神生活的理论”,因此,他把实践哲学与广义伦理学或者实践智慧看做是同义词。他的实践哲学包括三部分内容:第一是幸福论(felicitology),也称为快乐主义或者幸福主义,主要是研究生活中的快乐的科学;第二是行动学(praxiology),主要是研究行动的实践性的科学;第三是狭义伦理学(ethics proper),也称为道义论或者道德责任理论,主要是研究一个人如何生活会获得令人尊敬的美名的科学。科塔宾斯基指出,这里所使用的“科学”一词“绝不是数学、物理学或者语言学之类‘科学’的含义,……而是从满意度、效率和公平的角度,指导人们如何构建最合理、最可能实现的行动计划”[2]。科塔宾斯基的实践哲学分别从快乐、效率和道德三个角度,系统地对人类所有行动进行研究。这种研究不仅试图在理论意义上对人类行动进行指导,同时还要尽可能使这些关于如何行动的建议在现实实践中切实可行。因此,科塔宾斯基的实践哲学在哲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本文将对科塔宾斯基的实践哲学思想进行系统介绍,并对该思想进行简评。
一、 幸福论
科塔宾斯基对幸福论的思考是从他的博士论文《穆勒和斯宾塞的伦理学中的功利主义》开始的。他在文章中对斯宾塞和穆勒的伦理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他认为,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把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看做是最大的价值。但是,由于斯宾塞在研究人文学科的问题时,滥用了自然主义和生物进化论,甚至把获得普遍幸福等同于保存物种(或者社会)。因此,科塔宾斯基对穆勒的伦理思想评价更高一些,因为他的思想促进了利己主义和较低的快乐主义的发展。但是,科塔宾斯基认为穆勒和斯宾塞的思想都是不完善的,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绝对的幸福论者、功利主义者,他们都试图把伦理标准建立在这样一个原则的基础之上,即对每个人来说最大的价值就是他自己的幸福。
1914年,科塔宾斯基发表了一篇短文,他在文中将功利主义与基督教伦理进行了比较研究。在这篇文章中,他明确提出反对功利主义。他指出,这种快乐主义计算方法之所以受到推崇,仅仅是因为它从表面上看来似乎具有比较理论化的结构。比如,这种计算方法认为,增加幸福的唯一方式是减少痛苦。但是,这一计算方法却没有对一些人的幸福中包含了另一些人的痛苦提出异议。科塔宾斯基认为,这种来自经济学的类比不能够成为道德标准的证据,应当反对功利主义伦理学。
至于基督教伦理,科塔宾斯基认为它应当具有真理地位的资格。因为当一个人从痛苦走向快乐的时候,他在这个过程中体验到了痛苦、悲伤、快乐、幸福等不同的感情,因此,他会对自己的感情产生独特的满足感,这就好比只有当一个人口渴得厉害时,他才能体会到喝水对解决口渴的满足。进一步来说,当一个人看着他人陷入痛苦而不帮忙时,他一定会产生内疚的感觉;反之,当一个人未能给幸福的人提供更多幸福的时候,他不会产生这种感觉。因此,当在一个人幸福必然与另一个人不幸福相关,或者两个人都幸福(当然都是较低层次的幸福)的选项之间进行选择时,功利主义伦理必然会选择前者,而基督教伦理必然会选择后者,因为基督教伦理不允许将一个人的幸福建立在另一个人的痛苦之上。科塔宾斯基认为,从这个角度来看,基督教伦理显然比功利主义伦理更优越。
科塔宾斯基在对功利主义伦理和基督教伦理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幸福论。他认为,幸福论者必须持有的最基本的态度应当与基督教伦理所宣扬的一样,是一种利他主义的态度,也就是“考虑其他人的幸福”,而不是像自我中心主义者与自我主义者那样,或者以自己体验幸福和快乐为中心,或者不在意他们的快乐是否会引起其他人的痛苦。
那么,幸福论者除了持有利他主义的基本态度之外,还应当具有什么特征呢?科塔宾斯基指出,在回答这一问题的时候,应当将最狭义但强有力的伦理学理性----良心的唤起----引入到讨论的过程中。同时,作为另一个辅助点,还应考虑行动学的某些观点。综合这些考虑,科塔宾斯基总结出幸福论者的四个基本特征[3]:
① 理智地看待生活(从这样的理智中既产生了对颂扬性编史工作的批判----这经常会在为上帝做出牺牲的面具下暴露出私人利益,还可以减少将卑劣的、罪恶的动机归咎于政治敌人);
② 思考什么是真正存在的(也就是确认实际存在的情况);
③ 注意行动可能发生的条件和限制(一个明智的人知道他能得到什么,而不去追求更多);
④ 在确立各个行动和计划的指令时,建立精确的理性层次(意识到较大的重要性就是与罪恶斗争时的有用性)。
熟悉的旋律,张扬青春活力。抵达深圳,未经助跑,原地起跳。纵横谈讲话整理工作,不是实习,而是实战。虽然课堂中也曾以快速度记下老师讲课的内容,但仅仅是为了复习方便,对词句准确度没有过高要求。如今,要跟随讲话速度,还要注意词句准确性,晚上仅整理讲话内容就到深夜,但这也只是第一天。
因此,在科塔宾斯基看来,幸福论应当是对幸福和痛苦进行反思的理论,它的基本原则就是“与所有使我们不开心的事情做斗争,但是要注意的是,必须去做那些比较重要的事情,而且必须预先考虑可能发生的后果,选择罪恶比较小的去做,……还有,不要直接为了你自己的愿望而奋斗;你要根据你心中的信仰,竭尽全力、全身心地投入到值得热爱的事业中去并实现它”[2]。
二、 行动学
行动学是科塔宾斯基在实践哲学研究乃至在他整个学术生涯中最注重的研究领域。他说:“如果有人问我,你既是一名教师又是一名学术研究者,那么什么是而且仍然将会是你主要从事的学术研究领域呢。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我将提及的……是行动学。”[4]
科塔宾斯基的行动学研究工作开始于1910年。一开始,他把行动学研究称为“行动理论”、“一般实践”或者“一般方法论”。后来,他采用了法国学者鲍德奥(Louis Bourdeau)创造的“行动学”一词。1955年,科塔宾斯基出版了被誉为“行动学的权威性典籍”----《良好工作的理论解释》一书,该书也标志着他的行动学研究达到了高峰。
科塔宾斯基指出,行动学是从效率的角度研究“用任何方式做任何事情的方法”,“而不是只研究那些仅仅适用于某个专业的工作的方法”[5]22,因此,行动学的目标就是要成为对人类所有领域的行动进行研究的学科,成为关于人类行动的一般方法论。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由于科学研究只是各种形式的行动或者工作中的一种,所以,科学方法论只是行动学所包括的研究领域之一。
科塔宾斯基把行动学的研究内容划分为三大部分[6]:第一部分是对与行动有关的所有概念进行分析和定义,第二部分是从效率角度对行动进行评价,第三部分是提出使行动更有效率的建议或者警示。科塔宾斯基作为利沃夫—华沙学派的重要代表,继承和发扬了这个学派“强调语义学分析”的传统,他指出,“必须对行动学中的所有概念进行充分地分析和定义,这也是行动学家最重要的工作”[5]23。因此,这一部分内容在他的行动学体系中占了较大的篇幅。他不仅强烈呼吁行动学研究者应当重视这方面的研究,而且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地把主要精力放在构建行动学的概念体系上。
在1955年出版的《良好工作的理论解释》一书中,科塔宾斯基实现了这一目标。他在书中把他认为与行动有关的概念都列出来,把它们分为两组,一组是与行动组成要素有关的概念,包括行动者、自由冲动、结果、产品、材料、方法、方式、行动的可能性等;另一组是与行动类型有关的概念,包括简单行动、复杂行动、个体行动、集体行动和心理活动等。由于这些概念在日常生活中或者在其他学科中也被应用,所以,科塔宾斯基详细地分析和定义了它们在行动学中的含义,并列举大量具体的生活事例帮助界定和说明。
针对行动学如何评价行动的问题,科塔宾斯基本人明确地提出了效率原则。值得注意的是,效率原则实际上隐含了一个前提条件,也就是说,使用效率原则评价某个行动时,该行动应当是已经实现既定目标、产生一定效果的,否则无法研究该行动是否有效率。因此,科塔宾斯基提出的行动学评价原则一般被称为效果(effectiveness)和效率(efficiency)原则,简称“双E”原则。
在现代管理学和组织理论中,“效率”一词通常指的是资源的最优化使用。在科塔宾斯基看来,这只是一个行动被看做是“有效率的”含义之一。他认为,“效率”指的是判断一个行动有助于实现一个任务的所有特征的集合,包括经济性、简单性、熟练、确定性、理性等[7]75-94。因此,行动的行动学价值或者实践价值是“不同于伦理价值和艺术价值的价值体系,从行动学的角度来看,具有较高的行动学价值或者实践价值的行动在艺术价值上可能是中立的,在道德价值上可能是被排斥的”[1]121。所以,行动学评价是完全不同于伦理学、艺术等学科从善恶或者是否艺术的角度对行动进行的道德评价或者艺术评价。
在面对从效率角度评价行动这个复杂的问题时,科塔宾斯基清楚地意识到,他所提到的行动是否经济、简单、熟练、确定、理性等标准并不能够完全解决问题。而且,他所列出的评价标准也并不具有绝对性,因此,其中涉及到的很多问题还是须要进一步分析,比如,有些行动的经济性可以用生产率或者节省成本来衡量,但很多行动的评价是无法这样做的,像艺术作品带给人的精神享受,痛苦或劳累引发神经系统的能量损耗,等等。
至于如何获得使人类行动更有效率的指令或建议,科塔宾斯基认为,可以从如何使行动更加经济和工具化、如何更好地准备和组织行动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提出相应的行动指令和建议。
行动的经济化就是要减少行动的成本损耗,使行动干预最小化、利用行动发生的可能性而不实施行动、使行动自动化以及使行动内化或外化,这些都是使行动更经济的基本方法。行动的准备既包括原材料、工具等的准备,还包括执行者自身具备适当的力量、知识和技巧,且后者更为重要。由于行动计划可以被看做是执行者在知识方面的特殊准备,而计划又是关乎行动成败的关键,所以什么是好的行动计划、如何制定好的行动计划是行动准备方面的研究重点。科塔宾斯基将行动的工具化定义为在行动中普遍利用各种工具和仪器。他既注意到了在行动中利用工具和仪器的好处(比如,工具和仪器帮助人们完成那些靠人体器官完成不了的行动),还讨论了人类行动过度依赖工具的危害(比如,新工具的诞生会淘汰旧工具,而原来那些操作旧工具的工人就会面临下岗或者重新培训)。许多行动会涉及到多个要素或多名执行者,因此,如何组织好这些要素就是行动的组织问题。根据这些要素在行动中的相互关系,科塔宾斯基从合作关系和斗争关系两个方面入手阐述行动的组织问题。当行动中的要素是合作关系时,确保所有的要素齐全、剔除无用的要素、实施劳动分工等是基本方法;当行动中的要素是斗争关系时,集中优势兵力、获得既成事实、故意拖延等是切实可行的。
三、 狭义伦理学
科塔宾斯基认为,狭义伦理学中包括两个对立的价值:一个是值得尊敬性,即“值得尊敬的事物”;另一个是可耻性,即“令人鄙视的事物”。那些具有值得尊敬的动机、意图、行动和人,在道德意义上都是积极的、好的;而那些具有可耻的动机、意图、行动和人,在道德意义上都是消极的、不好的。
科塔宾斯基以这两个对立的价值为基础,提出了狭义伦理学的两个理想----积极的理想和消极的理想。积极的理想是“可靠的引路人”,一个人在困境中可以依靠他,“这样的引路人不是利己主义者,而是可以信赖的、勇敢的、勤劳的、镇定的人”[2]。消极的理想则是“不可信任的、利己主义的、刻薄的人,为他自己的安全着想,不愿为其他人而努力,希望能尽最大努力使自己快乐,随心所欲地折磨由他照管的人,不能给别人带来信赖感,忽视他自己的责任”[2]。
这样一来,科塔宾斯基就从狭义伦理学中提出了关于实践的建议:如果一个人想受到尊敬,他应当效仿可靠的引路人的理想,他应当拼命地努力和尝试,虔诚地、无私地行动,以便使他照管的人免遭厄运。让他以可靠的方式承担这个任务,让他不要在危险面前退缩,而是勇敢地面对;让他不遗余力,让他冷静,不屈服于那些会削弱行动意愿的诱惑[2]。
但是,科塔宾斯基指出:“我们的研究丝毫不是在为独立的伦理学提供完整的体系框架,我们只是想就一系列观点和指令提出可能的基本原则”[1]83。因此,他认为,人们不应当期望对这些特定原则进行精确论述。狭义伦理学的建构只是为了对具体的、日常生活的道德行为提供指导,而不是作为理论争论的基础。而且伦理体系的研究已经表明,越在理论意义上详细阐述伦理体系,所提出的基本准则就越精确,但是,应用于实践的可能性越小。换句话说,想要成为日常生活的真正的道德指导,伦理体系必须是“开放的”,不能太精确也不能太严密地进行定义。实际上,就狭义伦理学来说,它对基本行为规则以及如何将其应用于个体和社会生活中的建议已经进行了阐述,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已经具有伦理学体系的基本要素。
那么,科塔宾斯基的狭义伦理学是要求人们为成为最值得尊敬的人而奋斗吗?科塔宾斯基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认为:“它(人们的良心----笔者注)不需要最高的成就,而是需要可靠性。当一个人没有获得不好的名声时,这就是令人满意的。经受住考验的人,就会获得与仁慈和令人尊敬的人交朋友的权力。”[2]因此,在科塔宾斯基看来,狭义伦理学的最高判断标准就是良心。“每个有良心的人都知道,人生最大的苦难就是违背良心。这个苦难不能与任何其他损失相比。”进一步来说,“独立的伦理学在这个意义上是独立的,即我们自己的良心的呼声是不能被其他人所替代的。每个人与其他人是相互独立的,因此,他一定要按照自己的良心做事。这样一来,良心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最高判断标准。它对任何道德问题都给出了严格的、绝对的终极判断”[2]。
四、 简 评
“行动”作为西方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很多哲学家都对它进行过研究。与其他哲学家的研究相比,科塔宾斯基的实践哲学的特色在于:把行动的效率[注]这里的“效率”一词与科塔宾斯基的行动学中的“效率”含义一致,指经济性、简单性、确定性、理性等。维度与行动的伦理维度严格区分开来,以此作为对行动进行研究的不同视角,从而建构出不同的行动模式。
科塔宾斯基并不是第一个把行动的效率维度与伦理维度分开研究的学者,早在18世纪,亚当·斯密就已经这样做了。他在《道德情操论》中以“同情”为出发点,研究了个体怎样控制其“利己”的感情或行为。所以,《道德情操论》研究的是道德哲学,只关注行动的伦理维度。然而,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又以“利己”为出发点,研究了个体在经济活动中完全追求个人利益的行动。因此,《国富论》研究的是不受道德情操限制的行动,只关注行动的经济维度。
亚当·斯密和科塔宾斯基都没有采用一般行动研究的善恶标准,前者从行动的经济维度和伦理维度,后者从行动的效率维度和伦理维度来审视人的行动。亚当·斯密关注的是社会秩序和社会利润如何能从理性个体的不一致的行动中产生,因此,他开创了现代经济学。而科塔宾斯基主要研究的是行动手段与行动目标之间的一般关系,构建行动的一般方法论,所以,他的研究对所有的行动理论,比如规划理论、组织理论、管理理论、设计理论等都有相当大的启示意义。美国技术哲学家米切姆认为“科塔宾斯基的行动学混合了我们现在所谓的系统论、博弈论、控制论、运筹学以及各种管理理论”[8],波兰经济学家兰格认为“政治经济学、规划理论、控制论等理论都与科塔宾斯基的行动学密切相关”[9]。
作为利沃夫—华沙学派的重要成员,科塔宾斯基深受他的导师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影响,继承和发扬了后者倡导的“精确地阐述每个概念的含义”的研究方法。科塔宾斯基说:“每个思想家都在思考这个世界,但是每个人的思考角度不同,这好比大家透过不同的窗户看同样的风景一样。我的同行们或者透过数学玻璃看世界,或者透过物理显微镜看世界,而我迷恋于透过人类语言这个窗格子来看世界。”[10]因此,在科塔宾斯基看来,数学哲学、自然科学哲学、人文科学哲学等,都是从语言学角度对数学、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的概念和方法进行分析和批判性评价。实践哲学当然也不例外,他甚至把实践哲学中的行动学亲切地比喻为“人类行动的语法”[6]。
但是,科塔宾斯基非常反对使用哲学术语进行哲学研究,他指出,不同的哲学流派会产生不同的哲学术语,这些术语并不是把哲学思想表述得更加清楚和精确,而是会使人越来越糊涂,更加会造成哲学术语使用的泛滥。为此,他曾经专门撰文《必须放弃“哲学”、“哲学的”之类的词语》,反对传统意义上的关于哲学的看法。另一方面,科塔宾斯基从一开始就把实践哲学定位于指导人类行动的一般理论,它所面对的不仅是哲学界人士,更多的是非哲学界的普通民众。因此,科塔宾斯基用日常语言来建构他的实践哲学,以便使其成为非哲学界人士也能看得懂的实践理论。所以,科塔宾斯基的实践哲学语言平实、简单,基本上用的都是日常生活中的词汇和概念,几乎没有出现过哲学专有名词。可以说,科塔宾斯基从语言学角度对人类行动进行的分析,不但使语言分析成为了研究人类行动的一个重要哲学方法,而且也为该理论的广泛传播和未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纵观20世纪的西方哲学,它是在一片“哲学转向”与“哲学危机”之声中走完了全程。虽然,现代哲学家们对于20世纪的西方哲学究竟是发生了转向还是出现了危机的问题众说纷纭,但是,大多数哲学家都认为,20世纪的西方哲学应当从精神世界回归生活世界。科塔宾斯基就是最早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哲学家之一。
科塔宾斯基从哲学研究伊始,就反对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去探讨世界的本原、认识的本质,也不认为哲学的任务是寻求关于宇宙的永恒真理以便建立华丽的哲学大厦,而是积极主张研究与人类现实生活密不可分的问题,从事“小”哲学研究。1918年,科塔宾斯基在华沙大学的就职演讲《大哲学和小哲学》中明确提出:“让我们放弃构建大的哲学体系吧,让我们致力于小哲学吧,它会导致所有学术追求的改革”[1]79。这个演讲以温和的方式(与维也纳小组激进地宣布他们的纲领相比)提出一个新的哲学纲领:提倡学术界的研究工作要以人们的现实生活为基础,只有这样,学术研究的成果才能具有实践意义。科塔宾斯基的演讲在波兰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热烈的讨论。
科塔宾斯基反对20世纪之前的西方哲学以思辨形而上学和二元论的思维方式,把人看做是没有血肉的抽象存在,把人与其对象相分离的纯粹主体,抹杀了人的现实存在或者本真性。他的实践哲学中的主体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他渴望这个或者那个,以这种方式或者那种方式行动,或者通过一些智力方面的努力来实现他渴望的目标”[7]14,是生活在相互联系、不断变化着的现实中的。因此,他的实践哲学是对现实实践世界中的主体的反思。科塔宾斯基的实践哲学作为欧洲哲学史上首先明确地定位于研究人类行动的哲学思想体系,体现出了鲜明的“实践导向”的哲学特征,它要对人类行动进行全方面、多维度、系统化研究,将人类行动的实践指令规范化、系统化,希望能够为其他关于人类行动的学科提供一般的方法论原则。在流派众多、纷繁多样的20世纪哲学舞台上,它是试图扭转传统西方哲学中理论定向的研究倾向的为数不多的哲学思潮之一,对于促进现代哲学在“大方向”上摆脱重思辨轻实践的哲学传统、回归现实生活世界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Skolimowski H. Polish Analytical Philosophy: A Survey and a Comparison with British Analytical Philosophy[M]. London: Routledge, 1967.
[2]Gasparski W W. A Philosophy of Practicality: A Treatise on the Philosophy of Tadeusz Kotarbiński[J]. Acta Philosophica Fennica, 1993,53:57-70.
[3]Gasparski W W. Praxiology and Ethics: the Business Ethics Case [M]∥Gasparski W W. Human Action in Business: Praxiological and Ethical Dimensions.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6:10.
[4]Gasparski W W. Tadeusz Kotarbiński and His General Methodology: Lecture in Honor of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Father of Praxiology[J]. Cybernetics and System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1986,17:242.
[5]Kotarbiński T. On the Essence and Goals of General Methodology (Praxiology)[M]∥Gasparski W W, Pszczolowski T. Praxiological Studies: Polish Contributions to the Science of Efficient Action. Dordrecht: D. Reidel Pub. Co., 1983.
[6]Kotarbiński T. The Aspirations of Praxiologists[J]. Methodos: A Quarterly Review of Methodology and of Symbolic Logic, 1961,13:169-173.
[7]Kotarbiński T. Praxi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s of Efficient Action [M].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65.
[8]Mitcham C. Thinking Through Technology: The Path Between Engineering and Philosophy[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33.
[9]Gasparski W W. Oskar Lange's Considerations on Interrelations Between Praxiology, Cybernetics and Economics[M]∥Auspitz J L, Gasparski W W. Praxiologies and the Philosophy of Economics.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2:449-465.
[10]Gasparski W W. Tadeusz Kotarbinski's Philosophy as a Philosophy of Practicality[M]∥ Airaksinen T, Gasparski W W. Practical Philosophy and Action Theory.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3: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