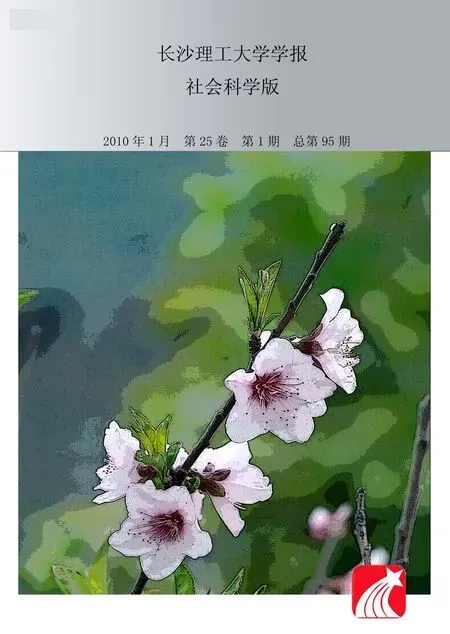论法律效力的形成机制
——以哈贝马斯的法律有效性理论为视角
李小萍
(南昌大学 法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1)
一、法律效力内涵的再认识
我国学者一般认为,“法律效力是指对其所指向的人们的强制力,是法不可缺少的要素”。[1]依此,法律效力即法律规范的强制性、约束力,并且往往直接与军队、警察、监狱和法院等国家暴力机器相联系。这样,法律效力就被当然地归结为国家权力。
这种理解本身不可自圆其说,例如它无法解释诸如国家赔偿等国家承担责任的情况。同时,这种界定只是一种形式上的理解,认为法律效力来源于立法权,来源于立法机关的权力和权威,因而不同等级的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或法规)其效力也就呈现出等级效应。至于法律规范内容是否符合正义或者正当、有没有得到遵守和服从则被排除在外。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我国从规范角度对于法律效力的界定关注的是法律的接受,没有考虑到法律的可接受性。实践中,这种理解可能会导致法律工具化取向,对我国法治建设极其不利。
罗伯特·阿列克西(Robert Alexy)认为,效力可以分为社会学的、伦理的和法律效力三种。社会效力即“实效”或“功效”,伦理的效力是指法律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法律效力包括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种。广义的法律效力又分为实证的与非实证的两种,前者仅包括法律社会的效力,后者包括社会的效力和伦理效力;狭义的法律效力,是指当一个规范由有权机关依规定的方式创设,并且不违背上位法时,这一规范就具有法律上的效力。[2]魏德士也将法律效力分为法律效力(应然效力)、现实效力(实然效力)、道德效力(认可效力或确信效力/接受)三类,三者是法律效力的三个维度,缺其一,法律秩序就不会持久和稳定。[3]
法律不仅仅是规范和调整社会生活的工具,它还必须反映一定的价值,即法律必须以被社会接受、认可和尊重为前提和基础,必须具有合法性。这是法学理论发展到今天的共识。由此,法律效力包含价值、规范和实效三个维度。
但法律的价值、规范和实现这三个层面并非当然的和谐、而是存在着持续的张力。自然法学、分析法学和社会法学分别从价值、规范和法律的实现三个角度来解释法律为什么有效、以何种方式有效这一问题,这种类型化的认识路径虽然便于深入地认识事物,但同时也带来各个层面间的隔阂甚至紧张,相互之间的不契合使法律处于分裂之中。综合法学认识到了这一点,但一个具有效力的法律规范如何可能、其形成机制是什么,该理论并没有明确。
法律如何反映其所在社会的价值追求,法律规则如何体现这一价值并能够要求它所指向的人们必须一体遵行?包含价值的法律规则如何与社会生活形成良性互动?法律的价值、规范和法律的实现之间如何实现动态平衡?其实这些问题可归结为法律效力形成机制这一问题。本文通过对法律效力形成机制的探讨,努力使上述问题得到合理的解决。最后本文结合当下的中国法治建设的现状,为我国法律效力更好发挥提供建议。
二、基于交往理性的法律效力观
法律的价值、规范和实现之间如何融会贯通?考夫曼教授认为“了解此难题,意味已洞察法律哲学的整体结构”。[4]贝马斯的通过商谈形成的法律效力理论可以说为我们解决法律效力的形成提供了一个可行的路径。本文以他的理论作为法律效力形成机制的理论基础。
(一)交往理性是现代社会制度合法性的根据
哈贝马斯的法律效力理论,是以交往理性为基础的。由于现代社会作为一种主体能力的实践理性被异化为工具理性,抹杀了人性的自由和个体间的差异。建立于其之上的包括法律在内的制度也失去了“合法性基础”,成为一个强制的工具。但理性又是任何批判的基点。因此,他用交往理性取代实践理性。
哈贝马斯认为,社会交往以一定形式形成的规则体系是当代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为此,他反复区别了“有目的的理性行动”和建立交往关系的交往实践两种实践观。他认为,前者是作用于客体、取得关于客体的经验内容的活动,层次较低;后者是达致意义的相互理解、重建合理性规范的活动,是主体之间的,层次更高。
使交往理性成为可能的媒介是语言。语言是为理解服务的,它把诸多主体间的互动连接在一起。任何人,只要用语言来与其他主体就某物达成理解,“必须从这样的前提出发:参与者应该无保留地追求他们的语内行动目的,他们的同意是同对于可批判的效力主张的主体间承认相联系,并表现出准备承担来自共识的那些同以后交往有关的义务。”①行为规范的正当性是以理由为支撑的,因而语言也是使一切规范合理化、效力的根据。无论是以规范“合目的性”实用意义的话语、追求“善”的伦理意义话语,还是以“正义”为目标的道德话语,行为规范的正当性主张都是以理由为支撑的。②以语言为媒介的交往理论就是要回答什么样的规范才是“正当的”,从而具有效力。因此,规范的正当性应在交往行为的主体间、从实践话语中把握。对于一个具有效力的法律来说,其正当性只能产生于交往主体之间的公共辩论和理性审察,是主体间共识的结果。
(二)哈贝马斯的法律效力理论的内涵
哈贝马斯的法的效力理论是在回应理性工具化以后,“基于合法律性的合法性何以可能”这一最根本的问题,因而法律效力的证明问题是其商谈论的核心。
在哈贝马斯的理论中,法律是一种张力的存在,张力广泛存在于法律内外。例如,表现在法律有效性之中的事实性与有效性的张力,内在于具有强制的现代法律与具有合法性的政治权力之间,内在于法律运用之中的法律确定性原则与合法性原则之间,等等。张力也外在于法律而存在,即宪政的规范性自我理解与政治过程的事实性之间。法律有效性之中的“事实性”主要表现为法律的实证性、确定性或可预见性、强制实施,有效性主要表现为法律规范的合法性和“合理可接受性”,即要求法律规范值得被遵守。
但在前政治和近代以前的国家,由于习惯、道德、法律、甚至宗教教义构成一个复合的规则体系,法律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合而为一,其张力也隐而不显。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形而上学和宗教的世界观已经崩溃,建立在其之上的法律的合法性基础也几近丧失,合法性和有效性之间的张力就显现出来,法律如何才能不等同于事实上的强制力,如何因值得人们遵守而实现社会整合?尤其是,越来越多的从社会结构上来说不可缺少的策略性互动在现代经济社会被释放出来了,人们之间的行为冲突也越来越多。在策略行动者与交往行动者相互排斥的取向中,社会整合如何可能?
哈贝马斯认为,“走出这种困境的一条出路是对策略性互动的规范性调节,对此行动者们自己要达成理解。”①(P32)具有整合能力的社会规范必须同时满足相互矛盾的条件:“一方面,这些规则要作出一些事实性限制,这些限制会改变有关信息,以至于策略行动者觉得有必要对其行为作一种客观上有利的调整。另一方面,这些规则又必须表现出一种社会整合力来,因为它们对其承受者施加了一些义务——根据我们的前提,这些义务只有在主体间承认的规范性效力主张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①(P32-33)而有效的行为规范“只是所有可能的相关者作为合理商谈的参与者有可能同意的那些行为规范”[5]。法律是行为规范的一种,它是所有可能的相关者在合理商谈中达成的共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哈贝马斯的通过商谈的法律效力理论力图沟通法律不同维度方面存在张力,力图将法律的效力与公民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找到法律效力的实现路径。
三、法律效力的形成机制
价值、规范及其实现是法律效力中相互包容的有机部分。为了知识的承接性和便于分析,下面从这三个维度来分析法律效力的形成机制。
(一)法律价值的形成
法律应追求什么样的价值、反映谁的价值取向?回答这些问题首先需要确定在价值多元的现代社会价值共识是否可能这一前置性的问题。
在祛魅、多元、又尊重自由、民主的社会,有没有价值共识?事实证明,在协商群体中,具有极端立场的群体成员在讨论后一般都会发生一点变化,或者朝着更加缓和的立场转移,即价值共识是存在的。[6](P34-35)(法律的“一个核心目标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一部分是将不同意见转化成创造力,一部分是不可能达成一致意见时使其成为没有必要。”[6](P7)
同时,使得商谈进行的法律程序本身也会保障共识的妥当性。③任何一部法律都是通过过程形成,而法律的形成过程必将主体的理解、价值取向带入其中。法律价值是在个人之间交往过程中,通过商谈中“批判的生成”程序中达成的共识,是“多个互相独立的主体从其本身的‘对象’出发达到实际上趋同的认识”。[7]
在公民的个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中,他们根据自己的不同需要形成不同的交往群体,如政党、妇女组织、消费者组织、大学院系、学生组织、广播、电视、互联网等等,在这些群体中进行着非制度化的对话与商谈,并使有关政治、法律、经济发展、个人权利等问题“议题化”或“问题化”。这些议题通过各种法律程序进入制度化的商谈之中,在各种意见充分表达的基础上达成某种价值共识。
法律的价值也就是这种通过各个主体之间不断的价值重叠、理性妥协,通过逐层之间价值筛选而凝结的结果。人们的价值评价是随着政治和社会文化环境不断变化的,商谈也总是即时性的,所以通过商谈的价值选择总能反映社会变化。对话、商谈、论争的交往无处不在,价值之间的冲突、选择、妥协、提升也无处不在。有效的法律价值就是在不同形式、不同层面的交往中,通过“批判的生成”的程序进行层层叠加、逐步抽象形成的共识。商谈程序中价值共识是经过程序中自由平等主体的论证妥协,是经过程序筛选的共识价值,不同于社会上的原始道德规范、社会舆论、意识形态。
(二)法律规范制定
规范是法律的现实表达。从形式上看,法律是民主国家的代议机关制定的一套规则,但仅仅如此显然不能深刻理解法律的本质。因为这样界定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法律规范的真正效力是什么、被公民认可与遵守有什么意义?从动态角度看,这需要解决具有效力的法律规范的证立问题。
有效的法律规范基于一定的价值判断,否则,法律规范最终会化约为事实力量的对比,法律成为政治统治的工具,少数人的权利将会无从保障。那么,法律规范如何反映社会的价值取向,价值通过何种机制进入法律规范?
法律是由经特定民主程序选举产生的代议机关按照多数决原则制定和修改的。对于法律的制定来说,不仅仅包括法律的起草、讨论、批准和公布,还包括立法之前的选举等都是在理性对话、在商谈和沟通中进行的。以选举这一实现民主的重要方式为例,无论是直接民主还是间接民主,选举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人一票原则的实现过程,其背后包含了广泛的沟通与妥协。例如在我国,从候选人的提名、介绍到对被选举人的监督、罢免等等都是在众多的理由与信息传递、争论、说服甚至妥协中进行的。代议机关的立法过程也必然是代表之间的沟通与妥协的过程。这些程序中的沟通主要体现在:(1)选举前,公民和公民之间通过各种媒介进行公开自由的对话;(2)选举阶段,就是选民选举候选人让其比较充分了解自己所关注问题的立场与观点的程序,并按照平等原则选出代表自己利益的代表;(3)代表将其选民的观点、立场带进更高一级的选举程序中去;(4)代议制机关中的代表们之间通过自由公开的辩论、说服达成共识,或者剔除根本无法共识的问题;④(5)代表们通过平等投票决定法律规范的取舍。实在法就这样产生了。法律规范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在之后的沟通、协商中进一步修正。
这样,经过逐层选举、协商、形成共识而制定或修改的法律规范,就把社会形成的价值共识涵摄进来了,使法律规范具有了合法性。这样,社会的价值共识通过民主程序获得了制度化形式,法律规范因此具有了可接受性和合法性,因而就具有了权威。通过代表,选民对有关立法问题非的不同意见就得到了表达、争论与探讨。
(三)法律的实现:有效的法律规范必须回应现实生活
立法过程本身源于国家和社会生活,但代议机关在这种价值与规范之间沟通的过程到此还远没有结束,沟通还会也必须延展到法律文本之后,进入到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去,与现实生活形成循环往复的动态过程。
考夫曼认为,法律的发现是一种使生活事实与规范相互对应,一种调适、同化的过程。[8]一方面,生活事实必须具有规范的资格,必须与规范产生关联,必须符合规范。另一方面,规范必须与生活事实进入一种关系,它必须符合事物。表达了社会价值共识、通过科学的立法程序产生的法律规范在正常运行情况下,是有能力涵摄社会生活的,能够为人类以及个人的生存发展提供秩序以及符合人性的生活方式。反过来,这样的法律规范也能够得到人们的接受与遵守,而不仅仅是以“力”使人屈服。社会现实与法律之间通过各种行使的主体间商谈以及立法程序而互动。
(四)法律效力三维度之间的沟通
法律具有效力在于自由、平等主体在法律保障的民主程序中的商谈,商谈以及保障商谈顺利进行的法律程序成为效力产生的机制,它使得法律内部各环节以及法律和社会生活之间的动态平衡。商谈赋予法律程序以实际内容,程序保证商谈共识的可能性。效力形成机制因此在法律的价值、规范和实现之间、在法律的个体理解与公共理解以及社会生活和法律文本之间起着关键的沟通作用。
社会生活不断发展,人们的价值观也在不断变化。社会价值往往比法律规范变化迅速,以至于二者之间常常紧张。法律程序保障的商谈沟通了这种张力。同时,从商谈中产生的蕴含了价值的法律规范本身是即时性的东西,需要随着变化的社会生活不断做出调整。在法律实施中,法律共同体成员通过法律保障程序中的对话、沟通、协商和论证,反复按照上述价值和规范形成共识的过程与法律文本形成对话,通过修改、解释等方式促进法律自身的完善,也使法律规范与社会生活相适应。这样,法律实现的过程本身就是法律再形成过程,法律的遵守者同样是这个过程的参与者。这样,通过程序所具有的反思理性,法律规范就与社会生活沟通起来,成为生活中的法律。
四、法律效力形成机制与我国法治建设的实现
我国法治建设的实现最终需落实在法律效力上。我国“十一五”规划草案当中规定:“本规划确定的约束性指标,具有法律效力。”这是法律效力首次明确出现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计划)纲要的文字表述中。“之所以这样强调,是为了防止再次出现‘规划起来轰轰烈烈,实施起来无声无息’的现象。相关指标具备了法律效力,那就可以违法必究。”⑤可见这些年来法治化进程中,法律生成后在实践中运作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从文本到实践还有很长的路。以哈贝马斯的商谈论为理论基础的法律效力形成机制对我国的法治建设是具有借鉴意义的,这至少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完善我国的选举制度。以哈贝马斯商谈论为基础的法律效力形成机制强调自由平等主体法律程序中的商谈,这对完善我国选举制度是值得借鉴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选举制度是其基石。选举过程体现了双重社会功能:政府不断寻求民众对其合法性的广泛认可,而公众也在寻求选择政府的发言权。[9]选举的有效运行可以过滤社会所需要解决的问题、提炼民意、协调各种冲突价值等。但我国选举的形式化与选举民主、公开性还存在一些矛盾,例如正职必须等额选举、动员提名人撤回提名、“陪选”、“贿选”等现象,⑥这使得选举徒具形式,公民日常关注的问题、及其看法、观点不能很好通过代表反映出来,公民个人以及公民间关于法律的理解也不能充分通过选举这个制度化渠道得到表达,最终可能使得制定的法律并非社会所必需、使得原则性的法律规范无法及时与真正的社会需要相连接,法律无法通过正式的制度化渠道获得自主发展动力。另外,选举中城乡代表所代表的选民数差别也实际存在,这有碍于选举平等原则的实现。因此,我国应努力落实选举主体的平等以及选举程序的公正、公开,以使选举成为表达民意的顺利通道。
第二,完善我国的立法程序。法律规范是在立法程序中制定出来的,科学的立法程序对于法律效力来说至关重要。立法程序包括立法者从社会生活中析出应予调整的社会关系、收集信息和法律草案的起草、通过和公布等环节。这与我国的选举制度直接相接,是个整合价值并使之规则化的过程。但我国的立法程序还存在一些需要完善之处。例如提出法案阶段还存在提案权制度与实际运作中的提案权相疏离的情况、审议程序缺乏可操作性、整体表决方式本身的不足等。[10]这使得社会关注的问题或议题不能很好地与法定的意见和意志形成相衔接,法定的意见和意志形成过程本身不能充分体现民意,制定出来法律规范不能充分体现社会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浪费了立法资源。立法程序的完善是制定反映社会价值共识、适应社会发展法律的必由之路,完善我国现有立法程序是当务之急。
第三,以完善宪法解释和宪法修改为切入点完善法律发展的机制。
法律的发展并非仅仅指法律规范变动,还表现为原则性、概括性的法律规范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不断注入新内涵,即法律解释。由于宪法的根本法地位及其司法中基本空置的现状,我国尤其应完善宪法解释和宪法修改。下面仅以此为例来进行说明。全国人大常委会是我国法定宪法解释主体,但实践中它几乎没有行使过严格意义上的宪法解释权。因此,应从两方面完善宪法解释:一是,对宪法解释的程序、标准等问题作出具体规定,强化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解释的职能;二是,宪法解释中必须要将精英话语与大众话语结合,避免法律精英的宪法解释与广大民众疏离、致使宪法内涵受少数人左右的危险。对于修宪而言,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主要表现为“政策性修宪”,⑦那么,修宪提案如何体现全国人民的要求,如何反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加强修宪程序建设是不可或缺的路径。宪法是否需要修改、修改什么、如何修改等等,都应是经过反复辩论、交涉的锤炼和审查下的理性选择。
由于上述三个方面存在的种种问题,使得非建制化的商谈和建制化的商谈都可能会受到阻碍,使得商谈共识往往排除了某些主体的选择。这些都是我国在法治建设过程中需要逐步完善的。
法律效力形成机制只是一个理想模型,很大程度上只是一面镜子,是反观现实中法律效力问题的一个应然标准,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应不断以此为尺度来评价、甚至批判现实法律,使其更具有效力。
[注释]
①见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4-5页。
②见哈贝马斯:《论实践理性的实用意义、伦理意义和道德意义》,曹卫东译,载《对话伦理学与真理的问题》,沈清楷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80页。哈贝马斯在另一书中具体提出交往的有效性要求:(1)说出某种可理解的东西;(2)提供给听者某种东西去理解;(3)由此使他自己成为可理解的;(4)达到与另一个人的默契。可概括为可领会性、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四项。参见J.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2-3页。
③季卫东认为在就实质正义方面的问题无法达成一致时,有关决定只要符合程序要件就应认为是妥当的。参见季卫东:《法律程序的形式性与实质性——以对程序理论的批判和批判理论的程序化为线索》,载《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1期。
④协商中由于各种原因总是存在无法达成共识的议题,对于这样的困境问题,孙斯坦称之为“协商飞地”,从政治议题中剔除这些议题是保护而不是损害民主政治的手段之一。参见凯斯·R.孙斯坦著:《设计民主:论宪法的作用》,金朝武、刘会春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引言”及“第四章”的有关分析。
⑤“法律效力”首次表述于“十一五”规划草案中》,新华网,2006年3月7日,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06-03/07/content_4268629.htm,最后访问日期2009年2月20日。
⑥选举中的这些现象的总结参考了强世功、蔡定剑:《选举发展中的矛盾与选举制度改革的探索》,载《战略与管理》2004年第1期。
⑦“政策性修宪”借用的是殷啸虎先生的提法,参见殷啸虎:《论“政策性修宪”及其完善》,载《法商研究》2000年第1期;朱应平:《改进中共中央修宪工作的几点建议》,载《法学》1997年第12期。
[参考文献]
[1]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105.
[2]Robert Alexy,The Argument from Injustice: A Reply to Legal Positivism,translated by Bonnie Litschewski Paulson and Stanley L.Paulson,Oxford: Clarendon Pres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85-88.
[3]魏德士.法理学(丁晓春、吴越译)[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149.
[4][德]阿图尔·考夫曼.法律哲学(刘幸义等译)[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284.
[5]J.Habermas,Between Facts and Norms:Contributions to a Discourse Theory of Law and Democracy,translated by Wliiiam Rehg,The MIT Press 1996,p.107.
[6][美]凯斯·R.孙斯坦.设计民主:论宪法的作用(金朝武、刘会春译)[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7][德]阿图尔·考夫曼.后现代法哲学:告别演讲(米健译)[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46.
[8][德] 阿图尔·考夫曼.类推与“事物本质”——兼论类型理论(吴从周译)[M].北京: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87-89.
[9][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216.
[10]蔡家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程序制度分析及完善[J].中天学刊,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