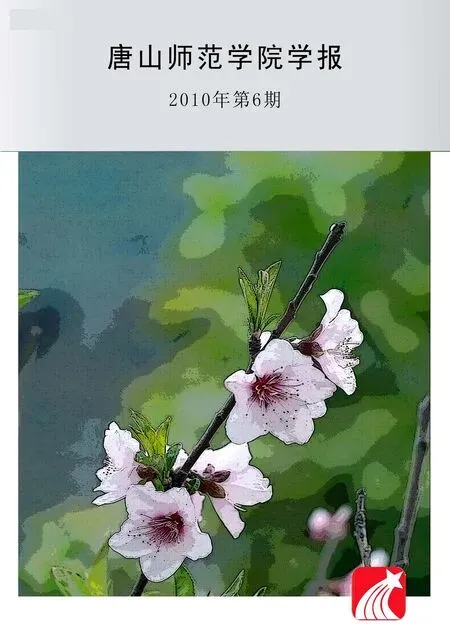史书魅力管窥
王文才
(唐山师范学院 中文系,河北 唐山 063000)
史书有史书的价值,文学有文学的魅力。优秀史书不仅具备深刻的认识价值,而且具有不朽的艺术魅力。其魅力从何而来?笔者以为,作为史书,其首要条件是真实。尽管作者对有些人、事的态度可以用“春秋笔法”来体现,但它必须是“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1]之作,而不能像稗官野史那样无中生有,任意起灭,必须有齐之南史、晋之董狐那种秉笔直书的精神,其人、其书才能受到后人的尊重与喜爱。当然,“尚实”固然重要,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但仅有“实”又是不够的。“前四史”之所以能赢得人们的普遍好评,除了史料的翔实、观点的进步、内容的真实之外,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文笔的优美与技巧的娴熟,所谓“言而无文,其行之不远”[2]。这与当时文史不分,文即史,史亦文有关。而在史书的诸多表现手法中,虚构也是必不可少的。
虚构本来是“文艺创作中为概括生活、塑造形象、突出主题所采取的一种艺术手法”[3],也就是说,“虚构”是文艺创作中特有的一种艺术表现手法,在其他学科中是不使用的。而实际上,不仅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需要虚构,即使一向崇尚“实录”、以“实录”为第一要义的古代史书,同样运用了虚构;其文学价值的体现,在很大程度上也有赖于虚构。即如二十四史之首、被称作“史家之绝唱”的《史记》,尽管班固极力推崇它“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但无论是其记事、记人还是记言,皆大量采用了虚构的手法。如张良为圯上老人进履、李广夜射卧石没镞等事皆如此。离开了虚构,其文学性就要大大逊色甚至不复存在。这决非本人危言耸听、故作惊人之语,事实上,历代史书均如此。“前四史”所以备受后人称赞,在很大程度上即得力于它们在写人记事方面运用了后世文学中常用的表现手法,因此才体现出了鲜明的文学特色。不仅“前四史”如此,其他史书亦不例外。今试从《国语》中撷取几例以证其说。
《国语》中的《周语中》和《晋语四》均记载有“晋文公勤王”这件事。事后周襄王犒赏晋文公,赐以阳樊之地。可惜阳人并不买这位大名鼎鼎的晋文公的帐,无奈晋文公只好派兵“围之”。就在阳樊人民即将遭遇灭顶之灾时,当地一位名为仓葛的人站了出来,用一番大道理折服了这位不可一世的春秋霸主。对于仓葛的这段话语,《周语》和《晋语》不仅记述角度不同,字数上的差距也极为明显:前者为189字,后者仅83字,相差倍余:
王以晋君为能德,故劳之以阳樊,阳樊怀我王德,是以未从于晋。谓君其何德之布以怀柔之,使无有远志?今将大泯其宗祊,而蔑杀其民人,宜吾不敢服也!夫三军之所寻,将蛮、夷、戎、狄之骄逸不虔,于是乎致武。此羸者阳也,未狎君政,故未承命。君若惠及之,唯官是征,其敢逆命,何足以辱师!君之武震,无乃玩而顿乎?臣闻之曰:“武不可觌,文不可匿。觌武无烈,匿文不昭。”阳不承获甸,而祇以觌武,臣是以惧。不然,其敢自爱?且夫阳,岂有裔民哉?夫亦皆天子之父兄甥舅也,若之何其虐之也?(《周语中》)
君补王阙,以顺礼也。阳人未狎君德,而未敢承命。君将残之,无乃非礼乎!阳人有夏、商之嗣典,有周室之师旅,樊仲之官守焉。其非官守,则皆王之父兄甥舅也。君定王室而残其姻族,民将焉放?敢私布于吏,唯君图之。(《晋语四》)
出自一人之口、评价同一件事,言之多寡,何以如此悬殊?笔者以为,一方面由于双方史官所站的角度、所持的态度、思想倾向不同,因此,他们在记述历史事件时必然表现出自己的好恶与爱憎,支持与反对;另一方面限于当时的书写工具十分落后,无非刀刻斧凿,不能每言必录。而实际上,即使在今天的电子时代,恐怕亦难以只字不漏地完全记录下来,无论是晋史还是周史,都只能记其大概,只好根据个人好恶,各取所需。由此,我们也就不能排除各位史官在记述不及的情况下,难免有“凭想像造出来”(《现代汉语词典》对“虚构”词条的解释)的嫌疑。就是这些“凭想像造出来”的部分,使《周语》与《晋语》各自呈现出鲜明的思想倾向。
如果说以上一条尚有一些事实依据的话,那么,《晋语四》中“骊姬夜半而泣”一段则完全是“好事者为之词”(孔鲋《孔丛子》卷六《答问》第二十一)。
骊姬本是居住在骊山脚下的骊戎国君之女。花季之年,本应过着衣食不愁、忧虑不想的生活。怎奈偏偏遇上老耄糊涂、昏庸好色的晋国之君晋献公,而这位晋献公偏又喜欢穷兵黩武,在公元前672年对骊戎发动的一场战争中,“克之,获骊姬以归,立以为夫人,生奚齐。”被灭其族、杀其父的骊姬并不满足于已有的“夫人”之位,还要为自己的儿子争得太子之荣,正如《晋语》一中史苏所言“子思报父之耻而信其欲”。而此时晋国已立老实忠厚的申生为太子,要想达到自己的目的,并非易事。于是她在优人施的导演下,于夜半时节分上演了一幕精彩的攻心战。
优施教骊姬夜半而泣谓公曰:“吾闻申生甚好仁而强,甚宽惠而慈于民,皆有所行之。今谓君惑于我,必乱国,无乃以国故而行强于君。君未终命而不没,君其若之何?盍杀我,无以一妾乱百姓。”公曰:“夫岂惠其民而不惠于其父乎?”骊姬曰:“妾亦惧矣。吾闻之外之人言曰:为仁与为国不同。为仁者,爱亲之谓仁;为国者,利国之谓仁。故长民者无亲,众以为亲。苟利众而百姓和,岂能惮君?以众故不敢爱亲,众况厚之。彼将恶始而美终,以晚盖者也。凡民利是生,杀君而厚利众,众孰沮之?杀亲而无恶于人,人孰去之?苟交利而得宠,志行而众悦,欲其甚矣,孰不惑焉?虽欲爱君,惑不释也。今夫以君为纣,若纣有良子,而先丧纣,无章其恶而厚其败。钧之死也,无必假手于武王,而其世不废,祀至于今,吾岂知纣之善否哉?君欲勿恤,其可乎?若大难至而恤之,其何及矣!”公曰:“若何而可?”骊姬曰:“君盍老而授之政。彼得政而行其欲,得其所索,乃其释君。且君其图之,自桓叔以来,孰能爱亲?唯无亲,故能兼翼。”……“君盍使之伐狄,以观其果于众也,与众之信辑睦焉。若不胜狄,虽济其罪,可也;若胜狄,则善用众矣,求必益广,乃可图也。”
申生在中国历史上是有名的大孝子,献公既然立他为太子,那他必然在性格、为人等方面深得献公和众人的喜欢,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直接诬陷申生,说他如何凶残暴戾、毫无人性,显然无人相信,更何况“知子莫如父”?那样做无疑是自陷泥淖。骊姬聪明就聪明在她先将申生极力拔高,谓其如何如何深得众人拥戴,由他代父为君,早已是众望所归、人心所向。而且他杀父弑君的理由“非常充分”:(1)杀君利众,既得君位又无恶于人;(2)杀君利家,既不彰父恶,又使其家族不废;(3)献公家族有不爱亲的“光荣传统”,“惟无亲,故能兼翼”。而且她明知晋献公如果失去她,将“寝不安,食不甘”[4],她偏假惺惺地说“盍杀我?无以一妾乱百姓”;明知这时的晋献公嗜权如命(这也是封建统治者年老后的通病),她却故意戳其痛处:“君盍老而授之政。彼得政而行其欲,得其所索,乃其释君。”晋献公眼中娇柔可人的骊姬,是多么忧国忧君?但他的爱子申生,却在骊姬的精心包装下,由一个愚忠愚孝的典型,突然之间变成了一个即将杀父弑君的恶魔。骊姬所说的这些事,虽属空穴来风,但却直吹得晋献公瑟瑟发抖。这段文字,生动地刻画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代女阴谋家骊姬阴险狡诈、能言善辩的性格为人,真可谓力透纸背、入木三分,后世许多描写女阴谋家的作者在此面前也难免感到汗颜。
关于这段记述,孔鲋曾经评价说:“人之夫妇,夜处幽室之中,莫能知其私焉,虽黔首犹然,况国君乎?余以是知其不信,乃好事者为之词。”[5]后世一些学者为了维护《国语》的“尊严”,则强为解释说,这是当时的“内朝女史所记”,难道一国之君与其夫人“夜处幽室之中”,岂允许“女史”在旁恭候,以便“君举必书”?这不等于允许他人日夜窥探其隐私?未免牵强附会、迂腐可笑。以我愚见,这段记述确如孔鲋所言,“乃好事者为之词。”而实际上,也正是这些“好事者为之词”——虚构成分,才使骊姬这一形象更加鲜明突出、血肉丰满,同时也突出体现了《国语》的文学价值。如果没有骊姬这一夜“谆谆教诲”,我们就无法想像晋献公怎么会对一个向以忠厚老实、仁慈宽爱著称、深为献公宠爱并已立之为接班人的申生下此毒手。很显然,作者在这里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融入了自己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判断,将骊姬形象按自己的主观意愿加以补充、完善,使其更加完美全面。晋献公由慈父一变而为凶手,绝不是凭空而来,而应该有一个变化过程。文学历来讲究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以及其变化的内外因。正是有了这一不眠之夜,才使晋献公对申生的态度陡变,有了事实上的存在依据。
而《晋语五》中被李元度看作“失实”(《天岳山馆文钞》)之作的“鉏麑刺赵盾”的故事,同样是作者肆意发挥想像、大胆虚构的产物。
灵公虐,赵宣子骤谏,公患之,使鉏麑贼之,晨往,则寝门辟矣,盛服将朝,早而假寐。麑退,叹而言曰:“赵孟(即赵盾)敬哉!夫不忘恭敬,社稷之镇也。贼国之镇不忠,受命而废之不信,享一名于此,不如死。”触庭之槐而死。
老臣赵盾犯颜骤谏,被荒淫残暴的晋灵公视作眼中钉、肉中刺,必去之而后快,于是派刺客鉏麑在凌晨时分前往。凑巧的是鉏麑看到的赵盾既不是在酣睡如泥,也不是在尽情享乐,而是“盛服将朝”,只因时间尚“早而假寐”。赵盾那恭谨、严肃的作风没能感化残暴的国君,却感动了刺客:“赵孟敬哉!夫不忘恭敬,社稷之镇也。”以至于这位刺客进退两难:“贼国之镇不忠,受命而废之不信,”情急之下,遂“触庭之槐而死”。短短一段文字,就将刺客鉏麑当时那犹豫不决、踟蹰院内时的形体动作和其矛盾、痛苦的心理活动非常清晰地勾画出来了。关于这段记载,柳宗元曾批评道:“赵宣子为政之良,谏君之直,其为社稷之卫也久矣,麑胡不闻之,乃以假寐为贤也?不知其大而贤其小欤!使不及其假寐也,则固已杀之矣。是宣子之大德不见赦,而以小敬免也。麑固贼之悔过者,贤可书乎?”[6]哪有国之重臣的忠心耿耿不能为人所知、不能为人所敬,反仅仅以“盛服将朝,早而假寐”就免于一死的?柳氏之言固然有理,但他显然是用现实生活的逻辑作评判是非的标准来对这段记录进行评说的。在他看来,此段文字也许根本不值得记录;纪昀、李伯元等人也对此发出过质疑(分别见于《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一、《文明小史》第二十五回)。这也怪不得柳、纪、李等老先生,他们的质疑也不是没有一点儿道理。试想:鉏麑当时的心理活动是无人知晓、死无对证的,因为当时既无史官相随,更不会有赵家人听见、看见,否则,鉏麑恐怕就不是“触槐而死”,而是被“乱棒打死”了。对于这段记述,如果从今天叙事的角度来评价它,应该说它是虚假的;但若从艺术的视角去审视它,则又是真实的,这就是生活与艺术的区别。这正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说:“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为只要生活中曾经有过或可能出现的,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它就是允许的,是真实的。就这段文字来说,如果将鉏麑的心理活动和自言自语省去,那就变成了“晨往,触槐而死”(“盛服将朝,早而假寐”也当省略,因那是鉏麑看到的,又由双眼作用于大脑的,也属他的心理活动)。如此一来,简则简矣,真亦真矣,可鉏麑好端端的衔君命以往,为什么要“触槐”而死就失去了依傍;鉏麑的死,就变成了千古疑案;赵盾性格为人的巨大感召力就无从体现了,而且对赵盾和鉏麑的形象,无疑也是一种损害。尽管我们承认,柳氏的说法不无道理,但应该看到,这是作者根据自己的主观理想将赵盾的人格理想化了。文学艺术不仅仅是再现生活,应该在这“生活”中注入作者的情感、理想,还应该有所取舍,否则,它就不能称其为文学,而只能是一部地地道道的“流水账”。因此,我们说这些“不实”之词,恰恰是《国语》一书的闪光点,是其艺术生命之所在,它生动地向我们昭示了《国语》的魅力。
由此,不难看出:不仅文学允许虚构、需要虚构,优秀的史学著作同样离不开虚构。虚构不仅能使历史典籍熠熠生辉,而且还能让历史人物“生命之树常青”,换句话说,优秀的史书之所以有恒久、巨大的艺术魅力,所以令后人心驰神往,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叙事细节上的虚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