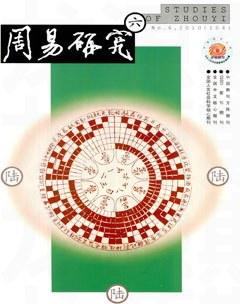道器之辨中的三种范式及其转换
陈屹
摘要:道器之辨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形成了三种理论范式并实现了范式转换,即从汉唐宇宙生成论范式下的“道先器后”说转换为宋明本体论范式下的“道体器用”说,进而在明清之际转换为生存论范式下的“治器显道”说,而生存论范式开启了人文主义视野和趋时更新的开放价值取向。
关键词:道器;范式;范式转换;孔颖达;朱熹;王夫之
中图分类号:B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882(2010)06-0014-07
道器以一对范畴的形式出现首见于《易传·系辞上》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和此句密切相关的是《系辞》中另两句话,“一阴一阳之谓道”和“形乃谓之器”。单从字面上,这三句中至少涉及道与器、形而上与形而下、形与道器、阴阳与道一系列范畴之间的关系。事实上,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关于道器之辨的争论,正是围绕着上述范畴而进一步展开的。
张立文认为,中国哲学史上的道器观主要有器体道用、道体器用、道不离器、道器统一等几种观点,并将历史上的道器之辨总结为“有无范畴转化”的横向进程和“道器上联阴阳、下行心物”的纵向进程。张氏从范畴史的角度,对中国哲学发展中的道器之辨做了体系性的总结,但以横向、纵向的结构总结道器之辨,主要是涵盖了汉唐儒学和宋明理学的观点,而淡化了明清哲学道器观的革新意义。吴根友师主要着眼于明清之际的哲学转型,认为由宋至明清道器观是从“崇道黜器”到“由器求道”,标志着传统价值观向近代性“崇新求变尚奇”价值观的转变。陈赟特别注意到宋明理学由于道的理化,而以理气之辨取代了道器之辨,这样道器之辨其实存在着宇宙论和存在论视域的不同,并认为船山的道器论开启了不同于以往形而上学框架的后形而上学视域,陈赟的研究方法和解释都富有新意,但形而上学与后形而上学对举都是西方哲学语境下的概念,其应用有边界和限制。
本文试图引入“范式”和“范式转换”的概念,认为在道器及其相关范畴的研究中,从汉唐儒学到宋明理学再到明清之际哲学形成了各自的理论范式并实现了范式的转换,并抽取三种理论范式的代表人物孔颖达、朱熹、王船山同时兼及其他哲学家的道器观进行阐述。
一、引论
“范式”一词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的概念,即从paradigm翻译而来。它主要是指一定历史时期的科学共同体所公认的科学实践的范例,“它们包括定律、理论、应用和仪器在一起——为特定的连贯的科学研究的传统提供模型。”从这一点看,将“范式”视作某一时期的哲学家群体所共同认可和遵循的学术传统、思维形态、价值信念也未尝不可。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笔者将范式概念应用于中国哲学发展中的道器关系研究。
孔颖达《周易正义》中,在汉唐儒学主流的“无形生有形”的元气宇宙论范式下,提出了“道先器后”说。此种范式下的道器观,无法从根本上凸显儒家之道和佛、道两家的区别,特别是无法保证儒家伦理和道德规范的必然性和恒常性,及至宋明,为朱熹所代表的理本体论哲学范式所取代,即出现了范式的转换。“理”本体论,强调的是以“理”为本、为体,“本体”是根本究竟的意思,表征的是万事万物得有存在和生成的逻辑起点、终极根据和必然规律。从而,道器的关系也不再是时间生成上的先后关系,而是体用关系,即“道体器用”说。道在逻辑上先于器,是器之为器的所以然和当然之则,由于以理为道,道器范畴又表现为理气范畴和理物范畴。随着理学的官方化和意识形态化,理本体论的范式的危机也随之出现,其存理而遗人,导致了人的伦理异化;同理学相互激荡的心学,及至阳明后学也沦为空谈心性。适逢明清巨变,知识分子普遍反思宋明理学的弊端,针对后期理学的桎梏化、心学良知的知觉化,而现实的生活世界、人的生存及其历史性生存意义被遮蔽。船山以“天地之生,以人为始……自然者天地,主持者人”的卓越创见,在人文主义的视野下开启了不同于理本体论范式的生存论范式,从人的生存和践行出发,以天为器、以人为道,在以“人文化成天下”的历史过程中人道得以彰显和流行,其道器观即是“治器显道”说。
二、宇宙生成论范式下的“道先器后”说
汉唐之际,在《易传》经学范畴内,对道器关系进行论述的当首推孔颖达。其在《周易正义序》中,从《易纬·乾凿度》的宇宙论出发,而论及《系辞》中的道器关系。《易纬·乾凿度》在《系辞》的宇宙生成论中融入了道家的宇宙观,将“易有太极”的“易”视为更为原初的“太易”,对应于“无形”或“道”,而“太极”则是“有”、是元气混而为一、天地未分时的状态,包含太初、太始和太素。这样,“易有太极”其实就是“无中生有”,于是便有“太易一太极(太初、太始、太素)一阴阳二气与天地一四象一八卦以致器物”的宇宙生成序列。孔颖达正是秉持这样的宇宙生成论而说道器关系,“道”就是“无形”的领域,而“器”就是“有形”的领域。“无形”而生“有形”,即是道生器。从宇宙生成次序上讲是“道先器后”,其背后的理论范式也可界定为“无形生有形”的元气宇宙论。孔颖达在疏解《系辞》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时,进一步强化了其“道先器后”说。
道是无体之名,形是有质之称。凡有从无而生,形由道而立,是先道而后形,是道在形之上,形在道之下。故自形外已上者谓之道也,自形内而下者谓之器也。形虽处道器两畔之际,形在器,不在道也。既有形质,可为器用,故云“形而下者谓之器”也。
“道是无体之名,形是有质之称”,“体”、“质”互文。“道”指无形质,而不是抽象的“无”;“形”为形质、体质。“形而上”是形质之外已上,是先于有形之物的“道”的领域;“形而下”是形质之内而下,是属于由形质而成器用的“器”的领域。由于在宇宙生成次序上,有形生于无形,所以“形由道而立,是先道而后形”,明确提出其“道先器后”说。形、器都为“有形”,所以同属形而下,但它们有区别。《礼记·学记》言“玉不琢不成器”,则“器”是“形”的进一步加工或生成后的产物,其结果是具有了器用。孔颖达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说“器,谓物堪用者”,所以对“物”而言,首先是有形质,当其有了器用则成“器”。还需指出的是,当孔颖达说“道在形之上,形在道之下”时,其实他已经改变“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为“形之上者为道,道之下者为形器”。然而,“形之上”与“形而上”不尽相同,“形而下”更不对应于“遭之下”。这种语式的变化凸显道与形器的对立和二分,强化了二者的区隔,而不是从“形”的角度来联系沟通道与器。
综上所述,孔颖达的道器观是“无形生有形”的宇宙生成论范式下的“道先器后”说,其强调的是宇宙发生的时间次序。但是,宇宙生成论范式致命的问题在于,无形何以生出有形?“忽然而生”的说法,只是一种偶然性,没有必然性,整个世界都不过是幻象。另外,此种范式毕竟夹杂了道家和玄学的因素,而没有凸显儒家的性格,儒家的“道”绝不可能建立在“太易”的“无形之道”上,否则儒家的一整套伦理道德规范、社会价值理想如何安放?如何显示其合理性和必然性?这是汉唐儒学主流的宇宙生成论范式所
无法解决的,特别还面对着佛、道两家越来越强的挑战,儒家需要新的范式,于是,在宋明,道器之辨在理学的范式下获得了新的诠释。
三、本体论范式下的“道体器用”说
从汉唐到宋明,以理学的建立为标志,儒家的理论形态出现了一次重大的范式转换。宋明理学家主要关注的不再是宇宙如何生成的问题,而是处在生活世界中的人及人文社会的价值根源和根据问题,而且这种价值是不同于佛、道两家的儒家的伦理和道德规范,要寻求它们的形上学根据。简而言之·宋明理学的核心问题是“性与天道”问题,是重建儒家的心性形上学。这样,从汉唐儒学占主导地位的宇宙生成论范式就转换为本体论范式,道器范畴也被重新诠释和定位,特别是以“理”说“道”,“理”成为最高、最终极的范畴。
张载首先抛弃了汉唐儒流行的“以老解易”传统,他认为“道”和“器”不是“有”与“无”关系,也不是“无形”生“有形”的关系,而是“幽”与“明”的关系。张载持气本原论观点,整个宇宙不过是气聚散于太虚的生成演化过程。“道与“器”则是气化流行过程中的两个不同阶段,气化流行即道、气化流行的凝结则是器。
张载以一阴一阳为形上之道,而在二程看来,阴阳之气仍为形而下,而不是儒家的形上之道。
程颐明确指出道与气的不同,阴阳之气是形而下,而形而上之道则是所以一阴一阳者。一阴一阳的气化流行只是实然的状态,问题是这样的气化流行何以可能,它的根据、动力、原因何在?如果没有根据和原因,那么气化流行就只是一个偶然现象,儒家的一整套理论都将丧失必然性根基。另外,气化流行何以是如此这般进行而不是别的方式进行,它的规律、规则何在?而所谓的根据、动力、原因、规律正是程颐所说的“所以”,故形而上之道本身不是气,而是气化流行得以可能、得以有序运行的根据、动力、原因和规律。形上之道是抽象的、必然的、绝对的、终极性的,亦即是程颢自家体贴出来的“天理”。在二程,天道和天理属于同一个范畴,作为形上之道的“理”上升为本体论的概念。
万物统一性的根据是“皆有此理”,天地之间只是“理”而已,一切存在物都依赖“理”而得以存在,“理”是最根本、最真实的存在;同时,此“理”只是自在的存在,“己何与焉”,它不是被创造物、没有存亡加减,而是大全,“元无少欠,百理具备”。在这两层意义上,“理”成为终极性、根本性、普遍性、恒常性的实存,亦即是“理本论”。在“理本论”的背景下,程颐用“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来说明道器、理事、理象关系从而有道器一源、道体器用之说。及至朱熹,成理学之大成,道器关系在人的哲学体系中,就首先表现为本原论上的理气关系和禀赋论上的物理关系。
若论本原,即是有理然后有气,故理不可以偏全论。若论禀赋,则有是气而后理随以具,故有是气则有是理。
朱熹是从“本原”和“禀赋”两个角度论述理气关系。“本原”是指终极性的根源,推本溯源的说,是理先气后。不过,这个先后不是时间上的概念,而是理论上的逻辑先后,凸显理气的不杂。从“理”是本体、本原的角度说,“理”是“气”及“气化流行”存在和发生的根源、根据,其重点在所以然之理。“禀赋”是针对具体、个别的器物而言,则是理随气具,有什么样的器物就必具其当然之理,凸显在具体器物上则理气不离。此时,“理”是指个体的本质和规律,重点在当然之则。无论是“本原”角度,还是“禀赋”角度,朱熹都强调理气的不离不杂,认为作为所以然和当然之则的“理”更为根本,所以,朱熹是理气合一的理本论。
朱熹从“本原”和“禀赋”两方面建构的理气合一的理本论,融摄了张载的气本原论和二程的理本论,使其理论范式具有了更大的解释空间。他将描述“道器”关系的形上形下之分用于区分“理气”,于足便有“形而上者谓之理,形而下者谓之气”之说,此时“理”与“气”都是在“本原”的层次上说,“气”指阴阳二气,“理”是所以阴阳者。而“道器”关系,在朱子哲学就转换成“理物”关系。
对任一事物而言,理气浑然一体,道器相须。“即形器之本体而离乎形器,则谓之道;就形器而言,则谓之器”,道器或理物都必须即“形”而言。所以,朱子反对“无形谓之道,有形谓之器”的说法。因为如此说,道与器就截然二分,理与物就毫无关系。因此,朱熹一方面强调道器相须,但从“本原”的视角,理、气决然是二物”。他最终要坚守的仍然是作为形上之道的“理”的终极性和纯粹性,“理”在朱熹哲学成为一个静止的抽象绝对实体。
朱熹的理本论,为现实世界的人和人伦社会提供了终极的存在根据和价值信仰根源,并从根本上保证了儒家伦理和道德规范的绝对性、必然性、恒常性和普遍性;而且,无论是“性即理”、还是“心即理”,都高扬了人的道德理性和道德尊严,增强了人的道德自律意识。但是,“理”的本体论范式,会使“理”绝对化、实体化、静止化、名词化,在学理上会使“理”丧失鲜活的、丰富的内涵。船山就说“理之则有理矣”,他区别了动词性的“理”和名词性的“理”。“理”本来是生成的动态过程,这一动态过程表现为动词性的“治理”,“治理”的结果则成其“条理”或“文理”,而在理本体论范式下,“理”丰富的内涵就丧失了,其结果是“立理以限事”。而在专制社会后期,理学意识形态化,导致伦理异化,动辄“以理杀人”,理学成为了一种抹杀人文意识、取消人的主体性和个体性的伦文主义,人消失在绝对的“天理”视野中。这时候,需要一种人文主义的觉醒,而明清之际“天崩地解”形势,为范式的转换提供了机缘,最终滋生了王船山人文主义视野下的生存论范式,道器之辨也转变为“治器显道”的新的诠释方式。
四、生存论范式下的“治器显道”说
明清之际的巨变,促使儒家知识分子对自身学术传统进行深刻反思,而船山则是在哲学反思领域中集大成者。船山的根本问题,是面对其所处时代,个人之艰难险阻、颠沛流离、命悬一线的生命历程,人何以能够空无一切的度过一生?虽然是“七尺从天乞活埋”,但又“六经责我开生面”,“我”的地位突出。所以,人的生存和历史性存在成为船山哲学首出的视野,实现了从“理”本体论范式到生存论范式的转换。
船山以人道明天道,强调“人之独”,所谓“壁立万仞,只争一线”;同时,人又是历史性的存在,“过去,吾识也。未来,吾虑也。现在,吾思也。天地古今以此而成,天下之赢赢以此而生。”人的生存涵摄过去、把握当下、预知未来,人正是在历史性生成中实现人道、成就事业。萧蓬父认为船山哲学“首重人极,以史为归”,反映了人文意识的觉醒,其“明有、尊生、主动”、以“人文化成天下”的易学精神,为近代“人文易”奠定了理论根基。船山从人的生存和践行的角度出发去理解和肯定现实世界中的一切存在物及其价值,“自人而言之”以明“两间之有”,提出了“天下唯器”、“尽器,则道在其中”的新道器观。
承前文所述,船山是接着宋明讲的,用“隐显”的范畴区分“道”与“器”、“形而上”与“形而下”。船山认为“形而下”是指成形以后、形之成乎物而可见可循者,这是“显”的领域;而形而上是“隐而未见”的领域,其前是“未形而有隐然不可瑜之天则”以及成形后“可用以效其当然之能者”,前者是未形时之隐然不
显,后者是成形后“隐于形之中而不显”,这两者其实对应于理学家所说的“所以然”与“当然之则”。但船山紧接着说,当成形后,则其“前乎所以成之者之良能著,后乎所以用之者之功效定,故谓之‘形而上而不离乎形。”这句话非常关键,是说只有从现实中的器物出发才能把握道,道才得以著、得以显、得以定。所以,船山首先要肯定的是人的生存和践行中所直接遭遇到的器物或事务。作为形而上的在天之道,是属于“天”的领域,“天”是其所是、是自在自然的存在,即船山说的“天之天”,而“天之为天者,肆应无极,随时无常”,“天之化裁人,终占不测其妙;人之裁成天,终古而不代其工”。所以,船山认为人不能执理以限天,我们所要把握的是“人之天”而不是“天之天”,从而其视域与宋明理学相比,发生了一个根本的转变。其不以“天理”为首出,而以生活世界中从事着社会实践的“人”为首出,在人文主义视野下开启了生存论的范式。故而,人必须亲身于作器、治器、述器、尽器的活动中而求在人之天道,而不“僭于天之天”、“滥于物之天”。程朱理学以“天理”为首出,正是“援天以治人,而亵天之‘明威、以乱民之‘聪明”。船山通过区分“天之天”与“人之天”,将宋明理学高悬的“天理”拉回到现实中“人”,而从人的视野出发,他敏锐的观察到对《系辞》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理解,首先要清楚“渭之”的确切意义。
船山说“‘谓之者,从其谓而立之名也。‘上下者,初无定界,从乎所拟议而施之谓也。”“从其谓”中“谓”即是“从乎所拟议”中“拟议”的意思,“拟议”是指揣度商议;揣度商议只可能是人的行为活动,故“从其谓”的主语是人。那么,此处用“谓之”即是说,其实本没有形上形下、道器之分,只是从人实践需要的角度为其区分命名而已,“于彼固然无分之地而可为之分,故日‘谓之,我为之名而辨以著也。”所以,道器关系即不是宇宙生存论范式下“道先器后”的时间上的区分,也不是本体论范式下的“道体器用”的逻辑先后的划分,更不是上下空间上的划分,而是生存论范式下人给予的一种命名上的区分,所谓“上下皆名也,非有涯量之可别者也。”
从人生存和践行的视野出发,“天下唯器”,“器”不是外在于人的被观察者、被研究者、被解释者,而正是在人的生存和践行活动中“器”的真实性得以显现并获得肯定。船山因而强调“器”的优先性,“无其器则无其道”,有了弓、矢才有射道,有了车、马才有御道,道依器存。“器而后有形,形而后有上”,有了器才显现出形上之道,有了具体、个别的事物才显现出其规律和法则。而且,道的显现必须通过人“治器”、践行活动而实现,所谓“自其治而言之,而上之名立焉”。“治器”、践行、事为都是作为人的生存的动态历史过程,故而“道”也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朱熹的理本体论,以理为道,而将道静止化。而船山认为“道”随着人类生存和实践活动的发展“因时而万殊”,“汉、唐无今日之道,则今日无他年之道者多矣。”船山的道器观开启的是一个开放、求新、尚变的价值取向。
船山从人文主义视野下的生存论范式出发,划分天之道和在人之天道,天之道是自在自然的,在人之天道则是在人的生存和践行过程中显现出来的。所以,他强调不以理限天、以理限事,天之天在人之视域之外。当他说道在器中、理在事中时,形上形下对道器的区分,不是时间上、空间上和逻辑上的区分,而是从人的生存和践行活动出发给予的命名区分。“器”在生存论范式下其真实性得到肯定、并取得优先的地位,而“道”则在人的“治器”实践活动中显现,并随着这一活动过程而趋时更新,所以船山的道器观可概括为“治器显道”说。
五、道器之辨中范式及其转换的意义和启示
本文分析了道器之辨中的三种范式,即宇宙生成论范式、本体论范式和生成论范式,在此三种范式下,分别形成了“道先器后”说、“道体器用”说和“治器显道”说。宇宙生成论范式,是人对宇宙生成的一种解释,它建立在古典天文学的观察和人对观察结果的反思,其考虑的核心问题是宇宙的始基是什么?而追寻的结果,“道”即是始基,并从物理时间的先后次序产生出“器”。在这种范式下,关注更多的是自然,“道”和“器”本质上都是外在于人的,人最多不过就是气化流行中的一个自然器物而已;亦即是说,在宇宙论中,人的存在的神圣性得以消失,人只是一个宇宙生成的解释者和旁观者。而在本体论范式下,其对现存的人、社会和宇宙的存在进行了哲学上的反思和追问,它关心的核心问题是人、社会、宇宙为什么存在、而且必须是如此存在?于是,“道”便不是始基,而是终极根据、根源和规律,道和器物的关系也随之改变。“道”是器之为器的所以然和当然之则,整个世界获得了必然性根据,人的神圣性也得以彰显,“道”是人存在的终极信仰和终极关怀。但本体论范式,其本质是将人、社会、宇宙抽象为绝对的、静止的精神实体,人和世界上的一切都是被其决定的,人只是由自然物变成了一个能认识和反思“天理”的存在物。无论是宇宙论范式、还是本体论范式,其根本的问题都是忘记了生存着的人。人在这两种范式下最终都只是作为客体而存在,在“道”的面前人永远都是“用”,而且其极端后果就是消用以人体。生存论范式的思考视野则和前两种范式完全不同,它是从人的生存和历史性存在出发的,是人的生存和实践行为肯定了宇宙的存在、道的存在及其价值。道和器不是外在于人的,恰好是在人的治器、践形的生存过程中,“器”和“道”的真实性得以显现,并随着人的实践活动的深入而不断发展更新。宇宙论开启的是一个自然的社会和生物的人,本体论开启的是一个价值规范的社会和道德的人,而生存论开启的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和一个不断生成和发展的人。而且,三者不是完全分隔、不相通约的,恰好是生存论的范式涵摄了宇宙论和本体论,预示着中国哲学可能的发展趋向。
在三种范式下,它们都共享了相同的概念和范畴,可以说,道器之辨是中国哲学发展史上一个固有的传统。但是,随着范式的转换,道器范畴不断获得新的内涵和新的价值。所以,“传统,并非已经死去的历史陈迹,而是至今活着的文化生命。它渊源于过去,汇注于现在(经过现实一代人的参与),又奔流向未来。”通过分析道器之辨中的三种范式及其范式转换,可以有力的证明中国哲学绝不是“死水微澜”、静止的存在物,而是一滩活水,不断生成着而趋时更新。而对于现今中国学人来说,我们仍然面临着当代的道、器问题。就“道”而言,至少有西方的“道”和中国的“道”,是用西方的“道”来根治中国的“器”呢?还是用中国的“道”来对峙西方现代性导致的“器用”崇拜和“器用”泛滥?笔者认为,萧萐父先生所说的“多维互动,漫汗通观儒释道;积杂成纯,从容涵化印中西”甚为精当,在此前提下,立足于当代中国的“器用”,面向未来,或许可以走出一条打上世界印记的中国式的康庄大“道”。
责任编辑:张克宾刘保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