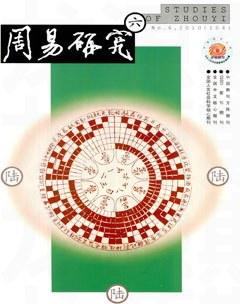蔡元定对河图洛书的区分
庹永

摘要:蔡元定主张“河十洛九”、“河先洛后”,与刘牧的“河九洛十”、“河洛同出”说相反。蔡元定强调河图与洛书的区分,与朱熹的“虚中为易、实中为范”说企图融合河图、洛书也不同。其目的是加强十数图与《周易》八卦的关联,九数图与《洪范》九畴的关联,进而将《洪范》纳入易学系统。其子蔡沈的《洪范皇极》以《周易》为象学,对应河图,以《洪范》为数学,对应洛书,正是这一目的的体现。这一区分是对刘牧河图、洛书说的发展,蔡氏父子由此构建了其范数之学。
关键词:蔡元定;蔡沈;河图;洛书;洪范;范数之学
中图分类号:B24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882(2010)06-0043-06
一
蔡元定,福建建阳人,朱熹的弟子兼好友,在象数易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曾参与朱熹《易学启蒙》一书的创作。《易学启蒙》中的“河十洛九”说便是蔡元定的观点,后被朱熹所接受。蔡元定没有留下专门的易学著作,其《皇极经世指要》是对邵雍学说的介绍与阐发。他对河图、洛书的论述,保留在《易学启蒙·本图书》中,其中有一段话注明为“蔡元定日”,文中,蔡元定通过批驳刘牧,表达了他对河图、洛书的基本观点。刘牧是宋代河洛之学的开创者之一,主张“河九洛十”、“河洛同出”,“河洛同出”即河图、洛书同出于伏羲之世。蔡元定从三个方面对刘牧的观点进行了反驳。
首先,蔡元定以前人的说法作为依据,指出刘牧之说与诸家说法不符。他说:“古今传记,自孔安国、刘向父子、班固皆以为河图授羲,洛书锡禹。关子明、邵康节皆以十为河图,九为洛书……惟刘牧臆见,以九为河图,十为洛书。”《易学启蒙》对以上诸家的说法都有引用。蔡元定认为刘牧的说法与这些说法都不同,纯属自己的主观见解。
其次,蔡元定以经典作为依据,指出刘牧之说与经典不符。他说:“盖《大传》既陈天地五十有五之数,《洪范》又明言天乃锡禹洪范九畴,而九宫之数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正龟背之象也。”(《朱子全书》第一册,第211页)这是说,《系辞》讲天地之数总和为五十五,十数图所有数字的总和也是五十五,《尚书·洪范》讲天赐大禹《洪范》九畴,而九数图正是由一至九九个数字组成。所以,十数图对应《周易》,九数图对应《洪范》。再综合前人“伏羲则河图作八卦,大禹则洛书作九畴”的说法,十数图即是河图,九数图即是洛书。
再次,蔡元定提出新的理论,重新解释经典文句的含义,使刘牧的论证失效。他说:“(刘牧)又引《大传》,以为二者皆出于伏羲之世。其易置图书,并无明验,但谓伏羲兼取图书,则《易》《范》之数诚相表里,为可疑耳。其实天地之理一而已矣,虽时有古今先后之不同,而其理则不容于有二也。故伏羲但据河图以作《易》,则不必豫见洛书,而已逆与之合矣。大禹但据洛书以作《范》,则亦不必追考河图,而已暗与之符矣……假令今世复有图书者出,其数亦必相符,可谓伏羲有取於今日而作《易》乎?大传所谓‘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者亦泛言圣人作《易》作《范》,其言皆出于天之意。”(《朱子全书》第一册,第212页)蔡元定通过“天地之理一而已矣”这一理论说明,表明河图、洛书无论出现在什么时代,它们在天理的层面上必然是相通的,以此并不能说明河图、洛书同出一世,因此,《系辞》的说法只是泛言圣人效法天理,并非确切的事实陈述。
若仔细推敲,这三个方面的论证都是不充分的。对于第一个方面,清代学者潘耒已经指出:“朱蔡之说,谓孔安国、刘歆、关子明、邵尧夫皆言十为图、九为书,按此四家之说唯安国略有可据。刘歆但言河图、洛书相为经纬,八卦九章相为表里,不言孰为图孰为书。关子明《易传》未尝一言及图书,《洞极经》乃阮逸伪撰,其七十二象朱子尝斥之为乱道者,而顾取其说以证图书耶!尧夫真得希夷之传者,然《经世书》数万言,绝不及图书,唯《观物外篇》一条言之,亦泛论方圆,未尝直指九十也。”对照《易学启蒙》所引诸家之语,这些批评都有道理。关键问题还在于,即便诸家的说法都很明确,仅以诸学者的说法作为根据也是不够的。刘牧正是通过否定孔安国的说法来表明自己的观点,他说:“且孔氏以箕子称天乃锡禹九畴,便谓之洛出龟书,则不思圣人云‘河出图、洛出书在作《易》之前也。”刘牧以《系辞》的说法为根据,否定了孔安国的说法。所以,经典依据更为关键。在第二个方面的论证中,蔡元定也提出了经典依据,但这些依据仍然不够充分。因为,虽然天地之数的总和与十数图数字的总和相等,但《系辞》并未明言天地之数即是河图之数,也未明言天地之数与画卦的关系;虽然《洪范》九畴与九数图之“九”对应,但《洪范》并未提及洛书,二者与河图、洛书的联系仍然只能算作主观联想。刘牧就是通过重新确定洛书的内容,从而建立十数图与洛书的关联,他说:“且《书》之九畴,惟五行是包天地自然之数,余八法皆是禹参酌天时人事类之耳,则非龟所负之文也。今详《洪范》五行传,凡言灾异必推五行为之宗,又若鲧无圣德,汩陈五行,是以彝伦攸皲。则知五行是天垂自然之数,其文负于神龟,余八法皆大禹引而伸之。”刘牧认定洛书只包含五行的内容,《洪范》其余八条为大禹自作,从而切断九数图与九畴的联系,同时又通过五行这一环节建立了十数图与洛书的关联。对于蔡元定第三个方面论证,既然河图、洛书在理的层面上相通这一点,不能作为二者同出的理由,它同样也不能作为二者不同出的理由,但不能证明自己的说法就合理,他所依据的仍只是刘歆等人的说法,而缺乏经典依据,所以,这一条反驳的力度也很有限。
蔡元定对自己观点的论证是不充分的,之所以如此,问题不在蔡元定。归根到底,传统儒家经典中关于河图、洛书的记载都未指明河图、洛书具体为何物,而引起后世的争论。所以,除非有新的出土文物或文献,否则一切关于河图、洛书的具体论述都只能是作者自己的推测与想象。其实,河洛之学是宋代才出现的一种学问,是融合诸如河图洛书说、五行生成数、九宫数、卦气说等,逐渐形成的一种易学的新形式,因此,各家的说法其实都是在进行理论创新。为了增强自己学说的有效性,各家都试图证明自己的说法古已有之。既然是一种理论创新,对今天的学术史研究来说,问题的重点就不在于各家古已有之的论证是否成立,而在于作者要表达的观点,以及他为何要提出这样的观点。对于蔡元定的河图洛书说,问题的重点就在于,他对河图、洛书的基本观点是什么?以及,他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观点?
二
通过上面蔡元定对刘牧的反驳,可以看出,他对河图、洛书的基本看法:其一,以十数图为河图,以九数图为洛书,即“河十洛九”。其二,认为河图出于伏羲之世,伏羲据之作八卦,洛书出于大禹之世,大禹据之作九畴,可称之为“河先洛后”;虽然蔡元定关于河图、洛书的论述都载于朱熹的《易学启蒙》,但朱熹最初对这两个观点都不赞同,后来朱熹的观点虽然有局部的改变,但从根本上说,仍不同于蔡元定。
其一,朱熹最初以十数图为洛书,他在给蔡元定的一封回信中说:“前日七八九六之说于意云何,近细推之,乃自河图而来,即老兄所谓洛书者。欲于《启蒙》之首增此一篇,并列河图、洛书以发其端。”@可
见在这个时候,朱熹是主张“河九洛十”的。不过在《易学启蒙》成书时朱熹已经接受了蔡元定“河十洛九”的观点,因为《易学启蒙》首列两图的名称采用的是“河十洛九”的说法。
其二,朱熹最初认为九数图并非出于大禹之世,而是先出。在一封给蔡元定回信中朱熹说:“河洛辨说甚详,然皆在夫子作传之后,其间极有不足据以为说者,鄙意但觉九宫之图意义精约,故疑其先出。而八卦十数、九畴五行各出一图,自不相妨,故有虚中为易、实中为范之说,自谓颇得其旨。今详所论亦是一说,更俟面论,然恐卒未有定论。不若两存,以俟后人之为愈也。”不知朱熹所谓的九数图先出,是否就是刘牧的河图、洛书同出伏羲之世的说法。需要注意的是这封信中“虚中为易、实中为范”的说法。朱熹这一观点也体现于《易学启蒙》中:“河图之虚五与十者,太极也……析四方之合以为乾坤离坎,补四隅之空以为兑震巽艮者,八卦也……洛书而虚其中则亦太极也……四方之正以为乾坤离坎,四隅之偏以为兑震巽艮,则亦八卦也”,(《朱子全书》第一册,第215页。)这是“虚中为易”。还有“洛书之实,其一为五行,其二为五事,其三为八政,其四为五纪,其五为皇极,其六为三德,其七为稽疑,其八为庶证,其九为福极……河图之一六为水,二七为火,三八为木,四九为金,五十为土,则固洪范之五行,而五十有五者又九畴之子目也”,(《朱子全书》第一册,第215页)这是“实中为范”。所以朱熹说:“是则洛书固可以为易,而河图亦可以为范矣。且又安知图之不为书,书之不为图也耶?”(《朱子全书》第一册,第215页)还说:“是其时虽有先后,数虽有多寡,然其为理则一而已……苟明乎此,则横斜曲直无所不通,而河图、洛书又岂有先后彼此之间哉?”(《朱子全书》第一册,第216页)可见,朱熹并不主张严格区分河图、洛书,而是有意将二者融合,甚至认为,对二者名称和先后的区分都不必过于死板。根据朱熹信中所说,他自认为“虚中为易,实中为范”的说法“颇得其旨”,并告诉蔡元定“不若两存”,表明蔡元定并不赞成这一说法。从蔡元定的方面说,其《皇极经世指要》成书于1189年,比《易学启蒙》晚三年,其序中说“龙马负图,伏羲因之以画八卦”,未提及洛书,而且整部书中论述《周易》的地方也丝毫未提及洛书。还有,蔡元定在《西山公集·答江德功书》中说:“伏羲之画,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然后能毕天下之能事。不然,天生河图特一技术之末耳。”此处讲伏羲画卦,也仅与河图对应,并未提及洛书。可见,《易学启蒙》中“虚中为易、实中为范”的说法确实不是蔡元定的观点。
总的来说,虽然朱熹最后认同了“河十洛九”与“河先洛后”的说法,但这只是局部细节上的认同,从根本上说,朱熹主张融合河图、洛书,而蔡元定则强调对河图、洛书的区分,他意图加强十数图与《周易》八卦的关联,九数图与《洪范》九畴的关联。那么蔡元定这么做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蔡元定虽然没有留下专门的易学著作,但其子蔡沈著有一部《洪范皇极》。《宋元学案·九峰学案》说:“《洪范》之数,学者久失其传,西山独心得之,未及论著,亦日‘成吾书者沈也。先生沈潜反复者数十年,然后克就。”蔡沈在《洪范皇极内篇·序》中说:“先君子曰:‘洛书者,数之原也。余读《洪范》而有感焉。”看来,蔡元定非常重视《洪范》与洛书中蕴含的“数”学,他加强洛书与《洪范》九畴的关联,目的就是企图以河洛之学为桥梁,将《洪范》引入易学系统,进而发挥《洪范》之数,只是未有成型的著作。清代潘末对此早有发觉,他说:“季通父子尊尚《洪范》,自作一书,以九九积数,有卦有辞。复著《洪范皇极内外篇》欲以准《易》,故指九为洛书。”
蔡沈的《洪范皇极》对河图、洛书有非常明确的区分,比如“河图体圆而用方,圣人以之而画卦。洛书体方而用圆,圣人以之而叙畴。卦者阴阳之象也,畴者五行之数也。象非耦不立,数非奇不行。”还有“河图非无奇也,而用则存乎耦。洛书非无耦也,而用则存乎奇。耦者,阴阳之对待乎。奇者,五行之迭运乎。”还有“数者,动而之乎静者也。象者,静而之乎动者也。动者用之所以行,静者体之所以立。”综合这些说法可以列出一个表格,如下所示。

通过表格可以明显地看出,河图、洛书对应着两个互补的系统,河图对应《周易》系统,洛书对应《洪范》系统。也就是说,《洪范皇极》以河洛之学为桥梁,将《洪范》引入传统易学系统,并大大地加以发挥,使之成为与传统易学同等规模的互补系统。这也正是蔡沈的主观目的,《洪范皇极·内篇序》中说:“《易》更四圣,而象已著。《范》赐神禹,而数不传。后之作者,昧象数之原,窒变通之妙,或即象而为数,或反数而拟象,《洞极》用书,《潜虚》用图,非无作也,而牵合附会,自然之数,益晦蚀焉。”蔡沈以传统易学为“象”学,他认为还有一个“数”学,蕴藏于《洪范》之中,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其《洪范皇极》的目的就是要使“范数”之学得到发扬。
但“数”与“象”并不对立,蔡沈说:“数之与象,若异用也,而本则一。若殊途也,而归则同。不明乎数,不足与语象;不明乎象,不足与语数。二者可以相有,不可以相无也。”象与数两个系统是互相依赖、互相补充的。不仅如此,在理的层面,二者还是相通的,蔡沈说:“阴阳五行,固非二体;八卦九畴,亦非二致。理一用殊,非深于造化者,孰能识之。”这与蔡元定在《易学启蒙》中所说的“其理则不容于有二”是一个意思,“理一”与“用殊”同等重要,河图、洛书在理上相通,但不能因此而忽视二者的不同作用,反之亦然。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虽然蔡元定认为河图、洛书“其理则不容于有二”,但不会象朱熹那样主张“虚中为易,实中为范”,混淆二者的不同作用。
三
蔡氏父子区分河图、洛书,从河洛之学本身来说,是对刘牧河图、洛书说的发展,而其主要目的,则是为进一步阐发“范数之学”奠定基础。
刘牧的河图、洛书说应当说还很不完善,他在用九数图搭配八卦、五行时,其实完全没有用到九数图的方位。《易数钩隐图·遗论九事》说:“昔虑牺氏之有天下,感龙马之瑞,负天地之数出于河,是谓龙图者也。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与四为肩,六与八为足,五为腹心,纵横数之皆十五……且天一起坎,地二生离,天三处震,地四居兑,天五由中,此五行之生数也。且孤阴不生,独阳不发,故子配地六,午配天七,卯配地八,酉配天九,中配地十,既极五行之成数,遂定八卦之象,因而重之以成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此圣人设卦观象之奥旨也。”刘牧首先说明河图即是九数图,然后以一、二、三、四四个生数配坎、离、震、兑四正卦·但若以此搭配九数图,则兑居东南,离居西南,根本不是正卦方位。还有“酉配天九”,酉的方位应在正西,九数图九的方位在正南,也对不上。刘牧这里对应的实际是十数图的方位,并明确提到“中配地十”。而刘牧曾明确指出十数图不含八卦,说“今河图相传于前代,其数自一至九,包四象、八卦之义,而兼五行之数。洛书则惟五行生成之数也”。所以刘牧在此处的论述是混乱的。
实际上,刘牧在整部《易数钩隐图》中根本没有一处用到九数图的方位,九数图的方位仅仅在介绍河
图的时候出现过一次。这表明刘牧的河图、洛书说还不够成熟,他虽然以九数图为河图,并且同时关联八卦和五行,但九数图的方位根本没有发挥作用。
刘牧对此有所解释,有人问到二图搭配五行方位不一致的问题:“洛书云‘一日水,二日火,三日木,四日金,五曰土则与龙图五行之数之位不偶者,何也?”刘牧回答:“洛书九畴惟出于五行之数,故先陈其已交之生数,然后以土数足之,乃可见其成数也。”意思是十数图才是专门表达五行的,九数图只是先表达一下生数,而成数在十数图中体现。但无论如何,如果九数图的方位不起作用的话,那就只是几个数字,也就失去了其作为一张图的意义。
刘牧已经意图区分河图、洛书的不同作用,他说:“所谓象之与形者,《易》云‘见乃谓之象,河图所以示其象也,‘形乃谓之器,洛书所以陈其形也。”还说:“河图之数惟四十有五。盖不显土数也,不显土数者,以河图陈八卦之象,若其土数则入乎形数矣,是兼其用而不显其成数也。洛书则五十五数,所以成变化而著形器者也,故河图陈四象而不言五行,洛书演五行而不述四象。”他以形上和形下区别河图、洛书的不同作用,其实已接近蔡沈的区分,但在具体论述上有不少混乱之处。蔡氏父子则通过河图、洛书的不同形式,比较好地表达了奇偶、象数、体用、阴阳五行等范畴之间的关系,是对刘牧学说的发展。
蔡氏父子区分河图、洛书不同作用,意在阐发“范数之学”。对应《周易》“象”的系统,蔡沈构建了一个“数”的系统,将“数”的地位提高到了很高的高度,他说:“溟漠之间,兆朕之先,数之原也。有仪有象,判一而两,数之分也。日月星辰垂于上,山岳川泽奠于下,数之著也。四时迭运而不穷,五气以序而流通,风雷不测,雨露之泽,万物形色,数之化也。圣人继世,经天纬地,立兹人极,称物平施,父子以亲,君臣以义,夫妇以别,长幼以序,朋友以信,数之教也。分天为九野,别地为九州,制人为九行,九品任官,九井均田,……数之度也。”从溟漠之间到有仪有象,再到天地形成、四时运行,最后讲到圣人之教、国家制度,蔡沈分别称之为数之原、数之分、数之著、数之化、数之教、数之度。他用数整合了传统的太极、阴阳、五行等理论,构建儒家的形而上学,同时用数整合儒家的伦理规范、度量衡、国家制度,蔡沈以数贯通了形上与形下、天道与人事。这和周敦颐太极图的目的相同,都是对完善儒家形而上学所作的努力。
不过,虽然蔡沈重视数。但并非以数为万物本原,在蔡沈的理论中,数并不是一个本体范畴,而只是一种表达工具。他说:“有理斯有气,气著而理隐;有气斯有形,形著而气隐。人知形之数而不知气之数,人知气之数而不知理之数,知理之数则几矣。”从本体层面描述宇宙万物的时候,他使用的仍只是理、气范畴,而数则是次一级的概念,所谓“理之数”、“气之数”、“形之数”。对数的工具性地位,他有直接的论述,他说“物有其则,数者,尽天下之物则也。事有其理,数者,尽天下之事理也。”
另一方面,虽然数并非是本体层面的概念,但因为数可以尽理,于是就成为把握天道的途径。蔡沈用自己的“范数之学”对《中庸》中的诚论作了新的解释,他说:“不明乎数不明乎善也,不减乎数不诚乎身也。故静则察乎数之常,而天下之故无不通,动则达乎数之变,而天下之几无不获。”还说“虚明则神,神则圣,圣者数之通也。窒暗则惑,惑则愚,愚者数之塞也。”构建了自己独特的“通数成圣”理论。
责任编辑:张克宾姜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