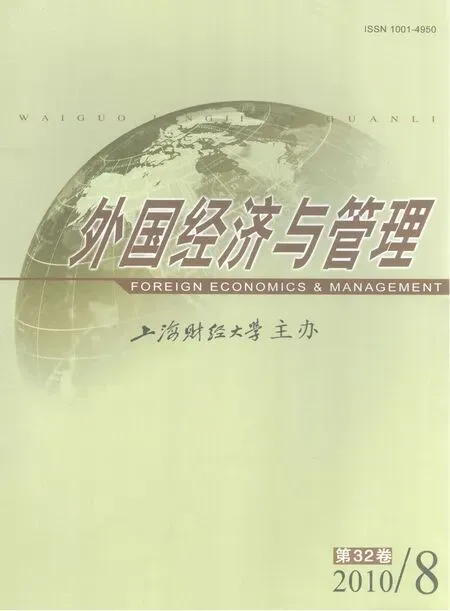基于商业决策视角的伦理观研究述评
吴红梅,刘 洪
(1.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南京210095;2.南京大学商学院,江苏南京210093)
一、引 言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西方国家频繁爆发的商业丑闻引起人们对商业伦理的重视,促使人们把目光聚焦于商业个体面临伦理问题时的决策行为。学者们建立了商业伦理决策的理论模型,并实证分析了个体、组织与情境等层面影响商业伦理决策的因素。[1]其中,个体层面的伦理观相关变量受到了广泛关注。[2]有学者认为,当个体面临的问题具有较高的伦理道德强度时,伦理观会影响个体的感知、判断、行为意图甚至情感,最终影响个体决策。[3]此时伦理观对决策行为的影响要大于其他一般价值观对决策行为的影响。三十多年来,学者们围绕个体伦理观的定义、结构、测量、影响因素和效果、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差异等内容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国际竞争的日益加剧,企业经营的国际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深刻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伦理观差异是取得跨文化经营成功的有力保障。商业决策视角的伦理观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有鉴于此,本文对基于商业决策视角的伦理观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首先介绍了有关伦理观概念、结构和测量方面的研究成果,其次考察了伦理观的前因变量和影响效果,再者分析了不同国家和人群的伦理观差异,最后展望了未来的研究方向,以期为我国学者深入开展伦理观研究提供一些启示。
二、伦理观的概念、结构和测量
(一)伦理观的界定
价值观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个体内在特征,是指个体针对人、事、物所秉持的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及其对人生、政治、道德与审美价值等所形成的高度概括化的观念。[4]其中个体对道德的态度就是伦理观。伦理观是个体在伦理问题上所信奉的伦理哲学和伦理立场。[5]伦理观因人而异:首先表现在个体判断特定行为对错的标准存在差异,因为个体用以说明行为发生情境的解释各不相同;其次表现在个体对特定行为错误程度的裁定存在差异。伦理观引导个体感知、判断、选择和评价与伦理相关事件和行为,甚至左右个体的道德情感。[3]
西方学者用以表述伦理观的英文名词不尽相同。根据笔者所检索到的文献,用以表述伦理观的限定词主要有三类:第一类以“ethical”开头,第二类以“moral”开头,第三类以“personal”开头。表达伦理观的名词更是丰富,达十六种之多,其中还不包括名词单复数的变化。目前学者们较普遍使用的中心词主要有:philosophy、position、ideology、belief、orientation、tendency、thought、inclination、pre-disposition、viewpoints、attitudes、standpoints以及values等。相对而言,“ethical ideology”与“moral philosophy”这两个词语的使用频率较高。
(二)伦理观的结构
学者们对于伦理观概念的界定基本达成共识,大多数学者认为伦理观是指个体内在的伦理哲学或伦理倾向。但是,他们对伦理观内部结构的划分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从而出现了多种观点相持的局面。总的来说,有关伦理观内部结构的划分主要有二元说、三元说、四元说和五元说四种观点。
1.二元说
持二元说的学者认为,虽然个体的道德哲学千差万别,但是归根溯源只体现出两种评价标准,即义务论和目的论。其中,义务论强调道德行为动机必须是善意的。康德的形式主义是最典型的义务论。在康德看来,行为只有遵循了普遍的伦理规范才是合乎道德的。而目的论强调道德行为结果必须给人带来福利。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是典型的目的论。在现有研究中,不少学者将商业决策者的伦理观一分为二。例如,DeMoss和 McCann(1997)把个体的伦理倾向分为权利倾向和关怀倾向;Schminke (1997)与Alder等(2007)提出将个体伦理哲学划分为功利主义与形式主义两种[6];Lam和Shi(2008)将个体的伦理观分为对明确违反法律和规范的行为的态度以及对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的关注[7]; Schlenker等(2008)和McFerran等(2010)则把个体的伦理观划分为原则性强的伦理思想和权宜之计的伦理思想两种[8]。虽然学者们的划分在称谓上不尽相同,但是从本质上都可以归为义务论和目的论的二元说,因为这些不同的伦理构念只不过是义务论与目的论的不同表现形式罢了。
2.三元说
持三元说的学者们把个体道德哲学分为三类:功利主义、权利主义和正义论。功利主义根据行为带来的社会结果评价行为,认为为社会大众带来福利的行为就是善行。权利主义强调个体所赋有的权利。而正义论关注行为或决策应该带来的结果公平性。1984年至2009年期间,学者们陆续开展了四次调查来探究管理人员的行为与其内在伦理哲学的关系。第一次调查是由Fritzsche和Becker于1984年开展的。他们调查了539位营销经理人,向他们询问其在面临商业贿赂、商业泄密、环境污染与产品质量等决策困境时可能采取的道德立场。结果显示,大多数被试会选择功利主义态度来应对伦理困境,少数被试采取权利主义态度,只有极少数被试才会基于正义论来决策。第二次调查是由 Premeaux和Mondy于1993年开展的。他们俩仍然沿用了1984年Fritzsche和Becker设计的四种决策困境,调查结果表明,虽然上世纪九十年代管理人员就开始意识到必须慎重处理商业活动中的伦理问题,但是当时现实中大多数管理人员仍然持功利主义态度来决策。第三次调查是由Premeaux于2004年开展的。Premeaux只是重复了1993年Premeaux和Mondy开展的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管理人员还是依赖功利主义的伦理哲学进行决策;但是,此时人们开始倾向于选择伦理适当行为,因为这样做是合乎伦理的或者选择不道德行为的风险很大。第四次调查是由Premeaux于2009年基于前三次调查开展的。调查结果表明,虽然安然倒闭引起商业界巨大的震荡,但是事实上并没有给管理人员的商业决策哲学带来根本性的变革,管理人员仍然秉持功利主义立场,但是重视商业伦理的氛围正在悄然形成。综合来看,四次调查结果基本一致:不管时代如何变迁,二十年来主导管理人员决策的伦理哲学仍然是功利主义。
3.四元说
Forsyth(1980)提出个体伦理哲学的差异表现在两大维度,即相对主义和理想主义。相对主义源于义务论,表示个体拒绝普遍伦理规范约束的程度,关注行为制约的原则、规范;而理想主义源于目的论,表示个体对他人福利的内在关注程度,关注行为的结果,特别强调避免伤害他人。Forsyth认为,个体伦理哲学均包含上述两个维度,但是两者在个体身上体现出的水平相异。由此,他根据相对主义和理想主义在个体身上体现出的水平把个体分为四类:(1)情境主义者,代表理想主义和相对主义水平都比较高的个体。情境主义者拒绝普遍的伦理规范,主张根据具体情境对行为进行伦理判断,同时也强调行为不能伤害他人。(2)例外主义者,代表理想主义和相对主义水平都比较低的个体。例外主义者更多的是运用功利主义而非义务论的立场来看待问题。另外如果经过计算,某些伤害他人的行为的积极结果要大于消极结果的话,例外主义者更容易接受这些伤害他人的行为。(3)绝对主义者,代表理想主义水平高而相对主义水平低的个体。绝对主义者认为,行为只有遵守普遍的伦理规范才会达到最佳的结果。他们根据康德的绝对命令来做出伦理判断,重视他人福利。(4)主观主义者,代表理想主义水平低而相对主义水平高的个体。他们根据自身的价值观来评价行为是否符合道德标准。同时他们也是实用主义者,站在个人立场来衡量收益和成本,因此在他们的眼中,某些伤害他人的行为并不是不道德的行为。
4.五元说
持五元说的代表学者主要有于1988年开发MES的Reidenbach和Robin以及Beekun、Westerman和Bargh(2005)[9]等。他们认为个体的伦理观念可以分为五种类型:(1)利己主义。它属于目的论,认为只有给自我带来最大长远利益的行为才是合乎道德的。(2)功利主义。同样属于目的论,与利己主义不同之处在于它强调行为必须给所有的受众都带来最大的利益。(3)义务论。它重视行为是否遵守一定的规范以及行为动机的善良与否。(4)公平。它起源于卢尔斯的正义论,强调合乎伦理的行为应当尊重行为受众的应有权利。(5)相对主义。它认为没有必要存在一个普遍的伦理法则,每个人都可以对行为是否合乎伦理做出自己的判断。
(三)伦理观的测量
1.EPQ
Schlenker和Forsyth于1977年开发出测量个体伦理观的工具,后来Forsyth对其作进一步修订,开发出了EPQ(ethical position questionnaire)。EPQ分为两个子量表,子量表中的每个测项都以陈述语句的形式出现。其中一个子量表度量相对主义水平,包含十个测项。例如,“撒谎是否合乎道德取决于当时的情境”、“不存在对所有人都合乎道德的方案,道德标准因人而异”。另外一个子量表度量理想主义水平,也包含十个测项。例如,“绝不能给他人带来生理和心理上的伤害”、“如果行为可能伤害无辜的人,那么就不应该实施”。测量时要求被试回答自己对上述陈述的同意程度,回答采用李克特九点计分法,1分表示完全不同意,9分表示完全同意。
EPQ在心理学和商业研究领域中均得到了广泛的应用。1992年之前,除了Forsyth等人的研究,绝大多数关于伦理观的研究都是在非商业领域展开的,学者们使用EPQ研究个体伦理观与个体的其他态度变量以及行为之间的内在关系,比如持有不同伦理观的个体对性的态度(Singh等,1989)、对右翼政治倾向的态度(McHoskey,1996)、对使用动物做实验(如Galvin等,1992;Wuensch等,1998)以及心理研究实验的态度(如Schlenker等,1977;Forsyth和Pope,1984);持有不同伦理观的个体对模糊性的忍受程度(Yurtsever,2000)、自我调控能力的高低(Rim,1982)、对一些社会行为的评价(Bowes-Sperry和Powell,1999)以及是否受马基亚维利主义人格特征的影响(Leary等,1986);伦理观与错误行为(Forsyth,1981)、创新行为(Yurtsever,1998)的关系等。1992年伦理观研究发生了巨大的转折。Forsyth认为,个体的伦理观可能影响其在商业活动中的伦理判断、决策和具体的商业实践,因此他号召学者们对个体的伦理观及其商业活动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10]由于 Forsyth研究的影响,西方学者们开始将视角转向商业领域,深入探讨伦理观在个体商业态度与行为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功能。他们应用EPQ进行实证研究,从而产生了大量的实证结果。
三十多年来,学者们普遍认为 EPQ具有良好的信度(理想主义子量表信度保持在0.70~0.92之间,而相对主义子量表信度保持在0.66~0.87之间)和效度,因此EPQ受到极大的推崇。大约有29个国家的一百多位学者采用过该量表,被试人数达三万多。[3]一些学者开发出了不少测度个体伦理态度的工具,这些测量工具也从侧面证实了EPQ的结构效度。首先是Hogan于1970年设计开发的个体伦理态度调查问卷(survey of ethical attitudes,SEA)。个体在SEA上面的得分与其在EPQ上面的得分是负相关的(p=-0.31),SEA得分较低的个体偏好相对主义的伦理立场(Forsyth,1980)。其次是同年Christie和Geis构建的马基亚维利主义问卷(Mach V)也证明了EPQ的结构效度。高马基亚维利主义的个体跟理想主义是负相关的(r=-0.48),与相对主义正相关(r=0.20)。因为在某种情况下高马基亚维利主义者会拒绝普遍的伦理规范,并且他们认为欺骗、撒谎等行为都是不可避免的(Leary等, 1986)。最后是 Gilligan的关怀伦理测量问卷(care ethics survey)。关怀伦理与理想主义正相关,与相对主义负相关(r=-0.13),这从一定程度上证明了EPQ的结构效度,因为关怀伦理强调个体对他人福利的促进作用或者避免伤害他人(Forsyth等,1988)。
2.MES
Reidenbach和Robin于1988年开发出MES(multidimensional ethics scales),该量表包含个体的五种伦理信念,即利己主义、功利主义、义务论、公平以及相对论。MES度量个体面对伦理问题时的伦理哲学选择行为,包含30个测项,其中利己主义维度七个测项、功利主义维度十个测项、义务论维度六个测项、公平维度两个测项、相对论维度五个测项。每个测项均给出两个极端选择,分别代表个体态度的正反两个方向,两级间设置了从1到7的等距分值,被试根据自己的态度选择相应的数值。笔者认为,利己主义、功利主义、义务论、公平以及相对论都是个体处理商业伦理问题时可能采用的伦理标准,因此,实际上MES测度的并非是商业决策者的伦理判断过程,而是其在进行伦理判断时所依据的标准。
3.SETA与MEV
Brady于1990年开发出包含功利主义与形式主义两个维度的问卷——SETA(survey of ethical theoretic aptitudes),该量表包含15个测项,例如“评价人的行为应该依据好/坏还是正/误”、“个体做决策的时候应该关注的是自己的良心还是他人的需要与愿望”。SETA设计的测项只有两个选项。1996年,Brady和Wheeler在 SETA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研究,开发出 MEV(measure of ethical viewpoints),该量表包括20个测项。该量表旨在揭示个体采取的是功利主义还是形式主义的伦理立场以及其所秉持的立场的强度。MEV采取两种方式测试,一种是设计七个伦理决策情境,对于每一个情境向被试提出四个问题,其中两个问题与功利主义倾向相关,另外两个问题涉及相对主义倾向。第二种是一项纸笔测试,列出13个品质特征,被试根据这些品质对自身的重要性给出一个分值,采取李克特七点计分法,1分表示“对我不重要”,7分表示“对我非常重要”。
4.MEO
Froelich和Kottke于1991年开发的量表——MEO(measure of ethical orientation),用来描述个体感知到的内心冲突,即当个体为了维护组织利益需要做出伦理可疑行为,而这样的行为并不能遵循社会公认的伦理标准。他们俩设计出十个测项来考察被试的态度,其中包括被试感知到自身价值观与公司价值观的冲突、公司给员工造成的必须牺牲自我价值观的压力、员工感受到的上司与同事的伦理可疑行为以及整个公司的伦理氛围等。代表性的测项有“上司命令下属伪造一份文件的行为没有错”、“员工可能为了维护公司声誉需要向顾客撒谎”,测试时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法。不少学者(如Dolecheck等,1987;Preble等, 1988;Hunt等,1989;Froelich等,1991;Smith等,2007)采用MEO来测度个体的伦理观。
5.正直量表(integrity)
Schlenker及其合作者在2008年进行的研究中也使用了“ethical ideology”这个表述,但是与Forsyth不同,Schlenker等人将个体伦理观区分为原则性强的伦理思想和权宜之计的伦理思想两种。[11]他们开发出一张用以测度个体品质的量表——正直量表,该量表包括18个测项,例如“品质高尚的个体愿意坚持自己的原则,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如果个体相信某些东西是正确的,那么他也应该坚持这些原则,即使他可能会因此而失去朋友,或丧失一些获利的机会”、“如果行为是出于正当的原因,那么撒谎或者欺骗都没有关系”。该量表采用李克特七点计分法,被试根据自己的观点表明对每个测项的态度,1分表示强烈不同意,7分表示强烈同意。随后,McFerran、Aquino和Duffy(2010)也使用了该量表考察了个体的人格特征、道德认同感与个体伦理观之间的关系。该量表的开发者们认为他们测度的是个体的伦理观,而在笔者看来,事实上他们所测度的并非个体所信仰的具体的伦理哲学本身,而是个体在生活与工作中对自己所信奉的伦理哲学的坚持程度的高低,特别是当个体遭遇一些伦理决策的两难困境时,个体可能会迫于利益或者压力放弃自己的伦理标准。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该量表的使用频率并不高。
三、伦理观的前因变量和影响效果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许多学者在Forsyth的研究基础上对伦理观进行了广泛的探索,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学者们在考察伦理观与其他相关变量的关系时,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人格特质、组织价值观、相关的态度与行为变量四大方面。其中,态度变量包括个体对商业伦理、职业伦理以及消费伦理的信念、组织承诺与职业承诺等,而行为变量主要涉及个体对商业伦理问题的感知、判断以及行为选择。下面我们将从这四个方面展开具体阐述。
1.人格特质对伦理观的影响
首先,个体的人格特征类型影响伦理观。如果个体感知世界依靠直觉,决策依靠情感,那么他很可能是情境主义者,而若个体决策依赖思考,那么他很可能是绝对主义者。但是对于那些认识世界仰仗感觉的个体,不管其决策过程依赖情感还是依赖思考,他们很可能是情境主义者。[12]高马基亚维利主义者会采取相对主义的伦理立场来处理伦理问题(Wakefield,2008);具有创造性的个体基本上属于情景主义者(Bierly等,2009)。其次,不同的人格倾向可以有效预知个体伦理观的差异。Kenhove、Vermeir和Verniers(2001)基于比利时市场的研究发现,消费者的封闭性倾向越高,其理想主义维度得分也就越高。McFerran等(2010)也认为,员工在责任心、宜人性与开放性等方面的分值越高,其相对主义水平就越低。此外,有学者研究得出,公司高管的精神健康状况越良好,其理想主义水平也就越高(Fernando等,2010)。
2.组织价值观对伦理观的影响
科尔伯格认为大多数成年人的道德认知发展水平都处于约定性阶段,个体所处的群体发挥着较大的影响。商业组织关于伦理道德的观念是组织成员所共享的。如果公司奖励道德行为而惩罚不道德行为则会强化员工对其自身行为正面结果的关注,从而有助于提升理想主义水平,但是却负向影响相对主义水平。Karande等(2002)针对美国、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千名营销人员的实证调查证实了这一观点,但也有学者只发现公司价值观对理想主义水平(Douglas等,2001)和相对主义水平(Fernando等, 2008)的单边作用。
3.伦理观对个体其他态度变量的作用
首先,借助个体伦理观可以显著预测个体的消费伦理观念。一般来说,如果消费者的理想主义水平较高,那么他们会认定各种问题消费行为都是错误的。[13]研究发现,黑人大学生(Swaidan、Rawwas和Al-Khatib,2004)和老年消费者(Ramsey等,2007)比较符合此类情形。而相对主义水平比较高的消费者就比较容易接受有问题的消费行为,Bonsu和Zwick(2007)针对加纳消费者的研究以及Lu等(2009)针对印尼消费者的研究均支持了此观点。就影响效果而言,对于同一个消费者来说,其理想主义水平对其消费伦理观念的影响最为强烈,而相对主义水平对消费伦理观念的作用很微弱甚至几乎没有影响。[14]
其次,伦理观与个体对企业伦理和社会责任的领悟力密切相关。总体而言,个体的理想主义水平越高,个体就越发感觉企业伦理、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经营成功的重要性。[15]类似结论在美国经理(Vitell和 Hidalgo,2006)、泰国 MBA(Singhapakdi等,2008)与西班牙经理(Vitell、Hidalgo和 Nishihara, 2010)身上都成立。而相对主义水平越高,个体就越会轻视企业伦理对企业经营成功的价值,其社会责任感比较低(Kolodinsky等,2010),而且会倾向认同各种不正当行为,如商业贿赂(Tian,2008)。
再次,通过伦理观还可以预知个体的职业伦理信念、组织承诺与职业承诺。Shaub、Finn和Munter (1993)以美国207名审计员为调查样本,分析发现,伦理倾向影响个体的组织承诺和职业承诺:相对主义水平高的审计员具有较低的组织承诺和职业承诺程度,而理想主义水平高的审计员的职业承诺程度最高。Kim和Choi(2003)针对韩国公共关系从业人员的研究发现,绝对主义者最信奉自己的职业伦理,主观主义者对自身职业伦理的承诺则比较低。
最后,伦理观还影响个体其他方面的态度。McHoskey(1996)发现,大学生的政治倾向与相对主义维度负相关,而其社会支配倾向与理想主义维度负相关(Wilson,2003)。Lee和Sirgy(1999)研究发现,美、韩两国的国际营销人员的理想主义水平正向影响其生活品质的定位。另外,学者还发现伦理观对个体看待实验使用动物的态度(Galvin等,1992)、员工对工作场所安装监控设备的态度(Alder等,2008)等都具有显著的影响。
4.伦理观对个体伦理决策行为的作用
Rest认为伦理决策行为包括四大阶段,即伦理意识、伦理判断、伦理意图和伦理行为。在整个伦理决策过程中,个体的伦理观都会发生直接或者间接的作用。
首先,伦理观影响个体的伦理意识。整体来看,个体的理想主义水平高,其会比较关注自身行为的潜在结果,如果行为会引致较大的伤害则可能引起个体的伦理敏感度上升。实证研究表明,美国营销人员、注册会计师(Yetmar和Eastman,2000)、专卖店员工(Dubinsky、Nataraajan和 Huang,2004)以及普通员工[6]的理想主义水平高,他们比较关注行为的潜在结果,避免伤害他人,正好证实了上述观点。而如果个体的相对主义水平高,则他会拒绝普遍伦理规范的约束,这样由于缺少社会一致性的判断而无法裁定行为是否合乎伦理,因此此类个体较少关注伦理问题。调查显示,美国商科学生(Cho、Yoo和Johnson,2005)与泰国MBA学生(Singhapakdi、Gopinath、Marta和Carter,2008)比较符合此类情形。
其次,伦理观影响个体的伦理判断。伦理观代表了个体不同的伦理标准。有学者认为伦理观直接影响伦理判断,Boyle(2000)针对美国的营销人员、Kim和Choi(2003)针对韩国公共关系从业人员、Hartikainen和Torstila(2004)针对芬兰财务人员以及Chiu和Erdener(2003)针对中国香港、上海两地的管理人员的实证研究都验证了此观点。其中,绝对主义者的伦理判断最为严厉,而情景主义者和主观主义者的伦理判断相对要宽容得多。另外,也有学者认为伦理观并不直接作用于个体的伦理判断,只有当个体面临高道德水平的伦理问题的时候,他的伦理观才会影响他的伦理判断。[16]
再者,伦理观影响个体的伦理意图。比较多的研究认为伦理观直接作用于个体的伦理意图。一般而言,相对主义维度与个体的不道德行为正相关,而理想主义维度与之负相关。无论是使用动物做实验的行为、制造预算松弛的行为、作弊行为、越轨行为、盈余管理中的机会主义行为还是问题营销行为,上述结论都成立。甚至在一般消费者那里上述结论也成立。Nebenzahl、Jaffe和 Kavak(2001)针对土耳其和以色列两国消费者的调查显示,如果理想主义者感觉到公司是不道德的,那么他们会较少购买该公司的产品。[17]
最后,伦理观影响个体的伦理行为。一般来说,理想主义者总是关注行为的积极结果,个体的理想主义水平越高,他越关心他人福利,因而不容易实施不道德行为。而个体的相对主义水平越高,其行为没有普遍伦理规范的约束容易导致一些问题行为的产生。这种影响在商业人士的谈判行为(Banas等, 2002)、对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和隐私权的接受程度(Winter等,2004)、社会负责性投资行为(Park, 2005)、有问题的会计行为(Emerson等,2007)以及项目管理的具体决策行为(Huang等,2009)等方面体现得更甚。
四、不同国家和人群的伦理观差异
不同国家和人群的个体之间是否存在伦理观差异?差异内容与程度如何?是什么原因导致彼此的差异?这些问题引起了学者们极大的研究兴趣。
1.不同国家和地区间伦理观的差异
首先,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商业伦理观存在差异。具体来说,学者们普遍认为信奉儒家伦理的地区在理想主义和相对主义两个维度的得分都比较高。以营销人员为例,调查表明,韩国营销人员的理想主义水平比美国营销人员高(Lee和Sirgy,1999);马来西亚的营销人员在理想主义和相对主义两个维度上的分值均高于澳大利亚的营销人员(Karande等,2002),也高于美国的营销人员(Axinn等,2004)。同时中东地区商业人士的理想主义水平高。埃及、约旦、沙特阿拉伯的营销人员理想主义水平比美国同行高(Attia等,1998);土耳其消费者的理想主义水平也高于美国消费者(Rawwas等,2005);土耳其旅游业从业人员的理想主义水平高于澳大利亚同行(Yaman等,2006)。
其次,同一文化背景但处于不同地区的个体的商业伦理观也存在差异。例如,虽同属于西方文化背景,但美国人决策并非依赖自我主义,俄罗斯人决策时也并非依赖功利主义[9];美国经理要比西班牙经理更注重商业伦理对企业经营成功的巨大作用(Vitell和 Hidalgo,2006)。在中国,广东经理人理想主义水平高于北京同行。[18]在中东地区,相比埃及人,黎巴嫩的消费者理想主义水平较低,而相对主义水平较高,因此更容易接受有问题的消费行为(Rawwas、Vitell和Al-Khatib,1994)。Nebenzahl、Jaffe和Kavak(2001)的调查显示,土耳其消费者的理想主义水平比以色列消费者高。
2.基于不同人口学特征的伦理观差异
首先,不同年龄段的伦理观差异。一部分学者认为老年人身上体现了多种伦理信念。总体而言,老年人比年轻人更加倾向于理想主义而较少关注相对主义,他们对营销行为的评判更加严格(Kim和Choi,2003;Ramsey、Marshall、Johnston和Deeter-Schmelz,2007;Fernando、Dharmage和Almeida, 2008;Marques和Azevedo-Pereira,2009)。在这些学者看来,老年人似乎更愿意遵守法律等规章的约束,加上老年人阅历丰富,因而他们在处理伦理问题时表现得更加审慎和成熟。但是另外一部分学者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Brady和Wheeler(1996)研究发现,员工年龄越大,功利主义(目的论)维度得分越低,而形式主义(义务论)维度得分越高。Karande、Rao和Singhapakdi(2002)比较了美国、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营销人员的伦理观后发现,随着年龄增长,相对主义水平也会随之增加。
其次,不同性别的伦理观差异。一些学者研究发现性别显著影响个体对可疑消费行为的伦理判断。相比男性,女性的理想主义水平高,因而会更多感知到有问题的消费行为(如 Karande、Rao和Singhapakdi,2002;Marques和Azevedo-Pereira,2009)。Lam和Shi(2008)研究发现,在全职员工中,女性做出的行为似乎显得更加符合伦理。[7]这些结论都进一步验证了Gilligan的关怀伦理说。
最后,不同宗教信仰的伦理观差异。不少学者认为凭借宗教信仰可以很好地预测个体的伦理观。Chen和Liu(2008)对台湾研究生与本科生的调查显示,个体的宗教信仰与相对主义水平显著负相关,并且随着信仰类型的不同影响效果也迥异,信仰基督教往往与高道德水平显著相关(Lam和Shi,2008)。Fernando、Dharmage和Almeida(2008)针对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股票经纪人的调查显示,宗教信仰与其相对主义水平显著相关,信奉基督教的股票经纪人要比其他人表现出较高水平的理想主义倾向。
五、未来研究展望
三十多年来西方学者持续关注个体的伦理观对其商业态度以及行为的影响。国外学者的研究结果为我国企业的管理实践和商业伦理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启示与借鉴意义。但是,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迁都对个体伦理观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与主题。今后我们可从以下六个方面来不断更新和完善相关研究。
第一,持续关注伦理观的测量工具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稳定性和可靠性。首先应特别关注量表的跨文化适用性。现有的测量工具大多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开发出来的。毋庸置疑,东、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存在差异,学者们在进行本土化探索的时候应该对现有量表进行必要的修订,使之适应于各国独特的文化情境。以EPQ为例,Cui、Mitchell、Schlegelmilch和Cornwell(2005)在英、美、澳、文莱以及中国香港五个地区的调查也显示,EPQ必须经过修订才可以在非西方文化情景中运用。[19]鉴于不同文化背景下伦理标准存在差异,Forsyth也警告说,在跨文化情境下使用 EPQ必须谨慎。[3]笔者认为,在我国,千年儒家文化传统造就商业个体独特的伦理观,我国管理者的价值观内涵、结构与西方同行存在明显差异。因此,修订伦理观的测量工具显得尤为必要。其次,已有测量工具的信度和效度得不到充分保证。一些量表仅仅是设计几个情境,每个情境后面附上1到2个问题;还有的虽然使用较为成熟的量表,但是随意删除测项。因此,未来研究应该关注伦理观测量工具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第二,伦理观的变化机制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组织层面和社会层面的伦理观和个体层面的伦理观是一成不变的还是不断变化的?如果是变化的,那么是由哪些因素引起的?其中的变化机制又是怎样?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的探讨。组织伦理观与个体伦理观之间的作用机制又是怎样?这又值得学者们作进一步的探索。此外,根据Woodbine(2004)在中国深圳的调查显示,我国传统的价值观与儒家工作伦理并没有如预期那样显著影响员工的态度和行为选择。[20]产生这样结果的原因何在,这是由于我国快速的工业化进程中传统价值观对个体影响作用的消退还是由于转型社会中传统价值观借助其他中介机制作用于个体态度和行为呢?这些问题还等待着解答。所以,未来研究应该采取一种动态的视角来探析伦理观。
第三,未来研究应该深化对不同商业人群伦理行为的理解。在众多探索伦理观的文献中存在四大倾向:首先,学者大多关注商业人员的伦理意图,即他打算如何行动,而不是实际的行为选择。未来研究应该加深对伦理观与真实商业伦理行为之间的关系的理解。其次,现有的理论模型缺乏伦理观与个体伦理决策行为之间的中间变量。大多数研究都是直接探讨伦理观的作用。笔者认为,在企业组织中,个体的行为并不必然受价值观等信念的支配,管理人员的伦理决策行为除了受自己的伦理信念系统的影响之外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制约。这些因素可能是决策者个体的人格因素,也可能是组织层面的其他中间因素,还可能是当时当下所要解决的问题所处的情境本身。未来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在研究模型中引入其他中介或调节变量以提高解释效果。再者,现有研究比较关注营销人员、会计与审计人员等人群。在当今商业环境下,几乎每一个商业领域都会遭遇伦理冲突的困境。未来研究可以关注其他领域的行为,比如人力资源管理。最后,现有研究大多选择商科学生作为调查对象,未来研究应直接调查商业从业人员的伦理决策行为,还可以调查企业员工的伦理行为或对学生与商业从业人员进行比较分析。
第四,未来研究还应该重视伦理观的匹配。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学者们只关注个体与组织之间的价值观匹配,但是对伦理观的匹配鲜有涉及。研究个体与组织在伦理观上的匹配有助于理解个体工作搜寻和工作定位,可以预测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和离职倾向;考察员工之间伦理观的匹配能加深我们对工作关系、员工行为和员工绩效的理解。在动态的竞争环境下,个体与企业在伦理观上的协同能大大降低个体面对价值冲突的风险,降低决策难度同时也避免给组织造成经济和名誉损失。未来值得国内学者探索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有效测量个体与组织伦理观的匹配并探索实践中达到匹配的路径。
第五,国内学者应该深化不同文化背景下伦理观的对比研究。首先,不同国家文化背景下的员工对于什么行为是合乎道德的有着自己的观念和标准体系,企业如果不能深刻理解,就会陷入决策的伦理困境。其次,员工多元化带来伦理观的碰撞。系统探究不同文化背景下个体伦理观的异同将有助于我国企业选拔外派员工,制定人力资源管理策略,应对决策伦理风险,从而保障海外经营成功。
第六,如何干预商业个体的伦理观值得探索。按照科尔伯格的理论,大多数成年人处于约定性阶段,即他们承认对社会的义务,服从合法的权威,个体的伦理判断受到家人、朋友、同事的影响,同时也受到社会的法律、规章制度等的约束。今后国内学者可以探究我国企业可以通过哪些管理途径来影响员工的伦理倾向以及实施效果。
[1]吴红梅,刘洪.西方伦理决策研究述评[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6,28(12):48-55.
[2]O’Fallon,M J,and Butterfield,K D.A review of the empirical ethical decision-making literature:1996-2003[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05,59(4):375-413.
[3]Forsyth,D R,O’Boyle,E H,and McDaniel,M A.East meets West:A meta-analytic investigation of cultural variations in idealism and relativism[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08,83(4):813-833.
[4]黄希庭等.当代中国青年价值观与教育[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
[5]Forsyth,D R.A taxonomy of ethical ideologies[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80,29(1):175-184.
[6]Alder,G S,Schminke,M,and Noel,T W.The impact of individual ethics on reactions to potentially invasive HR practices[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07,75(2):201-214.
[7]Lam,Kit-Chun,and Shi,Guicheng.Factors affecting ethical attitudes in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08,77(3):463-479.
[8]McFerran,B,Aquino,K,and Duffy,M.How personality and moral identity relate to individuals’ethical ideology[J].Business Ethics Quarterly,2010,20(1):35-56.
[9]Beekun,R I,Westerman,J,and Bargh,J.Utility of ethical frameworks in determining behavioral intention:A comparison of the U.S.and Russia[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05,61(3):235-247.
[10]Forsyth,D R.Judging the morality of business practices:The influence of personal moral philosophies[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1992,11(5/6):461-470.
[11]Schlenker,B R.Integrity and character:Implications of principled and expedient ethical ideologies[J].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2008,27(10):1 078-1 125.
[12]Allmon,D E,Page,D,and Roberts,R.Determinants of perceptions of cheating:Ethical orientation,personality and demographics[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00,23(4):411-422.
[13]Vitell,S J,and Paolillo,J G P.Consumer ethics:The role of religiosity[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03,46(2):151-162.
[14]Steenhaut,S,and Kenhove,P V.The mediating role of anticipated guilt in consumers’ethical decision-making[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06,69(3):269-288.
[15]Vitell,S J,Bakir,A,Paolillo,J G P,Hidalgo,E R,Al-Khatib,J,and Rawwas,M Y A.Ethical judgments and intentions: A multinational study of marketing professionals[J].Business Ethics:A European Review,2003,12(1):151-171.
[16]Douglas,P C,Davidson,R A,and Schwartz,B N.The effect of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ethical orientation on accountants’ethical judgments[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01,34(2):101-121.
[17]Nebenzahl,I D,Jaffe,E D,and Kavak,B.Consumers’punishment and rewarding process via purchasing behavior[J].Teaching Business Ethics,2001,5(3):283-305.
[18]Redfern,K,and Crawford,J.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ethics position questionnair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04,50(3):199-210.
[19]Cui,C,Mitchell,V,Schlegelmilch,B,and Cornwell,B.Measuring consumers’ethical position in Austria,Britain,Brunei, Hong Kong,and USA[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05,62(1):57-71.
[20]Woodbine,G F.Moral choice and the declining 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value orientations within the financial sector of a rapidly developing reg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04,55(1):43-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