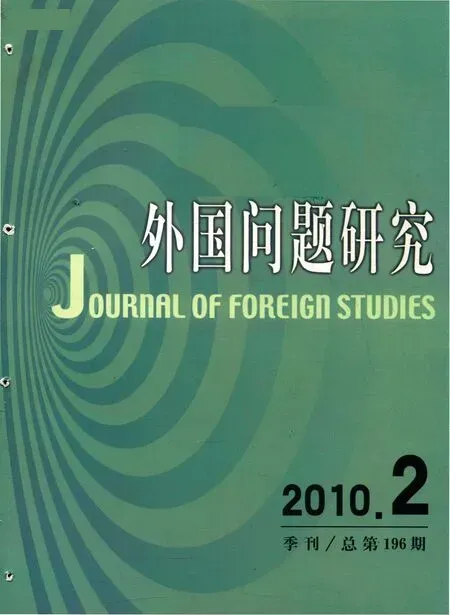朝鲜诗人李尚迪与道咸文人的交游
李春姬
(长春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吉林长春130022)
朝鲜朝正祖(1776-1800)以降,经朴趾源等北学派文人的不断推介,朝鲜文人了解了清朝文化及文坛动向,使他们清楚地认识到清朝学术继承中华文明和传统的事实,改变了以往敌视清朝的“华夷观”。政界和文坛要人金正喜、赵寅永、申纬等注重“燕行”,积极接受清代学术和思想,使朝鲜文人与清京城文人之间逐步形成了“同传中华文化,四海皆兄弟”的同流意识,为促进两国文人深层次的文化交流提供了良好的人文环境。在朝鲜,文人随同使团赴京“燕行”成为了一种时尚,又一次掀起了北学中国文化的热潮,两国文人之间交流的广度和深度达到了空前的水准。此时,与清朝文人进行频繁交流的朝鲜文人多数为才华横溢的“译官中人”①朝鲜时期的“中人”乃“非两班非常人,居于中间”的社会阶层,从事医、译、算、律等技术活动的人。朝鲜国制规定他们“进不得为士夫,退不得为常贱”。(参见[韩国]《正祖实录》卷33,正祖15年11曰壬午条;卷51,正祖23年5月壬戍条)但由于朝鲜国策之需,医、译中人受到朝廷的重视。如《正祖实录》卷41正祖18年10月丁卯条曰:“国俗专尚阶分,尤重于仕路。而士族以外医译次,士族然后为卿大夫,非士族而为卿大夫之资格,腰犀而顶玉者,医与译也。”。译官中人以其语言优势、对新事物的敏感和接受能力,引领了19世纪朝鲜和清朝两国文人之间的交流。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便是道咸年间频繁出使清朝,并在清文人中树立较高文学形象的译官中人李尚迪。
一、李尚迪其人
李尚迪(1803—1865)字惠吉、允进,号藕船,海邻居士,祖籍牛峰(现韩国京畿道江阴)。据《牛峰李氏族谱》记载,牛峰始祖为公靖,至公靖七代孙英年分派,英年历官兵曹参判、户曹员外郎,李尚迪从系英年。牛峰李氏为世袭译官家族,历代译科及第者达三十余人。牛峰家族成员不仅精通汉语,而且通晓中国经典,有较高的文学修养,祖祖辈辈任职于司译院教诲厅,为朝廷培养翻译官。李尚迪生父廷稷及从叔廷柱均工于诗,为当时著名的中人诗社——松石园诗社的主要成员,并以“寝胙百家,晨唱夕和,名篇杰句,往往脍炙于世”[1]1。李尚迪少承家学,私塾郑民秀、朴善性、金正喜等文人学经史诗文以及书画,于1823年应译科试中榜首,并以善诗书而扬名文坛。三年后进春塘台讲筵受到国王“引见之命”,特蒙“前席承聆玉音朗然吟诵臣旧作”之优渥,(《恩诵堂集自序》)后曾多次受国王赐田沓、奴婢等殊恩。至1847年连升5次品阶,授知中枢府事职,并参加秘书省校刊正祖、纯祖、宪宗三朝《国朝宝鉴》。
李尚迪于1829年第一次以朝廷使团随行翻译官身份访问了清都燕京,之后频繁“燕行”,共达12次,结交百余名清朝文人。李尚迪与他们一同亲历了中英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火烧圆明园等重大的历史事件,创作大量诗歌表达了一个读书人对剧变的时代及其社会的人文关怀,抒发了动荡年代文人的情怀。李尚迪生前在京城琉璃厂出版了诗文集《恩诵堂集》24卷,并以其诗才和人格博得了清朝文人的赞誉,为“海内巨卿通儒竞相推诩”[2]4。朝鲜后期代表性诗选集《朝野诗选》、《大东诗选》、《古今詠物近体诗》均载其诗数篇,晚清文人符葆森辑《国朝正雅集》卷九十九选录当代朝鲜诗,其中收录尚迪诗共有七首,居朝鲜诗人之首。
李尚迪是中人,有别于士大夫阶层。在朝鲜“国俗专尚门阀,名分截然”,中人“无以为用”。因此,“学而优则仕”、“修身、齐家、平天下”的理想到了中人那里,因“国俗”而变成了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但他凭借“译科榜首”的才能,利用代表朝廷赴清的“燕行”机遇,在燕京文坛开辟了新的文学活动平台,走出了海外发展的路线。可以说,李尚迪的文学活动及其文学成就与清道咸文坛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蕴藏着他的心路历程的文集《恩诵堂集》中,有七百余篇诗文与清文人相关。另外,从李尚迪与清文人的日常交往和情感传递的三百多封信函内容中,也不难发现他为“留得香名海外知”而辛勤耕耘、苦心经营的行迹、心迹。他用一生的追求和努力,克服了常人难以忍受的辛劳,不断地与清文人进行了沟通和交流,拓展了自己文学活动的空间,深受京城文人的尊重和赞誉。正如朝鲜后期著名文人崔性学所云:李尚迪“以文章远播海内”,而“鸡林声价重幽燕”[2]5。也就是说,清道咸文坛成就了朝鲜诗人李尚迪。
纵观李尚迪的文学生涯,因其“频年奉使北学於中国”而独具特色。他在朝鲜文坛是“一麟角瑞世”而卓然为“近世诗文名家”[2]6,以“文采风流,令人心醉”的“海东诗人”而扬名清道咸文坛[2]8。李尚迪及其文学成就对19世纪中朝两国文学交流及其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了解李尚迪的文学生涯,将有助于我们提高对李尚迪乃至朝鲜社会特殊阶层—中人文学的认识,也可以从李尚迪与道咸文人的文学交流活动中深入了解19世纪中朝文学交流的真实、生动的一面,进而深入理解内外矛盾极其尖锐的东亚语境之下两国文坛间互动及其内涵。
二、生性慕中华
朴趾源《热河日记》云:“东方慕华即其天性也”。仰慕中原文化是朝鲜文人之传统,由来尚矣。这一点取决于他们的知识结构。朝鲜半岛自从引进汉字以来,文人士大夫从小学习汉字,研习汉文典籍、文献,从而成为了中华文明的接受者和传承者。中国历代文献中出现的神仙、圣哲、贤人以及他们思想、行迹、操守、语录均成为了朝鲜文人追踪、标榜的对象。经历千余年的潜移默化、传承和发挥,中华文明已成为了朝鲜文人的全部知识内容。朝鲜半岛识字阶层无人不知孔子,无人不晓杜甫。仰慕中华,向往中原,卧游江南等已成为了朝鲜文人的追求和理想,也是他们笔下最为常见的表述内容。“壬辰倭乱”期间,当时著名文人许筠见到明朝派遣的援兵,便迫不及待地笔谈江南文化,验证自己想象中的江南和实际江南的距离。当满清入关后,朝鲜文人认为他们一直仰慕的“中华”文明随明朝的灭亡而不复存在。1644年作为人质扣留在沈阳的昭显世子闻知清兵攻入福建的消息,便慨叹道:“中华之礼乐文物将复入腥膻矣”[3]68。(《沈阳日记钞》)虽然朝鲜屈于武力转而事大于清,但鄙视不识礼仪的“蛮夷”,以“小中华”自居。当时,一些朝鲜文人随朝贡使节到清,沿途记录了许多所见所闻,并将此记录称为“燕行录”,一改过去冠名“朝天录”的心态。对清的这种“华夷观”便是朝鲜文人所表露的秉承中华文明的姿态。然而,经过北学派文人的不懈努力,朝鲜文人逐渐了解和认清了清朝先进的学术和文化,重新激发了他们固有的“慕中华”情结,纷纷赴京结交清朝文人,与清朝文人交流学问,切磋文艺。经过与清文人的交流,朝鲜文人再次认同了中华文明。李尚迪也不例外,他在《子梅自青州寄诗,索春明六客图》诗云:“貌余三韩客,生性慕中华。”
李尚迪文集的开卷诗为其21岁时作《读书》,诗云:“朝暾丽轩窗,正坐读经史。小少有微尚,窃慕古贤士。春秋二百年,季扎一人已”。李尚迪从小读中华经典,窃慕中国的古贤士“季扎”。事实上,开启读书人交友准则的古代吴国“季扎”行迹影响了李尚迪的交游观。他在用自己的半生与清朝文人交游过程中,始终以吴季扎为楷模,“遍交海内贤人君子。上自名公钜卿,下至武夫侠客方技隐士”,始终坚持“以道义相规,勗以性情,相契切磋文字,商榷艺术,莫不欢若平生,失以金石”[4]63。可见,李尚迪不仅遵循了中国传统文人的“友道”,也实现了朝鲜文人“慕中华”的夙愿。
三、李尚迪与道咸文人
李尚迪的交游关系呈现以“燕行”为媒介,身临京城文坛而展开的特点。且为朝廷使节团译官这一特殊身份,他所结交的国内(朝鲜)文人大多数是士大夫官僚文人,如金正喜、申伟、沈象奎、申在植、赵秉铉等。这成为了作为中人阶层的李尚迪日后多次“奉使”赴京的人脉资本,也构成了他和清朝文人结交的交友链。李尚迪与清文人的交游具有繁多而多重的特点。根据其诗歌《怀人诗》、《续怀人诗》、《西笑编》中提到的人物及其相关内容,李尚迪与清文人的交游大致可分前、中、后三个时期。
前期(1829-1837年间,燕行4次),“交游多老宿,菁莪际乾嘉”。年轻的李尚迪初来京成便结交了乾嘉汉学名流,如吴崇梁、仪克中、刘喜海、汪喜孙、黄爵滋、陈庆镛、阮常生、丁泰等。这些人均年长于李尚迪,而且与乾嘉领袖翁方纲、阮元有着或学缘,或弟子的关系。李尚迪与这些人的交往很受其师金正喜的交游关系之裨益。金正喜于嘉庆14年来到京师与翁、阮建立了翰墨之缘,师徒之谊。金正喜主导朝鲜的金石学,京师汉学家们又因金正喜而关注朝鲜金石学。于是,京师学者文人多是愿与其“师弟纳交”①道光朝士,多与阮堂(按:金正喜)师弟纳交。石州(按:张穆)尝以仪征(按:阮元)所著诗书古训及自著亭林年谱邮赠,诗中所云:“敬以老阮书,用慰阮堂情。”([清]张继文辑,《先伯石州公年谱》道光二十一年条,民国十年刊本,太原:平定普新石印馆)。李尚迪通过与这些当朝学者文人的交游,开阔了视野,获得了汉学及金石学知识。尤其在与这些学者文人进行“笔战”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了其文藻,获得了他们的认可。金石学家刘喜海于道光十年完成其力著《海东金石苑》,特请“海东诗人”李尚迪作了题词,颜其卷首。
中期(1838-1847年间,期间燕行4次),李尚迪结交了“后起数君子,贤豪尽名家”。在初期交游的基础上,扩大了结交范围。此时结交的清文人多为乾嘉年间贤豪名家的后起之秀,如祁寯藻、何绍基、张穆、端木国瑚、王鸿、张曜孙、潘曾玮、潘祖荫、洪齮孙、蒋德馨、赵振祚等。他们与乾嘉年间名流齐韵史、蒋士铨、张慧言、洪亮吉、刘奉禄等有着或血缘,或学缘,或地缘关系。这些文人中有经学派文人、常州学派文人、边疆史地学派文人。当时正值鸦片战争,他们反对脱离现实的汉学,主张面对现实,力求新变,积极开展国防之学术、团练等救国学术和运动。李尚迪与他们频繁接触,共同探讨摆脱危机之良策。在这过程中,李尚迪深深体会到了清文人具有的救国理念、学术主张和文学倾向,并将张慧言著《笺易注元室遗稿》、桂馥著《晚学集》、恽敬著《大云山房集》、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集》等书籍及时传播到朝鲜文坛,为同样面临着“洋扰”及西学洗礼危机的朝鲜文坛提供了理论依据。他还将《词选》、《复堂词话》、《同声集》等代表常州词派的书籍和词学理论推介到朝鲜文坛,对发展朝鲜词学理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期间,李尚迪的“岁寒松柏”之节操在清友人间博得赞誉,又以与张曜孙、王鸿等地方文人坚持卅年如一日的“水鱼之交”、“知己之交”,在中朝文学交流史上留下了佳话。此间,在京城琉璃厂出版的李尚迪文集《恩诵堂集》,通过知交“流传至江南、冀北”。
后期(1848-1864年间,燕行4次),李尚迪结交“新知乐何如,如背痒得爬”。此时的“新知”有孔宪彝、叶名沣、朱琦、冯志沂、许宗蘅、王拯、王轩、董文涣等新进学者文人。这些人同属由当朝“皇师”祁寯藻及何绍基、张穆、孔宪彝等人连续主持的“顾祠修禊”文人群体[5]69。他们推崇顾炎武的经世致用之学,力求转变学风。这些“新知”对李尚迪早有所闻,或有“诗君画里廿年前”者,或有“诗卷久相识”者,或有“伊川巾,东坡笠,吾以想先生”者[2]5。他们对深谙清朝世情,而“清谈仍剧饮,高詠复群贤”的“藕船老人”深表仰慕,纷纷“词赋风流老作家,知交许订忘年交”[6]。他们相互以“自古读书人,惟思报国恩”互勉[7]356,强调共同维护和传承“同道意识”。这种“同道意识”使得李尚迪和“顾祠修禊”文人面对内忧外患时局,极力推崇清初提倡经世致用,讲求学以致用学风,形成砥砺志行的“士人”风气起到了推动作用。近代学者王国维将此学术风气称之为“道咸以降学之新”。学术风气的变化必然导致文学倾向的转向。道咸年间盛行的宗宋诗风,“顾祠修禊”文人祁寯藻、何绍基等“喜言宋诗”[8],强调“学问”和“性情”等,这些倾向不仅改变了李尚迪的文学观,也直接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
综上所述,朝鲜诗人李尚迪通过“燕行”结交了诸多清道咸年间文坛名流及其同人,与他们共同面对时代变迁,共同经历了文坛变化。他在与清文人进行交流的过程中,经不断思辨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多元化的诗学观念,提出了性情以学问为基础的学理指向,法古须为体现个性服务的诗歌取向,禅与妙悟而自得的诗歌境界等创作理论。李尚迪的诗歌创作体现了传统读书人身临多变世界而体验的感受和认知,形成了“上溯风雅之旨,下尊汉魏唐宋元明诸大家之体制,乃研其妙,融其情”的风格[2]4。由此,李尚迪在清道咸文坛树立了“诗品极佳”的“三韩名家之最”形象[9],转而在其国内卓然推为当时“宗匠”。
[1]李闰益.梦观斋遗稿序[A].闾巷文学丛书5[M].驪江出版社,1983.
[2]崔性学.藕船精华录序[A].金奭凖编.藕船精华录[C].首尔大学校图书馆藏,同治八年刻本。
[3]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 第27册[M].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
[4]兰言汇草(张曜孙条)[M].韩国学中央研究院藏书阁藏(手抄本).
[5]魏泉.“顾祠修禊”与“道咸以降之学新”[J].清史研究,2003(1):122.
[6]温忠善.制句奉题藕船先生大集[A].海邻书屋所藏中州诗[C].首尔大学校奎章阁藏.
[7]李尚迪.闻冯鲁川之任庐州即题其微尚斋集后[A].恩诵堂集续卷9[C].亚细亚出版社.1983:27.
[8]陈衍.石遗室诗话卷1[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9]醉香山楼选录.海邻尺牍(王拯条)[M].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