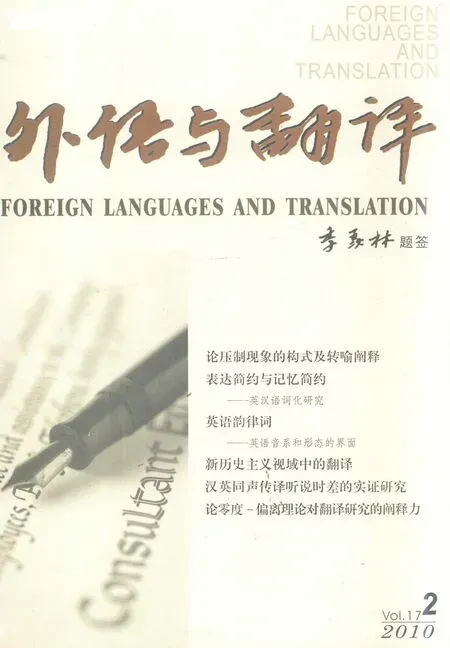从《观察》周刊看储安平的期刊编辑与经营理念*
袁新洁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新闻系,湖南湘潭 411201)
从《观察》周刊看储安平的期刊编辑与经营理念*
袁新洁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新闻系,湖南湘潭 411201)
1946年9月1日,储安平主编的《观察》周刊在上海创刊。从《观察》的刊行过程可以看到,储安平独特的报刊编辑与经营理念,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观察》的成功:一是坚守独立自主的理念,确保刊物的客观独立;二是坚持“高度”的要求,尽可能满足大多数读者的愿望;三是采取民间“股份制”的模式,避免官僚资本和政党势力的渗入;四是运用力争直接订户的策略,巩固基本发行量;五是奉行“负责、迅速、公平”的精神,重视建立与撰稿人及读者的良好关系等。
《观察》周刊;储安平;期刊经营理念
1946年9月1日,储安平主编的《观察》周刊正式在上海创刊[1]。由于《观察》的言论倾向和编辑风格顺应了当时的时政情境和读者需求,其一经创办,就倍受瞩目;一经出版,即风行各地。在短短的不足三年的刊行时间内,最高发行量就飙升至15万余份,赢得了全国范围内大批知识分子读者的青睐,成为全国一个很有影响的时政论坛。从《观察》的创办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储安平身上强烈的职业意识,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观察》的成功。本文拟就储安平的报刊编辑与经营理念,对《观察》的成功作简要的探析。
一、坚守独立自主的理念,确保刊物的客观独立
在政党报刊盛行的年代,一份报刊要想保持思想上的独立客观,首先必须在经济上独立自主。否则,将会沦为大财团或者政党的言论工具。储安平深谙此理,他在筹办《观察》之初,就十分重视吸收同人入股,不接受来自政党或者政治团体的筹款。这与他的新闻从业经历是分不开的。
储安平早年曾任国民党《中央日报》副刊编辑,后被聘为该报的总编辑。但不久便辞职,之后还主编过《文学时代》、《客观》等刊物。由于这些刊物不能在经济上做到独立,使他的自由主义抱负得不到施展。待到《观察》在国内影响力日益增大之时,一些国民党人士便想以投资的方式,控制该刊,遭到储安平的拒绝。后因内战不断升级,物价飞涨,《观察》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影响。其中纸张价格上升带来的影响尤为突出,从创刊到出第二卷,半年时间纸张即涨价8倍。到1948年8月,纸价涨得令人咋舌,半年内涨了16倍。除此之外,印刷、稿酬、杂工等费用也让储安平捉襟见肘。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有读者建议凭借此时《观察》的声望,接受读者的捐款,或者向读者募捐,以解燃眉之急。但储安平还是谢绝了这些读者的好意,在艰难的时局中坚持了下来。
正因为这样,储安平自豪地宣称:“本刊是一个纯粹民营的刊物,既无政治集团在后指使,亦无经济集团在后支持,平时用纸都是向市上纸商零购的。”[2]经济上的独立自主,确保了其言论的客观自由,这也使得《观察》周刊在读者心中的可信度日益增强。尽管战时国内生活水平不断下降,但《观察》的读者群体却逐步扩大。如1947年8月30日出版的《观察》第三卷第1期,发行量达到1.9万份,是创刊号初印数的3倍多;半年以后出版的第三卷24期,发行量增加到2.5万份,为创刊号初印数的5倍。此后印数一直跃升,第四卷增加到5万份,第五卷更是增加到10万多份。发行量的扩大、订户的增加,使《观察》在经营上的困难减轻,确保其在艰难的环境中保持了独立的本色。
二、坚持“高度”的要求,尽可能满足大多数读者的愿望
储安平认为,报刊要尽可能满足大多数读者的愿望,一是要注意提高“本刊质量”,二是要“尽量满足读者的要求”。在提高质量方面,他强调这是编者的责任,也是扩大销售量的直接有效的方法。在满足读者要求方面,他强调由于每个读者的具体要求不同,难以一一满足,但要尽可能做到满足大多数读者的愿望。如“读者投书”和“周末文摘”两个栏目,就是应多数读者的要求而设置的。
针对部分读者关于《观察》文章过于严肃甚至枯燥的说法,储安平在第一卷报告书中说明了两点:第一,《观察》确实是一份硬性的高级刊物,是给高级知识分子(包括大学生)看的刊物,而中学生等并不在该刊的读者对象范围之内;第二,《观察》是一份理性刊物,以理服人,绝不欢迎类似党派间那样的凶狠的攻击谩骂出现,因此无法满足一些读者希望看到“刺激”文章的要求。对此,储安平的态度是坚决的,“不过这几年来,大家太苦闷了,以致人人都希望读到所谓‘刺激’的文章,感情越冲动的文章越容易吸引读者;但此与本刊的基本精神相背,我们无意如此”,储安平强调,“我们不拟迁就读者的口胃而改变我们的方针”[2]。
针对部分读者提出的“每期有时事短评”、“专论应更为触及现实”等建议,《观察》进行了适当的改进,但终究还是没有设立“时事短评”一栏——没有将《观察》办成一份完全跟着时事走的刊物。在第二卷第12期刊发的对323位读者反馈意见的分析中,认为可以接受《观察》这种严肃风格的读者有227人,“希望稍微轻松一点的”有100人(多选),储安平认为,“这项答案使我们大大满意,并增加我们的自信”[2]。
储安平坦率而执著地坚持这一办刊理念。在第四卷报告书的“编辑检讨”部分中,面对读者来信中对“观察通信”一栏的赞扬,储安平却是“内心暗自惭愧”[2]。他认为雅俗共赏的“通信观察”,固然更容易“讨好”读者,但硬性的“专论”,在一段时间以来的不够充实也是其不够叫座的主要原因。他依旧坚持,“本刊是一个政论刊物,重心应当在专论部分”[2]。由于时值1948年,内战正如火如荼,知识分子普遍沉默,储安平表示“当尽心尽力,广征佳稿”,但也无奈地说明“有无成就,不敢先说”[2]。
三、采取民间“股份制”的模式,避免官僚资本和政党势力的渗入
1946年1月,《观察》第一次发起人会议在重庆举行,该会决定了刊物的名称、缘起尤其是“征股简约”,即《观察》将采取一种民间集资、入股分红的模式,预定股额为1000万元。在征集股金时,储安平特别注意不接受来自官方或政治团体的资金。对于不少闻讯后汇来股款的人士,储安平表示,在当下的环境中兴办报刊必定存在不可预见的风险,“我们还是请他们再为考虑……一般公务人员都非常艰苦……若仅从生活零用中,节省出钱来入股,我们实在感觉不安”[2];另外,刊物还进行了制度化的规定,如“办满一年时,主持人应向出资人提出财政报告”等[2]。
在半年多的刊物筹办过程中,由于入股人以“教书为生”的知识分子为主,而教职人员从八年抗战以来一直在“饥饿线上挣扎”,所以一开始筹款并不顺利。后来,凭借原《客观》的一些老读者及一些家底丰厚的学生等人的入股,情况才开始有所起色。当时,在“物价激涨”的上海,对于兴办一份刊物,“似非有二千万元不能”,但《观察》筹集一千万元“尚感不易”。储安平形容说,“这些日子是黝暗的,但我还有着一盏明亮的灯……吹不灭,抢不掉……驱散着周围的昏暗”[2]。至1946年7月,资金逐步到位,但考虑到暑期来临,学校放假,故发刊日被推至9月1日,储安平在第一卷报告书中兴奋地写道,“这是一个热闷的夏天,但也是一个富有生命的夏天”[2]。
事实证明,《观察》并没有让它的出资人感到失望。直到第一卷末,《观察》的资金已由开始时账面上的一千万上升到两千万。储安平说,“在经济上,本刊的发行数足以证明本刊可以自给,无须仰求‘外援’”[2],并给那些总认为某某刊物不是属于这一党就是属于那一派的人们以这样的认识——办刊物并不一定要靠哪一党哪一派的津贴。储安平不仅仅是创办初期集股时不接受官方资金,就是在创办后也一直都是如此。正是储安平不接受任何官方的资金,使得《观察》从一创办开始就避免了官僚资本和政党势力的渗入。
四、运用力争直接定户的策略,巩固基本发行量
《观察》的读者分为零售读者和直接订户两种。储安平在当时就认识到:“直接定户是一个刊物的基本读者,也是这个刊物最忠实并最关切这个刊物的读者”,因而《观察》比较重视争取直接订户的工作。储安平多次强调,争取订户的工作,“必须有通盘的计划,中途零零碎碎的,无甚补益”。可见,他把“推动订户”的工作,作为了整个编办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来做,换言之,争取订户,必须从整体上、从长远上来规划。因此,至第一卷第24期出满时,“除在创刊前分散过一次宣传品以外”,《观察》没有“在此方面有所努力”。直到第二卷出版时,杂志社各项工作业已走上正轨,才开始在“推动订户”方面作出努力。并且针对部分读者因考虑到刊物是否会中途夭折而不愿订阅的想法,储安平承诺,“我们主持这个刊物,不是一件随便轻率的行为,除非因政治打击而遭封闭,我们决不中途停止”[2]。
基于上述认识,储安平把争取订户的活动开展的别开生面。
一是通过《观察》撰稿人的帮助,在各高校征求学生新订户。1947年2月,《观察》以此方式主动“出击”,却因当时学生贫困,“拿不出2万块钱(约合抗战前法币1元——引者注)”,而“几乎可以说全面惨败”[2]。这一次行动,尽管没有达到增加订户方面的目的,却扩大了《观察》在青年学生中的影响。
二是呼吁原有的订户,介绍其亲友成为《观察》新订户。这一行动“出乎意外地获得了可观的成就”。在这一点上,我们惊异地发现,虽然储安平没有学过商业心理学,却善于分析和利用读者的购买心理。比如,他明确指出:“旧的一卷业已结束,新的一卷即将开始,在心理上这个时期最适合征求订户”[2]。此言具有指导意义。
三是为直接订户提供各种优惠服务,如八折优惠等。另外,从第四卷第13期开始,《观察》设立了多达1500个名额的“半价定户”,并力求将名额在学生、公务员(包括军人)和后方小城市读者间合理分配,以便“为清寒读者有一点服务”[2]。
四是对定户来信所要求的修改投递方式(《观察》提供平寄、挂号、航空平寄和航空挂号四种方式)、修改地址、续订、托购其它书籍等事宜,刊物均有专人回复并尽快办理。而由于国民党政府的邮政检查制度及蔓延各地的战火,有些地方的定户不能按时收到甚至收不到刊物,储安平在报告书中均详尽说明情况并诚恳致歉。
五、奉行“负责、迅速、公平”的精神,重视建立与撰稿人及读者的良好关系
储安平在第一卷报告书中强调,《观察》周刊办事的基本精神是“负责、迅速、公平”。对于撰稿人,《观察》同人都是“最尊重并最热诚的”。另外,《观察》的稿酬一向是透明公开的,并能根据物价的上扬及时调整。即便如此,储安平仍然经常自责懊恼,一面是对物价疯长的忧虑,一面是对稿酬微薄的无奈。
《观察》与读者的互动也是比较积极的。第一,《观察》对读者来函十分重视,有专人负责,虽不可能“每信必复”,但也尽量复短信予以说明;第二,从第一卷第13期开始,刊物设立“读者投书”这一固定栏目,专门刊载一般读者的原创短文;第三,对于一般读者或并未列入撰稿人名单的学者的投稿,编辑将其与“固定撰稿人”一视同仁,只论质量不计名气。以第三卷为例,在理论性最强位置最重要的“专论”专栏中,总共的72篇稿件里有17篇为读者投稿,占24%左右;而在偏软性的“通信观察”一栏中,总共的80篇稿件里更是有39篇为普通读者所赐,接近半数。《观察》同人表示,“本刊虽有基本撰稿人七十余位,但本刊仍为全国作者读者共同之刊物。园地公开,绝无私见,稿件取舍以稿件本身为标准。撰稿人来稿亦有退还者”[2];第四,《观察》进行了较为科学的读者调研。在第一卷第24期上,附有“读者意见书”表格一份,这份兼具开放式和闭合式问题的问卷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之后储安平撰写了《三百二十三位读者意见的分析与解释》,对问卷进行了分析。
此外,储安平还强调在基层广大读者中间做踏实的推销工作。具体有四种方法:第一,鼓动杂志社成员及其亲友动员他人订阅该刊。第二,设立代理发行点,如北平新宾书店等。第三,出版多种“《观察》版本”。由于内战爆发后,交通受阻,许多偏远地区的读者读不到或未能及时读到《观察》,自第三卷起,该社先后出版了“华北航空版”、“西南航空版”、“台湾航空版”等。第四,重视刊物自身的宣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每期出版,都在上海《大公报》封面位置刊载广告一次,内容为本期刊登的文章的标题和作者姓名,即使在杂志社财政困难时期或上海《大公报》广告费猛涨之后,仍照刊不误;二、在刊物中穿插“征求直接订户”之类的广告,据笔者粗略统计,此类广告计23条之多。
正是《观察》同人在上述五个方面的齐心努力,最终使得这份完全由知识分子操办的刊物在编辑和经营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而这一切是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迅速实现的。其主要表现为:一是尽管自第三卷以后出现愈来愈大的亏空,但若加上“《观察》丛书”的收入,杂志社即使仍有亏空,也尚能生存下去;二是从收入递增率来看,成绩是明显的,特别是第一、二卷时期,由于物价上涨情况尚不严重,有较大的盈利;三是在短期内,杂志社人员组织不断发展,销售量、定户数均以异常的幅度持续飙升,从而创造了现代中国编辑与出版史上的奇迹;四是杂志社经营两年余,其停刊不是因为经济问题,而是由于“言论态度”被国民政府查封的。
[1]本文中所提到的《观察》,均指1946年到1948年期间的《观察》周刊.
[2]储安平,张新颖.储安平文集[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
2010-03-23
袁新洁(1970-),男,湖南永顺人,主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