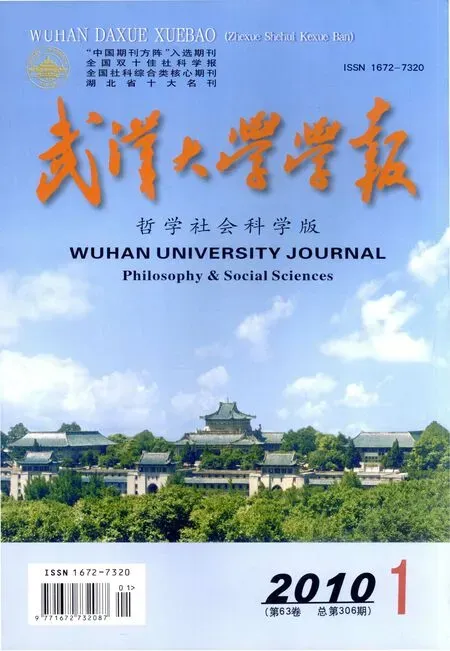论公共秩序发展趋势之限制适用
马 德 才
论公共秩序发展趋势之限制适用
马 德 才
公共秩序虽因其实质在于维护本国国家及其人民的利益而被称为国际私法中的“安全阀”,但由于它缺乏一个确定、统一的概念与适用标准,因而该制度在实践中容易被滥用。而公共秩序的滥用势必大大降低国际私法在协调各国法律冲突中的价值,妨碍国际民事交往的稳定和安全,有悖于当今世界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甚至走向国际私法价值取向的反面。正因为如此,所以有必要对公共秩序加以限制适用,且业已成为公共秩序的发展趋势之一。我国有关立法也应顺应这一发展趋势加以完善。
国际私法;公共秩序;限制适用
公共秩序如同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有利于法官根据本国利益的需要,随机应变地适用;另一方面,由于它缺乏一个确定、统一的概念与适用标准,因而该制度在实践中容易被滥用,成为一种法官任意排除外国法适用的工具。而公共秩序的滥用势必大大降低国际私法在协调各国法律冲突中的价值,妨碍国际民事交往的稳定和安全,有悖于当今世界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甚至走向国际私法价值取向的反面。如果不给公共秩序以合理的解释,那就会在很大程度上等于取消了国际私法的原则[1](第252页)。德国学者沃尔夫也同样对公共秩序滥用表达了这种担忧,即“萨维尼所表示的希望‘随着各国法律的自然发展,这些例外情形可望逐渐消除’—是太乐观了。相反,目光短浅的现代民族主义大大地增加了这些‘例外情形’的数目,从而严重地损害了国际私法作为倾向于国际规定的一个法律体系的价值。”[2](第273页)正因为如此,所以有必要对公共秩序加以限制适用。实际上,现在,对公共秩序的适用加以限制已成为国际社会较为普遍的要求,且业已成为公共秩序的发展趋势之一。而对公共秩序加以限制适用主要体现在各国都谨慎而严格地适用公共秩序、公共秩序的适用标准趋向客观说、适用公共秩序排除本应适用的外国法后并非一概代之以法院地国的国内法等方面。本文拟对此作一探讨,我国有关立法也应顺应这一发展趋势加以完善。
一、各国都谨慎而严格地适用公共秩序
从立法层面来看,有关国内立法及国际公约中的公共秩序条款对公共秩序的表述所使用“明显违背”的措辞就体现了限制公共秩序的基本精神。国内立法方面,例如1986年《德国民法施行法》第6条规定:“如果外国法律规范的适用结果与德国法律的基本原则明显不符,则它不得予以适用。如果其适用与基本权利不符,则尤其不得予以适用。”1987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法规》第17条规定:“适用外国法律明显违反瑞士公共秩序的,则拒绝适用。”1991年《加拿大魁北克民法典》第3081条规定:“外国法律规则,如果其适用将会导致一种与国际关系中公认的公共秩序明显背离的结果,则应排除适用。”1998年《委内瑞拉国际私法》第8条规定:“依照本法应适用的外国法规定,仅在其适用将产生与委内瑞拉的公共政策的基本原则明显相抵触的结果时方排除适用。”2004年《比利时国际私法典》第21条规定:“只要适用根据本法确定的外国法律将导致明显违背公共政策的结果,则该外国法不适用。”2005年《乌克兰国际私法》第12条规定:“外国法规范不予适用,如果其适用引起的后果明显与乌克兰基本法律秩序(公共秩序)不符。”等等。国际公约方面,包括海牙公约在内的各个公约中的公共秩序条款也表达了这种限制公共秩序的普遍意向。例如,1956年《扶养儿童义务法律适用公约》,该公约第4条规定:“本公约宣告可予适用的法律,仅在其适用与受理案件的机关所属国的公共秩序明显地相抵触时,始得不适用之。”这一表述几乎已成为后来海牙公约的公共秩序条款的一个公式。诸如1961年《关于未成年人保护的机关的权限和法律适用的公约》第16条、1961年《遗嘱处分方式法律冲突公约》第7条、1965年《收养管辖权、法律适用和判决承认公约》第15条、1971年《交通事故法律适用公约》第10条、1973年《扶养义务法律适用公约》第11条、1973年《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第10条、1978年《夫妻财产制法律适用公约》第14条、1980年《结婚仪式和承认婚姻有效公约》第15条、1985年《信托法律适用公约》第18条、1986年《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法律适用公约》第18条、1989年《死亡人遗产继承法律适用公约》第18条、1996年《关于保护儿童的父母责任和措施的管辖权、准据法、承认、执行和合作的公约》第22条与第23条第2款(d)项、2000年《关于成年人国际保护的公约》第21条、2005年《协议选择法院公约》第9条第5款、2006年《关于由中间人持有证券的特定权利的法律适用公约》第11条第1项等,具有相同或相似的规定。这表明,海牙公约适用公共秩序其条件趋于严格,显然是为了防止缔约国滥用公共秩序,从而避免妨碍公约统一化目的。另外,在区域性国际公约方面,例如1975年美洲国家组织制定通过的《美洲国家间关于汇票、期票和发票法律冲突的公约》第11条规定:“经本公约所述的可适用的法律,如果缔约国认为其显然违背它的公共秩序时,得拒绝在其境内适用。”1980年欧盟部分成员制定通过并于1991年生效的《合同义务法律适用的公约》(即1980年《罗马公约》)第16条规定:“凡依本公约规定所适用的任何国家的法律,只有其适用明显地违背法院地国的公共秩序时,方可拒绝适用。”2007年7月11日欧洲议会、欧洲理事会制定通过并于2009年1月1日起适用的《非合同之债法律适用条例》(即2007年《罗马公约II》)第26条规定:“本条例规定适用的任何国家的法律规则,只有在这种适用与法院地国的公共政策(公共秩序)明显不符时,才可以拒绝适用”。
从司法层面来看,各国法院也都是从严适用公共秩序。例如,在德国,德国法院要想以公共秩序为由拒绝外国法律的适用,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1.依据德国国际私法规范本应该适用外国法律;
2.对外国法律适用结果的审查;
3.不符合德国法律的根本原则;
4.明显不符合。
可见,《德国民法施行法》为德国法院援引公共秩序排除外国法的适用设置了较为严格的限定条件。对此,德国学者们也持赞同意见。在他们看来,德国法院决不能滥用公共秩序条款,尤其是使用其服务于政治或其他的非法律的目的。这表明,在萨维尼影响下的德国是把排除外国法的适用视为一种例外,亦即德国法院较为谨慎地援用公共秩序。在英国,根据英国国际私法学者对英国判例的分析,英国法院主要在两类涉外案件中援用公共政策排除外国法适用:
1.涉及外国合同的案件。1980年《合同义务的法律适用公约》(简称《罗马公约》)第16条规定对英国的影响是:任何国家的法律,只有其适用明显地违背英国的公共政策时,英国法院方可拒绝适用。在此类案件中,英国法院曾以公共政策为由拒绝执行帮诉合同、限制贸易合同、在胁迫或强制下签订的合同、涉及有欺诈和败坏因素的离婚合同、对敌贸易合同和违反与友好国家法律的合同,尽管这些合同依其准据法是有效的。
2.涉及外国身份的案件。
时至今日,英国法院仍以公共政策为理由,拒绝承认任何根据惩罚性即歧视性的外国法而取得的身份的效果。这种身份如奴隶身份和剥夺一切权力的宣告,以及强加于教士、修女、新教徒、犹太人、外国籍人、有色人种、离婚的人和挥霍浪费者的无行为能力地位的身份。不过,仅仅是外国的某种身份或关系为英国法所不知道这一事实,不能成为英国法院拒绝承认的理由[3](第78页)。除了合同和身份这两类案件之外,英国以公共政策为理由排除外国法律适用的例子是很少的。这大致表现为:
1.如果没收私人财产的外国国有化法令是“惩罚性”的,亦即是针对特定个人、或特定公司、或特定家庭、或特定种族的人、或特定的外国国籍的人的财产,那么英国法院就会以公共政策为由拒绝承认该外国国有化法令。
2.如果外国的外汇管制立法已成为一种压迫和歧视的工具,哪怕原来通过时是为了保护国家经济的真诚目的,那么英国法院亦可依据公共政策拒绝适用。
3.根据公共政策的理由,在拒绝承认外国离婚或婚姻无效的判决,以及拒绝执行外国对人诉讼的判决,这都是可能的,但是实例极为罕见。
在美国,美国法院由于公共秩序的任意性特点,故在适用时采用相当谨慎的态度,且级别越高的法院在适用时越是小心。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几个重大案件中更是反复强调,应对公共秩序作限制性解释而不能做扩张解释;不能以外国法与美国的实体法不同为由适用之;只有当法院地的重大政策会被侵犯时,才能以之为由排除外国法的适用;作为对抗法律选择条款的可执行性的原因,公共秩序不能由“假定的公共秩序”推演而来,而必须基于明示、确切的“法律或判例”[4](第57页)。从实证主义角度考察,最近几十年间,美国法院在司法实践中适用公共政策排除外国(州)法或拒绝承认或执行外国(州)法院判决及仲裁裁决的判例,呈现出现明显下降趋势。在法国,法国法院在很长的时间里“滥用公共秩序范畴”,拒绝承认在离婚问题和已婚妇女的财产问题上比法国法规定更大自由的外国法律。法国法院还否定社会主义的国有化法律的效力。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国际联系增加的影响下,在这一问题上发生了某些积极的变化[5](第69页)。即在司法实践中,如果外国法违背法国公共秩序,法国法院会排除适用,亦即法国法院在实践中开始将公共秩序作为一种例外来对待。
可见,各国国际私法的立法与司法实践表明,各国都是谨慎而严格地适用公共秩序。
二、公共秩序的适用标准趋向客观说
根据各国国内立法及国际私法条约可知,公共秩序的适用标准大致有两个,即主观说标准和客观说标准。其中,主观说标准认为,法院地国依照自己的冲突规范本应适用某一外国法时,如果该外国法本身的规定与法院地国的公共秩序相抵触,即可排除该外国法的适用,而不问具体案件适用该外国法的结果如何。它强调外国法规则本身的可厌性、有害性和邪恶性,而不注重法院地国的公共秩序是否因适用该外国法而受到实际上的损害。法国学者巴蒂福尔等人也持此观点,他们认为法官必须可以公共秩序为由拒绝适用其内容不能接受的法律[6](第488页)。一些国家的国内立法采取了这种立法标准。例如,2004年《卡塔尔国民法典》第38条规定:“依照上述条款应适用的外国法,如果其规定违反了卡塔尔的公序良俗,则排除该外国法的适用。”该标准的优点在于运用方便,只需法院地认为外国法本身与法院地的公共秩序不符,即可排除该外国法,而无须就个案加以研究,以决定案件是否与法院地有所联系或外国法适用的结果是否违反法院地的公共秩序。但其缺点也较明显,即倘依此标准,外国法适用的范围势必大大缩小。这无异于强求外国当事人依法院地国的法律及道德标准行事,且当事人在法院地国起诉,常属偶然,如完全以法院地法为标准,实在难以达到公平。由此可知,如果根据主观说标准,适用结果必致不当,国际私法适用外国法的目标恐怕也难以达到。而且,该立法标准还容易导致公共秩序的滥用,对于许多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依冲突规范本应适用的外国法以及本应承认和执行的外国判决,也可能因公共秩序而得不到适用或承认。这就不利于维护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的稳定。所以,只有少数国内立法采取主观说的公共秩序立法标准。
而客观说标准认为,在援引公共秩序排除外国法适用时,仅仅是外国法的内容违反法院地国的公共秩序,并不一定该外国法的适用,只有是外国法适用的结果危及法院地国的公共秩序或个案与法院地国有实质性联系时,才能适用公共秩序以排除外国法的适用。它又可分为联系说标准和结果说标准。相比主观说标准,采用客观说标准,尽管法官对于每件诉讼要探求其与法院地国的各种联系或外国法适用后所生附带事件之合法性,运用起来恐怕没有主观说标准那么方便,但是,客观说标准仍较为可取,因为它重视个案情形,易于为个案获得公平的结果。而且,客观说标准使得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受到以下两方面的限制:一方面是外国法的内容与法院地国的公共秩序不符;另一方面是适用外国法的结果危及法院地国的公共秩序或案件与法院地国有实质性联系。因而,法官在行使公共秩序时所享有的自由裁量权就大为减弱,于是公共秩序的限制适用也就随之增强。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各国立法和实践中多采用这种标准。例如,德国、瑞士、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泰国、埃及等国都采用此标准。此外,前述国际私法公约中也大多采取客观说标准且为其中的结果说标准。
三、适用公共秩序排除本应适用的外国法后并非一概代之以法院地国的国内法
一国法院基于公共秩序排除本应适用的外国法后,怎么办?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因为法院不能以没有法律为由拒绝审判。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过去的国际私法理论倾向于用法院地法的相应规定取代被排除的外国法,因为这种做法符合某些国家通过公共秩序限制外国法的适用,扩大本国法适用范围的要求,所以现在仍有一些国家的立法与实践采取这种做法。例如,2004年《卡塔尔国民法典》第38条规定:“依照上述条款应适用的外国法,如果其规定违反了卡塔尔的公共良俗,则排除该外国法的适用。此时,适用卡塔尔法律。”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这种做法会助长公共秩序的滥用倾向,也不符合法院地国冲突法的原意,因为既然有关的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应适用外国实体法做准据法,就表明它与该国有更密切的联系,适用该外国法更为合适。因此,他们主张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妥善处理,而不能一概代之以法院地法,必要时可考虑适用与该外国法有较密切联系的另一外国法[3](第83页)。而且,目前许多学者主张对以法院地法取代被公共秩序排除适用的外国法的做法应尽可能地加以限制。因为,从法院地国冲突法的精神来看,既然有关的民事关系应适用外国法做准据法,就表明该案件跟有关的外国有更密切的联系,用外国法解决更为合适。所以,应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妥善加以处理,切不可认为在外国法被内国公共秩序排除后概由法院地法取代都是合理的[7](第285页)。德国学者沃尔夫也持此观点。他认为:“在外国的法律规则被排除适用的情形下,它的地位大半由法院地法代替。但是这种代替应该尽可能加以限制。通常应该适用的外国法如果含有一个无可反对的法律规则甲,而这个规则附有一个违反英格兰公共政策的例外乙的时候,不适用例外乙的结果并不是就须要适用英格兰法,而是须要适用该外国的主要的法律规则甲。”[2](第269页)这种主张相对较为合理。这种较合理的主张目前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有关国际私法立法所采纳。例如,1995年《意大利国际私法制度改革法》第16条规定:“如果适用外国法的结果与公共秩序相抵触,则不予适用。在此种情况下,如果对于相同案情存在其他连结因素,则适用依据该连结因素制定的法律;如果缺乏此种连结因素,则适用意大利法律。”再如,2005年《乌克兰国际私法》第12条第1款规定:“外国法规定不予适用,如果其适用引起的后果明显与乌克兰基本法律秩序(公共秩序)不符。在此情形下适用与法律关系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如果不可能确定或适用此法,则适用乌克兰法。”等等。这种适用公共秩序排除本应适用的外国法后并非一概代之以法院地国的国内法,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对公共秩序适用的一种限制。
四、顺应公共秩序限制适用的发展趋势,完善我国有关立法的相关规定
我国在立法上已有比较完备的关于公共秩序制度的规定。早在1950年11月,当时中央人民政府法律委员会在《关于中国人与外侨、外侨与外侨婚姻问题的意见》中指出,对于中国人与外侨、外侨与外侨在中国结婚或离婚,我国婚姻登记机关不仅应适用我国的婚姻法,而且应在适当限度内照顾到当事人本国婚姻法,以免当事人结婚或离婚被其本国认为无效,但“适用当事人的本国的婚姻法以不违背我国的公共秩序、公共利益和目前的基本政策为限度”。这里使用了“公共秩序”、“公共利益”、“基本政策”等措辞[8](第228页)。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一次在国际私法中全面规定了公共秩序保留制度[3](第174页)。该法第150条规定:“依照本章规定适用外国法律或者国际惯例的,不得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公共利益。”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
1.我国在公共秩序的立法方式上,采取了直接限制的立法方式,即按照我国的冲突规范,某种涉外民商事关系本应适用外国法,只是适用该外国法却与我国的公共秩序相违背,因而我国法院凭借自己的公共秩序直接排除该外国法的适用。
2.我国在公共秩序的立法标准上,采纳了与大多数国家相一致的客观说标准且为其中的结果说标准,这有利于适当限制公共秩序的运用。
3.我国在公共秩序的排除对象上,不仅指向外国法律,还指向国际惯例。除了《民法通则》之外,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以下简称《海商法》)及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航空法》(以下简称《航空法》)也分别从法律适用角度规定了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并且作了与《民法通则》第150条相同文字的规定。
其中,《海商法》第276条规定:“依照本章规定适用外国法律或者国际惯例,不得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公共利益。”《航空法》第190条规定:“依照本章规定适用外国法律或者国际惯例,不得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公共利益。”但是,相比公共秩序限制适用的发展趋势而言,我国公共秩序的立法规定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而我国有关公共秩序的立法规定应当顺应公共秩序限制适用的发展趋势加以完善。
(一)使用“明显违背”措辞限制公共秩序的适用
前文已述,为了保证国际私法在协调各国法律冲突中的价值,以及国际民商事交往的稳定和安全,顺应当今世界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就必须对公共秩序加以限制适用,这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要求。基于此,有关国内立法及国际公约中的公共秩序条款对公共秩序的表述所使用“明显违背”的措辞就体现了限制公共秩序的基本精神。然而,我国《民法通则》等法律有关公共秩序的条款却没有“明显违背”此种限制公共秩序适用的措辞,从而表明我国有关公共秩序的立法不仅表现出对公共秩序的适用规定过于宽泛,不符合国际私法立法的基本精神,而且表现出它不能顺应国际社会限制公共秩序适用的发展趋势,有鉴于此,我国公共秩序立法应使用“明显违背”措辞来限制公共秩序的适用。
(二)适用公共秩序排除本应适用的外国法后并非一概代之以我国法律
在依公共秩序排除本应适用的外国法后,法院面临着一个重新选择准据法的问题。对此,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立法对该问题的解决做出了规定,但是,我国包括《民法通则》在内的法律中所有的公共秩序保留条款对于排除本应适用的外国法后的法律选择问题都没有作规定,从而在我国公共秩序保留制度适用问题上就存在立法空白。这样,法官当然不能做到“有法可依”,不利于法官在具体案件中的操作,而法官又不能以没有法律规定为由拒绝审判,因此,我国立法应明确规定依公共秩序排除外国法后的法律适用问题。不过,前文已述,对公共秩序加以限制适用是国际社会较为普遍的要求,其表现之一就是适用公共秩序排除本应适用的外国法后并非一概代之以法院地国的国内法,而是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妥善处理,必要时可考虑适用与外国法有较密切联系的另一外国法,如果再没有与该外国法有较密切联系的另一外国法时,则可以适用本国法。这样规定比较合理,其合理性表现在:一是比较符合法院地国冲突法的原意;二是可以防止公共秩序的滥用倾向。因而,这种较合理的主张目前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有关国际私法立法所采纳,例如前述1995年《意大利国际私法制度改革法》第16条、2005年《乌克兰国际私法》第12条第1款都作了此等规定。所以,在此问题上,我国可参照国际上的此等普遍做法,规定在外国法被排除适用后,“必要时可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应的法律”,以弥补我国依公共秩序条款排除外国法后的立法空白,同时可与国际社会普遍限制适用公共秩序的要求相一致。必须指出的是,该条款隐含的意思是:当外国法被排除后,就可以适用与该法律关系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如果没有这种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时,即可以适用我国相应的法律。
综上,顺应公共秩序限制适用的发展趋势,对我国的公共秩序可作如下设计:“依照本法规定应适用外国法律时,如果适用结果明显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共秩序的,则不予适用,必要时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应的法律。”
[1] 李双元、徐国建:《国际民商新秩序的理论构建-国际私法的重新定位与功能转换》,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 [德]马丁·沃尔夫:《国际私法》,李浩培、汤宗舜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3] 韩德培:《国际私法》,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4] 霍政欣:《公共秩序在美国的适用-兼论对我国的启示与借鉴》,载《法学评论》2007年第1期。
[5] [前苏联]隆 茨等:《国际私法》,吴云琪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
[6] [法]巴蒂福尔、加拉德:《国际私法总论》,陈洪武等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年版。
[7] 李双元:《国际私法》,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8] 黄 进:《宏观国际法学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责任编辑 车 英)
On the Limited Application of Public Order Development Trend
Ma Decai
(International Law Institute,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y,Nanchang 330013,Jiangxi,China)
Although the public order is know n as the"safety valve"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owing to its safeguarding the interests of the home nation and its people in essence,it is to be abused easily in practice because of its lack of a firm,unified concepts and applicable standards.The abuse of public order is bound to greatly reduce the value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course of coordination of conflict of law s and hinder the stability and security of the international civil exchanges,and is contrary to today’s general trend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and even be the opposite coin of the values trend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That is why it is necessary to limit the application of public order,and it is one of the development trends of public order.The relevant legislations should conform to this development trend and to be imp roved accordingly.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public order;limited application
DF97
A
1672-7320(2010)01-0027-06
马德才,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国际法研究所所长,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博士生,江西南昌330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