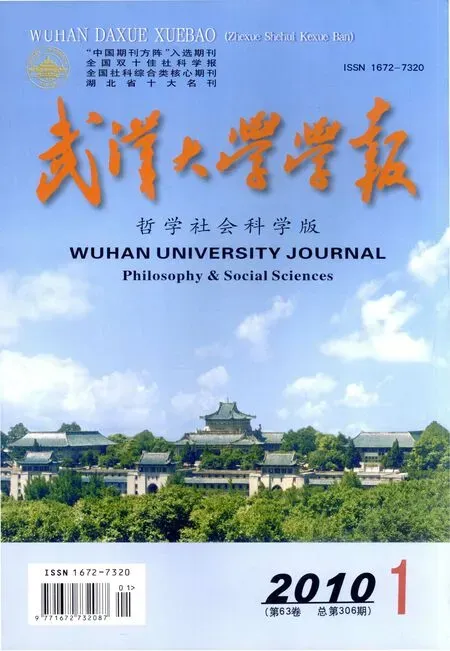全球化背景下多元公民身份体系的建构
郭 忠 华
全球化背景下多元公民身份体系的建构
郭 忠 华
公民身份是连结个体与民族国家的制度性纽带,体现了个体与国家之间的互惠关系。在全球化时代,以民族国家作为参照系的公民身份越来越受到侵蚀。全球化不仅外在地削弱了公民身份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制度性关联,而且还内在地给个体的自我认同机制造成了改变。针对这种情况,本文提出了多元公民身份体系的构想。多元公民身份超越民族国家的视界,建立一个包括亚国家、国家和超国家层级在内的公民身份体系,以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政治空间和认同方式的改变。
全球化;公民身份;民族国家;多元公民身份
现代公民身份以民族国家的建制作为政治基础,体现了民族国家内部个体与国家之间的互惠关系,具有明显的排他性特征。20世纪中后期以来日益强化的全球化进程对传统民族国家的关系结构带来了冲击:它一方面使民族国家与公民身份的固化关系趋于松弛,另一方面又促进了本土化和全球化之间的悖论性发展。公民日益疏离于传统管治关系的同时,地方自治和全球治理的趋势迅速强化。面对新的形势,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公民身份已难以适应时代的需要,多元公民身份的发展变得势在必行。
一、公民身份与民族国家的关联
与民族国家相比,公民身份有着更加令人肃然起敬的历史。公元前6-4世纪的斯巴达和雅典,公元1世纪左右的罗马共和国,中世纪后期的意大利城市共和国,都曾盛行过公民的话语。1789年法国大革命过程中颁布的《人权宣言》则标示着现代公民身份的开端,代表了此前一系列孕育过程的结果。欧洲中世纪末期发生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为倒转传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和确立个体在一切政治架构中的核心地位奠定了思想基础,而英、美、法等国的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则扮演了现代公民身份的助产婆。在近代自然法学说和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双重推动下,公民身份理论实现了形态演化和内涵更新,现代公民身份取代其古典的形式支配了此后的历史。现代公民身份以民族国家的建制作为出发点,公民身份假设了民族国家的政治前提,是国家成员资格、公民权利和公民义务的集合体。哈贝马斯指出:“今天,‘Staatsb ürgerschaft’或‘citizenship’这个表达可能不仅仅用于表示国家的组织成员,而也用来表示通过公民权利和公民义务从内容上来界定的地位了。”[1](第661页)
首先,公民身份以民族国家的架构作为政治前提,公民身份表示个体在民族国家中的成员资格,只有先建立起民族国家,才谈得上成为民族国家的成员。在这一方面,公民身份与国籍具有相同的含义。“国际法不承认国籍与公民身份之间的任何区别,国籍决定了公民身份。”[2](第122页)按照通行的做法,个体可以以两种方式获得民族国家的公民身份:血统主义或属地主义。血统主义即以继承的方式获得公民身份:个体一出生便从父母那里获得了公民身份。属地主义即经由国家领土获得公民身份:个体一出生即获得了出生地的公民身份。当然,这只是一种最简单的界定方式,实际情况比这要复杂得多,但无论如何,公民身份总是以民族国家的建制作为出发点,表明个体作为民族国家成员的资格。
其次,与这种成员资格相联系,公民身份还意味着民族国家授予其公民的权利,只不过在不同的时期和国家,公民身份权利的内容存在差异而已。1949年,英国社会学家 T.H.马歇尔对公民身份权利的内容首次做了清晰的勾勒。在他看来,公民身份权利由三个部分组成: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公民的要素由个人自由所必需的权利组成:包括人身自由,言论、思想和信仰自由,拥有财产和订立有效契约的权利以及司法权利……政治的要素,我指的是公民作为政治权力实体的成员或这个实体的选举者,参与行使政治权力的权利……社会的要素,我指的是从某种程度的经济福利与安全到充分享有社会遗产并依据社会通行标准享受文明生活的权利等一系列权利。”[3](第7-8页)除此之外,马歇尔还将每一种要素对应于相应的历史时期和国家机构:公民权利主要发展于18世纪,与这一权利最直接相关的是法院;政治权利主要发展于19世纪,与这一权利相对应的机构是国会和地方议会;社会权利发展于20世纪,与之对应的机构则是各种社会公共服务机构。至此,马歇尔描绘出了一幅完整的公民身份权利图景,并且将这幅图景与民族国家牢牢地绑在了一起。
最后,公民身份还意味着公民对民族国家所应履行的义务。公民身份实际上是权利与义务的集合,代表了个人与国家之间的互惠关系。我们可以把权利看作是国家对公民应该履行的义务,而把义务看作是个人应当对国家承担的责任。那么,在通常情况下,个人对于国家的义务又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对于这一问题,不同的公民身份传统做出了不同的回答。公民共和主义传统对公民义务通常有着相当高的要求,它强调公民必须具有节制、正义、勇气、智慧、审慎等美德;强调公民之间应当形成兄弟般的情谊;强调公民献身于国家公共事务,并且把这种参与看作是防止内部纷争和政治变质的关键。公民自由主义传统更钟情于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要公民义务。当代自由主义思想大师哈耶克认为:“自由与责任不可分”,“个人自由的范围同时也是个人责任的范围”[4](第107,108页)。在现代国家,无论何种公民身份传统处于支配地位,忠诚、兵役、纳税、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全、遵守宪法和法律等都被看作是公民必须履行的义务。
《大不列颠全科全书》指出:“公民身份指个人同国家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个人应对国家保持忠诚,并因而享有受国家保护的权利。公民身份意味着伴随有责任的自由身份。一国公民具有某些权利、义务和责任是不赋予或只部分赋予在居住的外国人和其他非公民的。一般来说,完全的政治权利,包括选举权和担任公职权,是根据公民身份获得的。公民身份通常应负的责任有忠诚、纳税和服兵役。”[5](第236页)这一定义不仅表明了公民身份的内容,而且还表明了公民身份与民族国家的内在关联。从本质上说,公民身份是个体与国家之间互惠关系的制度化。通过公民身份的授予,民族国家不仅统一和凝聚了领土范围内的人口,并且通过对公民权利和公民义务的界定解决了政府可能出现的合法性危机、财政危机和贯彻危机等。另一方面,通过取得公民身份,个体也解决了民族认同和政治归属的问题,并且消除了政治统治的“天然暴力的特征”[1](第659页),使民族国家与民主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6](第244页)。但是,民族国家与公民身份之间的关系并不像表面上那样牢不可破。20世纪80年代以来,面对全球化所带来的身份变化,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公民身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失语,以至有学者惊呼:“我们没有形成能够表达全球成员资格观念的概念工具。”[3](第229页)
二、全球化对民族国家公民身份的冲击
全球化是一个非常晚近的词汇。“直到20世纪80年代晚期,‘全球化’词汇才开始得到使用。”[7](第1页)从初次诞生到迅速扩张、从毫不知名到风靡世界,“全球化”概念本身就是全球化过程的一部分和全球化的最佳写照。学术界有关全球化的论争由来已久,但无论你对全球化持何种态度,一个无可改变的事实是,今天,全球化这一引人注目的潮流已经改变了传统经济、政治、文化在同一民族国家边界内部在一定程度上齐步成长的历史格局。原来那种由国家确定的以民族国家为界限的对内经济和对外贸易的经济秩序,正演变成为一种跨国经济,在这种一体化经济网络中,民族国家的驱动因素不再构成全球交换关系网络的节点。与经济全球化的浪潮相一致,人们的生活和交往也越来越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甚至有学者认为,“全球化指的是社会交往的跨洲际流动和模式在规模上的扩大、在广度上的增加、在速度上的递增,以及影响力的深入”[8](第1页)。但还必须看到,全球化还从最微观的层面改变了个人的日常生活模式,“全球化不只是一个‘外在’的现象。它不仅指大规模全球体系的产生,而且指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环节的变革”[9](第107页)。反映在民族国家向度上,全球化使民族国家的单一空间模式上下拉伸为一种“三维空间”模式。这种空间不仅外在地改变了公民身份与民族国家的传统关系,而且还内在地改变了个体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方式。
从内在的角度来看,全球化改变了个体的政治认同对象和认同方式。公民身份不仅是权利和义务的总和,同时还意味着一种情感和想象的空间,这是一个个体可以向真实的社会世界投以感情的主观领域,即“文化公民身份”[10](第87页)。当民族国家尚未受到全球化浪潮洗刷的时候,通过公民身份的纽带,民族国家扮演了公民政治认同的稳定对象,传统、主权、民族、领土等因素则充当了政治认同的媒介。通过对这些因素的体认,个体形成了对民族国家的忠诚感和归属感,通过与其他民族国家的比较则加深了对自身的文化体认。但是,随着全球时代的来临,不仅传统政治认同媒介的意义发生了改变,而且还从根本上危及个体自我认同机制本身。在高度现代性的今天,尽管几乎所有的民族国家都珍视传统在凝聚公民方面的重要性,但从某种程度而言,我们今天生活的社会是一种“传统已经终结”了的社会[9](第40页)。从民族的角度来看,在全球化时代,国家作为民族共同体的政治想象正经历着亚民族和超民族力量的撕扯,大多数民族国家都呈现出分裂的趋势,族群的政治想象日益代替了对整个国家的想象,而诸如欧盟等众多地区性组织的发展则从超民族的层面弱化了个体原有的国家认同。其他的认同媒介或多或少也都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实际上,在认同方面,最致命的莫过于个体的身份认同本身被置于危机的状态。面对纷繁的全球世界,“我是谁”或者“我们是谁”的问题已成为个体不得不做出回答的问题[11](第1-2页)。所有这些现象结合在一起,不可避免地使个体对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趋于弱化。
与民族国家的单一空间相比,全球化还塑造了另外两种空间结构:全球性空间和地方性空间。两者都把民族国家条件下的公民身份架构置于拷问的境地。与此前的世界相比,毋庸置疑,今天的世界是一个真正“全球”的世界,一个地区所面临的问题同时也是整个世界所面临的问题,人类生活在一个彼此相依的世界中。全球性空间的形成促进了民族国家的融合和地区性组织的成长,而欧盟又是其中发展得最为完善的典范。地区组织的发展给传统公民身份带来了挑战。以欧盟为例,欧盟成员国的公民不仅拥有所在国的公民身份,而且还拥有统一的欧盟公民身份。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各成员国很难就欧盟公民身份做出统一的解释。欧盟公民身份如果不能像成员国公民身份那样赋予相应的权利和义务的话,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传统公民身份理论已经丧失了对它的解释能力?抑或意味着另一类型公民身份的诞生?从文化公民身份的角度来看,如何去说明一个公民在忠诚于自己国家的同时,还必须忠诚于统一的欧盟。对于一名爱尔兰公民来说,他在获得爱尔兰公民身份的同时,还可以获得英国和欧盟的公民身份。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他相应具备了三个层次的忠诚呢?即使我们对其各个层次的忠诚都持肯定的态度,从忠诚所要求的“专一”而言,也早已违背了忠诚的含义。
全球化在促进全球时空融合的同时,还推动了本土化的发展。“全球化不仅产生向上的拉力,而且也产生向下的推力,给地方独立带来了新的压力……全球化是世界上不同地方的地方文化的复兴的理由。”[9](第8-9页)这是因为,全球化并非一定需要通过民族国家的传导才能深入到它的内部,在许多情况下,全球化的许多影响可以透过民族国家而直接进入地方,并对它们造成影响。如果加上下面将要谈到的全球化抽离民族国家传统管治能力的事实,当前本土化发展的情形也就变得更加容易理解。在今天的民族国家体系中,几乎每一个国家都存在着这样的城市,它们坐落在民族国家的领土范围内,但由于经济贸易和文化传播,它们实际上更是“世界的城市”,而不是民族国家的城市。发生在这些城市中的细微事件可能对整个世界造成影响,而世界脉搏的每一次跳动都能在它们身上得到体现。美国的纽约、英国的伦敦、中国的香港等等,它们尽管被冠以民族国家的称谓,实际上却更是全球化的推动者和体现者。本土化除了体现在城市从民族国家中被抽离外,还体现在地方自治、地方独立等的发展上。由于全球化所带来的分化组合,许多地方产生了自治和自决的要求,尤其是那些尚未建立自己国家的民族,它们希望建立自己的国家以跻身于世界民族国家之林。无论本土化采取哪一种形式出现,它都使地方身份认同的权重大为加重,从而从民族国家内部瓦解单一公民身份所具有的意义。
除上述影响外,全球化还直接挑战民族国家本身,在民族国家与公民身份这一坚实的链条中楔入失谐的因子。在公民社会与民族国家的链条中,主权、民族主义和公民身份充当了其中最为坚实的环节。但是,在全球化力量的冲击下,这些坚实的环节却被越来越被涵化和消解。从主权的角度来看,全球化成为挑战民族国家主权的最有力因素,众多地方自治组织和分离主义运动试图从民族国家中分离出去,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同时,面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本土化和全球化的双向发展,民族国家还被迫同时向下和向上让渡其部分主权。在内外两种力量的侵蚀下,主权所蕴含的管治能力越来越遭到削弱。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来看,民族主义曾经充当了国家与公民之间最牢固的心理纽带,但是,伴随着国家主权的削弱和文化的全球激荡,这种有效的凝固剂也开始出现分化发展的趋势:一是朝着多元文化主义的方向发展;二是朝着原教旨主义的方向发展。前者尽管以一种开放的态度海纳各种文化,但至少使传统的公民身份认同不再那么牢不可破。后者则完全是一种对全球化的逆反,旨在以更加传统的方式捍卫已经被全球化逼入死角的民族文化,它拒绝对话,而且常常与暴力联系在一起。从公民身份的角度衡量,公民身份意味着公民与国家的契约。但是,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即使是一个非常仁慈的国家也未必能够真正保护自己的公民,更何况随着国际移民浪潮的发展,原有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也会趋于淡化,甚至造成与公民身份的脱节。
三、多元公民身份体系的构想
全球化给传统民族国家的公民身份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和张力,但是,公民身份是否就真的耗尽了自己的潜能?是否真如特纳所言,全球化已使公民身份概念在某些方面“显得多余和过时”[3](第229页)?抑或如马歇尔所断言的“今天的公民早已被有效地‘剥夺了公民权’”[12](第37页),或者如伊格纳蒂失所言,公民身份压根就是一个“谜”[13](第53页)?公民身份无疑存在着难以数计的问题,但是,自古希腊以来,公民身份也历经变迁,最终才发展成为今天的形态,相对于民族国家的公民身份来说,古典公民身份早已面目全非。因此,今天的情况或许更意味着一种新的转型的开始:“它要求我们不能忽视这一主题,而是去理解它所存在的复杂性和张力,并积极寻找解决之道。”[14](第159页)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前批判者就其困境和危机所做的评判,或许更应被看作是检视公民身份所具有的非凡弹性是否已走到了它的极限,被看作是寻求解决公民身份困境的一部分。在这种探索中,只有建立多元公民身份体系才能消除全球化给民族国家公民身份所带来的挑战。这种公民身份体系不再把公民身份看作是一个仅仅表明个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单一概念,而是以全球化所催生的“三维空间”作为出发点,建立一个包含亚国家、国家、地区乃至世界层级的公民身份体系,提升公民身份的包容能力。鉴于前文已经对国家层级的公民身份多有论述,在接下去的篇幅里,本文将把重点放在对亚国家、地区和世界层级的公民身份的论述上。
亚国家层级的公民身份实际上已经存在着某些成熟的实践。在实行联邦制的国家,公民既是较低层级的联邦成员单位(如州、邦、加盟共和国)的公民,同时也是联邦层级的公民。但全球化所带来的本土化表明,即使在具备了这种双重公民身份架构的国家,亚国家层级的公民身份也应当有更丰富的内容。地方自治的发展,尤其是城市在全球化背景中所突显出来的重要性,使它们要求有属于自己的公民身份。我们可以把这一层级(次州、次邦)的公民身份称作“城市公民身份”(municipal citizenship)。城市公民身份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在德国的慕尼黑,城市公民身份甚至已经得到了有效的实践。这个外来人口占总人口近20%的城市有着丰富多彩的外来文化,城市政府鼓励其居民在城市中展示并传播自身的文化。通过这种措施,慕尼黑呈现出一种“所有人的文化”和“文化为所有人”的文化特色。这种文化特色为它的居民找到了一种共同的身份,并且使他们感到骄傲和自豪。城市公民身份与国家公民身份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后者更着重于作为国家的成员资格以及附载在这一资格上的权利与义务,因此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城市公民身份则更侧重于城市文化的形成和公民对这种文化的认同,因此更强调文化的一面。
地区层次的公民身份介于国家公民身份与世界公民身份之间,主要是为了适应全球化所带来的地区性组织的发展。在这一方面,欧盟为地区公民身份提供了发展的典范。欧盟尽管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却预示了世界其他地方治理模式的潜在发展方向。它在保留传统民族国家公民身份的同时,还授予统一的欧盟公民身份。欧盟公民身份超越了把民族国家作为公民身份唯一参照系的传统做法,从而对公民身份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固定关联形成了挑战[15](第94页)。欧盟公民身份同样被赋予了某些重要权利,如在成员国领土内自由迁徙和居住的权利;居住在成员国的非该国公民,可以与该国公民一样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欧盟公民身份为成员国公民提供了更大的认同空间。在由于民族国家的合作和融合而导致地区性组织蓬勃发展的今天,欧盟公民身份为其他地区性组织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世界公民身份在实际中尽管并不存在,但却是一种与公民身份的历史同样久远的理念。这种公民身份主要体现为一种普世认同的感情和对人道主义的接受上。在公民身份体系的建构中,世界公民身份理应成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是因为,作为一种人类理想,它的价值在当今仍然具有重要性。通过20世纪的两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以及接踵而来的核武器威胁和环境灾难,所有对人类命运有所关切的人们都应当更加怀有一种世界主义的精神。如果说这些惨烈的事件是民族国家所导致的结果的话,民族国家的公民身份就更应得到世界公民身份的补充。另外,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全球化也的确催生了一部分世界公民,如霍克所区分的5类全球公民:全球化改革运动者、全球化商界精英、地球环境维护者、具有政治远见的地方主义者以及跨国化行动主义者[16](第140页)。但实际上,全球公民更加关注人道主义的活动,更加关注人类的普遍性问题。他们在多元公民身份体系中居于同样重要的地位。

图1 多元公民身份的层级示意图
多元公民身份体系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范围依次扩大的层级结构。最底层是由于公民居住在特定城市而形成的城市公民身份,它主要体现在对城市文化的认同上。其上是州、邦、加盟共和国等联邦单位的公民身份,它所蕴含的权利和义务通过联邦宪法得到界定。城市公民身份和州公民身份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亚国家层级的公民身份。国家公民身份存在于亚国家公民身份之上,它是公民作为民族国家成员资格的体现。在民族国家仍然占据统治地位的今天,国家公民身份仍是所有层级中最为重要的一层。紧邻国家公民身份的是地区公民身份,它是地区性组织赋予成员国公民的公民身份。这一层级的公民身份为成员国公民在地区性组织范围内自由往来和在第三国获得成员国的外交保护方面提供了便利。世界公民身份处于层级结构的最顶层,它具有强烈的普世主义关怀,在弥补民族国家公民身份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每一层级的公民身份各有侧重,它们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多元公民身份体系的基本轮廓。
多元公民身份是全球化背景下取代民族国家公民身份而建立起来的一种身份体系。它针对20世纪中后期全球化所带来的空间结构的变化和认同模式的改变,将公民身份的空间范围从单一的民族国家上下延伸至城市和全球的层次,同时,将公民身份的认同对象从单一的民族国家扩展为多元化的政治共同体,以此提升公民身份的包容能力和解释能力。社会历史的沧桑巨变曾经把古典公民身份变成历史的陈迹,公民身份通过以民族国家公民身份取代城邦公民身份的方式而获得新生。今天,全球化所带来的沧桑巨变又一次把民族国家的公民身份逼入了死角,公民身份能否重获新生?多元公民身份体系至少提供了某种思考的路径。
[1] [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
[2] [英]戴维·米勒等:《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 郭忠华、刘训练:《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4] [英]弗·哈耶克:《自由宪章》,杨玉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5] 《不列颠百科全书》第4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
[6] [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
[7] [英]安东尼·吉登斯:“全球时代的民族国家”,载《中山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8] [英]戴维·赫尔德等:《全球化与反全球化》,陈志刚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9] [英]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周红云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0][英]尼克·史蒂文森:《文化与公民身份》,陈志杰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7年版。
[11]Hungington,S.2005.Whoarewe?London:Free Press.
[12]Horseman,M.&A.Marshall.1994.TheDisenfranchisedCitizen,AftertheNationState:Citizens,Tribalism andtheNewWorldOrder.London:Harper Collins.
[13]Beiner,R.1995.TheorizingCitizenship.Albany,N 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 rk Press.
[14][英]德里克·希特:《何谓公民身份》,郭忠华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7年版。
[15]Wenden,C.W.1999.“Post-Amsterdam Migration Policy and European Citizenship”,EuropeanJournalof MigrationandLaw1.
[16]Steenbergen,B.1994.TheConditionofCitizenship.London:Sage Publications.
(责任编辑 叶娟丽)
Construction of Multi-citizenship System under the Globalization Background
Guo Zhonghua
(Cente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275,Guangdong,China)
Citizenship is the institutional ligament and the recipro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the nation-state.In the global age,citizenship which baseson the nation state has faced various challenges. Globalization has not only weakened the institutional linkage between the citizenship and the nation-state,but also inherently set crises to individual’s self-identity mechanism.This paper advances that,in order to overcome the contemporary dilemma of the citizenship,we must set out beyond the nation-state and construct a multi-citizenship system which contains the sub-state citizenship,the state citizenship,the regional citizenship and the world citizenship.
globalization;citizenship;nation-state;multi-citizenship
D0
A
1672-7320(2010)01-0084-06
郭忠华,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教授,政治学博士;广东广州510275。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08YA-01);教育部研究项目;中山大学“211”工程三期行政改革与政府治理研究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