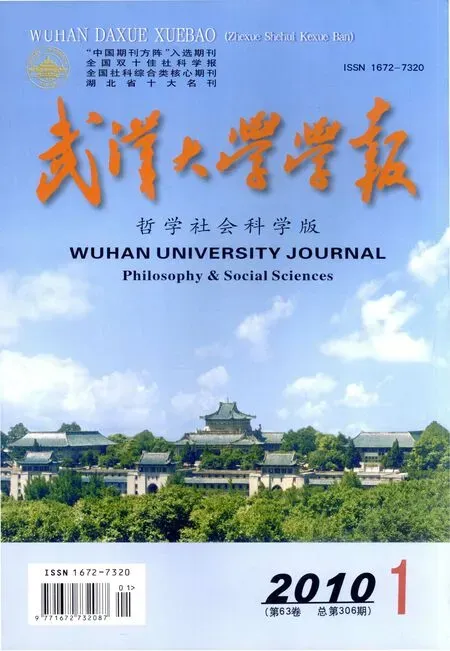古典共和主义公民身份的发轫与传承——兼对新共和主义者的一种批评
郭 台 辉
古典共和主义公民身份的发轫与传承
——兼对新共和主义者的一种批评
郭 台 辉
公民身份是古典共和主义的核心议题,对古典共和主义的不同认知成为新共和主义兴盛的推动力。绘制古典共和主义公民身份的不同发轫及其在后来选择性传承的路线图,可以廓清其内在紧张。多重传统的内在紧张使之难以适应现代社会,但选择性传承却又为其新生平铺道路。新共和主义者争夺其古典资源的原因在于,固守某种传统模式而无视其发轫的多重性和传承进程中的选择性。
古典共和主义;公民身份;新共和主义
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共和主义首先在政治思想史领域得以复兴,逐渐波及到政治哲学、历史学、法理学等领域,90年代之后成为超乎自由主义、社群主义之上的一门显学。当代共和主义理论家的代表主要有斯金纳、波考克、桑德尔、泰勒、佩迪特等。他们之所以被统称为“新共和主义者”[1](第121页),是因为或多或少都囿于古典共和主义的核心议题,包括共同体、自由、自治、公共善、公民美德、公民身份、宪政与法治等。然而,他们对共和主义传统资源的不同拣拾催生出新共和主义内部的学术之争。比如,波考克与斯金纳同是思想史“剑桥学派”的主将,但各持一端,前者以亚里士多德为源头,把公民美德、公共善与政治参与视为共和主义的构成性特征,后者把西塞罗视为发祥地,把这些特征视为实现个人消极自由的工具[2](第360-368页)。此类争论让古典共和主义的内在差异更为明朗,但我们仍需追究:争论的症结何在?争论各方的认知缺陷何在?本文从古典共和主义的公民身份为考察路线,简要绘制从斯巴达到日内瓦、从柏拉图到卢梭的路线图,试图对新共和主义阵营的内部之争提出一种批评。
一、公民身份及其发轫
古典共和主义与公民身份的关系非常紧密,以至于所探讨的议题都可以归结为公民身份的问题[3](第531页)。尽管如此泛化,但我们还是要考察西方公民身份传统的路线图,以清理古典共和主义的发轫与传承,让古典共和主义的公民身份有其确切的渊源与变迁路径。
公民身份是一个独特而复杂的主题。其独特性在于,它不像共和主义的其他议题那样有清晰的伦理价值,其本质不能用单一的道德价值和制度框架来确定,也“没有一个中心的使命和明显的职责、理论、法律契约”[4](第4页);其复杂性在于,它在历史上是一种适用于所有政治组织形式但模棱两可的制度,在利益上包括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冲突、交易、妥协以及相关资源和责任的分配资格,在价值上包括使个体变得高贵的一种身份以及与之尊严相一致的一种特权。相应,公民身份的传统“是公共的善一直
彼得·雷森伯格提出两种公民身份的划分,认为第一种公民身份的时间跨度是从柏拉图到卢梭,其特征:(1)在一个有限的、面对面的空间中实现自我统治;(2)按照对共同体的效忠程度来授予特权;(3)公民在参与军事、政治与法律制定并服从法律中实现自我价值。简言之就是“小规模的、文化上是整体的、等级体系的、有歧视的,同时也是道德的、理想的、精神的、积极的、参与的、共同体主义的,甚至是英雄主义的”[5](导论第8页)。这与古典共和主义的要求是一致的,即公民以美德和责任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以行动的能力、智慧和技艺对共同体表现出至上的忠诚,防止权力的集中专断以使个体和共同体相互受益[6](第124页)。这种古典共和主义公民身份的序幕是斯巴达、雅典和罗马共和国[7](第43页)。
在古希腊,城邦世界是由众多个性化的城邦组成,每个城邦都有支配着家庭、传统与语言的监护神,因此,城邦需要用以勘定其成员资格的某种原则与制度,个体以此获得神、军队和法律的保护,城邦得到成员的效忠。这样,公民身份很早就成为古希腊用来分配特权的手段,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只是用理性的语言提升斯巴达与雅典的不同经验。斯巴达政体把选举、职位控制和政策制定局限于少数的贵族阶层,但在辩论、协商以及确保民众同意的程序上还是涉及到所有公民,因此是最早的共和政体[8](第1页)。而捍卫共和主义的最重要角色是战士—公民,其最重要的运行机制是特定的公民身份。虽然斯巴达的公民身份被看作是“雅典公共服务观念的一种强化”[5](第8页),但留下的独特遗产有二:公民义务及其效忠共同体的荣誉都表现在战场上;勇气与卓越是人类最好的财富。斯巴达模式的奉献美德、尊重法律和服从传统经过柏拉图的阐释对后世影响深远。
虽然阐释雅典共和主义公民身份模式的代表是亚里士多德,但其历史更应该追溯到梭伦改革,经过克里斯提尼,到伯利克里时代才完成雅典公民身份制度的建构,而亚里士多德是其理想类型的理论提炼者。在梭伦之前不存在清晰的公民身份观念[9](第55页),只有当梭伦取消公民的所有债务,并重新组织公民的军备力量时,才使公民身份成为雅典政治史的重要议题。但他把进入400人团议会的成员资格、荣誉、特权与财富关联起来,把责任和公民的追求与法律制定关联起来,由此开创出公民身份的物质化和法律化传统。正如亚里士多德总结的那样,当城邦出现内部矛盾时不必诉诸于武力就可以剥夺公民身份。这使得公民身份的性质和界限首次明朗起来,更具有可操作性[10](第54页)。然而,财富的不平等分配导致派系结盟,这必然破坏物质化的公民身份及其相关法律,使雅典社会仍陷于危机中。克里斯提尼改革的目的是“混合人口以便让更大多数的人享有公民身份”[11](第5页),让要求公民身份的雅典人都服从自己制定的法律,为了维护和平,甚至让许多外国人和奴隶都享有公民身份。伯利克里进一步把公民身份视为中心议题和甄别等级的特权,以对付雅典公民的物质化和趋利化倾向。他的墓前演讲不仅让听众理性地选择公共服务,而且进一步用雄辩术把公民身份表达成一种道德的原则和公民宗教的教义,因此公民身份成为城邦的一种统治技巧。在此后的两个世纪,雅典公民意味着经济利益、法律地位和政治特权,在这个意义上,雅典公民身份变得“物质化、法律化和政治化”[9](第68页)。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把希腊城邦的公民身份制度提升为一种观念形态,而波利比乌斯与希腊斯多葛派把这种公民身份的制度与观念传播到古罗马,并且经过格拉古和盖尤斯的发展,西塞罗最终成就古典共和主义公民身份的理论体系。罗马早期制度深受希腊的影响,很早就把公民身份视为一种军事扩张的手段,把公民身份给予刚刚被征服的城镇,让许多拉丁城市拥有有限的第二公民身份,即只有法律和经济权利而没有罗马公民独占的政治权利[12](第100页)。公元前123年格拉古通过立法把公民身份授予给拉丁人甚至整个意大利人,由此,公民身份不但对罗马人来说意味着积极参与公共生活的特权,而且对罗马人控制的殖民地来说也意味着法律和经济地位的提升,可以消极地获得罗马法律和军队保护。这样,公民身份的积极与消极区分首次发挥一种公共政策的作用,确保罗马人与其他城镇的次等公民之间各得其所。因此,罗马共和国早期扩张时的公民身份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政治纽带,表现为某种合法的地位或利益,既传承古希腊的积极公民,但也发展出符合自身扩张的消极公民。
盖尤斯把格拉古对公民身份的立法实践提升到理论高度,由此被波考克称为“盖尤斯主义”。在盖尤斯看来,“公民”是指某个根据法律自由行动、自由提问和预期可获得法律保护的人,其地位是通过财产授权、占有、转让等行动来体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得出:1、罗马公民不仅生活在一个“人和行动”的世界,也生活在一个“事物”的世界,公民身份“成为一种有权占有某些事物的法律地位”[13](第43-44页);2、“公民”从政治人转向为法律人,公民之间是在法律共同体中围绕财产占有而进行交往;3、公民不仅是罗马立法者的臣民,而且也是被授予执法权力的统治者和地方官员的臣民,从而把“既统治也被统治”的公民转换成表达忠诚和服从的“臣民”;4、罗马公民既可以通过道德责任、职位担任和战争荣誉来体现其积极的公民身份,也可以没有古希腊人的道德义务、立法素质、参战能力,甚至不关心公共生活就拥有商业利益和诉讼权利。格拉古的实践与盖尤斯的法理学总结得到斯多葛主义哲学体系的形而上学论证,因为后者认为上帝规定了人的正当行为,人只是根据对正当事务的理性感知而行动[7](第45页)。
西塞罗的思想在很多方面都代表古典共和主义理论以及共和式政治家的顶峰[14](第2页)。一方面,他秉承伯利克里的修辞和雄辩,认为拥有美德和修辞技巧的政治家使公民接受共同体的福祉和善,激励城邦共同体的团结并确立其法律和身份机制,而公民通过其内在的理性和言语能力分辨公共之善,由此构建出积极的公民身份;另一方面,他推崇斯多葛学派的理性和盖尤斯的法律,强调理性是维系共同体秩序的自然法则,理性言说是用以激发人们参与政治的有效机制,从而让有能力的人们“进入到公共职务并参与引导政府行为”[15](第25页),但大多数“消极公民”依法享有各种财产权利,服兵役和纳税,并有限参与政治活动。这样就出现两种西塞罗式的共和主义公民身份,既强调公共生活的辩论与协商对构建积极公民身份的决定性作用,又张扬消极公民身份的理性能力在共和国中的意义。由此,后世的各种选择性传承为了更凸显出公民的参与、义务和战士作用而寻求雅典和斯巴达模式的支持,但也可以从西塞罗相互矛盾的思想中找到部分滋养。
二、选择性传承
随着212年罗马帝国皇帝颁布《安托尼亚那赦令》让所有自由人都成为帝国公民,加上基督教普及平等观念,公民身份在11世纪后期以前都不是一种重要的观念和制度。但在此后兴起的城市共和国以及近代掀起的反专制浪潮,公民身份再度成为政治论争的中心议题。这几个世纪的古典共和主义者各取所需地捡拾古希腊罗马的公民身份传统,从而形成各种选择性的传承。在这个过程中,马西利乌斯、尼古拉、马基雅维利、卢梭成为考察古典共和主义公民身份路线图的关键人物。
在千禧年之后,地中海沿岸的经济以意大利的城市发展为典型开始得以复苏,商人为新兴的自治城市提供了驱动力和物质基础。但自治城市的巩固需要商人像古代公民一样稳定的效忠、赋税和道德义务,同样,商人在新的经济竞争中明确其利益关系,行会的成员资格需要地方政治和法律制度的长期保护。到13世纪中期为止,公民身份已经意味着利益、保护和制约,因此成为一种有价值的特权和政治议题。但这个阶段的公民身份与古希腊罗马并无必然联系,因为他们不具备一种积极的公民伦理、公共语言和美德。只有在自治城市面临危机而需要其市民的团结奉献时,才可能发展出一种公共的价值体系和公民身份的道德基础。经过立法者、神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努力,古典共和主义的公民形象才得以集体记忆并运用,而且,罗马法的持续有效、识字率的提高和古典文化的复兴也为思考公民身份提供了条件。
在14世纪,马西利乌斯和帕瓦多的尼古拉是中世纪后期传承古典共和主义公民身份的代表人物,但各有侧重,前者主要发展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参与、修辞与辩论,后者则强调斯多葛主义的服从、法律与理性。在马西利乌斯看来,公民身份并不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一个公民“是指,在政府或协商或司法的作用下,根据其身份而参与公民共同体的人”[16](第9页)。这些公民是共同体的立法者和执行者,也是最有影响、最遵守法律的部分。不仅如此,这种共同体的构建是一个协商并一致同意的过程,是具有演说才华的积极公民通过劝说,促使大众进行社会政治合作,而人们听从这种劝说才结合成共同体。为了共同体的民众普遍认可并遵守法律,作为立法者的积极公民必须进行公共演说。不同的是,尼古拉强调共同体的理性基础,不仅运用理性使人联合和立法,而且理性能力的差异要求少数人统治多数人,“智慧者是普通法的制定者、捍卫者和执行者,其余的人自愿服从”[17](第175页)。显然,尼古拉强调法律与统治权是基于斯多葛主义自然法的理性基础。
15世纪早期,城市共和国的共和主义者与其前辈有所不同,他们在公民身份中注入公民美德和人文主义的道德情感,确立一种爱国主义的价值优先权。公民人文主义的精神是以古典伦理哲学和历史典范为道德基础,而但丁和布鲁尼是推进和捍卫这种精神的象征。在此基础上,马基雅维利对这时期的共和主义公民身份做出了合理化和修辞化的阐释。他糅合性地传承古希腊罗马的公民身份观念,使公民重现纪律、灵魂、坚韧和军事力量的古典形象。首先是追求柏拉图的战士—公民形象,认为人民是由服兵役的公民组成,他们必须掌握领导权进而展现出一种确定自身命运和力量的美德;其次是坚持亚里士多德的公民积极参与,赞同占多数的公民有着至高无上的判断,各阶层的公民参与是共和国得以强大的条件;其三,他直接重申西塞罗关于辩论与理性能力的公民美德主张。但新共和主义者们对马基雅维利的这些主张存在很大争议,主要在于,他笔下的公民美德与自由属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构成性价值(波考克)还是西塞罗主义的工具性修辞(斯金纳)。这种争论本身并未考虑马基雅维利对古典积极行动、公共荣誉、公开辩论与理性服从的选择性糅合,没重视其目的是走出当下城市共和国危机的问题。马基雅维利的公民身份理论实际上折射出内在紧张的古典传统,成为后世探讨公民身份议题不可绕过的桥梁。但不可忽视的是,即使在意大利城市共和主义的全盛时期,人们既是被动的臣民也是积极的公民,因为诸如宗教、家庭、等级和行会等制度和观念结构使之只能是消极被动的角色[5](第139页)。
如果从商人—公民的意义上来看,马基雅维利时代的公民身份关联到财产保护、利益分配和权利义务问题,勇气与荣誉这些古希腊公民美德更多是一种修辞和道德力量。虽然随着资产阶级力量的上升,公民人文主义的道德与修辞难以继续发挥作用,但公民身份成为后来反专制的一种理想追求,进而“等同于共和主义”[5](第235页)。在这个意义上,卢梭赞同马基雅维利对公民宗教、公民战士和公民教育的重视,由此敬仰他为“深刻的政治思想家”[18](第49页)。但出于对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警惕,卢梭对公民身份的古典传承不是通过李维而转向罗马,而是通过普鲁塔克而转向斯巴达,他“用其风格和道德强化把柏拉图的社会政治观念回归到欧洲政治思想的最突出位置”[5](第260页)。对卢梭来说,日内瓦才是理想的斯巴达城邦,有着小规模的共同体、组织秩序良好的人口,有着同质的宗教、政治文化和好公民的评价标准。在这种共同体中,“公意”是公民、共同体与公民身份得以实现的灵魂,因为这是个人转化成公民的最高法则,是结合成共同体的道德基础,唯此体现公民的自我立法、共同体奉献、公民身份落实以及共和政治运行;公民在自我立法中获得自由,“一方面是主权者另一方面又是臣民”[18](第66页);公民身份是公民在服从、奉献、忠诚和立法中体现的一种荣誉、情感和道德,而且是在“公意”指导下通过公民与共同体的完全融合。这就理顺共同体的大我与公民小我的关系,消除公民与城邦在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权威与服从之间的矛盾。所以,卢梭是“最纯粹的古典共和主义者”[19](第86页)。
三、一种批评
以上简要绘制了古典共和主义公民身份的多重发轫与选择性传承的路线图,据此可以归纳古典共和主义的基本共识与内在差异,指出“新共和主义者”在对待古典共和主义议题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自己的一种批评。
首先,应该从思想倾向和价值追求来划分古典/现代共和主义,不应仅仅按时间维度把古希腊罗马确定为古典共和主义范畴,把中世纪之后的思想家均归入现代共和主义范畴[20](第7-18页),更为合理的标准应该是观念形态和制度体系本身,至少要把马基雅维利、哈林顿和卢梭等人的部分观念以及佛罗伦萨的城市共和制度划入为古典范畴。尽管他们处于近代社会的语境,但所直接秉承的公民美德、战士—公民和小共同体制度仍然与古希腊罗马是一致的。确切说来,共和主义是古典还是现代的,其参考指标在于,政治共同体是小型的城邦还是大型的领土国家,公民身份是特权还是普遍平等,公民共和是通过直接参与还是代议宪政。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共和主义的开启应该归功于孟德斯鸠,他规定政府权力的分立与制衡,并通过宪政来保障公民的政治自由,从此背离古典共和主义的基本特性。
其次,古典共和主义有着明显的内在差异,而不是同质性阵营。尽管古典共和主义与现代共和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等相比较有其某些特性,但在发轫的思想家之间、甚至在思想家(西塞罗最为明显)自身的思想内部都存在紧张性关联,更不用说发轫者与传承者之间的更大差异。古典共和主义的三个传统难以化约为所谓的“雅典主义”或“罗马主义”,其原因有二:三种维系公民—城邦运转的公民身份模式各有所指,任何简化都将悬置城邦性质和公民共和的差异;即使像卢梭这么纯粹的古典共和主义者也无法完全划入到哪种模式,更不用说像马基亚维利这样的复杂人物。如果说发轫者的主张较为简单清晰的话,那么传承者却是托古言志,为解决当下问题而裁剪古典资源,即使像马基雅维利这种历史学家也是囿于克罗齐的“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窠臼。与每一个发轫者受困于特定时空的重大命题一样,每个传承者在其政治共同体前途未卜时也总是转向历史。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理解共和主义是如何从古典通向现代的,换言之就是由于思想家对古典资源的选择性传承才可能使共和主义本身适应现代大型社会的变迁。显然,新共和主义者为了分析当下更为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不得不重申共和主义从古代到近代的驳杂路线,但三种早期模式及其身后的选择性传承使当代各种共和主义理论难以自圆其说。
其三,新共和主义者固守某种古典共和主义模式,无视其内在的紧张和多元。新共和主义的当代大规模复兴始于思想史领域对近代公民人文主义的重视,他们试图以佛罗伦萨的“公民特征”来“探究近代欧洲积极价值观的起源”[21](第3页),并且驳离古典共和主义公民身份的大部分要素。马基雅维利由此被纳入新共和主义者的解释视野,并且同时成为波考克和斯金纳竞相为自身理论辩护的对象。波考克由此上溯到亚里士多德,下追到18世纪的美国和英国,强调公民的美德伦理和积极参与,“公民身份首先是一种相互平等的行为模式以及践行积极生活的模式”[22](第43页),但悲壮地认为这种共和主义在18世纪走向终结并蜕变为自由主义。同属于“历史语境主义”思想史家的斯金纳则由此上溯到西塞罗,认为古典共和主义公民身份所强调的爱国、美德和行动均为一种修辞,都是为了公民“免于依附的自由”[23](第302页),而这种自由伴随着现代共和主义一直保留至今。二人的差异应该归因于他们对当下问题关怀和价值判断的不同态度。波考克与阿伦特、桑德尔、泰勒等人一样,重新挖掘并弘扬传统的积极价值,试图立足于现代性外部来批判现代性,并为人们展望美好的未来。其逻辑必然推崇亚里士多德的公民理念,进而从一种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路线来剪辑其身后所有的古典共和主义资源。但斯金纳的初衷是直面作为现代主流话语的自由主义,利用从传统中发展出的“第三种自由”即共和主义的自由来拆解消极/积极自由的现代二分法,其结果当然走向“新罗马共和主义”。显然,他们各自的价值追求和目的使之只能固守某种古典共和主义模式,他们所修饰的古典共和主义及其公民身份模式并非完全是真实的,只能服务于他们自己的问题意识与价值理念。
实际上,古典共和主义公民身份的观念和制度体系中或多或少都包括波考克、斯金纳以及其他新共和主义者所提出的主张,但问题在于传统资源交织着矛盾、紧张和多元。其观念和制度不仅容忍森严的社会等级,更是与军国主义和英雄主义密不可分,战争进而成为公民团结与集结的原动力。同时,公民共和的精神需要其相应制度来保障和体现,反之亦然,共和宪政的制度体系需要公民共和精神来滋养,“法治需要美德来提供动力,美德需要法治和制度来保障”[24](第320页)。因此,任何单向度地扩张古典共和主义的某方面而有意忽视其他方面都只能是掩耳盗铃。在危机重重的当代社会,当我们只有通过挖掘传统资源才能寻求真善美的确定性时,理应首当其冲承认共和主义内部存在充满紧张的多重传统以及选择性传承的理论流变,然后进一步评估并扬弃其阵营内部的各种构成要素,整合其相对优势。唯此才能使这种政治文明的遗产趋于完善,并对当代面临的政治困境做出更有力的回应[25](第128页)。
[1] Weithman,Paul.2004.“Political Republicanism and Perfectionist Republicanism,”TheReviewofPolitics66(2).
[2] Burtt,Shelley.1993.“The Politics of Virtue Today:A Critique and a Proposal,”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87.
[3] [加]威尔.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刘莘译,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
[4] Isin,Engin F.&Patricia K.Wood.1999.Citizenship&Identity.London:SAGE Publications.
[5] Riesenberg,P.1992.CitizenshipintheWesternTradition.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6] Arendt,H.1965.OnRevolution.New York:The Viking Press.
[7] [英]德里克.希特:《何谓公民身份》,郭忠华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8] Jones,A.H.M.1967.Sparta.Oxfo rd:Blackwell and Mott.
[9] Manville,Brook.1990.TheOriginsofCitizenshipinAncientAthen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0] Ehrenberg,Victor.1960.TheGreekState.Oxford:Blackwell.
[11]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颜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2] Scullard,Howard H.1973.RomanPolitics,220-130 B.C.2d ed.Oxford:Clarendon Press.
[13] [英]J.G.A.波考克:《古典时期以降的公民理想》,载许纪霖:《共和、社群与公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4] Wood,Neal.1988.Cicero’sSocialandPoliticalThe ough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5] [古罗马]西塞罗:《论义务》,王焕生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6] [意]马西利乌斯:《和平的保卫者》,殷冬水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7] 任军锋:《共和主义:古典与现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8] [法]卢 梭:《社会契约论》,杨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19] [意]瑞吉·马尔科·巴萨尼:《共和学派的破产》,载应奇、刘训练:《共和的黄昏》,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20] 萧高彦:《共和主义与现代政治》,载许纪霖:《共和、社群与公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1] Hankins.2000.RenaissanceCivicHumanism.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2] [英]约翰·波考克:“德性、权利与风俗——政治思想史家的一种模式”,应奇、刘训练编:《公民共和主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
[23] Skinner.1993.“The Republican Ideal of Political Liberty,”MachiavelliandRepublicanism.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4] [澳]菲利普·佩蒂特:《共和主义》,刘训练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5] Nederman,Cary J.2000.“Rhetoric,Reason,and Republic:Republicanism——Ancient,Medieval,and Modern,”in Hankins,James(ed.).RenaissanceCivicHumanism:ReappraisalsandReflection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责任编辑 叶娟丽)
The Outsets and Successions of Citizenship in Classical Republicanism
Guo Taihui
(School of Politics&Administration,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31,Guangdong,China)
The citizenship is the key issue of Classical Republicanism,the different cognitions of which is the impetus of New Republicanism.It is useful to make clear that the citizenship of classical republicanism has various outset and selective successors,descriptions of whose lines can help us to understand their inner contradictions.Inner contradictions of the various traditions make it difficult to be suitable for the modern society,but their selective successions pave a new way to develop further.The reason of New Republicanists scrambling for the classical resources is that they defend tenaciously only one traditional model but ignore its variety of outset and selectivity in the process of successions.
classical republicanism;citizenship;new republicanism
D0
A
1672-7320(2010)01-0090-06
郭台辉,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政治学博士;广东广州510631。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08CZX035);广东省社科基金规划项目(08YA-01)都不得不与私人的善讨价还价和妥协退让的历史”[5](导论第8页)。所以,公民身份是指一套涉及到个体与共同体关系的价值体系及其制度规范,其独特性与复杂性为考察古典共和主义传统的内在紧张与选择性传承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