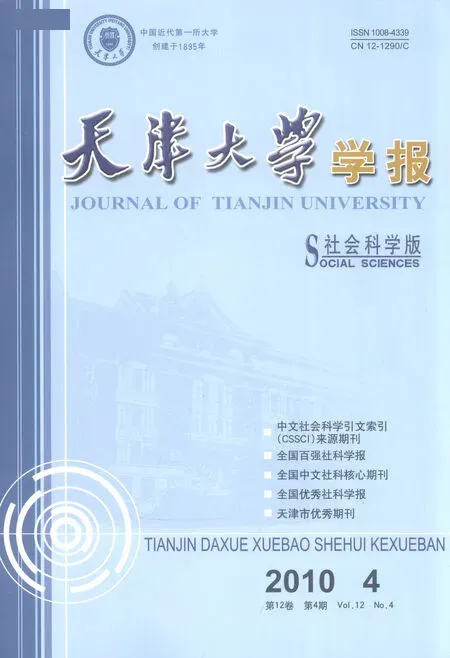戊戌变法前后的两次“文学无用论”思潮探析
张宜雷
(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天津 300191)
戊戌变法前后的两次“文学无用论”思潮探析
张宜雷
(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天津 300191)
戊戌变法前后,中国文坛上曾出现过两次“文学无用论”思潮。前者以梁启超等人为代表,后者以严复、王国维和周氏兄弟为代表。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把它们混为一谈,实际上二者的内涵并不相同。戊戌变法前的文学无用论,从实用的角度看待文学,把文学看作一种工具,认为无用即无价值,本质上是一种否定文学的理论。而戊戌变法后的文学无用论则认为文学是一种艺术,它本身就是目的。文学虽非实用却自有独立的艺术价值。因此,本质上不但不是否定文学的理论,而且是一种更深刻、更彻底的肯定文学的理论。
戊戌变法前后;文学无用论;艺术价值
二十多年前,赵慎修先生曾在一篇当时非常有影响的文章中提出:“戊戌变法前后的文学思潮特征截然相反,不可混为一谈。在这(即戊戌变法)之前,以否定文学的社会作用为主;这时(即戊戌变法失败后),则以夸大文学的社会作用为主。”[1]
对于否定文学社会作用的思潮,赵文举梁启超、严复等有关言论为例。梁启超在《万木草堂小学学约》中称:“词章不能谓之学也。……若夫骈俪之章,歌曲之作,以娱魂性,偶一为之,毋令溺志。”在《林旭传》中他劝林戒诗云:“词章乃娱魂调性之具,偶一为之可也,若以为业,则玩物丧志,与声色之累无异。”严复则认为,西方诸国之所以强盛,是因为他们“先物理而后词章,重达用而薄藻饰”,而中国之所以贫穷衰弱,则是因为“其学最尚词章”[2]。他的说法被认为“更具理论色彩”。据此,该文说,我国历史上经历的战乱不止一次,但都没有出现过否定文学的思潮。近代中国否定文学的思潮是空前的。
对于戊戌变法失败后夸大文学社会作用的思潮,赵文首举的例子是梁启超那篇人们耳熟能详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并举林纾、邱菽园等人有关言论为例。这些言论与梁启超的观点大同小异,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了。赵文对此总结道:“当时许多人都相继发表文章,煞有介事地编织关于外国以文学兴邦的神话。……在中国历史上,文学的地位从来没有像中日甲午战争前后被贬得那样低,也从来没有像1902年以后被捧得那样高。”[1]181
综上所述,戊戌前指责文学“无用”与戊戌后鼓吹文学能救国有大用的,其实是同一伙人,即以梁启超为核心的维新党人。为了叙述方便,我们把前者称为“文学无用论”,而把后者称为“文学救国论”。何以出现这种前后相反的情况呢?赵文对此的解释是:梁启超等人“由在朝的智囊团变成了流亡海外的清议派。这使他们的政治理论和策略发生了重大变化,……戊戌变法之前,维新派诸人认为中国只需要君主立宪和声光电化、农矿工商之类的货色,那么,西方仿佛也只有这些名堂。所以,当时的西学也不包括文学。现在,梁启超鼓吹‘文学新民救国论’,于是乎,文学救国也就成了欧、美诸国和日本致富致强的根本经验,文学也就成了西学的核心了。”[1]182
原因是否如此简单?如果以为只凭梁启超一张嘴就可以忽左忽右,忽是忽非,忽悠全国民众,那不但是对梁启超鼓动能力的无限夸大,而且也是对文学真正价值的亵渎和对国人智力水平的严重贬低。细绎当时文坛的思潮流变,人们就会发现,在戊戌之后,也并非只有梁启超等人鼓吹的“文学救国论”,而是还存在着另一股新的“文学无用论”思潮。也许正是这后一种思潮,值得人们特别重视。
一
当然,赵先生作为一位严谨而有造诣的学者,他分明还看到了戊戌变法之后,也仍然有“文学无用论”的存在。但他把这些都视为对“文学改革的进步潮流”的“抵制”。他提到了康有为与严复。康有为1905年访美后发表《物质救国论》,认为“美国人不尚文学,唯事工艺致富”,“盖大地之尚文学,无若中国者”,但却十分贫弱。赵文认为,康有为“把他戊戌变法以前鄙视文学的思想更加理论化、系统化了。”对于严复,赵文认为他仍坚持戊戌前的观点,并引用了严复《诗庐说》中的两段话:“诗者,两间至无用之物也,饥者得之不可以为饱,寒者得之不足以为温,国之弱者不以诗强,世之乱者不以诗治。”“故诗之失,常诬而愚”。
赵文关于康有为文学观的评论大抵不差。但是,对严复的《诗庐说》是否可以如此简单地看待呢?不错,严复在此文中的确又讲了诗歌是“无用之物”,但这与戊戌前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文学无用论”(包括严复自己的看法)是否一样呢?恐怕未必如此。因为在这篇文章中,严复又写道:
虽然无用矣,而自大地生民以来,异种殊族,繁然杂居,较其所以为群者,他事或偏有无,至于诗歌,则莫不有。……是故诗之于人,若草木之花英,若鸟兽之鸣啸,发于自然,达于至深,而莫能自己。……且吾闻之,世之有所为而后为者,其物皆奴系而不足贵也。术焉,器焉,得其所蕲,则等诸蘧庐而已。然则诗之所以独贵者,非以其无所可用也邪?无所可用者,不可使有用。用则其真甚矣。
这一段文字意在说明,诗歌虽无具体功用,而于人生不可或缺。文中关于诗“发于自然”与反对“有所为而后为”的提法,使人容易想到道家思想的影响。但严复此文的思想资源出处远不止于此。如从中得出诗因此“独贵”的结论,这就不是道家思想所能限制的了。在本文中,严复又说:诗是“又所谓美术之一也”,而“美术,意造而恒超夫事境之上”。这才是诗之价值不在具体功用而又“独贵”的关键所在。
清末民初“美术”一语,系翻译名词,相当于今之“艺术”。鲁迅对此曾解释说:“美术为词,中国古所不道。此之所用,译自英之爱忒(art or fire art)”[3],art今译即艺术。严复此文,堪称是中国近代最早明确指出诗歌属于艺术的文字。而其关于艺术价值的理解显然是出于西方现代文艺学,表现了一种现代型纯文学体系的价值观,即审美价值观。
二
如果人们继续考察戊戌后的中国文坛,就可以看到,严复这种新的“文学无用论”并非孤立的现象。几乎与他同时,在1904—1907年间,王国维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对文学是否有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而独到的思考。在《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一文中,王国维开宗明义即指出:“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当世之用者,哲学与美术而已。天下之人嚣然谓之曰‘无用’,无损于哲学、美术之价值也。”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把文学艺术的“用”与“价值”分离开来思考的人。在戊戌前的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看来,文学无用即无价值。在戊戌后的梁启超等人看来,文学因有救国之用而又有了价值。严复看到了文学“无用”而“独贵”的一面,但他并未讲清何以如此。王国维才明确指出,对文学艺术而言,“用”与“价值”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人们虽可以说文学艺术无“用”,但却无损于它的“价值”。
随后他又再三举例,说明传统文学观中的所谓文学之“用”如忠君爱国、劝善惩恶之类,并非文学价值的真谛。“‘自谓颇腾达,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非杜子美之抱负乎?‘胡不上书自荐达,坐令四海如唐虞’非韩退之之忠告乎?‘寂寞已甘千古笑,驰驱犹望两河平’非陆务观之悲愤乎?如此者,世谓之大诗人。……呜呼!美术之无独立价值也久矣!此无怪历代诗人多托于忠君爱国、劝善惩恶之意,以自解免,而纯粹美术上之著述往往受世之迫害,而无人为之昭雪也。此亦我国哲学美术不发达之一原因也。”
杜甫、韩愈、陆游的上述诗句,在我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中,向来都被认为是忠君爱国的典范而受到肯定。然而王国维却用“如此者”三字,表达了对此类诗句的不以为然,并将其作为“美术之无独立价值也久矣”的例子。既然文学的价值不在传统文学观中的忠君爱国、劝善惩恶之类具体用途,那它必定另有所在。王国维在再三宣称文学艺术“无用”之后,道出了他心中艺术(包括文学)的真正价值:夫哲学与美术之所志者,真理也。
王国维拈出真理二字,遂使一切文以载道、兴观群怨、忠爱劝惩之类的传统文学的实用型价值观,顿失光辉。他也解释了艺术之价值与具体用途不能一致的原因:“惟其为天下万世之真理,故不能尽与一时一国之利益合,且有时不能相容,此即其神圣之所存也。”[4]
王国维感叹国内学界热衷于“利用”而蔑视艺术的风气,他说道:“呜呼!我中国非美术之国也。一切学问,以利用之大宗旨贯注之。治一学,必质其有用与否;为一事,必问其有用与否。美之为物,为世人所不顾久矣。……诗词亦代有作者,而世之贱儒,辄援‘玩物丧志’之说相诋。故一切美术,皆不能达完全之域[5]。……”梁启超劝林旭戒诗就有称诗玩物丧志的话。王国维斥之为“世之贱儒”,虽不能说是专指梁启超,但应是包括梁启超在内的。
王国维也对梁启超等人大肆鼓吹的“政治小说”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又观近数年之文学界,亦不重文学自己之价值,而惟视为政治教育之手段,与哲学无异。如此者,其亵渎哲学与文学之神圣之罪固不可逭,欲求其学说之有价值,安可得也!”[6]他认为,这种把文学视为政治手段的做法,是“不重文学自己之价值”,而这种“学说”也是毫无价值的。
比严复和王国维稍晚,1907年前后,留学日本的鲁迅和周作人两兄弟也开始探索这一问题。而他们对此的思考,也是从文学“无用”的现象开始的: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一切美术之性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故其为效,益智不如史乘,诫人不如格言,致富不如工商,弋功名不如卒业之券。
这段话出于鲁迅的《摩罗诗力说》。它与严复《诗庐说》中那段议论,可说是如出一辙。然而周氏兄弟毕竟更年轻、更敏感,更多地了解和应和了20世纪初西方现代文艺学的潮流。在与严复、王国维一样描述了文学的“无用”之后,正是鲁迅最先明确地正面揭示了文学的审美价值:……特世有文章,而人乃几于具足。英人道覃有言曰:“美术文章之杰出于世者,观诵之后,似无裨于人间者,往往有之。然吾人乐于观诵,如游巨浸,前临渺茫,浮游波际,游泳既已,神质悉移。而彼之大海,实仅波起涛飞,绝无情愫,未始以一教训一格言相授,顾游者之元气体力,则为之陡增也。……文学不用之用,其在斯乎?”[7]
鲁迅指出文学是艺术的一种,它的价值不在实用方面,而在于使人“兴感怡悦”即得到审美的享受,“涵养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职与用也”。周作人也说:“文章一科,后当别为孤宗,不为它物所统”[8]。文学自有独立的审美价值,不必依赖“它物”而存在。周作人并指名批评梁启超说:“故今言小说者,莫不多列名色,强比附于正大之名,谓足以益世道人心,为治化之助。说始于《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篇。”[8]327认为梁此文是将小说引入歧途的始作俑者。对梁启超等人鼓吹的政治小说,周作人斥之为“本源未清,浊流如故。”[8]329
周氏兄弟与王国维一样,都以反复强调文学的“无用”来论述文学的审美价值,抵制把文学当作政治或经济工具而利用的倾向。鲁迅曾经坚决驳斥“笃守功利,摈斥歌诗”的行为,认为“黄金黑铁,断不足以兴国家”。周作人则指出,中国古代“文章之士,非以是为致君尧舜之方,即以为弋誉求荣之道,孜孜者惟实利之图,至不惜折其天赋之性灵以自渎樊鞅。”[8]315然而,尽管周氏兄弟否认文学的实用性,但并不像王国维那样消极地看待人生。他们认为,既然文学发自人的内心,一个民族的文学就是一个民族的“心声”,“文章之中可见国民之心意”。因此,文学是一种“不用之用”,它的功用不在具体方面,而在改造人的精神方面。“文章为国民精神之所寄,精神而盛,文章即因以发煌;精神而衰,文章亦足以补救。文章虽非实用,但却有远功。”[8]329周氏兄弟这些观点,在当时虽没有引起人们注意,但为五四新文学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可以说是五四时代“改造国民性”与“为人生的文学”的先声。
三
比较戊戌变法前梁启超等人鼓吹的“文学无用论”与戊戌变法失败后严复、王国维和周氏兄弟的“文学无用论”,可以感到二者有如下区别。
第一,戊戌前的文学无用论,从实用的角度看待文学,将文学看作一种器物,一种工具,一种为了某种目的之手段(如古人谓之载道之具,康梁等人谓之富国强兵之具)。若达不到该种用途,便弃如敝屣。而戊戌后的文学无用论,则认为文学是一种艺术,它本身就是目的。因此它既不是具有某种用途的工具,也无须成为什么东西的手段,无须乎为它物所用。
第二,戊戌前的文学无用论,把“用”与“价值”简单地等同起来,认为无用即无价值。而戊戌后的文学无用论,则认为“用”与“价值”是不同概念,文学虽无“用”却有价值,其价值并非实用,而是另有所在。
第三,戊戌前的文学无用论,从“无用”中得出否定文学的结论,本质上是一种否定文学的理论。而戊戌后的文学无用论,则认为文学虽“无用”却不可否定,文学自有独立之价值,自有存在之理由,无须以有用无用来衡量。此即严复之“独贵”、王国维之“真理”、周氏兄弟之“具足”之所在,亦即独立之艺术价值。因此其本质上不但不是否定文学的理论,而且是一种更深刻、更彻底的肯定文学的理论。
然而,戊戌前的文学无用论与戊戌后的文学无用论亦非没有相通之处。这种前后迥异而又相通的复杂情况,有时甚至反映在同一个人身上。如严复,他在戊戌前曾说文学“一言以蔽之:无用。非真无用也,凡此皆富强而后物阜民康,以为怡情遣兴之用,而非今日救弱救贫之用也。”[9]持论与梁启超颇相似。但说文学“非真无用”,在富强以后可以“怡情遣兴”,又为文学另有价值留下了后路。而到戊戌之后,严复在《诗庐说》、《法意按语》等文章中重提诗之“无用 ”,与前论似乎相通,赵文亦称其仍坚持戊戌前之观点。其实比照二者,不难发现其相异之处。一是前者云怡情遣兴当在富强之后,而后者云大地生民,异种殊族,则莫不有。此异种殊族(如非洲黑人、美洲印第安人等),未必皆富强。天下万邦万族,不富强者多而富强者少。不富强之种族是否有怡情遣兴之资格?此前者所否,而后者所是也。二是前者云无用当束之高阁,而后者云无所可用乃为独贵。“独贵”二字一出,前案尽翻。故前后之思路虽有相通,而价值取向却截然相反。可以说,严复此时的文学观已与梁启超相去甚远,而与王国维和周氏兄弟相近了。这种同一个人的文学观念在戊戌前后相通而又相悖的状况,说明了这一新旧交替的时代人们思想演化的复杂性,也增加了后人清理和判识这些思想理路的难度。
[1] 赵慎修.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思潮的变迁[J].中国社会科学,1984(1):175-191.
[2] 严 复.原强·天演之声[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27
[3] 鲁 迅.拟播布美术意见书[M]//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71.
[4] 王国维.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M]//王国维美论文选.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86.
[5] 王国维.孔子之美育主义[M]//王国维美论文选.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7.
[6] 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M]//王国维美论文选.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74.
[7] 鲁 迅.摩罗诗力说[M]//中国近代文论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783.
[8] 周作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近世论文之失[M]//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第3卷.北京:三联书店,1977:306-330.
[9] 严 复.救亡决论[M]//天演之声.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68.
“Uselessness of Literature”Before and After the 1898 Reform Movement
ZHANG Yi-lei
(Institute of Literature,Tianji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Tianjin 300191,China)
Around the period of the 1898 Reform Movement,there appeared two trends of thoughts of“uselessness of literature”in the literary world of China.The first one was represented by Liang Qichao et al.and the second by Yan Fu,Wang Guowei and Zhou Brothers.The two,long been confused with each other,two are actually different in their connotations.Being a theory of literature negation in nature,the first one,takes literature as a tool from a pragmatic perspective,and considers it useless.The second deems literature an art,taking literature itself as the purpose.Although literature is not pragmatic,it has independent artistic value.Therefore,the second is not to negate literature,but a profound and penetrating theory of literature affirmation.
around the period of the 1898 Reform Movement;uselessness of literature;artistic value
I209
A
1008-4339(2010)04-0375-04
2010-01-21.
张宜雷(1952— ),男,副研究员.
张宜雷,94963036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