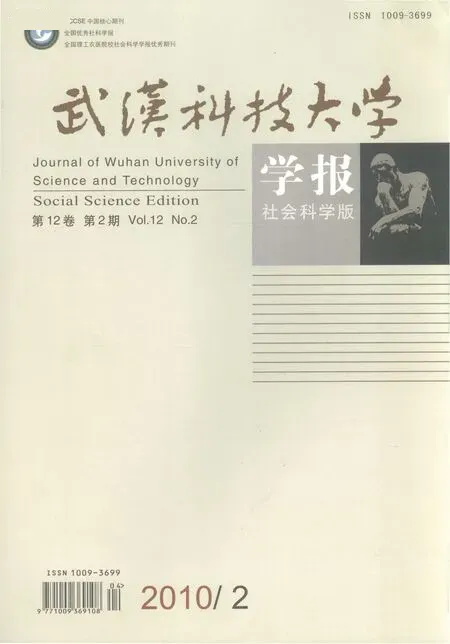马克思恩格斯视域中的世界文化交流思想
张殿军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国际政治研究所,天津300191)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随着以经济全球化为基础的文化全球化的到来,发展对外文化交流,提升国家地位和国际形象,日益成为各国开展文化外交活动的重要内容。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正确认识对外文化交流的发展过程和规律,我们有必要探讨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文化交流的思想论述,这对于增强我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和感染力,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国力”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一、世界文化交流是历史转向世界历史的逻辑必然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世界文化交流是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血”与“火”的对外殖民扩张、民族历史转化为世界历史而产生的一种必然现象。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由于受制于自然地理环境和交通条件,各民族和国家曾长期处于彼此相对隔绝和孤立的所谓“民族历史”状态。作为人类实践活动产物的文化交流也由于受地域和技术水平的限制而很难实现。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勃兴,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各民族、国家之间交往的普遍发展,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狭隘的封闭的民族和国家壁垒开始被打破,越来越多的民族和国家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卷入到普遍交往的行列中来,从而形成了一个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世界有机整体。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给以透彻的分析。针对黑格尔把世界历史看作是“绝对精神”的体现、是自由概念的发展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马克思旗帜鲜明地指出,交往之所以由地域性走向普遍性,进而“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1]773,并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1]89。马克思根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认为生产力发展的不同水平决定着交往的不同范围、形式和内容,影响着人们相互联系和依存的程度。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1]68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交往实践活动之所以发生,人类历史之所以能转变为世界历史,其真正动因来自于资本扩张的世界需求。资本是天生的自由派,无限制地攫取最大利润是资本的固有本性,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动机就是要榨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决定了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马克思指出,对于资本来说,为了能够进行剩余价值的生产,“任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2]269,它既要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产方式的状况,又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2]290。为此,“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3]33。可以说,资本主义经济就是通过“时间消灭空间”的运动方式,消灭了前资本主义时代自然形成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孤立和封闭状态,“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276。于是,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1]114。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论述,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生活由分散、孤立和封闭到彼此开放、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演进和变迁的一般规律。
人类历史由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必然导致以经济交往全球化的发展为反映基础的文化交往的世界化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和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和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和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1]72。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资本不断追逐利润的内在需要推动着世界市场的形成,与各民族间相互往来和相互依赖的增强,随之而来的便是精神交往和交流的世界性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去那种地方的与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276由此可见,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必然使世界上各个民族和国家之间经济交往和联系越来越密切,在这样的基础上,也就必然产生世界各国之间不同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联系与交往和交流。世界文化交流是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逻辑必然结果。
二、世界文化交流的作用形式
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也是世界各国文化不断走向世界并发挥各自独特影响的过程。但是由于世界历史发展不平衡规律作用的结果,因此,作为世界文化重要构成部分的各国文化对彼此的影响程度是迥异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历史现象都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说明,同样每一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也可以极其简单地由这一时期经济的生活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4]335由于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化所依靠的经济生产方式和社会经济结构不同,因而,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在世界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也就是说,文化上的先进与落后是生产力及其所决定的生产方式先进与落后的反映和表现。先进的生产力必然催生先进的文化,而先进的文化又必然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恩格斯根据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研究成果,就曾指出:“蒙昧时代是以获取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人工产品主要是用作获取天然产物的辅助工具。野蛮时代是学会畜牧和农耕的时期,是学会靠人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5]24这充分说明,经济与文化是紧密联系融合在一起的。与先进生产力发展相联系的先进文化在世界历史交往中必然会对处于经济发展落后阶段的民族文化构成冲击,从而引起落后民族文化的变迁和文明的更新,而世界经济发展是绝对不平衡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就曾根据世界生产力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将世界划分为截然相对的两部分。譬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就把世界分为“大工业发达的国家”和“非工业国家”两大部分;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又把世界分为“机器生产中心区”和为中心区发展工业服务的“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而恩格斯则把世界划分为“大工业中心”和“生产谷物和棉花的卫星”等。由于西方国家先于非西方国家进入大工业社会,因此,尽管西方列强对非西方国家和民族的侵略和扩张,完全是出于资产阶级贪婪自私的本性,但它依靠强权建立起来的文化输入和超时空的文化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为殖民地带来了先进的西方文化,推进了当地文化内涵的丰富和发展。
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在他撰写的一系列关于印度的论文中,就曾具体分析了英国殖民者对印度的侵略行径及其造成的文化后果。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马克思曾说过,由于印度的文明发展程度较高,“相继侵入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鞑靼人和莫卧儿人,不久就被印度化了。”而“不列颠人是第一批文明程度高于印度而不受印度文明影响的征服者。”马克思指出,英国对印度的殖民侵略,尽管具有反人类理性的不道德行为,但资产阶级在全世界的扩张实际上却承担着双重的历史使命:一是“破坏性使命”,即消灭旧的印度式的宗法社会;二是“建设性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1]768。在另一篇文章中,马克思还指出,西方工业文明和现代化进程向非西方社会的文化输入和渗透,使得“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东方落后国家如果不想灭亡和摆脱落后的话,就必须按照西方资本主义的样子来发展自己。马克思这样写道:“资产阶级……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1]255“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277显然,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非有些学者所说的是“欧洲中心论”的表现,而是强调的是先进国家对经济落后国家所产生的文化影响。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西方资本主义在对东方社会的侵略和破坏过程中,不自觉地扮演了推动历史发展的角色,为东方社会的文明进步指明了方向。正是这种建构于这种先进文化基础的西方文明对非西方社会文化的影响,才为东方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才使它们收到“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1]73,从而加快了东方文明的前进步伐。
先进的文明通过文化的交流能够加快落后文明的文化变迁和演进进程,这只是人类社会文化流动的一条客观规律和相互作用的主要方式之一。在人类历史上,处于后进的民族和国家也曾征服过比它先进的民族和国家,最终导致征服者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文化,为被征服者文化所同化。譬如,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日耳曼人征服了古罗马,蒙古人和满族人征服了中原和汉族,但在文明层次上前者最终却被后者所“同化”。马克思观察到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这一文化现象,深刻指出,由于文化发展与经济政治发展具有不平衡性,所以并不是所有先进的文化或文明成果都集中在一种社会形态、一个国家或民族之中。“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提琴”[6],“因为对哲学发生最大的直接影响的,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而经济的作用往往是疏远的和间接的[1]704。所以,马克思指出,伴随世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和交流,“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1]768。
三、世界文化交流的行为准则
世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总是在一定的时空中展开的。人类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过程既是各国文明不断扩大文化交往和对话的过程,也是不断发生价值冲突和文化排斥的过程。早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在描述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和演进的进程时,就曾敏锐地观察到与世界历史时代到来相始而终的是不同民族、国家经济、政治和文化观念的对撞和冲突。他这样说道:“我们赞成自由贸易,因为在实行自由贸易以后,政治经济学的全部规律及其最惊人的矛盾将在更大的范围内和在更广的区域里,在全世界的土地上发生作用;因为所有这些矛盾一旦拧在一起,互相冲突起来,就会引起一场斗争。”[5]295-296
为此,就必须建构公平和合理的为文化交往主体共同认可的全球性普遍规则来规范和调节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文化交往行为。即“努力做到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至高无上的准则”[7]607。就文化方面而言,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文化民主
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文化是生存在一定时空条件下的人们为在必然王国状态下,摆脱外在的、盲目的和异己的必然性的奴役和束缚,实现自身生存、发展和享受需要而在社会实践中创造的财富的总和。因此,作为各民族和国家与自己所生存的对象化世界的交互作用而形成的精神文化,历史虽然有长短,但没有高低、优劣之别和贵贱之分,它们都是人类社会的宝贵财富。作为世界整体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每一种文化都在世界文化体系中发挥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世界上无论民族大小、无论其社会处于何种发展阶段,都一律平等。各民族应该相互尊重各自的文化,并以平等的身份与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文化进行交流对话。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古往今来每个民族都在某些方面优越于其他民族。如果批判的预言正确无误,那末任何一个民族都永远不会优越于其他民族,因为所有的欧洲文明民族——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现在都在‘批判自己和其他民族’。”[8]因此,只有实行文化民主和文化平等,才能保证各民族和国家的文化生存和发展权利,促进世界文化的共同繁荣发展。
(二)反对文化中心主义
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各民族和国家经济、政治和文化交往的日益增加,增进了相互之间的沟通和理解,加速了世界文化的最终形成。但也不可否认,伴随不同文化交流的广泛开展,一些经济发达和科技领先的民族和国家在以其文化影响世界其他国家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滋生文化优越感和对其他民族的文化偏见和歧视,产生一种“文化中心主义”倾向,妄图用自己的文明模式和发展道路包办天下,实现世界多元文化归于一统。对于这种文化傲慢主义和中心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给予了严厉的批判。针对“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给自己脱离现实的纯思辨的学说赋予了世界历史意义,炫耀自己的学说在精神上是超越民族狭隘性的“普遍主义和世界主义”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德国中心论”是建立在“凌驾于任何民族偏见之上,……带有更多的民族局限性。他们不承认其他民族的事件是历史的。”[9]46-47把“德国中心论”推广为“普遍主义”是以狭隘的民族世界观为基础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德国人的虚假的普遍主义和世界主义是以多么狭隘的民族世界观为基础的。”德国人认为自己有着对“人的本质”王国的领导权,他们把“这个虚无缥缈的王国、‘人的本质’的王国同其他民族对立起来……他们在一切领域都把自己的幻想看成是他们对其他民族的活动所下的最后判决……这种傲慢的和无限的民族妄自尊大是同极卑贱的、商人的和小手工业者的活动相符合的。如果民族的狭隘性一般是令人厌恶的,那末在德国,这种狭隘性就更加令人作呕,因为在这里它同认为德国人超越民族狭隘性和一切现实利益之上的幻想结合在一起,反对那些公开承认自己的民族狭隘性和承认以现实利益为基础的民族”[9]555。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文化“中心主义”就是文化专制主义,它的存在不但会使本民族文化的生命力枯竭,而且也将使人类文明发展失去多姿多彩的自由选择空间,从而扼杀世界历史的可持续发展。
(三)尊重文化多样性
如上所述,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化发展繁荣的基础。因此,保护文化的多样性,是现实世界的客观要求。马克思认为,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源运动的历史必然性并不是一把打开所有民族资本主义起源道路的万能钥匙,即使极为相似的事件,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会引起不同的结果。马克思说:“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和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这些变异和程度差别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所提供的事实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10]他还曾以浪漫主义的诗句生动和形象地论述了人类精神世界的多样性:“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11]由此可见,坚持文化的多样性同反对文化中心主义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二者相辅相成,统一于世界文明发展的客观历史进程中。
当然,强调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存在,并不否认文化的统一性。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统一性存在于多样性之中,统一性和多样性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统一性以多样性为基础并通过多样性来表现,没有多样性就没有统一性,没有统一性的多样性也是不存在的。世界历史既是多样的,又是统一的,是“多样性的统一”。马克思在1857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一书中就称“多样性的统一”是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科学上正确的方法”[7]103。恩格斯在论述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关系时也指出,强调多样性“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的规律支配的”[12]。
四、文化交流的世界意义
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之一。任何民族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其他民族文化的交流,没有各种不同文化的相互交流、融合和创新,世界文明的进步和发展就无从谈起。
(一)文化交往和交流摈弃了世界历史主体生产力发展的重复性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各民族和国家进行的文化交往是促使社会生产力得以保存、传播和扩散的基本条件。世界各地的不同民族和国家在为改善自己的生存发展境遇而“战天斗地”的过程中,曾有过许许多多的发明创造。但是,这些发明创造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在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每天都在重新发明,而且每个地域都是独立进行的。”[1]107-108因此,分散的、封闭的和隔绝的文明发展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是文化上发明创造的重复性。而这些发明和创造一旦遇到一些纯粹偶然的突发性事件,例如,蛮族的入侵甚至是通常的战争,都足以使一个具有发达生产力和有高度需求的国家处于一切都必须重新开始的境地。
因此,马克思强调指出:“某一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域都必须单另进行……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1]61换言之,世界性文化交往的普遍建立,完全能够使不同民族和国家通过横向的文化交流和积累而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从而避免发明创造上的“重复”和时间、金钱的大量“浪费”,绕过一切“从头再来”的阶段,加快生产力和社会文明发展进步的步伐。
(二)经济落后国家赶上先进国家的重要途径
世界经济政治发展是不平衡的。在世界历史条件下,通过实行对外开放,积极参与世界交往实践已成为世界各国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落后国家完全可以通过借鉴和吸纳发达国家已有的先进经验和科学技术,实现后来者居上,达到跨越式发展的现代化目的。恩格斯就曾以德国为例作过这样的描述:“在1848年以前,德国实际上是没有大工业的。手工劳动占优势;蒸汽和机器很少见……,1849年以后没有到过莱茵普鲁士和威斯特法利亚的人,在1864年以后就认不出这些地方了。蒸汽和机器到处被采用。大工厂代替了大部分小作坊。轮船先是在沿海航行,后来又在横渡大西洋的通商中逐渐排挤了帆船。铁路增多了;在建筑工地、煤矿和铁矿上,到处都非常活跃。”[13]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通过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赶超世界先进国家,这并非是德国一国的成功做法,而是19世纪欧美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带有规律性的普遍现象。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文化交流思想对我们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展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仅仅指望“单独开始”和从头做起显然是徒劳无益的,社会主义的文化不可能在“空地”上进行。社会主义国家如果要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跳越性发展,就“必须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并且用它来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取得全部科学、技术知识和艺术,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14]。
(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
从发生学的意义上讲,文化是特定民族和国家在特定时空条件下,为改变生存环境,满足自身生存、发展和享受需要的过程中而创造出来的,具有鲜明的民族个性和特色。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成果,文化既是人作为主体区别于动物的自我确证的需要,同时也是人的自由发展程度的价值标识。“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与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4]456。但文化一旦创造出来便作为一种文化主体不可抗拒的因素以外在的客观力量制约着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从而使人成为特定时空的以特定文化为载体的“文化人”。人要不断突破现有文化规范和文化制度对他的控制与制约,迈向新的更高一级的自由,除了要不断地根据时代发展进行本民族的文化创新,提高主体内在的文化水平之外,还要兼收并蓄和广为吸纳其他先进文化,不断地建构有利于充分开发文化主体的潜能、有利于全面提高人的文化素质的社会交往活动。这是因为在马克思看来:“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4]89“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3]34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揭示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既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又取决于一个民族和国家与其他文明交往、交流机会的多寡和对其他文化的吸收程度。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的不断增多和彼此吸纳,不仅能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本民族和国家原有文化内涵,同时也能提升整个民族文化品格和精神境界,克服本民族和国家现存文化地域性和民族性的某些局限性,拓展个人自由与发展的空间,从而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马克思.资本论:第 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05.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216.
[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1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892.
[1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7.
[1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341.
[1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192.
[14] 列宁.列宁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