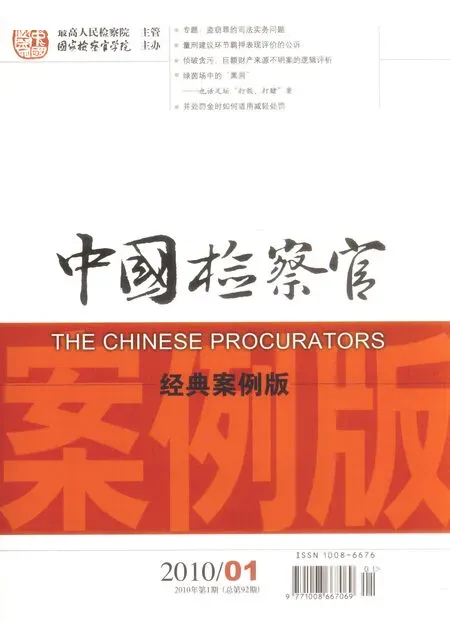盗窃被发现后公然夺物的行为定性
——兼论“平和手段”下抢夺罪与盗窃罪的界分标准
文◎胡 胜
盗窃被发现后公然夺物的行为定性
——兼论“平和手段”下抢夺罪与盗窃罪的界分标准
文◎胡 胜*
我国刑法理论的传统观点认为,盗窃是指秘密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抢夺是指乘人不备公然夺取公私财物的行为。但是,根据这两个传统定义的字面含义,基本上不可能将盗窃罪与抢夺罪的本质特征区分开来,因为“秘密窃取”本就意味着“乘人不备”,反过来说,“乘人不备”同样也具有秘密性,所以“乘人不备”并不是抢夺罪的主要客观要件。正因如此,许多教科书删除了抢夺罪定义中的“乘人不备”一词,形成了如下定义:抢夺是指公然夺取公私财物的行为。[1]
这说明,构成抢夺罪的行为包括两个方面:“夺”和“取”。这里的“夺”是从所有人、保管人身上直接抢,或当着所有人、保管人的面拿走其所有或保管的财物,“取”即为实际控制财物。[2]因此,抢夺罪并不要求行为人必须从被害人的手中,或包中,或车中夺得财物,只要是在被害人“不及抗拒”或者行为人致使被害人处于“不及抗拒”的状态后,行为人利用这一状态实施“强力”或者“平和”的手段公然取得被害人的财物,均可构成抢夺罪。
2009年1月26日晚,犯罪嫌疑人金某某窜至椒江区东升街264号手机号码超市,当时店内无人。金某某见玻璃柜台里面放着一个铁皮箱而柜门未锁,即伸手入内将铁皮箱提出欲盗取钱财,因箱内硬币发出声响被店主田某发觉,田某一边喊着“抓贼”一边从二楼赶下。见此,金某某将铁皮箱往身上一抱就往外跑,田某随后追出,边追边喊“抢钱、抢钱”。金某某逃跑至100米外的江城北路幸福超市附近时,将所抱铁皮箱扔下后再跑,后在幸福超市对面被田某及群众抓住。经清点,被盗铁皮箱内有人民币1369.2元和123张手机号码卡(经鉴定价值9050元人民币)。
本案中金某某的行为构成抢夺罪,因为金某某在其盗窃行为已被当场发现的情况下,不顾店主田某的喝止和追赶,公然抱着钱箱跑离被害人的控制范围,其行为性质已由秘密窃取转变为公然夺取而涉嫌抢夺罪。虽然金某某在行窃被发现后抱箱逃离是其盗窃行为的自然延续,但该一公然夺物的行为同时已符合抢夺罪的构成要件,而抢夺罪的罪质较之盗窃罪为重,且本案的涉案金额达10000元以上,按照浙江省的规定,抢夺罪的法定刑高于盗窃罪,对金某某的行为便应以抢夺罪而非盗窃罪论处。
一、“平和手段”下盗窃与抢夺的界分
一般来说,盗窃与抢夺之间的区分并不困难,但司法实践中又总是存在一些界限模糊的行为,即传统抢夺罪与盗窃罪的“中间地带”,如行为人当着财物所有人或管理人的面,以平和的手段拿走财物,本案情形即一著例。
很显然,此种情形既不属于通说的盗窃,因为其取财行为相对于财物所有人或管理人而言并不是“秘密”而是“公然”进行的,也不属于通说的抢夺,因为它没有强夺行为,而只是采用平和的手段“拿走”。但对该类行为显然又不宜以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为由宣告无罪。因为既然非法秘密窃取他人财物的行为也成立盗窃罪,举轻以明重,则非法公然“拿走”他人财物的行为就不可能为无罪。所以,现在的问题是,是维持“只要不是秘密窃取的,就认定为抢夺罪”的通说,还是倒过来,“只要不构成抢夺罪的,就认定为盗窃罪”?
笔者认为,将盗窃限定于秘密窃取,本就是一种相当自然的文理解释,更何况司法解释已对此作了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法释[1998]4号《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根据《刑法》第264条的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公私财物的行为,构成盗窃罪。”司法实践自然不能突破这一限制,而只能将传统的“抢夺”含义扩大解释为包含不使用强力而以平和手段拿走财物的行为。对此,有学者认为“所谓夺取,即丧失他人之所持有,而移入自己所持有是也”[3],而不以夺取方式上采用“强力”为限。也就是说,盗窃与抢夺的区别不在于取得财物的行为是否具有强力性而在于其是秘密还是公然的实施。
在行为人使用“强力手段”夺取财物时,被害人自然能够即刻认识到行为人的行为性质,因此该种抢夺行为无疑具备“公然”的特征。那么,在行为人使用“平和手段”抢夺财物时又该如何判断其究竟是公然夺取还是秘密窃取呢?一般情况下,应根据行为人主观上对自己取得财物行为方式的认识加以判断。
当然,对行为人主观认识的确定不能仅凭一面之词而应根据其作案手段、行为方式、周围环境等客观情形进行判断,采取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方法。如果犯罪嫌疑人根据其实施行为时的客观环境,主观上确信他的行为是秘密而不被他人察觉的,即使事实上已有人观察到整个偷盗过程,这种行为也构成盗窃。反之,如果行为人发现第三人已知悉其窃取他人财物的行为而不顾,明目张胆地公开将犯罪进行到底并企图携带所盗财物逃跑的,则应该承担公开夺取他人财物,即抢夺罪的刑事责任。
二、盗窃被发现后公然夺物的行为定性
本案中金某某的盗窃(未遂)行为与其随后实施的公然取物逃离行为还存在一种吸收关系,因为它们是为了同一目的在同一时间段内针对同一对象先后实施的两个行为,后一拿走财物的行为正是前一盗窃行为发展的当然结果。按照我国刑法理论,对此便应依照“重行为吸收轻行为”的吸收犯处断原则择一重罪处罚,即以罪质重、危害大、法定刑高的犯罪行为,吸收罪质轻、危害小、法定刑轻的犯罪行为。[4]
秘密窃取与公然夺取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侵财行为,其社会危害程度自然也有差异,一般说来,后者重于前者[5]。如根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浙江省公安厅联合发布的关于盗窃罪、抢夺罪犯罪数额标准的规定,抢夺罪的构罪量刑标准中数额较大、巨大、特别巨大的起点分别是一千元、一万元和八万元,而相应的盗窃罪数额标准则分别为二千元、二万元和十万元。由此可见,在实务操作中也已确认抢夺罪的罪质重于盗窃罪。
当然,在一般情况下,行为人实施盗窃后必然伴随有携物逃离的行为,该一行为是之前盗窃行为的自然延续,如果前后二个行为在刑法上的评价(法定刑)并无明显差别,则将后一行为视作被前一盗窃行为吸收而不再单独评价亦无不可。但是,如果后一行为的刑法评价明显重于盗窃则不能再以盗窃论处,否则便有轻纵犯罪之嫌。
笔者认为,在“盗窃被发现后公然夺物”的行为具备以下情形之一时必须以抢夺罪论处 (均以浙江省关于抢夺罪、盗窃罪的定罪量刑数额标准为基础):(1)盗窃数额在一千元以上不满二千元的,即数额已达抢夺罪而未达盗窃罪的构罪起点要求。(2)盗窃数额较大即在二千元以上不满二万元而犯罪未遂的。(3)盗窃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二万元,即达到抢夺罪数额巨大的标准而未到盗窃罪相应标准,并且犯罪已达既遂的。
在前述第(1)、(2)两种情形下,依照刑法规定该行为不构成盗窃罪,而只涉嫌抢夺罪,当然只能以抢夺罪论处。而在第(3)种情形中,依盗窃罪其法定刑最高为三年有期徒刑,而定抢夺罪则法定刑便升格至三至十年有期徒刑,自应以重行为抢夺罪吸收轻行为盗窃罪。本案即一适例:金某某窃取的财物合计价值10419.2元人民币,并已达到既遂的犯罪形态,故对该行为必须以抢夺罪论处,如此才能罚当其罪。当然,如果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发生变化则应作相应的调整。
注释:
[1]参见张明楷:《盗窃与抢夺的界限》,载《法学家》2006年第2期。
[2]参见肖中华、闵凯:《论抢夺罪认定中的四个争议疑难问题》,载《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3]郑爰诹:《中华民国刑法集解》,朱鸿达修正,世界书局1929年版,第394页。转引自张明楷:《盗窃与抢夺的界限》,载《法学家》2006年第2期。
[4]参见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 2003年第2版,第372页。
[5]参见刘树德:《析抢夺、抢劫及盗窃之界分》,载《法律适用》2004年第7期。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检察院[318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