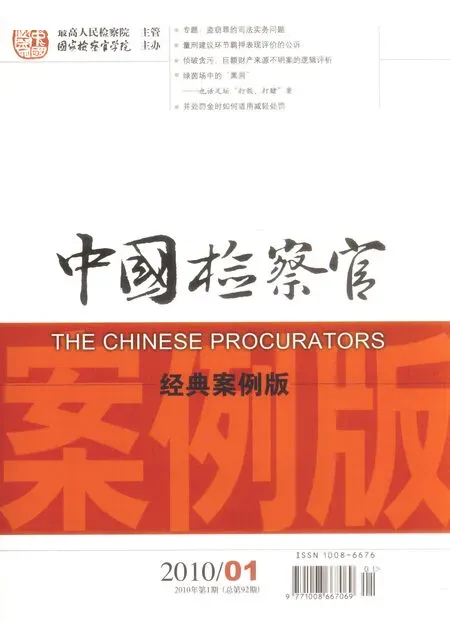盗窃罪与职务侵占罪辨析
文◎黄晓平
盗窃罪与职务侵占罪辨析
文◎黄晓平*
我国《刑法》第271条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以职务侵占罪定罪处罚。但实务中部分案件由于主体、行为方式与条件等方面因素,导致在职务侵占罪与盗窃罪之间的定性模糊。
一、两罪辨析的理论考察
首先,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窃取他人占有的财物。它以夺取占有为基本特征,行为对象必须是他人占有的财物,实质表现为侵害他人对财物的占有。而侵占犯罪是以事前占有他人财物为前提,将占有转变为非法所有。“在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之前即已经持有他人的财物,是世界各国和地区包括我国的刑法理论公认的侵占犯罪的定型性。……对于职务侵占来说,即使是采用秘密的‘窃取’手段、隐瞒事实真相或虚构事实的‘骗取’手段,也都是将原为自己持有的本单位财物转变为自己非法占有,因而都属于侵占行为的范畴。”[1]这里有必要明确占有的含义,因为占有的归属,是区分盗窃罪与职务侵占罪的重要因素。刑法上的占有是人对财物事实上支配、管理的状态,它必须是事实的、现实的占有,但并不以实际上掌握财物为必要。“占有是指事实上的支配,不仅包括物理支配范围内的支配,而且包括社会观念上可以推知财物的支配人的状态。”[2]它不仅必须从“物理的角度加以考虑”(包括财物的种类、形状、所处位置、控制的物理手段等),也要从 “规范的角度即社会生活的一般常识和规则的角度加以考虑”(如几个接触财物者之间的关系等)。[3]所以,判断某人对财物是否事实上占有,应当根据社会上一般人的观念并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而定。
其次,从职务侵占罪的立法沿革与立法原意分析。1979年《刑法》没有规定职务侵占罪,只有贪污罪的规定。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行的《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犯罪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第10条规定,“公司董事、监事或者职工利用职务或者工作上的便利,侵占本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定为侵占罪。这里的“职工”是指除董事、监事之外的公司经理及其他行政管理人员、业务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可见人员范围不以从事“组织、监督、管理性职务”为限,而是以“有业务或工作上便利”为已足。现行刑法吸收了《决定》的有关内容,将罪名由侵占罪改为“职务侵占罪”,主体范围也有所扩大。将本罪的主体从公司、企业人员扩大到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包括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中并未从事公务的非国家工作人员,也可以成为职务侵占罪的行为主体。根据《刑法》第271条第1款规定,职务侵占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但根据该条第2款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有前款行为的”,依照第382条、第383条规定的贪污罪定罪处罚。
立法演进背后所体现的意图,是把职务侵占罪从贪污罪中独立出来,对于公司、企业、单位人员虽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但利用职务便利的贪污行为施以惩戒。贪污罪的客观行为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刑法上对职务侵占罪行为方式未作限制,而根据《刑法》第271条第2款,国家工作人员“有前款行为的”,以贪污罪论,表明职务侵占罪中将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的行为包括侵吞、窃取、骗取等行为,司法实践对此也持相同认识。因此,可以说职务侵占罪规定的行为是非国家工作人员贪污单位财物的行为。职务侵占罪主体的本质特征应理解为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中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从事职务的人。这里的“职务”,从合目的性的角度作广义的理解,不仅包括公司、企业或单位人员所从事的管理、监督、经营等公务活动(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除外),还包括从事一般工作、劳务的,如普通职工、业务员等。此外,职务侵占罪既然惩治的是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行为,与贪污罪类似,犯罪行为所侵害的不仅是单位财物所有权,还包括正常廉洁的职务活动,特别是对单位财物的正常职务关系。实质的犯罪论认为,犯罪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判断,是从实质上判断是否存在达到值得科处刑罚的法益侵害,而不能以形式要件的相符为充分。因此,只要基于合法根据或者授权等,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人员事实上从事了特定的工作、业务等,不论其劳动关系的形式如何,都与单位建立了实质的职务关系。其利用该种便利非法占有单位财物的行为,都应以职务侵占罪论处。
二、实务问题的研判
职务侵占罪与盗窃罪在非法占有单位财物的具体方式上可能存在相同之处,即都为秘密窃取,那么二者的区分关键就成为判断行为人是否有 “利用职务便利”。实务中的疑难问题也通常表现于此。行为人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窃取本单位财物,应当定性为“职务侵占罪”还是“盗窃罪”?例如,公司聘用的业务员在收取货款的过程中,找借口支开同事而取得公司的货款;超市的保安利用值班之机,秘密运出并贩卖超市的财物;公交车的司机,秘密打开已经加锁封闭的无人售票之投币箱,获取营运款,等等。
上述实务问题研判的要点在于,行为人实施的秘密窃取行为,是否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这具体指向行为人与被非法占有财物的关系。一般观点认为,所谓“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行为人利用自己在单位所具有的一定职务,并因这种职务产生的方便条件,即管理、经手本单位财物的便利”[5],或者说是,“利用自己主管、管理、经营、经手单位财物的便利条件”[6]。笔者认为,不论是主管、管理抑或是具体的保管、持有等关系,都应从行为人工作职责的角度作实质判断,该表面上的关系是否真实、合法。由于案件情状的复杂多样,应当结合案发当时的情形,从行为人的职务身份、职责内容、财物状况、监管措施等方面,判断行为人是否基于职责范围内的权限,或者其他合法的根据,实际地支配、管理本单位的财物。
(一)从“身份”判断转变为“实际职责”的判断
行为人在实施占有行为之前,对单位财物是否负有经手、保管的职责,不能单纯地以行为人的职务作为判断依据。行为人实际合法地持有、管理财物,并不限于在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中担任一定的领导或管理职务(如董事、监事、经理、会计等),也并不以单位正式人员、合同工或者临时工来区分,而应当视行为人对财物的事实支配状态,以及与其职务的关联。事实上,这种实际职责的赋予可能存在三种途径:一是在本单位担任一定职务,利用主管、管理、经营、经手财物的权力及方便条件;二是在单位中从事劳务活动而合法保管、持有本单位的财产;三是受单位临时性委派或授权而合法持有、保管、使用本单位财产。以下通过数则案例予以具体说明。
[例一] 2001年11月,周建、张荣光应聘于厦门顺通达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担任集装箱货柜司机。2002年1月至6月,周建、张荣光在分别代表顺通达公司承运外单位货物到厦门海天码头的路程中,多次采用事先改制集装箱商业封志,待货物装箱后再予以拆封的方法,窃取货柜中的部分货物并贩卖。[7]
从实质论的角度出发,需以“实际职责”为基准,判断行为人是否享有和利用了实际职责所形成的便利条件。从身份来看,司机只负责实施运输,对运输公司的财物没有管理和经手职责。但运输途中,承运货物已处于司机的实际占有和支配范围内,而且从一般社会观念也可推知,司机对货物负有保管、看护的义务。因此,运输过程中司机由于从事业务工作,实际地承担了合法持有、保管公司承运货物的职责。本案中,周建、张荣光是顺通达公司聘用的司机,代表顺通达公司经手承运外单位货物,合法持有货物并负有妥善保管的责任,其盗卖货物构成了“利用职务便利”,应以职务侵占论罪。
[例二] 被告人张伟系安徽省高炉酒厂车队驾驶员。2002年11月的一天,张伟驾车到徐州市某银行为本单位以大额面值人民币兑换小额面值人民币后,认为有机可乘,遂与个体出租车司机黄超军预谋,待其再次出车去银行兑换时共同窃取其单位现金。二人商量了作案方法,张伟为黄超军绘制路线图,并提供自己驾驶的轿车钥匙。2002年12月18日,高炉酒厂派张伟到徐州换钱,张伟电话告诉黄超军。当日,张伟与该厂押运人员一同到达徐州,将其驾驶的装有现金62.5万元人民币的轿车停放在徐州市教育学院水安公寓后离开。黄超军乘隙上前,用张伟事先给其的该车钥匙打开后备箱,盗走现金人民币62.5万元后逃离现场。[8]
本案定罪问题的焦点在于,被告人张伟在非法占有单位公款的行为实施之前,是否具有经手保管该笔公款的职责,从而得以利用职务便利进行窃取,抑或是仅仅利用了其熟悉工作环境、条件的方便条件?本案中,公诉机关和一审法院认为应定盗窃罪,理由是:被告人张伟只是单位司机,根据其工作性质,不具有对单位公款直接经手、管理的职责;案发前,尽管张伟受单位指派驾车去徐州换钱,但公款单位已另派专人随车负责押运,所以张伟的工作只是行车往返,并无保管公款的义务;本案的盗窃行为得逞,主要是利用了被告人张伟熟悉工作环境与条件(如提供轿车钥匙、路线),了解相关信息(告知出车日期等),并非利用职务便利。相反的辩解意见认为,被告人张伟对所开公车上承载之公款负有保管责任,应以职务侵占定罪。
这里仍然涉及到了“实际职责”的认定问题,这种实际存在的职责不以表面上的身份、职务范围为限制,而是需要综合案件情形研判,行为人是否在事实上已经合法地控制了该单位财物?如果存在并利用了这一事实关系,行为人将单位财物非法据为己有,不论其采取的具体手段是窃取或者其他,均构成 “利用职务便利”。与之相对,需要加以辨析的是“利用工作之便”。它一般指熟悉作案环境与条件,接近他人管理、经手的单位财物等便利,与非法占有的单位财物没有职责上的权限或直接关联。
本案中被告人张伟为被害单位在岗司机,驾车至徐州为单位兑换现金系受单位指派,具有接受单位临时性委派、承担工作任务的性质;虽然该单位为公款专门配备了随车押运人员,但从现实状况看,公款始终置于张伟所驾车辆的后备箱中,并且由其实际掌握钥匙,押运人员对公款的存取、看护都须由张伟使用钥匙才能完成,因此张伟与押运人员对随车公款事实上形成了共同保管的状态。并且该事实状态系因为其接受单位委派、履行岗位职责而形成,二者存在直接关联。因此,本案中被告人张伟勾结单位以外人员盗窃本单位公款,是利用了其实际控制并经手保管涉案公款的职务便利,应当以职务侵占罪定罪处罚。
(二)从对涉案财物的处分权限进行考察
如果侵犯之财物系属于本人经管,则行为人利用此种便利秘密窃取,一般表现为“监守自盗”,无需克服他人控制、支配的障碍就可实现秘密转移占有的犯罪目的。反之,如果被侵犯财物不属于行为人经管,即其没有合法权限持有、管理该财物(即使实际由其控制占有,但由于缺乏合法依据而不存在职务关联,故不牵涉职务侵占),那么行为人想要实现非法占有的意图,必须采取不为财物的所有者、保管者或者经手者发觉的、秘密的方法,暗中窃取财物。换言之,此种情形中,盗窃是犯罪得逞的主要方式,使单位财物脱离了有权经管人员的占有或者控制。行为人对于被非法占有的单位财物是否有权处分、支配,可以从单位管理制度、监管措施等方面判断,如果不存在类似的具体依据,也可以由一般社会观念推知。例如,商店的店主与店员共同管理商店的货物,店员窃取商店内的商品应成立盗窃罪还是职务侵占罪?在这种情况下,一般认为占有应当属于上位者(店主),下位者(店员)即使事实上握有财物,也只不过是一种“辅助占有”,无权对财物进行处分。如果店员基于非法目的将财物据为已有,成立盗窃罪。[9]但这也不能一概而论,假设上位者与下位者之间具有高度的信赖关系,按照常理可认为下位者被授予了一定处分权时,那么其非法占有财物,则构成职务侵占罪。又比如,某公司雇佣搬运工甲、乙二人,从货车上卸载货物,期间没有委派人员监督,甲趁无人注意窃取车内小件货品。那么该期间货物实际由甲、乙共同保管,二人合法占有了涉案货物,应属于职务侵占行为。
[例三] 被告人吴某在中国建设银行南通分行(以下简称南通建行)营业部担任押运员,主要工作职责是负责该营业部所属运钞车的安全保卫。2001年6月14日上午7时许,被告人吴某在南通建行城中分行地下金库负责提款警戒过程中,发现解款员将一现金包(内装30万元人民币)掉落在运钞车右车门下方,遂将该现金包捡起放于其通常乘坐的座位旁,后又藏至运钞车后座底下。当日上午9时,吴某又伺机进入运钞车,用雨披裹住现金包离开单位。[10]
首先从管理制度来看,本案中被告人吴某系银行押运员,其工作职责只是担任运钞车警戒,防范盗抢等事故,根据《中国建设银行押运员守则》、《建行安全保卫岗位操作规程(试行)》等规章制度,押运员“在押运工作中不准许参与清点、登记、搬运押运物品”,因此对解款员搬运中掉落在金库内的财物没有经手、保管职责。其次,从当时的环境、监管措施分析,也可以认定掉落的现金包仍属银行所有和实际控制。现金包掉落在金库库区,进出库区有严格的登记批准制度,库区内有闭路录像监控设备,因此属于金融机构特别监管场所,该区域内的财物均由银行实际控制。故此,吴某对于所窃财物不具有任何占有、管理、处分的合法权限,其将金库内现金包移到运钞车,后采取秘密藏匿、掩盖的方法将财物转移,使银行失去对该财物的控制,符合秘密窃取公共财物的行为特征,构成盗窃罪。
(三)从被侵犯财物的状况进行检查
被侵犯的财物本身状况,也是判断行为人与财物之间关系的一项重要依据。这主要是,对单位财物的封口、加锁等,直接影响关于该财物占有归属的认定。行为人基于职务占有某种封缄的包装物时,是否同时占有了其中的内容物?对此,刑法学界有区别说、非区别说、修正区别说等。区别说认为,封缄物整体由受托人占有,但内容物为委托人占有;非区别说则认为,封缄物整体与其中的内容物没有区别,性质相同,故均由受托人或者委托人占有;修正区别说认为,封缄物整体由受托人占有,但内容物由受托人与委托人共同占有。[11]
笔者赞同区别说观点。首先,采取封缄、加锁、加密等措施,显然意在保护委托人对于其中物品的支配,非经委托人及其授权人同意,他人(包括受托人)不得处分该财物。对经封缄的财物,委托人仍认为由本人持有,并无放弃、转让支配的意思。其次,封缄物整体与内容物存在明显的区别,受托人在保管过程中,实际管理和占有该封缄物;但没有委托人的授权、同意,提供钥匙、密码等,受托人不能开封开启取出内容物,因此,内容物不处于受托人的物理支配范围。受托人不法取得封缄物,不能认为已经占有其中的内容物,仅构成对包装物整体的侵占,只有进一步开锁开封将内容物非法据为己有,才侵害委托人的占有权益,因而构成盗窃罪。
[例四] 货主A饲料公司,委托B物流公司从舟山海域的海轮上载进口大豆,运输到南京等地。B物流公司与C航运公司签订《航次租船合同》,再由挂靠在C航运公司的 “浙椒机878号”等多条船进行减载运输,采用大豆入舱不计重,由货主封舱,船方原船原交的方式为货主运载大豆。途中,“浙椒机878号”船主张某等采用不破坏封舱条,解开第一和第二舱盖连接卸扣及前后小舱盖螺丝的方法,入舱偷得大豆1200袋约50吨,价值人民币15万余元,变卖后得赃款人民币11万余元,后案发。
本案中,“浙椒机878号”船的船主张某挂靠于C航运公司,对外以C航运公司名义,负责完成该公司承接的货运业务,因此张某等人应视为C航运公司的职员,代表公司对所承运的货物负有保管责任。基于这种职务行为,张某等人在途中秘密窃取大豆据为已有,似乎当然地是“利用职务便利”,从而构成职务侵占。但本案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货物承运是采取“入舱不计重、由货主封舱、船方原船原交”的方式,即货舱封缄,只有货主同意后才能开封,承运人无权进入舱内、处分货物。据此推知,承运人仅对经封缄之货舱整体具有经手、保管职责,舱内货物实际仍然由货主占有和支配,承运人不能持有和控制。张某等人采用不破坏封舱条,解开第一和第二舱盖连接卸扣及前后小舱盖螺丝的方法,秘密进入货舱窃取货物,使得被盗货物在不被(货主)发觉的情况下被转移占有。这里的窃取行为,显然与张某等人的职责范围无关,而是利用熟悉船身情况与作案条件、运输途中无人监管便于行动等条件实施盗窃,直接侵害货主对于舱内货物的占有,所以应以盗窃罪论处。
注释:
[1]冯兆蕙:《职务侵占罪司法认定问题探究》,载《河北法学》2008年第9期。
[2]张明楷:《刑法学》(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724页。
[3]参见黎宏:《论财产犯中的占有》,载《中国法学》2009年第1期。
[4]同[2],第747页。
[5]周道鸾、张军主编:《刑法罪名精释》(第三版),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526页。
[6]同[4]。
[7]参见《人民法院报》2003年12月15日。
[8]参见《人民法院报》2005年3月28日。
[9]参见陈凌:《受托人盗窃集装箱内货物该如何定性》,载《中国检察官》2006年第3期。
[10]参见《人民法院报》2003年1月27日。
[11]同[2],第726页。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研究室干部,法学硕士[1000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