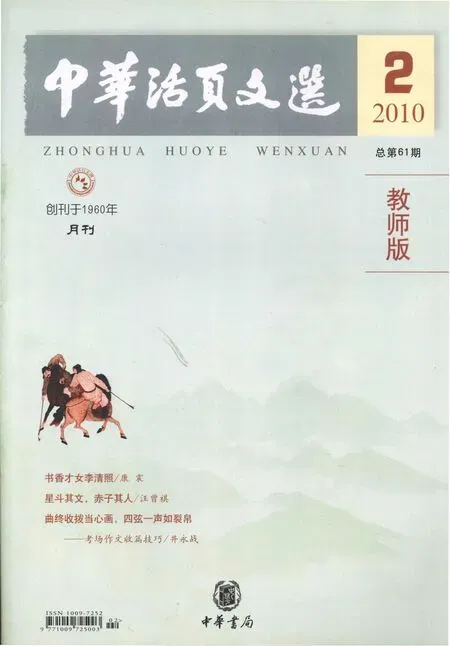暗香浮动文深沉——从《藤野先生》几处闲笔看鲁迅先生的爱国深情
■ 徐 霞(山东省邹平县黛溪中学)
再读鲁迅先生的《藤野先生》,就像毕淑敏笔下的《常读常新的人鱼公主》一样,这次才真正走近了鲁迅先生,不是为他笔下的与藤野先生深情的师生情结,而是为潜行在文章始末的深沉的爱国咏叹调。
1.情缘何时:“东京也无非是这样。”
鲁迅在《藤野先生》的前一篇《琐记》中写到当时的境遇:“爬上天空二十丈和钻下地面二十丈,结果还是一无所能,学问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了。所余的还只有一条路:到外国去。”
1902年4月鲁迅先生抱着求学救国的希望到日本学医。这一年,血气方刚、踌躇满志的他,积极参加反清爱国活动。所谓“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而唯有“诗歌,可以言志也”,于是他提笔写下了他创作中的第一首诗《自题小像》,发出了“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爱国誓言。正因为内心涌动着如此难以抑制的爱国激情,寻求救国道路的他初到东京,就发出了沉重失意的感慨:“东京也无非是这样。”好一个“无非”,无非即与国内无样,一个不起眼的副词直言不讳地道出了一个爱国志士满腔爱国热忱所遭受的回击:一群只望镀金以求得一官半职的“大清”牌纨袴子弟,不学无术,浑噩度日。糜烂庸俗的丑恶行径,正如南京那般乌烟瘴气。这犹如倾盆冷雨浇了个全透,厌恶、失望、痛苦、忿怼诸多复杂心绪郁结心胸,全凝聚在提笔之际看似闲置却有着千钧感慨与讽刺的开篇之言中。受内心爱国情怀的驱使,鲁迅不甘地自问:“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这既是对令人生厌的东京的决绝,也是自己希望学到本领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的迫切,所以他说“待到东京的预备学校毕业,我已经决意要学医了”。
2.情关何处:“日暮里,不知怎的,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
去仙台的途中,鲁迅仍然对“日暮里”、朱舜水客死的“水户”记忆犹新。原因何在?细思量,情有三分:(1)睹名触情,“日暮乡关何处是”,求学游子惯有的去国怀乡情思使之然;(2)难以割舍的爱国情感所系,更何况祖国正风雨如磐、令人担忧;(3)“日暮里”,如此惹眼的一个驿站名,又怎能不引起一个有着传统古典诗人情怀的爱国志士的共鸣呢?如此这般怎能不让人印象深刻?这里的情缘剪不断,理还乱,故鲁迅只好借“日暮里,不知怎的,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只因这份忧国之思难以排遣,一直延续到提笔写下这篇文章之时(即1926年)。至于“其次却只记得水户了”,很明确,“这是明的遗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是打上烙印的能见到老乡的地方。而朱先生更是鲁迅颇敬仰的一个人:“不为清政府效劳,去日本讲学,常面向故乡泣血,背朝北方切齿。1665年,被水户藩主德川光国聘为宾师,迎至水户讲学,德川光国欲为建新居,以‘耻逆虏之末灭,痛祭祀之有阙,若丰屋而安居,非我志’四次力辞。”为图复明,百折不挠,“自誓非中国恢复不归、以致老死异国”,在我们今天看来,为反清复明而奔走确实不值,可他的忠君爱国思想和高尚严峻的人格确实是与日月同辉的,这般民族气节不正与鲁迅先生的“我以我血荐轩辕”志同道合吗?我想这也许正是鲁迅先生崇敬他的原因之一吧。
“日暮里、水户”,只因为情所系的两处地方,所以才在东京至仙台数百里的诸多驿站中凸显出来,深深地定格在鲁迅先生的记忆里。二十余年后写本文时仍难以忘却,仍要一吐为快。读到这里,谁又能说这几句是鲁迅先生顺手拈来的呢?
3.情为哪般:“大概是物以稀为贵罢。”
初到仙台的鲁迅先生确实受到了优待,“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出身为礼仪之邦的中国人,理应心怀感激的,因这是滴水之恩,更要有礼尚往来。然而作者身为一弱国国民,切身感受就像北京的白菜进浙江被尊为胶菜,福建野生的芦荟进北京温室一样,鲁迅先生拿它们作类比,感受到的不是真正的尊重与友好,而是“物以稀为贵”,这是一个来自异国他乡的留学生所特有的敏感,更是作者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使然,包含了一个弱国国民无处言说的酸楚。这也就更加坚定了鲁迅先生在仙台要学有所成来救治国民的爱国信念。即使生活条件再艰苦(“每天总要喝难以下咽的芋梗汤”),也丝毫动摇不了他科学救国的意志。这真是身处异国,一举一动,无不系挂着风雨飘摇中的中国,一情一感,无不闪耀着炽热的爱国主义的火花呀!再读这句“大概是物以稀为贵罢”,扪心读来,又怎能轻松得起来呢?
而在仙台所遭遇的“匿名信”事件与“看电影”事件更直接刺激了鲁迅先生做出了惊人之举——弃医从文,一切只为救治弱国及其子民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指看电影事件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呐喊》自序)
4.情归何处:“我以我血荐轩辕。”
鲁迅与藤野先生分别20年后的1926年,正值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进入高潮的时期,也是鲁迅世界观发生伟大飞跃的前夜。这年秋天在反动军阀及其御用文人的迫害下,鲁迅离开北京,来到厦门。他在一封信中曾说:“我来厦门,虽是为了暂避军阀官僚‘正人君子’们的迫害,然而小半也在休息几时,使有些准备。”所谓“休息”和“准备”,乃是回顾自己走过的革命路程,清理和解剖自己的思想,总结斗争经验,以迎接新的更大的战斗。
于是乎鲁迅先生在文章篇末写到:“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在这里作者与藤野先生的深情厚谊时时触动着他热爱祖国、勇于革命之心,于是决心以笔为刃和反动势力斗争到底。他始终如一地践行着他的情志: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自题小像》)
许寿裳在《怀旧》中写:“1903年他(鲁迅)二十三岁,在东京有一首《自题小像》赠我。”鲁迅于1931年重写时题:“二十一岁时作,五十一岁时写之。”在30年中他很少写诗,从这以后才开“诗戒”。这是他献身“救国救民”运动的宣言:尽管祖国在黑暗中,我没有理由不爱她。虽然满腔热忱不被理解,我只管奉献我青春的热血。这是《呐喊》和《彷徨》的先声,也是鲁迅毕生奋斗的旗帜,是何等坚贞、猛烈地对祖国的爱啊!30年过去了,鲁迅无愧无悔。正如他在1922年写的《彷徨·题辞》:“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虽然好像有些心情上的落寞,但他却靠着自己至死不渝的信念成为了为国家前途和光明“荷戟独彷徨”的永远的文坛斗士。
今朝读《藤野先生》中的这几处闲笔,细思量,犹如凌寒傲雪的梅香,又怎能释怀,怎能不为之动容呢?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仙台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