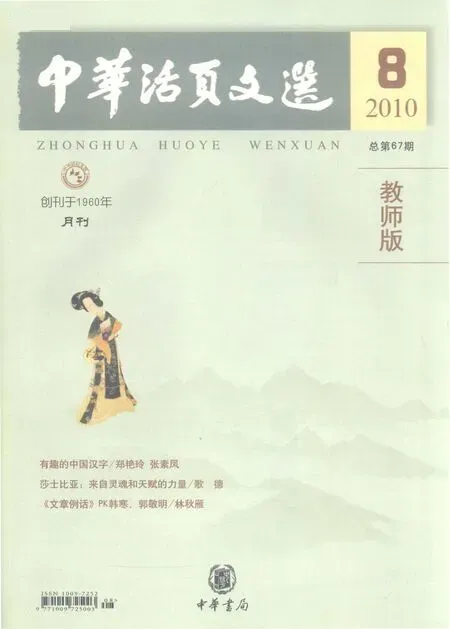论沈从文“生命情结”之形成
谢敏玉(广东省佛山市南海中学)
论沈从文“生命情结”之形成
谢敏玉(广东省佛山市南海中学)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沈从文算是一个特例。“五四”之后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和意识形态都比较注重文学作品的社会性和政治性的影响,对于“文学作品表现生命本体”这一命题,普遍采取了一种忽视乃至漠视的态度。与当时主流思潮相悖,沈从文倾心于表现湘西那种原始、自然、健康的生命形式,主张文学的根本宗旨是表现生命,企求通过文学达到对“生命的明悟”。笔者认为,沈从文“生命情结”之形成受到了湘西传统文化、民情习气以及其独特的生活经历、人生感悟等多方面的影响。
一、湘西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民情习气的濡染
沈从文出生在湘西,从小耳濡目染于当地的地域文化。沈从文的故乡及他在青少年时代游荡的沅水流域皆属楚地,地方民风中弥漫的浓厚楚巫气息对沈从文的浸淫可谓进其血液,入其骨髓。沈从文本人也从不讳言流淌在身上的“楚人血液”对他性格和作品的影响。
湘西因其闭锁的特殊地理环境得以保留了一部分原生态的楚巫文化。楚巫文化起源于原始社会,在春秋战国时发展到鼎盛,相比中原文化以及发展到后来成为正宗地位的儒家文化而言,前者更具有人情味和人性美,更有利于主体人格的个性发展。“从《楚辞》到《山海经》”,从庄周到‘宽柔以教不报无道’的‘南方之强’,意识形态各领域仍然弥漫在一片奇异想象和炽热感情的图腾——神话世界之中”。用沈从文的话来说,楚文化就是 “浪漫情绪与宗教情绪混而为一”,“是浪漫与严肃、美丽与残忍、爱与怨的交缚不可分”。楚文化中天真灵动、浪漫多彩、热烈奔放的成分和楚地人民追求自由、浪漫、多情的个性,深深影响着沈从文,他在一系列湘西题材作品里,着重表现了一种洋溢着生命力的人性内容;他从湘西下层劳动者身上发现并加以赞美的人性和生命的活力,与楚文化所张扬的那种博大、自由、浪漫、率真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楚地信鬼好祠,巫风繁盛,在不少典籍中都有详细而生动的相关记载。王逸在《楚辞章句》中云:“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歌舞可称是巫的专职,故凡恒舞酣歌者,便称巫风。”原始歌舞的普遍盛行,不仅使楚人沉浸在艺术的氛围里,而且在塑造楚民族的性格上起到了极大的作用。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说:“楚信巫鬼,重淫祀。”“淫祀”便指楚地巫傩的神灵。“与道貌岸然的‘人为宗教’完全相反,都是一些贪吃、又好色的野性神灵,没有声色鄙俚的歌舞娱神,神是不会降临的。”即便在宗教活动中,情欲也被视作再自然和再神圣不过的事情。屈原《九歌》里描写的神神相恋、人神相恋,天真活泼、烂漫多情的民风习俗,就是这种人神不分的宗教氛围的一种历史明证。沈从文《神巫之爱》里写云石镇花帕族年轻美貌的女子五十人,等候神巫在晚间到来,给全村带来神的恩惠;她们视神巫为美男子,期盼神巫的爱情。这些情节就明显带着巫风余韵的影子。
湘西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种堪称“情天恨海”的文化景观。据《中华风俗志·湖南志》载:“湘西苗族,每逢佳节良宵,有跳月之风,童男处女,纷至森林山巅,唱歌跳舞,此唱彼和,至情投意合,虽不相识,可相约订婚。”他们在爱情上表现得如此热烈奔放。又据胡朴安编《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载,“(苗人)睚眦杀人,报仇不已,故谚曰 ‘苗家仇,九世休’”, 因情生仇更是随处可见,苗风在这里又呈现出一种粗野、蛮横的特色。这种风气从远古一直流传到近代,沈从文在赞美他们自然健康的爱情观的同时,也认同了乡下人性格中的近乎原始的粗蛮雄强一面,并认为这恰恰是当地人生命力充溢的一种表现。
湘西地处中国腹地,是历来的统治者征服南方和大西南首要控制的战略要地。自秦统一中国后,各种势力长期重兵驻守湘西,对地方进行武力征服,令当地民众长期饱受战乱的袭扰。同时,湘西山高林密、滩险流急,生存条件十分恶劣,生命在这里延续要付出的艰辛是不言而喻的。面对命运和环境的险恶,湘西人无暇悲天悯人,他们把生死、苦乐看成了人生的必然,顽强地拼搏求生,少一些人生穷途的悲哀感,多一些逆境求存的生命坚韧力。另外,楚地巫鬼文化的深厚传统也使他们对世间万物往往抱着听天信命、任其自然的态度。但这种看似消极的人生态度并没有冷却他们对人生的热情,他们听凭命运的安排却又丝毫没有悲剧感。这份面对命运的坦然和从容令沈从文心折不已,在他的作品中也因而常常凸现一种在生与死的界线上从容淡定的风度。
地域上的闭塞同时也造成湘西在文化教育上的保守和落后,由于缺乏科学知识,当地人对于自然力量有着一种宿命性的依附和信赖心理。也正是在这种依附和信赖中,湘西氏族才更深刻地体会到生命受之于天地的光辉与神圣,生命自由的崇高与可贵,于是对生命滋生出一种近乎宗教膜拜的情绪。这种文化氛围很自然地对沈从文的思想产生很大的影响。他曾说:“一种由生物的美与爱,有所启示,在沉静中生长的宗教情绪,无所归纳,我因之一部分生命,竟消失在对于一切自然的皈依中。”在他看来,生命之所以是美丽的,就在于它体现了人与自然高度契合中生成的和谐。因此,沈从文对顺应本性、皈依自然的乡土生命十分倾心,在他的作品中,乡下人与自然相融,“很从容的各在那里尽其性命之理”,生命简单平凡却又庄严美丽。
沈从文是在湘西这块古老神奇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作家,深受楚巫文化的熏陶、濡染;他以湘西浪漫的人性世界、独特的民情风俗为蓝本,建造起一个淳朴、自由,充盈着雄健民族生命元气的“湘西世界”。
二、沈从文的独特生活经历和个人感悟
沈从文的先世大多不是汉人,他的祖母(沈宗嗣的母亲)是苗族。关于这位祖母,沈从文在《从文自传》中说:“祖父本无子息,祖母为住乡下的叔祖父沈洪芳娶了个苗族姑娘,生了两个儿子,把老二过房作儿子。按当地习惯,和苗族所生儿女无社会地位,不能参预文武科举,因此这个苗女人被远远嫁去,乡下虽埋了个坟,却是假的。”沈从文以为母亲也是苗人,他在1930年写的一篇小传里说过,他的外祖父和外曾祖母都是贵州的苗人。沈从文自认为来自苗家,对好勇斗狠的苗族文化一向引以为豪,对苗民备受压迫的处境深表同情。正因为在心理上对苗族的亲近,沈从文在描写湘西生活时,很少持评价者的态度,也不是以一种审判者或者启蒙者的形象出现,而是采用一种平等审视的态度,去发现乡下人生命的细微委曲之处。对乡下人处境同情的体察,对生命原初状态的尊重,使沈从文对笔下的湘西生命常带着一种悲悯感。
沈从文的生命意识,源自他童年的体验、感受与幻想,形成于他青少年时期在沅水流域的独特经历。《从文自传》记载了他青少年时代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逃学、打架、骂野语乃至赌博——野得无法收拾的顽童生涯;十四岁即厕身行伍,浪迹四地;在“清乡剿匪”中无数次地目睹杀戮;所属军队在鄂西境内一夜间全数覆灭,自己侥幸死里逃生;在芷江发生的初恋及由此派生的“女难”;在常德的“打流”,在川东龙潭与一个有着杀人放火吓人记录的山大王的交往……湘西自然山水的滋养和小镇淳朴的人情的濡染使沈从文养成了热爱自然的秉性和追求生命自由的精神理念。童年时代目睹家乡数千苗民被残酷屠杀使他的心灵发生了震动;后来他在湘西土著部队里的种种遭际,领略到的生命闪灭的倏忽、人生价值的低微都使他感到迷惘和困惑。这在主观上促成了沈从文在现实的细微寻常处发掘和确立生命中的存在,他的态度中,自然天成地拥有了一份平和冲淡的独特风格。他从寻求生命的意义的角度出发,触目皆善、皆美,即便是乡野的妓女,粗俗的水手,迟钝的小民,也因家乡边地的淳朴风俗和原始生命力而在他眼里显得浑厚可爱。
为了追求人生和生命的更大意义,沈从文离开湘西,来到了北京。城市文明的嘈杂、浮躁、隔膜、利已主义让他觉得失望和难以适应,对城市的文化的厌弃迫使他始终处于都市的边缘。初到京城时,他四处碰壁,衣食无着。但即便在这样沉重的心理压力下,他也没有退回湘西,而是拿出了湘西人的勇气与任性,发誓一定在要在城市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价值。城市对他的轻慢不止煽起他思乡的情绪,更激发了他一种向别处去寻找精神支柱的迫切愿望。唯有对家乡的记忆才能向他提供这样的精神支柱,从湘西的风土人情当中,他提取出与城市生活风尚截然不同的道德范畴——他那渲染牧歌情致的热情主要发源于在城市的受挫情绪和自卑感。在他的湘西作品中,他弘扬了保持在湘西山民身上的朴素、淳厚、粗犷的优良品质,讴歌了与现代文明相对峙的原始生命力,从正面展示了自然人性的活标本,以之来对照城市生命力的萎缩和衰竭。
沈从文在作品中常常写到死亡的不可预期,写到生命无常的感觉,这与他对死亡的切肤体会有关系。湘西的历史,旧时的环境,使他过早地认识到人生的艰辛,过早体会到命运中的随机性与偶然性。如果说目睹别人的惨事,沈从文只是一个旁观者,那么,面对亲朋挚友的死亡,他深切地感到生命无常的无奈和悲哀。他的许多少年朋友都早早去世,他本人也是多次侥幸地生存下来。1931年沈从文失去了四位至为熟悉的朋友——其中胡也频牺牲在国民党的独裁下,徐志摩在空难中丧生。沈从文沉痛地悲叹:“他们的死,虽有天灾,更多是人祸!”“(他们)一例守住各自的理想,多力,强健,勇猛精进,活得虎虎有生气,到头来生命竟结束到不易想象的情景中。”对死亡的切肤体会激发了他对生命力的无限热爱,也引发了他对生命意义和生命价值更加深入的思考。
沈从文不同于五四时期的大多数作家,后者从书本或留学深造中获得前人或同辈思想成果作为自我精神的养料,而沈从文则凭借自己的天赋和敏感,去体验、感悟人生。他独特的生活经历,以及他对现实人生的感悟等,凝结成了他在作品中对生命理想和生命意义永恒探索的 “生命情结”。
参考资料:
1.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
2.沈从文《沈从文文集》,花城出版社。
3.林河《中国巫傩史》,花城出版社。
4.凌宇《沈从文传》,十月文艺出版社。